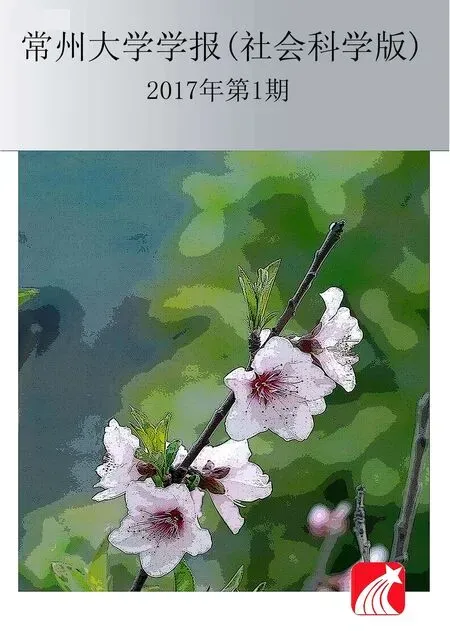晚明书画艺术的情感本性观念考论
——以徐渭和董其昌为主要考察对象
吴衍发
晚明书画艺术的情感本性观念考论
——以徐渭和董其昌为主要考察对象
吴衍发
晚明人文思潮推动了美术领域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自我意识的标榜,致使以画寄情的文人画相当繁盛,直抒性情的书法异军突起,书画理论成果显著,艺术的情感本性在晚明文人书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出现了徐渭、董其昌等一大批著名的书画家、书画家兼理论家。他们在书画艺术中强调艺术家自然性情的抒发和主体精神的彰显,突出对笔墨情趣的倡导、形式美的追求和诗书画的融合,确立了文人画的主流地位,而文人书画所特具的自娱性和抒情性特征,则进一步彰显了书画艺术的情感本性,影响了晚明以后山水画的发展与演进。
情感本性;书画艺术;徐渭;董其昌;晚明
晚明人文思潮推动了美术领域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自我意识的标榜,带来了书画艺术的繁荣。文人书画家强调自然性情的抒发和主体精神的彰显,突出对笔墨情趣的倡导、形式美的追求和诗书画的融合。董其昌“文人画”概念和“南北宗”论的明确提出,奠定了文人画的崇高地位,文人画被视为画学正脉,引导着中国山水画的时代潮流。而文人画的最本质特征即在于它的抒情言志之特质,使书画艺术的情感本性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中国画向来重视生命,视生命为画的最高纲领。而这种对生命感的追求,就是重画中生机、生趣、天趣、意趣、生意。谢肇淛说:“今人画以意趣为宗。”[1]高濂提出“天趣、人趣、物趣”三者,认定画以得“天趣”为高,并谓“求神似于形似之外,取生意于形似之中。”[2]48李日华指出:“凡状物者,得其形,不若得其势;得其势,不若得其韵;得其韵不若得其性。”[2]50唐志契也强调:“凡画山水,最要得山水性情。”[2]51凡此等等,无不充分体现出晚明文人艺术家对生命精神的追求,也与文人画在当时的发达有密切关系。文人画家游心于画,以绘画形式来显现生命情感,正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3]170
晚明思想文化领域对“复古”思潮的反拨和对传统礼教的“反叛”,表现在美术领域即为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自我意识的标榜,表现在书法领域,则是直抒性情的书法的异军突起。徐渭、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邢侗、米万钟、周天球、王世贞、陈继儒、赵宦光、倪元璐、陈继儒、崔子忠、陈洪绶等一批书画家、书画理论家涌现出来,群星丽天。笔者姑且以在书画方面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徐渭和董其昌为例,来考察他们对艺术情感本性的理解。
一、徐渭书画艺术的情感本性论
通过徐渭的诗文、题跋、书札、画作等,我们可以了解他关于书画艺术本性方面的基本观点。
徐渭曾把书法艺术列于其所好的诗文书画诸艺术之首。在书法艺术方面,他十分强调“心”的重要功能,主张“真率写情,浑然天成”。作为一代书家,徐渭长于行草,其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4]。徐渭草书中那种追求怪异的趣味和强烈的抒情性在明代独树一帜,震铄古今,开启了有明一代的写意书法。
书法艺术是线的艺术,其关键在于运笔。徐渭在论书方面十分强调运笔,他认为临摹范本“时时露己笔意者,始称高手”(《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因此,书法运笔之妙,在“心手尽之”。“运笔”不仅是手创造的,更在于“心之神明”,古人所谓“手到心到,意在笔先”,是之谓也。古人书法有自观察客观物象而得者,即通过对客观物象的观察体验而领悟到运笔之法,由此乃知“心”在运笔中的重要性。“余玩古人书旨,云有自蛇斗、若舞剑器、若担夫争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观雷大简云听江声而笔法进,然后知向所云蛇斗等,非点画字形,乃是运笔。知此则孤蓬自振,惊沙坐飞,飞鸟出林,掠蛇入草,可一以贯之而无疑矣。以此知书,心手尽之矣。”(《玄抄类摘序》)从对客观物象的体悟中领会并提高运笔方法,这样书家就可以摆脱摩仿古人笔法的窠臼,从而有更加自由灵活的发挥,其创造性和个性特征也能得到更好的体现。既然客观物象随处可见,那么书家也就随处可悟运笔之法。只要懂得这一道理,自然也就懂得运笔之妙不仅是手的技巧,更在“心手尽之”。对于心手之于书法的关系,徐渭进一步解释说:“自执笔至书功,手也;自书致至书丹法,心也;书原目也,书评口也:心为上,手次之,目口末矣。”[5]535“心为上”,不仅强调了“心”在书法艺术中的重要性,更揭示出了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
基于“心为上”这一原则,徐渭强调作书要“出乎己而不由于人”。“夫不学而天成者尚矣,其次则始于学,终于天成。天成者,非成于天也,出乎己而不由于人也。敝莫敝于不出乎己而由乎人,尤莫敝于罔乎人而诡乎己之所出,凡事莫不尔,而奚独于书乎哉?”[5]1091只有“出乎己而不由于人”,其书才会革除因因相袭之习而有所自由,有所创造,才会表现出人格个性之美。这正是徐渭强调“心”在书法艺术中之作用的美学真谛所在。
书法是净化了的线条艺术,它源于书法家的心灵感受,饱含着书法家的情趣,因而与诗画相通,与乐舞相近。它有诗的韵味、画的意境、乐的旋律和舞的节奏。徐渭很懂得这一点。他赞赏“陈道复花卉豪一世,草书飞动似之”[5]487,通过草书,像绘画一样表现所喜爱的花卉;他还赞赏“真行始于动,中以静,终以媚”,像诗赋一样,“媚亦胜也”;所谓“媚者,盖锋稍溢出,其名曰姿态。”[5]515也许正因为书法极富创造性和个性的艺术表现形式,所以徐渭才那样重视书法,把自己的书法列为其所好诸艺术之首。
绘画方面,徐渭亦同样强调性情的自然流露,率意写真。晚明时期,摹古与创新两种意识激烈碰撞,成为当时画坛的基本格局。徐渭“大涂小抹”,开创了泼墨大写意画时代,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相对于“小写意”而言,“大写意”抓住对象的基本特征和神情,对之高度概括和夸张,以极其简略而准确的笔墨传神达意,约略相当于书法中的草书;而小写意则在把握对象形体结构的前提下,笔墨的运用较之于“工笔画”概括简练,生动活泼,不拘谨,但也不狂放,约略相当于书法中的行书。因而,张岱《跋徐青藤小品画》指出,徐渭写意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态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徐渭视“逸”为妙品,而这一“逸”字则是真我、真情的自然写照,正如其题花卉诗云:“飞鸣栖息,动静如生。悦性弄情,工而入逸,斯为妙品。”[5]487他的书画也多以逸气见长。他为友人沈文泉作画,其《跋画为沈文泉》自题:“随手所至,出自家意,其韵度虽不能尽合古法,然一种山野之气不速自至。”艺术是自我真性情的表现,徐渭《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中云:“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己意者,始称高手。”[5]577徐渭强调书法艺术、绘画以及其他艺术都是一己情感的表现,唯有“寄兴”、“露己”的艺术家才称得上是高手。徐渭题《独喜蒙花到白头图》云:“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千秋。”他的画是其内心郁闷、愤懑等各种情感与情绪的表达,痛快豪放,真实泼辣,如其题《螃蟹》诗云:“稻熟江村蟹正肥,双鳌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这是对权贵的憎恨与轻蔑;又如其题《葡萄图》诗所云:“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他那不得志的心情,正于此诗中充分流露出来。
徐渭以水墨写意画见长,墨法上主张“不求形似求生韵”[5]154,逸笔草草,愤笔挥洒,从不描头画角,亦不刻画修饰,而是任由直觉,横涂竖抹,一挥而就,达到了纯任天机的自由境界,堪称墨戏之作。他在题画诗中亦常云:“老夫游戏墨淋漓”、“墨中游戏老婆禅”等。他的“不求形似求生韵”,不仅是其画风的写照,更是“以墨寄情”,与元代倪云林的“不求形似,聊寄胸中意气”实乃同一观点。徐渭在《画百花卷与史甥》诗中云:“世间无事无三昧,老来戏谑涂花卉。”“三昧”是佛教用语,强调修行时心神平静,排除杂念。在墨戏中追求三昧,就是追求生命的智慧。他晚年自号漱汉,今上海博物馆珍藏着其晚年所作的一幅《风鸢图》长卷,四米多长,带有自传性色彩,画心上题曰“漱汉墨谑”四个大字;其《七言诗·百花卷与史甥》亦题有“漱老谑墨”四字,真可谓是“沉重的墨戏”。其现存作品《牡丹蕉石图》、《石榴》、《雪蕉图》和《墨花卷》等,皆笔墨酣畅、淋漓尽致,更多的是其生命中的激情与愤激之情的表达。我们完全可以说,他的生命奔泻出淋漓而又洒泼的墨色与线条,躁动的笔墨后面游动着不羁和无奈。明代后期,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盛行于世,推动了中国美术水墨写意画的迅速发展。
二、董其昌书画艺术的情感本性论
董其昌是晚明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一代书画名家。他精于书画鉴赏,收藏丰富,于书画理论多有著述;他工于书法,尤以行楷见长,自谓于率易中得之,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他提出的“南北宗”论对晚明以后的画坛影响深远。董氏书画创作追摹古人,但又能融合变化,集大成又创新格,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其作品平淡古朴、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中平淡天真的个性。
董其昌的书论大都散见于其书画题跋,而集中反映于《容台别集》(卷二、卷三)和《书品》之中。董氏受禅宗影响极深,故而在论书时喜欢“以禅喻书”,其所阐发的许多重要的书法美学观皆来之于禅宗的启发。董氏书法初宗米芾,远师晋唐,行书温婉恬淡,草书流丽潇洒,以平淡蕴藉、富有禅味的书风自成一派,与徐渭的狂放、王铎的恣肆书风形成鲜明对照,对明末清初书风影响很大,以致被视为“自钟、王发端以来,文人流派书法发展史上追求意境最为成功的书法家”[6]2。董氏书法崇尚自然天趣,追求“直率”和“淡”的境界,提倡“熟而后生”。这些艺术观念突出表现为书法艺术乃是自然性情的抒发和主体精神的彰显,如其谓书法,“欲造极处,使精神不可磨没。所谓神品,以吾神所著故也。何独书道,凡事皆尔”[3]32。在他看来,能称为“神品”的书法作品,皆是因为主体精神得以彰显的缘故,如果个性之情和主体精神“磨没”了,也就无“神品”可言。他在论书中多处谈及“率意而书”,譬如:“古人神气淋漓翰墨间,妙处在随意所如,自成体势,故为作者”(《论用笔》);“晋、唐人结字,须一一录出,时常参取,此最关要。吾乡陆俨山先生作书,虽率意应酬,皆不苟且,常曰‘即此便是写字时须用敬也。’吾每服膺斯言。……吾乡陆宫詹,以书名家。虽率尔作应酬,字俱不苟。且曰:‘即此便是学字,何得放过”(《评书法》);“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多非作意书,第率尔酬应耳”(《评书法》);“今人朝学执笔,夕已勒石,余深鄙之。清臣以所藏余书,一一摹勒,具见结习苦心。此犹率意笔,遂为行世,予甚惧也”(《跋自书》)。董氏这种对自然性情和主体精神的强调和追求,与晚明追求个性解放的艺术思潮是一致的,与李贽的“童心”、公安派之“性灵”一脉相通。所不同的是,董氏语言和行为比较温和,没有表现为李贽和三袁那样的极端与偏激。他反对一味地模仿古人,但不否定追慕古人,学习古人,他能在传统文人书法中融合变化,优游自如,脱去前人窠臼,形成自己独特的书风。
“淡”是董其昌艺术观的一大特征,也是其诗文书画审美最核心的标准。“淡”作为一种率真超逸的意境,成为董氏一生书画追求的目标,《容台别集》中有许多关于“淡”的描述。董氏跋《黄庭经》说:“以萧散古淡为贵”;读颜帖,他说:“平淡天真,颜行第一”;临怀素《自叙》中云:“皆以平淡天真为旨,人目之为狂乃不狂也”;评杨少师他谓:“书骞翥简淡,一脱唐朝姿媚之习”;论苏东坡则云:“奇崛真率”、“意忘工拙”、“天骨俊爽”。董氏关于“淡”的本质观念和集中阐述,主要见诸以下文字:“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极才人之致,可以无所不能,而淡之玄味,必由天骨,非钻仰之力,澄练之功,所可强入。萧氏《文选》,正与淡相反者,故曰‘六朝之糜’,又曰‘八代之衰’,韩柳以前此秘未睹。苏子瞻曰:‘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为平淡,绚烂之极。’犹未得十分,谓若可学而能耳。《画史》云,若其气韵,必在生知,可为笃论矣。”(《容台别集》卷一《魏平仲字册》跋)
在董氏看来,“淡”犹如绘画中之“气韵”,“必由天骨”,“必在生知”,必从人的性情中来,“非钻仰之力,澄练之功,所可强入”,唯有经过“辞采绚烂,渐老渐熟”阶段,“乃造平淡”。董氏强调“淡乃天骨带来,非学可及”。这实则是强调“淡”与书家自身的素质禀赋及才情有关,亦即“淡”乃由人的性情和品质而带来。虽然“淡”非后天人力可强入,但还是离不开学习和模仿,这“渐老渐熟”的过程,正是后天不断学习与模仿的过程。何谓“淡”?“质任自然,是之谓淡”,淡就是一任自然,天然,就是天真,就是不用意,不露斧凿痕迹。由此可知,他所追求的“淡”的境界,正是自我人格精神的表现,是艺术家自然性情的反映。董氏正是站在自然人性论的立场上,强调情感的自然性与先天性,难怪他说“淡”是“非学可及”的了。而作为那后一阶段“渐老渐熟”阶段所造的绚烂之极的平淡,正是“熟”后其人格精神的反映。
与追求“淡”的意境相一致,董其昌提出了“熟而后生”的主张,追求生拙的意趣。他在《容台别集·画旨》(卷四)中说道:“诗文书画,少而工,老而淡,淡胜工,不工亦何能淡。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这是董其昌在创造“淡”的意境时对所需笔法技巧的强调。当然,这种率真超逸的“淡”的意境的创造,必然赖于精熟的笔法技巧。显然,“熟而后生”正是针对这种技巧而言的。董氏强调“生”即是“淡”,“熟”即是“工”,“工”乃“淡”之前提,“熟”乃“生”之前提,苏轼的“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即是最好注脚。董其昌比较自己与赵孟頫短长时即曰:“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第作意者少耳”(《容台别集·论书》卷二);“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容台别集·论书》卷二)。
董氏之书,因“生”而得“秀色”,亦因生而有“秀润”。“生”乃是董氏自我个性与情感的一种体现。在董氏看来,“熟”可得共性,然而,也正因为如此,“熟”也就容易混同于一般而泯灭个性,这便是“俗”,即所谓“因熟得俗态”。显然,董氏所谓“熟”后求“生”,实乃以“生”破“熟”,以“生”破“俗”,而求得己之个性。“生”明显寓有以无法求率意天真之意,已经超出了“淡”的意境内涵,而升华为他自己的“精神血气”了。对此,黄惇教授解释道:“我们不妨把董氏所说的‘熟’,看成是于古人书法中得到的‘他神’,而把董氏的‘生’,看成是超越古人的‘我神’,如他自己所说:‘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以离者,非欧、虞、褚、薛名家伎俩。直要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哪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容台别集》卷二)’”。[6]15董氏说的“粉碎始露全身”,这“全身”之内涵,实与徐渭所言“真我面目”以及袁氏兄弟所谓“独抒性灵”相同。董氏还说:“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当观其举止、笑语、真精神流露处。”(《评书法》)此所谓“精神流露处”又和徐渭所主张的“活精神”以及袁中郎所说的“本色独造语”如出一辙。论临古帖,董其昌以为“余书《兰亭》,皆以意背临,未尝对古刻,一似抚无弦琴者”(《容台别集》卷二),则更与徐渭论临《兰亭》当“窥其露己笔意,必高手也”的观点契合。凡此种种,多透出董其昌书论中的个性解放精神。
三、“文人画”概念和“南北宗”论的提出
就书画艺术的本性理论探讨,董其昌的突出影响是他所提出的“文人画”概念和“南北宗”论。隆万之际,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明四家”为代表的“吴派绘画”*关于“吴派绘画”,参见周积寅:《吴派绘画研究》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1。的影响逐渐淡出,而与之呼应的则是徐渭的水墨大写意画派(野逸派)、松江董其昌的“华亭派”(正统派)等文人画派日益兴盛。明末画家唐志契指出苏松品格之同异:“苏州画论理,松江画论笔。理之所在,如高下大小适宜,向背安放不失,此法家准绳也。笔之所在,如风神秀逸,韵致清婉,此士大夫气味也。”[7]古人论画有“论理”与“论笔”之分,“论理”则强调画之本法,而“论笔”则重在笔墨抒情,用董其昌的话说,就是“以蹊径之怪奇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3]217。“论理”与“论笔”之别,照今天的话讲,就是在构思和营造画面中的法理规矩与笔墨情趣两种出发点、两种表现方法的差别。也就是说,绘画强调论笔,绘画的中心不再是形象的塑造,而是笔墨的抒写,这就颠覆了“存形莫善于画”的本质。包括徐渭所讲的“不求形似求生韵”,同董其昌的观点是一致的,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到笔墨,但是反映在其创作中,也是强调以笔墨为中心,用笔墨来表现情感。笔墨之精妙高于形象,形象就要为笔墨服务,于是形象就变成了各种皴法,如披麻皴、斧劈皴、折带皴等笔墨的表现方式。形象的塑造必须深入生活,苦练造型,而笔墨的抒写不必深入生活,但要苦练书法。于是“画法全是书法”、“书法即是画法”,这就使绘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国画由画家画的“论理”向文人画的“论笔”的质变,“隆万之际”是一个关键节点。董其昌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3]151显然,董其昌以笔法作为“文人之画”法脉建立的依据,而“南北宗论”的提出,则标志着这一转折点的完成。清人梁穆敬读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将董氏所详言的书画之旨,归其要曰“用笔”、“用墨”[8]。自此以后,“以形为神之基础、以物为我之前提的需要‘积劫方成菩萨’的绘画性绘画,让位于以神置于形之上、以我居于物之先的可以‘一超直入如来地’的书法性绘画”[9]。清人方薰说:“书画一道,自董思翁开堂说法以来,海内翕然从之,沈、唐、文、祝之流遂塞,至今天无有问津者。”清人李修易也说:“我朝画学不衰,全赖董文敏把持正宗。”显然,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正统派被视为画学正脉,引导着中国画山水画的时代潮流。
究竟什么是“文人画”?陈衡恪在《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中这样界定:“‘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所谓‘文人画’。”[10]而“文人画与其他绘画流派相异的最本质特征正在于它的抒情言志特质”[11],世人对此多有论及。李公麟云:“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性情而已”[12];李俊民《锦堂赋诗序》亦云:“士大夫咏情性,写物状,不托之诗,则托之画,故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得之心,应之口,可以夺造化,寓高兴也”[13];王蒙论画强调“绘事寄情”(《跋马和之画卷》);吴镇亦指出“写竹之真,初以墨戏,然陶写性情终胜别用心也”(《梅花道人遗墨·竹谱》),徐渭亦称画当“悦性弄情”[5]572(《与两画史》);李流芳则自诩“为林木山水以自娱”(《论画》);董其昌更提倡“以画为乐,寄乐入画”,“写胸中丘壑”(《画禅室随笔》)……凡此种种皆说明文人画抒情写意之本性。
由于董其昌的主盟和“南北分宗”的提倡,文人画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并与诗文、书法进一步融合,带来了晚明文人画的发达与繁荣。而文人画所特具的自娱性和抒情性特征,使艺术的情感本性得到了进一步彰显。今之论者徐建融教授,针对隆万之际中国绘画史上的质变,提出“隆万之变”[14]这一看法,认为“隆万之变”是中国绘画艺术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徐建融教授从画家身份不同、绘画作品的变化以及绘画功能的变化等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隆万之际中国绘画风格发生的重大变化。应该说,徐建融教授关于“隆万之变”的见解有独到之处,“隆万之变”也确实反映了此时期艺术现象或艺术事实的根本性变化,但这种变化还没能发展为影响绘画史的根本变革,并由此而成为绘画史上的里程碑。譬如说,隆万以后,读书的文人成了中国画史的主流,画工的地位完全被边缘化。从徐渭、董其昌、“画中九友”、陈洪绶,到“清四僧”、“四王吴恽”、“扬州八怪”,中国画史成了读书人的一统天下,画工一点地位也没有了。事实上,这个趋势自“元四家”起即已奠定了基础,而至晚明以后,“诗在布衣”现象更为普遍,布衣文人真正成为艺事的主流。另外,绘画题材的消长也是一大变化。随着绘画政教、鉴戒作用等功能的减弱,人物画题材逐渐衰微,而山水、花鸟画像五代两宋时期绘画一样日益盛行。与这一消长现象相对应的是艺术创作中客体对象和观念的变化,表明艺术创作中主体人生价值观和审美观的转换,其实质是文人意识的强化。人物画的衰微,表明文人对社会现实的冷漠和对绘画政教、鉴戒作用的鄙夷,而山水、花鸟画的盛行,则反映了文人对返归自然的向往和畅神怡性作用的追求。毫无疑问,文人画家地位的提升、绘画功能和题材的变化,使得文人画家可以厕身于绘画本身艺术性的追求,尽情抒发主观情感。尤其是艺术功能的变化,使艺术由重内容转向重形式,艺术本体的自律性得到强化,并突出表现在对于笔墨情趣的强调、形式美的追求和诗书画的融合等方面。随着文人画主流地位的确立以及文人画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文人画影响了有清一代和民国时期山水画的发展与演进。
[1]谢肇淛.五杂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35.
[2]周积寅,陈世宁.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辑注[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3]董其昌.画禅室随笔[M].屠友祥,校注.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4]袁宏道.徐文长传[M]//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九.钟伯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716.
[5]徐渭.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黄惇.中国书法全集:第54卷[M].北京:荣宝斋,1992.
[7]唐志契.绘事微言[M]//潘运告.明代画论.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259.
[8]梁穆敬.序[M]//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北京:中国书店,1983:序1.
[9]徐建融.晚明美术史十论[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266.
[10]彭修银.中国绘画艺术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53.
[11]林木.论文人画[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6.
[12]岳仁.宣和画谱[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157.
[13]李俊民.锦堂赋诗序[M]//李修生.全元文:卷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36.
[14]徐建融.晚明美术史十论[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4.
On Emotion Nature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aking Xu Wei and Dong Qichang as Major Objects of Study
Wu Yanfa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trend of humanistic thoughts promoted the awakening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art field, which led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literati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to express emotions. The theory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was remarkable, and the emotion nature of art was expressed the most vividly. There emerges Xu Wei, Dong Qichang and other well-known painters and calligraphers and theorists. They emphasized natural temperaments and subjective spirits, advocated the ink sentiment, pursued formal beauty, and integrated poetry,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Therefore, the mainstream position of literati painting was establish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lf-entertainment and lyricism of the literati’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further demonstrated the emotional nature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nd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landscape painting in later Ming Dynasty.
emotion nature;art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Xu Wei;Dong Qichang;the late Ming Dynasty
吴衍发,艺术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讲师。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晚明书画消费与文人生活”(16BA008)。
J0
A
10.3969/j.issn.2095-042X.2017.01.013
2016-10-20;责任编辑:陈鸿)
——记董氏膏方微商爱心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