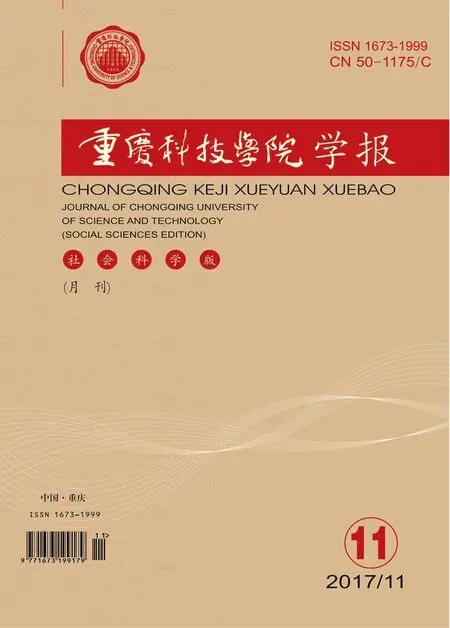近代日本女子修身教科书中的女性形象探析
——以高等女学校修身教科书为例
李月明
近代日本女子修身教科书中的女性形象探析
——以高等女学校修身教科书为例
李月明
1899年《高等女学校令》的颁布确立了近代日本良妻贤母主义的女子教育理念。通过明治后期、大正、昭和前期3个阶段的女子修身教科书的修订,日益固化了国家主义思想与良妻贤母主义影响下的女性形象,突出了义勇奉公、温良贞淑、母性爱的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目标要求。尤其是在昭和前期,这种女子教育目标要求与日本的国防建设紧密联系,将女性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最终使女性沦为了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帮凶和受害者。
近代日本女子修身教科书;女性形象;良妻贤母;战争工具
189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高等女学校令》,使日本式的良妻贤母主义成为日本国家女子教育的理念,并规定高等女学校的教科书由文部大臣审定。1903年,日本政府通过《小学校令施行规则中改正》,确立了教科书国定制度,主要对修身、国语、历史、地理等课程进行统一编撰[1]。随后,文部省组织教育界人士编撰女子修身教科书。1911年后,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成为高等女学校统一使用的教材。女子修身教科书是由当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井上哲次郎、东京音乐学院校长汤原元一、东京帝国大学总长小西重直等多名学术界人士执笔编撰的。他们在国家教育方针及理念的影响下编撰的女子修身教科书中,必然融入了浓重的国家主义色彩和传统儒教良妻贤母思想。
一、井上哲次郎编撰的《女子修身教科书》中的女性形象
《高等女学校令》颁布后,又颁布了《高等女学校学科及其程度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该《规则》规定:“修身科要以《教育敕语》为宗旨,要重视贞淑之德的涵养。 ”[2]1903年,井上哲次郎按照《教育敕语》和《高等女学校令》的教育理念,编撰了以高等女学校为对象的《女子修身教科书》(共4卷)。
井上哲次郎编撰的《女子修身教科书》在开篇“学校的目的”中指出:“高等女学校是为了普及女子中等教育,增长知识,提高品位,培养贞淑的女性而设立的。”[3]但从《女子修身教科书》的内容来看,第2卷讲述女子在家庭、国家、社会3个方面的心得与义务,突出了对女子国体观念的培养、传统儒教道德观念的灌输,以及培养合格的良妻贤母的教育目标。
第一,尊国体、遵国宪国法、义勇奉公的女性。《女子修身教科书》第2卷第2编“关于对国家的心得”明确提出,女子要尊国体、遵国宪国法及义勇奉公。第4卷第3编将其纳入到女子的国家义务之中,指出:“明治盛世遭遇困境,为了国民的幸福,女子必须磨炼自己,积累德行,以维护国体的尊严为己任”[4]9。同时,国民必须遵守与服从国宪国法,即使某些法令会因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而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但这都是“应时局之需要,国民不得违背”[5]。1898 年颁布的《民法典》确立了父家长制的绝对地位,妻子的行为必须得到丈夫的许可,方能行使如订立各种契约等权利。在婚姻方面,男女并没有实现平等。这样的法律就是以牺牲女性的自由平等为代价,换取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家长制的保留。除此之外,该书积极贯彻落实《教育敕语》精神,如《教育敕语》规定:“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也就是“一旦危急时刻,女子不能袖手旁观”“虽然不能同男子一样厮杀于战场,但同样可以义勇奉公,如制造武器、生产绷带、提供兵粮、救助负伤者等,这些职务适合由女性来完成。”[4]13此时日本已经开始对女子进行国防教育,为保卫国家的安全,女性必须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为皇室、为国家效忠。
第二,孝父母、友兄弟、育子女的良妻贤母。19世纪末,儒教的良妻贤母主义教育思想一时占据主导地位。顺从、贞淑、温良的传统儒家妇德观念贯穿于《女子修身教科书》之中,如第2卷第1编“关于家庭的心得”就体现了对父母的孝顺、对兄弟姊妹的友善、对奴婢的怜悯等内容。第3卷第2编“对家族的义务”主要从父母、舅姑、夫、兄弟姊妹、子女、亲戚、奴婢、祖先、家门9个方面论述了女性在“家”“家族”中的义务[6]1。该编主要是规定婚后女子在家庭、家族中应履行的义务。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差异分工下,男子外出谋事,维持家庭乃至家族的生存;女子在家负责整理家务,侍奉公婆,教育子女。但是,妇女也并不是对公婆和丈夫绝对服从,而是互相思考如何配合对方,如“夫妇一身同体,以诚相待,互相弥补不足之处”[6]45,共同为创造美满的家庭生活而努力。这完全不同于一直以来儒教的“三从”道德观,而且妇女不再是限定于家庭、家族的良妻贤母,而是成为为国家的繁荣、为世界的和平、为人类的生存而奉献的良妻贤母。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逐步参与社会活动。但是,其实质是培养以“为国家”为根本目标的良妻贤母,如果国家正值缓急之时,则应毫不吝啬地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自己的生存之地。正如《教育敕语》中所宣扬的:“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
井上哲次郎所描绘的良妻贤母形象是一个基本上无条件服从丈夫、劝谏丈夫的好妻子。同时,女性的作用不再限定于家庭范围内,而是从社会、国家的视角发挥女性作为良妻贤母的作用[7]。
二、汤原元一编撰的《新制女子修身教本》中的女性形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兴起自由主义、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运动。随后也传入日本,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教育思想才被大众广泛关注。因此,在日本文化界兴起一股民主主义风潮,在教育界开展了新教育运动。在此影响下,国家主义思想与儒教的道德观淡化,国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一民主之风引起了日本政府的警惕。1917年日本政府设立了直属内阁的教育咨询机关——临时教育会议。1920年颁布了《高等女学校令中改正》,其中高等女学校的设立一直是“以女子必须达到高等普通教育的水平为目标”,经过修改增加了“还要特别注意培养国民道德和涵养妇德”等内容[8],以此强化国家主义良妻贤母观。
在此背景下,东京音乐学院校长汤原元一于1921年执笔编撰了《新制女子修身教本》(5卷)。与井上哲次郎的教育理念相比较,一方面汤原元一的《新制女子修身教本》增加了“明治天皇(上·下)”“皇室”“天皇”等文章,旨在向学生宣传“天皇与国家的关系、天皇所行使的权力、天皇是唯一主权存在的必要、皇室与臣民的关系”[9]252等关于皇国史观的教育内容。此外,还特別介绍明治天皇对国家发展的作用,认为“明治时代的大发展是天皇所赐”[9]171。
另一方面,汤原元一的女性观更为进步。在大正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国民的儒教道德观逐渐淡化,女性要求男女平等、享有参政权的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与欧美的女性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良妻贤母主义教育观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理想中的良妻贤母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10],出现了“职业妇人”。 汤原元一认为:“女性的天职是家庭的主持,但同时也可以从事其他职业”[9]362,并阐述了女性从事职业的必要性,而这个必要性就是男女之间没有差异。这可以从他的“女性特性论”中看出来,在《新制女子修身教本》中也渗透了“女性特性论”思想。例如,他在第2卷第9课“自重”中讲到:“无论哪个国家,谦逊的美德可以提高女性的品位。因此,女性为了世间、为了别人也要去学会谦逊,这也就意味着并不是做任何事都称之为美德。这是女性应尽的本分。女子应尽的本分说明女性并不逊色于男性。男女各尽其本分,社会才会进步,人的价值也会提升。”[11]
汤原元一的“女性特性论”强调了女性谦逊的美德,从侧面反映了女性地位的提高和权利的保障,这在当时是进步的,同时说明了这一时期的女子修身教科书具有一定的开明性。
当然,汤原元一的教育理念与井上哲次郎是一致的,都是以良妻贤母主义教育思想为中心。汤原元一编撰的《新制女子修身教本》从多方面论述了女性作为良妻贤母的职责,如“女子的长处与短处”“女子的本领”两篇文章阐述了女子的一大特性——母性爱的发挥,并认为这种母性所展现出来的以柔制刚、妇德、妇容能为社会、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汤原元一虽然肯定了“职业妇人”的出现及其必要性,但是,并不代表他已放弃传统的良妻贤母主义的教育理念。他坚持认为女性的天职是家庭的主持者,即使外出从事其他职业的女性也要明确自身在家庭中应尽的本分,也就是说作为家庭主持者的女性天职是不可动摇的。
三、小西重直编撰的《昭和新女子修身训》中的女子形象
1926年日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预示着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将开辟一个“新的局面”——日本总体战体制的确立。与此同时,日本既定的国防政策也在逐步实施,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步。其基础在于国民精神的团结,而国民精神团结的根本则在于教育。女子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扶翼皇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为了深入贯彻日本政府新的国防观念,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总长的小西重直编撰了《昭和新女子修身训》,经文部省检定后于1938年发行使用,1941年刊发了修订版。《昭和新女子修身训》要培养的女性形象是忠君爱国、义勇奉公、涵养妇德的日本式良妻贤母。与明治后期、大正时代相比较,国家主义思想和良妻贤母主义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女子修身教科书中完全摒弃了自由主义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昭和新女子修身训》中的插图及敕语强化了“国家总动员”的国防观念。首先,《昭和新女子修身训》1~4卷中的插图分别为“岩仓邸行幸”图、“宪法发布观兵式行幸”图、“凯旋观舰式”图、“神宫亲谒”图。通过各种描绘天皇的插图要求女子要做到忠君、遵法、爱国、敬神。其次,在插图后附上了《天壤无穷的神敕》《教育敕语》《戊申诏书》《振作国民精神诏书》及《赐青少年学徒敕语》等,并要求学生背诵,旨在向高等女学校的学生强化国体观念以及义勇奉公精神。这也是昭和前期国定修身教科书的一大特色。
第二,《昭和新女子修身训》中宣扬皇国史观的内容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从第2卷的目录中发现,关于皇国史观的内容共有11课,如“我国国体”“皇祖皇宗”“天皇”“皇室”“敬神崇祖”“臣民”“忠君爱国”“祖先”“忠孝一致”“戊申诏书(一)”“戊申诏书(二)”。全书共20课,其中强调皇室崇拜的就占了50%以上,足见日本政府对培养女子皇室、皇族崇拜精神的重视。
第三,《昭和新女子修身训》仍以培养国家主义儒教传统的良妻贤母为教育目标。从明治末期开始,“良妻贤母”一直是女子教育的目标,至昭和前期,“良妻贤母”中的国家主义思想与女性的天职——妻子与母亲的作用成为强调和灌输的内容。首先,妻子作为丈夫的贤内助,应帮助丈夫管理家庭事务,维持家庭的幸福安宁。而“家庭是构成国家的基本单位”[12]90,只有家庭安宁和睦,国家才会繁荣昌盛。因此,女子不仅仅是家庭中的一分子,也是国家组织中的重要成员。也就是说,一方面女子在家中恪守妇道,做到夫唱妇随,成为一个从顺、温良、贞淑的妇人。这就要求女子必须对裁缝、园艺等技能勤加练习。另一方面,不管平时还是战时,也不管是家庭主妇还是职业妇人,女性的最终使命就是对“皇运的扶翼”。在第4卷第19课“皇运的扶翼”中强调:“必须理解‘皇运扶翼’在战时与平时的意义。一旦危急时刻,国难当道,生命轻于鸿毛,大义重于泰山,做到灭私奉公,忠君爱国。”“在战争状态下,女子可以在战后方服务,如援助出征军人,对应召者家人进行慰问,做好防空准备,对灯火进行管制,进行经济上的物质动员等。”[12]108其次,女性的第二大天职就是尽到母亲的责任。女性天生拥有以“母性”为基础的“温柔”“爱情”“感化力”“牺牲的精神”等特性,这是“母性”的本质[13]。 而《昭和新女子修身训》所强调的是“母性”的“牺牲精神”。虽然教育子女是父母共同的责任,但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因此,教育子女的责任就落在母亲的身上。而母亲不能对孩子过分溺爱,放纵其成长,否则,不仅毁掉孩子的前程,而且也破坏家庭的安宁,甚至危害国家的利益[12]90。这种“牺牲精神”更多的表现在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士兵。这就将“母亲的特性”抽象化、理念化了。
四、结语
通过对明治后期、大正时期、昭和前期3个阶段的高等女学校的修身教科书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国家主义思想与良妻贤母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的日本女性形象日益固化。尤其是总体战体制建立后,日本政府利用修身教科书突出女性的特性,要求女性做到铳后奉仕与培养下一代皇国民,动员女性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服务。这就使女子教育完全成为了军国主义的附属工具,使得女子教育的发展逐渐偏离了近代先进的女子教育理念的轨道,从而阻碍了日本近代女子教育的正常发展。因此,战前的良妻贤母的教育理念最终使女性沦为了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帮凶和受害者。
[1]日本文部省.小学校令施行規則中改正·学制百年史[EB/OL].[2017-06-20].http://warp.ndl.go.jp/info:ndljp/pid/286794/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hpbz198102/hpbz 198102_2_049.html.
[2]日本文部省.高等女学校ノ学科及其程度ニ関スル规则·学制百年史[EB/OL].[2017-06-20].http://warp.ndl.go.jp/info:ndljp/pid/286794/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hpbz198102/hpbz198102_2_069.html.
[3]井上哲次郎.女子修身教科书:卷1[G].东京:金港堂书籍,1903:2.
[4]井上哲次郎.女子修身教科书:卷2[G].东京:金港堂书籍,1903.
[5]井上哲次郎.女子修身教科书:卷4[G].东京:金港堂书籍,1903:40.
[6]井上哲次郎.女子修身教科书:卷3[G].东京:金港堂书籍,1903.
[7]小山靜子.良妻贤母という規范[M].东京:劲草书房,2007:204.
[8]日本文部省.高等女学校令中改正·学制百年史[EB/OL].[2017-06-20].http://warp.ndl.go.jp/info:ndljp/pid/286794/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hpbz198102/hpbz 198102_2_072.html.
[9]汤原元一.新制女子修身教本教授參考书[G].东京:东京开成馆,1925.
[10]林言禅.良妻贤母と女性教育について[D].中部大学,2004:25.
[11]汤原元一.新制女子修身教本:卷2[G].东京:东京开成馆,1928:18-19.
[12]小西重直.昭和新女子修身訓:卷4[M].东京:永泽金港堂,1941.
[13]蔵澄祐子.近代女子道德教育の历史:良妻贤母と女子特性论という二つの位相[J].东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纪要,2008(34).
(编辑:文汝)
K313.42
A
1673-1999(2017)11-0097-03
李月明(1991—),女,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日本史。
2017-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