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政治及其激进溢出
——《权力的游戏》与政治哲学
吴 冠 军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上海200241)
马基雅维利政治及其激进溢出
——《权力的游戏》与政治哲学
吴 冠 军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上海200241)
《权力的游戏》是晚近几年横扫各类影视奖项、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极高人气的美国电视剧。在高成本的精良制作与奇幻架构的外衣之下,该剧具有政治哲学的丰富内蕴,它标识出了现代性政治的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去道德化的马基雅维利式政治,在这个视野下,政治问题被转化(简化)成了技术问题,它构成了现代性政治的支配性模式;而对它的激进溢出,便构成了该剧的后两个政治哲学维度,它们分别是:(1)世俗秩序中的神学政治,其吊诡之处在于,激进原教旨主义恰恰是以极端世俗秩序作为其温床;(2)打碎旧秩序的革命政治,其挑战在于“革命的第二天”,即如何保证真正的解放。作为奇幻剧情剧的《权力的游戏》,实际上恰恰构成了当下政治世界的一个“(超)真实再现”。
《权力的游戏》;马基雅维利;神权政治;革命;制序
引言:“三眼乌鸦”的幻像
对于恐怖片,齐泽克曾提出一个鉴赏观点:一部恐怖片的好坏,就是看当我们把恐怖要素移除之后,它到底是讲一个什么故事。①参见齐泽克的The Pervert's Guide to Cinema由Sophie Fiennes导演执导。绝大部分恐怖片之糟糕不在于其低成本的制作,而恰恰在于一旦拿掉那些刻意营造的恐怖环节,整个电影就苍白无力到连一个连贯性的叙事都支撑不起来。在制作成本上奇幻片普遍要高出恐怖片一大截,但是齐泽克这个论点完全可以平移到前者上:当我们把那些用高成本制作出来的奇幻元素拿掉之后,该片还剩下什么?美国HBO有线电视联播网推出的剧集《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无疑是影视界近些年来最受瞩目、制作最精良、人气最高的奇幻巨作(没有之一),其得到的奖项数远超过同时期大屏幕上的《霍比特人》系列以及各种超级英雄系列。①至本文成稿时,《权力的游戏》已获得581项行业奖项提名,并赢得其中的204个奖项。见“Game of Thrones”,Wikipedia,<https://en.wikipedia.org/wiki/Game_of_Thrones>(accessed 25 august 2016).《权力的游戏》改编自乔治·马丁(George R.R.Martin)的奇幻文学作品《冰与火之歌》系列,从2011年4月起热播至今,已经连续推出六季(在这过程中投资规模不断加大)。其不仅在美国本土和整个英语世界引起热烈反响,②根据《Vulture》杂志2012年的排名,《权力的游戏》在欧美世界粉丝数超过Lady Gaga、贾斯汀·比伯、《哈利·波特》以及《星球大战》。这几年来,大量新生儿被用《权力的游戏》里角色名字取名,2012年“艾莉亚”(Arya)变成了美国上升速度最快的女孩名字,从711位上升到413位。“卡丽熙”(Khaleesi)也迅速变成一个很流行的女孩名字。在大洋的这一边同样拥有了数量极为庞大的粉丝群体,剧中史塔克家族孩子们甚至都有了各自专门的中文昵称——“三傻”“二丫”“萝卜”“囧雪”……在该剧集所掀起的追捧热潮下,原著的中译本亦长年盘踞在各大热销书榜上。
《权力的游戏》被归类为“奇幻剧情”(fantasy drama),讲的是一个虚幻世界里的故事,那里充斥着诸如“异鬼”“血魔法”“绿先知”“易形/狼灵”“龙”等等奇幻事物。很多影视批评家们如伊恩·博格斯(Ian Bogost)将《权力的游戏》的成功归功于其奇幻主题,并把该剧视作为始于2001年《指环王》三部曲、《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史诗奇幻剧热潮之最新一浪。而这些奇幻剧之所以获得商业成功,正是因为它们有效地向人们提供了逃离现实生活的一个出口、一剂迷药。[1]然而,《权力的游戏》是否真的只是因为出色地提供了奇幻元素而成为一部现象级巨作?根据HBO的数据,《权力的游戏》观众平均年龄为41岁,[2]这个数字成为了以青少年为受众对象的奇幻片的一个歧出。《权力的游戏》粉丝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澳大利亚前首相朱莉娅·吉拉德以及荷兰外交部长法兰斯·蒂莫曼斯。蒂莫曼斯在2013年的一个演讲中,当谈到欧洲政治所面临的挑战时专门引用了《权力的游戏》里的著名台词:“凛冬将至。”这些年美国媒体亦大量运用《权力的游戏》的语言,来评论奥巴马医改、叙利亚内战等等国内与国际政治事件。这标识出了《权力的游戏》所展示的那个奇幻世界,同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现实世界”具有诸种结构性的同质性(structural homogeneities)。就像《权力的游戏》剧中那只“三眼乌鸦”使布兰·史塔克不断看到关于真相的“幻像”,《权力的游戏》自身亦是一只让我们在“幻像”(奇幻片)中瞥到真相的“三眼乌鸦”。如齐泽克所言,真相必须经过“绕道”(detour)、通过“斜视”(looking-awry)才能被触及:进入奇幻世界,恰恰是更好地进入当下世界。[3]
当我们尽数移除该剧中的各种奇幻元素后,剧中世界之规模,仍然令人叹为观止:这个完全架空的世界,有其自身的地理、历史乃至各地迥异的文化、语言、气候、风俗、制度、信仰,丰富细腻程度与我们当下现实世界相比亦并未逊色多少,几乎达到了一个“平行世界”的文明规模。“冰与火之歌”现已拥有自身的维基百科,其词条数在本文成稿时多达7163条(该站中文维基之词条数亦达5298条,每篇严谨程度与维基百科一般无二)。①AWiki of Ice and Fire,<http://awoiaf.westeros.org>(accessed 24 august2016).冰与火之歌中文维基.<http://zh.asoiaf.wikia.com>(accessed 24 august2016).该架空世界的“真实性”——或者说“超真实性”(hyperreality)——也丝毫不弱于我们生活其内的这个“现实世界”。如拉康所分析的,“现实”同样是个符号性秩序(symbolic order),一样是倚赖包括维基百科在内的各种话语体系编织起一个充满各种历史、文化以及形形色色细节的巨大“矩阵”。一旦我们全球范围内“焚书坑儒”,砸毁数据服务器,我们的“现实”即刻就会比《权力的游戏》里那个虚构出来的世界更加苍白无力,显得更“不真实”。对比“现实世界”,作为奇幻剧的《权力的游戏》,恰恰因其架空设定,反而更能没有禁忌地演绎前者的诸种逻辑。当我们移除其奇幻元素后,一个更裸露的“权力的游戏”就展现在我们眼前。
“权力如浮影游墙”
关于权力,《权力的游戏》有一个著名对白,发生在该剧两个重要人物之间。御前情报大臣瓦里斯对被临时授命做代相的提利昂·兰尼斯特(“小恶魔”)说了如下这段话:“权力存在于当人们相信它存在的地方。它是一个把戏,如浮影游墙。一个十分矮小之人,也能投射出一个十分硕大之阴影。”②《权力的游戏》第二季第三集《死去之人会永远不死》。政治性的“权力”(power)和纯粹的“力量”(force)不同,它既强大又脆弱:权力运转的每一个瞬间(如某人发出指令而一群人服从时),必定是有一套叙事在支撑着,而这套叙事被抽走之后,再强大的权力也即刻烟消云散。瓦里斯又让提利昂猜一个谜语:三个大人物即一个国王、一个教士和一个富商同在一室,中间站了一个剑手,他们都叫这个剑手杀掉另外两个人,剑手会杀谁?提利昂认为取决于剑手。瓦里斯指出如果剑手是最关键因素,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假装认为国王握有至高权力呢?这个谜语同其关于权力的论断构成了很好的互文关系:剑手拥有的只是“力量”,在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里或许最为强大,但在人之群处而形成的共同体里,“权力”才至关重要。那三个大人物看似都握有极大权力,他们的权力其实是由三套不同的叙事在支撑,剑手会听谁的命令取决于当时哪套叙事在“政治之墙”上投射出了最硕大的阴影(王冠、神祇或金钱)。而政治哲学(以及政治神学),就是研究支撑权力运转的那诸种叙事。
《权力的游戏》里政治哲学第一课,就是所有的德性、荣誉、虔诚、誓约,都是维持“现实秩序”权力运作的“把戏”之一部分。会玩“权力游戏”的人,需要让别人(而非自己)深信这套体系。回到瓦里斯的谜语:国王、教士、富商可能都不相信支撑自身权力背后的叙事,但是必须要让那个剑手对之深信,才能指挥他杀死其他两人。所以,从第一季开始,《权力的游戏》就把我们带入到了一个马基雅维利式“去道德化”的政治世界中:在“权力游戏”里,如果没有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智慧和手段,那就只有横死一条路,不管你实力(力量)有多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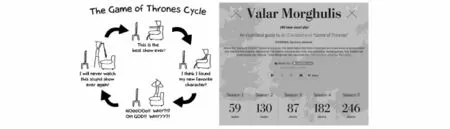
这也造成了该剧目前最受观众诟病的一点,即它违背虚构作品(小说/电影/电视剧)的主配角差序原则:虚构作品必须要形成突出的主角,以使得读者/观众有投射关注与认同的对象,从而建立起作品-受众之间的有效心理关联,关联越强,作品越受欢迎。影视制作的入门原则就是要让观众能很快确认剧中男一号、男二号以及女一号、女二号;与此对应,所有影视奖项也都是分列男女主角和男女配角。然而,《权力的游戏》完全颠覆了观众们一贯的观剧体验:从其第一季开始,他们被迫习惯核心主角突然下一幕就会横死,主演随时准备“领便当”的状况,原作者与编剧们完全不珍视观众在观剧过程中对主角们所培养起来的情感。有人已经总结了“观看权力游戏之心理循环”(the Game of Thrones cycle):(1)“这是我看过的最棒的剧!”(2)“我找到了新的最喜欢的角色!”(3)“哦,不!!为什么?上帝阿!!为什么?”(4)“我再也不看这部愚蠢的剧了!”(然后再重新回到1)①“The Game of Thrones Cycle”,The Doghouse Diaries,<http://thedoghousediaries.com/5805>(accessed 24 august 2016).第一季终首相奈德·史塔克被斩首处决;第三季终其子“少狼主”罗柏·史塔克、其妻凯特琳·史塔克以及所有史塔克家族在北境的忠实追随者在“血色婚礼”上被尽数屠戮,这些一次次地刷新观众们震惊与痛心的心理指数。《华盛顿邮报》在第六季开播前夜公布了一项统计:该剧只前五季就共有704个角色“领了便当”(包括人和动物),刷新美剧“残忍”新高。[4]尤其是“血色婚礼”那集,剧情在一片浓郁甜蜜气氛中突然一秒钟反转,许多观众热切关注故事发展的理由之一(“少狼主”及其妻、其母、其整个班底),就此被彻底抹去,不给观众留一线余想(在原著中至少凯特琳后来还被复活)。
然而,当那些对剧情表示不信服,惨呼“不!!为什么?”的观众返回头去检视剧中所有的线索时,却会看到这些意外结果却又完全在逻辑之内:信任他人的承诺/誓言,信任符号性规则(如“不得加害屋檐下的宾客”这条维斯特洛大陆上神圣的“宾客权利”)的约束力,使得这个曾经极具实力的家族、史塔克父子两代人瞬间遭到彻底覆灭。荣誉、善良、忠诚、信义这些德性,在政治世界里作用甚微,这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者之间的“游戏”。奈德是一个令其对手如“弑君者”詹姆·兰尼斯特都称赞的“高尚之人”,然而他断然拒绝御前财政大臣“小指头”培提尔·贝里席之建议(拥护实为瑟曦王后与其弟詹姆乱伦之子乔佛里即位,并以摄政王身份攫取至高权力),但同时又继续对“小指头”保持信任,终致自己一秒间从首相沦为“叛贼”。奈德有荣誉但“无谋”之极的举动,还包括决意揭破乱伦秘密却又事先约见并告知瑟曦自己整个计划(好让她有时间带着三个孩子离开都城),等等。奈德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处(首级还被挂到城墙枪尖上被羞辱)的下场。仔细梳理剧中线索,其实完全不算意外。观众极度强烈的意外感,纯粹来自男一号绝不会突然横死这条影视制作入门级原则。与奈德之死相似,其子罗柏率众称王后在战场上未尝一败,但却因相信“宾客权利”及其封臣们效忠之誓,亦在弗雷家族与波顿家族联手设局下一夕间尽皆受戮,碧血横飞。在史塔克家族倾覆的血野上,兰尼斯特家族、提利尔家族、马泰尔家族、艾林家族、波顿家族以及“小指头”、瓦里斯等等各路高手们继续各施神通,继续彼此算计,明争暗斗。
在利奥·施特劳斯看来,马基雅维利去道德化的政治现实主义,实乃真正标识了现代性的肇端。至此之后,形而上学(雅典)与宗教(耶路撒冷)不再具有真理地位,而纯粹成为“浮影游墙”的叙事,沦为权力游戏玩家们手里的“把戏”。这导致(1)政治生活与道德脱钩;(2)政治问题(从治理到政治正当性)变成了技术问题。[5]用这个洞见来反观《权力的游戏》,剧中“小恶魔”提利昂·兰尼斯特就代表了能出现在马基雅维利舞台上(并能不横死)的最理想的政治人:熟谙各种政治手段和权术,不信神也没有特别强的荣誉感(并且以公开出入妓院而为其父深恨),但具有职责意识(和一定同情心),并有高超的技术能力来履行其所居之位所承担的职责。其父泰温·兰尼斯特极其厌恶这个侏儒儿子,但仍派他去都城作为自己缺席时的代相,就是深信其技术能力,并且在乔佛里一世进一步肆意妄为时有能力也有担当去严加阻止。而后来瓦里斯把他救下来后推荐给狭海对面的“龙母”丹妮莉丝·坦格利安,也同样是因为目睹了其代相时期的作为与能力,深信他是能够辅佐丹妮莉丝重返铁王座并保持维斯特洛大陆长久和平的不二人选。
“诸神要求正义”
不过,《权力的游戏》中的政治哲学并未仅止于此:在马基雅维利主义政治之底色中,《权力的游戏》至少还从两个向度上继续走向纵深,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空间。首先是世俗秩序中的宗教问题。在史塔克家族土崩瓦解,原国王之弟史坦尼斯·拜拉席恩军队被新结盟的兰尼斯特与提利尔两大家族联军击溃后,“权力游戏”的核心斗争,变成了在兰尼斯特与提利尔这两个“盟友”家族之间展开。新晋太后瑟曦想方设法阻止王后玛格丽·提利尔对自己年纪尚幼的二儿子托曼一世之精神控制,但又不方便自己公开出手,她想到的办法是:废掉原先那位腐败不堪的大主教,并扶植宗教狂热分子“大麻雀”代之,旨在借用这支“外部的”宗教力量来压制提利尔家族权力在都城的蔓延。果然,玛格丽之兄、身为提利尔家族继承人的“百花骑士”洛拉斯·提利尔以及玛格丽本人,先后被教会以违反神之律法(鸡奸、作伪证)打入大教堂地牢。提利尔家族的“荆棘女王”奥蕾娜夫人去找大主教交涉,结果发现他们说的完全不是一种语言:
大麻雀:你的孙子、孙女发下神圣誓言然后说谎,天父审判我们所有人,无论贵族之子还是渔夫之子,只要触犯了神的律法,就要受到惩罚。
荆棘女王:你想要什么?金子吗,我可以让你成为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修士。
大麻雀:(冷笑)
荆棘女王:不然是什么?
大麻雀:我能想象这让你感到奇怪。你遇见的每个人都有其隐藏的目的,而你得意于自己擅窥人心。但我要告诉你一个简单的真理:我侍奉诸神,诸神要求正义。①《权力的游戏》第五季第七集《礼物》。
面对这个看上去无比虔诚、不穿戴华丽长袍的新任大主教,狡诈老练、毒杀乔佛里一世(并成功嫁祸提利昂)幕后黑手之一的荆棘女王,却完全无计可施。在这一刻,“权力的游戏”遭遇其溢出——极端原教旨主义信仰。在“大麻雀”身边聚集起大量的“麻雀”(意指底层虔诚信众)与“信仰战士”,面对这个快速崛起的巨大力量,不单提利尔家族无计可施,在“权力游戏”中似乎占得上风的瑟曦太后,随后自己也被教会以通奸和乱伦罪打入地牢,等待宗教审判。“权力游戏”中你死我活的对手们,双双被狂热宗教力量压制。那么问题在于,这种极度原教旨化的信仰,怎么就一下子产生了呢?
吊诡的是,极端原教旨主义,恰恰是从一个彻底世俗化的土壤中产生,并成为对后者的激进反动。让我们把考察的视线从奇幻世界拉回到当下的现实世界。在当代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我们面对的不是“历史终结”后的大同盛世,而恰恰是“伊斯兰国”的崛起。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所导致的贫富剧烈分化,使底层民众——尤其是全球秩序之“边陲地区”(借用沃勒斯坦的术语)的底层民众——越来越被激进地“无产阶级化”,沦为了该秩序中的“被排除者”(齐泽克术语)、“赤裸生命”(阿甘本术语)。他们面对巨大的不公(乃至被该秩序彻底“抛出”)却全然无能为力。在“冷战”结束后的这个“历史终结”时代中,现代性不再提供“新自由主义”(自由民主+全球资本主义)之外的任何替代道路。这些孤独绝望的年轻人没有替代性的理念/理想以激励,因此大量转到极端宗教化思想,甚至发展出绝不妥协的面相:“整个世界已经抛弃你了,但真主没有抛弃你,你只有投奔他!”“世界是邪恶的,唯一要做的就是修改它回到神设定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伊斯兰国”尽管如此残暴(并不惜在媒体上公开展现其残暴性),却仍不断有大量年轻人投奔过去,并且有为数不少的来自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的“志愿者”的原因。②据一份2014年发布的法国研究机构报告分析,“伊斯兰国”头目多来自伊拉克、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突尼斯,并且有着3000多名来自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志愿者”。2014年中,估计有约500名英国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伊斯兰国作战。“James Foley:British jihadist called John is world'smostwanted man over beheading of journalist”,Mirror Online,20 August 2014,<http://www.mirror.co.uk/news/world-news/james-foley-british-jihadist-called-4080797>(accessed 11 December 2015).替代性的现代理念/道路是需要证成的,对于为什么要这样来变更世界,要提供理据(是故现代性的理念/道路之争,往往是知识分子为先锋);而信仰是自我证成的,信者恒信,年轻人甚至不需要受教育,直接就能成为“圣战志愿者”,甚至失败也无法令其放弃信仰,相反可能使其更加坚韧,更加极端化(神圣事业需要“殉道者”)。在一个同整个现行秩序(“文明世界”、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为敌的战斗中,只有加倍虔诚才能抓住“道义”的制高点(抓住能为当下所有行动提供证成依据的“至理”)。①对“伊斯兰国”与全球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分析,请参见吴冠军《“历史终结”时代的“伊斯兰国”:一个政治哲学分析》,见《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2期。
同样的虔诚,便是“大麻雀”权力的根源,并获得人数不断增长的“麻雀们”的投奔和追随。维斯特洛大陆上尽管也有多种宗教并存(七神信仰、旧神信仰、光之王、淹神、千面神……),但在《权力的游戏》故事上演的时代,民众整体上已经极度世俗化,甚至是一个很“污浊”的世界。我们看到尽管各个地方风俗迥异,但有一点高度相同,就是妓院的盛行。从都城“君临”到“长城”脚下,从巨型城堡到乡野小镇,妓院无处不在,上到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皆出入其中,纸醉金迷,甚至王宫“红堡”内都有通向妓院的密道,用来给那些自视高贵的大人物(包括国王与首相)来偷腥。“七神”信仰(同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相似,七神是同一神的七个位格),是包括都城“君临”在内维斯特洛大陆南方各地所共同信奉的宗教。然而,整个教会却早已经堕落不堪,宗教的律法形如“浮影游墙”,前任总教主正是在“小指头”所经营的豪华妓院搂群芳共销魂时,被一群宗教狂热分子(“麻雀们”)拖出来裸体游街示众。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极度世俗化之污浊土壤里,最容易反弹出极端原教旨主义,一有风助,立刻漫野成长:“大麻雀”正是抓住两大家族政治角力的机会——“伊斯兰国”也正是抓住美国打垮萨达姆世俗政权(我们世界的两大“家族”)且于数年后又全部从伊拉克撤军的机会——而迅速变成为一个恐怖性的“溢出”。荆棘女王与大麻雀对话中的后面一部分也饶富意味:
荆棘女王:诸神如何传达指示?渡鸦还是快马?
大麻雀:诸神的指示记载在《七星》圣经上,你的书房里若是没有,我可以把我自己那本送给你。
荆棘女王:我读过《七星》圣经。
大麻雀:那想必你记得书中关于鸡奸与伪证的章节。你的孙子孙女将与任何触犯神圣律法的人一样受到惩罚。
荆棘女王:那么这肮脏的都城之内半数男女老少都触犯了神圣律法。②《权力的游戏》第五季第七集《礼物》。
荆棘女王触及了原教旨主义信仰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在一个早已极度世俗化的世界中,宗教已蜕化为一种文化习俗,而要圣典经籍上的教义和律法按照字面意思严苛地重新生效,就只有选择暴力性的“恐怖主义”(在世俗秩序眼中)方式。剧中“大麻雀”就任大主教后,“麻雀们”随即四处出动打砸,扫荡妓院,抓捕同性恋,强迫整个城市一起“净化”;修士与修女皆如凶神恶煞般严酷残暴,动辄对“不虔敬者”施加武力。而在我们的世界中,“伊斯兰国”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社交媒体上公示行刑处决,打砸文物等暴行,在世俗秩序眼中至为凶残狰狞,“什么样的人能下得了这样的手?”而在其追随者眼里看来,只是“这肮脏的世界之内绝大多数男女老少都触犯了神圣律法”而已:真神(安拉)要求正义,必须“净化”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把《权力的游戏》看作是一本政治哲学教材的话,那它的第二课就是:作为马基雅维利政治之激进溢出的原教旨主义信仰(往往伴随极端恐怖主义),恰恰就是产生自最世俗、最污浊的政治秩序中。今天这个“后世俗”社会清晰地标识了:当代复兴的神权政治,本身即为现代性世俗政治的淫秽的补充。在污浊的马基雅维利政治与淫秽的神权政治之外,是否还有溢出性的选项?
革命的第二天
《权力的游戏》确实没有辜负我们。“龙母”丹妮莉丝·坦格利安这条故事线,构成了马基雅维利主义政治的另一个歧出。丹妮莉丝一开始抱持的,也是不惜一切代价复国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逻辑,包括接受其兄安排嫁给多斯拉克部落领袖卓戈卡奥(换取军队反攻维斯特洛大陆),以不守契约的方式获得整支“无垢者”军队(交易达成后立即用本来作为交易品的龙烧死交易的另一方),充分利用自身美貌(与联姻可能性)来合纵连横获取支持与资源。这些策略和手段,和她试图推翻的狭海对岸那些现行统治者们,实则处在同一个逻辑水平线上。但是就在这个漫长的复国征程中,丹妮莉丝却提出了平等理念与解放目标。这,是她的先祖与维斯特洛大陆上所有政治人物——其中包括奈德·史塔克、提利昂·兰尼斯特、琼恩·雪诺这些剧中“正面人物”在内——都完全没有想过的事。提出这个目标完全是丹妮莉丝一个人的决断(甚至几次强硬地拒绝其顾问们的现实主义建议),最早在她目睹作为征服者的多斯拉克部落种种暴行时便种下了此念,随后看到“奴隶湾”各城邦中奴隶们之凄惨处境,更坚定了要做一个“粉碎镣铐者”。
决定性的变化发生在丹妮莉丝解放阿斯塔波后挥师进军渊凯之际。此前,解放理念最初提出,仍可以视作为一个策略——即,用它来发动城内民众哗变(号召他们自己站起来解放自身,并以自由人来参加她的解放事业),从而坐收瓦解抵抗乃至以小吞大之功。然而,对这位兵临城下的“粉碎镣铐者”,渊凯的“贤主们”(wisemasters)慷慨提议给予大量黄金与船只作为礼物,只求她领兵离开渊凯,登船西征维斯特洛。贤主们坐拥城坚池固之外,还拥有“次子团”等雇佣军事力量;而他们给出的这份厚礼,则已填上了彼时丹妮莉丝复国惟一所欠之“东风”(有军队有龙但还缺跨过狭海的船)。当丹妮莉丝做出拒绝该礼物的决定后,她也就几近脱离了马基雅维利轨道。其时的丹妮莉丝,宁愿暂缓复国大业,也要终结奴隶制,解放所有奴隶。其后的她,完全不同于狭海彼岸那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已是真正成为了一个激进的革命者——“粉碎镣铐者”。被她解放的奴隶们欢呼她为“弥莎”(Mhysa,剧中涵义为“母亲”),显然是“弥赛亚”(Messiah,救世主)的代指。
丹妮莉丝的解放目标并非只停留于废除奴隶制。其母国——维斯特洛大陆上的“七国”——的政治体制接近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奴隶已为法律所禁绝(其顾问乔拉·莫尔蒙爵士,就是因贩卖奴隶而被通缉,是以逃到狭海对岸)。然而,丹妮莉丝旨在彻底取消贵族(王室、封建大家族)与普通平民之间的差等。后者尽管是自由人,但处于社会结构的最底层,无领地及头衔,只耕种前者的土地,在行政管理上缺乏发言权。尽管多数家族有法律保护当地平民免受骚扰虐待,然而实施这些法律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当提利昂·兰尼斯特问丹妮莉丝“你觉得在维斯特洛谁会支持你,坦格利安家族已经不复存在,没有一个活着的血亲可以支持你”时,后者回答“平民”。提利昂觉得不切实际,仅有平民而无贵族富人支持的统治,根本就不可能维持。作为一个优秀的马基雅维利式顾问,提利昂向丹妮莉丝提供了他的局势分析,最后推断只有提利尔家族还可能会支持,但也远远不够。然而,丹妮莉丝的回应大出提利昂意料:
丹妮莉丝:兰尼斯特、坦格利安、拜拉席恩、史塔克、提利尔,这些大家族不过是同一车轮上的辐条,一会这个家族在顶端,过会是另一个,不断滚动,碾压地上黎庶。
提利昂:停止这车轮,是个美好的梦,你不是第一个做过这个梦的人。
丹妮莉丝:我不是要停止这个车轮,我要粉碎这个车轮!①《权力的游戏》第五季第八集《艰难堡》。
丹妮莉丝同提利昂的思路完全不在一个平面上:她不是想联合哪些贵族,而是想粉碎所有贵族,粉碎包括自己家族在内整个贵族封建制,而代之以彻底的平等。从这个时刻起,她挥师维斯特洛大陆的主旨已然变更,即从复国(复活坦格利安家族统治)变为革命(废除不平等的现实政治结构)。于是,《权力的游戏》一剧在马基雅维利政治与神权政治之外,进一步触及革命政治的问题。
革命政治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革命的第二天”问题,即,粉碎旧秩序的革命成功之后,如何建立起具化(embodying)-制度化(institutionalizing)解放目标的新秩序?更初步地,如何先确立起全新而有效的治理?当丹妮莉丝挥师解放了另一座奴隶制城邦弥林后,原先已获解放了的阿斯塔波和渊凯因没有形成有效的新秩序,很快重新又落入“贤主们”之手。拆除原有共同体结构之后,那些被解放的奴隶发现自己反而完全不知道如何存活;丹妮莉丝治下的弥林,很多“前奴隶”因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乃至存活的方式,甚至找她请愿要求重回原先“主人”家里为奴。“自由人的自愿做奴隶”,这个政治哲学的经典难题,②诺齐克曾言:“一个自由体系是否将允许这个人把自己卖为奴隶?我相信它将允许。”丹妮莉丝也遭遇到了,她被迫选择同意。弥林街头,还多处出现“杀死主人!弥莎自己是一个主人!”的涂鸦,对自任“弥林女王”的丹妮莉丝亦造成了相当有力的话语挑战:救世主和奴隶主并无二致,都是高高在上的特权阶级。
理念与实际治理,并不是一件事:倘若最终未能形成同理念相匹配的有效的替代性共同体组织方式,革命便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大规模流血而已:要么随即再度被旧势力“复辟”,要么仅仅成为我们所熟悉的“改朝换代”(社会-政治结构保持不变的“汤武革命”模式)之工具。攻下弥林后的丹妮莉丝,已然实在地获得了足够数量的船只。其顾问乔拉·莫尔蒙建议放弃已被奴隶主复辟的阿斯塔波、渊凯以及乱成一团的弥林,直接挥师渡海进攻君临,那座都城正因为几大家族对铁王座的各种明争暗斗而前所未有的薄弱。在那个时刻,丹妮莉丝做出了又一个至关重要的“反马基雅维利式”决定:留下来治理。
丹妮莉丝:我若连奴隶湾都无法掌控,如何治理七国?人们凭什么信任我,凭什么追随我?
乔拉:你是塔格利安传人,你是龙之母。
丹妮莉丝:我不能只是这些。我不能让我已解放的民众重新堕入镣铐中。我不会航向维斯特洛。
乔拉:那么,你要怎样?
丹妮莉丝:我会做女王该做之事,我要治理。①《权力的游戏》第四季第五集《托曼一世》。
放弃绝好反攻母国机会的丹妮莉丝,开始了异常艰巨的治理过程。她的主要治理思路归纳起来有如下两项:(1)平衡理念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以给社会缓冲的方式来进行变革;(2)建立法律之程序正义并严守之,不允许革命后“翻身奴隶”对“前主人”的法外复仇,并以此回应“女王是新主人”的话语攻势。此两者具体实施起来,皆危难重重。在后面的剧情中,部分性地恢复“习俗”(开放角斗场)导致了丹妮莉丝直接遇险几至丧命;而依法惩罚一个首义的翻身奴隶之法外行刑,则导致了一度丧失前奴隶们之拥护。在剧作者们对剧情的设定(此时《权力的游戏》已极大地偏离原著)中,丹妮莉丝在得到渡海流亡而来的提利昂·兰尼斯特的辅佐后,理念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达到最佳交融状态。提利昂深知权力需要“好的叙事”来支撑,而丹妮莉丝对手们采用的故事相当有力量——“反抗异邦入侵者”。提利昂献计利用宗教(信仰“光之王”的教士们)来宣扬女王(“神选之人,从烈火中重生,来再造世界”),收获了良好效果。最后经过多年治理,一个稳定的非奴隶制的新秩序,终于在奴隶湾建立了起来,丹妮莉丝亦亲自将“奴隶湾”改名“龙湾”。《权力的游戏》第六季终,取得稳定治理的丹妮莉丝,终于带领大军航向维斯特洛。
丹妮莉丝这条故事线,可谓是电视剧对原著改编最重的部分,甚至遭到了粉丝们的如下抗议:“把龙母硬改成了改天换地解放劳苦人民的革命派。其剧情走向之幼稚可笑,可以说是脱离了‘权力游戏’的精髓。”②alienbat.<http://www.zhihu.com/question/47434083/answer/106382728>(accessed 24 august2016).然而,恰恰是电视剧,越出马基雅维利政治(“权力游戏”)而触及革命政治,尤其是“革命的第二天”问题。丹妮莉丝在奴隶湾的艰难处境昭示出理念与治理并非一事,绝无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革命”)。革命本身总是暴力性的,对于之前的既存秩序,带来的总是混乱乃至暴乱。革命“成功”所获致的,实际上是一种暂时性的“打开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走向任何方向。相当多的时候革命恰恰会导致“从坏到更坏”(from bad to worse):革命往往肇因于一种非常糟糕的现状,但却没有任何力量(如某种自然形而上学或历史形而上学力量)保证它所形成的“新秩序”不会比原先更糟!
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并不一定带来真正解放。革命的重要性,就是在于它打开了一个——借用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术语——“制序”(ordering)的时刻。制序和秩序(order)构成对立,是后者之前或之后的关键时刻。这个短暂性的时刻之所以关键,盖因正是制序决定秩序而不是相反。制序就是革命之后的立宪(constituting)时刻——构建共同体的关键时刻。在我们历史教科书上“革命派”与“立宪派”总是作为政治对立面而出现,然而革命和立宪恰恰不能分作“两派”,只有当两者联结在一起时,革命才不会沦为纯粹的暴力行动。因此,革命的第二天,比革命本身更重要。
我们看到,丹妮莉丝在制序上的实际作为仍然有限。马克思对何以如此提供了洞见:根据其政治经济学分析,只有当既有生产资料占有模式成为遏制生产力发展的阻力时,革命才会带来真正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之更新。在这个意义上,丹妮莉丝革命是理念主义的,而非唯物主义的。这就注定其困难不在于粉碎镣铐,而在于持久地保持无镣铐的状态(真正的解放)。丹妮莉丝仅凭个人一己所持之理念,无从在制序层面上开辟出真正的制度创新。我们这个世界里,追求平等与解放的激进实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斯巴达克斯起义,然而即便起义成功,其胜利果实也无法持久。缺少真正的制度更新和社会结构的有效重组,解放之后就会发生“自由人的自愿做奴隶”——获得解放的奴隶重新自愿返回原先受奴役状态,只因该社会组织方式不但熟悉,而且可操作。解放所面临的关键难题在于:被解放者既需要新的生活意义,也需要切实具化解放目标的新的生活方式,前者涉及理念层面的“启蒙”,而后者则由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之更新来提供保证。故此,真正的挑战,永远发生在“粉碎镣铐者”成为制序者/治理者(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这是丹妮莉丝这条线的精彩所在。
尾声:即将到来的“冰与火之歌”
可见,就政治哲学而言,《权力的游戏》至少提供了三个丰富的维度:马基雅维利政治(现实主义政治)、神权政治(原教旨主义政治)、革命政治(理念主义政治)。目前《权力的游戏》共播完了六季,根据HBO官方讯息透露,该剧制作与投资方还会制作两季(但每季长度有所缩短)。在第六季终,我们看到维斯特洛大陆地平线上同时出现了两个相对“正面”的政治力量,来对抗自我加冕的瑟曦女王所代表的既有秩序:从东边来的丹妮莉丝(“粉碎镣铐者”)和自北方南下的琼恩·雪诺(新晋“北境之王”)。“冰与火之歌”的主题至此也终于清晰。
这两个至今还未在“权力的游戏”里“领便当”的角色,有两个共同之处(除了剧情揭示他们都有坦格利安血脉)。第一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在各自冒险中发展出了独特的政治思路。丹妮莉丝提出了那个平行世界中没有人提出并坚持到底的平等与解放的理念。而琼恩亦做了一件整个维斯特洛大陆没有人会去提出并贯彻之事:平息长城两边数千年的敌对。数千年血债恨仇,怎么可能化解得了?做成了这件事,当然便成为古往今来一等一的大人物。琼恩的政治智慧,是用“外敌”来联合仇敌与化解宿怨(这个智慧继承自“塞外之王”曼斯·雷德)。人与“非人”(异鬼/死者军团)之争有效地转换“维度”,使得原先千年对垒变成“同室”操戈。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关于外星“异形”入侵地球的想象(近几十年有大量此类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小说),亦代表了此种转换“维度”引入“外敌”之琼恩式思路。各种民族主义话语,也经常熟练操持此种政治智慧,来构建与强化“民族-国家”之凝聚力。这个进路如果操作得当,甚至不需要“外敌”之真实存在,想象性-虚构性的“外敌”同样可以达到效果。[6]
当然,琼恩的政治思路在具体实践层面上仍是困难重重:长城里外之仇恨深如血海,琼恩这个有荣誉感(归功于奈德·史塔克的教育)但缺谋少智的“私生子”,最后竟然成功地做到让“野人”与北境贵族并肩作战(对战的不是异鬼而是盘踞在临冬城的史塔克家族仇人拉姆斯·波顿)。这,就引出丹妮莉丝和琼恩第二个相似之处:他们都是靠一路开了魔法“外挂”(龙、复活术……)才没有早早地“领了便当”。该剧隐藏至深的“主角光环”随着“冰”与“火”这两个隐喻的清晰化,还是被显现了出来。这亦反过来让我们看到:“冰”(用异鬼来联合)与“火”(用解放为号召)这两条路都绝不好走,在现实政治世界里实践起来都是九死一生。
从支配性的“权力的游戏”,到从世界边隙处坚韧刺出来的“冰与火之歌”,最后维斯特洛大陆会展现出怎样的政治景象,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一起拭目以待。
[1]JoelWilliams.Mainstream finally believes fantasy fans[EB/OL].(2012-03-30)[2016-08-24].http://geekout.blogs.cnn.com/2012/03/30/mainstream-finally-believes-fantasy-fans/.
[2]James Hibberd.HBO:Game of Thrones’piracy is a compliment[EB/OL].(2013-03-31)[2016-08-24].Entertainment Weekly.http://www.ew.com/article/2013/03/31/hbo-thrones-piracy.
[3]SlavojŽižek.Looking Awry: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M].London:MIT Press,1991.
[4]Valar Morghulis:An illustrated guide to all 704 deaths in“Game of Thrones”[EB/OL].(2016-04-04)[2016-08-24].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entertainment/game-of-thrones/.
[5]Leo Strauss.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M]//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84-89.
[6]Guanjun Wu.A(Psycho)Analysis of China’s New Nationalism[M]//Leigh Jenco.Chinese Thought as Global Theory:Diversify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16:101-132.
Machiavellian Politics and Its Radical Excesses:Game of Throne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WU Guan-jun
(Department of Politic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Having received 204 industry awards and 581 nominations,Game of Thrones indeed is themost acclaimed American TV series of our time.Enshrouded with high-cost exquisite production and fantastic construction,the drama entails profundity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embodied in three keymotifs ofmodern politics.The first one is the demoralized Machiavellian politics,which reduces political issues into technical ones.It is the dominantmode ofmodern politics,whose excesses constitute the other two motifs of the show.They are:(a)theocratic politics in secular societies,whose paradox is that it is the extremely secular order that nurtures radical fundamentalism;(b)revolutionary politics that overthrows the“old order”,with the“next-day-afterrevolution”issue being its severest challenge(i.e.how to ensure an authentic emancipation).As a fantasy drama,Game of Thrones is nothing less than a“(hyper)real representation”of today’s political world.
Game of Thrones;Machiavelli;theocracy;revolution;ordering
J912;D0-02
A
1007-6522(2017)01-0065-12
10.3969/j.issn 1007-6522.2017.01.006
(责任编辑:李孝弟)
2016-08-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3CZX059)
吴冠军(1976- ),男,江苏吴县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