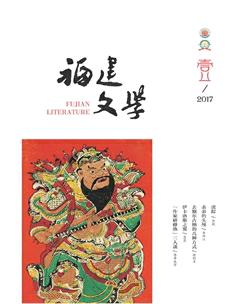这一杯苦涩的咖啡
刘登翰

一缕浓浓的咖啡的焦香味,越过岁月的蒙尘,沉沉地坠落在我的心中。
这是20多年前的一次偶遇。为了追寻一首民间流传的长篇说唱《过番歌》,我们来到这座叫作善坛的闽南山村。闽南濒海,但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听到涛声,像我们现在正要进入的这座村子,就深藏在一片大山之中。尽管山路崎岖,百多年来,仍有一条曲曲折折的山路,把山里人引向大海,引向那个凝结了我们几辈先人心魂足迹的渺渺的异国他邦。
我们已经在这片山海相间的闽南土地上,流连了半个多月。我们走进一座村子又一座村子,在榕须纷拂的晒谷珵,在青瓦红砖的农家大厝,一曲又一曲地听着乡间老人为我们演唱那些如晨霜夜露般即将消失的过番歌谣。他们互相提醒着,订正着,补充着,像咀嚼着自己生命曾经的每一个细节,一首又一首地把这些流传了几代人含着辛酸和苦涩的谣曲,从岁月的深处挖掘出来,曝晒在今日榕荫下斑驳的阳光中。
半个多月,我们就沉浸在这种如梦如幻的往昔追寻中。
这次寻访,源自于一脉遥远的因缘。20世纪60年代,一位法国的青年汉学家施博尓来到台湾做道教的科仪研究。他的有心让他走遍大半个台湾,并收集了大量流传于民间的歌仔册唱本。他在《台湾风物》上发表了一篇《五百旧本歌仔册目录》,引起台湾学界的注意,研究歌仔册便从寂寞中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由厦门会文堂刻印于清末民初、署名“南安江湖客辑”的300多行唱本《新刻过番歌》,就是其中的一种。施博尔回到法国,将这部用闽南方言写成的长篇说唱,介绍给专事研究东南亚文化的同事、法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苏尔梦教授和她的先生、法国远东学院院长龙巴尔教授。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以18世纪贵州夜郎国作为学位论文的苏尔梦和她的夫婿龙巴尓,携带这部唱本,来到福建社会科学院寻求翻译。因缘际会,我有幸接下这份工作,并开启了我后来关于过番歌资料的捜集和研究——此是后话。1989年8、9月间的这次闽南之行,便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一行——一对法国夫妇和一个闽南汉子,穿梭在20世纪80年代还少有异邦人迹的闽南乡间小道,自然惹人眼目。龙巴尔本有几分贵族血统,但他一身牛仔加衬衫的打扮,却也朴素平实,只有他衬衫领口间常围着的一条绸质彩色围巾,才透出几分法国男人的潇洒浪漫;自称是农村出身的苏尔梦,在印度尼西亚住过几年,最为适应这个环境,有时甚至还赤著脚和尾随的孩子打闹。只是连着十几天整日泡在闽南铁观音醇厚的茶香里,开头还不断称赞,渐渐却显出有点不适,私底下悄悄地说:如果有一杯咖啡就好……
我们最先来到南安县,这是施博尔收集的《新刻过番歌》的出产地。这首长篇说唱描述一位破产农民迫于生计漂泊南洋的故事。故乡难离亲情难却,他一步一回头地循着由南安至厦门洋船之所经路线溪尾——岭头——官桥——安平,叙述沿途景致,唱出心中的不舍、无奈和茫然;七天七夜大洋波涛的喧吼,将这个孤独无助的落番者,送到举目无亲的异国他邦。人地的生疏和谋生的维艰,让他尝尽了更甚于大洋波涛的起落人生和命运波折。无尽的乡思之苦和现实的谋生之难,终于让他悟出了“劝恁这厝那可度,番平千万不通行”。“过番歌”保留下万千蹈海落番者的一份失败的人生记忆,是表面敷着金光的“番客伯”们背后都曾经历过的那份酸辛。它在18、19世纪以长长短短的歌谣和不断衍生的异本,在民间广泛流传,正是那段历史夕照斜阳般即将退去的一个证明。
当一拨又一拨老人围坐在月色皎皎的晒谷埕上,或者红砖大厅摆置祖宗牌位的香案前,用苏武牧羊调、孟姜女哭长城调或者歌仔戏的杂念调,断续地哼着这首传唱百年的古旧谣曲时,他们幽幽的眼神和苍凉的声音,令人难忘。就是在这样的座谈中,一位从安溪卖茶到南安的老人不经意地说起,安溪也有一首《过番歌》,小时候他听过,比南安这首还长,是从安溪一路唱到南洋去的。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正是这不经意的一说,让我们一路从南安追踪到安溪的善坛来。
善坛在上安溪,是个山区。我们走在村中,总感到脚下不断在上山下山。闽南人下南洋,应当是从靠海的人家开始。濒海的人生,习惯了波荡涛涌,由近海捕捞、养殖走向远海经营,乃至落番谋生,都顺乎自然。然而当这种越洋走海,发展向深深的内山,成为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潮流,可见为命运驱遣的人生推力,有多么强大。深藏大山之中的善坛,变成了著名的“侨乡”,这背后藏着多少辛酸和无奈,只有这一命运的亲历者才能体味。
七八位老人应邀来到村中的一座小楼。底层还堆着刚收割的稻子,溢满了庄稼的清香;楼上是一个敞开的厅屋,像是昔日留下的村委会办公的地方,四壁还留着残破的标语,如今成了老人闲聚和年轻人玩乐的场所。几位老人都有过过番的经历,大约也都像《过番歌》的主人公那样,饱尝了谋生的艰难和乡思之苦,才毅然返回家乡。他们对这首流传在安溪的四百余行的《过番歌》十分熟悉,仿佛一句句唱的都是自己。唱词中有期待也有失望,但更多的是苦涩。他们沉浸在回忆之中的那种五味杂陈的神情,深深感染了我们。曾经在印度尼西亚三年采录华人寺庙和墓志碑铭的苏尔梦,有着特别强烈的感受。华人谋生异邦,并非全都落荒而逃。少数侥幸获得成功的人士,他们创业发家的传奇,大多留在传说和故事里;而铭刻在更贴近百姓人心的民间谣曲,表达的几乎全是伤心、悔恨和苦痛。历史将怎样看待这份沉在底层的民间记忆,全面而正确来讲述这个被表面金光敷满了的过番故事?
这个座谈会实际上是个采风会,虽然与会者没有一个能够完整地唱完这首长篇歌谣,但他们互相提醒、补充,终于能把400多行唱词回忆得八九不离十。特别引起我们极大兴趣的是唱词的最后两句:“要知此歌谁人编,去问善坛钟金仙。”
历来民间歌谣、特别是长篇说唱,都是在流传中经不同传唱者不断地丰富、补充、修正而最后完成的集体创作,很难像文人作品那样有专属的作者。那么这位被明白写进唱词里的“钟金仙”(“仙”是一种尊称),究竟是谁呢?是这部长篇歌谣的最初创作者,还是在它的流传成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传唱者?
钟金确有其人。一位也在关注这部歌谣的中学老师告诉我们:钟金,安溪善坛人,1879年生。小时读过6年私塾,识文断字。22岁那年迫于生计,辞别双亲和新婚的妻子,過番来到当时尚属马来亚的实叻(新加坡)和槟榔屿,当过“龟里”(苦力),起早摸黑扛木炭、背米包,历尽艰辛。几年后忍不住乡思之苦,两手空空返回家乡。据说他返乡之后常常编歌劝人:“番平好趁(赚)是无影,劝你只路呣窗行(不可行)。” 他特别喜欢哼着这首《过番歌》,一段一段地教给乡亲们演唱,引起许多同是过番者和他们亲人的共鸣,每每噙泪唱至夜半还不舍散去。钟金的经历和《过番歌》所唱的相似,歌中所述的过番路线,就是从善坛的土塘出发,经坂头、龙门、东岭到厦门搭船,这是所有过番者三步一回头留恋不舍的必经路线。它成为肯定钟金是这首《过番歌》作者的重要证据之一。然而唱词最后两句所说的 “要知此歌谁人编,去问善坛钟金仙”是什么意思?已于20世纪30年代作古了的钟金老人,会怎样回答呢?
这是我们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疑问。
有幸的是这位中学老师告诉我们,钟金还有子裔留在善坛。这个骤来的消息,让我们在欣喜之中决定立即前去拜访,或许从这位钟氏后人身上还能寻得一点线索。
翻过一道坡坎,眼前一幢经过修葺改建的传统老厝,红砖铺地,青石砌墙,在一片土屋中显得特别精神。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客气地把我们迎进门来,只见天井后的一进大厅,撤走了香案摆上沙发茶几,俨然成了中西合璧的客厅。同行的老师介绍说这就是当年钟金的孙子。老人身体硬朗,言谈举止可以看出是经过世面的。我们说明了来意,他却露出一脸茫然。他听说过自己有一位会唱歌仔的祖父,却无缘聆听祖父的歌唱,也未曾从父亲的手上接过祖父遗下的一纸半页歌仔册之类的家传。倒是秉承着祖辈的传统,祖孙三代都曾经过番到了南洋。尽管祖父屡再编歌劝世,莫去南洋,但抵不住命运的驱遣,他们还是在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的无望中走向大海。略有不同的是,父祖两代都只在南洋浅尝辄止地待了三五年,唯他这辈一去三四十年。他当过苦力扛过麻包,在庄园割过橡胶种过咖啡,还在锡山里采过矿。在度过了最初的难关之后小有积蓄,便开店学做生意。他从实叻到马六甲和槟榔屿,也从马来亚来到印度尼西亚。他期待事业能有起色,光宗耀祖回到家乡改变父祖辈的命运。然而不幸却遇到20世纪6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大排华,店铺被烧了,财产被抢了,幸好祖国派船把他们接回故乡。海外拼搏数十年依然两手空空,到了晚年他常常恍惚:该诅咒的是命运吗?
我们一时无言,只有氤氲的茶香在空旷的厅屋飘袅。老人喝不惯时下流行的清香铁观音,只喝传统制法的老丛水仙,用一把铁壶在炭炉上烧水,塞得满满的紫砂壶里,倒出来的茶汁浓似酱油,入口的苦涩绝非寻常茶客所能接受。老人不断添水,我也频频举盏,唯有龙巴尓和苏尔梦,只是礼貌地抬抬手,并不真喝。这情景让老人看到了,“哦,这里还有两位法国朋友呢!我们改喝咖啡吧,我有上好的印度尼西亚‘猫屎,上个月朋友才从苏门答腊专门捎来的。”
于是重整杯盘,老人端出一套镶着金边的精美咖啡具,拿出包装奢华注入氮气以防止氧化的咖啡豆,熟练地研磨起来。这种“猫屎”咖啡是产于苏门答腊的一种麝香猫,吃下新鲜多汁的红色咖啡果,经肠道发酵而重新排泄出来的内核坚果,通过繁复的清洗加工制作而成。它特殊的浓郁香味,曾经是印度尼西亚进呈荷兰王室的贡品,至今仍是世上最为昂贵的咖啡。随着老人研磨的沙沙声,一缕缕香气已开始飘溢出来。望着这香气弥漫的偌大一落大厝,我们信口问道:“你孩子呢,没和你们住在一起?”
老人“唉”了声:“年轻人,住不惯乡下喽!”接着又半是感叹半是欢喜地说,“这小子,命好,不像我们。八九岁跟我从印度尼西亚因排华回来,在国内读的书。20多岁,正赶上开放,便像脱缰的野马,拿着安溪的茶叶南北乱闯。现在总算安定了,在北京开了间小公司,专卖安溪的乌龙茶和德化的牙白瓷。家搬到县城去了,置了楼,说是方便采购。不过还算有孝,找了个远房亲戚来照料我的生活,三天两头一通电话,十天半月回来一趟。我这日子过得安生!”
壸里的水烧得“咕嘟嘟”响。“猫屎”咖啡的冲泡规矩严谨而繁多,要有专用的虹吸式塞风壸,水要沸腾1分45秒至2分钟,温度达到96摄氏度,水压9一10atm,才移开火源,用冰湿毛巾反复擦拭咖啡壶底,让水温急速下降,表面呈现出金黄色的绵细泡沫,不能加糖也不能加奶,还不许用汤匙搅拌……老人细细地说道,一丝不苟地操作,仿佛他正在创作一件精美的艺术品,面对自己生命的一件杰作。
一股浓郁的咖啡的焦香在厅屋里回荡。我们端起杯子浅斟一口,入喉苦涩无比,瞬间一种特殊的芳香穿透全身,唇齿间生出薄荷般的甘爽。老人眯着眼,陶醉在自己的杰作之中。我们也醉了,不知是因这咖啡,还是为这老人。
这一杯苦涩的咖啡,喝到这里,才品出了一点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