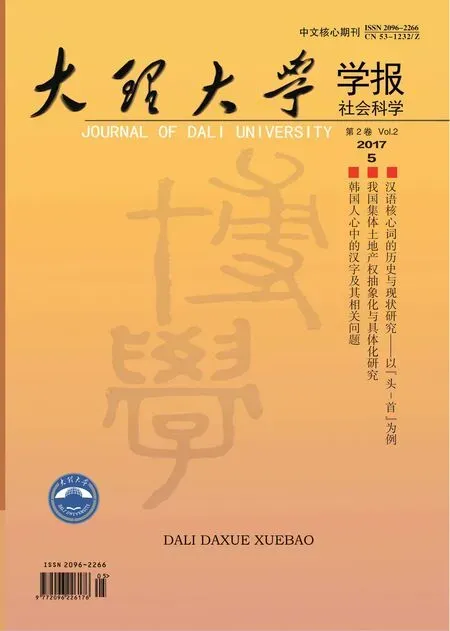民族宗教学视域下的蒙古族民族与宗教关系探究
张玉皎
(大理大学学报编辑部,云南大理671003)
民族宗教学视域下的蒙古族民族与宗教关系探究
张玉皎
(大理大学学报编辑部,云南大理671003)
蒙古族的血统追寻、民族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民族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宗教的参与,蒙古族自然崇拜、灵魂观念、祖先崇拜、萨满教、喇嘛教等宗教思想也伴随着蒙古族的形成、发展应运而生,蒙古族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关系是民族宗教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民族宗教学;蒙古族;民族宗教关系
民族发生学上狭义的民族,“是在原始社会末期或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形成的,国家的产生则是它形成的标志”〔1〕。民族的出现比宗教晚得多,但它的前身——氏族,则是与宗教同样古老。宗教伴随着氏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原始先民将接触到的事物都加以超人化、神秘化,造出各种神灵,对之敬畏崇拜。随着氏族联合成部落,部落演化成民族,宗教的神灵也相应地由各氏族的祖先崇拜发展为全民族的民族之神;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多神崇拜逐渐走向一神(至上神)崇拜,神权为君权提供了信仰上的支持。民族宗教学的创始人牟钟鉴先生说:“从氏族到民族与从氏族宗教到民族宗教是同步的。最早的民族文化是宗教文化。”〔2〕在蒙古族形成的过程中,宗教的作用不可小觑,在血统的追寻、民族的统一、民族国家的稳定及民族文化的形成方面,都离不开宗教的参与,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关系是蒙古族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一、血统之源——远祖崇拜
蒙古族的血统之源,要追溯到原始氏族社会时期,那时的蒙古人尚未形成蒙古民族的概念,各自以氏族、部落的形式活动于广袤的大草原。在远古时代的蒙古社会中,灵魂观念已经盛行,原始蒙古人将所接触到的事物看成有“精灵”存在其中,由想象、类比而概括为天神、日神、月神、火神等,从而产生了蒙古族原始的萨满教。随着萨满教的形成、发展,灵魂观念进一步复杂化,其功能也多样化,相应的祭祀活动也很丰富,但重要的祭祀活动都是在部落内举行,排斥外种(姓)人员参与。
随着灵魂观念的发展,蒙古族先民把对他们有影响的灵魂成为“翁昆”。这种灵魂观认为人死后,翁昆与氏族部落仍维系着一定的关系,它会暗中监视,并参与人的活动。每一个部族都有自己特定的神灵,他们认为这些神灵与自己保持着某种近乎于“血缘”的关系,负责他们的福祉。能赐福庇佑本氏族人生活平安、生产丰收、诸事顺遂的翁昆,叫善翁昆,是氏族部落的保护神。常作祟、降祸于人的翁昆称为恶翁昆。因此,蒙古族先民“以木或毡制成偶像其名曰Orgoh翁昆,悬于帐壁,对之礼拜”〔3〕30。善与恶的划分标准,在古代社会完全是根据部族的利益确定的,本部族的神灵是光明之神,是善神,而其他部族的神则毫无疑义地被视为恶神。如哈答斤人将阿答腾格里奉为天父,而布里亚特部则将其视为恶神;哈答斤人认为外姓氏的人要成为他们的媳妇或女婿,首先必须祭祀阿答腾格里神,表示忠于哈答斤人,否则会招来灾祸〔4〕。由此可见,此时在原始蒙古社会中,各氏族、部落之间的区分是很明显的,不但有仅限于本氏族内部人员参加的祭祀活动,而且祭祀的神灵也因氏族不同而各异,神灵的善恶标准完全根据氏族利益确定,尚未形成各氏族公认的神灵。
随着家长权力的增强、扩大,生前具有组织和领导才能、出众的智慧和勇敢无畏的品格,并在生产和战争中对本氏族部落作出了许多贡献的头领,死后就受到长久的怀念,其灵魂从众多的灵魂中上升为祖先神,所谓“盖汝乞求百姓灵神来告之也”〔5〕28。《蒙古秘史》中也有俺巴孩合罕之妃斡儿伯、莎合台二人,往行祭祀的记事〔5〕33。这表明,各蒙古氏族先民已将祖先的灵魂当作神灵来崇拜了。在长期的祭祀祖先的过程中,血亲观念逐渐形成,每一蒙古氏族的人对内外都称自己是某某氏族(牙素特恩)的人,“蒙古氏族(斡孛黑)是一个共同祖先(额卜格)的子孙,是同一族(牙孙)的亲属”〔6〕。
私有制的产生特别是阶级的产生,对祖先崇拜的内容产生了影响。父系氏族取代母系氏族后,强有力的武力掠夺使一部分人成为统治阶层,相应地,萨满教的神灵也出现了等级化。蒙古萨满教的高级神灵都冠以腾格里(天)的称号。“有扎牙哈腾格里是命运之神,能保护牲畜和财产。苏尔得腾格里是人民和军队的保护神,也成战旗之神,出征要祭祀它。基萨罕腾格里是胜利之神,保佑战士凯旋。巴图尔腾格里是勇敢之神,给人勇气。岱青腾格里是战神,用俘虏来祭祀战神。”〔6〕这些腾格里神统一归天主霍尔木斯塔腾格里领导。霍尔木斯塔腾格里也可以称为天父。神灵权力统一于霍尔木斯塔腾格里无形中削弱了原有意义上的祖先神灵的势力。这样一来,出现了各氏族共同认可的、超越了氏族祖先的民族之神、血统之源——腾格里(天)。当然,承认腾格里神一统天下的蒙古人并没有放弃祖先崇拜,《出使蒙古记》记载,他们也相信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上帝),接着记载妇女们制作很多神偶。表面看似乎是多神和一神之间的不统一,其实这反映出了一神是多神抽象化的表现,可以说,腾格里(天)的产生是祖先崇拜达到极限的表现。而在萨满教由多神崇拜逐渐走向一神崇拜的过程中,草原上分散的蒙古氏族部落也逐渐走向统一的蒙古民族。
二、统一之基——腾格里(天)崇拜和天命观念
公元8世纪至13世纪中叶,蒙古族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蒙古社会由原始氏族制转变为奴隶制,经由忽图剌汗至成吉思汗时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社会处于急剧变革的时期,蒙古汗国的建立使蒙古族雄踞在大漠南北,屹立于中国的北部边疆。这一时期的腾格里(天)崇拜和天命观念,可谓为蒙古族的崛起与统一提供了信仰上的支持。
古代蒙古族素有拜天之俗。“鞑靼民族之信仰与迷信……皆承认有一主宰,与天合名之曰腾格里。”〔3〕39他们认为自己民族的祖先就是奉天命而生的。“奉天命而生孛儿帖赤那,其妻豁埃马阑勒,渡腾汲思而来,营于斡难河之下不尔罕哈勒敦,而生者巴塔赤罕也。”〔5〕1这就是说,成吉思汗的祖先是奉天命而生的,是天赐给人间,代表天的人。这种奉天命而生的思想,为蒙古的最高统治者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阿兰豁阿“感光生子”也是蒙古汗权政治思想和“天”观念相结合的有力说明。阿兰豁阿是成吉思汗十一世祖朵奔蔑儿干之妻,她的丈夫早年去世,而很长时间后她却连续怀孕生下三子,在兄弟和丈夫族人的责难下,她说:“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天窗门额明处入来,将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子里去时节,随日月的光。……这般看来,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那时才知道也者。”〔5〕21这可以看作蒙古社会“汗权天授”观念的理论来源,大汗权位,是由天来安排的,这就为成吉思汗“一统之制”的统一观打下了基础。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之后,他说:“赖长生天之力,得天地之赞助,而匡普天下之百姓,俾入我一统之制矣。”〔5〕248而“天无二日,地无二罕”的思想也是这种国家意识的表现。由此可见,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的基础上形成的天神(至上神)崇拜,为民族国家的出现提供信仰上的合法性支持。为蒙古族统一中国、建立元朝奠定了理论上、信仰上的基础。
三、治国之策——至诚应天和教权并行思想
从13世纪下半叶至14世纪下半叶,蒙古族统一中国,建立元朝。从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开始,蒙古族社会的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政治哲学,围绕如何治理国家而展开。忽必烈提出“至诚应天”观,认为只有对天忠诚,给民众带来实惠,就会得到天地和列祖列宗的保佑,即“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世祖二》,《元史》卷五)。“诚”不是一般的诚,必须是“至诚”,唯有“至诚”,即最为忠诚、极为诚心才能应天,才能理解“天意”,甚至代表“天”的意志。忽必烈显然把自己当作“至诚”者。从理论上看,“天人关系”是个古老的哲学问题,“诚”的思想并非忽必烈首创,在成吉思汗时代,“诚”“以诚配天”等概念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它们的形式和内容还是比较简朴的。到了元代,忽必烈不满足停留在简朴水平之上的理论,而是用“至诚应天”取而代之。人在天的面前是否有主动性,还是人的作用大于天呢?忽必烈这里强调以“至诚”去“应天”,给予人的作用以应有的地位。从表面上看,人至少可以与天平起平坐;但从深层次看,忽必烈提高了人在天面前的作用。用“实惠”去“拯民”,更是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在实践上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丰富和补充。而这种提高人的作用、以人为本的思想,为元朝的宗教政策打下了基础。在蒙古族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的思想中,充满了重人事的入世思想。元朝采取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萨满教五教并存的政策,允许各民族宗教信仰自由,这对维护元朝统治的稳定及为以后各朝制定宗教政策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元朝,喇嘛教在蒙古草原逐渐传播开来,佛教思想在蒙古族的意识形态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关于如何看待国家政权与宗教的关系,约成书于忽必烈时期的《白史》给出了明确的论证。《白史》又称《十善福经白史》,开篇就说:“尊圣佛教始祖经主喇嘛及大元世尊至权皇帝之经教之律如护身绫结牢不可解,皇权之法如金制镣铐坚不可摧。”〔7〕这里把佛教的“经教之律”比喻为护身绫结,将政府的“皇权之法”比喻为金制镣铐,前者牢不可解,后者坚不可摧。二者之间竞相呼应,又各自成为系统。可见,《白史》已明确将“经教之律”与“皇权之法”看作是并行的,既表现了统治者重视宗教的地位,又说明宗教不可逾越皇权之上,政教两道统一于国君,二者并行而治。这种理性对待各种宗教并兼顾以人为本的思想,维护了元朝的统一和稳定。
四、一佛化万心——“印、藏、蒙同源”和天、佛、汗合一思想
在元朝灭亡以后,退居大漠的蒙古族封建领主相互征伐,各部难于统领,原来至高无上的蒙古族汗徒有虚名,“腾格里”的地位也随之跌落。16世纪宗喀巴创立的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地区,得到蒙古封建领主和百姓的响应。喇嘛教针对萨满教野蛮的殉葬制度,竭力宣扬“不杀生”的思想,并吸取了萨满教中与喇嘛教不相抵触的祭山、水、火等传统仪式,因此很快适应了蒙古社会环境,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印、藏、蒙同源”说流行于世。17世纪以来创作的一批新型的编年史著作,从佛教历史观的立场出发,按照印度——西藏——蒙古王族一脉相承的谱系,使蒙古的封建世俗贵族同佛教联系在一起。《蒙古源流》中,更是将蒙古族族源说成是来自西藏诸王的后裔,西藏诸王则是印度诸王的后裔,而印、藏、蒙王统的始祖是开天辟地的玛哈萨玛迭兰咱汗(大法禅王)。作者也认为蒙、藏、印的诸王是诸佛、菩萨的“化身”,受佛旨降临人间,具有无比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喇嘛教并不否认成吉思汗的博尔济绵氏族祖先孛端察尔是“感光而生”的“天之子”,从而使蒙古族传统的“天”和喇嘛教结合起来,“腾格里”(天)被融入到“空”之中,“空”作为万物之源代替了“腾格里”的作用,它产生地、水、火、风,随后产生须弥山,进而产生世界,有了人类。蒙古诸汗是佛、菩萨的化身,如喇嘛教大师扎巴坚赞说:“此后将有一日,东方之蒙古国帽若栖鹰,靴以猪鼻,屋类木网,彼国额真,乃菩萨化身,名曰阔端可汗,彼将请汝,汝宜远行,汝之禅教大兴彼处。”〔8〕“汗”成了喇嘛教的“佛”和天命论的“天”的结合物,亦即“天、佛、汗合一”说。
“印、藏、蒙同源”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编年史的作者虽承认蒙古诸汗王是“天之子”,但已不愿承认《蒙古秘史》关于苍狼、白鹿为祖先的传说,而是将印度的玛哈萨玛迭兰咱汗视为蒙古族的祖先。这种族源观的变化,说明喇嘛教神学逐渐融合并取代了蒙古传统的天命论。而“天、佛、汗合一”说,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蒙古族内部的民族认同感,加强了蒙、藏、印民族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但也减弱了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的差异。
五、蒙古族的民族宗教关系及意义
(一)蒙古族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民族宗教学的学科成立时间较短,理论体系还有待完备,对于宗教在民族形成、民族演变、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释还需要更多文献资料的支撑和更全面的理论论证。研究以民族为载体的宗教,是民族宗教学的切入点。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蒙古民族与宗教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以开展。
从氏族到民族与从氏族宗教到民族宗教是同步的。氏族是规模较小的血缘集团,民族是若干氏族和部落在增强地缘凝聚力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宗教在蒙古族形成中的作用主要是:其一,超越氏族祖先,寻找民族内各氏族共同认可的英雄祖先,以之为民族之神、血缘之源,形成远祖崇拜的民族认同;其二,图腾从氏族徽号扩大为民族标志,或构建综合图腾以代表民族;其三,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的基础上形成天神(至上神)崇拜,以便为民族国家的出现提供信仰上的合法性和支持;其四,宗教的认同促进民族的认同,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拉近不同民族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宗教的差异也划清民族的差异。
通过梳理并简要论述在蒙古族哲学史上反映出的关于宗教与民族关系的历史进程,不难看出,在蒙古族形成之前,它的前身——蒙古各氏族部落均有自己的信仰,并只在自己氏族内部进行祭祀活动,此时的萨满教也处于多神崇拜的阶段,诸神之间不相隶属,各司其职。当出现腾格里(天)崇拜,萨满教由多神崇拜走向一神崇拜时,说明分散的蒙古氏族部落也逐渐归并形成了蒙古民族。腾格里(天)崇拜是祖先崇拜发展到极致的一种表现,它超越了氏族祖先,成为蒙古族内部各氏族共同认可的血统之源,形成了最初的民族认同,也是蒙古族的民族标志,是蒙古族最早的文化符号。
腾格里(天)崇拜和天命观念为蒙古汗国的统一和稳定提供了信仰上的支持。蒙古汗国建立的时期,也是腾格里(天)崇拜和天命思想流行的时期,阿兰豁阿“感光生子”的事例更说明成吉思汗等统治阶层包括普通百姓在内,都将汗权看作是“天命”所属、极其神圣不可置疑,为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合法性和信仰上的支持,使蒙古族内部更加团结、凝聚于以汗为中心的统治阶层中。
忽必烈时期的至诚应天和教权并行思想,一方面提高了人的作用,增加了以人为本的入世思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宗教的狂热,使统治者对待宗教更加理性,奠定了元朝宗教政策的基本思路。另一方面政教两道并行,统一于国君,维护了元朝政治统治的稳定,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治国经验。
“印、藏、蒙同源”和天、佛、汗合一思想,则体现了宗教的同化作用,佛教成为蒙古民族的精神支柱,但也减弱了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的差异,甚至导致民族“同源”思想的出现。
(二)民族与宗教和谐互动的意义
民族宗教学的核心理念是:族教和谐,多元互补。作为“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民族标识中的重要因素——宗教,维系着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精神家园。宗教可以促进民族融合、交流和社会稳定,也可以造成不同信仰的民族之间、同一民族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相互排斥甚至冲突,更有可能升级为国家之间的矛盾。因此,通过对民族与宗教关系的研究,把握两者之间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内在规律,促进两者的良性互动,从而确立和实践平等对话、共生共荣的现代文明准则,才有助于实现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世界和平的伟大理想。这也是本文的研究旨趣所在。
蒙古族哲学史中所反映出来的宗教与民族的互动关系,是一种良性的互动模式,有利于社会祥和、稳定,有利于民族团结。尽管在蒙古族哲学史中,无神论思想占据了很大的篇幅,成为近代蒙古族哲学思潮的主流。但是在蒙古族哲学的诞生、演变、成熟的过程中,宗教仍起着重要作用,离开了宗教思想,蒙古族哲学似乎无源可循,蒙古族文化更失去了生命。在蒙古民族形成、蒙古汗国的建立、元朝的统一、蒙古民族的文化传统乃至蒙古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或以其神圣性凝聚民族精神、或以其鲜明性指导民族建设、或以其全民性连结民族情感,不论以何种形式,蒙古民族的血液中离不开宗教的浸润。如今实行民族和谐、宗教自由的政策,作为民族文化的各种宗教也都有了合法、平等的地位,会得到越来越健康的发展。蒙古族的民族与宗教的和谐互动,可以为中华民族建立多宗教和谐稳定的体系提供借鉴经验,为中华民族建设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增添光彩。
〔1〕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
〔2〕牟钟鉴.民族宗教学导论〔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2.
〔3〕多桑.多桑蒙古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霍日查巴特尔.哈答斤13阿答天祭祀〔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91-92.
〔5〕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6.
〔6〕蔡志纯,洪用斌,王龙耿.蒙古族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16.
〔7〕鲍音.《十善福经白史》浅译〔J〕.蒙古学情报与资料,1987(2):46-47.
〔8〕沈曾植.蒙古源流笺证:卷二〔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golian Ethnicity and Reli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Religious Studies
Zhang Yujiao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Dali University,Dali,Yunnan 671003,China)
Mongolian descent,national unity,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state an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participation of religion.Mongolian natural worship,soul concept,ancestral worship,shamanism,Lamaism and other religious ideas are accompanied by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ngolian group.The Mongolian ethnic and religious intera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thnic religious theory study.
ethnic religion theory;Mongolian;ethnic and religious relations
B916
A
2096-2266(2017)05-0022-05
10.3969/j.issn.2096-2266.2017.05.004
(责任编辑 张玉皎)
大理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KYBS201633)阶段性成果
2016-12-29
2017-02-24
张玉皎,博士,主要从事佛教女性主义、民族宗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