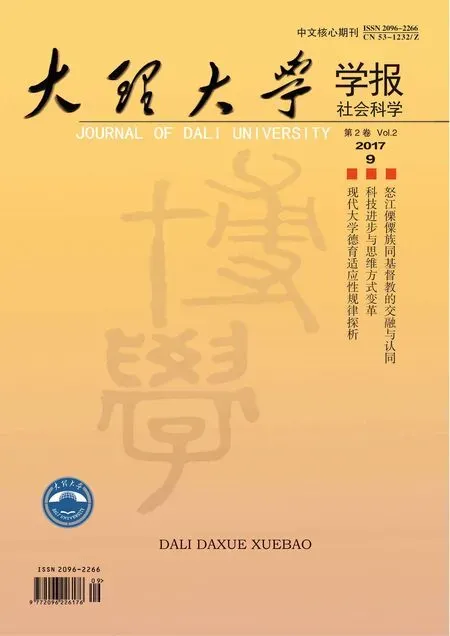怒江傈僳族同基督教的交融与认同
郭硕知
(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云南大理 671003)
怒江傈僳族同基督教的交融与认同
郭硕知
(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云南大理 671003)
我国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生活着傈僳这一古老的民族。大约在一百年以前,迁徙至此的傈僳人开始接受基督教信仰,这种更为精致且增进民族认同的新宗教取代了傈僳人原有的文化解释体系,并且通过神圣的方式建造了以“得救”信仰为核心的新文化底色与社会结构。在当代,这块神圣帷幕的整全性也受到了一些挑战,但这并不足以撼动傈僳族的基本宗教生态。
基督教;傈僳;得救;认同
云南怒江地区沿江生活着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其中傈僳族占大多数,以傈僳语为主要通行语言。傈僳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早在唐代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记载,唐人樊绰《蛮书》中就有“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邛部台登城东西散居”〔1〕的记载。傈僳族人有着自己的创世神话和民族信仰“尼”以及相应的祭司巫师“尼扒”等。自20世纪初由内地会(ChinaInlandMission,CIM)的傅能仁(J.O.Fraser)、神召会(The Assemblies of God)的马导民等传教士传福音至这一地区,基督教逐渐成为了当地各少数民族的主体信仰。据统计,2005年怒江福贡县15 053户57 526人信仰基督教,占总农户数的75%,总人口的69%(资料来源:福贡县宗教事务局2006年填报《福贡县基督教情况统计表》)〔2〕。根据调研结果,近年来,怒江傈僳族信仰情况总体稳定。
笔者曾在福贡、贡山等地实施短期调研。当地的基督教认同不仅在于个体信仰,而且最为明显的标志是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具有很强的本地化倾向。其深层的文化意义在于基督教为怒江傈僳人提供了超验而稳定的意义系统,由此构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这里,基督教为傈僳民族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帷幕。
一、怒江傈僳族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特色
尽管接受了内地会、神召会等不同差会的信仰传统,当代怒江州内傈僳族的信仰方式却相对统一,总体上具有注重行为、强调牧养、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贴合紧密三个特色。
怒江地区的傈僳族基督徒通过日常行为表达自身信仰的虔诚,具有律法主义的倾向。差会神学渊源既对当地的信仰生活进行了塑造,也由此为当地人解决了实际生活问题。在当地影响最大的差会是内地会和神召会。在泸水、碧江(1986年撤县,含知子罗在内的大部分地区划归福贡)一带传教的内地会并非一个严格的教派,而是一个传教组织,它十分注重对其所传基督徒行为的规诫。该会在1909年发起戒毒运动,并根据《圣经》中不准醉酒的戒规,进一步在傈僳人中实行了不准饮酒等措施。主要在福贡、贡山等地传教的神召会强调灵恩、医治与活出圣洁,因此同样十分关注信徒的行为。并且当时傈僳族经济贫穷、文化落后,常过度靡费。针对此种状况,杨思惠夫妇在里吾底村教傈僳人实施蔬菜种植。这些传教士有意识地传授的耕种养殖知识,减少酒类消费等活动,都针对着当地的生活实际,让信仰者通过宗教得到世俗生活中的益处。作为傈僳基督徒基本规范的“十条教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的。马导民等传教士依据“十诫”和当地情况提出了不能吸烟喝酒、不能调戏妇女等个别规定,并逐渐成为传统。20世纪80年代由恢复活动的怒江基督教会正式整理制定了当地的十条教规:不喝酒、不吸烟、不赌钱、不杀人、不买卖婚姻、不骗人、不偷人、不信鬼、讲究清洁卫生、实行一夫一妻等。这一规定已经成为了怒江傈僳基督徒内心中的自我约束,它被当地人认为是必须遵守的取悦上帝的方式,也是瓦枯(傈僳基督徒)自我归类并与酒鬼(非信徒)相区别的标志。
基督教规定的行为准则在周期性的牧养活动中频繁被提及。当地信徒每周三、周六的晚上都要去教堂礼拜,而周日全天都在教堂参与三坛礼拜仪式,全身心投入到宗教神圣氛围之中,这种信仰方式已经成为了当地的生活习惯。不但如此,傈僳教会非常频繁地(几乎每月都有数次在不同的村子)举行信徒或教牧人员的培训,以牧养的方式不断强化信仰共同体。笔者曾经参与观察在福贡县鹿马登乡赤恒底村汪咱村民小组教堂举行的乡级培训。其内容不仅包含《圣经》神学,亦含有对傈僳文字、音乐、舞蹈和行为准则等的训练。并且这种牧养是双向的,教牧人员巩固信徒最终得救的信念,并提醒约束他们的行为。普通信徒则捐赠自己的部分收入给教会,使教牧活动得以持续。由于怒江全州四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信徒捐献的收入有限,马帕、密支帕等教牧人员大部分都非专职,平时也须进行耕种等生产活动。
并且,傈僳族教会注重整体性,完全属于怒江州两会系统,受家庭教会或外来传教的影响非常小。这从侧面反映了傈僳人的基督教宗教认同和本民族认同的交融。在云南各个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中,普遍认为基督教是一种高级文化,并以此作为树立民族自豪感的标志。傈僳人由于日常行为更为注重神圣教规,这种文明生活也得到了当地非信徒一定程度的认同,因此,当地基督教所规定的行为规范,形成了傈僳民族自我归类的范畴。在当地与怒族共同的宗教生活中,基督教以傈僳化的方式呈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福贡地区傈僳族、怒族的‘基督教化’的过程亦是‘傈僳化’的过程,加速和强化了傈僳族宗教文化对怒族同化的趋势。”〔3〕基督教已经成为了傈僳民族的宗教,并通过民族的文化影响力使得当地的宗教认同包含了对傈僳族的民族认同。
二、傈僳族基督教的意义解释体系
文化层面上,人类的生活需要意义系统的建构。在怒江地区,基督教不仅以神学律法的方式塑造傈僳人的生活,而且在傈僳族基督教化过程中也形成了一整套的意义解释体系。
访谈中,当地基督徒表示升入天堂是最终归宿,得救是信仰的核心,而遵守不吸烟、不喝酒,按每周三、四、日三天五次的礼拜等教会的行为规定是得救的必要条件,甚至时时提防,唯恐惹恼上帝而因此失去了上天堂的资格。这种终极得救的渴望深入人心,消弭了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区隔,尽管存在着神圣的时间和空间(礼拜日、教堂等),但是基督教的解释体系却弥散在傈僳族整全而神圣的文化生活之中。
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信仰很少有如怒江傈僳一样生活化的表达,傈僳信徒生活中的每个节点和习惯都被笼罩在宗教的解释之中。当地傈僳族教徒严格恪守礼拜日并认为这既继承了犹太人守安息日(周六)的传统,也是耶稣复活的纪念日(周日),从而将礼拜日定在周日。基督教中耶稣复活意味着赎罪之后的得救,这种必须严守的神圣时间直接表达着傈僳基督徒对复活事件的重复模仿,并巩固了已经成为核心宗教意识的得救信念。
而且由于年老的原生宗教巫师(尼帕)大都已经过世,现在傈僳族的生活方式已经难觅原先民族宗教的痕迹。傈僳基督教的“十条教规”中就有“不拜鬼”的规定,也禁止血祭和传统请尼帕主持并耗费颇多的婚礼等。这不仅体现了神召会等差会重视信徒行为的传统,也在客观上起到了代替原有民族宗教和习俗的效果,使得怒江傈僳族从原有的民族宗教社会完整地进入到了基督教化社会。教会所规定的不吸烟喝酒等行为方式已经成为了傈僳基督徒的标签,而无论是否是信徒,傈僳人大多认为吸烟喝酒是不好的行为,基督教的解释体系已经作为习俗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几乎全部的怒江傈僳族。
实际上傈僳的原生性宗教难以提供统一的民族认同的神圣支点。在信奉基督教以前,傈僳人以万物有灵论的神灵观在不同的村寨崇奉不同的尼(精灵),通过驱鬼、卜卦、血祭、神判等方式表达信仰,而且各个村寨都有各自的原生图腾信仰。“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傈僳族内部还保存着氏族制度的残余,各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名称。傈僳族的氏族图腾名称有虎、熊、猴、羊、蛇、鸟、蜜蜂、荞、麻、菜、竹、霜、犁等20多种。”〔4〕可见,因为没有一个统一全族的高位神出现,信仰组织松散,傈僳族的原始信仰无法构建全族的宗教认同。
傈僳的基督教化不仅在于对当地文化和习俗的改变,更是对原有解释体系和生活神圣性的更替。基督教的傈僳化不仅仅是表象,而且是从一个相对原始的包罗万象的解释系统直接过渡,成为了与原先民族宗教有对应更新关系的民族基督教。作为普世宗教的基督教在怒江的场域下成为了一种新的民族宗教,并以一神教的特性巩固了民族认同。这种新的宗教认同所分享的共同价值取向则由敬畏巫鬼更新为升入天堂的“得救”。
两种宗教的解释性更替,具体体现在医病与神话之中。傈僳族历史上曾流行巫医,它需要以牲畜祭祀鬼神。而当代傈僳教规中强调不拜鬼(鬼指曾经的被祭祀者),并在医术上保留了傈僳的传统医学。当遇到一些疑难杂症之时,除了请傈医治病外,病人家属通常请基督教村长老进行代祷,而痊愈或延长生命的结果通常归功于主的恩赐,并且这往往成为教徒皈依的理由。在治疗手段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傈僳人对疾病痊愈的解释方式产生了变化,这种解释的变化甚至延伸到对民族自身的理解。在询问一些村民傈僳族源时,他们会追溯到《圣经》中诺亚的三个儿子,以此代替了傈僳原有的创世神话、洪水神话等〔5〕。
文化的解释需要语言文字作为载体。1908年进入云南地区传教的傅能仁牧师被认为在20世纪初最早将基督教传入我国傈僳民族,并与范善庆(Herbert Flagg)、巴叔等人共同创制傈僳文,在1919年结束了傈僳族无文字的历史。他们编写了傈僳字典、《基本信仰问答》及《儿童祷告书》等文。傅能仁等传教士用拉丁文的变体创制傈僳文字的主要目的是翻译圣经,因此将许多基督教化的词语注入傈僳的语言之中,比如恩典、救赎、团契、谦卑等。并且在傈僳的传统教育中,教堂学经正是他们掌握文字的最重要途径。这就使傈僳的解释体系中天然带有了基督教的因素。如同“世界”“缘分”等汉语词汇很难脱离佛教的内在精神一样,基督教精神也通过语言文字塑造了傈僳人。并且当地的基督教对于传教的热情并不十分高涨(马帕只在本乡传教),反而更为注重“牧养”本乡教牧人员和信徒等。这些信友的培训学习将傈僳文《圣经》作为教材,这本身也是学习傈僳文字并且巩固文化价值观的过程。
价值观不仅是文化的取向,也左右着社会结构的形成。对得救的共同追求与信仰方式,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认同共同体,由此影响着怒江傈僳族的社会秩序。
三、基督教塑造的社会秩序
怒江傈僳人以替换原生宗教的形式接受了基督教的解释话语。以文化角度分析,这是对生活神圣意义的追求。而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观察,则呈现出意义所带来的秩序。
社会结构的基督教化导致了怒江地区社会样态的整体变革。基督教传入并广布怒江之时与当地傈僳人转入定居并接受民国政府管辖的时间相差无几(1916年设立上帕、知子罗等行政公署,1930年修通了怒江两岸的牛马道)〔6〕。他们基本完成了历史上大规模西迁的流动状态(尽管有的傈僳人在50年代继续西迁至缅甸、泰国)。而在此之前,傈僳族受到藏族和纳西族的排挤从金沙江来到怒江,又在怒江获得怒族和独龙族的认可,从而在怒江取得了主要民族的地位,从此开始了相对稳定的农耕生活并接受了民国政府的管辖。这样的社会变迁是宗教更新的重要因素,英格(J. Milton Yinger)指出:“只有那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主宰自己生命的人们才能够‘担负’得起一神教。”〔7〕人们有了通过生产方式和政治治理等管理自然和社会的手段,从而可以在一些程度上放弃巫术和职能神对社会各个层面神学意义上的严格管理,并接受一神教对社会生活的解释与干预。在怒江定居并取得区域优势的傈僳人已经在这样的程度上主宰了自己的生活,具备了接受一神教的条件。而且基督教这种更为抽象的一神教在传入之初是将上帝作为一种诸神的统摄或者替换,传教士宣扬上帝为万能的神,有病无需杀生祭祀本主,只要祈祷上帝就行,从而将一些巫术、血祭变为祈祷,并逐渐消弭了傈僳地方诸神。傈僳人原生性信仰中30多种“尼”作为互不隶属的掌管自然或人间事物的精灵,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怒江傈僳社会结构的完善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他们不再完全依赖于自然神和职能神的事无巨细,而只需一个更为超越且强有力的上帝来掌管全部事务,并提供一个彼岸世界作为永恒的保证。
这也在生活层面带来了变革。基督教传入前的一些地方志中对傈僳族的社会生活多有贬抑之词,康熙《大理府志》载“(栗粟)骨肉有隙,辄相仇杀,颇为旅患,近稍向化矣”。然而傈僳族基督教要求的不杀人行盗、不沾烟酒、不奉巫鬼等规定明显改善了当地的经济和政治状态,由此带来了信仰的持续发展和民族认同度的提高。经济方面,据云南当地学者介绍,以前有70%左右的粮食用来烧酒,且怒江多山,傈僳人壁耕的作物产量本身不具备可用于产酒的余力。拜巫鬼治病也需要血祭,当地人的猪仔往往养不大就要因祭祀而被宰杀。因此提出了多种生活规范的基督教代替传统生活和祭祀习惯之后,傈僳人节省了大量的食物支出,生存压力变小,得到了生活中实在的好处,提高了生存能力,同时进一步减小了接受基督教的难度。政治方面,基督教不强调民族祖先历史传说,并且吸收了傈僳、怒、汉等民族互为兄弟的故事,使得基督教的信仰记忆成为当地民族认同的集体记忆。与怒族、独龙族等民族共同信仰构筑的认同(同时也有政府强有力的管辖)使当地文化(语言、文字等)依然以傈僳为主,但政治上呈现平等,民族仇杀减少,社会和谐稳定。这样也促进了当地各民族对基督教的接受程度。可以说,基督教通过规范当地教徒的行为,塑造了社会秩序,从而培植出信仰的土壤。
基督教带来的秩序也成为了个人信教的理由之一。据福贡一位民间艺人介绍,他信教之前嗜酒好交,常酒后撒酒疯导致家庭生活不和睦,而信教就不能喝酒,并且也能够以此为由阻止以前的酒友登门。因此基督教成为了他追求生活秩序与和睦家庭的方式。这种秩序也成就了傈僳人基于自己信仰纯粹且生活文明的优越感而来的族群认同。在傈僳本族内部有瓦枯和酒鬼的区别,尽管并不是非基督徒一定嗜酒如命,但是以此区分可见基督教为他们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以具有精神致幻作用的酒作为身份的区别方式,实际上区别的不单是信仰,而是区分其是否在社会秩序之中。这种严格的戒规也导致了傈僳基督教与其他民族或地区信仰基督教方式的区隔,从而体现了自我民族的认同。近乎民族宗教合一的凝聚力是造成傈僳基督教信仰相对封闭的原因之一。它如同一层无形的围墙,成为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使毒品、艾滋病等情况在云南当地的傈僳人中间不至于泛滥。
基督教整全地代替了傈僳传统宗教的解释体系,也重新塑造了傈僳社会的神圣秩序,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固定不变。比如,基督教废除了傈僳“公房”群婚的习俗,并且规定婚姻禁止收送彩礼,从而提高了女性地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傈僳的主内婚姻双方基本不能见面,由村长老与另一方的长老、牧师等相互联系并主持仪式,可以说是教会“包办”婚姻。然而在事实上,自80年代起年轻人有自己的“中秋会”等教会外恋爱渠道(礼仪依然是教会的),而教会包办的婚姻则时常出现男女不相配甚至逃婚的现象。所以现今的傈僳基督教会就改变了直接干预婚姻的做法,赞成教会内自由恋爱,由当事人自行通知长老举行仪式。福贡某马帕甚至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与汉族人(无论是否基督徒)成婚。
在这里,宗教与社会相互塑造,基督教成为了傈僳族的立基(niche)。然而近年来由于怒江乃至全社会的迅速变化,也对当地傈僳人的信仰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挑战。
四、今日之挑战
20世纪90年代至今,傈僳的基督教信仰比例等指标趋于平稳,也基本没有了“恒尼”“斯利匹”等教会内部分裂因素的影响,因而学者们与当地的教牧人员都持傈僳基督教信仰状况稳定的观点。有的当地学者甚至认为如果中国出现一个全民信仰基督教的民族,那就应该是傈僳族。但数据稳定的背后并非意味着毫无危机。
社会流动、心理变化、教会内部的纷争等都是造成宗教不稳定的因素。随着当代的经济发展与交通便利程度的提高,傈僳社会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怒江基督教信仰最为核心的地区福贡曾在21世纪初成为了云南的无毒县,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基督教习俗化的严厉戒规,对吸烟喝酒、婚前性行为等的严格禁止,为傈僳人修造了一座无形的城墙抵御毒品、艾滋病等的泛滥。由于社会在不断发展,傈僳人的经济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入教标志之一的每周三天五次的礼拜活动对于一些人而言成为了一种负担和脱离教会的推力。据福贡一位非信徒农客司机介绍,他本身就没有吸烟喝酒的习惯(家里有基督教渊源),但是自己开车谋生根本没时间去教堂,所以只能不信教。并且随着社会流动的增大,福贡等地傈僳族年轻人有相当一部分外出打工和上学。他们大多原本就接受了基督信仰,因此往往参与所在地的团契,从而部分接受了不同团契和教会的思想,并且因为习俗不同和条件所限也难以完全遵守傈僳基督教的规定。由于各个教会所属宗派和神学理论的区别,进而影响了年轻一代傈僳基督徒对信仰和民族的整体认同。但实际上许多人在回到自己的村寨之后依然回归到傈僳传统的信仰方式之中,民族和家乡的认同以及传统文化的压力成为了抵御分离的有效壁垒。
教会内部的权力之争等也存在着对傈僳信仰结构的挑战。访谈中几乎问到的所有州县教牧人员都认为当地极个别的教职人员存在争权夺利的现象。相互争夺与争讼是对自己诉求的表达,因此在教会内部无论影响大小都至少有信仰之外的诉求,政治和经济因素掺杂其中会让局面更为复杂。这或许与现行体制中教职人员能够更为容易地获得世俗权力与荣誉不无干系。信众的拥戴、两会领袖的突出地位等都可能为个人在社会层面获取名望等政治经济资源,并提供晋升之阶。单一的社会资源获取渠道消弭了傈僳基督教强调的“得救”这样的普遍价值,而有条件的某些宗教领袖由此成为了稀缺社会资源的竞争者。但通过调研也反映出这只是极个别现象,传统的共有的“得救”这一集体资源的分享(并且取之不尽)所带来的认同仍然处于傈僳基督教的主导。
五、结语
上述对传统傈僳基督教稳定性的挑战并不强烈到足以撼动基础的地步。在当代信息化程度发达且地理隔膜不再巨大的世界中,民族、血缘、行为方式等建构和巩固的宗教共同体不可能不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发生一些转变与动摇。传统也会以流动的方式衍进,其间出现的挑战不过是与各种社会文化等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基督教作为文化解释与社会认同的核心不仅在于它对傈僳环境的适应,也同自身神学的完备与包容性相关。这种理论精致的宗教在傈僳人心中是文明的象征,也是一种高尚生活的标志。可以说当代傈僳族及其生活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基督教的重新塑造,他们也在这一塑造过程的场域中促使基督教呈现出本地化的状态。因此,怒江傈僳人的生活依然笼罩在傈僳化了的基督教这一大幕之下。然而没有人完全生活在宗教符号建构的整体意义世界中,大多数人只是在某些时刻寓居于这个世界当中。这层帷幕尽管非常密实,但远非天衣无缝,社会流动与世俗化都在悄然影响着傈僳族的宗教认同。
〔1〕樊绰.云南志校释〔M〕.赵吕普,校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73.
〔2〕高志英.基督教与民族社会文化变迁〔M〕∕∕李志农.全球化背景下的云南文化多样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315.
〔3〕高志英,龚茂莉.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互动:20世纪前半期基督教在福贡傈僳族、怒族地区的发展特点研究〔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9(6):184-190.
〔4〕李月英.云南怒江傈僳族的宗教信仰〔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5):12-16.
〔5〕黄昌莉.从创世神话中探讨傈僳族的远古生活〔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1):107-111.
〔6〕肖迎.怒江地区民族社会发展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151-152.
〔7〕英格.宗教的科学研究〔M〕.金泽,译.刘澎,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30.
Integ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Lisu People with Christianity in Yunnan Nujiang Prefecture
Guo Shuozhi
(Institute of National Culture Research,Dali University,Dali,Yunnan 671003,China)
Lisu people,an ancient ethnic group,resides at the Nujiang Lisu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Yunnan province in China. About one hundred years ago,the Lisu people who had migrated here before began to accept the Christian faith.Christianity,as a new religion which was more delicate and facilitative for Lisu people's ethnic identification,replaced their original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system,and thus,Lisu people have built up a new cultural found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centering on the belief of"salvation"by sacred means.Although in today's world,the wholeness of this religion is confronted with challenges,the basic religious ecology in Lisu people is not shaken.
Christianity;Lisu;salvation;identification
B97
A
2096-2266(2017)09-0001-06
10.3969∕j.issn.2096-2266.2017.09.001
(责任编辑 张玉皎)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宗教认同研究”(13AZJ002)阶段性成果
2017-03-25
2017-04-24
郭硕知,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宗教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