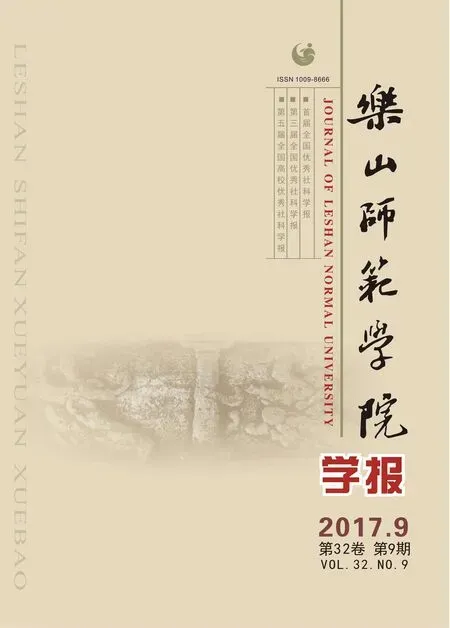《东人诗话》中的“以苏济黄”倾向
马 也,任竞泽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东人诗话》中的“以苏济黄”倾向
马 也,任竞泽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东人诗话》作为朝鲜高丽朝与李朝更替时极具转折意义的诗话,其诗论倾向在深受我国江西诗派影响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高丽朝诗人的创作观,从而形成了在诗歌批评方面的“尊黄”和诗歌创作论方面“崇苏”的不同倾向。更进一步的是,这部诗话在其整体价值追求上表现出了“以苏济黄”的风貌,展现了朝鲜文人作为接受者在面对我国文学作品和理论批评传入时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
《东人诗话》;江西诗派;徐居正;苏轼;黄庭坚
一、“高丽文士专尚东坡”
朝鲜古代诗学从高丽朝后期的12世纪末13世纪初开始接受宋代江西诗派,这是朝鲜第一部诗话《破闲集》作者李仁老生活的时代。[1]然而,也是在这个时期,江西诗派的影响方兴未艾,文人们对苏轼却是情有独钟。由此,这一现象对李朝初期出现的《东人诗话》在创作方面的价值倾向产生了不可否认的重要影响。
(一)高丽朝时期出现的“苏黄”内涵
在高丽朝时期的几部诗话中,笔者发现“苏黄”之称已经开始被朝鲜文人所使用了。然而不同于我国文学史上的“苏黄”并称,朝鲜文人在此时使用“苏黄”之称时并不太关注“苏黄”的不同与对立,几乎只限于对宋朝江西诗派的代称。在《破闲集》和稍后出现的《补闲集》中笔者找到了相关的痕迹:
及至苏黄,则使事益精,逸气横出,琢句之妙可以与少陵並驾。[2]12
近者苏、黄崛起,虽追尚其法,而造语益工,了无斧凿之痕,可谓青于蓝矣。[2]29
李学士眉叟曰:“吾杜门读苏黄两集,然后语遒然韵锵然,得作诗三昧。”[2]89
在上面引用的三则诗话里,我们能够看出,朝鲜文人在高丽后期已经开始接受江西诗派。不过,此时将二者并提,并没有像我国传统理论批评中过多强调二者的差异,在论述时所见到的诸如“使事”“酌句”“造语”“斧凿”等等都是谈江西诗派重视用事和琢炼的情形。但是从三则诗话中所表现出的倾向看,此时诗话中出现的“苏黄”,只是披着江西诗派的外衣,在创作追求上仍然是“崇苏”的。从“逸气横出”,“了无斧凿之痕”到“得作诗三昧”,无不体现出其在创作观念上不只限于“使事”“琢句”,而是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其关注的是诗歌的精神风貌,以及提出“诗家三昧”的陆游所主张的“诗外功夫”,此时的朝鲜文人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精神。
然而,仅从“苏黄”的内涵偏向论述高丽文人的“崇苏”倾向,的确有些过于单薄,朝鲜文人对于苏轼的具体态度又是怎样的呢?于此,笔者在下文将给出高丽诗话以及《东人诗话》中出现的直接论述。
(二)高丽文人“专尚东坡”之风气
据考证,苏轼文集于高丽高宗(1192—1259)时被朝鲜刊行。[3]从《东人诗话》中便能直接找到相关的文字记载:
高丽文士专尚东坡每及第榜出则人曰三十三东坡出矣。[2]185
从徐居正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文人普遍形成了“学苏”的风尚,“三十三东坡”也许是夸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苏轼于高丽后期在朝鲜文人中间的影响之广泛。当时,崔氏武臣政权当政,政治统治处于黑暗时期,文人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甚至一些文人的人生经历与苏轼极为相似,由此也使得高丽文人对苏轼的接受几近情有独钟。从笔者手头的资料来看,高丽文人专尚东坡之风大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东坡人格的尊崇
在《东人诗话》上卷中有这样的一则记载:
东坡平生功名出处自比白香山,牧隐亦尝以东坡自比。熙宁中王安石以新法误天下,东坡有《山村五绝》,有“迩来三月食无盐,过眼青钱转手空”等句,坐议时事谪南荒,谓其诗曰“乌台诗案”。牧隐谪长湍,《寄省郎十首》有“黜僧还恐似王轮,满庭青紫绝无人”等句,为台官所弹,祸且不测,其视乌台诗案,亦无几矣。[2]172
在这则诗话中出现的“牧隐”为高丽后期诗人李穑(1328-1396),其人生经历与东坡极为相似,因其敢于直言,被置于极刑,并被流放,史称“牧隐诗案”。[4]李穑在其诗《山水图.节东坡烟江叠嶂图诗句》中有这样的诗句:“君从何处得,去路无由缘。故人应有招,云散山依然。”这是他变用苏轼诗歌《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而作的。苏轼有“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还君此画三叹息,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之句。[5]195苏轼的这首诗是写于“乌台诗案”之后,虽然悲慨,但却在失意中探寻一种豁达的人生境界。显然,正是李穑敬仰和学习苏轼达观的人格,这才有其变用的这首诗。
2.对苏轼创作观念的接受
对于苏轼的创作风格,高丽文人可谓是推崇备至,在高丽时期的诗话中可以看到一些直接论述,如崔滋的《补闲集》中就有相关的记载:
今观眉叟诗,或有七字五字从《东坡集》来。观文顺公诗,无四五字夺东坡语,其豪迈之气,富赡之体,直与东坡吻合。[2]98
陈补缺读李春卿诗云:“啾啾多言费毫,三尺喙长只自劳。谪仙逸气万象外,一言足倒千诗豪。”吴芮公曰:“逸气一言可得闻乎?”陈曰:“苏子瞻品画云,摩诘得之于象外,笔所未到气已吞。”[2]99
这三则诗话分别是从崇尚苏轼创作风格,追随苏轼进行创作实践以及论述苏轼诗歌创作观念等三方面来表现文人们对苏轼创作风格的钟爱与创作观念的承袭。在论述苏轼创作观念时,朝鲜文人抓住“气”这一文论范畴展开学习与进行诗作批评,对苏轼“了无斧凿之痕”的诗歌风格大力推崇。而且,我们在高丽朝的诗话著作中总能见到文人诸如“率然而作”这样的评价字眼,同时“气”“意”等文论范畴也频频出现。
因此,虽然也有相关的文献记载高丽朝已经开始接受江西诗派的影响,但是此时几乎一边倒向了“学苏”,这一点对李朝初期的文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种风尚也继续沿袭到李朝初期。不过,此后随着我国江西诗派的深入影响,在这部处于历史交替时期的《东人诗话》中的价值风貌已有了鲜明的变化。徐居正在诗论中表现出了很强的学习江西诗派的痕迹。
二、风尚就此一变——徐居正对黄庭坚的诗论承袭
徐居正在诗歌批评中一改高丽朝“专尚东坡”之风气,流露出了很强的“尊黄”意识,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诗应学黄
在徐居正看来,学诗之人在学诗初始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音律词句方面,而像东坡之诗是“非学可到”的,他倡导学诗之人应首先打好基础。在其诗话中有直接的论述:
稼亭、牧隐父子相继中皇元制科,文章动天下,今二集盛行于世。牧隐之于稼亭,犹子美之于审言,子瞻、子由之于老泉,自有家法。评者曰:“牧隐之诗雄豪雅健,天分绝伦,非学可到;稼亭之诗精深平淡,优游不迫,格律精严。”[2]213
在这则诗话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徐居正将高丽朝诗人牧隐比作苏轼,称其“天分绝伦,非学可到”,由此可以看出徐居正并不是完全否定了高丽朝文人的学苏风气,他只是认为东坡之诗充满了天才的想象与创造力,其艺术水平值得尊仰肯定,但对于初学者来说确实非常困难。在其诗话中,还提到宋代王安石学苏轼时终“不能及”的例子:
半山与东坡不相能,然读东坡《雪后》“叉”韵诗,追次至六七篇,终曰:“不可及”。时人服其自知甚明。[2]190
徐居正用“自知甚明”这样似乎是充满嘲讽的语气议论王安石试图“学苏”的做法。他这样去论述也在某种程度上是给当时的朝鲜文人以一种警示。从而,在其诗话著作中便大张旗鼓地讨论江西诗派的种种诗法,企图给后来的学人一种借鉴。黄庭坚所代表的江西诗派的诗歌创作对学诗之人来说是易于掌控的,他说道:“近世学者不学音律,先作乐府,欲为东坡所不能,其为诚斋、后山之罪人明矣。”[2]183
在这三则反例中,我们能鲜明地感受到徐居正对于“苏黄”的不同倾向,他同高丽朝文人一样对苏轼堪称尊崇有加,认为其“不可学”也是“不可及”的,而对传入朝鲜的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则是注重诗法的学习并大力借鉴了黄庭坚为代表的论诗方式,从而让我们已然能初步感受到徐居正“以苏济黄”的理论倾向了。
(二)“不可以辞害意”
徐居正虽然在“学诗”方面强调要先学音律词句,但是他在上卷最开始便强调不能单方面地追求辞藻与炼字,总体上应该以“意”为主,这个主张也证明其在接受江西诗派时深得其旨,并没有走向极端。他在著作中举了这样的例子:
金学士黄元登浮碧楼,见古今题咏,不满其意,旋焚其版,终日凭栏苦吟,只得“长城一面溶溶水,大野东头点点山”之句,意涸痛哭而去。
黄元因为过分注重词句而最后落得“意涸痛哭”的下场,从而以一个反例为后来学人开辟了一条作诗行吟的标准。这一则诗话为其摆出自己鲜明的“不可以辞害意”的立场打开了大门,于是便紧接着有了下一则诗话:
陈司谏“雨余庭院簇霉台,人静柴扉画不开。碧砌落花深一寸,东风吹去又吹来。”砭者曰:“落花称深一寸,似畔于理。”余曰:“赵退庵之‘蒲色青青柳色阴,路上飞花一膝深。’其曰一膝,则又深于一尺矣。况太白诗‘燕山雪花大如席’,又曰‘白发三千丈’”是不可以辞害意,但当意会尔。
由此,徐居正在这部诗话中确立了“以意为主”的理论倾向,即使应该学习黄庭坚一派的诗法,也要强调“意”的重要性,为其在整体诗学追求上打下了理论基础。
(三)作诗不可无来处
对于黄庭坚提出的“脱胎换骨法”,徐居正在这部诗话中采用大量篇幅倡导后人学习使用,同时也将“用事”是否有来处以及精切与否当作了谈论诗歌优劣的标准之一。
一方面,他在几则诗话中非常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这种立场:
古人作诗,无一句无来处。[2]167
诗不蹈袭,古人所难。[2]170
古人诗多用经书语。[2]188
凡诗用事当有来处,苟出己意,语虽工,未免砭者之议。[196]高丽忠宣王入元朝,开万卷堂。一日,王占一联云:“鸡声恰似门前柳。”诸学士问用事来处,王默然。益斋李文忠公从旁即解曰:“吾东人诗有‘屋头初日金鸡唱,恰似垂杨袅袅长’。以鸡声之欢,比柳条之轻织。我殿下之句用是意也。且韩退之《琴诗》曰:‘浮云柳絮无根蒂’,则古人之于声音,亦有以柳絮比之者是矣。”满座称叹。忠宣诗苟无益老之救,则几窘于砭者之锋矣。
徐居正不仅指出“古人”所谓的“无一句无来处”之普遍现象,同时也从反面用高丽忠宣王作诗后不知自己诗句的来处而被嘲讽的例子告诫学人,在作诗时若不关注自己用事的来历,即使做到语意精切,也会成为众人嘲讽的对象,是得不到认可的。
另一方面,徐居正在具体的诗歌批评中广泛使用了这个标准,成为他评诗的手段之一:“余尝爱郑圆齐公枢《读〈中宗纪〉》诗:地下若逢韦处士,帝心还愧点筹无。语虽用唐人‘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之句,点化自妙,真得换骨法。”[2]208在这一则中徐居正将朝鲜文人的诗句与我国唐人诗句作以比较,并用黄庭坚的“换骨法”作以审度,认为这句诗点化自妙。从而表现出了非常强的承袭江西诗派诗法的意识。在这方面,徐居正在这部诗话中所例举的例子很多,大部分是用朝鲜诗句与李白、杜甫、苏轼等大家作以参照,显示出朝鲜文人对我国唐宋诗人的学习是非常深入的。例如:
李文顺平生自谓摆落陈腐,自出机杼,如犯古语,死且避之。然有句云“黄稻日肥鸡鹜喜,碧梧秋老凤凰愁”,用少陵“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之句。[2]170
李政丞混《浮碧楼》诗:“永明寺中僧不见,永明寺前江自流。山空孤塔立庭际,人断小舟横渡头。长天去鸟欲何向,大野东风吹不休。往事微茫问无处,淡烟斜日使人愁。”一句二句本李白“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四句本韦苏州“野渡无人舟自横”,五六句本陈后山“度鸟欲何向,奔云亦自闲”,七八句又本李白“忽为浮云蔽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之句,句句皆有来处,装点自妙,格律自然森严。[2]168从确立学诗与评诗标准,再到批评实践,徐居正在“无一句无来处”这一点上可谓是花了很大的心思。除此之外,他在接受江西诗派的诗法时也将“炼字锻句”推崇到了很高的程度。
(四)炼字锻句
在炼字方面,徐居正直接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凡诗妙在一字,古人以一字为师”。[2]174他在多则诗话中讨论了自己对诗中的某一字到底怎样安置的看法,让我们看到了他在这方面的重视程度。比如:
金直殿久,尝有联云:“驿楼举酒山当席,官渡哦诗雨满船。”卞文肃公季良曰:“当字未稳,宜改临。”金曰:“‘南山当户转分明’当字有来处。”卞曰:“古诗有‘青山临黄河’,如金者岂知临字之妙乎?”金竟不屈,终不能一字相师,义安在乎?然今之评者曰:“临字不如当字之稳。”
在这则诗话中,文人们为了诗句中究竟该用“临”字还是用“当”字争论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在这里徐居正以字是否为“稳”作为判断用字是否贴切的标准,也就是说,用字是否得当主要看是否能恰合语境,对诗句的整体效果有利。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黄庭坚“句中有眼”,“点铁成金”的思想,也能看出徐居正在诗法方面“尊黄”时可以做到灵活有致,不会单独将某一条作为金科玉律。
在句法方面,徐居正强调诗人们应做到对仗,但不能有重叠。他指出“天下无无对之句”[2]189,并举了东坡的“公独未知其趣耳,臣今时复一中之”作为例证之句,认为该诗句为“奇对”。此外,他还认为“句法不当重叠”。[2]194如淮南小词“杜鹃声里斜阳暮”,苏东坡曰:“此词高妙。但既云斜阳,又云暮,重叠也。”
因此,徐居正的“尊黄”意识以“东坡不可及”作为开端,将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诗法作为学习模仿的榜样,从炼字锻句到用事再到脱胎换骨法等方面的研习,不仅体现出朝鲜文人谦卑的学习心态,也体现出他们在面对“苏黄”时灵活变通的态度,从而也为我们探寻徐居正在《东人诗话》中流露出的“东坡情结”敞开了大门。
三、《东人诗话》中的东坡情结
在《东人诗话》中,随处可见的是徐居正对黄庭坚一派诗法的发扬与在批评实践中的运用,而笔者在上文曾指出,此时的朝鲜文人正是认为“东坡不可学”、“不可及”,才退而求其次以黄庭坚的诗法作为学诗要义的。所以他们不仅继承了高丽朝的传统,也在诗歌整体风貌的追求上时时刻刻流露出了其内心的“东坡情结”。这种情结大致表现在“学黄”时仍不忘东坡风尚以及直接表露对苏轼的钟爱这两方面。笔者从文献中将之挑选整理了出来,以期对《东人诗话》的整体风貌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一)学习诗法时不忘东坡
在学习江西诗派的诗法时,徐居正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带着他内心的“东坡情结”,对朝鲜文人的诗作加以点评:
金员外克已《醉时歌》:“钓必连海上之六鳌,射必中日中之九鸟。六龟动兮鱼龙震汤,九鸟出兮草木焦枯。男儿要自立奇节,弱羽织麟安足诛。”语甚豪壮挺杰,其意本少陵“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其词本涪翁“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湖叶秋菊之英。”虽用二家语词意,浑然无斧凿之痕,真窃狐白裘手。[2]164
在这则诗话中,徐居正除了像之前一样分析诗句的来历,也在分析过后对诗句的总体风貌作以点评,并用“浑然无斧凿之痕”这样的标准去衡量该诗,让我们仿佛能嗅到其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价值倾向。而在笔者整理的另一则诗话中,这种倾向便愈发明朗直接了:
一日濮阳吴君世文与金东阁瑞廷、郑员外文甲置酒林亭,文顺亦与会,吴以所著三百二韵诗索和,文顺援笔步韵,韵愈强而思愈健,浩汗奔放。虽风樯阵马未易拟其速。东方诗豪,一人而已。古人诗集中无律诗三百韵者,虽岁月锻炼尚不得成,况一瞥之间操纸立成乎?[2]166
在这则诗话中,高力诗人李奎报与文人们饮酒赋诗时,表现出了非常杰出的创作才华,在“一瞥之间操纸立成”,而且作的是三百二韵的律诗。此时,徐居正一方面叹服其在短短的时间内诗韵皆和,一方面也称赞“浩汗奔放”的诗歌风貌,从而在称李奎报为“东方诗豪”的同时也流露出对苏轼创作风尚的尊崇。
(二)直接表露“东坡情结”
徐居正从东坡作诗能“即境”,能“出肺腑”,具有“清绝”“超迈”之“气象”等方面表露其对苏轼的崇仰的。
首先,徐居正在其诗话中提出了这样的论断:“作诗非难,能造情境模写形容一言而尽,此古人所难。”[2]202也就是说,徐居正认为诗人能将自己遇到的情境写得非常清晰明畅是很难的,这一认识也符合我们通常的艺术规律。然而,笔者在另一则诗话中找到了相关的例证:
太白《浔阳感秋》诗:“何处闻秋声,萧萧北囱竹。”东坡《漱玉亭》诗:“高岩下赤日,深谷来悲风。”能写即境语。印学士份《秋夜》诗:“草堂秋七月,桐雨夜三更。倚枕客无寐,隔窗虫有声。”其清新雅绝不让二老。[2]200
“此古人所难”之事,在这则诗话中徐居正认为苏东坡是可以做到的,并且举了相应的诗句作为例证,从而将东坡的形象树立在了学人的心间,也将自己的东坡情结表露无遗。
其次,徐居正批评实践中提出的“诗出肺腑”与“诗能感鬼神”等主张事实上也是在暗合苏轼的作诗主张。苏轼曾提出“诗要有为而作”[6],也就是说诗歌应该反映作者的真实感受,在这一点上徐居正在论诗时也在积极地向东坡靠拢。例如:
李侍中公遂《下第》诗曰:“白日明金殿,青云起草庐。那知广寒桂,尚有一枝余。”林西河椿《下第》诗:“科第未收罗隐恨,《离骚》空寄屈平哀”。又曰:“科第由来收俊杰,公卿谁肯荐非才。”其气象大不同。李终得大魁入台衡,林竟不第。诗出肺腑,或者天其先诱乎?[2]201
这则诗话中李诗虽然比林诗在表达感情上要婉约含蓄,但却能从中感受到深切的进取仕途之心情。其将自己的情感巧妙地化用在诗句的“用事”之间。从而做到了“托物比况”,情融入境。林诗虽然在语句间直白表露了自己的情感,但却在诗中并没有达到“诗出肺腑”的气象,浅白直露反而有害于情感的抒发。
最后,徐居正在这部诗话里也大量运用“气象”这一文论范畴作为自己品评诗歌的标准,提出了“诗当先气节而后文藻”的理论主张。一方面是受到我国“气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在表达对苏轼诗歌境界的向往和追求。
李陶隐《登松山》诗有“飞上危巅一瞬间”之句,论者以谓有躁进之气,果不大施。益斋《登鹄岭》诗“徐行终亦到山头”,论者以谓从容宽缓,有远大气象,果能辅助五朝,功名富贵终始双全。诗者,心之发气之充,古人以谓“读其诗可以知其人”,信哉![2]214
苏轼在其《李太白碑阴记》中也曾鲜明地指出“士以气为主”,诗歌之“气”往往与诗人的个人情志修养有关。在这则诗话中,“论者”对陶隐和益斋为人的判断是从其诗歌中入手的,并且也得以证明。在这一点上,徐居正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我国的“文气论”传统,积极倡导作家的个人情志在诗句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弥补在学诗中一味地“尊黄”之弊端。此外,徐居正还利用“气象”这一范畴直接品评东坡与朝鲜文人的诗句,并提出了“清绝豪迈”的美学追求,使得东坡在《东人诗话》中的形象更加鲜明而完整。
李正言存吾平生慷慨不群,其论逆盹一疏文章气节直与日月争光,为诗亦豪迈绝伦。其《送湖奉使还台州》诗云:“秋风不识留君意,直送飞艎到浙江。”读其诗,其气象可知。[2]211
太白《浔阳感秋》诗:“何处闻秋声,萧萧北囱竹。”东坡《漱玉亭》诗:“高岩下赤日,深谷来悲风。”能写即境语。印学士份《秋夜》诗:“草堂秋七月,桐雨夜三更。倚枕客无寐,隔窗虫有声。”其清新雅绝不让二老。[2]200
在这三则诗话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徐居正用“气”这一范畴品评诗歌,在后两则中也能非常明确地看到他的诗歌美学倾向,在其看来苏东坡的诗歌清新雅绝,豪迈绝伦,由此也在这部诗话中多次运用“清绝”“豪迈”等意象品评诗歌,并将这两者意象与“气象”结合起来,其对诗歌整体的美学追求至此便交汇而成了。笔者认为,这也是徐居正“东坡情结”最高妙的流露。
四、“各臻其极,归之于正”
从高丽后期专尚东坡之风,到后来随着江西诗派影响的深入,“学黄”在文人之中广泛开展。但是朝鲜文人在其学习汉诗的过程中,并不满足只学诗法,而是在前期传统和独立批判精神的相互影响中始终不忘东坡,对于遥遥“不可及”的东坡之诗频频流露出内心的钟爱。在《东人诗话》中,徐居正一方面倡导文人学诗,用江西诗派的一套诗法品评诗歌,一方面也在大力主张作诗“气节”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了以学黄诗为基础,以东坡“气象”为导向的价值倾向。笔者在这部诗话中整理出了其在面对这一问题的直接论述:
古之诗人立意措词虽不同,要皆各臻其极,归之于正而已。[2]200
梅圣俞、苏子美齐名一时,二家诗格不同,苏之笔力豪俊,以超迈横绝为奇;梅则研精覃思,以深远闲淡为高。致各臻所长,虽善论者未易甲乙,然欧阳子隐然以梅为胜。李陶隐,郑三峰齐名一时,李清新高古而乏雄浑,郑豪逸奔放而少锻炼,互有上下。[2]175
在这两则诗话中,徐居正表示江西诗派与苏轼“诗格不同”,“各臻所长”,二者作诗的路径方法不同,江西诗派的诗人往往“研精覃思”,苏轼则以“笔力”见长,从而显现出不同的气象来。二者“互有上下”,若是将二者之长都发挥到极致,那便可以达到他所说的“归之于正”的境界。在这两则诗话的论述中,徐居正流露出了较为客观的学诗态度。作为接受者的朝鲜文人,在面对外来文化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两类诗人的所长与不足实在难得,而且也在这种谦卑的心态中表达出极力想要“归之于正”的心情。然而,即便是他能清醒地看到二者各自的所长和不足,希望将二者在“立意”和“措词”方面的不同优势充分结合起来,徐居正在诗歌的总体追求上仍然表露出他内心崇尚东坡之豪迈气象的情结:
客又问:“陶隐《岭南楼》诗押‘烟’字‘秋深官道映红树,日暮渔村生白烟’,浩亭河文忠公仑云‘十里桑麻深雨露,一区山水老云烟’,孰优?”余曰:“陶固雅绝,得诗家法,终不若河之深远,有宰相气象。”[2]207
或问于浩亭河公曰:“陶隐诗文可以炼琢,精深雅高,阳村诗文平淡温厚,成于自然。毕竟陶优于阳乎?”浩亭曰:“陶之琢炼,阳为之有裕;阳之天机,陶终不能及也。且应制诗二十四篇,阳村为之,而陶隐必不能也。”[2]209
金政堂得培题金海客馆云:“来管盆城二十春,当时父老半成尘。自从书记为元师,屈指如余有几人?”田政堂录生题合浦云:“此地来游仅十春,岂啬来镇有今晨。壁间拙字知余否,曾是当年下笔人。”两公皆文章钜手,兼总戎兵。其橫槊哦诗,气象大异于雕篆酸寒者之所为也。[2]229
在这三则诗话中,徐居正对两类诗人的诗歌气象作以比较分析,他认为,“得诗家法”的陶隐虽然炼字锻句非常成功,然而其雅绝的诗歌气象终不若“成于自然”的“天机”之作。在笔者例举的最后一则诗话中,徐居正竟将带兵打仗之人所赋诗歌与文人墨客的诗歌气象作以比较,其用“雕篆寒酸者”来形容重于文字锻炼的文人,其内心之褒贬倾向已经显而易见了。
因此,从高丽朝后期的学诗风尚,再到徐居正所处时期开始大力“学黄”,以及内心不灭的东坡情结以及对诗歌“气象”的追求,无不显现出朝鲜文人在面对我国传入的汉诗文化时所展现出的谦卑心态。在徐居正的诗话中,也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东坡不可及也”,虽然会用朝鲜文人与苏轼作以比较,称赞个别诗人堪称“诗豪”,但还是坚持认为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东坡那样的高度。由此,也使得徐居正在“学诗”方面倡导学人努力学习黄庭坚一派的作诗传统显得更加合理贴切,只有学好炼字锻句,用事技巧等诗法,才能在另一种层次上追求东坡所代表的“自然”“豪迈”之气象。此外,徐居正在《东人诗话》中所表现出的学习中国文化的谦卑心态,对于当下国人在面对外来文化如何自处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1]马金科.论朝鲜古代诗学对“江西诗派”概念的接受[J].延边大学学报,2007(6).
[2]蔡美花,赵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3]刘艳萍.韩国高丽文人对苏轼及其诗文的接受[J].延边大学学报,2008(41).
[4]崔雄权.苏轼与韩国汉诗风的转换与诗学价值的选择[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2).
[5]王水照.苏轼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6]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7]朴贞宣.浅谈《东人诗话》中的“气象论”[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8(11).
[8]马金科.试析朝鲜半岛接受江西诗派的文化语境[J].延边大学学报,2013(4).
[9]马金科.从《东人诗话》看徐居正的诗歌批评观[J].延边大学学报,2001(3).
[10]马金科.论高丽、李朝诗人对黄庭坚诗学的接受与变通[J].东僵学刊,2009(3).
[11]马金科.从“苏黄”含义的转变看江西诗派在朝鲜汉诗中产生的影响[J].延边大学学报,2003(3).
[12]贾丹丹.典范的追随与反争:《东人诗话》与中国诗学[J].古籍研究,2007(2).
On Inclination to Unify the“Su and Huang Style”in North Korea Notes and Comments on Poetry
MA Ye,REN Jinɡze
(School of Arts,Sh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Shannxi 710119,China)
Accomplished at the turning point of Gaoli Dynasty and Li Dynasty of North Korea,the poetic workNorth Korea Notes and Comments on Poetry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Jiangxi poetic school and also inherited the writing style of poets in Gaoli to some extent,which leads to the different inclination that poets tend to look up to Huang Tingjian in poetic criticism while follow Shu Shi in poetry creation theory.What’s more,the overall value of this poetic book showed the combination of“Su Huang”style which embodied the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critical spirit of Korean literati as the recipient in face of China’s literary works and theoretical criticism.
North Korea Notes and Comments on Poetry;Poetic School of Jiangxi;Xu Juzheng;Su Shi;Huang Tingjian
I206.2
A
1009-8666(2017)09-0013-08
10.16069/j.cnki.51-1610/g4.2017.09.003
2016-11-24
马也(1993—),女,陕西延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任竞泽(1968—),男,内蒙古宁城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
[责任编辑、校对:方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