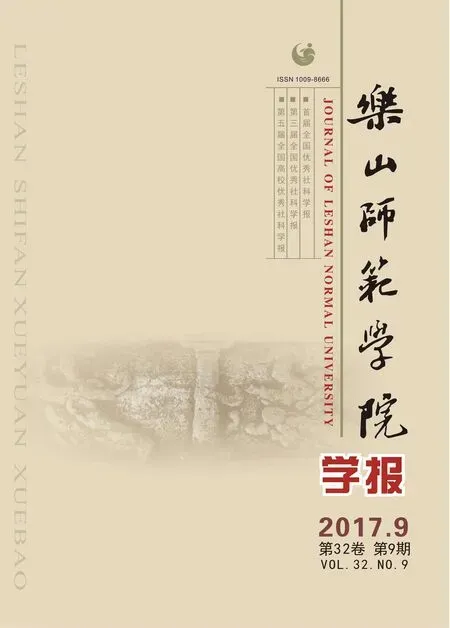萧衍诗歌史地位重估
李 鹏
(亳州学院 中文与传媒系,安徽 亳州 236800)
萧衍诗歌史地位重估
李 鹏
(亳州学院 中文与传媒系,安徽 亳州 236800)
对萧衍诗歌史地位的认识,目前学界的关注度较低,而萧衍本身所具备的政治权力、文学修养及文化影响力对当时及后世诗歌的发展确有较多影响。因此正确认识萧衍对齐梁文学繁荣所做出的贡献、对齐梁文学思潮的引领及其个人文学创作的实绩,对重新估价萧衍的诗歌史地位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萧衍;兼收并蓄;创新性诗歌
萧衍是横跨齐梁的一位重要诗人,在以往的诗歌史叙述中,论齐代诗,则强调其“竟陵八友”之一的身份,地位不及沈约、谢朓;论梁,则四萧并称,风头逊于其子萧统、萧纲。如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在谈永明体提谢朓,谈梁诗提萧纲,并指出“齐梁时代诗坛领袖人物沈约”[1]320,未注意萧衍。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在分析竟陵八友在六朝文化史中的地位时,将他们的创作成就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以沈约、谢朓为首的诗歌创作;一是以任昉、陆倕为首的骈体创作。”[2]31詹福瑞《南朝诗歌思潮》一书在论述永明诗歌思潮时指出“以王融、谢朓、沈约为核心的竟陵文人集团,有意识地推动诗歌创作和理论批评”[3]84,而在论述梁陈诗歌思潮时,詹福瑞虽提到了萧衍在传承军伍文化和士族文化中的作用,但主要的研究精力仍放在对宫体诗人的研究中。阎采平《齐梁诗歌研究》将梁代诗歌发展分为前后两期,指出“萧衍、萧统集团活动在梁代前期诗坛”[4]63,并说明在“梁初诗坛上,沈约声誉最高”[4]66,而“在梁代后期诗坛上,萧纲文学集团是创作实绩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文学集团”[4]68。总的看来,目前对萧衍其人、其诗的理解亟待加深,所以本文拟对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进行重新评价。
一、历代学者对萧衍其人其诗的评价
对萧衍其人其诗的关注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唐宋时期诗评家评这段诗学,或整体观照齐梁诗,或评永明体之沈约、谢朓,或评宫体萧纲、萧绎,虽对萧衍偶有提及,但不甚重之。
对萧衍的正面评价,首先源自史学家,观照重点在于其基于政治权力而产生的文学影响力。如《南史·文学传序》:“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甚。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武帝每所临辛,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5]1762《南史·梁武帝本纪论》:“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5]226,“帝博学多通,及登宝位,躬制赞、序、诏、诰、诔、箴、颂、笺、奏诸文百二十卷”[5]223。《梁书·文学传序》:“高祖旁求儒雅,文学之盛,焕乎俱集。”[6]685魏征《梁论》亦谓:“魏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6]151这些记载反映了萧衍的史学地位在于:第一,以帝王之尊,提倡文学,促进了文学繁荣;第二,勤于著述,对应用文体发展起到了贡献。
明清之际对萧衍诗的肯定逐渐增多。王世贞《艺苑卮言》对萧衍的创作实绩给予了总体评价,认为,“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其次则汉文、宣、光武、明肃……梁武、简文、元帝……凡二十九主。而著作之盛,则无如萧梁父子。”[7]1072“梁氏帝王,武帝、简文为甚,湘东次之。”并对具体作品进行了点评,“武帝之《莫愁》、简文之《乌栖》,大有可讽”[7]997。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也对萧衍的作品进行了评价:“七言歌行,梁武尤盛。《河中之水》《东飞伯劳》,皆寓古调于纤词,晋后无能及者。”[8]46认为其乐府诗辞藻虽稍显雕琢修饰,但情感蕴藉颇有古意。陆时雍《诗镜总论》对这两篇作品也持相似的看法,并对萧衍的文学风格进行了评价:“梁人多妖艳之音,武帝启齿扬芬,其臭如幽兰之喷,诗中得此,亦所称绝代之佳人矣。《东飞伯劳西飞燕》《河中之水歌》,亦古亦新,亦华亦素,此最艳词也。所难能者,在风格浑成,意象独出。”[7]1408认为其诗歌风格清丽平浅而不乏雅正厚重,与宫体“妖艳之音”颇多不同,明清论诗家也多持此观点,认为萧衍为齐梁诗雅正派的代表。如徐学夷《诗源辩体》:“梁武帝乐府五言,情虽丽而未甚靡,齐梁间乐府,唯武帝稍为有致。”[9]125陈祚明《采菽堂诗选·萧纲题注》:“齐、梁作者,渐即秾华。然观梁武、昭明,尚是雅音,纤丽不极。至于简文,半为闺闼之篇,多写妖淫之意。”[10]762
进入当代,文学史著作对萧衍其人其诗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未提及萧衍,但在叙述梁陈文学时持贬义态度,称这段文学为“色情文学”,并称其“掌握在荒淫的君主贵族的手里。这些作品的内容,正是他们荒淫生活的反映”[11]201。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萧衍得到了较高程度的认可。“梁武帝的时代,又是一个花团锦簇的诗人的大时代,也许较永明时代更为热闹。萧衍他自己是竟陵八友之一,天生的一位文人的东道主,他自己又是那么的工于诗,故集合他左右的诗人们,是较之前一个时代更为众多,也更为活泼。”[12]170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给予了萧衍高度评价,说:“以梁武帝萧衍和昭明太子萧统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对梁代文学的繁荣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萧衍早年预西邸文士之列,不仅对文学创作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文学修养亦颇为出众,自即皇帝位之后,尤能重用文士,倡导并鼓励文学创作。”[13]144其书较多地引用了《梁书》记载,以说明萧衍对当时文学的影响。
在先贤今哲的研究基础上,笔者认为,萧衍在诗歌发展史上值得一提的贡献有两点:第一,萧衍兼收并蓄的文化思想为当时诗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学环境;第二,萧衍富于想象力和创新性的诗歌,为中国后来的诗人们开创了一些可能性。
二、萧衍的兼容与齐梁诗坛的繁荣
人们习惯把齐梁诗看作一个整体,视其为接连汉魏古诗和唐近体诗的桥梁。在这一个时期的诗歌史叙述中,诗人个体的个性及影响则较容易被忽视。其实,任何一种文学风尚的形成都离不开个别或少数作家的引领。齐梁间,作为帝王的萧衍,很好地将其政治上的权力转化为文学上的影响力,为本时期的文学繁荣作出了贡献。
(一)“唯才是务”的用人观念促使文学成就成为品评人物的重要标准
萧衍在任用官员时,兼容并蓄,既重门第,又给庶族阶层进身的机会。他一方面维护门阀,尊重高门,给王亮、王莹、谢览、谢朏这样的高门子弟以重用;另一方面又恢复考试制度,克服了在仕进过程中对寒门士族及南方土著的歧视。“设官分职,唯才是务”[6]23。家族血统虽然重要,但一个人的学术和文学成就则逐渐成为品评人物的重要标准。无论是往时世家大族以相互通婚等手段维护地位的方式需要寻求新的出路,还是寒门庶族急于改变特权较少的社会地位而获得认可,文学或者说诗歌都成了可以传承的事业,这不仅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较大影响,甚至为初唐解决士庶之争,使初唐四杰这样的寒门子弟发声歌唱开启了先声。
(二)会通三教,学术思想得到相对解放
萧衍个人在对待儒释道的态度上是兼收并蓄的。其《会三教诗》:“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14]1531虽然三教依次排列,意在说明佛教才是其最后的归宿,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其宗教信仰的发展轨迹及其会通三教的文化思想。
萧衍佞佛,早年在萧子良西邸时即表现出对佛教的热爱,及其登基,更被群臣称为“皇帝菩萨”。《梁书·本纪》载,其曾三次舍身寺院,再由国家和大臣施舍大量财物将其赎回,如第二次舍身,“功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6]92。萧衍既对造像、法事、斋会、受戒等宗教仪式十分热衷,又倾心于对佛学义理的研习和探求,如对佛性说等的关注。可以说,梁武帝挟万乘之尊推广佛教,使佛教势力的影响远超前代,同时也促进了佛教的本土化进程。
佞佛,但也尊崇儒家思想。个人行止上,他重孝。父亡,“(萧衍)时为齐随王谘议,随府在荆镇,仿佛奉闻,便投劾星驰,不复寝食,倍道就路,愤风惊浪,不暂停止。高祖形容本壮,及还至京都,销毁骨力,亲表士友,不复识焉。”[6]95文化政策上,劝儒生以官禄。“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笈者云会矣。”[6]662天下研经之习翕然成风。以至于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称:“南朝的儒学在梁代最为兴盛。”[15]6
梁武帝改宗佛教之前,对道教很是看重。萧衍的家族是世代信仰天师道的,《隋书·经籍志》说:“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16]1093萧衍还和道士陶弘景关系密切,《梁书·陶弘景传》载:“义师平建康,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6]743而且他们的关系始终不渝,直到天监十五年,萧衍还为陶弘景建太清玄坛,支持其弘扬道教。可见,梁武帝改宗之后,也并未排斥道教。
萧衍同重三教并不奇怪,一方面三教同属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根本上并无抵触;另一方面,作为统治者对各教兼容并包更易取得民心,巩固统治。更何况在晋宋之际三教已有趋同情形,特别是到了齐梁之际,很多士人出入内外两教,所以萧衍于天监初年明确提出“三教同源”说,以政治力量促进了三教合一,这也成为了先唐学术思想上的一个顶峰,为本时期各个文学流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三)对各个文学流派的容纳
吏治用儒,在文学上则需标举雅正;信仰以释,杂入道思,又允许文学回归人的心灵,回归自身的兴趣爱好,所以罗宗强称其“是一位复杂的人物,他对于其时各派之文学思想,似乎都可以兼容”[17]282。
萧衍对各派文学思想兼收并蓄。齐梁之际,以裴子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人圈子,其诗歌思想的根基,是传统的儒家诗教说。裴子野强调诗歌政教之用,说:“古者四史六义,总而为诗,既行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善惩恶,王化本焉。”[18]581其诗文好为古体,这种文风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梁书·裴子野传》载:“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6]443裴氏的文学观是违背晋宋以来文学追求个人情性的思想主潮的,所以“当时或有诋诃者”,而后来又遭到萧纲“了无篇什之美”[18]115的严厉批评,笔者认为裴子野影响的持续存在应与萧衍尚儒有关。萧衍本人的文学思想多被视为复古的、守旧的,裴子野好古体恰与其相合,《梁书》即有记载,普通七年北伐,裴奉敕作《喻魏文》,即得到了萧衍的大加赞赏。
雅正诗风在萧衍的庇佑下得以在一个短时间内存在发展,但萧衍又允许变化,又要满足自身的兴趣爱好,所以文学的主流还是主流,并未因治国的需要而改变。
晋宋以来,诗人们比较有意识地摆脱传统的诗教目的,追求以文学表达人的性情,这其中虽偶有旁出,但并未对总的方向产生太大起伏。
永明时,诗歌取材无关大雅,言情婉曲深长,声律趋向自觉。竟陵八友,萧衍得预其中。其于当时诗坛影响虽不及谢朓、沈约,但从沈约在梁朝建国后的文坛地位,及萧衍子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所说,“近世谢朓、沈约之诗,……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18]116萧绎所给予“诗多而能者沈约”[6]693的推崇,可以看出萧衍对沈约所主导的有梁前期诗坛的认可。当然,学界经常提及萧、沈二人的两段公案亦需注意:
先此,约尝侍讌,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及闻赤章事,大怒,中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6]243
萧、沈二人晚年稍有隙,但二人却都有隶事的爱好,而为诗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即为沈氏诗歌主张之一,这对当时诗风由雅向俗的转化较有影响。
约撰《四声谱》自谓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约也。[6]243
此经常被用证明萧氏不辨四声,并有人批评到“四声未分,梁武帝常作聋俗”[4]182。但笔者注意到,萧衍不好四声,但有求知欲望,不遵用,但也并未排斥,基本上算是兼容的。
梁中后期,梁武帝又默许萧纲、萧绎兄弟主导了诗坛,“宫体之号,自斯而起。武帝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武帝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无不应对如响,帝叹异之,宠遇日隆。”[6]447萧衍对徐摛态度的转变,实际上是对宫体诗态度的转变。由最初的不满意,到实际上的默认,妥协,可见萧衍兼容并包的态度。
综上诉述,萧衍选拔官吏的准则进一步推动了时人对文学的重视,而其兼容并蓄的思想又有力地推动了儒释道三教的会通,并且很好地容纳了当时各个文学流派的自由消长,促进了本期文学的繁荣。
三、创作实绩与诗歌发展可能性
萧衍个人的雅好及较高的创作水准,对其时文学风尚的推波助澜作用也不容忽视。他富于想象力和创新性的诗歌,特别是其乐府诗,为中国后来的诗人们开创了一些可能性。
齐梁人热衷于“四声”的发现,将诗的音乐性寄托于语言文字本身,对诗的欣赏方式也由“唱”而变为“吟”,这是诗歌发展的必然。后来便有了近体诗。但文学应具有多样性,诗歌像“被之金竹”时代那样凭借外加的乐调来维持其声调美的方式,也应予以适当保留。萧衍虽默许了自己不太了然的“四声说”,却以实际行动对“被之金竹”诗歌方式的保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吏治用儒,则需礼乐教化。“梁氏之初,乐缘齐书。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遂下诏访百僚……”[16]287在《隋书·音乐志》中还有梁武帝自制礼乐的记载,“是时礼乐制度,粲然有序”[16]304。
正乐崇礼,但对更易感染人的俗乐新曲的兴趣也浓。逯钦立《全梁诗》存萧衍诗106首,乐府占54首,清商曲占38首,且其中多有自造、改作。“初,武帝之在雍镇,有童谣云:‘襄阳白铜蹄,反缚扬州儿。’识者言,白铜蹄谓马也。白,金色也。及义师之兴,实以铁骑,扬州之士,皆面缚,果如谣言。故即位之后,更造新声,帝自为之词三曲。”[16]305
萧衍改作乐府诗,常不依本事,而借以写儿女之情。“梁天监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我们且看其第一首《江南弄》:“和云,阳春路,娉婷出绮罗。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耀绿垂轻阴。连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蹰。”[14]1522《三洲歌》属西曲,本事写送别之意,为商贾经巴陵三江所作,与女子的妙姿丽声本无关联。本诗却以宫廷园囿之景起笔,良辰美景,春色静好,舞女的情感也化为了蹁跹舞姿。而此时,深居后宫的“中人”望见如此的风流场面,不禁独自踟蹰,整首诗欢乐中点缀着宫怨,儿女之态尽显。而其第六《游女曲》“纷氲兰麝体芳滑,容色玉耀眉女月”[14]1523则更是已涉描摹女性体态了。
以乐府写女性,将景色打并入艳情,萧衍的这种写法,无疑对轻艳诗风的风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萧纲便深受其父影响,改作了大量的相和旧曲,此在杨德才《论萧衍的乐府诗》中有较详细论述,不再赘述。
另外,《江南弄》还被一些学者视为词的滥觞,如梁启超便说:“凡属于《江南弄》之调,皆以七字三句、三字四句组织成篇。七字三句,句句押韵,三字四句,隔句押韵……”[19]184虽然,词的起源问题至今说法不一,但起自萧衍说不也至少说明了萧衍为后世诗歌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可能性吗?
总之,作为帝王的萧衍容纳并引领了其时的文学思潮,作为诗人的他也以较高的创作水准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是一位人们不甚重视的诗人,却成了齐梁诗歌思潮的有力推动者,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3]詹福瑞.南朝诗歌思潮[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
[4]阎采平.齐梁诗歌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5]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丁福保.历代实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胡应麟.诗薮内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9]徐学夷.诗源辩体[M].杨维沫,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0]陈祚明.采菽堂诗选[M].李金松,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2]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
[1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卷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4]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16]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7]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8]严可均.全梁文[M].冯瑞生,审订.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9]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Reappraisal of Xiao Yan’s Status in Poetic History
LI Penɡ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Media Studies,Bozhou Institute,Bozhou Anhui 236800,China)
Xiao Yan’s status in poetic history has neverbeen r ecognized in academic circles.However,Xiao Yan’s political power,literary accomplishment and cultural influence indeed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at his time and the later generations.Therefore,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Xiao Yan’s contribution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Qi Liang Literature,the leading role in the literary field at that time and his personal achievements in literary field.
Xiao Yan;Eclectic;Creative Poetry
I206.2
A
1009-8666(2017)09-0021-05
10.16069/j.cnki.51-1610/g4.2017.09.004
2016-11-15
亳州学院科研课题“齐梁诗风嬗变研究”(BSKY201407)
李鹏(1986—),男,安徽六安人。亳州学院中文与传媒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国诗学。
[责任编辑、校对:王兴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