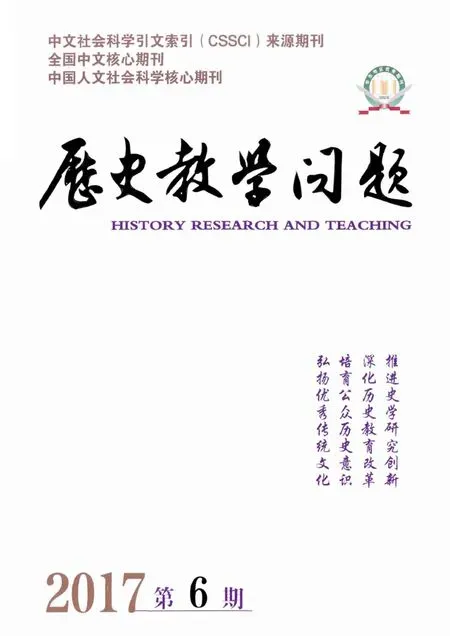“礼”与“法”之间:试论两宋士大夫的法律观念
白 贤
目前,关于两宋士大夫的法律观念,史学及法史学界存在不同的认识。何忠礼先生指出:由于“重儒轻法的传统思想”“受人情关系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以及“提倡忠恕、以‘弛刑’为贵的陈腐观念”,使得宋代士大夫“法制观念淡薄”。①何忠礼:《略论宋代士大夫的法制观念》,《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而陈景良先生则认为,两宋士大夫“工吏事、晓法律”,具有“批判实用的精神”和“重视权利诉讼”的观念,“展现了宋代法律文化实用向上、保护社会个体成员合法权益的时代个性”。②陈景良:《试论宋代士大夫的法律观念》,《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在陈先生主编的权威法史著作《中国法制通史》(宋代卷)中,他又重点阐述了这一观点,可视为目前法史学界的主流看法。③参见陈景良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5卷第1章“士大夫的法律思想”部分,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52-74页。由于两宋士大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群体,何、陈二先生关于其法制(法律)观念的论断均有历史依据与客观存在。但笔者同时以为,所谓法律观念往往深植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以类似“优劣”“高低”式的判断极有可能将复杂的历史面相简单化。以下不揣浅陋,以“礼”与“法”的关系为视角,从礼法观、立法观以及司法观等几个方面入手,对两宋士大夫的法律观念试作探究,以期丰富对宋代法制史以及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认识。
一、礼法观:“礼者,圣人之法制也”
梁治平先生在论及法的内涵时说:民族法与民族语言同是民族历史文化的产物,具有特定历史文化的鲜明性格。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法”至少要作两方面的理解:一是文字学、语言学上的一个字、词,其次是我们称之为“法”的那种社会现象。作为字、词的“法”与作为社会现象的“法”密不可分。历史决定着观念,观念又左右着历史。④梁治平:《“法”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对此笔者深以为然。因此,我们需对“什么是法”加以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的考察。
(一)语源意义上的“法”
法的古体写作“灋”,据《说文·灋部》:“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有论者据此认为古代之法在语源上兼有公平、正义之意。蔡枢衡先生则认为“平之如水”乃是“后世浅人所妄增”,因为把罪者置于水上,随流漂去,类同驱逐,是为古时很重的一种刑罚。⑤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0页。又《尔雅·释典义》云:“法,逼也。”可见法还有强制服从之意。再如《管子·心术》:“杀戮禁诛之谓法。”《盐铁论·诏圣》:“法者,刑罚也,所以禁强暴也。”说的都是此种含义。至于与此同义或相似的称谓如刑、律、令、格、式、诏、敕、例等,均含有强制、规范之意,可泛称为“法”“法令”“律”“律法”“刑法”“国法”,等等。
宋代此种意义上“法”的称谓以“律”“刑”“刑法”等居多。如《宋大诏令集》中的《令幕职州县官习读法书知通幕职州县官秩满试法书诏》:“夫刑法者,理国之准绳,御世之衔勒。重轻无失,则四时之风雨弗迷。出入有差,则兆人之手足何措。”又如北宋名臣宋祁所云:“臣闻刑法者非由天降,非从地出,直以圣人因世制宜而为之中也。故前王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命,大者甲兵铁质,次乃鞭扑流宥,期在禁乱惩恶,辅德养善,防情之大宝,经国之善物而已。”①宋祁:《议刑篇上》,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3册)卷四八八,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再如“明法科”“试刑法”“以刑弼教”中的用法,均同此类。
(二)文化意义上的“法”
从历史文化的发展而言,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法经历了一个“法律儒家化”的过程,通常也被称作“以礼入法,礼、法结合”。所谓“礼”,是指儒家的伦理规范和行为方式。所谓“法”,则指国家所订立颁布的律典和条例。礼、法本来分属道德与法律范畴,有其自身之运行逻辑。以礼入法、礼法不分,必然导致内在矛盾的发生,从而使执法者陷入两难之境,如古代司法中屡屡出现的容隐、复仇问题之争论,均是礼、法冲突的结果。但同属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二者又有根本上的相通之处。即所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②班固:《汉书》卷四八《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252页。“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③范晔:《后汉书》卷四六《陈宠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554页。但在儒家士大夫看来,在礼、法关系上,礼高于法。因为“礼者,天地之序也”,④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三七,中华书局,1980年,第1530页。乃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⑤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一,中华书局,1988年,第12页。随着汉代以来的“以儒治国”及隋唐科举“经义取士”的推行,使法的地位越来越屈从于礼,形成所谓“德主刑辅”的态势。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法律从本质而言成为了一种“礼法”。⑥梁治平:《法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页。
在以儒家“道统”自居、以“天下为己任”的两宋士大夫看来,儒家礼法更是万古不变的至高法则,是国家治乱兴衰的根本所在。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时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司马光不但认为“国家之治乱,本于礼”,⑦司马光:《谨习疏》,《司马光奏议》卷七,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8页。甚至将礼视为决定人生死的原则,即所谓“人有礼则生,无礼则死”。⑧司马光:《答范景仁养生及乐书》,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5册)卷六二,巴蜀书社,2009年,第59页。按,司马光文中曰:“《记》曰:‘人有礼则生,无礼则死。’”但考之《礼记·曲礼》,原作:“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口中所言“天理”,实则也是儒家之“礼法”而已。他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⑨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学而》,《朱子全书》(第6册),第72页。“盖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⑩朱熹:《晦庵集》卷一四《戊申延和奏札》,《朱子全书》(第20册),第656页。“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⑪朱熹:《晦庵集》卷四〇《答何叔京》,《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38页。“礼字、法字实理字,日月寒暑、往来屈伸之常理,事物当然之理”。⑫朱熹:《晦庵集》卷四八《答吕子约》,《朱子全书》(第22册),第2242页。违背了儒家的三纲五常则是罪大恶极、天理不容,即“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⑬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六《释氏》,《朱子全书》(第18册),第3932页。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朱熹主张:“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⑭朱熹:《晦庵集》卷一四《戊申延和奏札》,《朱子全书》(第 20册),第657页。
需要强调的是,将儒家“天理”视为最高法律准则是两宋士大夫的普遍做法。即使被认为“行申、韩之术”的王安石也认为:“刑名法制非治之本,是为吏事,非主道也。……盖精神之运,心术之化,使人自然迁善远罪者,主道也。……而每事专仰法制,固有所不及也。”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〇,中华书局,1979年,第5590页。南宋陈亮虽倡导“王、霸并行”,但依然认为“仁义孝悌所以率先天下”。②陈亮:《陈亮集》卷一一《廷对》,中华书局,1987年,第116页。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在两宋士大夫眼中,法有“礼法”和“国法”之分。礼法乃是天下之理、根本之法;而所谓国法(或曰刑法、律法)上承法家、依律为断、以刑立威,深为士大夫所不齿。③如司马光认为:“文法俗吏之所事,岂明君贤相所当留意耶?”见司马光:《应诏论体要》,《宋文鉴》卷四九,齐治平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第753页。柳开也说:“夫法者,为治之末者,乱世之事也。皇者用道德,帝者用仁义,王者用礼乐,霸者用忠信。亡者不能用道德、仁义、礼乐、忠信,即复取法以制其衰坏焉。将用之峻,则民叛而生逆;将用之缓,则民奸而起贼,俱为败覆之道也,圣帝明王不取也,圣帝明王不用法以为政也。……且执法者,为贱吏之役也。”见柳开:《请家兄明法改科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6册),第315-316页。虽然以礼入法的法律儒家化运动使礼、法关系日益密切且相互为用,但礼绝不等同于法。甚至礼、法的融合还会给一些“唯礼是从”的士大夫带来危机感,这是由两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属性决定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治国当以儒家礼仪教化为主,“国法”自然要处于“礼法”之下。此种看法在南宋名公真德秀口中可得到印证,他在《谕州县官僚》中说:“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轻重之不可逾者,国法也。”④《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谕州县官僚》,中华书局,1987年,第6页。可见判断是非的“天理”(礼法)是置于权衡轻重的“国法”之上的。甚至还有人对这种天子所制的“国法”提出了质疑,因为“天子制法者也,故先所私,而后法则无嫌也。诸侯从上者也,故先定法而后行其私”。⑤张耒:《张耒集》卷三六《礼论三》,中华书局,1999年,第600页。窃以为,明确了这一点,即法的“礼法”与“国法”之别,那么两宋士大夫依赖法律又鄙视法律,认为“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却说“执法者,俗吏者贱役”,明知“律义甚明”偏要“曲法妄断”甚至公然“对抗圣裁”,等等,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便有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二、立法观:“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
儒家思想是一种有着“秩序情结”的理论,⑥参见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社会学的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以儒家“礼法”为灵魂的中国古代法律自然也就以维护儒家的伦理秩序为旨归。
(一)儒家礼法主导下的秩序观
儒家之礼的主要作用在于“别贵贱”“序尊卑”,从而确立以“亲亲、尊尊”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度。随着法律儒家化的进程,这种等级被不断制度化、体系化,最终以法律的形式得以确立。在此儒家化的法律体系中,处处体现着“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的规定。如在国家层面,居于最高等级的皇帝以“君权神授”“代天行命”的名义凌驾于任何法律之上,可以根据需要制定或更改法律,甚至直接“以制敕断罪”。皇帝之下,庞大的官僚集团在触犯法律时也可因特殊的身份而减免刑罚。在家族层面,子女在遭到父母责罚时,无论对错与否,均需坦然接受。法律甚至规定:如果子女因“违反教令”被父母杀死,也可免罪。⑦如元律规定:“诸父有故殴其子女邂逅致死者免罪。”明清法律也规定:“子女违反教令而依法处决,邂逅致死者无罪。”(《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四·诉讼》;《大明律》卷二五《刑律·诉讼》“干名犯义”条;《大清律例》卷三〇《刑律·诉讼》“干名犯义”条)但如果子孙杀害父母,法律则不分故杀或是误杀,均属罪大恶极,要处以最残酷之刑罚。在所有罪行当中,“谋反”位居“十恶”之首,为“常赦所不原”,也是因为破坏了以“王者”为中心的礼法秩序所致。⑧参见甘怀真:《从唐律反逆罪看君臣关系的法制化》,收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又见徐燕斌:《礼治模式下中国传统法律的秩序观——以唐律中侵害皇权罪为中心》,《北方论丛》2009年第4期。
可见,在这种“礼法”秩序中,所谓的公平、正义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维持由“礼”所构建起的封建等级与伦理纲常。虽然维护社会秩序乃是古今中外所有法律的通例,但如此一以贯之的“以维护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为特征的”的“法”还是不多见的。⑨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二)两宋士大夫对法的功用之认识
两宋士大夫普遍认为,唐末五代的战乱是因为君臣失序、礼法败坏所致,故而格外重视儒家礼法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如范祖禹在总结唐代教训时说:“昔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齐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诛其亲者,谓之‘定内难’;逼父而夺其位者,谓之‘受内禅’。此其闺门无法不足以正天下,乱之大者也。”①范祖禹:《唐鉴》卷二四,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17页。南宋的真德秀也劝诫理宗说:“唐太宗英主也,然于事亲友兄弟一有惭德,三百年之家法,遂不复正。”②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八,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01页。在两宋士大夫看来,要维护这种建立在伦理纲常之上的社会秩序,不惟要依靠国家之“国法”,更需仰仗儒家之“礼法”。实际上,两宋士大夫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来探讨“法”的功用的。
北宋名臣范仲淹说:“先王重其法令,使无敢动摇,将以行天下之政也。”③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宋文鉴》卷四三,中华书局,1992年,第663页。富弼明确指出:“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为首务。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第3455页。王安石更是认为:“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日亦不足矣。”⑤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二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02页。即使“唯礼是从”的司马光也承认:“王者所以治天下,惟在法令。”⑥司马光:《司马光奏议》卷三三《乞不贷故斗杀札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63页。并且说:“礼与刑,先王所以治群臣万民,不可斯须偏废也。”⑦司马光:《策问十首》,《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5册)卷七二,第373页。也许是因为律法被两宋士大夫所普遍轻视,一些士大夫还会借助上天,将其纳入“天意”的范畴,以增加其神圣性。如李觏指出:“然而天讨有罪,王者奉之以作五刑。刑者非王之意,天之意也。”⑧李觏:《李觏集》卷一〇《刑禁第三》,中华书局,1981年,第98页。
虽然很多两宋士大夫认识到了法律的重要性,可是一旦在讨论礼与法的关系时,法律往往会屈居于礼之下。因为在大多数两宋士大夫看来,律法只是权宜之计,并非治本之策。如范仲淹即认为:“期于无刑,求之于礼义。礼义既充,熟而成风,然后天下熙熙而遂,乐也无穷。”⑨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八,李勇先、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1页。苏轼也说:“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后者刑也。”⑩苏轼:《拟进士对御试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九,中华书局,1986年,第302-303页。作为司法官员的大理卿金安节也认为:“治民之道,先德后刑,今守令虑不及远,簿书期会,赋税输纳,穷日力办之,而无卓然以教化为务者。愿申饬守令,俾无专事法律,苟可以赞教化,必力行之。”⑪脱脱等:《宋史》卷三八六《金安节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1859页。而且,在两宋士大夫眼里,刑法往往是不得已而用之。朱熹对此论述最具代表性。他说:“臣闻昔者帝舜以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而使契为司徒之官,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又虑其教之或不从也,则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无刑焉……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耸然,不敢肆意为恶,则是乃所以正直辅翼至若其有常之性也。”⑫朱熹:《晦庵集》卷一四《戊申延和奏札》,《朱子全书》(第20册),第656页。
三、司法观:“有司议罪,惟当守法”与“分争辨讼,非礼不决”
就司法主张而言,两宋士大夫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以王安石为代表,认为“有司议罪,惟当守法”,即严格依据法律条文断狱定罪,我们暂称之为“国法派”。另一派以司马光为代表,主张“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即将礼作为最高的决狱标准,我们暂称之为“礼法派”。从两宋的文献记载来看,以后一派的支持者为多。
(一)国法派:“有司议罪,惟当守法”
王安石作为熙宁变法的领导和中坚力量,坚持“有司议罪,惟当守法,情理轻重,则敕许裁奏”。他对此解释说:“若有司辄得舍法以论罪,则法乱于下,人无所措手足矣。”⑬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〇《刑考九》,中华书局,1986年,第1475页。李觏的论述更为全面,他说:“先王之制,虽同族,虽有爵,其犯法当刑,与庶民无以异也。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杀,是为君者私其亲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杀,是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亲,臣私其身,君臣皆私,则五刑之属三千,止谓民也。赏庆则贵者先得,刑罚则贱者独当,上不愧于下,下不平于上,岂适治之道邪?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⑭李觏:《李觏集》卷一〇《刑禁第四》,第99页。
难能可贵的是,许多两宋士大夫依据“法与天下共”的思想,将帝王与有司也置于法制的框架之内。据《宋史》卷三五三《张近传》所载,权臣吕惠卿之弟温卿以不法闻,大理正张近受诏鞫治,哲宗谕之曰:“此出朕命,卿毋畏惠卿。”张近对曰:“法之所在,虽陛下不能使臣轻重,何惠卿也?”
(二)礼法派:“分争辨讼,非礼不决”
根据《礼记·曲礼上》:“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论语·为政》亦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分争辨讼,非礼不决”自然被“礼法派”视为决狱的金科玉律和根本原则。在对于司法者自身的专业素养方面,司马光甚至认为:“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①司马光:《司马光奏议》卷三七《起请科场札子》,第403页。朱熹提出:“凡听五狱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盖必如此,然后轻重之序可得而论,深浅之量可得而测。”②朱熹:《晦庵集》卷一四《戊申延和奏札》,《朱子全书》(第20册),第656页。
令人诧异的是,“礼法派”虽以儒家道统自居,但在量刑上却多坚持重刑主义。如以“忠恕”“爱民”著称的司马光、朱熹均倡导重刑主义,甚至后者主张恢复肉刑。这似乎与儒家力主的“仁爱”背道而驰,但仔细想来,儒家的所谓“仁爱”并非是施于所有人,对于违反“三纲五常”的礼教罪人向来严惩不贷。而且,唯有惩治之严厉,才能维护儒家礼法与宗法秩序的神圣不可侵犯。因此,从捍卫礼法的角度而言,“以礼决狱”与“重典治民”非但没有矛盾,反而是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在大部分两宋士大夫眼中,治国之法有“礼法”与“国法”之分,而礼法是解决一切纠纷、维护伦理秩序的根本途径。在司法实践中,则坚持先德后刑、明刑弼教。如南宋名公蔡杭所云“本职以明刑弼教为先”,③《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〇《恃富凌族长》,第392页。胡颖所谓“当职务以教化为先,刑罚为后”,④《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〇《因争财而悖其母与兄姑从恕如不悛即追断》,第362页。即是明证。在许多两宋士大夫看来,只要“以礼观之”,就无“难决之狱”。究其根源,乃是古代士大夫阶层“得君行道”“以礼治国”的政治理想与文化属性使然。由于时代环境的激励,此种观念在士风高扬、充满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两宋士大夫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