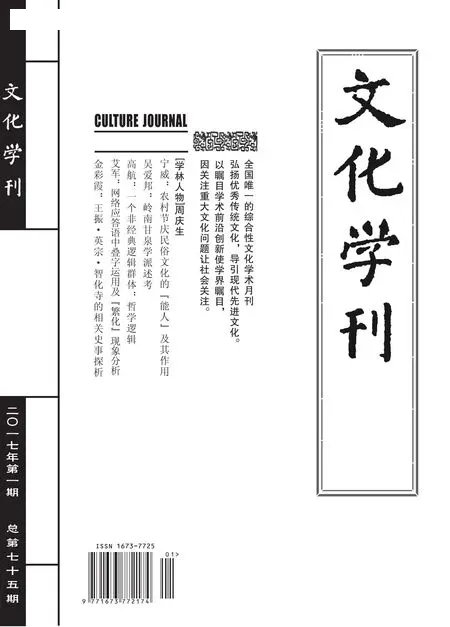从曾巩《为人后议》中看濮议之争
袁 堃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 成都 611756)
【文史论苑】
从曾巩《为人后议》中看濮议之争
袁 堃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 成都 611756)
历史上,宋仁宗无后,将堂弟濮王之子赵曙过继为子,史为宋英宗。宋英宗即位后,欲将濮王称为“皇考”,由此引发了以司马光为首同以欧阳修为首的两派大臣之间长达十八个月的争论,最终以皇太后下书为止,后世称其为“濮议之争”。在这场争斗中,曾巩作为欧阳修的学生,通过《为人后议》这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曾巩;《为人后议》;濮议之争
濮议之争是宋朝著名的历史事件,曾巩作为当时的大臣,在其《为人后议》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曾巩的《为人后议》[1],主要的观点是为人后者,应当为本亲降服,但不应为此绝其父母之名。因此,这篇议论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
一、为人后者,应当为本亲降服
第一,降服可以明为后者之重。《仪礼·丧服》记载:“何如而可为之后?同宗则可为之后。何如而可以为人后?支子可也。”[2]按照曾巩的观点,《仪礼》此说是因为继承大统者,便应当明为后者之重,“天子之大宗,是为天地、宗庙、百神祭祀之主,族人万事之所依归”,《仪礼》乃曰“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收族者也”。因此继任者地位既尊且重,于原亲者降服,则可以强调自身继承大统之后身份地位有所变化,以此显出郑重之感。
第二,为后者因责任重大,须“割弃私爱,节之以礼”。天子之大宗,地位十分重要,如若不能遵循“礼”之传统,则就没有继承正统的资格。
第三,若已经从大宗之属,则应当“从所后者为服”,而为其父母,则降一等服齐衰期。如此便能显出大宗与小宗之区别,突显大宗之地位。
二、绝其父母之名
(一)亲非变则名固不得而易矣
意为血缘关系没有变化,自然名称也不应有变化。曾巩引用戴德、王肃之《丧记》云:“虽除服,心丧三年。”意为虽然服齐衰期,但其住所、言语、饮食等,当与原服相同。曾巩引用此文,意在证明称呼是血缘关系的外在符号,虽为人后者在政治关系上已从属于大宗,但在血缘关系上仍归属于原先的小宗,既然血缘关系没有变化,那么作为血缘关系外在表现的称谓也不应有变。不仅不能有变,更应在除服之后,在内心服丧三年,期间虽已除服,但仍应同服丧期间一样遵循礼制。而后作者又引崔凯《丧服驳》云“本亲有自然之恩”来说明,降一等已足够表明大宗之尊,而如果强行改亲者之名,则未免太过矣。这一点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以情为主要论点。
(二)适子不得后大宗
《仪礼·丧礼》中有云“适子不得后大宗”。曾巩在文中引用此句,意在说明,小宗之传重者不可以为人后,因为此人要继承小宗之传承,只有小宗支子,即非传重者才可以为人后。这种“使传重者后己宗,非传重者后大宗”的做法,是一种可以两全的做法,既保证了己宗的传承,又尽了保全大宗继承的本分,如此“两义俱安”。而若是因为降其一等则变革其名,使其父母不再是父母,岂不背离此种“两义俱安”的局面?《礼记·大传》有云:“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3]曾巩在此也作出解释。
夫人道之于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绝,尊尊也。人子之于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绝,亲亲也。尊尊、亲亲,其义一也,未有可废其一者。故为人后者,为之降其父母之服,《礼》则有之矣;为之绝其父母之名,则《礼》未之有也。
这一点以《仪礼》与《礼记》为例,说明尊大宗与亲父母同为圣人制礼所要求,不存在偏颇,不可废其一也。
(三)前朝史实论证
曾巩在文中举出前朝史实:汉宣帝同样是为人后者,在其称皇考、立庙之后,后人只评论其立庙不妥,并未议论其称呼皇考这一行为,因此说明称皇考是被允许的。而魏明帝为了禁止为人后者厚其本亲,故禁止将“考”称为“皇”,将“妣”称为“后”,但并没有禁止称“考”、称“妣”,因此皇帝称生父为“皇考”也应被允许。
(四)从情理出发,改之过矣
曾巩在文中指出,欲使为人后者改其父母之名,无非是“恶其为二”矣。然则“名出于实”,为人后者受过父母的自然之恩,如若强行令其改变事实,未免过之矣。虽然难以避免“为二”的局面,也仍旧有解决的办法,即“以礼引之”与“以礼厌之”。“以礼引之”即使为人后者,为大宗之主服斩衰三年,同时“为其祭主”;“以礼厌之”则是使为人后者为亲生父母服齐衰期,并不得为其祭祀。以礼为引导,弱化为人后者之“为二”,便不用以此为理由强行改变事实。这一点从解决之道出发,为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以上,曾巩从情、理出发,分别论证了为人后者不应改变对其父母的称呼。
另外,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考证了“皇考”这一称呼。提出“考”一词,只是对父亲去世的统称,如果不加位号、不立庙奉祠,则无“朝廷典册之文”与“宗庙祝祭之辞”,无不合礼法之处。
三、结语
《为人后议》有理有据,以《仪礼》为基础,举出各类实例证明为人后者在对待其亲生父母应有的方式。历史上,宋英宗于治平二年(1065)四月初就举行了崇奉生父濮安懿王的典礼。之后又令“有司博”求典故,以使自己的行为能合乎宗法,后又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前后罢官多人。最终在治平三年(1066),皇太后下书尊濮安懿王为皇,尊其夫人为后,此事才得以终了。濮议之争的重点在于宋英宗赐予生父濮安懿王及其三位夫人什么样的名分。从《为人后议》中可以看出,曾巩支持宋英宗的做法,主张不应改变其对生父的称呼,应追封其生父为“皇考”。
宋英宗向天下表明了自己“笃孝”的决心,其死后的谥号为“宪文肃武宣孝皇帝”,概括了英宗这一生最大的特点。
[1]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142-146.
[2]楊天宇.仪礼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00.
[3]宋元递.礼记正义[M].郑玄,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72.
【责任编辑:周 丹】
K244
A
1673-7725(2017)01-0205-02
2016-10-20
袁堃(1992-),女,安徽黄山人,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