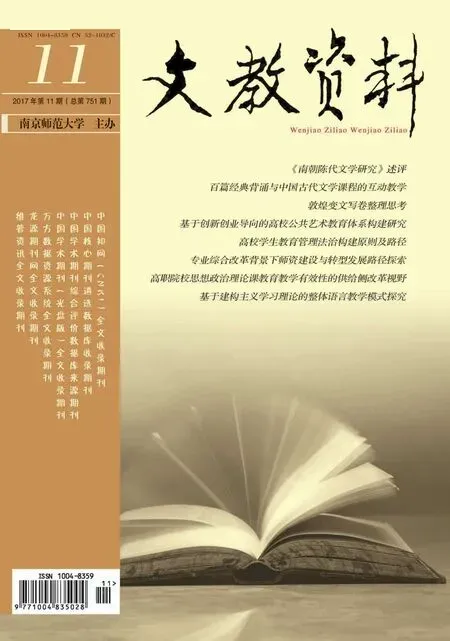回归本体,小中见大
——评胡峰《诗界革命——中国现代新诗的萌蘖》
李雁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回归本体,小中见大
——评胡峰《诗界革命——中国现代新诗的萌蘖》
李雁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现代诗歌的萌发、破土和形成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胡峰的《诗界革命——中国现代新诗的萌蘖》聚焦于新诗现代体式的萌芽阶段,剖析新诗与“诗界革命”之间的复杂关联,它让诗歌研究回到了诗歌本身——诗体,从发生学的角度切入现代诗歌的起始阶段,以翔实的史料和严谨周密的逻辑剖析“诗界革命”这一文学运动与现代诗体的联系,其价值在于对诗歌本体的关注,意义重大。
诗歌研究 本体 发生学
中国的古典诗歌从《诗经》开创的四言诗到屈原的骚体诗,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言诗、七言诗,至唐代出现了诗歌的大繁荣,诗歌流派众多,出现了杰出的诗人,创作群体从贵族、官僚扩展到社会各阶层。在诗歌的文体方面也异彩纷呈,既有古体诗,又有近体诗,既有新乐府,又有格律体,诗歌从体裁、语体到风格等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拓展丰富。进入现代,中国现代诗歌的转型发生在晚清,因此,传统的诗歌开始在质与形的两个层面发生巨变。这个过程是复杂而曲折的,并非一蹴而成。胡峰的著作 《诗界革命——中国现代新诗的萌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选择这个转折时期,聚焦于新诗现代体式的萌芽阶段,剖析新诗与“诗界革命”之间的复杂关联,寻找其背后的历史缘由,意义重大。
一、质:时代所决定的现代诗歌的“内”的塑造
诗歌是文学王冠上闪闪发光的明珠,诗歌所包含的语言的美、情感的美几乎凝聚了艺术所达到的极致,当然,20世纪后,小说成为文学研究的中心,这是时代的要求使然,毕竟诗歌所关怀的更多的是人的灵魂世界,是一个更缥缈空灵的存在。诗歌的研究者可能要比其他文体研究者具备更敏感精细的体验和严谨精密的逻辑思维,也需要更大的学术积淀与勇气,仅就这一点,胡峰的《诗界革命——中国现代新诗的萌蘖》就已具备特别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胡峰的视角不仅仅满足于对现代诗歌进行较为宏大、宽泛的审视,尽管对诗歌现象的宏大的观察仍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思考,但胡峰仍然寻找到一条更踏实和基础的学术视野,让诗歌回到诗歌,让历史回到历史,找到现代诗歌的萌发、定型的起始,找到现代诗歌、现代诗体之所以成为自己的动因、缘由与过程。
从时间性上观察,现代诗歌的萌发、破土和主干、枝丫的形成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从空间性上观察,现代诗歌的产生经历复杂的过程。其深层动因在于社会变革,而审美形态则受制于较多因素。其复杂在于诗歌的形成并非仅仅是纯粹审美选择造就的,存在外部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创作主体、西方文化、诗人主体等元素的干预,传统文化的知识背景、西方留学后的新诗歌资源的加入、创作主体的生长经历、美学理想、特定文学团体的审美追求等都在某段时期决定了诗歌的某种内涵,赋予了诗歌特定的理念、价值、立场、情感,在诗歌史上留下了深浅不一的痕迹,并在不同的时期被阅读者接受、鉴别、给予价值重审。
在这个时间的延展中,时代精神,时代的主题、需要是其中关键因素,其隐隐然决定了现代诗歌的精神取向,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决定了这个时代独特的精神面貌和品质,进而影响到了这一时期诗歌的风格气质。唐诗的繁荣,从纵向的诗歌的发展轨迹来讲,唐代以前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储备为唐诗的繁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唐诗的生存背景看,唐代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也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文治武功,欣欣向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积极趋势反射到诗歌的创作中,使唐代前期的诗歌充满积向上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彩,折射出一个民族建立了一个盛世王朝后的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对现代诗歌来说,现代诗歌史的撰写者们甚至以“20世纪”作为一个时间区间界定其属性,铸造了现代诗歌之所以称为“现代”的价值核心。现代诗歌的建设具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诗体的变革往往与时代、社会的变革紧密联系,因而文学的变革成为社会政治变革的有机部分。1917年的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运动,它的性质基本属于思想和文化领域内的革新运动,胡适曾经把这一时期当作一种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并且不无遗憾地回顾:“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1]胡适所持有的社会变革的文化立场使他对中国现代的从思想文化变革到政治变革耿耿于怀,这其中的价值判断是否中肯姑且不论,但它至少表明,我们所讲的现代精神在整个近现代历史上尽管光芒四射,像一束灿烂的闪电照亮了阴霾的历史的天空,它所涉及的问题尽管切入了中国现代化的根本,但它给予的历史启迪很快便被中国迫近的政治命题掩盖,中国人很快投入政治革新的实践过程中,而现代诗歌也裹挟进这一空前的革命热情中,热烈地追随着政治的脚步开始了与政治共舞的旅程。
二、体:多元因素下现代诗歌的“外”的形塑
“体”乃体式,是质所赖以显示的语言模型。艺术之所以称为艺术,文学之所以称为文学,诗歌之所以称为诗歌,很大一部分恰恰在于它所创造出来的言语阐释模式。传统的文学研究通常较为关注“质”的层面,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兴起,对小说体式的研究成为热点,带动了诗歌体的研究,但总体来看,诗歌的“体”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存在较多的空白点和薄弱点。说到现代诗歌,不仅在于内在精神的嬗变,应受到重视的还有重要的一点,即诗体的转变包括其内在本体的转变迁移,包括其语音、词汇、句式、意象、格律、结构、节奏、技巧的熔铸创新。其背后等诸种因素或隐或浅地与诗歌的形塑发生关联,影响着诗歌特定时期的样态。
胡峰的《诗界革命——中国现代新诗的萌蘖》的价值恰恰在于对诗歌本体的关注,它让诗歌研究回到了诗歌本身——诗体,从发生学的角度切入现代诗歌的起始阶段,以翔实的史料和严谨周密的逻辑剖析“诗界革命”这一文学运动与现代诗体的联系。在这里,胡峰所体现出的研究方法值得注意。
一是回归诗歌本体。按照胡峰的说法,“所谓诗歌本体,在这里主要是指构成诗歌审美世界的诸多要素的形态及特征”,诗歌的研究,与文学研究相似,大多采用的方法是外部研究,以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经济学等视角观察诗歌的形态,而且焦点在于诗歌的观念、情感等内容层面,反而对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的本体性特征较为疏忽,即便研究,一般的形式研究可能会停留在形式的范式、要素、结构,而胡峰则强调二者的融合,试图“在进行诗歌本体研究的同时,折射并勾连其背后所牵涉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形式’之外的‘内容’要素”[2]。因为内容产生意义,而形式也产生意义,形式并非单纯、脱离历史的存在,任何形式都是符号化的存在,存在丰富的社会、文化、心理意蕴。胡峰的研究恰恰在这一点上填补了前人研究的薄弱之处。
二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现代诗歌体式的建立不是一个必然的、确定无疑的过程,其中具有多种权利意志的角力,或者说,现代诗体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是历史与主体的共同构建。在这个过程中,时代、政治、哲学都参与现代诗体的形塑。近年来近代文学(或晚清文学)研究渐渐成为特点,近代已成为百年现代文学的起点,研究者从各个方面揭示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亲缘关系。小说与诗歌皆然。从新诗的发生上看,梁启超、黄遵宪所发动的“诗界革命”开启了现代诗歌的新篇章,“诗界革命”这一文学运动对现代诗歌的影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学术界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或者说还未充分挖掘“诗界革命”所包含的对现代诗体的引导价值。尽管“诗界革命”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和启蒙意义,但“诗界革命”提出的新诗的“新意境、新语句”的确已经涉及现代诗的体式的革新,在客观意义上展开现代诗的种种新的可能。胡峰的研究秉承文学的研究的历史的视野,从发生学上上溯初源,让诗歌回归历史真实,回到现代诗歌的客观环境,寻找被政治隐遮蔽的隐含的诗歌脉络,探查诗体内外诸多要素的勾连牵绊,寻找诗体起伏转换之间的背后的深层动因。
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文言的解体与白话的探寻”聚焦于现代语言的转换,包括口语、方言和新鲜词汇的运用,用历史研究的视角现代诗歌变革的场域与动因寻找其背后的理论基础与哲学阐释。第二章则是现代诗歌的声律研究,包括与现代诗歌韵律规则的突破和节奏模式的解放,作者选用了大量近代诗人文本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运用现代语言学和形式主义的批评理论寻找其规律和创作的得失。第三章是意象研究,包括物态化的意象与事象的类型学研究和更能研究。第四章是现代诗体的多维探求,研究现代诗人在诗体方面的创新,包括民谣体、歌体诗、散文体等诗歌样式。全书篇章结构合理,研究视角独特,内容翔实,逻辑清晰。特别是在史料搜集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胡峰的研究工作扎实,史料充实,坚持以史料为基础,重视原始材料的搜集,在这个研究较为浮躁,一些研究者不愿意花费时间、精力查找材料的时代,胡峰的踏实的研究精神殊为可贵。
诗歌是“高雅而又极为个人化的文学体裁,它具有诗人独特的情感体验与旁观者难以言说的话语表达方式”[3]。胡峰选择诗歌作为评说对象需要勇气,也反映了他对诗歌的当代关怀。中国诗歌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往,曾经留下璀璨的瑰宝,现代诗歌是现代人转折时期的精神记录,是一个民族寻求希望与新生的呐喊,而当代诗歌某种程度上陷入边缘化的尴尬处境,诗歌的言说与读者的呼应几乎处于难言的寂寞中,胡峰的著作把热情投注在现代诗歌、诗体的创新转变,在潜意识中也是一种希望,希望当代诗歌能继往开来,在喧嚣杂乱的时代坚持创造力,保持其恒久的美。
[1]胡适.胡适口述自传[A].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九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52.
[2][3]胡峰.诗界革命——中国现代新诗的萌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8,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