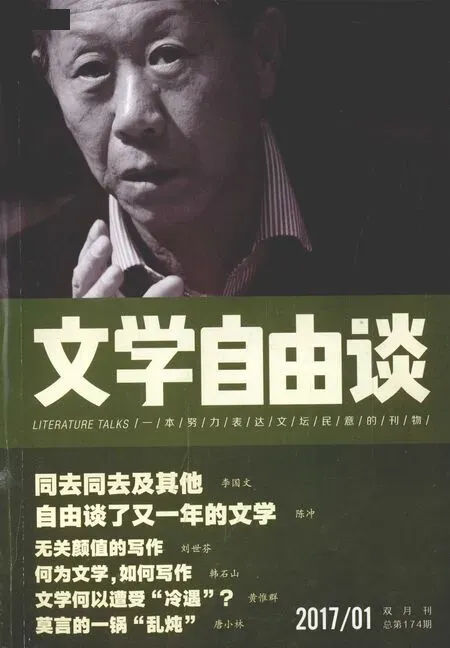来纽约为了相遇
〔美〕陈 九
来纽约为了相遇
〔美〕陈 九
旅居纽约二十多年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当你刻意去做某事,好像一切顺理成章,事后却发现,忙活半天不过是个背景而已,真正的目的另有所属,恍如冥冥之中早有安排,其意义早已超越你最初的打算。我来纽约从留学到定居的过程正是如此,因厌倦官场根深蒂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留学海外,拟通过自我放逐寻找丢失的个性,渴望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没人管,还能学本事拿学位,再把英语说利索了。 在国内时我老有“英语过关”的情结,不过关算什么有学问呀? 得说成串儿连成句,老一个个崩字儿多难堪啊? 总之,这些都是我当年出国的动机。
到了纽约,渐渐发现不那么简单。 上学也就是两三年的事,拿个硕士学位就行了,不能永远当学生吧? 再说“自由”这俩字,到纽约才明白,自由很简单,就是万事没人管,全靠自己奔,没人告诉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即使合法权益,你连知道都不知道,怎么争取啊? 越自由越惶恐。 看过电影《海上钢琴师》吗? 那个在船上长大的钢琴师为何不肯下船?下了船他不知道该怎么活,他受不了那种迷失无助的孤独,他害怕,宁愿与船同归于尽。每每看到这儿,我都情不自禁热泪盈眶,觉得自己正替他走下船,在雾蒙蒙的自由里奔吃奔喝奔生活,背后的大船已离我远去,我开始不可逆转的独行。至于英语过关,后来才醒悟,“过关”是指中国人关起门来和自己比,在美国你过什么关呀,永远过不了关,够用就得了,别再把中文忘干净就不错了。 而这一切都是自己当年的选择,如果那也算选择的话,说不出道不明的。
庆幸的是,我来的是纽约,事情便因此而不同起来。
纽约是座独特的城市,我一直想用一个词来比喻她:大码头,大货场,大影院,大博物馆,大时装秀,大饭馆……反正得有个大字,以示杰出。 纽约的确是座非凡的城市,可以说是座海纳百川的“世家城市”。它的历史虽无法同万里长城相比,但它什么都体现着日积月累的身价,珍惜每一滴历史荣耀,并带着荣耀一路前行。纽约是靠水滴石穿攒下的自信,使她成为巨大的文化参照系,像个大舞台——没错,大舞台! 这才恰如其分体现出纽约的魅力:一切成功或伟大在此最好别装,最好以本性状态表演。纽约是个容易穿帮的地方,搞不好闹笑话。 离开真诚,任何“伟大”都会因虚荣而一败涂地。
说纽约是舞台,是因为有太多人来此展示,这正是舞台的致命诱惑。如果说好莱坞是美国大片的舞台,纽约正儿八经就是世界的舞台。无论哪行哪业,最优秀的代表者必在纽约占有一席之地,这几乎是约定成俗的规矩。华尔街自不必说。当年美国“镀金时代”的代表者是费城,那里发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桶石油,是美国工业革命的结晶;纽约却利用水陆码头的天然优势,把金融证券业稳操手中。结果呢,算你狠,握住石油可以当富翁,而控制金融的则成为世界统治者。还有房产业,都知道迪拜的楼宇堆金砌银,可全加上也不抵半个曼哈顿。世贸大厦坍塌后为何非要在原地重建?那是纽约房产业,以至美国经济的信心象征。纽约二大道地铁线修了八十年尚未竣工,说资金不足,而重建世贸大厦的投资可修五条地铁,瞬间拔地而起,因为它是纽约霸主地位的权杖,就像当年成吉思汗的长鞭一样。 下围棋的都懂得“叫吃”,类似象棋的“将军”,世贸大厦就是面对“叫吃”长出的一口气,一口气就是一片天下。
既然是世界经济中心,文化必相得益彰。经济是啥?人来人往嘛。哪儿的人都到这儿来,日久天长便形成纽约文化独特的一面,那就是多元性和包容性。 有个统计数字说,联合国在册的世界语言共 195 种,纽约就存在 149 种之多。这么多不同文明的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惟有当年盛唐可以比肩。 从碎叶城下长安,李白父亲牵着五岁的小李白,风尘仆仆,走的是丝绸之路。 纽约却用金钱铺路,资本铺路,以至后来教育铺路,文化铺路,把众多精英汇聚旗下,形成巨大的“文化虹吸”现象,使纽约自然成为美国文明的旗舰。 从爱伦坡、霍桑、惠特曼、欧·亨利,到海明威、福克纳、梅勒,以及“垮掉的一代”(比如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无论其桑梓何处,都与纽约有着不解之缘。 好莱坞大多明星,像史蒂夫·斯皮尔伯格、小李子、汤姆·克鲁斯,均在纽约拥有宅邸,时不时便出现在曼哈顿的某个角落;纽约人巧遇名人的经历,不稀罕。 至于那些短暂停留的骚人墨客更数不胜数,很像当年的“下扬州”,未经过“瓜洲夜泊”的文人虽说也是文人,终怀有一份“思悠悠恨悠悠”的遗憾:看看,纽约还没去过耶!
洋人如是,华人亦如是。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曾国藩派出第一批旅美幼童始,中国近代史就与纽约难解难分,几乎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无论前清遗老、退役封疆,还是世家子弟、演艺名流,多少步履在此踱过,留下传说或湮没人海,在浩淼的时间长河里隐现着。 这么说不仅是一种陈述,更是丰富的感觉,像空气一样环绕着你。 我曾在《夏志清印象》中这样写道:“不久前我去一家叫‘白珠’的餐馆吃饭,都说那里风沙鸡做得好。发现隔壁有位老太太举止不凡,上前一聊,竟是冯玉祥家人。 还有一次我在华美协进社朗诵诗歌,下面有位年长女士风采夺目,经介绍方知是郁达夫的儿媳。还有民国外交家顾维钧的遗孀,爱新觉罗氏的金王爷,青海马步芳的后人,笕桥航校的少将教官,前国民党中央金库驻纽约襄理,中国近代史真是离不开纽约。 ”常说纽约是座五彩缤纷的城市,何谓五彩缤纷? 不是大都会博物馆,不是百老汇舞台剧,也不是时代广场、自由女神。从根本上讲,纽约的丰富是人,形形色色的人。 如果纽约真是座舞台,那么这些人来此不光为居住或闯荡,更为参加一场“人文演出”,在这座世界文化舞台上充任角色,彰显个性。
刚来纽约时心浮气躁,灵魂落在故里尚未带来,只知道走马观花,意识不到纽约的真正魅力。漂泊最怕找不着北,无所适从,老觉得自己是过路客,潜意识里不认同此地是你安身立命的另一处故乡。混在他乡只有随遇而安落地生根,才会以本地人的自觉心态关注周边环境,一个人影一声响动都会留意,你会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你只有属于纽约时,纽约才属于你,才会把自己的身世通过各种机会涓涓向你倾吐。比如在餐馆吃早餐时遇到胡因梦,过去只在电影中见过她,怎么突然竟从银屏上走下,走到我身边,坐在我对面呢? 还有著名学者董鼎山先生,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启蒙者,对我们这代人影响巨大,是我们高山仰止的偶像, 怎会在一次诗歌朗诵会后走上前对我说:“我叫董鼎山,非常喜欢你的朗诵”,像一位朴实慈祥的邻家阿伯?再比如著名散文家王鼎钧先生,我曾如醉如痴读他的《左心房旋涡》,揣摩他是怎样一个人,竟有如此超凡脱俗潇洒飘逸的智慧情怀?可就在纽约作家的聚会上,当我走向他介绍自己时,他竟先用山东方言对我调侃道:“呀,九爷,这不是陈九爷吗? ”搞得我无地自容,心中踌躇顷刻消散,充满无限的敬意。
这一切看似偶然,可这种偶然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吗?对我个人来说或许偶然,对纽约而言却是本性流露。 纽约的本质是啥?就是一部活着的历史,演不完的历史剧。我们在其他地方认为结束了的,在纽约却依然穿越着,从未中断。 这种感觉来源于生活的真实,再没什么比生活的本身更富戏剧性了。第一次在纽约遇到我从未谋面的 93 岁高龄的二舅爷,他是当年国民党中央金库派驻纽约的代表,曾组织过“美国医药援华会”,与陈纳德联名向马歇尔呼吁支援中国的抗战。抗战对我这代人来说早已结束,是过眼云烟。可当我面对他时,他说的语言,涉及的人物事件,仍充满浓郁的二战气息,让我瞠目结舌恍如隔世。 在曼哈顿的“华美协进社”朗诵诗歌时,“华美协进社”这几个字为胡适亲笔所书,是他和杜威教授用当年“庚子赔款”的部分返还,创办了这个以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目的的非盈利组织。仰望依然如新的匾额,时间仿佛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许就在我朗诵的位置上,曾闪过梅兰芳、刘半农、赛珍珠和老舍的身影? 俗话说物是人非,“人非”是没办法的,无法阻挡,可“物是”也不得了呀。睹物思人,历史才不会虚无。人们毕竟容易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纽约的每寸历史都不是虚无的,你只要在意纽约,心存敬畏,就已经徜徉在历史之中了。
居纽约二十余载,有太多“偶然”春风扑面。 什么东西都这样,一经启动便刹不住车,渐成模式。你只要注意对方,对方必注意你,这有点像谈恋爱,你老盯着姑娘看,人家铁定蓦然回首,看是否还在灯火阑珊处。 常有这样的质疑:你怎么总是遇到名人,咋就这么幸运呢? 答案还是上面那句话,只要心用到,芝麻芝麻开门来,纽约的文化宝藏自然会向你敞开,尤以那些活灵活现的人们为最。都说纽约藏龙卧虎,如何理解?关键是“藏卧”二字。这些“龙虎”都是以返璞归真的人生状态行走于纽约,洗尽铅华水落石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那才是人生最美妙的境界,最可爱的呈现。 当年著名的“唐夏论战”,唐德刚说中国小说好,夏志清非说西方小说妙,争执不下气氛凝重。可我见到的唐夏二人是在餐桌上,他们像孩子一样彼此调侃,酒酣耳热口无遮拦,让我感动。 还有京剧名家杨春霞,过去只在银幕上见过,可此时此刻她竟向我伸出手说,“来,拉您一把”,把我拉上台跟她一起反串现代京剧《智斗》,原来她的手也出汗,她的汗也是湿的。 名人不光是灿烂的,也是平凡的,只有平凡才真实可信,让你明白,原来每个人都可以活得很精彩。
原以为来纽约只为自由自在,可自由自在并不等于有滋味,丰富多彩。尤其当生活僵化成谋生手段时,就更原形毕露了。“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像老和尚念经,什么东西只要简单重复,每天上班连踩哪块石头都预先想到,那是多么麻木的情形。我始终认为麻木是死亡的一种。是纽约的多姿多彩拯救了生活,把漂泊变成相遇,与历史的相遇,与各色人物的相遇,仿佛冥冥之中自有主宰,为我落户纽约锁定归宿。为此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漂泊呀、他乡呀这些婉约派字眼儿,什么“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倚阑久,奈东风忒冷,红绡单薄”,还有“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这些情怀肯定有,但绝不是全部。 真实的纽约生活没这么酸楚,反倒蛮有味道,是独自一路。 你必须主动走近她热情追求,她会反身一把将你搂住,让你醉得喘不过气来。这是我的感受。
2016 年 11 月 5 日纽约随波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