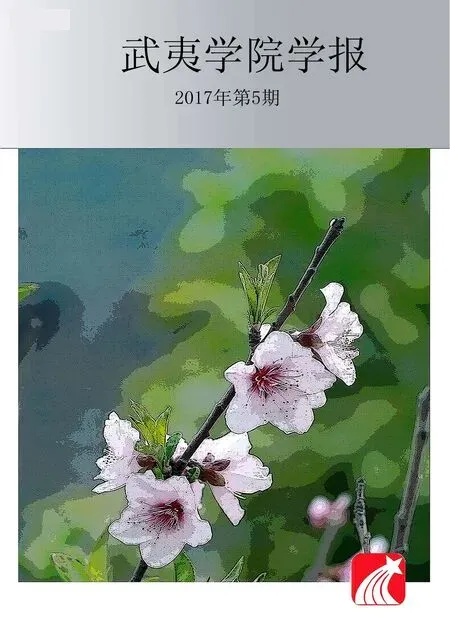人本主义视角下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冲突与并存
厉 越
(福建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人本主义视角下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冲突与并存
厉 越
(福建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高等教育哲学的认识论与政治论以一种对立又联系的矛盾关系并存于高等教育系统中,二者的争论不仅仅体现在哲学层面,而且对高等教育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无论是认识论哲学还是政治论哲学都没有从根本上诠释高等教育的本质,没有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忽视了人的发展需要和教育的本职所在。从人本主义视角出发,高等教育应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树立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和价值观,以此实现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的统一与超越。
人本主义;大学理念;认识论;政治论
一、高等教育何以存在:人本主义教育的观点
要探究高等教育存在的基础必然离不开对教育本质问题的思考。作为教育的子系统,高等教育与教育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一致的。只有把教育的本质问题搞清楚,才能对各种错综复杂的高等教育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进而指导具体的教育实践工作。古往今来,对教育本质问题的探讨一是教育理论界经久不衰话题,许多教育思想家都对“什么是教育”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形成不同的教育思想。柏拉图认为教育是心灵的转向。夸美纽斯认为教育在于培养和谐发展的人。斯宾塞认为教育就是为我们的完美生活做好准备。杜威也指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或改组,教育除了它过程自身,不存在任何外在的目的。综观西方教育史,虽然每个教育思想家对“什么是教育”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但这些思想又都蕴含着相似的教育理念,即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人的发展,人的教育才是教育的本质。特别是现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潮的兴起,将“人”的教育推向了极致。
人本主义教育思潮的兴起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它继承了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哲学,并结合了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成果。针对二战后西方社会过分崇尚科学教育和偏重智力发展,忽视学生兴趣、价值和个性发展等一系列危机,人本主义教育家要求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性,要求学校教育适应学生需要,发展学生的个性,促进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人性本位”,即以人为本,承认人的价值,强调人的潜能的发展。在教育的本质问题上,人本主义教育认为教育本质上是人性的养成和人格的培养,教育要发展人的个体性。通过教人如何去认识、去思考、去创造,唤醒人内心深处的价值感、生命感,培养富有个性、和谐发展的“完整的人”。如同人本主义教育家赫钦斯所说:“教育的目的,不在制造基督徒、民主党人、工人、公民、律师或商人,而在培养人类的智慧,由此而发扬人性,成为仁智之人,其归宿是人格,而不是人力。”[1]人本主义教育倡导的教育最终目的是人的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不在于其知识有多渊博,而是要落脚于人的潜能的开发,独立判断能力和独立个性的养成。人本主义教育思潮的出现切中了传统学校教育忽视学生兴趣、价值和个性发展的弊端,为人们重新审视和理解学校教育提供了正确的视角,对于扭转传统教育的过度理性化倾向发挥了积极作用。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给人们带来了诸多启示,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教育本质问题的理解必须以其对象—人为基点,对高等教育来说,大学应以学生为中心,教育要为了学生,教育要回归到学生。从教育与人的关系视角,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定义,教育就是促进个体个性的养成,价值的提升,让其更好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进而达到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样的,高等教育的本质也一定是教育性的,即以育人为根本,以养成学生的独立自觉品质,培养能够引导和改变社会的精英为目标。当然突出人的主体价值与大学发展知识、服务社会的功能并不冲突,教育的本质是教育功能实现的基础,学校教育功能的发挥无不是通过育人这一基本活动来实现的。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将大学的外在职能凌驾于其本质属性之上,更不能以职能实现为借口违背教育的本质,大学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活动也都是围绕育人这一本质而开展的。
二、大学理念的历史基础
探讨大学的存在和归宿,还必须溯源而上,回到大学的起点,从大学的最初意义上寻找答案。大学是什么?从纽曼到雅斯贝尔斯再到布鲁贝克,许许多多的教育家都对这个高等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时至今日,对于“大学是什么”的回答层出不穷,不断丰富着我们对大学的理解。虽然很难从这些纷繁复杂的定义中找到一个令所有人信服的答案,但是也不难发现,对大学的不同理解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也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从这一点来说,站在历史的维度上思考“大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对大学的产生、发展历程有个清晰的认识,才能懂得什么是大学之道,什么是大学真正的理念。
(一)大学的起源
“大学”是拉丁文“universitas”一词的译名,专指12世纪末在西欧出现的一种高等教育的机构。[2]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12世纪末的欧洲,大学的形成与欧洲自治城市的兴起和自治行会的出现密切相关。正如拉什达尔所说:“无论是先生大学还是学生大学,都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行会,大学的兴起只是11世纪和12世纪开始横扫欧洲城市的更大的社团运动的一个波浪而已。”[3]伴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复苏,自治行会逐渐完善并发展成为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遍布社会各行各业,出现了手工艺者行会、商人行会等。这为想从事高深学问的教师和学生提供了制度上的模版,他们聚集在一起并组织了自己的行会。巴黎和波伦亚的师生是最早组织起行会的学者群体之一。行会的组建吸引了大批热爱知识的教师和学生,行会的规模一步步的壮大。通过和教会或世俗权力的激烈斗争,学者行会获得了颁发学位证书和教学许可证的权利以及一系列特权,取得了独立的法人地位,获得了大学的身份。
首先是巴黎大学和博罗尼亚大学,再到后来的牛津和剑桥,一所所大学创立并取得合法地位,到15世纪,大学已经遍布欧洲各主要国家。随着学者的聚集,大学逐渐成为知识的中心,文、法、神、医等古典学科发展迅速,既培养了社会所需的职业性人才,如牧师、法官、议员等,又培养出引导社会舆论的学者,如哲学家、神学家、法学家等。即使是早期的大学,其属性也是多方面的,既包含知识性,也存在职业性。虽然当时的大学还仅仅面向少数人,但不能低估其对培养人才和活跃思想文化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等思想解放运动中,我们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大学的影子,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伊拉斯谟、路德、加尔文等改革先驱都是在大学成长起来的。
中世纪大学是“教师和学生的行会”,学生是大学兴起和存在的基础。正如神学家帕斯奎所说,中世纪大学是“由人建成的”。大学之于学生的意义,不仅仅是高深学问,更多的可能是地位与荣耀,通过大学学习,他们获得了进入国家机构和教会的通行证,担任官员、牧师、主教、议员等。大学之于社会的价值,也远不及当代大学来的“实用”,大学回馈给社会的更多的体现在道德和知识层面。知识性与职业性的双重属性,共同造就了中世纪大学的繁荣。
(二)大学职能的演变
大学职能是指大学“在社会分工中特有的专门职责”[4],规定着大学的功能与职责。之所以要从大学职能演变的视角探究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因为人们对高等教育属性的认识往往随着大学职能的变化而变化,大学职能对大学属性有着最为直接和明确的体现,亦可以说大学职能是大学属性的实践性体现。职能的演变根源于大学与外部环境相互关系的转变,影响着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选择。
自12世纪末现代大学诞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学的职能都相对单一,就是教书育人,为政府、教会等领域培养工具性人才。除此之外,大学鲜有其他职能,大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教化机构而存在。当时的大学思想相对保守,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并不密切,人们冠以“象牙塔”的称号。“大学培养的毕业生更多的是保存制度的技师而不是具有革新精神的思想和行动的发起人。”[2]科学研究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而仅仅是出于学者自身的好奇,属于个人活动。直到19世纪初,洪堡创建柏林大学,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办学理念深入大学的骨髓,在大学发展史上引起了革命性的变革,科学研究的职能才得以在大学确立。洪堡认为:“所谓高等学术机构,乃是民族道德文化荟萃之所,其立身之根本在于探究深邃博大之学术,并使之用于精神和道德的教育。”[5]大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机构,并且是发现知识和创造知识之地。以科研为导向的办学思想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并以德国柏林大学为起点,对欧洲及美国的大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所所研究型大学相继建立,大学进入了崇尚科学研究的新时代。
两次工业革命的兴起,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和发展经济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让人印象深刻,社会发展对人才、知识和技术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让大学介入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呼声日益提高。1862年美国《莫雷尔法案》颁布,赠地学院建立并在全美兴起,开创了大学直接服务于社会的先河。该法案规定:向各州每位议员赠拨3万英亩土地并售出,将所得资金建立永久性基金,用来资助、供给和维持至少一所专门学院,这所专门学院主要讲授农业和机械制造工艺等方面的知识,培养为当地工农业生产服务的各类技术型人才。[6]赠地学院运动不同于美国传统学院的办学思想,它将关心农业生产,推动实用知识和技术的推广等社会服务的理念蕴育于大学的建立及发展过程中,不仅推动了美国农业的发展,还引导大学走上了关心国家发展并服务于社会的道路。此后的“威斯康星计划”更是“把整个州交给了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指出:“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大学的主要职能,更为重要的,作为一所州立大学,它必须考虑每一项社会职能的实际价值。换句话说,它的教学、科研和服务都应该考虑州的实际需要,大学为社会,州立大学要为州的经济发展服务。”[7]在其领导下,威斯康星大学积极开展与州政府的合作,在全州进行技术推广和函授教育,为社会提供服务。这一服务社会的办学模式对美国其他州立大学甚至是私立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服务社会这一办学理念逐渐被认可并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大学发展的趋势和共识。
历经八百多年的发展,今天的大学已不同于中世纪时期仅仅以传播知识和培养人才为唯一职能的早期大学,大学早已走出象牙塔,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多元,融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为一体。大学的职能日益丰富,每一个职能的出现都是对大学固有职能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职能的演变既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也是大学自身发展诉求的生动体现。在大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应该看到无论其职能如何丰富和发展,其演进的核心仍然是人,是人的追求和创造的体现,是人类智慧的结果。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是人类延续大学存在的创造,因此其最终的落脚点也必须是人,虽然这里的“人”早已越过大学的围墙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学生。前文已经论述过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是育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也都是围绕育人这一本质属性展开的,教学是基础,科研是支撑,服务社会则是这一本质属性的升华。
四、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冲突与并存
关于高等教育哲学的认识论与政治论之争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最先引发这场争论的是1828年耶鲁大学发表的《耶鲁报告》,面对以实用学科为主的课程改革浪潮的冲击,《耶鲁报告》极力肯定以古典学科为主的人文教育的重要价值,排斥实用学科为主的专业教育,并声称“没有什么东西比好的理论更为实际,没有什么东西比人文教育更为有用”,强调共同学科如文学和科学的学习对学生的价值。虽然《耶鲁报告》的精神在19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哲学占据统治地位,然而多科技术学院、赠地学院、选修制的出现却让这种优势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由此拉开了美国教育学界进行高等教育哲学辩论的序幕。1978年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出版,他指出:“大学确立它的地位主要有两种途径,即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8]
持认识论哲学的人坚持大学按照自身的内部规律发展,即知识的发展规律。他们认为大学的存在的目的就是对知识进行尽可能深刻的思考,这种思考既不为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也不指向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仅仅是出于人们“闲逸的好奇”,不带有任何价值倾向和感情色彩。大学必须为知识而知识,以求获得最终的真理。为了实现真理的目的,认识论者试图让大学与外界划清界限,尽力保持知识的客观性和学者的自由。而持政治论哲学的学者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知识对国家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大学存在的目的就是通过发展知识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将大学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难免不使大学沾染上政治性,甚至将大学看作是政治的分支。大学要想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寻求外部权威的庇护,取得政治上的合法地位。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之所以会“缺乏和谐”,在布鲁贝克看来,二者的矛盾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想方设法摆脱价值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可能是认识到摆脱价值影响的想法过于天真,认识论者转而谋求 “价值自由”,他们所担忧的价值问题无非就是可能影响知识客观性的外界因素,包括感情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等一系列现实考量。学术一旦跨越了现实的鸿沟,知识便不再纯粹,容易受利益的摆布,其结果无疑是“学术的贬值”。恰恰相反的是,政治论者把价值问题作为了学术的组成部分,学者身份的变化使其难以保持以往的价值自由,不得不考虑其学术活动所带来的后果。布鲁贝克虽然引入了实用主义认识论的概念,试图以此调和认识论与政治论的矛盾,但结果如何,布鲁贝克对此也是模棱两可,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交替在大学占据支配地位,时而认识论占优势,时而政治论更强势,这主要取决于环境的变化。不管是认识论哲学还是政治论哲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据,无论是逻辑上还是实践上都能够得到检验且这种“交替领先”的局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继续。
虽然高等教育哲学的认识论和政治论难以实现真正的和谐,但却存在“共存”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必须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所谓的“建立”更确切的说是“回归”。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深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这也就不难理解其将“高深学问”作为其哲学体系构建的基点的缘由。抛开实用主义的影响而站在人本主义的高度,思考将高深学问作为高等教育的基点是否合适?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高等教育的本质是人,大学存在的核心是学生,正如纽曼那带有嘲讽的诘问:“如果大学的目的是进行科学和哲学的发现,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所大学要有学生?”人即是前提也是目的,对高等教育存在的争论自然不能忽视人的发展需要,而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其把高深学问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点,带有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将认识论与政治论冲突的症结归结于价值问题本身并无不妥,问题在于布鲁贝克并没有探讨价值问题的深层次意义。高等教育不管其职能有多丰富,其最终的价值指向既不是知识更不是利益,而是学生。大学如果忘记了其教育性,就不能称之为教育机构,履行好教育职责。从大学职能演变的历史不难看出,大学得以生存并延续至今既有认识论的因素也有政治论的因素,这两者既没有先后顺序,更没有重要性的区分,而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大学在履行自己的职能后可能产生功能,产生文化功能、经济功能等。这些功能是延伸性的,向外在延伸,向未来延伸。”[9]
雅斯贝尔斯说:“大学生活的一切都要仰仗参与者的天性。”[10]学生的发展需要决定了大学教育的目的。学生的需求具有多样性,有人进入大学是想追求“纯粹”的科学,本着求知的目的;而有些人进入大学更多的想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做准备,本着锻炼能力的需要。如果固守单一的认识论或政治论的理念办学,是否会扼杀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发展需要?这显然违背了大学的本体价值。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做才能真正恪守大学的本质呢,或许可以从英国的新大学运动寻找答案。面对牛津与剑桥对自由教育和古典课程的执着,英国高等教育适应科学教育发展的需要,采取一条迂回之路在传统高校之外建立了以伦敦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为代表的新式大学,这些新式大学相较于传统大学对社会需求更加敏感,具有全新的性质和目标。学校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开设讲授现代知识和科学的课程,如物理学、政治经济学、工程学、医学等,对科学、数学和商业等现代学科更加重视。新大学运动的兴起不仅促进了英国社会经济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更是增加了学生的选择余地,扩大了平民子弟的入学机会,对高等教育职能的转变具有影响深远。
从历史效果来看,英国的新大学运动确实是值得称赞的,且不管这项运动最初的动机或意图是什么,他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的影响却是里程碑式的。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传统大学虽然保守,拒绝对科学教育做出妥协,然而全盘否定这种保守性的做法不免有些片面,在认识论者的眼中,这种保守性甚至可能是值得称道的。当然这种保守性也不是绝对的,在新大学运动的压力下,牛津和剑桥在保持自身传统的前提下也适时做出了一系列改革,跟上了科学时代的步伐。在探讨新大学运动的社会功效的同时,不能忽视其实学生才是这项运动的最大受益者,城市大学的兴起增加了学生的入学机会;课程设置更加多样,既有文学、数学和哲学等古典课程,又有物理学、医学等现代科学课程,学生的选择面更广,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与需要选择学校和课程。英国的新大学运动在“保留”传统大学的基础上通过新建一批新式大学巧妙的避免了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的正面冲突,学生也能从中受益,是偶然也是必然。近年来我国积极引导和推动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发展,建设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型大学,这与英国的新大学运动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
在高等教育系统中,“保留”与“新建”大学是对认识论和政治论哲学冲突的有效避免,但若在同一个大学系统中,这两种哲学又要如何共存呢?克拉克·克尔提出了“多元巨型大学”的理念。“巨型大学是一个不一致的机构。它并不是一个群体,而是若干群体—本科生群体与研究生群体;人文学者群体,社会科学家群体,科学家群体,各专业学院群体;所有非学术人员群体;行政管理者群体。”[11]与传统大学相比,巨型大学更像是一个变化无穷的城市,它可以有多种发展理念,能为学生提供更加广泛的选择。它既能服务于教学和科研,又能服务于一般公众,具有多元化的目标。在克尔的多元巨型大学的设想中似乎看到了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并存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是否能变成现实还要打一个问号,毕竟多元巨型大学的设想能否真正实现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大学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大学的活动绝不会仅仅停留在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上,至于大学还有何种“潜能”,还不得而知。无论大学怎样变化,其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性不会改变,其育人的本质不会改变,大学种种“潜能”也必需围绕这一本质属性才能实现,而“教育是因人而生,因人而长,因人而发展和丰富的,由此去影响和变革社会,而不是相反。”[12]认识论哲学和政治论哲学的冲突与共存,即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又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源源动力。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的争论恐怕没有终点,它们代表的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两股力量,也是大学发展的两条路径,不管时代会作何选择,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将是学生。
[1]赫钦斯.教育现势与前瞻[M].姚柏春,译.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0:1-3.
[2]贺国庆,王保星,朱文富,等.外国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33,49.
[3]Rashdall,Hastings.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M].Vol.Ⅰ.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895:153.
[4]陈桂生.教育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33-234.
[5]陈洪捷,施晓光,蒋凯.国外高等教育学基本文献讲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33-134.
[6]徐继宁.中世纪大学与现代大学的职能比较[J].高教发展与评估,2009(01):77-83.
[7]刘宝存.何谓大学:西方大学概念透视[J].比较教育研究,2003(04):7-13.
[8]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2-23.
[9]张楚廷.评布鲁贝克的 “中心论”[J].高等教育研究,2013(03):1-4.
[10]雅斯贝尔斯.大学的理念[M].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47.
[11]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M].高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11.
[12]张楚廷.关于教育学的属性问题[J].现代大学教育,2012(06):5-9.
(责任编辑:陈 果)
The Humanistic Perspective of the Conflict and Coexist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Epistemology and Politics
LIYue
(School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108)
Higher education epistemology and politics are in such a rebationship that they conflict but connectwith each other and the debate is not just embodied in philosophical level,but also has a profound effect on higher education practice.However,both epistemolog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do not fundamentally interpret the ess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do not respect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people,and overlook the human development need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on.From the humanistic perspective,this paper think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 should be taken as the fundamental purpose,the people-oriented higher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values should be established,the unity and transcend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epistemolog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should be achiveved.
humanistic;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epistemology;politics
G649
:A
:1674-2109(2017)05-0084-06
2016-05-02
厉越(1992-),男,汉族,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