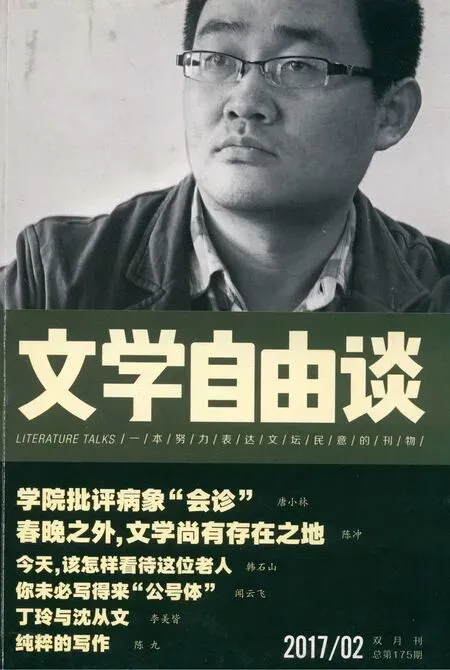是谁让毕飞宇“躺枪”?
曹澍
是谁让毕飞宇“躺枪”?
曹澍
今年第1期《文学自由谈》刊登了老曹的《毕飞宇,你实在不应该这样做》,对《文学报》上荆歌的文章《两个周洁茹》抒发了一点感慨。事后,《文学报》于2月4日在微信公众号上推送了江苏作家朱辉的文章《对荆歌〈两个周洁茹〉一文的说明》,并加了编者按。老曹读后,颇多不解。
在老曹看来,《文学报》(本文所说的该报,包括其纸媒和微信公众号)对“毕荆周事件”发表的两篇文章,貌似还原真相的辩诬,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锦上添花”——说是“越描越黑”也未尝不可。《两个周洁茹》对“欠一夜”事件,可谓叙述清晰,描写细致。尽管已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但对毕、周之间的对话都写得清清楚楚,而朱辉说毕飞宇无辜“躺枪”,怕是与事实——确切地说,是荆歌之所述——不符吧,或者说,是过于低估了荆作家的记忆力和诚实的写作态度了。就凭这一二三四的“证言”,若想把毕飞宇洗白,真是异想天开了。貌似辩诬,实则坐实,如此一来,此事就是跳进扬子江也洗不清了——这可真是应了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的网络谚语。可见,若说毕飞宇真的“躺枪”了,那这一枪还真不是老曹开的。
朱文的开头说“《两个周洁茹》读来蛮好玩”,《文学报》的“编者按”也说荆歌是在“趣谈”。老曹奇怪,这感觉怎么跟读者的感觉大相径庭呢?我接触到的读者,并没有觉得它有多“好玩”,也没有觉得那是“趣谈”,而是觉得非常无聊,十分低俗。难道该报和毕荆朱等作家对趣味的判断标准已经滑到普通读者的标准之下了?老曹以为,倘若《文学报》弃用《两个周洁茹》,“欠一夜”就只能是几个当事人闲来无事“把玩”的旧事,顶多也就是他们在朋友圈中调侃的段子,根本见不着阳光。
朱辉说:“这件事,是小说家聚会。小说家言,当信史用劲读,那就寡趣了。”这个说法真是太轻松了。民间有句俗语叫“事怕颠倒理怕翻”。老曹忍不住像曾经请教过毕飞宇那样,再请教一下朱辉:倘若周洁茹是你的妻子或者妹妹,你还会这样说吗?更何况“小说家聚会”与“小说家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小说家聚会”是指写小说的人的聚会,而“小说家言”就是指写小说的人的作品。朱辉的言外之意是:“欠一夜”确有其事,而《两个周洁茹》则是“小说”,其写到的毕、荆、周,并不是生活中的大活人。
那《两个周洁茹》到底是虚构的小说,还是写实的散文?这个问题老曹说了不算,朱辉说了也不算。谁说了算?大概是《文学报》说了算:它并没有把《两个周洁茹》当成小说,而是放在“人物版”的“作家说作家”栏目。显然,这就是一篇散文。而散文的情节是不允许虚构,必须真实;这一点,朱辉知道,荆歌也知道,因为这是常识。再说,当时还有一屋子参加笔会的“兄弟姐妹”,荆歌自然是不想瞎说也不敢瞎说,更没必要瞎说,他只是如实道来而已。既然如此,把《两个周洁茹》当作真人真事来读,或者像朱辉说老曹那样“当信史用劲读”,又有何不可呢?——至于它是否具备让老曹“用劲读”的分量和必要性,则又当别论了。
写到这里,老曹想起一件事:1990年底,史铁生给《上海文学》编辑部寄去《我与地坛》,编辑部打算将其作为小说发表,但史铁生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写的是散文,不是小说。据说,编辑部要把《我与地坛》当小说发,原因有二:一是那期正好没有重点小说稿,二是《我与地坛》用了很多小说技巧,比一般的散文写法复杂得多。双方僵持不下,史铁生甚至想要回《我与地坛》,投给别的刊物。《上海文学》实在舍不得。最后双方妥协,既没有标明是小说,也没有标明是散文,而是以“史铁生近作”的归类发表。
史铁生自己知道《我与地坛》是散文,荆歌自己也该知道《两个周洁茹》是散文,朱辉心里也同样清楚这一点。既然是散文,怎么就不可以当成“信史”来读呢?对“欠一夜”事件的评说,“上升到道德高度”有什么不妥吗?——除非衡量作家和非作家必须用两个道德标准:非作家挑逗小姑娘是行为不端,见不得人,而作家做了这样的事,就成了文坛佳话,并且蛮好玩,好玩到值得大肆宣扬;况且,作家难道就有免受道德评价的特权吗?
按《文学报》“编者按”的说法,老曹的文章,“对当事人毕飞宇、荆歌、周洁茹都产生了困扰和影响”。老曹疑惑的是,这“困扰和影响”的始作俑者,不正是《两个周洁茹》和发表它的《文学报》吗?对毕飞宇的困扰可能是,南京大学里听毕老师课的莘莘学子读了这张报纸,将如何看待才华横溢、幽默风趣、平易近人又英俊潇洒的毕老师?“知天命”已经三年的毕老师,又何以面对比他小三十岁左右的学生?再说荆歌,他已是“奔六”之人,想必他的孩子早已成人甚至成婚,这事万一让孩子知道,尤其是,如果这孩子还是个女儿,她会怎样看待身为作家的父亲?如果是儿子,儿媳会作何感想?说真的,“毕荆周事件”让老曹不由得想起当年迅翁怒斥“杜荃”是“才子加流氓”的旧案。
朱辉说,他是在周洁茹的朋友圈看到《两个周洁茹》的,以此来证明这是篇无伤大雅、没有伤害任何人的文章。周洁茹和她的朋友如何看待荆歌的文章,那是她和她的朋友的事,老曹不了解情况,不宜臆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周读此文的感受,绝对不会和毕、荆一样。此无他,是人性使然,而他们三人确凿无疑是有人性的。对这同一件事,世上焉有欺人者和被欺者、戏人者和被戏者都津津乐道回味无穷的道理?简单地说,前者是痛快了,后者是痛苦了,除非后者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否则,你打死我,我也不相信周洁茹对荆文及“欠一夜”事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从荆文中我们可以确定,周洁茹很在意此事:对“欠条事件”及其传播效果,“周洁茹很生气,给我打来电话,颇多责怪”。——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她事实上会有并不以为意的反应,那也许是时过境迁的十几年之后;或者,老曹确实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了。
老曹纳闷,堂堂上海滩的一张国家级大报,为何把身段放得如此之低,刊登出如此拿无聊当有趣的文章?难道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而有意为之?老曹不得而知。但是,《两个周洁茹》确实是实实在在地挑战了读书人和普通人的道德标准。老曹并非在恶意“大做文章”,而正是为了让“文学之事能回归本意”——学过中国古典文论的人都知道,“知人论世”正是传统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方法。《文学报》不至于认为只有作品才算“文学之事”,舍此而外的作家的种种都不在文学的范畴吧?否则,它也不至于开设“人物版”和“作家说作家”栏目了。
其实,朱辉的文章和《文学报》的“编者按”,只能把“毕荆周事件”越描越黑,这种做法极不明智。设想一下,如果《文学报》坦坦荡荡地认个错,反而会让读者仰视、敬佩;当然,沉默以对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唯独选择在微信公众号上辩诬,才是最不理性的。最晚自1842年咱国被迫开埠以来,江湖上都说上海人和江浙人善于领风气之先,站位高,脑子活,但“毕荆周事件”却让这一方水土人杰地灵的美誉蒙羞。
老曹真诚地希望当事各方,能通过“毕荆周事件”反躬自省,举一反三,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犯这种低级错误。老曹还想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虚怀若谷的胸襟和闻过则喜的姿态,更令人肃然起敬,更符合现代文明。
2017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