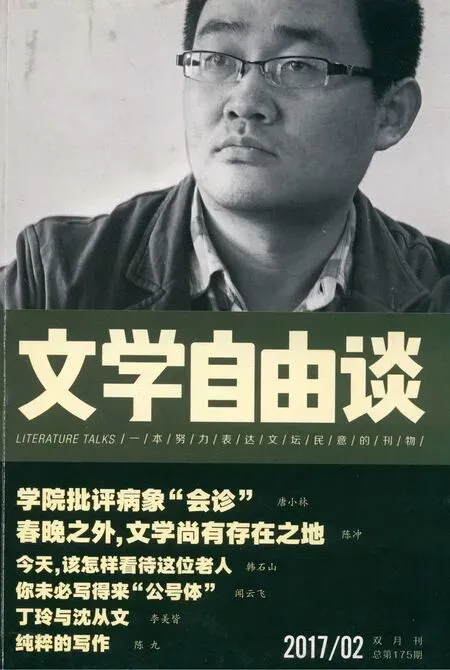打 赏(外一篇)
何永康
打 赏(外一篇)
何永康
一个文学圈的朋友,突然给我发来30元微信红包。我问何故?他说他弄了个微刊,转发了我一篇文化随笔,有读者阅读后打赏,这30元是分红。
打赏?分红?写个文章居然还有这等好事。我的脸发起烧来。从来不入股不炒股的人居然可以分红,居然还有人给我打赏!
据我所知,打赏的“赏”是赏赐的“赏”,一般来说,是上对下的激励和褒奖。譬如过去皇帝给臣子赏赐,官员给百姓赏赐,富人给穷人赏赐。《红楼梦》里经常写到主子给仆人赏赐。林黛玉就是一个慷慨的主,是个体恤下人的性情中人,凡有其他姐妹的丫鬟给她送东西过来,多少都要打发点散碎银钱;而薛宝钗似乎就很少这样,也不是说她多么吝啬,乃节俭持家的“好”女人也,难怪一天到晚把文章经济挂在嘴上,让贾宝玉烦。打赏得人心。看起来性情刁钻的林妹妹却人缘很好,而性情端庄的宝姐姐却让人难以亲近。由此看来,打赏是收买人心的手段。
那么,当下的“打赏”是什么意思呢?“度娘”说,在网上发布的原创内容,包括文章、图片、视频等,如果用户觉得好,看着喜欢,就可以通过发红包的方式表达对你的赞赏。近年来,不少作家诗人开起了微信公众号,原以为是为了便于交流,最不堪也就是显摆或者炫耀,没想到一些人“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并不那么单纯,已经不满足于“点赞”了。微博、博客和微信都增设了打赏功能,目的是让掌控平台的人从中获利,广种薄收,集腋成裘,借助文化发大财,也让俺们作家诗人发点小财——恰如民间所说,吃一个虾子分一只脚。
在古代,统治者最爱给文人打赏,说小点,是满足文艺帝王之雅趣;说大点,是显示朝廷对文化的敬畏,对文人的尊重。三国时,邯郸淳创作了一篇《投壶赋》,魏文帝曹丕认为写得好,遂“赐帛千匹”。《投壶赋》总共才一千多字,几乎一字一匹,也算得上是“一字千金”了。南北朝时,爱好文学的梁简文帝萧纲也爱打赏,“弘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皇帝的赏赐代表皇恩浩荡,物质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和恩宠,当然是要跪拜并山呼万岁的。对普通百姓来说,你和文人不是朋友,是断不敢轻易给文人施舍银两的,要么你就买一本刻印的书回家读,要么就是请文人喝杯小酒,吹捧一番了事。文人清高啊,你让人家的诗文沾上铜臭,岂不是糟蹋斯文、亵渎圣贤、打人白脸、毁人清誉吗?
古代很多文人都视金钱如粪土,今天的某些文人则视金钱为父母,以至于唯利(微利)是图,无孔不入。文人也是人,要养家糊口,卖文赚钱无可非议,收受润笔也合情合理。报刊、出版社和一些机构给你稿费、版税或奖金,其实就是给你的酬劳,你可以理直气壮地领取。但有的人却一味地向读者讨赏,违心地迎合读者以提高关注度和点击率,却偏离了“良心写作”的基本路线,就没有多少文人气了。这和网站视频中那些搔首弄姿、大尺度暴露隐秘的所谓“女主播”,以色相换取好色之徒的打赏有何两样?
这样的“打赏”,其实是“打伤”。打伤的是文学的品质和文人的品行。
君子固穷。我非君子,也不富裕,但尚未沦为乞丐,靠施舍度日。因此我实在是没法接受“打赏”这样的“礼遇”,便找了个机会,把那30元微信红包在一个微信群里散发了。唯如此,方能心安。
不妨缺席
有人说过:“当作家是要有成本的,最大的成本就是甘于寂寞。”这话很有道理,孤独体验历来就是作家的必修课,或者说是家常便饭。
然而,今天不少作家似乎“与时俱进”了,在浮躁的大背景下跟着浮躁,在喧嚣的大环境下附和喧嚣,总是沉静不下来。除了饮酒品茗喝咖啡、打牌下棋逛景区之外,还要去各种场合 “雅聚”,冒个泡,露个脸,扎个场子,刷个存在感;余下的时间还要交给网络,用“扣扣”、微信聊天,发不完的动态与状态,记不完的思想与行止。近年来,“微信公众号”也开始满天飞了,一些作家又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的新作旧著编辑制作一番以昭示天下,泛交五湖四海,尽显七情六欲。真不知道他们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来读书、思考,以及走心地写作。
被人遗忘,会被边缘化,就会有人说你“缺席”了,老了,走不动也写不动了,江郎才尽,油尽灯枯。其实,在我看来,缺席并不是在作时间的考量,有时候大把大把的时间是虚度的;也不是精力和笔力不济,“廉颇老矣”但尚且能“饭”。缺席,仅仅是图个心灵安静和耳根清静。
“孤独是灵感的催化剂。”这是大学者陆谷孙的一句名言。陆先生一生信守“寂寞出学问”的信条。不论是在动荡喧嚣、黄钟毁弃的荒唐“文革”中,还是在学术界浮躁炒作之风大行其道的当下,他都年复一年地独自窝在书房里,被学界尊称为“老神仙”。为潜心向学,“缺席”是陆先生的家常便饭,成为众人皆知的处事常态——缺席庆功宴、拜师酒、颁奖会,缺席一切与学问无关的社交。他的口头禅是“让我一个人呆着”。
如此看来,缺席,是一种大境界。
很多作家朋友的家里或办公室的墙壁上都挂着“宁静致远”四个大字,但大都是当书法欣赏或作为装饰点缀,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去践行这几个字,恰如我们经常批评社会浮躁、人心狂躁,自己的心恰恰也安静不下来。在光怪陆离、日新月异的社会里,名利的诱惑、感官的刺激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难以抗拒。就拿文化来说吧,近些年是大大的繁荣了,官办或民办的各种论坛、峰会一个接一个,让人目不暇接。文化人的活动更是多如牛毛,新书首发,座谈研讨,作品品鉴,名家讲座,创作体验,诗歌朗诵,等等,名目繁多,层出不穷。但这类活动,很多不外乎是觥筹交错的宴会,漫无边际的清谈,千篇一律的雅赏,相互吹捧的“研讨”……一个作家朋友经常向我抱怨,说应景太多,跑路太多,听空话说空话太多,根本静不下心来履行作家的本职——创作。
我就在心里嘀咕:就不能缺席一下吗?
想起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来。小说中,华威是一个披着热心抗日救亡的文化人外衣的国民党党棍。他到处开会,到处演讲,到处应酬上层宴会,忙得不可开交。他的忙,其实质是企图操纵一切,无孔不入地攫取权力与名利。小说发表已将近八十年了,华威先生夹着公文包,神情严肃、行色匆匆地从一个会场赶往另一个会场的市侩形象,依然复制粘贴在今天某些人的身上。这是文学典型形象塑造的成功,却也是批判现实和警醒世人的文学功能的失败。这当然不能怪作家,是千百年来人性弱点积淀成的抗改造势力的顽固习性所致。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道:“学须静也,才须学也。”写作也是一门学问,作家也应该是学者,需要独思与静处,而独思与静处,前提是要学会缺席。
缺席,意味着要和某些人与事的疏离。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食人间烟火,更不是逃避现实,是退后一步,让灵魂与这个世界产生一定的距离,才能把生活看得更透彻,更接近本质。好像观赏一副人物油画,近看,全是斑驳的色块,保持点距离,才能通过色调的明暗对比看到面部表情,读到肢体语言,看出人物与环境、背景的关系。
古来圣贤皆寂寞。其实,敢于和善于寂寞的人是不会真寂寞的。有书为伴,有先哲为伴,有自己笔下的人物为伴,有自己的思想为伴,寂寞从何说起?身居斗室,依然可以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笔下依然可以风生水起、波澜壮阔。都说作家凭作品说话,只要有拿得出手的作品,即使你缺席了某些场合,但你依然不会缺位——你真正的位置在读者心中。
当然,我所说的缺席指的是“选择性缺席”。凡事绝对不得。绝对缺席等于出局。作家不能一味地离群索居、孤傲清高。名利场、风月场是可以缺席的,而生活场(譬如下基层)是万万不可缺席的,缺了,你就没有气场了。
历史告诉我们,高妙者往往通过缺席,或成局外人,作壁上观,审时度势,以待天时,如辞官为民的陶渊明、静待明君的姜太公;或殚精竭虑,焚膏继晷,三年不飞,一飞冲天,如平凡世界的路遥、白鹿原上的陈忠实。
作家不妨学会和适应缺席。缺席,其实是让心灵隐居一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泥脚印儿》
徐连云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这是上世纪60后一代人关于成长经历的记忆书写。作者以朴实的笔触,还原了那个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真正面貌,揭示了那个年代中人与事向前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