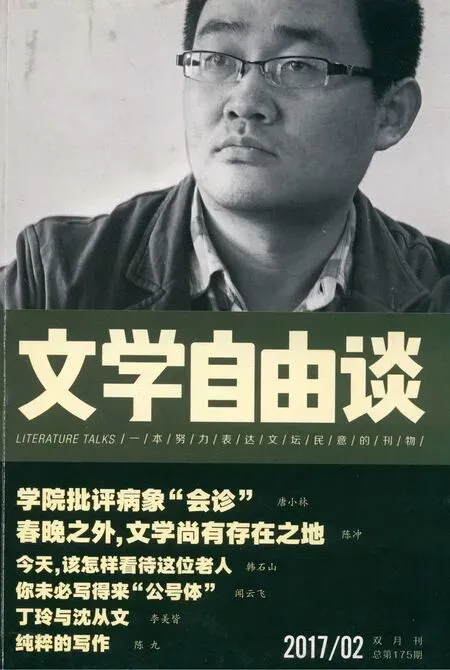春晚之外,文学尚有存在之地
陈冲
春晚之外,文学尚有存在之地
陈冲
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摇滚歌手鲍勃·迪伦。对中国文学界来说,这种事应该不是太突然,因为就在不太久以前,我们也认真讨论过崔健可不可以参评鲁迅文学奖的问题。这个讨论公众知道的内容并不多,人们比较有所了解的内容之一,是有个叫谢冕的北大教授,乃力挺派的主力。后来传出一个消息,说这位北大教授退休后住进了敬老院,于是广大人民群众不答应了。这个“不答应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是个很含糊的群体,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那里面不一定有听过谢冕授课的学子,也不一定有对崔健应否参评“鲁奖”持有任何看法的人,但他们表示的“不答应”是有力量的。他们这么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或者是因为他们觉得像谢冕这样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我们”不应该亏待他们,也或者还有别的原因。后来弄明白了,谢教授进的敬老院很高档,他住进去是想体验一下那里的高档服务,不是因为老无所依,广大人民群众也就放心了。这个“放心了”的“广大人民群众”,也是个很含糊的群体,里面不一定有智商极高的聪明人,也不一定有知识渊博的精英人士,但是他们肯定不会被任何人忽悠,比如那种伪摇滚的自恋自慰。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老无所依了,把你留在哪儿都够呛。
正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在这样混混杂杂缠缠绕绕地进行着,所以近几年来,每年的第二期《文学自由谈》,我都会把春晚扯上,一是借借它的话题性的光,同时也是给文学一个不同的角度,比如其中第一篇的标题就叫《文学眼看春晚》。到去年,这事儿有点难以为继了,因为似乎春晚里不怎么能找到文学了。你怎么能假装用文学眼,去看找不到文学的春晚?但我也不认为这就说明“文学已死”。我不喜欢动不动就说什么“已死”,况且这事儿真没那么严重。一台晚会里要不要有文学,完全是主办者的事,别人尽可不必操心。之所以还想议论几句,是因为忽然有了一个猜想:没有文学,不一定是主办者不想要,说不定是找不到能往里装进一点文学的写手了。
这么说真的有点不厚道,姑妄言之,就从比较容易说的地方讲。就不说文学性不文学性的了,只说文学里最基本的那个东西:文字。如果把一台晚会的文字整个儿翻一遍,工程量明显太大了,还是得随机抽样。说是随机,也还是有点代表性的好,这儿抽的样就是晚会后据说颇受点赞的歌:毛阿敏和张杰唱的那首 《满城烟花》,说是让人又想起了当年的风采和盛况。当年的风采和盛况我是记得的,就去找来看。很惭愧,毛阿敏的风采一时间没有抓到,她在舞台上的形状,已经被据说要花费上亿元的灯光切成了碎片,不过她的歌声还是让我记起了当年那上佳的汉语歌词: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这是谁的手笔,人们应该还记得,不用再在这里提醒了。可也就在这时,现场传出的一句歌词,已经像射钉枪里射出的钢钉,钉在了我的现实感觉上:“每当烟花推动世界年轮”!这是汉语吗?任何一个能通过小学毕业考试的学童,应该都能知道,“年轮”不是一种能转动的“轮”,也推不动,不仅虚张声势的烟花推不动,就是实打实的“长征5号”火箭也推不动。如果这个“世界”指的是地球,那么它一旦长出年轮来,就不可能是一个“球”了,只能是一个圆柱体;而一旦这个年轮转动起来,最可能出现的景观就是一层层往下掉皮,相当于天崩地裂,“世界”解体。中国人使用汉语已经几千年了,早已形成了严格的汉语诗学的规律和规则,意象怎样形成,联想怎样建立,意境怎样营造,都有特定的途径,不是字面上有一点重合或近似,就可以硬往一块去捏——看见一个“轮”字,立刻就有了车轱辘;也不是中纪委下令“老虎苍蝇一起打”,动物园里的老虎就吓得躲进老虎洞里不敢出来了。
这其实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用逻辑倒推的方法往以前“捯”,这个过程是可以捯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有时候好像不在,其实在。比如想到那些年时,我们都还能想起一些名字——阎肃、乔羽、刘炽、谷建芬等等,我们会说他们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词作家、作曲家。后来这些名字渐渐从“音乐界”淡出了。你或许还记得,谷建芬“金盆洗手”的时候,说过一句很伤感、但绝对是很清醒的话:我已经看得很清楚,现在的音乐界已经不需要我这样的作曲家了。这句话在当时相当地不好懂——音乐界怎么会不需要能创作出优美旋律的作曲家了呢?要到那个过程结束以后,人们才明白为什么不需要阎肃、乔羽、刘炽、谷建芬那样的词作家、作曲家了。在那个过程中,为了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多人付出各自的努力,相当地不容易。不说别的,单说要建立那样一支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的“职业观众”队伍,最后达到每年上十亿元的产业规模,容易吗?但是,这个任务最终还是完成了。这个过程相当长,做得也不是那么公开透明,再加上种种的遮遮掩掩,很多人都以为它早已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这是可能的,但并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中国历史的好玩之处,就在于它的不可终结性。总有人认为存在某种永不结束的东西,这个主要是让皇上们闹的。皇上们当然是万寿无疆,从理论上到制度上都可以千秋万代地把皇上一直当下去。但是也会出现一些其他情况,比如皇上身患重病,大臣们不得不跟他讨论其身后之事了。看来这是个根本无法讨论的问题,皇上怎么会有“身后”之事呢?但中国的大臣们是有足够的智慧解决这种事的。他们匍伏在地,磕三个响头,然后开口奏曰:启奏万岁,皇上千秋万代之后……对了,就这么简单,既然有千秋万代,就会有千秋万代之后。
其实,这个“千秋万代”之后,并不一定真要等很长时间。比如,在某一个“千秋万代”之后,广大人民群众不答应了。他们可能会问,在“千秋万代”之前的某一个时期,有一段不短的时间20年、30年,偌大一个中国,那么广袤的土地,那么众多的人口,为什么竟然没有出现哪怕一首稍微像回事儿的器乐曲,能够在音乐会上反复演出并受到听众的喜爱?就算是一句单抽出来的旋律,能够用某种乐器正常地演奏出来,让人听了以后能回味上一段时间,有吗?事实形成之后,真相自然就显现出来:这是一段几乎没有情怀、没有旋律的音乐史。这种情况的制造者,有可能含糊过去,也有可能被翻出来,谁个说过什么,谁个做过什么,谁个投过哪笔缺德资,谁个赚过哪笔昧心钱,张三李四刘五赵六王二麻子,一个个都被五寸长钉钉在中国音乐史的耻辱柱上。这就是不相信存在一个“广大人民群众”的结果。当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到“人民”这个词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看懂了他脸上那种敬畏的神态和情怀;而当他和阎肃侃侃而谈,对这位优秀的词作家给予极高的评价和期许时,有的人可能正在暗自庆幸,得意于已经先行一步,早把那个不需要这样的词作家、作曲家的局做好了。
想到这些,我也得为我们的文学界暗自庆幸了。文学界真的还远远到不了这一步。春晚里没有文学了,自然还会有人去看;而春晚之外,文学还有广阔的天地。就在不久之前,我就读到过两部出自年轻女作家的佳作,一部是张悦然的《茧》,一部是付秀莹的《陌上》。这两部截然不同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别令人高兴之处,就是都展现出了扎实的、上乘的“描写”现实的基本功。文学中的“描写”,相当于音乐中旋律;没有描写的文学,跟没有旋律的音乐是一样的。我一度有过担心,觉得文学的这种最基本的能力正在弱化,搞得不好甚至有可能失传,不想却在两位这样年轻的女作家身上再次闪出光芒!正像曹文轩在为《陌上》所写的序言里所说:“在一个失去风景的时代,阅读她的作品,我们随时可以与风景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