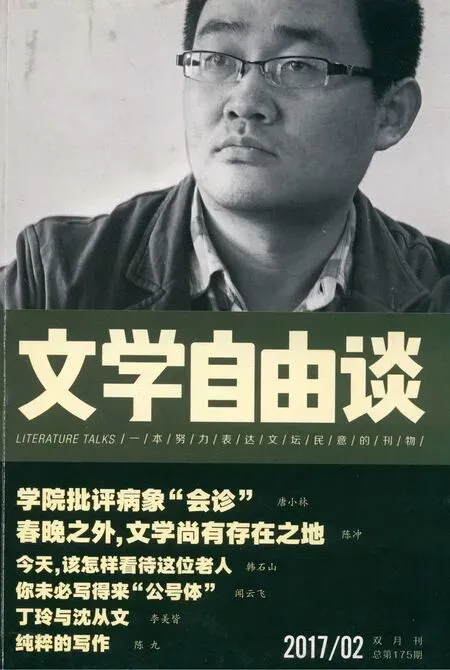学院批评病象“会诊”
唐小林
学院批评病象“会诊”
唐小林
在当代文坛,学院批评长期广遭诟病。一些大学已经变相成为学术垃圾的生产基地,某些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早已蜕变成为学术垃圾的“生产能手”。有的学者虽然大红大紫,著作等身,但其学术“成果”,大都是一些貌似“高大上”,实际上却缺乏学术含量,甚至在“忽悠”读者的“学术砖著”。多如牛毛的作家作品研讨会,往往成为学院批评家们倾情表演、集体歌唱的人生大舞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批评已被某些学院批评家当成了跑马圈地、为我所用、翻云覆雨的文字杂耍和屠龙术。在这些批评家看来,文学批评是没有是非标准和审美判断的,最多只有个人喜好。对于作家的同一部作品,他们今天可以愤怒猛批,明天可以拼命狂捧。总而言之,收鬼和放鬼的,都是这些批评家。他们采取有失批评家尊严的方式,跪在地下,一叩三拜,大唱赞歌,将文学批评当成了向当红作家大抛“媚眼”、求得青睐的文学谀评。在他们看来,所谓文学批评,其实就是向当红作家溜须拍马的谄媚书:于是,在众多的学术期刊中,我们看到了古今中外罕见的肉麻文字。
本文“请出”的几位批评家,虽只是当代学院批评家中极少数的几位,但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标本意义。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症状”,集中反映出当今学院批评典型的病灶,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学院批评深陷泥淖的典型特征。如何将学院批评的各种顽症汇总起来,进行科学的研判和医治,可说是当代文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必须时刻面对的一个巨大的难题。
孟繁华:出尔反尔为那般
1993年,贾平凹以“□□□□”“作者删去XX字”为噱头的性描写泛滥成灾的小说《废都》甫一出版,便立即遭到了文坛众多有识之士的猛烈批判。孟繁华在《贾平凹借了谁的光》一文中,对《废都》的严重病象,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判:“作家在描述这些性行为的时候,完全是以欣赏和投入的笔调进行的,它突出表现的是淫荡的生理快乐,它的叙述语调同《金瓶梅》、《肉蒲团》等所谓奇书已没有什么差别。不同的是西门庆和未央生毫无歉疚愧悔之感,这倒表现了二位恶人心理上的真实。”孟繁华进一步指出:“《废都》赤裸裸的‘性描写’,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大概是空前的。‘性’的隐秘性和其它涵义在这里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人生理需求上的放纵和刺激,从这个层面上说,它仅仅具备了商业的品格。”在孟繁华看来,《废都》无疑是一部 “淫秽小说”:“我确实无法想象,小说还会淫秽到什么地步呢?”由此,孟繁华将《废都》比作《花花公子》的“中国兄弟”,称其与那些不堪入目的黄色淫乱作品相比,不同的只是,它是经过了“严肃文学”包装的“嫖妓”小说。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多年之后,孟繁华却出尔反尔,像许多影视剧里的窝囊男人一样,狠狠打自己的脸,公开向《废都》举起了投降的白旗。孟繁华当众检讨说:“我当年也参加过对《废都》的‘讨伐’,后来我在各种场合表达过当年的批评是有问题的,那种道德化的激愤与文学并没有多少关系。”“经过十年之后,这部作品的全部丰富性才有可能重新认识。”这个重新认识包括:“一、作为长篇小说,它在结构上的成就,至今可能也鲜有出其右者。(笔者按: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长篇小说经典,其结构难道都不如《废都》?这究竟是孟繁华孤陋寡闻,还是其故意掩盖事实?)长篇小说是结构的艺术,很多长篇小说写不好,不是作家没有才华,没有技巧和生活,主要是对长篇小说文体的理解有问题,也就是对长篇的理解有问题。(笔者按:既然对长篇小说的结构理解都有问题,怎么又称得上是有才华的作家?我真不知道孟繁华发明的是什么太空逻辑)但《废都》在结构上无论作家是否有意识,都解决得很好;二、小说在思想内容上得风气之先:贾平凹最早感受到了市场经济对人文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可以说,这个阶层自现代中国以来,虽然经历了各种变故,包括他们的信念、立场、心态以及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但从来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的大潮的冲击。这个冲击对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太重大了。”紧接着,孟繁华将对《废都》的赞美,进一步推向了高潮,激情澎湃地宣称:《废都》“提供了知识阶层当代性的一个范本”。
有谁能想到,世界上居然会有如此既唱红脸又唱黑脸的“双料”文学批评家?当年被孟繁华批得狗屎不如的《废都》,摇身一变,又被他说成是世界上美丽无比的鲜花。但诚如学者周泽雄先生所说:“《废都》的庸常性质,在我心里早已牢牢固定,就我个人而言,只要我的文学鉴赏力一息尚存,它就不会重见天光。”“对暧昧情色抱有好奇,原是人心之常;作为一种偷袭读者下三路激情的手段,它也始终存在,只是真正的作家不屑为之罢了,故即使偷袭成功,也只是商业性成功,与文学成就貌合神离。”周先生还提到一些人搬出据称是季羡林说的“《废都》二十年后将大放光彩”来“作证”的做法:“季先生已驾鹤西去,我们无从核实那句话的真伪。不过我可以确认,季羡林虽在佛教文化和中亚语言的研究上成果斐然,但没有证据表明,他还具有值得刮目相看的文学鉴赏力……喋喋于所谓季老的预言,只能说明,他们下定了忽悠到底的决心,同时坚信读者都是不明真相之辈,只会唯名人之言是从。”
其实,孟繁华对同一部作品做出前后矛盾、判若两人的评价,并非孤例。在《在不确定性中的坚持与寻找》中,孟繁华盛赞张炜的《你在高原》:在当下这个浮躁、焦虑和没有方向感的时代,能够潜心20年去完成它,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奇迹。这个选择原本也是一种拒绝,它与艳俗的世界划开了一条界限。450万字这个长度非常重要:与其说这是张炜的耐心,毋宁说这是张炜坚韧的文学精神。因此这个长度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高度。但转眼之间,孟繁华又奚落张炜:“写这么长,真是考验我们的耐力和阅读能力。”在这样的文学批评中,孟繁华就像是“百变天后”,谁能告诉我,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孟繁华?
张清华:“神话”的制造者
在众多的学院批评家中,张清华最大的“特长”,就是在文坛制造神话。他只要开动起赞美机器,就像是在高速公路上 “醉驾”,一路狂奔,根本就刹不住车。无论是诗人,还是作家,只要张清华喜欢,一律都会被他吹捧得通体完美,光芒四射。
我们知道,诗人海子可说是当代文坛的一个“神话”,对于这样一个“神话”,人们已经有所警觉;而学院批评家张清华恰恰就是“海子神话”的制造者。张清华对海子大而无当的飙捧,简直令人咋舌,就像面对明星偶像时粉丝们在舞台下发出的一声声尖叫,除了刺耳,还是刺耳:“在人们回首和追寻当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脉络时,越来越无法忽视一个人的作用,他不但是一个逝去时代的象征和符号,也是一盏不灭的灯标,引领、影响甚至规定着后来者的行程。他是一个谜,他的方向朝着灵光灿烂的澄明高迈之境,同时也朝向幽晦黑暗的深渊。这个人就是海子。”“这位集诗人和文化英雄、神启先知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于一身的人,已用他最后的创作——自杀,完成了他的生命和作品,使它们染上了奇异的神性光彩与不朽的自然精神。由于这一切,海子对于当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他在诗歌和世界幽暗的地平线上,为后来者亮起了一盏闪耀着存在之光的充满魔力又不可企及的灯,使诗歌的空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阔和辽远。”
仅仅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张清华的确是把做文学批评当成了写诗。但文学批评并非是站在高山之巅,血脉偾张地抒发豪情。张清华的文章,缺乏的是客观冷静的学术分析,而是大量采用诗歌创作中常见的抒情、比喻、想象和夸张,将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混为一谈,以致让人在阅读时,就像看到了一个激情澎湃的抒情男高音,总是情不自禁地在引吭高歌。
在当代的学院批评家中,拿海子的死亡来说事的,并非只有张清华一人,但将海子的死亡吹捧得如此出神入化的,却非张清华莫属。事实上,海子的死亡,只不过是一个精神分裂者在人生失意之后发生的不幸悲剧。但为了吸引眼球,追求“学术成果”,张清华不惜人为地拔高海子死亡的意义:“尼采或许通过对上帝的否定而泯灭了自己内心的神性理想,海子则因保持了对世界的神性体验而显得更加充满激情和幻想,大地的神性归属使他心迷神醉并充满体验的力量,由此生发出主动迎向死亡的勇气。”在张清华的眼里,海子简直比屈原还要屈原,比古今中外任何一位诗人都伟大,是海子以他领悟神启的超凡悟性和神话语义的写作,提升了这个时代的诗歌境界。张清华甚至妄下断语说:“对海子来说,死亡意味着他走向他所叙述的神话世界的必由之路与终极形式,是他内心英雄气质的需要和表现形式。”在我看来,任何对海子死亡的妄加猜测和任意拔高,都是对死去的海子极大的不尊重。倘若海子地下有知,他也会为张清华的颟顸和这样不着边际的浮夸感到不安的。
为了在文坛制造神话,张清华常常都是在一种心潮起伏的跪拜式的状态下进行写作的。他如此飙捧莫言说:“尤其是在《丰乳肥臀》和《檀香刑》之后,莫言已不再是一个仅用某些文化或者美学的新词概念就能概括和描述的作家了,而形成了一个异常多面和丰厚的、包含了复杂的人文、历史、道德和艺术的广大领域中几乎所有命题的作家。”“莫言是在艺术的范畴里做出了最惊险、最具有观赏性和‘难度系数’的动作,这使他成为了最富含艺术的‘元命题’的、最值得谈论的作家。”(笔者按:在笔者的记忆中,“最最最红”“最最最伟大”这样的极限用法,早已被视为敝屣,成为笑谈。 )
张清华等学院批评家“巨大的学术成就”就是,开创了一种新型实用、专门用于谄媚作家的文体——“最字体”。在张清华的眼中,莫言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欢乐》中长达八万字不分段的极尽拥挤和憋闷,堪称是形式上的极限;《酒国》中通篇漫不经心地将写真与假托混为一谈的叙述,堪称是荒诞与谐谑的极限;《檀香刑》中刽子手赵甲以五百刀对钱雄飞施以凌迟酷刑的场面描写,堪称极限……”总而言之,当代其他的作家,没有哪一个能够像莫言这样对人类学的丰富要素有如此的敏感和贴近的理解。莫言的小说,不是被张清华飙捧为天籁之作、极致和奇迹,就是被夸耀为首屈一指,无人可比的“伟大的小说”。
的确,张清华就像是当代文学批评家中的夜莺,只要一张开歌喉,就要放声歌唱。他恨不得为那些当红作家拼尽全力,唱出世界上最美丽的赞歌。在张清华的文章里,不需要逻辑支撑,更不需要令人信服的学术分析,一切都是根据个人的喜好为评价标准。这里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他运用排比手法,书写的一段充满激情的赞美诗:
显然,母亲这一形象是使《丰乳肥臀》能够成为一部伟大小说、一部感人诗篇、一首壮美的悲歌和交响乐章的最重要的因素,她贯穿了一个世纪的一生,统合起了这部作品“宏伟历史叙述”的复杂的放射性的线索,不仅以民间的角度见证和修复了历史的本源,同时也确立起了历史的真正主体——处在最底层的苦难的人民。
作为一部虚构的文学作品,我不知道,莫言凭什么能够——像张清华所说的那样——见证和修复历史的本源。倘若历史的本源能够被一部小说随便修复,这样的历史岂不成为了泥塑木雕的人造工艺品?文学批评绝不是写诗,随时都可以“燕山雪花大如席”“黄河之水天上来”的。
张学昕:在文坛“大炼钢铁”
1958年,在中国的大地上,曾掀起过一场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以及粮食亩产超万斤的浮夸风。在浮夸风之下,连教授也要按其所种的农作物产量来评级,亩产1000斤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当四级,3000斤的当三级,4000斤的当二级,5000斤的当一级。
读张学昕的“学术文章”,我的脑子里总是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一幅当年粮食“高产”的美好图景:社员们乐不可支地坐在高入云天的稻堆上,赞美着他们连肚子都吃不饱的“幸福生活”……
如今,我们虽然再也看不到当年那些随处可见的“小高炉”,但意识形态里的“小高炉”,却依然牢牢地矗立在张学昕这样的学院批评家们的脑海中。张学昕撰写学术论文,采用的就是“大炼钢铁”和浮夸风似的模式,其学术论文,简直就像是当年的水稻高产报告。张学昕似乎坚信,只要把中国作家写作的水平确定为世界一流,向世人大声宣告他们写出的都是经典,中国的文学就完全可以用大干快上的方式,赶英超美了。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张学昕的文章中,到处都是对当红作家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似的肉麻浮夸:
多年来,贾平凹的写作特别注重对文学表达的古典性追求,他的大量作品都表现出“崇尚汉唐”文化的雅致和气度,并由此开拓出自己的叙述文体,他小说、散文兼工,常常在叙述中涨溢出各自不同文体规范的限制,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文体。
最令人惊异的是,贾平凹从容地选择了如此绵密的甚至琐碎的叙述形态,大胆地将必须表现的人的命运融化在结构中,对于像贾平凹这样一位有成就的重要作家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近于冒险的写法,但他凭借执着而独特的文学结构、叙事方式追求文体的简洁,而恰恰是这种简洁而有力的话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长篇小说的写作惯性,重新扩张了许多小说文体的新元素,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叙事心态……
我坚信,没有人会怀疑,相对于同时代的作家,苏童,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稳健、最富才华和灵气、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
我们在苏童的短篇小说中看到了一个作家,如何凭借智慧运用最精炼、最集中、最恰当的材料或者元素,表现复杂、丰富、开阔而深远的内容。
就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凝练、精致和唯美品质而论,苏童的作品在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中是首屈一指的……对一位同样也擅长写长篇和中篇的作家来说,我还是忍不住将其称之为“短篇小说大师”……因为苏童对短篇小说写作的酷爱,孜孜不倦的精心耕耘,不仅给他的写作带来激情、兴奋和快乐,而且给它的阅读者带来了无比的幸福。
音乐商要炒作和包装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就夸奖她天生丽质、采用的是原生态唱法。贾平凹絮絮叨叨、缺乏艺术构思、犹如一盘散沙的《秦腔》,曾令许多著名的作家和批评家读来头痛。这种忽悠读者的写作,居然被张学昕狂捧成了绵密的叙述,是成功的创造和艺术的探险。批评家并非媒婆做媒——麻子也要吹捧成天仙。照张学昕这样的逻辑,那些不从大门进入而是翻墙入室的人,也可以被称之为人生的另一种选择和别样的追求,是人生的冒险。
我始终觉得,作为一个学人,张学昕似乎从来都缺乏一种理性的思考和客观的分析。其文章不是以理服人,而常常是以夸张的手法和“演讲大师”似的煽情来诱惑人。在张学昕的文章里,动辄就是“假大空”的“最XX”“极致”“惊异”“首屈一指”“无比”“最高成就”……汉语中所有最高级的形容词,都被张学昕一网打尽。单说“幸福”,倘若苏童的小说真的能够给读者带来无比幸福的话,那些正在为找工作而烦恼,为买房而忧虑,或被婚姻困扰的人们,从此就再也不用发愁,他们只需人手一册苏童的小说,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拥有快乐的人生了。
难道文学批评就等于轿夫抬轿子?张学昕写作的病象,凸显出学院批评长年的沉疴。其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其实就像一个不得其门而入的门外汉。如:“贾平凹叙事的信心、耐心、功力,直逼汉语写作的极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贾平凹的写作水平就远远超过了曹雪芹;但稍有一点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便是《红楼梦》,也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存在着无可否认的瑕疵。张学昕对贾平凹不顾事实的吹捧,要么是不懂文学,要么是有违学术品格的瞎忽悠。又如:“一般地说,短篇小说对作家的写作来讲,较之长篇、中篇文体有着更高的精神要求和技术衡定指标。这不仅需要作家思考世界的功力,而且需要作家非凡的艺术能力。”小说作为一门艺术,从来就没有什么技术衡定指标,只有艺术评判的标准。说短篇小说比长篇和中篇小说的精神要求更高,就像说短跑比中长跑对身体的要求更高一样,完全是只有体育盲才会说出的外行话。而所谓的“精神要求”,可说是张学昕为了显示其学术“创造力”凭空发明的一个“学术名词”。
在这里,笔者还想就以下这段“太空语”,请教张学昕先生。我不知道,这段文字,读者诸君是否已经读懂,反正我要实事求是地讲,尽管文中的每一个字我都认得,但却无论如何也读不懂,并且越看脑袋越大:
确切地说,贾平凹《秦腔》的叙述,在努力回到最基本的叙述形式——细部,如同被坚硬的物质外壳包裹的内核,可摸可触,人物的行为、动作在特定的时空中充满质感。也许,贾平凹在叙述观念上,想解决虚构叙事与历史的叙述,或者说,写实性话语与想象性话语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他更加倾向将具有经验性、事实性内容的历史话语与叙述形式融会起来,在文字中再现世界的浑然难辨的存在形态。
与其说这样的文字是学术论文,倒不如说是张学昕在用绕口令和读者玩起了脑筋急转弯。并且我们看到,这种游戏一旦玩上瘾,张学昕就会乐此不疲:
这(《秦腔》)是一部真正回到生活原点的小说,它是作家内在化了的激情对破碎生活的一次艺术整合,是智慧与睿智对看似有完整结构的生活表象的真正颠覆和瓦解,我们就在这幅文学图像中强烈地感觉到了生活、存在的“破碎之美”。
以上这段文字,让我们真正领略到了什么叫做“不明觉厉”,什么叫做把人当猴耍,更使我们真正知道,梦呓似的文字,也可以故作高深地组合成讨好当红作家的“谄媚书”。
栾梅健:头脑发热的学界“粉丝”
众所周知,那些大牌明星的粉丝,是绝不需要什么音乐知识、懂得什么表演艺术的。他们只需要高举着“XX,XX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之类的牌子或者荧光棒,发出一声声刺耳的尖叫,就可以成为某些明星的“铁粉”了。
在当代文坛,批评家心甘情愿地为当红作家喝彩“站台”,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像栾梅健这样经年累月、不遗余力地为当红作家欣喜若狂、拍手叫好的批评家,的确是当代文坛一道“别样的风景”。从栾梅健的“学术”文章中,笔者基本上看不出其究竟有多少文学的感悟能力,虽然同为名牌大学的学者,栾梅健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学术水平与孟繁华、张清华都不在一个档次。栾梅健崇拜某些当红作家,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也纯属是私人的事;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谁要是批评栾梅健追捧的作家,栾梅健就会怒不可遏,对批评者进行头脑发热的大泼脏水。
鲁迅先生早就主张:“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但栾梅健却只允许说好话,绝不允许别人说半个“不”字。栾梅健将批评某些当红作家写作病象的学术文章,强行宣判为别有用心地挥舞着大棒的逻辑混乱的“酷评”。经过栾梅健脏水一泼,正常的文学批评,就被可怕地妖化成为了断章取义、哗众取宠的骂派文章。
栾梅健的文学鉴赏能力很低,因此只能常常撰写一些飙捧当红作家的谀评文章。在《论〈带灯〉的文学创新与贡献》中,栾梅健说:“《带灯》甫一问世,便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带灯》的电子书版,单本定价十五元,借助腾讯阅读平台大量的用户群基础及强势的推广传播,获得了单月过万册的销售成绩’,而‘结合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及各民营书店等实体渠道,今年年内 《带灯》销量有望突破五十万册。’在文学日趋边缘化的今天,五十万册的销售量,在当下的阅读市场,无论如何都算得上是一个奇迹。”恕我直言,我宁可相信这样的文字是一份赚得盆满钵满的商业报告,也绝不相信这是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如果仅仅是以销售量,以及赚钱的多少来评定作品的好坏和贡献的话,我敢说,《带灯》和《鬼吹灯》就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栾梅健对《带灯》里的文字大杂烩,不但视而不见,反而大谈其文学创新,又根本谈不到点子上。因此,他只能像路边的测字先生,故弄玄虚地说:“《带灯》的突破,主要在于贾平凹采取了他以往小说中从未有过的‘俯视眼光’。这种视角,既不同于他过去驾轻就熟的、从农村底层观察与描写的民间视角,也不同于当下文坛流行的、站在历史和道德高度对社会丑态与官场黑暗加以揭露的反腐小说。”栾梅健飙捧说,《带灯》最典型地调动了贾平凹四十余年之久的城市生活经验,及其作为文化名人和级别不低的公职人员的亲身感受。
小说毕竟是小说,如果真要说贾平凹这部凭空虚构的小说调动了其什么城市经验和亲身感受的话,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贾平凹换汤不换药和大炒冷饭的本领。而栾梅健的许多“学术文章”,几乎都是寻章摘句的“文字串烧”。如其论多位作家文学观的文章,只不过是将该作家的作品内容进行简单的复述,然后再引用一些作家本人谈文学和小说创作的文字,以及别的学者的评论文章,再署上自己的名字,就算制作完成了。如:
看贾平凹的文字,既有现代意识,又有传统气息,还有民间味道。重整体,重混沌,重沉静,憨拙里的通灵,朴素里的华丽,简单里的丰富,达到了语言大师的境界。
这段评论《秦腔》的文字,只不过是移花接木地挪用了谢有顺撰写的《秦腔》授奖词。至于将贾平凹称之为是“语言大师”,则清楚地说明,栾梅健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语言大师。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各种文字差错和硬伤可说比比皆是。一个连基本语法都不懂,写了一辈子小说却老是分不清结构助词“的、地、得”和时态助词“着、了、过”的作家,居然被栾梅健称为“语言大师”,这本身就说明也许才疏学浅的栾梅健自己就不懂语法。
作为一个中文系教授,栾梅健的中文水平,不禁令人担忧,其捉襟见肘的汉语知识,常常让人啼笑皆非。如:
在新时期文学之初,他又如饥似渴地关注欧美现代派作品、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和日本的翻译小说。
“如饥似渴”,出自曹植的诗歌《责躬》:“迟奉圣颜,如渴如饥。”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中也有这样的诗句:“思我良朋,如饥如渴,愿言不获,怆矣其悲。”在《古今小说·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中,则出现了“如饥似渴”的用法:“吾儿一去,音信不闻,令我悬望,如饥似渴。”形容要求或愿望非常迫切。栾梅健将“如饥似渴”和“关注”相搭配,显然属于用词不当,难免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在《废都》、《秦腔》、《古炉》诸佳作已然奠定当代文坛的重镇地位以后,贾平凹在最近发表的长篇小说《带灯》中,丝毫没有显露出马虎。
在汉语中,所谓“重镇”,通常指的是在军事上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城镇,后来也泛指在其他某些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的城镇。说贾平凹的几部小说奠定了“重镇”地位,这显然是一种词不达意的表述和不顾事实的瞎吹捧。此外,谁能说“丝毫没有显露出马虎”也值得大书特书?
后人常用朴拙而灵秀来形容贾平凹的艺术风格,其实这特性蕴含于他家乡的石头中,蕴含于他对家乡自然、风物的体悟与品赏中。
所谓“后人”,是指后代的人,或者子孙。连常用词都弄不明白,我真为栾梅健教授感到害羞。生在当代的栾梅健,怎么会知道后代的人对贾平凹的评价?
看到以上这些似通非通、语病扎堆的句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栾梅健的汉语水平其实就像洗脸盆里扎猛子,实在是太浅。
在《与天为徒——论贾平凹的文学观》中,栾梅健不顾事实地说:“多达六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古炉》,又被众多研究者认为是一部精准描写‘文革’十年浩劫的民族史诗。”据笔者所知,所谓“十年浩劫”“民族史诗”,只不过是出版商为了推销贾平凹的小说,印在该书封面上的一句广告语。将书商的广告语蓄意偷换成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这本身就是对读者的欺骗。而关于《古炉》中漏洞百出的描写,已有多位学者撰文指摘。一部人物颠倒、时空错乱、细节失真,多处穿帮的小说,在栾梅健的眼里,居然成了“精准描写”的旷世佳作。如此不负责任的海侃神吹,本身就说明,栾梅健的学术态度非常不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