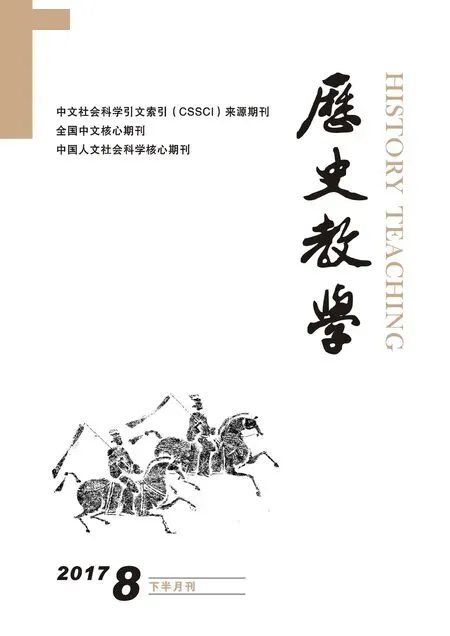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地下书店
江林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地下书店
江林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在近30年的斗争中,地下书店始终是中共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为获取在敌占区开展工作的机会,中共或主动成立、或随后接管、或施以影响,先后在全国各地创办了大量地下书店。中共在利用书店发行进步书籍的同时,还将书店作为党组织地下交通的据点,甚至直接参与到激烈的暴力革命行动中。在敌占区创办革命目的的地下书店,自然会遭到统治者的抵制与破坏,中共虽然竭力维持其存在,但由于敌我实力悬殊,最终往往难逃被查封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书店,革命文化,地下交通站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中,文化宣传始终是其重要的工作之一。从中共一大开始,宣传部门即与组织部门并立,成为中共中央的两大核心机构。①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页。书籍报刊作为文化宣传的主要载体与工具,其出版发行自然成为中共文化宣传工作的重点。身为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毛泽东,在参加革命之初,就曾经参与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著称的长沙文化书社,对革命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②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5年,第245页。
要出版发行符合自身政治理念的书刊,首要任务是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机构。在中共统治区域内,自然可以公开建立出版发行机构,传播革命理想与文化。而在敌占区,③敌占区的含义,根据不同时期中共“敌人”含义的变化而时有不同。在国民革命时期,指各地军阀统治区;在国共分裂时期,指国统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则既包括国统区,也包括沦陷区。由于统治势力的敌视与打击,无法公开活动的中共也通过直接建立或间接支持的方式,控制了相当一批以民营身份出现的地下书店,为宣传革命理念与文化甚或直接支援各地革命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地下书店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时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即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向导》发行所和上海书店等图书发行机构,标志着地下书店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共产党人著作和刊物的传播,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国民革命发展、扩大中共影响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27年国共分裂,进步文化事业普遍遭到查封,但中共并未轻视文化斗争的作用,而是大力支持地下书店的恢复与发展,中共中央创办了《布尔什维克》编辑部、秋阳书店等文化机构,各地党组织也纷纷加强对国统区地下书店的建设与领导,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共建立的地下书店遍布全国20余省市,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有相当大的影响,有力地支持了中共的革命事业;④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增订本),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463~472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尽管阴晴不定的国共关系影响了地下书店的稳定,尤其在皖南事变后,地下书店被普遍查封。但整体而言,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与中共实力的增长,中共领导的地下书店事业仍然在曲折中持续进步,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反对国民党独裁做出了贡献;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尚在经营的地下书店大多亮明旗帜,并入新华书店或三联书店,地下书店才最终完全消失。据不完全统计,在1921~1949年间,有明确记载的中共地下书店总计近200家,经营范围遍布全国各地。⑤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增订本),第458~507页。可以说,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地下书店始终是其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包括图书出版在内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与中国共产党文化宣传相关的研究成果,则主要集中在文化书社研究、延安时期的出版工作以及马列主义书籍在中国的传播等方面。①上述研究的主要成果,参见郑会艳:《长沙文化书社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刘苏华:《延安出版业研究(1937-1947)》,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张新强:《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出版、流通与阅读(1927-1937)》,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杨卫民:《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1920-1937)》,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王海军:《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书刊发行领域的博弈》,《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4期。而对发行主体的书店研究则稍显不足。②其中较重要的是对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解放战争时期合并为三联书店)的研究,可参见李亚洲:《时代夹缝的书香——以三联书店为典型的近代中国媒介公共领域探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但正如作者所言,上述三家书店曾长期保持独立性,不可否认其为“左翼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但若是直接归入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和文化机构范围内是不恰当的”(第32页)。所以,在本文关于地下书店的讨论中,一般不包含上述三家书店。尤其对中共在敌占区领导的为数众多的地下书店的记载,大多散见于作为革命史组成部分的回忆录中,缺乏系统性、总结性的学术研究。事实上,这种地下书店的存在,不仅在当时传播了中共政治理念、实际支援了革命行动,其在经营过程中逐渐探索形成的经验、教训,对新中国文化事业政策与出版发行实践提供了重要借鉴。
一、地下书店的建立
对于长期在敌占区处于非法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取得合法、公开的机会是顺利开展工作的重要前提。在众多行业中,开设书店之所以脱颖而出、逐渐成为中共的优先选择,主要是因为书店的特点恰好适应了其斗争需要。首先,书店通过售卖书刊以传播文化,既可以宣传中共的革命理念,又能够团结作为主要读者群体的进步青年,还便于共产党员以文化人身份参与社交活动;其次,书店是面向大众的公共空间,人员流动性强,且不易追查,地下党员得以从容来往与隐蔽,从而为地下交通与秘密集会创造了条件;最后,与其他商业活动相比,开设书店不仅成本低廉,其收入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共增加经济来源。当然,中共在建立书店之初,目的往往较为单纯,很难充分利用其全部优势,但在实践中,书店的上述特点或多或少都为革命事业发挥了作用。
根据发起者的身份与动机,地下书店的建立主要有两种途径。第一种,各地共产党组织或党员出于传播革命文化或便利地下交通等考虑主动建立的书店。如1930年开设的潼南书店,就是中共四川省委出于掩护军事联络站的考虑,命令潼南特支直接建立的;③青尔祺:《军事联络站与潼南书店》,新华书店总店编:《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20页。抗战期间作为中共重要联络点的浙东书店,也是中共浙江省委为发行抗日革命图书而创办,主要工作人员大多为地下党员。④孔望光:《回忆丽水浙东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112页。阜阳淮颍书局和荣县旭声书店,分别由中共党员张子珍和吴玉章建立,前者甚至以书店为基础成立了中共阜阳支部。⑤朱耕、王正夫:《张子珍烈士与怀颖书局》,新华书店总店编:《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87年,第9页;陈洪府:《吴玉章与旭声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29页。这种书店从建立之初即掌握在中共手中。第二种,是进步青年为学习、传播先进文化自发建立的书店。如青岛荒岛书店,最初即由两名进步青年建立,后受中共青岛市委委员乔天华影响,不仅积极传播进步书刊,甚至将书店作为中共秘密会议的场所,二人也先后加入共青团;⑥王懋昌:《三十年代的荒岛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54页。又如哈尔滨王忠生书铺,最初只因销路不错而发售进步书刊,但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下,思想觉悟逐渐提高,将书店办成了哈尔滨影响较大、效果较好的进步文化阵地。⑦平治国:《播火者的足迹——记王忠生书摊》,《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25页。这种书店数量较多,虽然并非中共直接建立,但由于发起人思想本身即倾向进步,加之地下党员施以影响,最终不但书店归于中共领导,进步青年本身也多投身革命。虽然初衷未必相同,但这两类书店最终殊途同归,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文化机构,为革命事业提供了帮助。
在地下书店的选址方面,建党之初,书店大多跟随中共中央设立在上海,此后,则与党派实力和革命形势的变化息息相关。在中共实力较弱时,大多数地下书店建立在中小城市中。从政治角度而言,敌人在中小城市的统治力量薄弱,书店较易开展诸如发行进步书刊、传递信息以及秘密集会之类的革命活动;从经营角度而言,大城市的图书市场往往趋于饱和,中小城市则相对而言竞争较小,地下书店开设于此,既维持了经济上的生存,也提升了传播效果。此外,由于地方势力相对独立,政治势力错综复杂,故对文化控制相对放松,所以为地下书店的创办提供了另一种机会。抗战期间开设在晋绥系傅作义部驻地五原的西北书店,甚至得以直接从延安新华书店批销图书,深受官兵欢迎。①高子俨:《河套地区的西北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107~108页。 傅杰:《丰都地下党的文化书店》、倪子明:《从成都明华书店到联营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109、127页。抗战胜利后,随着中共实力的不断增强,大型城市也逐渐出现了地下书店。仅在天津,中共就支持成立了知识书店和读者书店,以扩大舆论宣传的影响。②杨大辛:《回忆天津知识书店》、柳季:《传播新文化的据点——天津读者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258、323页。
在筹办书店的过程中,还有经费与书籍两个来源问题需要解决。在经费方面,虽然地下书店受中共领导,但中共党组织很少直接给予资金支持,经费主要由参与的党员自筹。至于具体来源,则以党员个人积蓄、社会名流投资、进步青年捐助等为主。以抗战时期建立的绥德抗敌书店为例,虽然为中共绥德特委直接建立,但资金来源却全由地下党员筹得,不但进步师生和开明士绅积极响应,连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也有所参与。③常紫钟:《忆绥德西北抗敌书店》,新华书店总店编:《书店工作史料》(第1辑),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79年,第57页。由于中共党员不乏打入地方党政机构者,地下书店甚至有利用敌方资金之举。如中共北流县委开办的北流书店,即通过时任县合作金库主任的中共地下党员李钧章向合作金库贷款而成。④李名魁:《地下党创办的北流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121页。总体而言,书店作为文化事业,开明人士多愿参与其中,且不索回报。例如作为三联书店前身之一的新知书店,“尽管形式上是私人投资的,实质上绝大多数股东出了钱,仅仅是对进步出版事业的一种支持”,股东不仅没有领取过利润,绝大多数人还将股权捐献给了国家。⑤徐雪寒:《新知书店的创立和发展简述》,新华书店总店编:《书店工作史料》(第2辑),北京:新华书店总店,1982年,第242页。地下书店之所以依赖社会集资,其根本原因是中共经费匮乏。随着抗战胜利后中共实力大增,其对地下书店的投资也有所增长,天津进步青年建立的知识书店经营受困时,中共立刻出资接办。⑥杨大辛:《回忆天津知识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258页。力有未逮时不肯放弃书店,条件具备则大力支持其发展,这充分说明了中共对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视。
在书籍来源方面,受经营条件限制,大多数规模较小的地下书店都只能取之于外。从天津读者书店的情况来看,地下书店发行的图书大体分三类:进步书店公开出版发行的进步书刊、中共在香港出版的革命书刊和解放区伪装出版的书刊。⑦柳季:《传播新文化的据点——天津读者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324页。其中,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等机构公开发行的进步书刊无疑是最多的,这些机构也成为地下书店书籍的主要来源。至于后两类明显更为“反动”的书刊,尽管国民党实施了严格的邮件检查制度,但中共与地下书店也仍然能通过更换封皮、货物夹带等方式实现传播。⑧张新强:《1927—1937年的“禁书”: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和沟通》,《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5期。另外,部分规模较大的地下书店有出版、印刷的能力,可以自行解决部分货源。如宁波新生书报社就秘密出版、翻印毛泽东著作和进步书刊,并发行到周边各地。⑨吕平:《抗战时期宁波地下党领导的新生书报社》,《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92页。
二、地下书店的功能
作为文化机构,地下书店最基本、也最易实现的功能,莫过于通过发行进步书刊以传播先进文化与宣传革命理念。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⑩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188页。从内容来看,这些书刊可以分为三类:进步文艺图书,包括《被开垦的处女地》《我的大学》《呐喊》《子夜》等苏联、中国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马列主义原典,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经典著作;中共出版物,包括《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领导人著作以及《新华日报》。①高子俨:《河套地区的西北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107~108页。 傅杰:《丰都地下党的文化书店》、倪子明:《从成都明华书店到联营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109、127页。与看重经济利益的民营书店不同,地下书店的工作重点是利用有限的书源尽可能地扩大传播范围。为实现这一目标,地下书店或设有陈列进步书报的阅览室,或开展租书业务,或组织流动图书馆互相借阅。①韦凯章:《广西融县七七书店》、戴剑萍:《中共西昌地下组织领导的进修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119、139页;朱耕、王正夫:《张子珍烈士与怀颖书局》,《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9页。 青尔祺:《军事联络站与潼南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21页。开设在中心城市的书店,还承担起向周边地区发送进步书刊的义务。青岛荒岛书店就曾向潍县革命图书馆按照书目寄送马列著作和进步文艺书籍。②王懋昌:《三十年代的荒岛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55页。必须承认,面对内忧外患不断的社会现实,共产主义理论和进步文艺作品的大量传播确实在进步人士与青年学生间“起了新启蒙运动的作用,启发广大的落后读者走向马列主义的道路”,甚至唤醒了其直接投身中共革命的热情。③胡愈之:《全国出版事业概况》,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3卷上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9~60页。在国共内战中,中共之所以能够赢得民心,并最终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除双方的实力消长与策略差异外,包括发行进步图书在内的中共舆论宣传手段功不可没。
地下书店还采取了各种手段以确保传播效果。对中共而言,评价图书发行的成绩,“主要地还要看发行的政治效果,就是所发行的图书对于人民群众所起的宣传教育作用”。④陈克寒:《加强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宋应离等编:《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4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265页。考虑到马列主义原典的理论性普遍较强,通过成立读书小组、开展读书会、组织集体学习等方式加强读者对理论的理解与接受,是地下书店利用的普遍办法。哈尔滨王忠生书铺就组织了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学习组织的读书会,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艺作品。⑤平治国:《播火者的足迹——记王忠生书摊》,《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26页。长沙文化书社还专门制作了名为《读书会的商榷》的铅印单页,从减少支出、获取心得、推动文化传播等几个角度论述读书会的好处。⑥王火:《关于长沙文化书社的资料》,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08~409页。有条件的书店,还尝试自行编辑、印刷、发行了部分进步刊物,如哈尔滨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旬刊、巴中辅仁书社出版的《一声雷》等。⑦平治国:《哈尔滨“开明书店事件”》、冯石:《川北巴中的辅仁书社》,《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12、18页。这些富有地方性与时效性的进步刊物,与民众生活结合较紧密,对扩大书店影响、提升宣传效果极有帮助。同时,各地书店,往往也是当地的文化中心,文艺活动多集中于此。以渠县八濛书店为例,但凡渠县要举办画展、音乐会、戏剧演出等文化活动,都先在书店集中。这类文艺活动中,大多夹杂着反帝、抗日等革命宣传,既团结了青年,又加强了传播效果。⑧鲜奇定:《八濛书店始末记》,《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126页。
当然,发行图书报刊与举办文艺活动进行文化层面上的斗争,只是地下书店所具有的若干面相之一。在中共的革命实践中,地下书店往往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其所担任的最普遍的角色,就是中共的秘密交通站。由于各方政治势力的忌惮,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及其活动都只能秘密存在,党员身份也多不公开,甚至彼此间以单线联系,这就为不同地区党组织及党员之间必要的联络带来了困难。一地党员因工作或生活需要到另一地区,当地党组织为安全起见,也不敢贸然接纳。这时,具备公开、合法身份的地下书店就成为双方接触的平台。初来乍到的外地党员,往往先被介绍到书店,书店工作人员在经过考察确认安全后,再介绍其与当地党组织联络。如镇平安国杂志社作为镇平党组织建立的出版单位,每次外地来的党员,都由店员侯遂生出面秘密接头,然后再和县委联系,“从未出过一点差错”。⑨王国谟:《镇平地下党组织创办的发行机构——安国杂志社》,《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84页。在天津地区,外地党员也是先到中共领导的北方书店探询,再与关系人取得联系,“没有使党的地下工作遭受任何政治损失”。⑩李子昂、宋少初:《回忆天津北方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25、28页。
同时,作为秘密交通站,地下书店还往往肩负着运送公文、信件的责任。书店人员进出密集、图书流动频繁的特点,恰好为较安全、合法地运送秘密文件创造了条件。潼南书店的中共党员谭世良就是以书店经理的身份为掩护,将周边地区来往的中共秘密信件,藏在书店楼上的缝隙里进行处理。①韦凯章:《广西融县七七书店》、戴剑萍:《中共西昌地下组织领导的进修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119、139页;朱耕、王正夫:《张子珍烈士与怀颖书局》,《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9页。 青尔祺:《军事联络站与潼南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21页。另外,由于书店人流大,易于隐藏,有些开设了地下书店的中共组织则在书店召开会议,甚至一部分中共地方组织就设在书店中,干部生活全靠书店解决。广东流沙合利书店创办后,中共潮普惠中心县委领导机关就设在书店楼上,经常召开会议领导当地革命工作。①张重仁:《合利书店与抗日救亡运动》,《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118页。 张锡荣:《在“生活”工作的日子》,《书店工作史料》(第2辑),第86页。时任中共北流县委书记熊景升更是食宿在地下党建立的北流书店里。②李名魁:《地下党创办的北流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121、122页。作为活跃在敌占区的中共据点,地下书店还为组织进步青年进入中共占领区提供了帮助。解放战争如火如荼之际,读者书店就通过伪造居民证及提供路费的方式,把天津的进步学生介绍到解放区,让他们投身于中共革命运动中。③柳季:《传播新文化的据点——天津读者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327页。
部分在地方政府担任职务而又主持地下书店的中共党人,利用自己的官方身份或社会地位,以书店为依托发展社会事业,对农民、工人等革命主力军进行教育。巴中辅仁书社经理苟寿南,以国民党县党部农民协会领导人的身份,组织书社成员开办农民夜校,并编印农民夜校课本,借机开展农民运动。④冯石:《川北巴中的辅仁书社》,《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18页。安陆书报合作社经理肖松年则利用自任主任的合作事业办事处,举办合作事业人员训练班,不但进行革命宣传,甚至组织农民进行军事训练。⑤彭泽生:《抗战初期的安陆书报合作社》,《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95页。这些行为,由于身披官方外衣,往往能取得更持久、有效的宣传效果。
地下书店及其工作人员,在革命需要或者上级指示时,还直接参与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后,巴中辅仁书社就大量印发了郭沫若所著《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并四处书写张贴“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等标语。⑥冯石:《川北巴中的辅仁书社》,《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18页。1930年,受“立三路线”影响,内江晓东书店和潼南书店四处张贴组织暴动、建立苏维埃的标语。⑦刘绍沛:《廖释惑烈士与晓东书店》、青尔祺:《军事联络站与潼南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16、21页。抗战期间,安徽蒙城大同书店为周边的新四军部队提供药品和纸张;⑧蒙城县新华书店:《蒙城地下党创办的大同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129页。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北流战时工作团解散时,北流书店甚至还帮助转运、藏匿了部分军火。⑨李名魁:《地下党创办的北流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121、122页。显然,这种极为激烈的革命活动很难为统治者所容忍,上述书店在为革命贡献了最后力量之后,纷纷遭到了查封。
三、地下书店的政治困境与隐蔽斗争
从公开身份来看,以私营面目出现的地下书店的存在无疑是合法的,但当其活动与政治挂钩尤其是被怀疑为中共革命提供协助时,则很难不为统治者所注意。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之地下书店参与的革命活动不可能完全保密,尽管书店竭力掩盖自身与中共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大多数地下书店还是在历经怀疑—调查—查封的过程后,最终以停业告终。虽然每家地下书店存在的时间普遍不长,但中共地下党员在维持书店存在的过程中付出的努力依旧值得称道。
与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书店相比,地下书店的日常经营活动有明显的不同——或者以统治者的眼光看来,是有明显的可疑之处。意在牟利的私营书店销售的图书,以销路较好的言情小说为主,对明显传播共产主义的书籍则敬而远之;地下书店却以发行进步书刊为主,并且千方百计推广所谓“禁书”。私营书店经理多结交文化人,往往对囊中羞涩的学生、工人等群体不屑一顾;地下书店则主要以学生、工人为组织对象。加之地下书店多开设在中小城市,社会关系简洁明了,一旦有“禁书”流传,很快就能追查到来源。如解放战争时期,《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当梧州地区一出现《新华日报》,当地政府立刻就查到是中共领导的八桂书店私下发行的。⑩李名魁:《记梧州八桂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226页。由于上述原因,地下书店几乎都是建立不久即遭到怀疑。
既然产生怀疑,就要展开调查——或者说,是在统治当局已经预设书店受中共控制这一结论后,寻找可以定罪的证据。对地下书店而言,最关键的“罪证”显然是经费来源,如果接受中共津贴,则是“赤化”书店无疑。1940年,国民党当局曾对生活书店突击查账,“有否领取共产党津贴,是查账的真正目标,结果查明‘无’,使国民党大失所望”。①张重仁:《合利书店与抗日救亡运动》,《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118页。 张锡荣:《在“生活”工作的日子》,《书店工作史料》(第2辑),第86页。对这一点,中共早有准备,尤其注意书店发起人以及出资股东的身份。在建立成都西川书局时,中共就确立了几条筹建书店原则:选择进步青年担任经理、利用社会关系就地募股、物色较为开明人士担任董事长。①傅登瀛:《记西川书局及其所属七家县镇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154页。 曾志巩:《赵醒侬传》,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0页。都是为了避免给人书店受中共控制的印象。当然,由于前文所述地下书店的资金来源,即使确实是中共组织或党员建立的书店,也多以私人积蓄出资,很难查到中共党组织直接资助。
当经费来源不能查出问题,统治当局就要从经营内容的违法层面入手,即出售的书报刊物是否违禁。1929年颁布的《国民党中宣部宣传品审查条例》中规定,“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为反动宣传品,须查禁查封。②《国民党中宣部宣传品审查条例》,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下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78页。 陈洪府:《吴玉章与旭声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28页。针对这一禁令,地下书店在公开发行允许出版的进步书刊的同时,往往另行秘密保存明令禁止发行的革命书刊,并通过熟人介绍、私下传阅等方式加以传播,尽可能避免被直接查获。上海书店发行的《向导》等刊物,要另租房子秘密发行;③徐白民:《上海书店回忆录》,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64页。 鲜奇定:《八濛书店始末记》,《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123~124页。旭声书店只把革命书籍销售给经过长期考察的进步读者或者是统战工作人员介绍来的进步人士,还要用国统区的报刊包夹。④陈洪府:《吴玉章与旭声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28~29页。相当一部分书店经销国民党控制的正中书局等出版的书籍,江津大公书店甚至出版了宋美龄记述西安事变的《西安半月记》作为发行进步书刊的掩护。⑤法纯:《江津大公书店始末》,《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190页。对需要邮寄的进步书刊,地下书店则往往采用抽换封面、货物夹带等方式。1929年中共刊物《布尔塞维克》就在邮寄发行时把封面改为《少女怀春》,从而得以顺利传播。⑥张克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书刊的伪装》,《新闻研究资料》1982年第4期。这甚至迫使国民党中宣部提醒各地邮件检查人员,要特别注意“假冒其他书名及封面之各种反动刊物”。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关于省市党部宣传工作实施方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7页。
虽然采取了种种隐蔽措施,但在敌占区从事革命宣传,总不能天衣无缝。一旦出售“禁书”被查,地下书店则以卖书仅为牟利、不知内容违禁为辞。1931年上海市商会曾经特别向国民政府上书,认为“经营书业者大多数系属商人,不惟无从事反动宣传情事,且或知识浅陋,不解内容,或无宽裕时间详细阅看”,呼吁当局“认为违碍之书籍,但由主管官厅禁止其代售,并不牵涉各该书肆本身营业”。⑧《上海市商会为书肆代售书籍如有违碍请宽予处分致国民政府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一),第229~230页。国民党政府采取的相对宽松的查禁政策,“对于一切反动刊物,仅仅予以禁止发行,并未株连编辑、印刷、发行一切有关系之分子”,也为地下书店“敢一再尝试,视法律如弁髦,今日印一三日刊,明日印一传单,层出不穷”提供了空间。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民国十八年查禁书刊情况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一),第214页。
尽管书店还可以作为秘密交通站使用,但为避免组织遭受损失,决定是否利用时往往慎之又慎。中共在接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在西昌建立的进修书店后,就因考虑到来往人员多且复杂,放弃了作为联络点的想法。⑩戴剑萍:《中共西昌地下组织领导的进修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137页。即使在确认相对安全的地下书店,中共在进行联络或召开会议时,也通常极为小心。南昌明星书店选用共青团员作店员,并准备了麻将、胡琴,开会时即以打牌唱戏作掩护。①傅登瀛:《记西川书局及其所属七家县镇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154页。 曾志巩:《赵醒侬传》,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0页。
为了维持生存,在地下书店的经营过程中,往往非常注意维护与包括国民党、军阀、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各方势力的良好关系。吴玉章建立旭声书店时,就请国民党要人孙科题写了匾额;②《国民党中宣部宣传品审查条例》,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下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78页。 陈洪府:《吴玉章与旭声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4辑),第28页。渠县八濛书店经理杨景凡,不仅重视拉拢当地国民党的有力人物,还特别注意获取在地方具有极大势力的袍哥支持,甚至本人还公开加入了国民党。③徐白民:《上海书店回忆录》,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64页。 鲜奇定:《八濛书店始末记》,《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123~124页。事实证明,这些为了保持书店的灰色色彩而做出的努力具有相当成效,八濛书店在当地经营六年,成为文化活动的中心,对宣传革命文化、团结进步青年、开展统战工作,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当然,尽管地下书店竭力维持,但由于中共的革命活动终究为统治者所不容,往往最终难逃被查封的命运。如前文所述,直接参与暴力革命活动的地下书店自然给了政府当局关闭的理由,而当政治气氛明显紧张时,查封地下书店则如同家常便饭。事实上,除自行停业外,大多数地下书店都是在譬如1927年国共分裂和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等政治气氛极度紧张的形势下被迫关闭的。但在查封之后,由于“禁书不禁人”的政策,地下书店还可以通过改换名号的方式继续经营。1941年当局封闭上海生活书店后,工作人员只是换了一块“兄弟图书公司”的牌子继续门市业务,“外界知道这个图书公司就是生活书店变相的人很多”。①张锡荣:《在“生活”工作的日子》,《书店工作史料》(第2辑),第90页。总而言之,面对极有可能要被关闭的命运,大多数地下书店采取了各种手段,尽可能的维持自身存在,为中共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四、对地下书店的评价
在革命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无疑是艰辛的。面对并不明朗的革命前景,地下党员既要面对生活上的困难、家人的不解,还要时刻提防来自统治者的威胁,从事地下书店工作也不例外。创办镇平涅光书店的地下党员樊道远直言:“那时的地下工作是很艰苦的,并且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危险。但我们工作起来却从不敢懈怠。当时一方面要工作,一方面又要生活,啥都得自己动手,做饭、拾烧柴,没有工资,从来没吃过炒菜。我当时没有收入,常遭家中人骂。况且与人相处,一听说你是共产党就没人敢理。”②樊道远:《抗战初期的涅光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100页。即使处于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书店工作也往往被人视为“做生意”,而不是闹革命。中共领导的地下书店不仅支援了当时的革命斗争,而且与中共控制区的新华书店系统一起,共同为随后新中国图书出版发行行业的建立、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
在战争年代,地下书店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直接支援了革命斗争。在政治上,地下书店掩护了基层党组织,便利了交通联络,对各地党组织的发展与革命活动的开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经济上,地下书店为各地党组织及地下党员提供了一定经济支持,南宁春秋书店甚至还资助了一部分进步人士;③李名魁:《记南宁苍梧书店——春秋书店》,《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78页。在文化上,地下书店通过发行书刊及开展活动,宣传了马列主义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对团结、教育进步青年助益良多。“白区是反动宣传统治的世界,在我们的出版物中,只要宣传了一点马列主义,宣传了一点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就算有了很大的成绩。”④王益:《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新华书店》,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7页。这也是地下书店最主要的贡献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下书店则为新中国的图书发行政策与实践提供了经营、管理的相关经验。与书报发行大多采用“无代价的分发与无目的的赠送”方式的解放区新华书店系统相比,⑤邓拓:《五年来发行工作的回顾》,《书店工作史料》(第3辑),第212~213页。敌占区的地下书店企业化程度更高,“在白区工作,把经济利益看得很重,那是不得不如此,因为如果经营不善,便有全军覆没之虞,有时不得不多考虑一些经济上的问题”。⑥王益:《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新华书店》,《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第397页。其具有的较为丰富的经营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华书店系统由机关向企业转型提供了帮助。一部分坚持到新中国成立时仍然存在的地下书店,也逐渐并入新华书店系统,扩大了新中国图书发行网络。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敌占区利用私营身份开设的地下书店对其革命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共日后加强对私营图书出版发行业的管理,“逐步排挤并最后消灭书籍的自由市场”,建立国家垄断的图书市场,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⑦《胡愈之关于发行工作贯彻总路线问题给陈克寒的信》,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7册),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第644页。
K25
A
0457-6241(2017)16-0042-07
2017-06-20
江林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责任编辑:杨莲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