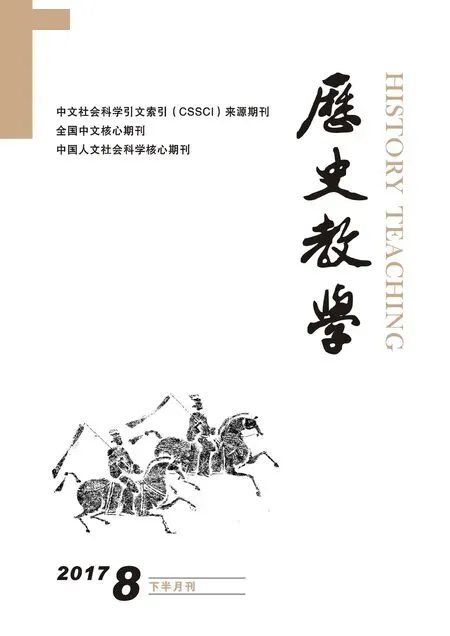战时中共在国民参政会的形象塑造*
洪富忠
(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00067)
战时中共在国民参政会的形象塑造*
洪富忠
(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00067)
抗战期间不仅是革命时期中共实力壮大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共形象得到正面提升的关键阶段。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中国各党派团结御侮之象征,国内政治风向演化之坐标,也是中共在大后方公开活动及形塑自身政治形象的重要舞台。中共在国民参政会成立及运转过程中,形塑了团结抗日的支持与合作者、反对投降与分裂的抗争者、民主政治与发展的引领者等多重形象。透视国民参政会与中共在大后方形象变迁的关联,为理解战时中共战略政略演变及中共何以壮大提供了一面参考棱镜。
国民参政会,大后方,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居于陕北一隅之地,且有近十年的时间被国民党“围剿”。在国民党控制绝大部分舆论宣传工具的背景下,中共的形象已经被极度地“污名化”,“正名”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形象塑造需要平台,而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中国各党派团结抗日的象征,其运转过程也是观察国内政治演变的风向标,为中外观瞻所系,备受各界瞩目,它不仅是中共在大后方重要的公开活动平台,也承载了形塑战时中共形象的历史使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国民参政会的研究无论在资料整理还是专题研究方面已然蔚为大观,硕果累累,其代表性研究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国民参政会中国共关系演变为主线;二是探讨中间势力以国民参政会为议政平台与战时中国政治演变;三是代表性人物与国民参政会之关系;四是关于国民参政会的提案研究。①上述四个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分别为周勇:《国民参政会》,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闻黎明:《第三种政治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王凤青:《黄炎培与国民参政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关于国民参政会提案研究,散见论文较多,整体性研究可参见黄利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参政提案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2007年以前有关国民参政会研究概述可参见王凤青:《国民参政会研究述评》,《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此后关于国民参政会的研究大致仍是前述四个方面的延伸与拓展。对于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塑造,相关研究还较为薄弱。②对于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塑造,尚无整体性研究,既有研究主要散见于少许论文,较为代表性的如刘兴旺、林志彬:《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体形象的塑造与认同——以〈新华日报〉为考察对象》,《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梁忠翠、马玉林:《〈新华日报〉与中共高层形象塑造》,《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洪富忠:《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形象在大后方的塑造及国共博弈》,《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4年第12期。从形象塑造视角探讨国民参政会对于战时中共之意义,既是对国民参政会研究视野的开拓,也是对中共大后方历史既有研究的拓展。笔者就此简而论之,祈望方家指正。
一、团结抗日的支持与合作者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战局渐趋明朗,日本侵华不再是此前先打后谈、谈后即停的渐进式模式,而是以迅速灭亡中国为目的的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面对危局,在加快国共谈判进程以尽快实现国内两大最具实力政党团结御侮的同时,也开始改革相关政治机构,以网罗各界人才,汇聚力量,并有限度地向党外人士提供政治参与的机会和平台,听取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共商抗日大计。1937年8月,被邹韬奋称之为“参政会的胚胎”的国防参议会成立,标志着“民主在抗战期间开始发展的小小萌芽”。①韬奋:《抗战以来》,重庆:韬奋出版社,1941年,第10页。1938年1月底,蒋介石“意欲召集党代表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民意机关之设置问题”,“一在调和党外分子不平之气,一在预防华北伪组织假借民意名义,成立某种组织,以反抗党治”。②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第86、89页。1938年初,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决定结束国防参议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③《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1938年4月1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486页。根据随后公布的《国民参政会条例》,遴选了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在职权、参政员产生办法等方面,中共认为瑕疵不少,但鉴于国共合作的需要及国内舆论多倾向于肯定国民参政会的背景下,中共方面还是做出了积极表态。1938年4月,中共在大后方的喉舌《新华日报》连续报道了国民参政会设立的相关情况并发表相关社评。中共认为这是“相当民意机构的初步形成,但尚不是普通民主国家的代议机关”,但也表示了理解:“在抗战初期,我们还不可能一下子便建立一个民选的代议机关”,“战时的相当民意机关的建立,是十分恰当和需要的”,同时要求国民参政会真正实现民意机关的职能和组织。④《论国民参政会的职权和组织》(社论),《新华日报》1938年4月18日,第2版。对于《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中参政员的选取办法,中共其实是有不同意见且是不满的,因为按照该条例,中共只能属于第三条丁项“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的范畴,且将丁项参政员候选人提名权归属于国防最高会议,⑤《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1938年4月),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 1938—1948》(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46~47页。未能体现出中共作为极具影响的中国第二大党的党派色彩及自主地位,其人数也与中共地位不相匹配。尽管如此,中共在上述社论中也仅是提出了特选五十人中,希望确定“各党派、各文化经济团体的人数比例,并由其自己推选”,表明中共不愿屈居于“文化经济团体”,突出政党属性的要求,其他方面并未予以过多要求。中共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者和推动者,首先就要在国人面前树立团结御侮的政治形象,而国民参政会作为中国各党派团结抗日的象征,中共对其成立的表态就不能不服从于这一大局,这既是大局使然,也是形塑自身政治形象的需要。
中共不仅表态支持国民参政会的设立,在皖南事变以前,中共对国民参政会的参与总体较为积极,这主要体现在参与人数、提案、舆论报道等方面。
在参与人数方面,可从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至第五次会议中,中共参政员参会情况得到体现。按照国民政府1938年6月17日公布的参政员名单,中共共有七名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邓颖超,皆是中共党内名动一时之俊杰或元老。毛泽东因身份特殊,从未亲自出席参政会,其余六位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一届二次会议。一届三次(陈绍禹、秦邦宪未参加)和一届五次会议(陈绍禹、吴玉章未参加)有四位代表出席,一届四次会议有五名代表(邓颖超未参加)出席。⑥参会人员统计来源参见郭德宏编:《王明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周勇主编:《国民参政会》;涂绍钧:《林伯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董必武年谱》编辑组编:《董必武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邓颖超革命活动七十年大事记 1919.5.4-1989.5.4》,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
中共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支持,还表现在积极提案方面。从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次会议到第五次会议,中共参政员共提案14件。具体提案如下:
一届一次会议提案三件:《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改善县区政治机构与保甲办法案》《加强保卫大武汉案》。
一届二次会议提案五件:《民众敦促各该国政府对日寇实施经济制裁案》《严惩汉奸傀儡民族叛徒以打击日寇以华制华之诡计而促进抗战胜利案》《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案》《关于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持久抗战争取胜利问题案》《加强国民外交,推动欧美友邦人士,敦促各该国政府对日寇侵略者实施经济制裁案》。
一届三次会议二件:《拥护蒋委员长严斥近卫声明并以此作为今后抗战国策之唯一标准案》《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
一届四次会议四件:《加强敌后游击活动以粉碎敌寇以战养战之阴谋案》《请政府设法从速救济河北水灾以安民生以慰民心以利抗战案》《请政府命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拥护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声讨汪逆肃清汪派活动以巩固团结争取最后胜利案》。①提案统计来源参见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上、下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续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
一届五次会议未提交提案。这些提案的内容涉及战时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体现了中共对战时战局与政局的全面思考。
在舆论报道方面,我们仍然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到第五次为例,以《新华日报》对国民参政会相关报道篇数,窥见中共舆论报道的活跃:
国民参政会的产生及一届一次会议,《新华日报》有126篇相关报道;一届二次会议有58篇报道;一届三次和四次会议各有37篇报道;一届五次会议(含关于第二届参政员选举)有78篇相关报道。②数据来源为新华日报索引编辑组:《1938年新华日报索引》《1939年新华日报索引》《1940年新华日报索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63年。这些报道内容丰富,既有各参政员对国内时局和参政会事宜的观点看法,也有中共参政员代表在参政会上的具体表现。在形式上,有通讯、社论、图片等多种方式,在当时的报道条件下应该说是做到了相当详尽的程度。除《新华日报》外,《群众》周刊也有相关报道,远在延安的《解放》周刊也不时发表相关信息,足见中共对国民参政会的重视。
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处于孤军奋战状态,即毛泽东所说“寇深祸亟,神舟有陆沉之忧”,唯有团结,才能“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③《毛泽东先生致大会电文》,《新华日报》1938年7月7日,第2版。代表出席多少,是否有提案,媒体报道活跃程度,也是中共对国内政治的一种态度,这种表态自然也在社会各界中留下深刻印象。
除上述中共在国民参政会参会人员、提案、舆论报道等情况外,国民参政会的参与者也为我们留下了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中团结抗日、支持抗战的描述与评论。
1938年7月1日,汪精卫招待到武汉报到的包括中共代表在内的部分参政员。参与茶会的王世杰就认为:“实际上现时不能与本党充分协调者,只是共产党。但茶会时彼等亦极主团结,惟其所谓目标只限于抗日耳。”④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第124页。参加了此次参政员茶话会的中共代表陈绍禹也在向毛泽东等的报告中提及茶话会情形,中共的态度是:“参政会不应有在朝党和在野党之分,刻应谈各党派一致团结、议决抗战建国问题,以表示中华民族团结,借增国内民众抗战信心和巩固中国国际地位的意见”,这些意见得到各民主党派的支持。⑤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第408页。显然,王世杰的评论虽然指出了国共之间的分歧,但也承认了中共是主张团结抗日的,且王的记载与陈绍禹的叙述也比较相符。1938年7月13日,王世杰又记载:“连日国民参政会讨论各案时,共产党参政员与其他参政员,力避冲突。盖中央以团结相号召,共党亦认团结为必要也。”⑥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第127页。应该说,中共作为团结抗日的支持者形象,在国民党内部部分高层中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国民参政会是战时中共参与层次最高、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参政议政平台。中共的一言一行不仅代表中共自身的态度与观点,而且会通过人际网络、社会媒体的传播,给大后方民众留下深刻影响,也促成社会各界对中共形成新的认识和评价。
陈克文曾记载,1938年7月5日下午,孔祥熙等各部会长官在武汉某银行举行招待参政员的茶会,“参政员均借此为互相认识之机会,握手、候问、介绍,记住址、致仰慕,笑靥迎人,强为喜悦”。⑦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 1937—1952》(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第248页。“强为喜悦”固然包含了某些尴尬的意蕴,但前述借此机会相互认识当是人之常情,中共参政员也概莫能外。参政员大都是社会贤达等知名人士,即便是国民党参政员也是社会上较有声望和国民党内较有影响之上层人士,不管观点有无歧见,但相互认识、沟通毕竟可以打破“老死不相往来”的隔绝状态,这对于急欲走向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共来讲,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国民参政会在形塑中共作为团结抗日的支持合作者形象方面,发挥了相当作用。
二、反对投降和分裂的抗争者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挟其精良装备与侵略野心,大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之态势。开战一年有余,中国方面丧城失地,北平、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接连丧失,国府退居重庆,大半河山落入敌手,军民伤亡惨重。尽管国共实现合作,全国抗日浪潮高涨,但现实是如此的残酷,中国究竟能不能抵抗暴日入侵?战抑或和?不仅一般普罗大众,就是党政高层、社会贤达、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也是忧心忡忡,主张谈判及求和之声不绝于耳。1938年11月28日,蒋介石与张嘉璈谈话,“乃知政府中人,仍对抗战全局多作悲观者,此种心理,应急力改正,勿使其蔓延”。①黄自进、潘光哲编:《困勉记》(下),台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641页。11月29日,王世杰约蒋廷黻、罗家伦等人晚餐,言及抗战前途,“蒋廷黻君极悲观,至谓国民政府幸存之可能,不过百分之五”。②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第162、127、261~262页。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内部部分官员求和言论沸沸扬扬,“和平救国”“曲线救国”等奇谈怪论迭起,严重动摇国人抗战信心。此外,国共关系虽维持了合作的基本走向,但国民党防共、反共的基本目标并未改变,双方关系几度紧张,冲突不断,为国内外所关注。国民参政会作为团结抗战之机关,同样是中共反对投降和分裂的重要舞台。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曾经有一段较为和谐的“蜜月期”,但国民党内部防共、反共的声音在国民参政会也不时闪现,中共在国民参政会内采取多种方式予以驳斥和反抗。1938年7月6日至15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会中氛围总体尚好,但也不乏缕缕噪音,王明在其《传记与回忆》中有非常生动的记载。此次参政会上,中共要揭露汪精卫和平救国主张的实质是向日本投降,汪精卫亲自出马,王明当面驳斥,“这也是轰动一时的:谁都知道陈绍禹揭露了汪精卫的汉奸投降路线”。王明也记载了复兴社反共分子马乘风发表反共言论后,其对马乘风与汪精卫的驳斥。王明记载:“绍禹的说话,不仅得到我们的朋友和同情者的热烈鼓掌,而且引起了许多中间人士的鼓掌赞同。”王云五表示:“陈先生,我党提案的意思和你的意思差不多。我并不想反对工人阶级。”《大公报》总编辑拉着王明的手说:“绍禹先生真雄辩也!”③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第409~411页。王明或许对自己的表现有些许夸张之处,但大致情形当不假。王世杰也在日记中记载此事:“马乘风(国民党员)发言,谓大家不当以‘苏联为祖国’,共党陈绍禹认为侮辱,严厉抗议,一时几致决裂。事后经予调解,始罢。”④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第162、127、261~262页。非参政员陈克文在1938年7月13日中午请蒋廷黻、甘介侯、李圣五等参政员聚餐,“席间圣五、介侯谈顷于参政会所见之国共两党党员冲突情形”。⑤陈方正编辑校订:《陈克文日记 1937—1952》(上),第252页。翁文灏则以“陈绍禹(C.P)说明尤为激昂”记载当时双方之争执。⑥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1页。王明雄辩的口才在当时很多人的接触中都有很深的印象,也只有中共参政员才敢于在这种场合对汪精卫之流当面驳斥。1940年4月2日,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作军事报告,指责共产党军队制造冲突,“董必武(共产党参政员)声明其指述不尽符事实”。4月9日,何应钦在答复梁漱溟的书面答复中,指责共产党军队甚厉,“共产党秦邦宪等以不出席相胁,予告以彼等尽可提出反辩,彼等遂仍出席。实则彼等亦并无退席之意”。⑦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第162、127、261~262页。不管中共代表退席与否,皆可见中共参政员以国民参政会为论政舞台,相机驳斥对于中共的不实言论或错误言论。
1938年12月底,汪精卫逃离重庆,走上投降的不归路。汪精卫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叛变的最高领导人,其投降叛国也是战时轰动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汪精卫出走后,蒋介石曾一度较为犹豫,并没有立即公开声讨。1938年12月27日,蒋介石致电香港《大公报》张季鸾,要求其关注香港舆论,对汪精卫应“宽留转旋余地”,蒋此时对汪精卫还抱有一丝希望,期望通过舆论“造成空气”,但“不可出以攻击语调”。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以公开发出“艳电”的方式走上耻辱的叛国之路。12月31日,蒋介石与中央同仁商讨复汪“艳电”问题,“仍主宽缓,留其转回余地”。⑧萧李居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第710、727页。中共对此坚决反对,认为在此种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不能有丝毫幻想余地,要在国民参政会内予以坚决揭露和斗争。在汪精卫“艳电”发表前的12月27日,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召开临时会,“黄炎培、周炳琳等提议去电慰问汪先生病,并派人促其早日力疾返渝。到会诸人均赞同,惟秦邦宪(共产党)反对”。①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第169、171~172、334页。在党内外的舆论压力下,1939年1月2日,国民党中央发表撤销汪精卫职权与党权的决议,对内、对外声明各一件。对外声明有“最后为揭破敌人造谣中伤之诡计,并粉碎其破坏国内团结之阴谋,更望汪先生早日痊愈,重返中央,与吾人携手前进,共同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等语,“共产党之《新华日报》,将以上诸语均略去不登”。②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第169、171~172、334页。刊登国民党相关惩汪文件,体现中共对国民党采取这一举措的支持,但又略去那一段有想象空间之文字,又表现了中共对投降派的决绝态度,在国人面前树立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鲜明形象。
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不仅对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势力作坚决斗争,也对国民党的反共分裂行为同样予以坚决反对,皖南事变即为典型。皖南事变发生前,中共对于何应钦、白崇禧所发“皓电”曾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参政会,阐明中共关于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等问题立场。③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续编),第74~78页。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骤然紧张,双方的斗争很快转移到中共参政员是否出席1941年3月召开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由于国民党方面不接受中共方面提出的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也不接受此后中共有所让步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中共方面决定不出席此次参政会。蒋介石推测中共不出席参政会之心理:“甲、观察我政府心理,是否焦急?乙、待居里到港后之态度如何?丙、观察社会与参政员一般空气如何?”④黄自进、潘光哲编:《困勉记》(下),第764页。蒋之推测大致符合中共当时不出席此次参政会之目的。这对于视团结抗日为根本,力图调解国共矛盾,力促中共参政员参加此次国民参政会的中间党派来说,不能不感到悲观失望,甚至对中共有所埋怨。⑤关于皖南事变后中间党派参与调解国共矛盾,力促中共代表出席参政会的过程,参见闻黎明:《第三种政治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第180~207页。国民参政会向来被视为国内各党派团结御侮的象征,中共参政员不出席此次参政会,以此作为对国民党的反击措施之一,表明其反对分裂的坚决态度。由于中共在皖南事变中是受害者,又是相对弱小的一方,不出席此次参政会,虽然中间党派对此有所不满,但国民党毕竟理亏,且因这一问题,“渐使美国方面群以中国将发生内战为惧”,⑥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第169、171~172、334页。加大了美苏等国对于国民党反共举措的打压,增强了中共的政治回旋空间。
皖南事变后尽管中共代表出席了国民参政会相关会议,但均未提交提案,且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较皖南事变前大大减少。这表明国共在表面上尽管还维持合作的局面,但彼此之间的罅隙却再难以抚平。囿于民族大敌尚未被赶出中国,为表示国共团结抗日,中共一般也很少缺席参政会。1943年夏,正值国共关系再次紧张之际,三届二次参政会召开,中共只派董必武一人参加,蒋介石认为是中共“尚畏清议与公论”之举。⑦高素兰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4册),台北:“国史馆”,2011年,第554页。蒋之“畏清议与公论”的评价未必符合中共实际,但中共的确要考虑不参加会议可能受到的舆论压力,故非特殊情况,中共一般不缺席参政会会议。对国民党的反共举动,中共通过在参政会减少出席人数,不提提案,甚至拒绝出席,以此树立中共坚持抗战,反对分裂的政治形象。
三、民主政治与发展的引领者
抗战必须发扬民力,凝聚民气,而民主则是调动社会各界一切积极力量支持抗战的有效手段。国民党当局虽也倡导民主,但实际上是以战时需要集权为由不断延宕民主政治的实施。对此,邹韬奋就认为,中国的抗战是“以半殖民地的国家抵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正需要大规模的民众动员,因此也特别需要民主政治”,“民主与集权不但相反,而且相成,因为由民主所产生的集权才特别有力”。⑧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上卷),第244页。毛泽东也在全面抗战初期一再强调要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国防政府”,认为“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要“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⑨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5、384页。国民参政会则是中共倡导民主政治的重要舞台。
民主的意蕴相当广泛,战时中共倡导的民主政治在不同阶段又有不同表现和侧重。由于蒋介石对中共最初拟以收编解决,收编不成,即思考是否对中共以“不使其取得合法地位”为要点。因此,在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在参政会中着力于争取包括中共在内各党派能有公开活动的法律地位。在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期间,王世杰就曾记载:“今晨参政会讨论关于政治结社之某案,争执颇久。缘共产党颇思该党取得合法地位,更便于活动故也。实际上共产党之公开活动,自抗战以来,并未被禁止。不过政府既未许其立案,则除在陕北等处而外,该党尚未能公然在其他各处设置分部耳。”①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第126页。王世杰实际上道出了当时中共略显尴尬的地位,虽然高层可以在大后方有公开活动,可称之为实际上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但因未有法律明文规定,中共的合法性始终操之他人之手,为国民党防共、反共提供了极大的弹性。
1939年2月,第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鉴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反共方针,中共中央致电南方局,要求对此次参政会采取“较冷淡态度”,王明在《新中华报》上发表文章,敦促国民党方面“提出实行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具体办法”。②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第441页。中共参政员领衔提出《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该提案对国民政府未能切实推进民权建设表示不满,指出,“至于各党派之团结,既已承认其存在,但还没有予以法律上之保障,以致摩擦时生莫由解决”,强烈要求“政府应给各党派以法律上之保障”。③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上卷),第468~469页。中共参政员对此问题的重视,作为提案审查委员会主席的黄炎培深有感触,曾有颇感为难之感:“共产党董必武提一案——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颇责政府施政失当,要求对各党派予以保障。国民党员大反对,余居中调停,修正通过。董失望,告假不到会。”2月19日,因董必武案结果不能圆满,董又拂衣而去,“问题在国民党政策不许他党活动,在法律上有地位,故对董案‘予各党派以法律上的保护’绝不放松”。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编:《黄炎培日记摘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页。
1939年9月第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召开期间,中共参政会员陈绍禹再次领衔提交《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在过去法律保障基础上要求国民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战党派的合法权利,取消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一提案属于第一次宪政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重点是反对国民党制造反共摩擦,解决国共矛盾,“至于宪政问题,在这里并不明显”。⑤闻黎明:《第三种政治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第81页。如果中共等抗日党派的法律地位得以真正解决,其合法地位和各种权利自然迎刃而解。国民党方面深谙此中意义,自然不会轻易给予这种法律地位,蒋介石也自认这是一招对付中共的妙棋:“中共不参加中央政权,中央不承认中共法律地位,保持现有实力,不使损耗,亦不与倭妥协,而政治经济,积极求进步,则俄亦无奈何我矣。”⑥黄自进、潘光哲编:《困勉记》(下),第743页。因此,自抗战结束,这一问题也未得到解决,但中共要求各党派有法律地位也照顾到其他中间党派的利益,有助于改善和提升其在中间党派中的政治形象。
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中力图解决党派合法性问题虽然符合战时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但毕竟还是属于较为具体的问题,这与其时中共的实力和地位是相符的。随着战争局势的演变及中共实力增强,中共对于民主政治的引领已经不再局限于党派的合法性问题了,而是关于抗战胜利后国家走向、政权结构等更为宏大的构思与安排。中共在国民参政会大致有两条路径:一是敦促国民党自己设定的“宪政”路径;一是提出自己的关于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新构想。
关于国民党设定的“宪政”路径,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主要是支持中间党派敦促国民政府实施宪政。⑦关于中共对国民党设定的“宪政”路径态度,参见洪富忠等《抗战期间中共政权诉求路径的历史考察》,《理论月刊》2016年第4期。在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最后折中通过治标与治本办法两条。中共方面认为,这些决议虽然“比较空洞,然仍不失为进步的决议”,故中共要“积极参加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的各种宪政运动”。⑧《中央关于第四届参政会的指示——关于宪政运动的第一次指示》(1939年10月2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327~328页。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成为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19名代表之一,参加了“期成宪草”的相关工作。不过,以中共对国民党多年的观察,对国民党真正实行宪政并不抱多大希望,周恩来在1943年就曾指出,蒋介石声明的开国民大会,宣布宪法,当然都是骗局。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898—1949》(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74页。就连王世杰也认为蒋介石赞成的提前召开国民大会以颁布宪法的举措“实际上未必有利于民治之发展”。②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第223页。中共提出的主张还是“宣传时期,国民党不会允许全部实行”。③《中央关于宪政运动的第一次指示》(1939年12月1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337页。中共之所以参加国民参政会组织的各种宪政活动,主要是考虑到以中间党派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对此比较热衷和看重,若不在这一问题上表明态度,中共就有可能失去这一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统战对象,毕竟中间党派是中共中间势力统战的中心。④洪富忠:《从边缘到中心:抗战时期中间党派在统战中的地位演变》,《求索》2014年第12期。包括在第二次宪政运动中,中共由冷淡到积极,目的也是“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⑤《中央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1944年3月1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678页。此后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更是清楚地表明,中共即便是赞成以“宪政”一词所代表的民主政治方向,但其实质内涵已经与中间党派所主张的宪政和国民党设计的宪政不同,其趣旨已大相径庭。
国共两党及中间党派所设计的宪政在战时均难以实现。中间党派设计的宪政为国民党所不愿,国民党自身的宪政为各派所不满,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为国民党所不取。基于现实的政治格局,中共提出了既有现实可能性,又能体现民主政治的新方向,即联合政府的建议。这一全新构想首先向国人公开就是在1944年9月15日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逐渐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由此成为1944至1946年国内政治斗争的主线。⑥参见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国民参政会再次成为中共引领战时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舞台。
国民参政会本身即为战时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印证。中共在这一舞台上不断宣示其关于战时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种种观点与构想,使社会各界对于中共政治理念的认识和理解较之战前有了更充分的认识,也使中共在大后方的政治形象愈加积极与清晰,大后方社会各界对中共诸多关于民主政治诉求的积极回应则是其形塑取得重要成效的证明。
结 语
政党作为近代社会的产物,是“现代民族国家中最有效的政治实体”。⑦〔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2页。任何政党为实现自己的纲领,无不重视其形象问题,无论其刻意为之或是无意为之,都会在社会大众中留下某种印象,而这种印象既观感又直接关乎其纲领或诉求能否实现,甚至影响其正当性与合法性。如果说在票选政治中政党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会直接影响到投票人的选择意愿,那么政党的形象同样可以通过公众以非票选的形式而影响民心走向。全面抗战时期,是中共革命时期军队、地域、组织等“硬实力”扩充的重要阶段,同样也是中共政治形象、声誉等“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时期。中共要改变此前国民党对中共的不实宣传,必须依靠一定的平台和方式,宣传自己的政策,形塑自身形象,而国民参政会正是中共在大后方形塑自身形象的绝佳舞台,其公开性、合法性、代表性、影响力等均是其他一般平台所不能比拟的。周恩来在1944年同谢伟思的谈话中就指出:“共产党明知这个会是用来作为装饰品的,也没有实权,而且分给他们的席位同他们的实力是不相称的。但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些席位,因为这给他们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以便使公众了解,而且这是他们所希望的开始走向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一个小小的楔子。”⑧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445页。这一看似对国民参政会的“贬”评,其实真正表明了其对于中共的重大意义。每一次参政会的召开,都会引起大后方各大报纸杂志的关注,大到蒋介石讲话、提案辩论、高官报告、参政员问政,小到发言风采、衣着形象、会场逸事,透过传媒,散布四方,使得众人皆知,对于任何政治力量扩大影响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共自然也概莫能外,因而非常看重这个“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大后方社会各界也以中共在参政会之表现作为观察时局的风向标。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不出席二届一次参政会,“世人多以为从此国内发生内乱而不能对倭抗战”。①蔡盛琦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5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第661页。国民党方面也深知国民参政会对于中共之意义,明确提出要防止中共“利用参政机会为其窃取政权之阶梯”,②《奸伪最近采取三种对策之研究对策》(1944年3月6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藏档案,馆藏号:特22/1.21。国民参政会也成为国共角力的重要场所。
概而言之,中共战时的壮大是多维的。它不仅体现在地盘大小、军队多寡、装备优劣等较为直观的“硬实力”方面,也体现在政治形象、声誉等“软实力”方面。二者相辅相成,但并非以简单的线性关系呈现,可能出现实力增加而形象下降的悖反现象。因此,从形塑视角观察战时各政治力量的变迁,不啻为一种新的研究理路。在大后方,绝大部分人看不到边区的火热场景,也看不到中共军队在前线的英勇杀敌,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表现就成为大后方各界了解认识战时中共的重要窗口。中共在大后方以国民参政会为舞台,较为成功地塑造了其作为团结抗日的支持与合作者、反对投降与分裂的抗争者、民主政治与发展的引领者等多重形象。透过国民参政会在形塑战时中共的重要作用,为我们观察战时中共政略战略的演变无疑提供了另一面棱镜。
The Image-building of the CPC in the National Political Council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it wasnot only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strength of the CPC duringtherevolutionary period,but alsoakey period for thepositivepromotion of theimageof the CPC.The National Political Council,as the people’s political symbol the wartime China’s political unity resist invasion,coordinatesfor theevolution of domestic political wind,alsowasthe important stage of image-building for the CPC in the Great Rear.During the National Political Council of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ng process,the CPChad shaped multiple image,such as the supporter and collaborators of unity against Japan,protesters of opposing capitulation and the division,leader of democratic politics development.Through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al Political Council participation and the CPC’s image changes in the Great Rear,which provided a reference prism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CPC’S strategy and policy evolution and thereason of growth in wartime.
the National Political Council,Great Rear,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Image-building
K25
A
0457-6241(2017)16-0034-08
2017-06-16
*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形象塑造及历史经验研究”(批准号:17BDJ047)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洪富忠,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重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大学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