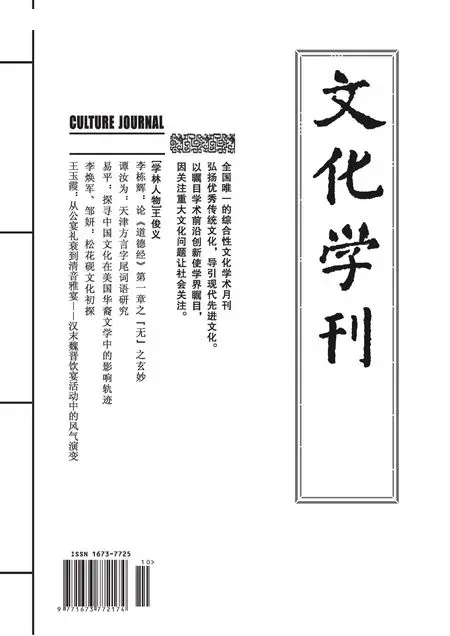侦查阶段贯彻证据裁判原则之思考
沈 晶
(湖北警官学院,湖北 武汉 430034)
【责任编辑:周丹】
【法律文化】
侦查阶段贯彻证据裁判原则之思考
沈 晶
(湖北警官学院,湖北 武汉 430034)
证据裁判原则是证据法学领域的基本原则,侦查阶段亦应遵循证据裁判原则。但在实践中侦查阶段贯彻证据裁判原则有所不足,表现为以证据为依据的理念及行为习惯尚未完全建立;偏重控诉证据,忽视辩护证据;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重视不够;对定罪的证明标准把握不准等。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对侦查阶段贯彻证据裁判原则进行深入思考。
侦查阶段;证据裁判原则;现状
一、证据裁判原则概述
证据裁判原则是证据法学领域的基本原则,证据裁判原则的适用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侦查阶段亦无例外地须遵循证据裁判原则,其基本含义为:应以证据为依据确认案件事实,没有证据则不能认定案件事实。详解之,证据裁判原则的内涵应作如下展开。其一,认定发生在过去的案件事实必须依靠证据,没有证据作为支撑的事实是不可靠的。这里需要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既包括实体法事实,也包括程序法事实,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都需要证据来加以认定,但是用证据证明程序法事实的证明标准一般较之对实体法事实的证明标准要低。其二,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有证据资格(证据能力)。毫无疑问,定案证据必须具有真实性和关联性,但在现代法治社会定案证据还必须具有合法性,这就意味着一个真实的证据即使它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但是如果其不具有证据资格的话,那么它就不能成为定案证据,即我们不仅要用证据还原案件的真实情况,且获取证据的手段和途径也应当是合法的。其三,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必须达到一定的证明标准。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达到一定质与量的标准,否则虽有证据,但证据的质量稀薄,则证据裁判原则空有形式,而不能发挥其实质作用。
二、侦查阶段证据裁判原则贯彻之现状
大体而言,刑事诉讼可分为侦查、起诉、审判三大阶段,侦查作为诉讼的起始阶段,承担着收集证据、抓获犯罪嫌疑人等任务。当前,司法改革的大方向毋庸置疑是走向审判中心主义,但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一直是侦查本位,实行侦查中心主义,即便是在当前其影响余温犹在。证据是诉讼的灵魂和核心,侦查阶段收集证据的情况直接影响诉讼的结果,侦查阶段能否正确贯彻证据裁判原则也将直接决定其后诉讼程序的走向。
近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区,证据裁判原则在理论上得以广泛和深入地探讨,并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得到广泛认可和实施,但在看到这些长足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应关注到证据裁判原则在侦查阶段贯彻不足的各种现状。
(一)以证据为依据的理念及行为习惯尚未完全建立
侦查行为往往具有主动性,但这里的主动性并不是任意性,侦查机关采取一定的侦查行为通常需要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之上,而这里的事实应当立于证据基础之上,但在实践之中出于各种原因及动机,侦查机关在采取侦查行为时并未完全以事实为依据、以证据为准绳,从而具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和非规范性。例如,对于一般逮捕通常需具备三个条件,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刑罚并具有逮捕的必要。其中,最后一个条件亦可称为社会危险性条件,即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其社会危险性的方予以逮捕。为防止实践中公安机关在申请批捕时就什么是社会危险性问题与人民检察院发生分歧,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于何谓社会危险性进行了列举式规定,这就提醒公安机关在请求批捕时向人民检察院提交的法律文书中应附有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客观证据,而非仅仅是公安机关主观上认为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然而在司法实践之中,这一点却常被公安机关忽视。侦查行为属于人民警察的公式勤务,需要迅速及时,这决定了侦查工作的高难度,但即便如此,侦查工作中仍应以达到一定证明标准的证据为行动的前提。
(二)偏重控诉证据忽视辩护证据
在审判者居中裁判、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等腰三角形状的刑事诉讼结构中,侦查机关应属于广义上的控方,但侦查机关又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控方,因为侦查机关属于国家公权力机关,因此其应当全面收集证据,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其中既包括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控诉证据,也当然应包括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辩护证据,而不是仅仅只收集控诉证据。就证据裁判原则的基本内涵而言,以证据还原案件真实情况是其应有之义,其中的证据既包括控诉证据也包括辩护证据,但在侦查机关办案过程中,仍若有若无地受有罪推定思维定势的影响,只注意收集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控诉证据,忽略了对其有利的辩护证据,这也是酿成刑事冤错案件的原因之一。
(三)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重视不够
以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为标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正式确立。而根据证据裁判原则,用以定案的证据必须具有证据资格,这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契合。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发现有非法证据的,均应当有排除的义务。然而在实践当中,侦查机关采用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情形一直禁而不绝;侦查机关注重实体公正甚于程序公正,注重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甚于证据合法性的倾向一直存在,结果可能是在审判阶段关键证据被认定为非法证据从而丧失证据资格,因为取证手段和途径的违法而导致控诉失败。
(四)对定罪的证明标准把握不准
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标准进一步予以了解释细化,明确界定了何为证据确实充分,其包括三个条件: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其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其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刑事定罪问题不仅涉及公共秩序,也涉及公民个人最重要的价值,如若对定罪标准把握不准,则容易酿成刑事冤错案件,司法公信力也将受到严重质疑,因此,准确界定罪与非罪的标准是刑事司法中的重要一环。经过若干年的法治建设,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原有倾向有了很大转变,但是实践当中这种倾向仍有存在,具体表现在对定罪证据的把握上:用证据证明事实无法形成证据锁链,难以达到“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的标准;将未经在法庭上公开出示、调查、辨认、质证的证据作为定罪证据;用以定案证据彼此之间尚有矛盾或依现有证据得出的结论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等。
三、侦查阶段应充分重视证据裁判原则
侦查阶段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对于整个刑事诉讼后续走向和刑事诉讼质量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侦查阶段充分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应着重如下方面。
(一)强化证据意识、树立证据裁判主义
刑事诉讼围绕着收集、审查和判断证据进行,证据是刑事诉讼活动的核心和焦点。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强化证据意识、树立证据裁判主义的重要性是显然的。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人员均能认识到证据在诉讼中重要意义,认识到证据是还原事实情况的唯一理性路径,并尽力收集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但往往重视证据的实体意义而忽视收集证据的正当程序,即对收集证据的手段、方法、途径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未予以重视。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正步入法制化的轨道,各种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正在趋于完备之中,但制度的有效运行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的正确,而且也取决于实施制度的人的观念是否正确,否则再好的制度也会沦为一张白纸。因此,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公安司法人员充分认识理解并自觉贯彻证据裁判主义的意义重大。
(二)公安司法机关秉持客观公正、全面收集证据
在控、辩、审三方组成的等腰三角结构中,侦查机关扮演的角色不仅是广义上的控方,亦是国家公权力机关,它不仅要为检察机关行使控诉职能提供证据支持,而且也要坚持国家公权力机关的底限正义,兼顾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即不仅要打击犯罪,而且要注意其所使用的手段和途径也应当是正当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以及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因此,公安司法机关尤其是侦查机关在实践中必须秉持客观公正,注意全面收集证据,纠正以往重视控诉证据、有罪证据而忽视辩护证据和无罪证据的倾向。
(三)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定的背景和出发点是遏制刑讯逼供、防范冤错案件、严格人权保障。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中央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法律界认为法庭能排除侦查中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改变“侦查中心主义”和“卷宗中心主义”痼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法官排除非法证据,还有利于改变当前公检法三方的关系,能对审前程序进行有效的事后干预,并倒逼侦查机关严格、规范执法。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实施状况并不佳,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部分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并未被有效激活。而基于对证据裁判原则的正确理解,我们不仅要强调用证据来回复案件真实情况,而且强调用以定案的证据不能是非法证据,据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能有效落实直接关系到证据裁判原则的正确贯彻,因此,实践当中务必要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保定案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当然必须要补充的是,实践中隐约出现另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取证程序的合法性,证据稍有瑕疵即以非法证据苛责之,导致执法过程的畏缩,甚至是懒作为和不作为。
(四)准确把握定罪证明标准
证据裁判原则是一个立体的系统,它不仅强调用证据还原案件真实的必要性,而且强调用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证据的质与量,即定案证据不仅需要具有一定的品质,定案证据的总和还必须达到必要的程度和标准,如果只强调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而忽视定案证据的质与量,则证据裁判原则虚有其表,极有可能在实践运行中被驾空。近年来媒体曝光的冤错案件,在很大程度上与未能很好地把握定罪证明标准有关系。综合判断刑事案件的证据是否达到定罪的证明标准,本应是法官的职责,但基于前述侦查阶段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性,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也应学会和习惯用法官的视角来预先衡量其所收集证据的质与量,以及是否达到了定罪的证明标准,并以此来引导和调整自身的侦查行为。
D925.2
A
1673-7725(2017)10-0153-03
2017-08-01
本文系2015年度湖北警官学院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15YB034)的研究成果。
沈晶(1975-),女,湖北钟祥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及证据法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