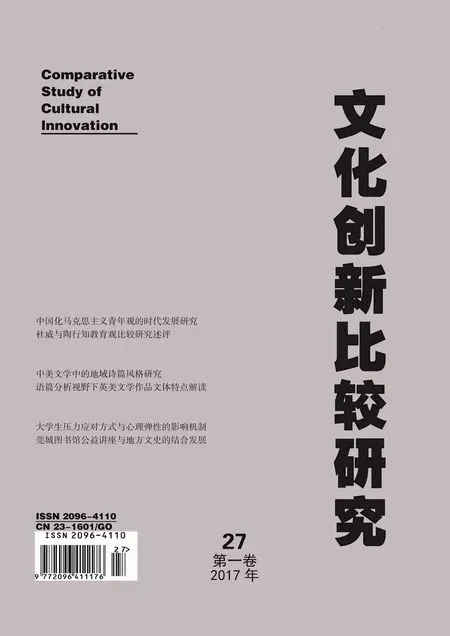杜威与陶行知教育观比较研究述评
李逢超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 541006)
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教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美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他洞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在不断学习与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教育观点,对美国乃至全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初期,陶行知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在继承他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教育主张,对中国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 杜威和陶行知教育理论的分析
陶行知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费正清曾评价说,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越了陶杜行威知。是”杜[1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
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中提出中国要注重试验主义,而陶行知将其试验主义教育理论进行了实践化、中国化。在最初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中,陶行知试验过杜威教育的三个理念。但结论是杜威的理论不适合中国实际,中国教育应实行“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陶行知认为教育需要联系社会生活,目的是从积贫积弱的国情出发,普及大众教育,提高国民素质。
1.1 “教育与生活”与“生活即教育”
杜威希望通过学校这一雏形社会,能够培养美国年青一代具有符合民主社会要求的素质;陶行知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将杜威的提法颠倒了一下,主张“生活即教育”。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乡村教育的生活教育理论。
陶行知看来,无论是教育还是生活都是广泛的,他的“生活教育”观点的外延大于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外延。 他“生活即教育”的观点产生于中国生活,目的也为改变中国生存状况,“生活教育”学说是从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富有时代特色,受到从进步教师代表的知识分子到社会底层劳苦群众的欢迎,并引起了国内外教育家的注目。
1.2 “社会即学校”与“学校即社会”
杜威的学校是特殊化的、理想化的社会,它是经过选择的,排除了一切恶劣因素的社会。陶行知指出他和杜威思想的不同之处:“要先能做到‘社会即学校’然后才能讲‘学校即社会’;要先能做到‘生活即教育’,然后才能讲‘教育即生活’。要这样的学校才是学校,这样的教育才是教育。”[2]
由此可见,杜威学校学生进行的是一种知识上的学习,一种为将来走上社会准备的知识原理的学习。而陶行知则正相反,学生主要通过自己眼前的生活摸索出现实生活技能,并以技能性学习为解决教育与现实生活脱节,解决中国贫弱之良策。事实证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重点不在原理、知识本身,而在解决问题的技能,在完全的实用。
陶行知立足于中国本土,开展了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乡村教育、大众教育,杜威则立足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普及教育后的基本问题。他的教育观点既联系了中国历史,扎根于中华民族土壤,又吸收了国外的优秀成果,联系实际,具有时代特点。
1.3 从“做中学”到“教学做合一”
杜威“做中学”反映了尊重儿童个性,强调了个人的直接主观经验的特点。而陶行知鉴于国内“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提出的中国学校一定要改革教学法,陶行知认为学生的“学”与教师的“教”要结合起来,通过“做”让师生共同完成任务。这两者观点的提出是出于完全不同的两种目的。
杜威实验学校中的“做中学”不同于陶行知,他指出“学校里的作业不应该是一般职业的单纯的实际手段或方法,使学生得到较好的专门技术……作为儿童去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起点。”[3]
首先,两者涉及的范围不同。杜威主张通过“做”来学习,但他认为学校是社会的雏形,但又不同于社会,为了避免学生沾染上社会中的不良事物,“做中学”要在校内通过模仿社会的生活实行,而不是从社会的、实际的事上进行学习。陶行知也以“做”为中心,但他主张的学习则是以实际生活为广阔的课堂,这样“教学做合一”涉及的范围要比“做中学”更广泛、更深远。
“做中学”中的“做”是让儿童从事游戏、手工这样的活动,这是一种模仿现实的虚拟活动,而陶行知的“做”既包含了校内的实验活动,也包括了真实的社会实践,从当时中国教育的现状来看,“教学做合一”在中国具有更大的实用性,因此也成为中国教育家认识、改变中国教育现状的有力手段。
再者,“教学做合一”突破了“做中学”“教”与“学”的限制。杜威认为传统的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学校里只会服从教师的命令,在社会上只会服从领导的命令。他希望学与做相结合的教育打破传统由教师传授学问的被动式教育,因此在杜威的理论中,他更强调“做”和“学”,相对忽视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陶行知认为,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做”密切相关,他希望通过做,让师生共同的完成自己的任务。陶行知重视教师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他认为要造成适当的国民,须有适当的教员,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发展,还要参与到学生的学习活动中,处于与学生共同发展的地位。
总之,陶行知学习“做中学”,但非囿于“做中学”,而是在结合中国实情的前提下,提出了适合中国教育发展的思想。
2 陶行知与杜威教育观点不同的原因
杜威与陶行知的成长背景、社会经历不同,最终影响了他们的教育观点。
杜威所处时代的美国刚刚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阶级对抗加剧。美国社会迫切需要转型,而教育文化的发展不能满足此时社会的需求,传统的教育方式不能提供现代工业文明需要的创造型人才,所以有识之士强烈要求教育改革。处于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由社会变迁所引起的社会活动对杜威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接受了这样一种立场,即哲学家必须持续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批评。”[4]此时,注重创造的实用主义思想满足了社会的需要。
反之,在中国,自鸦片战争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国侵略以及国内军阀混战的摧残,民生凋敝,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困苦,在温饱都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教育发展步履维艰,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想法在此时根本行不通。于是,他开始改造杜威的教育思想,使之成为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教育方式。
再者,杜威的哲学思想发展经历颇丰富。他读书时深受神学直觉主义、黑格尔的绝对主义哲学的影响,再到后来,又受詹姆斯《心理学原理》的影响,杜威提出了经验的、形而下的自我实现理论。杜威指出经过自己思想的不断碰撞,他已不满足于对生活和行动作形而上学的理解,直至进入到芝加哥大学,杜威终于完成了对自己哲学思想的改造。
而陶行知不仅受先秦儒家思想的影响,还受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的影响,1913年,先以“知行”为笔名发表文章,后改为“行知”,并一直沿用。所以说陶行知在学习西方哲学教育思想基础上,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成分。因此,他可以立足中国实际,在杜威的影响之下,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
总之,从陶行知身上我们看到,对待外来教育理论应该辩证看待,事实证明,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就用,生搬硬套可能不仅不会促进发展,还会错过发展时机。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在不断地交流中,各种思想、理论不断传到中国来,此时我们应该立足实情,进行有选择性、有创造性地利用,而不是盲目照搬。
[1] 周洪宇.陶行知研究在海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397.
[2]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41-182.
[3] 美·约翰·杜威著,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译.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5.
[4] 罗伯特·B·塔利斯.杜威[M].北京: 中华书局,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