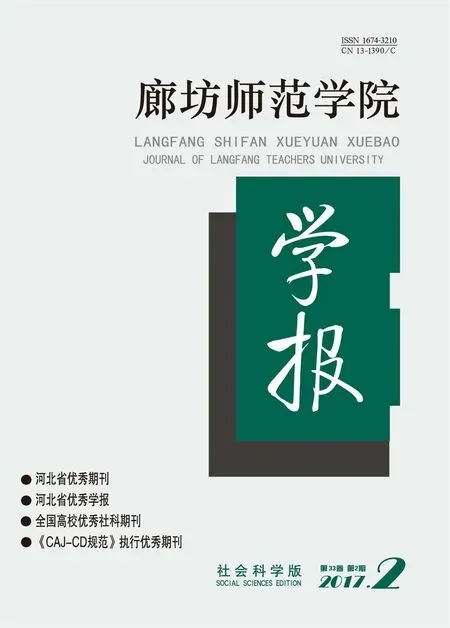《史通》“亡篇”说献疑
张固也,徐伟连
(1.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湖北武汉430079;2.布吉中学,广东深圳518172)
《史通》“亡篇”说献疑
张固也1,徐伟连2
(1.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湖北武汉430079;2.布吉中学,广东深圳518172)
所谓《史通》有几个“亡篇”的说法,与史传记载不相符合,且自相矛盾之处颇多。这些篇名内涵丰富,关联甚广,在书内其他各篇多已有所论述,没有必要别撰单篇。晚唐柳璨著书,逐篇批驳《史通》,共四十九篇,则《史通》篇数亦应相同。刘知幾之著《史通》四十九篇,不多不少,这是在刻意模拟《文心雕龙》,用刘勰的话来说,即“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因此,《史通》不可能另有“亡篇”。
刘知幾;《史通》;亡篇;刘勰;《文心雕龙》
《旧唐书·刘知幾传》云:“知幾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备论史策之体。”①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71页。《新唐书·刘子玄传》则说:“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古今。”②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21页。今本《史通》二十卷,内篇三十六篇,外篇十三篇,共四十九篇,与史传记载正相符合,似乎保存完整,并无遗缺。然而,宋代以来多数版本中,内篇目录多出几个有目无文的“亡篇”,历来信从者众而置疑者寡,但双方都没有提出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论述。“亡篇”之有无多寡,表面上看来似乎无伤大雅,实际上却关系到如何理解全书的编排结构及刘知幾对刘勰《文心雕龙》的模拟手法,因此有必要做一番深入细致的探讨。
一、“亡篇”说的由来
关于《史通》“亡篇”的明确记载,较早见于宋元之际王应麟的《玉海》一书:
《史通》上秩自《六家》至《自叙》三十六篇,及前叙及志中,共四十二篇。自《辨惑》(当作《辨职》,今本第三十五篇)以下,缺《体统》、《纰缪》、《弛张》、《文质》、《褒贬》五篇。下秩自《史官》至《忤时》十三篇(原注:内篇《六家》至《弛张》第三十八,外篇《史官建置》至《忤时》第十三)。《书目》:“《史通》二十卷,评议作史体例,商榷前人,驳难其失,分内外篇。内篇十卷,三十六篇,又有《体统》、《纰缪》、《弛张》三篇缺;外篇十卷,凡十三篇。③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721页。
傅振伦先生在《史通通论》中对此做过比较细致的分析,认为“盖其内篇《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嘉祐五年(1060)《新唐书》撰成之前,已不经见也”;“盖王应麟所见宋刊《史通》,有数种不同版本也”。④转引自刘占召:《史通评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0页。其实《玉海》只是类书,前两条正文、注文是否是王应麟亲见两种版本,难以质言。后一条则已明言抄自《书目》。《书目》是《中兴馆阁书目》的简称,南宁孝宗淳煕五年(1178)编撰成书,所著录的记载三个“亡篇”名目的宋本《史通》,其抄刻年代当然比这更早一些。
现存最早的《史通》版本为明嘉靖十四年(1535)陆深刻本,“此后,万历五年(1577)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1602)张鼎思刻本都以陆深刻本为照对或重要基础,李维桢、郭孔延、王维俭等对《史通》的评释之作则又以二张刻本为基础,而清代以来流传的《史通》也都以这些明刻本为基础”①王嘉川:《清前史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页。。张之象本据无锡秦柱家藏的宋版校刻,其内篇目录末仅有“《自叙》第三十六”,前后并无亡佚篇目。但清何焯批校本用朱笔将“自叙”改成“体统”,复添补“《纰缪》第三十七、《弛张》第三十八”二目于下,又加小字注云:“末三篇俱亡,或云《体统》篇即《自叙》也”。张鼎思本以家藏抄本作过校补,其内篇目录之末作:“《体统》第三十六、《纰缪》第三十七、《弛张》第三十八。右定凡三十六篇,并前序及志第七篇,共三十八篇”,而正文内亦作“《自叙》第三十六”,与张之象本同。清人所见影宋抄本应该都与张鼎思家藏抄本为同一系统,故卢文弨云:“案宋本目录作《体统》第卅六,《纰缪》第卅七,《弛张》第卅八,且总结云:‘右定凡卅六篇,并前序及志第七篇,共卅八篇’”②卢文弨:《群书拾补·史通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9册,第343页。。陆心源《影宋抄〈史通〉跋》云:“每卷有目,连属篇目。……目后有总结云:‘右定凡三十六篇,并前序及志第七篇,共三十八篇。’”③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5,《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30册,第65页。三者描述基本一致,而与王应麟的三种说法互有异同,但三“亡篇”都列在《辨职》第三十五篇后。直到明代郭孔延《史通评释》、王惟俭《史通训诂》等,才在内篇目录中先列“《自叙》第三十六”,后列三“亡篇”,篇名下各注“缺”或“亡”字。清人浦起龙《史通通释》同样以“亡篇”居后,而在书中具体谈到:
三亡篇,旧本仅见内篇目录之末,今依目补列于此。但《自叙》后不应更有余篇。尝阅章宫讲《山堂考索》,《纰缪》篇缀在《烦省》之下,其二篇者不复及。而先举其总曰五十余篇,则固有其文,而莫定其原次耳。再考《唐书》本传,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与今行本数合,毋亦史氏疏于原始乎?④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页。
浦起龙乃据王本删订,其怀疑“亡篇”次序不应在《自叙》之后,无疑是对的,却没有注意到这是晚明才出现的后移,此前并不存在这一问题。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收录《史通》据张之象本,其提要云:
凡内篇十卷三十九篇,外篇十卷十三篇。……其内篇《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有录无书,考本传已称著《史通》四十九篇,则三篇之亡,在修《唐书》以前矣。⑤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50页。
清末杨守敬说:“或者三篇之亡,即在唐代,故《唐志》就见存言之耳。”⑥程千帆题记,张三夕辑录:《〈史通〉三家评校抄》(续),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12,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新唐书·艺文志》未言篇数,“《唐志》”当作“本传”。这是相信《史通》有三个亡篇,而据史传所记篇数,推测三篇亡佚于欧阳修等编撰《新唐书》之前。
民国以来学者的《史通》研究远较之前广泛而深刻,涌现了大量新式校注和研究论著。但或许由于缺乏旁证材料,学界并不重视对“亡篇”问题的研究,至今没有一篇专门讨论的论文,似乎宋本的“亡篇”之说毋庸置疑。然而,仍有两位著名学者提出了简单的怀疑意见。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第八章说:
然《新唐书》本传已云《史通》内外四十九篇,且考内篇之序,所亡三篇皆在《自叙》之后,颇为不伦。或本无此三篇,抑编者之错置欤?⑦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96页。蒙文通先生在《馆藏明蜀刻本〈史通〉初校记》(下引程千帆先生书中作“张蕴华《明蜀刻本〈史通〉初校记》”)一文中认为:
《杂说下》篇杂记十条,尤为离异。详细绎之,其一、二两条,殆即《体统》;四、五、六、七、八各条,殆即《纰缪》;九、十两条,殆即《弛张》。岂此三篇者,惟有条记而书固未成欤?⑧蒙文通:《蒙文通文集》第3卷《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442页。程千帆先生针对二家之说,提出过较详的批评意见:
窃谓金氏本无此三篇之说,似不可从。盖伪造古亡书以欺世之事,固多有之,而伪造亡篇题目者盖寡。且此三篇之名目,既非别处旁记,而为宋本以来目录所固有,则其源流必有授受。……是故据《杂说下》篇以推证三篇之未成,转而不如据此以证三篇本有其书,既成而佚也。至编者错置之说,其言近是,然亦未达一间。盖此三篇本来次第若何,诚不可知,而今本目录附诸《自叙》之后者,则以其书既亡,后人因移其篇题于内篇之尾,而为现存三十六篇重编次第耳。①程千帆:《〈史通〉笺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页。
金氏仅仅以“亡篇”次序“不伦”,而以“或本无此三篇”作为两种解释之一。在知道宋本目录原列《自叙》前之后,其疑即涣然冰释。《杂说》上中下三篇都是以零星札记的形式,批评各种史书中存在的错误或瑕疵,篇内有《春秋》《公羊传》《汲冢纪年》《史记》《宋略》《后魏书》《周书》《隋书》以及“诸汉史”“诸晋史”“北齐诸史”“诸史”“别传”“杂记”若干条的小标题。显然,前十三者以批评对象不同立目,后者所谓“杂”指其批评对象杂泛,其性质和写法并无区别,根本看不出来前二条与“体统”、中五条与“纰缪”、后二条与“弛张”有何特殊关系,蒙氏之说确实没有多少道理。而程氏的批评,则并没有击中要害,而以“伪造篇题目者盖寡”“宋本以来目录所固有”两点理由来作反驳,是否能够从正面支撑起“亡篇”之说呢?
二、“亡篇”说的疑点
明清以后,藏书家佞宋之风日盛。人们对于《史通》“宋本目录”中的“亡篇”深信不疑,自然再正常不过了。然而,只要对上述各家“亡篇”说略加考察,就可以看出其间颇多自相矛盾,诚可谓疑点重重、漏洞百出。
一是究竟有三个还是五个“亡篇”?明清以来流传的宋本和新出各种版本中,一般只有《体统》《纰缪》《弛张》三个“亡篇”篇名,多数学者如程千帆先生讨论这一问题时也只提这三篇,傅振伦先生引及《玉海》记载的还包括《文质》《褒贬》二篇的版本,认为“王应麟所见宋刊《史通》,有数种不同版本也”。但问题在于,版本可以有很多,亡佚的篇数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或五篇,或三篇,或零篇。以理推之,主要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亡佚了五篇,但有的版本全部保留了五个篇名,有的版本连篇名都遗漏了两个;另一种可能是没有亡佚,宋人目录中因某种原因多出三个篇名,后来又编造出两个。通行的三“亡篇”说,恰恰是最不可信的。
二是内篇究竟是“右定凡三十六篇”还是“旧本定为三十八篇”②陆深:《俨山集》卷86《题史通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其实宋代以来各种版本内篇实际所存都只有三十六篇,所以前者显然是不计“亡篇”的结果,问题是内篇目录在《辨职》第三十五后多出三“亡篇”,则目录和书内都题作“《自叙》第三十九”,或标为第三十六篇而删三“亡篇”的篇次,皆无不可。奇怪的是,多数宋本、影宋抄本、张鼎思刻本等都不这样做,而是书内题作“《自叙》第三十六”,目录中没有《自叙》而另有“《体统》第三十六”,完全自相矛盾。为了弥缝这一矛盾,何焯、傅振伦就说《体统》篇即《自叙》,但前一篇名与后者内容方凿圆枘,铻难入。看了清何焯朱笔批校张之象本的做法,才恍然大悟:张之象所见才是真正的宋代善本,并无三“亡篇”③上引傅振伦《史通通论》云:“《玉海》卷49注云:‘《史通》内篇,《六家》至《弛张》第三十八篇,又《自叙》。’盖其时刻本目次,《自叙》殿末,且次于三佚篇之后也。陆深及张之象刻本亦然,此宋刻之一种也。”检《玉海》,并无“又《自叙》”三字,所述张之象本亦非是。,其他宋本目录正是用与何焯相同的做法,窜入所谓“亡篇”名目,而之所以非得替换掉《自叙》这一篇目,应该是受到某种三十八篇说的影响。
三是两种内篇共三十八篇的记载究竟何者较为可信?宋本内篇目录末作:“《体统》第卅六,《纰缪》第卅七,《弛张》第卅八。右定凡卅六篇,并前序及志第七篇,共卅八篇。”其中包含两种自相矛盾的三十八篇说,不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卢文弨引用后按云:“此语殊不可晓,恐有误也。”④卢文弨:《群书拾补·史通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149册,第343页。其中“志第七篇”,《玉海》作“志中”,更不可解。我们怀疑“志第”为记载篇第之意,“七”为“二”字之误,“二篇”即指今本《叙录》和内篇目录,合正文篇数,正好三十八篇。内篇目录及末尾统计文字,应该是刘知幾自加的。由于内篇结构序次严整,刘氏特意编定次序,而外篇皆为随手札记,谈不上什么结构,就没有为之编目。如果后世为阅读方便计,不可能只编内篇目录。宋代这句话已有误字,时人不解其意,又以为已有“亡篇”,就将三个篇名窜入目录中,并刻意不数《自叙》,以附会内篇共三十八篇之说。
然而这三个篇名,可能并非有意伪造,而是渊源有自。据陆心源《影宋抄〈史通〉跋》,宋本“每卷有目,连属篇目”。这并非指书前的内篇目录,而是每卷第一行书名之后,第二行接连标明该卷包含的篇名,而不标篇次。假如某个篇名下用小字标注“体统、纰缪、弛张”,而后人看不出这三个词语与上一篇名的关系,就很容易将其误认作三个“亡篇”。我们通过分析三个词语的涵义及其在《史通》中的使用情况,可以断定它们不可能是“亡篇”名称,并进一步推测出它们有可能是哪一篇名下的标注。
《史通》中使用“体统”一词共七次:
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自叙》)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忤时》)
兹又体统不纯,难为编次者矣。收之矫妄,其可尽言乎!(《探赜》)
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变三国之体统,改五行之正朔。(《探赜》)
寻其(《九州春秋》)体统,亦近代之《国语》也。(《六家》)
原夫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名目虽异,体统不殊。(《书志》)
观子长之叙事也,洎周以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叙事》)
“体统”始见于东晋慧远大师《大智论抄序》:“叙夫体统,辨其深致。”①僧祐撰,苏晋仁、萧鍊之点校:《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89页。梁刘勰《文心雕龙·附会》云:“夫画者谨发而易貌,射者仪毫而失墙,锐精细巧,必疏体统。”②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51页。可见“体统”是相对于细节而言的整体,慧远用来指《般若经》的经书和思想体系,刘勰用来指文章的整体谋篇布局。刘知幾所谓“辨其指归,殚其体统”,显然化用自慧远之语。但他对“体统”更加重视,除以上七例外,还经常使用“统体”“体制”“体式”“大体”“体”等词。其具体涵义,可以细分为四个层次:一,《自叙》一例指所有史书区别于其他书籍的总体特征,书中类似说法还有“史体”“载笔之体”等;二,中间四例指某类或某部史书的独特体例,书中具体说法还有“《书》体”“《史》、《汉》之体”等;三,《书志》一例指纪传体的内部体裁,书中具体说法还有“纪体”“志体”“传体”等;四,《叙事》一例指史书编撰的具体方法或体例,书中具体说法还有“编次之体”“摸拟之体”“叙事之体”等。
《史通》中使用“纰缪”一词仅两次:
又迁之纰缪,其流甚多。(《探赜》)
加以探赜索隐,然后辨其纰缪。(《暗惑》)
但其全书中“错缪”“乖缪”“舛谬”“讹谬”“牴牾”以及“诡”“诬”“愚”“妄”“失”等批评字词,“岂非谬乎”、“不亦谬欤”之类感叹,随篇可见,无处不在。有些篇目几乎把前代史书说得一无是处,如《载文》篇不惜笔墨地论述“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刘氏甚至公然标榜“疑古”“惑经”,对《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正经名史也大加批评。宋祁批评刘知幾“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③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4542页。,被后人视为的评。唐末柳璨、宋代孙何还专门著书,对刘知幾进行反批评。他们的做法,固然有思想上比较保守的一面,但却典型地反映了刘知幾过多批陈前人“纰缪”所引起的激愤。
《史通》中使用“弛张”一词三次,“张弛”“改张”各一次:
至于国有弛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邑里》)
其间则一褒一贬,时有弛张;或沿或革,曾无定体。(《惑经》)
班氏一准太史,曾无弛张,静言思之,深所未了。(《杂说上》)
凡此诸名,皆出当代,史臣编录,无复张弛。盖取叶随时,不藉稽古。(《称谓》)
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二体》)
“弛张”本义指放松或拉紧弓弦,引申为变化、变通、改革等。《礼记·杂记下》记载孔子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韩非子·解老》篇说:“故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弛张。”以上五例,或指郡国设置、人物称谓的变化,或指史书体例上的变通。其实刘知幾在史学上具有很强的革新精神和发展观念,主张史书要随着时代世事的变化,而采取一些必要的变通和改革。这一思想贯彻于全书的许多篇章,所以还经常使用带“革”字词句,如“刊革”“厘革”“变革”“沿革”“革旧”“革其流”“革兹体”等。《载言》篇说:“故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称谓》篇说:“变通其理,事在合宜。”《书志》篇说:“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当变其体。”更可以看作是刘知幾对史学“弛张”主张的言简意赅的理论性表述。
《史通》内篇三十六篇的名称都是史书体裁、体例和编撰方法的某一概念,可以把正文内容限制在某一具体方面。而据以上分析,“体统”“纰缪”“弛张”三个词语却广大无边,不受限制,《史通》每一篇的正面论述都可以说在谈“体统”,每一篇都在批评前人的“纰缪”,每一种针对“纰缪”提出的变通主张都是“弛张”。用刘知幾的话说,全书主旨就是“辨其指归,殚其体统”。晚清汪之昌曾经拟补此三篇①汪之昌:《青学斋集》卷32。又收入程千帆:《〈史通〉笺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205页。,乃融会今存各篇中的相关论述连缀而成,堪称《史通》研究的独特成果,但刘氏本人绝不可能如此自相重复,汪氏的补作恰恰足以反证《史通》没有“亡篇”。这里还应附带指出一种误说。傅振伦先生云:“(《群书考索》)历举其篇名,其中有《纰缪》一篇,其所录篇名,不应为亡佚之篇,盖《纰缪》在南宋之末尚存。罗璧《识遗》云:‘刘知幾《史通》辟迁、固之谬曰:韩王名信都古韩国……’一条,今《史通》无此语,或即《纰缪》之文。”②转引自刘占召:《史通评注》,第451页。《考索》乃宋代类书,随意摘录若干篇名而已,根本不能作为是否亡佚的证明。罗璧所引,则见今本《杂说上》,傅氏偶有失检。宋人引用《史通》不少,没有一条不在今本之内,这是《史通》没有“亡篇”之明证。
我们通过分析以上三个词语,又意外地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史通》各篇大都文字简短,主题单一,文章一气呵成,不容细作区分,再加小标题。但旧本有两篇例外:一是“《书志》第八”下注:“并序、《天文志》、《艺文志》、《五行志》、杂志。”二是“《叙事》第二十二并序”下注:“简要、隐晦、妄饰总三条。”后者注中三词,一望而知为《叙事》下的小标题,兹不具论。前者浦起龙认为:“旧注未协,本非原文,今刊正。”将其改作“序论、论天文、论艺文、论五行、后论”。其实两注都是后起的方式,非刘知幾时代所应有。《书志》篇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开头部分评论书志的特点与源流,其中有“名目虽异,体统不殊”之句;中间部分认为断代纪传体国史不应设立天文、艺文、五行三志;最后部分主张另立都邑、氏族、方物三志。这三个部分完全可以用“体统”“纰缪”“弛张”三词来作小标题,而表面上三词与“书志”看不出联系,也很容易被误认作“亡篇”之名。
至于“褒贬”一词,《史通》中共使用十三次,见于《表历》《论赞》《序例》《题目》《称谓》《载文》《因习》《浮词》《自叙》《惑经》《杂说上》《杂说下》等篇。褒贬是《春秋》大义之所在,也是中国史学的一大特点。刘知幾自然极为重视,其《自叙》篇说:“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全书中使用其他带有褒贬含义的字词文句更多,特别是前后相连的《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五篇,其实就是从五个角度论述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重要性。
《史通》中没有使用“文质”一词,但提及这两个单字或相关的论述不少,见于《六家》《本纪》《鉴识》《摸拟》《才第》等篇。特别是《言语》《叙事》二篇,几乎就是从两个角度论述文质关系的专篇。如《言语》说:“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亘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叙事》说:“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正如有学者所说:“刘知幾对于文和质的阐释,比前人更详具充分。”③赵俊:《〈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123页。
因此,“褒贬”“文质”两词与上述三词类似,也属于内篇很多篇题的应有之义,已经从多个角度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述,故不可能另撰这两个“亡篇”。它们应该是在三“亡篇”被窜入内篇目录之后,有人以为“褒贬”“文质”亦属史学理论中的重大问题并再一次将其窜入内篇目录的。
三、四十九篇说新证
《史通》“亡篇”说之所以长盛不衰,除了因尊崇宋本而不敢轻易怀疑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史通》全书四十九篇的明确记载,晚见于《新唐书·刘子玄传》,且没有更多的旁证。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解释的空间:北宋早期还有包括“亡篇”在内的版本流传,直到欧阳修、宋祁编撰唐史之时才告亡佚。
我们认为这种解释与史传记载书籍的通例不符,是很难成立的。纪传体史书记载书籍,主要有两部分。一是经籍或艺文志,早期主要依据国家藏书目录,都是实际流传的版本。二是列传部分也往往附载传主的著书情况,主要依据实录、行状、墓志、书序等官私材料,不一定真正流传。故同一部正史中,志、传记载往往不相符合,比较普遍的是志有而传无、志篇卷多而传篇卷少。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其原因难以详述,这里仅需注意一点,即史传记载书籍应该符合其成书时的状况,而不是其流传存佚状况。因此,宋祁编撰刘氏传记,有可能依据更原始的传记材料,而其中记载了《史通》的篇数。即使没有这类材料,宋祁根据当时传本来记载,那么只要他见过至今尚存的内篇目录,就应该记载为五十多篇,而不会只记存世的篇数。只有在宋祁根本不知道有“亡篇”一事的情况下,他才会如此记载。但假如真是这种情况,宋本目录中的亡佚篇目又从何而来呢?
不仅如此,唐末柳璨编撰《史通析微》的相关情况,也可以佐证柳氏所见《史通》亦为四十九篇。柳璨曾相唐昭宗,因助朱温诛杀士大夫而为人所不齿。但他精通史学,颇为时人称赞。“璨以刘子玄所撰《史通》讥驳经史过当,璨记子玄之失,别为十卷,号《柳氏释史》,学者伏其优赡。”①刘昫:《旧唐书》,第4669、4034页。《新唐书·艺文志》载其又名《史通析微》。宋人不满刘知幾“工诃古人”,因而对这部专门批驳《史通》的书籍评价较高,流通较广,后渐亡佚。幸好宋代书目中简单记载了它的一些基本情况。
《书目》:《史通析微》十卷,随篇评论其失。凡四十九篇。又第十篇摭知幾四朝实录之失。②王应麟:《玉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34页。
《史通析微》十卷,唐柳璨炤之撰。璨以刘子玄《史通》妄诬圣哲,评汤之德为伪迹,论桀之恶为厚诬,谤周公云不臣,褒武庚以徇节,其甚至于弹劾仲尼。因讨论其舛缪,共成五十篇。萧统云:“论则析理精微。”故以为名。乾宁四年(897)书成……按《唐纪》相璨在天祐改元,则书成犹未仕也。③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页。
南宋《中兴馆阁书目》明确记载《史通析微》共四十九篇,又说它“随篇评论”刘氏的失误。综合这两点来看,柳璨所见的《史通》同样应该是四十九篇的。它还具体记载了一个细节:“又第十篇摭知幾四朝实录之失。”这一点也值得注意。所谓四朝实录,包括《高宗后修实录》三十卷、《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睿宗实录》十卷,都是刘知幾、吴兢主持修成的。柳氏之书专门批评刘知幾之失,照理很多篇中都会批评四朝实录的缺失,这里何以专说其第十篇?原来《史通》第十篇为《序例》,专门论述史书的凡例,反映了刘氏在史书编撰体例上的一些根本主张。如“窃唯录皇后者既为传体,自不可加以纪名。”柳璨其他“随篇评论”,可能也会指出四朝实录一些零星的具体失误,不足深病。而第十篇针对的则是四朝实录体例之大端,很可能主要是涉及武后的评价。这是唐代史学家经常争议的一个重大问题,如唐德宗时沈既济“以吴兢撰《国史》,以则天事立本纪,奏议非之”,大意以为应该省《天后纪》并入《中宗纪》,则天退位后当称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宜称皇帝,不宜曰庐陵王;睿宗继位前宜曰相王,不宜曰帝④刘昫:《旧唐书》,第4669、4034页。。柳璨批评四朝国史,不外乎此,乃据《序例》篇皇后“不可加以纪名”之说,用刘氏之矛攻刘氏之盾。这一具体事例,更加确切地证明了《史通析微》和《史通》是一篇一篇对应的,不仅篇数相同,而且篇序也一样。明确了这一点之后,《史通》“亡篇”说就更加站不住脚了。因为如果说宋初还有包括“亡篇”的《史通》流传,仁宗朝史臣偶未见及,甚至根本不知道有“亡篇”一事,后来重现于世并有刻本,尚不无可能的话,那么唐末柳璨作为第一个著书批驳刘氏的学者,竟然没有见过《史通》完本,中经五代长期战乱而重现于世的可能就更加微乎其微了。
晁公武对《史通析微》的介绍更加详细,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在于其著录的篇数是五十篇。这表面上与四十九篇说矛盾,但其实很好解释:柳氏之书应该也有叙录,晁氏将其与正文一同计算,而多出了一篇。古书中这样的现象十分常见,不足为奇。但这提示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柳氏之书“随篇评论”,其编撰结构并无深意,然而刘知幾《史通》分为内外篇,正文四十九篇加上叙录共成五十篇,难道也纯属偶然,没有深层次的原因吗?由此我们又联想起刘勰《文心雕龙》的编撰结构。
傅振伦先生曾经讨论《史通》与《文心雕龙》之间的关系,颇多发明。其大意以为,一方面从思想上说,“《史通》一书,即就《文心·史传》篇意推广而成”;另一方面从编撰结构上说,“其书亦全模拟之”。①傅振伦:《刘知幾年谱》,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1页。关于后一点的论证,他只是比较二书部分篇名近似,既不尽妥当,也很不全面。后来有些学者做过补充论述,仍然未尽准确。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对其编撰结构作过明确说明,末云:“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②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6页。。即特意在正文四十九篇之外,加写《序志》篇,以凑成“大易之数”五十篇。今人一般据此将其正文分为三大部分:《原道》至《辨骚》五篇为“文之枢纽”,是全书的序论及理论核心;《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为“论文叙笔”,是文体论;《神思》至《程器》二十四篇为“割情析采”,是文学创作论、批评论。拿《史通·内篇》来做简单比较,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前两篇《六家》《二体》综论上古至唐初各种史书体裁,以引出下面对纪传体史书的具体讨论,与《文心雕龙》前五篇地位相当。《载言》至《序例》八篇分别讨论纪传体内各部分的体例,相当于《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题目》至《辨职》二十五篇讨论史书编撰方法和评论的各种问题,可以与《文心雕龙》文学创作论、批评论相媲美。书前的《叙录》,显然与《文心雕龙·序志》相对应。然而,由于纪传体内的组成部分比中古文体的数量少得多等原因,刘知幾无法像刘勰那样写出体系严整的四十九篇正文,而只有三十六篇。这对于一个如此刻意“模拟”的作者来说,当然是一大憾事。于是刘知幾把这三十六篇编成内篇,而把写作过程中和内篇完成后特意加写的读书札记十三篇合编成外篇。再加上叙录,全书就达到“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与刘勰《文心雕龙》更加形合神似了。
综上所述,史传记载《史通》四十九篇并非孤证,唐末柳璨所见本已然如此。在承认四十九篇说的前提下,刘知幾模拟刘勰而采取这一编撰结构的心态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所谓“亡篇”说的各种疑惑也可以涣然冰释了。夫复何疑,岂不快哉!
A Discussion on the Viewpoint of Lost Articles in Shitong
ZHANGGu-ye1,XUWei-lian2
(1.Institute of Historical Philology,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9,China;2.Buji Middle School,Shenzhen Guangdong 518172,China)
That there are lost articles in Shitong does not match historical records,and there are many contradictory views in this argument.These titles are so rich in content and wide in relationship that there are many related discourses in many other articles in this book,and there is no need to write other articles.Liu Can's criticism of Shitong articles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involved forty-nine articles,which have to be identical in number with those in Shitong.In effect,Liu Zhiji wrote forty-nine articles in Shitong,no more and no less.He intentionally imitated Wenxindiaolong by Liu Xie who once wrote that"There are forty-nine articles in the book." Therefore,the so-called lost articles in Shitong donot exist.
Liu Zhiji;Shitong;lost articles;Liu Xie;Wenxindiaolong
K092
A
1674-3210(2017)02-0058-07
2017-03-18
张固也(1964—),男,浙江淳安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先秦、唐代文献及古典目录学;徐伟连(1988—),女,江西鄱阳人,硕士,深圳市布吉中学教师,主要研究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