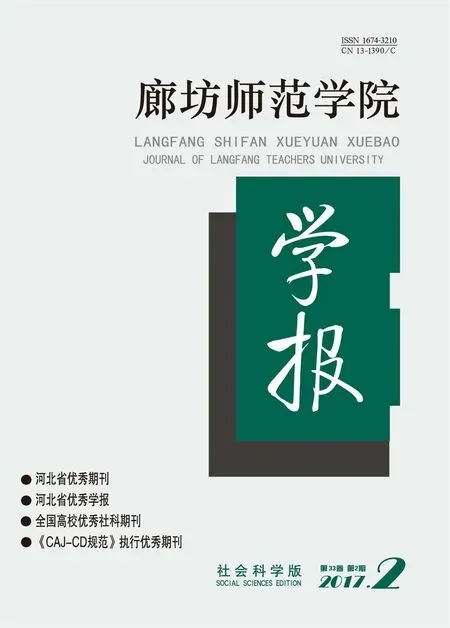论白桦“十七年”时期的云南边地书写
梁玉洁,吕东亮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论白桦“十七年”时期的云南边地书写
梁玉洁,吕东亮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十七年”时期,白桦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以云南边地生活为背景的诗歌和小说。他以现代性的隐喻手法、民族视角的叙事策略书写边地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重新审视云南边地的风貌,呈现了“中心—边地”“自我—他者”的关系。
“十七年”;云南边地书写;意识形态抒情;现代性隐喻;民族视角
在“十七年”时期的诗歌创作中,长篇叙事诗成绩斐然。文坛出现了一批被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称之为“西南边疆诗群”的诗人群体,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有公刘、白桦、顾工、高平、傅仇、周良沛等。白桦在“十七年”时期的创作,获得了诗界较高的评价。他1947年参加革命,1949年随军进入云南,从此开始了其文学生涯中边地书写的篇章:1952年完成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1953年发表短篇小说集《边疆的声音》、1955年发表抒情诗集《金沙江的怀念》、1956发表诗集《鹰群》、1957年发表长篇叙事诗《孔雀》和诗集《热芭人的歌》等等。此外,他还尝试散文、话剧、电影剧本等多种题材的写作。在此期间,白桦创作发表颇多,是个高产高效的青年作家。本文仅就白桦的诗和小说来论述其“十七年”时期的云南边地书写。
一、意识形态的抒情诗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折,使得一批知识青年踏入诗的疆域,青年诗人的涌现是当时的奇观。1954年公刘的《边地短歌》、1955年和1956年白桦的《金沙江的怀念》《鹰群》相继发表并产生良好反响,这些作者当时大多在军队服役。在他们看来,“走向诗和走向革命,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面。相对而言,随着西进的军队到了川西、云贵和康藏一带的作者,他们的创作有超乎当时一般水准的表现”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1-62页。。
“战乱基本结束之后的相对和平的环境,革命改造和经济建设的展开,增进了开放和沟通,人的视野为之一宽。他们于是有相当从容的心情,领略大自然实在的面目。”②谢冕:《置身于当代格局中——晓雪小议》,《文艺报》1988年第4期。白桦带着新奇的眼光开始了对云南边地风景的发现和书写,绮丽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营造着美妙和奇异,在这样一个诗歌王国里,他喷发着自己的诗情:“一朵金色的云,落在银色的雪山顶,素馨兰在凤尾竹下眨小眼,英格花在虎尾松上笑吟吟,——是雪山上开始融雪的春天啊!……”③白桦:《金沙江的怀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1、2、2页。。诗人无法按捺的激动之情,除了美好的景物外,更多的是对伟大将军的怀念,对伟大的党和领袖的赞颂。“将军的刀尝过敌人的血腥……将军的手臂指挥着红色战士前进。”④白桦:《金沙江的怀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1、2、2页。同时,将军也是亲切和善的,“将军的手抚摸过摩西孩子的毛头,将军的胡子亲过藏族娃娃的嘴唇,将军的笑声在雪山上回荡”⑤白桦:《金沙江的怀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1、2、2页。。刚强的将军变成了温和的父亲的形象,这一形象的塑造,也暗含着这样的意义:毛主席和共产党像一个父亲,给予了少数民族新的生命和新的生活,边地人民第一次从将军的口中知道了毛泽东,年轻的红军传递着勇敢坚毅的精神,他们深受感染,愿做红军的儿子,愿走红军的路。这样慷慨激昂的歌唱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白桦的这首诗中,可见文学包含的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通过对将军和红军的形象塑造,于无形中唱赞歌,感染人民尤其是远离中心文化的云南边地的人民,使他们自愿自主地拥护党。这就是当时西南边疆诗人“中心—边地”情感模式的体现,以伟大领袖为代表,以红军为坚强后盾,使各族人民自觉自愿地靠近中心话语,从而凝聚起更强的民族力量。
自古以来,云南就是远离内地的边疆地区,长期处于“边缘”状态,或多或少地疏离于主流文化。建国以后,党和政府致力于重建民族共同体,强化边地各少数民族对共和国的认同和忠诚。从文学方面来看,“十七年”时期诗歌的边地书写,就自然成为了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表意工具。白桦的诗歌通过叙写边地的“苦难与解放”和“党引导下的新人成长”,建构起了边疆与内地共享的革命历史记忆,加强了边地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鹰群》和《热芭人的歌》都表达了这样的主题:边地少数民族的贫苦大众遭受着阶级压迫和剥削,要想获得自尊自由和幸福生活,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抗剥削阶级,推翻反动统治。热芭,是藏族中一小部分靠歌舞为生的人,生活极其艰辛,解放前到处流浪,靠乞讨度日,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在党的解救下,他们获得了“比天堂更美好的”生活。《鹰群》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以培楚为首的藏民们从被奴役的境遇中逐步觉醒,在艰苦的斗争中,少年培楚被锻炼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并组织藏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长诗揭示了通向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各民族间的战斗情谊。这种叙事模式或隐或显地指向“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时代特色和主题,通过对旧的坏的过去的控诉,突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活的来之不易,各民族人民必须要捍卫新型的国家民族共同体。“苦难和解放”主题之后,白桦还有一个关于少数民族新人成长的主题。长诗《鹰群》就塑造了一批英勇的藏族青年,描绘了一幅瑰丽多彩的历史画面。从孩童成长起来的战士培楚,经过多次战斗的洗礼,最后光荣地出席了中南海的功臣宴;在全国胜利前夕不幸牺牲的青年顶珠,成了人们心中永远不朽的战士。在《热芭人的歌》中,男主人公悦喜受到启蒙,知道了毛泽东,自我意识被唤醒,参加红色游击队,成长为一名心中永远有红星的战士;新政权解放了少数民族被奴役的命运,女主人公朗玛成为一名受人喜爱的“民间艺术家”,以悦喜和朗玛为代表的热芭人最终获得了生活的自由和为人的尊严。白桦1954年的抒情短诗《送别》,则有别于其他作品中主人公的战斗成长方式,讲述的是金沙江畔的少年跨马走向繁华的城市,去读毛泽东的书,充实自己,从知识方面获得成长和进步,同时也肩负着教育家乡人民的重大责任的故事。从白桦此时期的诗作,可以感受到诗人正以前所未有的荣耀感和集体感,激情澎湃地展示和描绘边地新貌和新生活的蓝图。
二、《孔雀》的现代性隐喻
纵观“十七年”的文坛作品,明显可见抒“政治”之情是时代的规定内容。诗歌这一极具号角性的文学形式,就更不能远离时代的潮流和时尚了,诗人们深受时代情思的影响,带着青年人特有的希望与朝气,抒发着一曲曲建设祖国、团结民族的颂歌。然而,在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的边地,白桦除了抒发爱国团结的政治情绪之外,还有对边地爱情的吟唱。
20世纪50年代前期,对少数民族民间抒情诗和叙事诗的搜集、整理,成为一个小的热潮。其中,在少数民族民间诗歌基础上创作的叙事诗,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这包括徐嘉瑞、公刘、徐迟、鲁凝分别创作的同名长诗《望夫云》,白桦的《孔雀》,韦其麟的《百鸟衣》。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58页。对少数民族诗歌的整理和再创作,也体现了中原文化对边地文化的重视和吸纳,使远离腹地的文化,可以被纳入新的时代范式,为大众所熟悉和接受,也更有利于民族认同和团结。
白桦的《孔雀》取材于傣族最有影响的传说——召·树吞和喃·穆鲁娜的故事。《孔雀》的故事框架和许多爱情故事的模式如出一辙:两个渴望爱情的年轻人一见钟情,新婚燕尔忍痛离别,公主遭难飞回母国,王子凯旋、历经磨难、千里寻妻,最终和公主迎来了美满的结局。王子寻找公主的故事原型来自于中外皆有的“寻宝”传说,一个年轻人历尽艰难险阻,最终找到了真爱和幸福。但在新的时代,白桦以自己对这个民族传说的认知和探寻赋予这个古老的爱情故事以丰富的现代意义。白桦曾说:“写诗的时候,我没有局限于译本和一些传说的故事内容和思想内容,在结构和形式上汲取了傣族文学和‘赞哈’(民间歌手)的一些特点。我做了许多努力,希望它能传达出傣族人民美丽的心灵和我对傣族人民的敬爱!”①白桦:《白话文集》(卷3),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227页。这首抒情长诗散发出白桦浓郁的浪漫色彩和理想精神,流露出他对云南风土人情的热爱和对坚贞、纯洁、专一的爱情的赞美。
今天看来,《孔雀》的现代性隐喻更值得细细寻味。《孔雀》所书写的王子召·树吞寻找公主的艰辛之路,其中隐含着一个“新人”的成长之路。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王子自觉的自尊意识。凯旋的召·树吞在得知妻子悲惨的遭遇后厉声叱责父亲弑杀儿媳的行为,这使得勐板扎王失去了“人的尊严”,因为王子作为年轻一代的新人,已经具有了自我、自尊的意识。但是仅他觉醒还不够,作为一国之君的父亲没有了尊严,那么整个勐板扎国也就没有了尊严,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耻辱,所以王子要千里寻妻。而王子的千里寻妻之路其实也就是寻求尊严之路。这也正表明,新中国政权对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应该是双方面的,不仅要使其身体上摆脱压迫、剥削,而且精神上也要唤醒其为人的尊严,使其成为真正的新人。其次,王子不顾一切地踏上异国寻妻之路,这是新的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引导和改变,是将他引向一个更具有自我主体性的状态。在路途中,王子披荆斩棘、翻山越岭、射杀怪象、勇斗巨蟒、横过火焰河,最终到达了公主的母国,在历经勐奥东板国王的刁难后,顺利和公主团聚了。过程很曲折,但结局很美满。正值社会主义国家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时期,这首诗无疑是激励青年们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要为建设祖国做出贡献。这或许就是《孔雀》潜在的意识形态效果。
《孔雀》除了王子的身份隐喻外,其他人物形象的意义涵蕴也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喃·穆鲁娜公主,作为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勇敢地与王子陷入爱河,追随他左右,她是个纯洁的未受世俗浸染的少女。王子出征期间,她与人民共同劳作,为建设国家无私地奔走,却被恶人诽谤,含恨飞回母国时,依旧对这片土地和人民充满不舍和眷恋。她就是爱与美的化身,她的出现就是考验人性,善的人看到她会更善,恶的人看到她会嫉妒而变得更恶。从某种意义上说,公主隐喻着在新中国建设中无私奉献的可爱的人们,他们是建设国家的重要力量,也是新中国的希望。巫师作为恶势力的代表,他们生活在黑暗中,时刻想要吞噬光明,也正隐喻着那些企图分化国家势力、阻碍民族团结、破坏国家建设的反动势力,他们在边疆地区骚动,伺机摧毁各族人民努力建立起来的团结阵营,但他们最终是一定会失败的。
这首长诗还有一些不可忽略的隐含义。“神圣的土地,这里是美丽国家的边境!”②白桦:《白话文集》(卷3),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227页。勐奥东板的土地安谧美丽,人民能歌善舞,单纯善良,正像云南边地。由于远离中原文化的影响,没有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束缚,这里的人们自由奔放、热情善良,所以能有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色彩的爱情传说。王子和公主的美满结局实质上也有隐含义的存在。王子远离母国,千里寻妻,公主作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是不能割舍和抛弃的,正如云南虽是中国的边疆之地,但仍旧是祖国需要大力建设和保护的一部分。王子和公主最终幸福地结合,也暗示着“中心”与“边地”和谐共生的关系。这也说明,新中国要建立的是一个平等友爱的大家庭,各民族都是平等共存的,新的政权非但不会忽略边地,反而会更支持边疆的发展。
三、民族视角叙事策略的边地小说
除诗之外,“十七年”时期的白桦,在小说创作方面也是产量颇丰的。1952年创作完成,1953年发表的《山间铃响马帮来》,1954年被改编成电影,2011年被改编成电视剧,可以说这部小说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他创作的还有《竹哨》《边疆的声音》《无铃的马帮》等小说。白桦此时期的小说创作,自觉地采用了民族视角的叙事方式,重新诠释了“自我—他者”“中心—边地”的关系。
《山间铃响马帮来》讲述的是解放初期边地人民和政府联合对抗反动势力的故事。云南边地的反动势力企图抢劫政府马帮低价运给人民的生活用品,在与敌对势力斗争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人民和解放军团结一心,取得了胜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1954年,白桦又创作了同类题材的《无铃的马帮》,这是一部描写滇南边防反特擒匪斗争的中篇小说,一队从边境森林走来的奇怪的马帮(头马没有挂铃,驮着奇怪的货物,走的还是一条隐蔽危险的山路),引起了边防部队的怀疑,于是侦查员乔装跟踪,一路上与敌人周旋,同敌人进行着心理较量战,最终一举擒获特务。这两部小说叙述的框架极其相似,可以简单归结为边防军——特务双方周旋斗争的故事,马帮就是一个特殊的场域。但是,因为白桦采用了民族叙事的视角,这两部小说反映的就不只是简单的敌我斗争,而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马帮系列’小说,采用了民族视角的叙事方式,以边地少数民族的感知或认知来叙述故事,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特殊时代的边地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情感世界。”①王瑛:《写气图貌,于心徘徊——评白桦的〈山间铃响马帮来〉》,《名作欣赏》2014年第8期。小说着重表现了边地少数民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边地人民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他们不由地歌唱:“毛主席的太阳照亮了边界地啊!解放军带来了丰收的好年成哟!”②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站起来的声音1949—195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9、68、46页。“边界地人心跟着谁?跟着救星毛主席,永远前进不后退……山崩地裂永不悔。”③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站起来的声音1949—195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9、68、46页。瑶族姑娘、小孩儿们口中传唱着颂歌,是以少数民族“自我”的视角直接抒情,这要比白桦的作者视角或者说中心视角表达的感情更加真实诚挚。身处冷战时期的特殊背景,社会主义国家划分“自我”和“他者”的主要依据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话语。④王家平:《论“十七年”文学的云南边地书写》,《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5期。云南边地文学作品中的“他者”并不是与少数民族“自我”相对立的外来民族,它不是表面的以族别来划分,而是以拥护、支持党和政府为依据,带有政治色彩的评判。所以,云南边地的“他者”主要表现为“特务”和毁坏民族团结的敌对势力。由此可见,这种“自我”和“他者”的划分,已经因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自我”的阵营加入了更多维护和平团结的少数民族成员。这一切都有利于强化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白桦“十七年”时期的云南书写,在身份上,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同时也从三方面,体现着意识形态的“中心”与“边地”的关系。
首先,边地美与危险并存。《山间铃响马帮来》中有一段关于苗寨秋景的描写:“秋熟的香气弥漫了边地的山林。森林里的孔雀、翠鸟、野鸡和黄莺再也耐不住了,他们成群结队地落到森林边沿的大树上,飞舞着、吵嚷着……坡田上像闹市,歌声不断地回荡着。”⑤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站起来的声音1949—195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49、68、46页。这片丰收的景象,是边疆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艺术展现。虽然丰收的画面很美好、人民很欣喜,但处在国界边上时刻充满着危险,边地人民不仅要时刻防范外来者的威胁,还要面对基本物质生活难以维继的窘况。他们虽有政府的护卫和救济,但仍处于远离“中心”的危险境地。换句话说,人们一边感受着收获的喜悦,一边还要警惕地放哨站岗,保卫来之不易的安宁。其次,边地年轻人的爱情有别于传统爱情。正因为远离中原文化区,所以边地才能孕育出热情大胆的生命,才会有红花和大黑纯粹直白的感情。有别于传统爱情写作中男女扭捏不自然的情状,他们思想简单,少受中原文化区儒家思想的禁锢,没有那么多伦理纲常的束缚,是出于真性情的恋爱,这也是作者想表达的边地年轻人的情感状态。他们有着共同的斗争目标,一心为公,守卫边地人民得来不易的安宁,这种革命感情往往是最长久坚固的、经得起考验的。再次,来自“中心”的战士,勇敢地保卫“边地”。《边疆的声音》和《竹哨》讲述的是进入云南边地的汉族青年,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勇于战斗、无私奉献和不畏牺牲的故事。《边疆的声音》以边地两个接线员抢修电话线的故事展开情节,赞美了他们为保卫边地与前线和上级顺利连线而不顾个人性命、在极其严寒和危险的环境中一心为党为民的大无畏精神,这种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表现出整个解放军队伍无私的爱和党对边地人民的保护与爱护。《竹哨》叙述了年轻的战斗班长小李,在身负枪伤的情况下,凭着不怕磨难、坚强勇敢的执着信念,历经三天三夜终于爬出竹林获救的故事。他们都是最高尚、最可爱的人,他们和边地人民虽是不同族别,但都同属于一个国家,他们来到边地,为保护少数民族群众,致力于祖国建设,不辱使命,不怕牺牲,奉献自己。而边地人民的热情善良也深深地感染着他们,彼此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结语
白桦“十七年”时期的作品,不管是诗歌还是小说,都向我们呈现了一种新的云南形象:边地云南与祖国的“中心”地区紧密连接在一起,它不再意味着云南是处于文明之外、家国之外的“边地”或“他者”,云南与作者成长的中原地区同属于政治——地理上的中国。白桦的云南书写和当时的种种文化表述一样,以“家”的名义,将云南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这意味着,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少数民族和其他人群一样作为“国民”的一份子而存在着。①王家平:《论“十七年”文学的云南边地书写》,《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5期。
On the Writing of Bai Hua on Yunnan Frontier During the"17 Years"Period
LIANGYu-jie,LVDong-l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Xinyang Teachers College,Xingyang Henan 464000,China)
Duringthe"17 years"period,Bai Hua created a group ofexcellent poetry and novels with the background ofYunnan frontier life.He took the modern metaphor technique and the narrative strategyofthe national angle ofviewand wrote about the life condition,the thoughts and feelings ofthe people on the frontier.His reviewon the features ofthe Yunnan frontier presen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center-frontier"and"ego-person".
"17 years";The writingofthe Yunnan frontier;the lyric ofideology;modern metaphor;national perspective
I206
A
1674-3210(2017)02-0037-05
2017-02-21
梁玉洁(1991—),女,河南信阳人,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吕东亮(1980—),男,河南新郑人,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