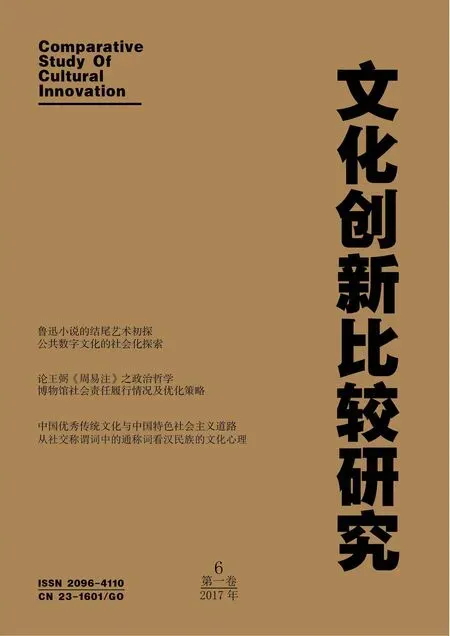立德成物 天人合一
——儒家人文主义视野下的“诚信”价值观
张南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北京 100872)
立德成物 天人合一
——儒家人文主义视野下的“诚信”价值观
张南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北京 100872)
“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体现了核心价值观传统与现代的统一。“诚信”是儒家的核心价值理念,“诚信”的本义包括真实不欺、信守承诺等含义。在儒家人文主义的视野下,诚信首先要求树立道德主体,培养道德自觉,这是价值的源泉所在。由此向外推广,诚信是处理朋友关系、进行一般性社会交往和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也是人与自然和生共处的核心原则。此外“诚信”既是内在于人的道德品质,又具有外在超越意义,因而具有道德宗教性,能够通过体证和修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最终实现人性的圆满完成。
诚信;儒家人文主义;身心;社会;自然;宗教
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刻的民族性和鲜明的时代性,它是每一个民族、国家凝聚纽带的灵魂所在及其在每个时代创造性地展现出的价值标准、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曾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对中华传统美德的赓续,表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深刻扎根于中国传统价值哲学尤其是儒家学说的时代开新[1]。从另一方面来看,将诚信作为核心价值和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也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诚信价值的缺失以及社会诚信体系不完善的现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今天缺乏对“诚信”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仅仅将诚信理解为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等,更多强调了诚信在社会人际交往层面的相互关系及功用价值,然而对于价值实践主体之内在价值这一维度似有未尽之处。实际上,作为儒家道德哲学中重要范畴的“诚信”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尤其是儒家人文主义对于道德内在价值的强调,能为我们提供更加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思考维度,有助于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与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
1 度越世俗化:儒家人文主义
陈荣捷教授曾指出:“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人文主义[2]。”实际上,将作为中国哲学主干的儒家精神传统定位为“人文主义”几乎已经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然而,用“人文主义”(Humanism)来总结儒家精神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一个即是作为舶来品的“人文主义”(Humanism)是否能够与土生土长的儒家思想完全对接。如若不能,就应该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我们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认为儒家传统乃是“人文主义”?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有何特点?
一般认为,19世纪以来西方语境下的“人文主义”指发端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以人类自身的经验为中心来看待一切的哲学世界观。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曾就“人文主义”(Humanism)在西方的演变做了详细地考察,他指出作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产物的Humanism是以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为基调的世界观[3]。之所以强调以人为中心,正表明了人文主义针对的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前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即以超越自然的眼光看待世界,聚焦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14~19世纪这种剥离神学外衣、彰显人类自身而走向世俗化的人文主义思潮被称为“世俗的人文主义”。结合保罗·库尔茨教授的相关研究[4],我们可将“世俗人文主义”归纳为以下特征:(1)强调运用理性思维、怀疑精神及科学技术方法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和建立社会秩序的工具基础;(2)主张将自律与道德作为伦理和社会规范的根基;(3)相信宇宙是人类理性可以认知的(自然科学),坚持人类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4)质疑超自然的、神秘的和超越性的存在,否定有神论;(5)相信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从宗教迷信经过形而上学而进入科学理性,后一阶段的发展否定前一阶段。虽然20世纪的人文主义有过局部的反思和多元化的发展,但是其核心精神依旧是主张消解神学宗教的神圣性,凸显人的中心位置。同时伴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世俗人文主义的无神论、世俗化程度不断加深。因此,从总体看西方“世俗人文主义”的发展,虽然在不同阶段会不断产生新特点,但根本核心特征——将理性人作为评价一切的价值标准且不承认人类经验之外的超越存在及真实性——却几乎没有改变过[5]。
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正面肯定了人类的价值,赋予了个人尊严,奠定了西方后世民主、自由、理智、人权和法治等核心价值理念,促进了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思想资源。然而,21世纪以来的西方频频爆发各种危机,如宗教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等等。杜维明教授敏锐地指出这种危机局面都与启蒙运动以来的世俗人文主义的视角盲点有密切关系,他将这些盲点归结为四点:人类中心主义、科学主义、“经济人”的观念、欧洲中心主义[6]。进一步综合可以归为两个突出的问题:宰制自然和边沿化精神性。超越神圣性的消解和征服自然的思想趋势给今天的人类带来了困境:狭隘的人类中心论对自然的宰制和破坏;狭隘的种族主义、宗教派别主义、恐怖主义将人类分裂为敌对的族群等等。当代的这些种种困境,都要求我们度越世俗的人文主义,反思启蒙心态,为人类发展探索新的的价值资源。
儒家传统作为“轴心时代”的精神资源之一,从古至今经历了一个由洙泗的地方知识不断向外辐射为中原文化、东亚文明圈的发展过程,时空的赓续绵延展现了儒家传统的思想丰富性与可诠释性,表明了儒家传统可以现代转化和转化现代的可能性。“仁者,人也”,人一直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的核心焦点。世俗人文主义认为人是一个“理性经济人”,是一个在法律制度范围内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存在,忽略了同情、责任等价值。而儒家将人视为一个综合性的关系性存在,有着情感、社会、政治、历史和终极关怀等多种面向;同时人又是一个发展和成长的过程性存在,通过终生学习与修身达至自我的圆成。此外,在儒家看来,人和万物都是天地化育的产物,一方面,人得五行之秀乃天地最灵,具有特殊的地位,故《礼记·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但另一方面,人与万物同为天道所化,具有根本的平等性。综合这两方面,人作为天地最灵之存在就有义务承担起参赞天地化育、关怀万物的责任,这凸显了个人内在德性修养的重要意义。所以,儒家经典《大学》从心、身、家、国和天下的秩序指点了儒家修身所具有的深刻内涵,表明自我身心的修养关涉着他者、自然、社会与精神信仰,主体个人的德性是外在普遍道德原则的根底。
可见,儒家人文主义是一种度越了世俗化的人文主义,其关注核心虽然依旧是“人”,但在儒家看来人是一个不断圆成的发展过程,而非符号化的静态实存。人同时关系着他者、自然与天道,如何做人的问题贯穿社会政治与天道流行,可以说儒家的人文主义体现的是“天人之际”的精神内涵。因此,儒家人文主义首先要求一个人挺立自我道德主体性,努力实现自我得身心和谐统一。此外,作为具有社会性的人,也要将自我修身推至社会交往中,与他者构成良性互动。人与万物的根本平等性则要求人应该与自然存在保持和谐,关爱万物。最后,由自我、社会、自然的贯通而体悟天道生生之德,形成超越情怀,敬畏天道,为此世的活动注入超越的意义。因此,儒家的人文主义所关注的四个维度分别为:(1)个人身心的和谐与道德主体性的挺立;(2)个人社会交往的健康互动;(3)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4)人心与天道的妙契辅成[7]。
2 儒家人文主义下的“诚信”
从儒家人文主义的视角反观“诚信”这一道德观念,我们应从上述四个维度出发对“诚信”的价值意义做更加全面深入地考察。
2.1 诚者自成
《增韵·清韵》云:“诚,无伪也,真也,实也。”此处指出了“诚”或“诚信”的核心内涵是真实。所谓真实,有两个层面:一是真实无妄;二是实有诸己。
真实无妄,是相对价值虚无而言。毋庸置疑,当代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重要危机就是价值的崩塌和虚无主义的盛行,这当然与前述的世俗人文主义有密切关联,所谓上帝已死,价值重估。然而,上帝确实死了,然而需要被重估的价值却长久飘散在虚无的旷野之中。在价值虚无的精神环境下,人们的心理状态不断世俗化,最终为空虚、追逐眼前享乐的心态所充斥。由于价值的虚无,人们习惯于对所有价值观念进行批判、解构和否定,人生不再有值得奉献生命的理由与追求。无疑,我们需要价值的重建。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不乏价值虚无的时代,如宋代佛老盛行,社会弥漫着空、无思潮,伦理秩序日渐崩塌与价值观念的混乱成为当时的社会背景。正如宋代理学家张九成批判佛教价值观所言:“(释氏)认廓然无物者为极致,是故以尧舜禹汤文武之功业为尘垢,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为赘疣,以天地日月春夏秋冬为梦幻,离天人、绝本末、决内外,茕茕无偶……有孤高之绝体,无敷荣之大用[8]。”因此,宋明理学家们建构道德形而上学,重新为社会秩序与价值规范寻找根基。今天的我们,面对价值虚无主义,同样应该重塑时代精神,重寻人类精神家园,重构整个社会的价值与伦理世界,在伦理价值方面为社会和个人立法。另一方面,所谓“真实”,即一种存在的真实性,而非仅仅是理智认知意义的真假。正如钱穆先生指出,此真实是“当知天体乃真实有此天体,群星真实有此群星,太阳真实有此太阳,地球真实有此地球。几此皆真实不妄。……凡此皆各各真实,不虚不妄”[9]。这种存在的真实性,正表明了价值观与人之存在方式之间的密切关联性,即价值在人的存在方式中呈现,人在价值中完成自我。
实有诸己,即“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10]。若要走出虚无主义的幽谷,就必须重新挺立自己的价值主体。明儒王夫之对“诚”与“实”有过经典阐述:“诚也者,实也;实有之,固有之也。无所待而然,无不然者以相杂,尽其所可致,而莫之能御也[11]。”所谓的实有之、固有之,与前文所讲之存在的真实性相关。如我们说水之性是润下,此“润下”既是水之所是(事实性)也是水之所应是(价值),故为水所实有或固有。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水真实地拥有了其本性。对于人而言,“天命之谓性”,人本应当有其本性,然而人因为具有理性思虑,总是放失自己所应是的本性,此时本性与实存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偏离,此非“诚”也。由此,人就需要“思诚”或“明诚”的道德修养工夫,重新复归本性,重新拥有其所应是,故《孟子·离娄上》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礼记·中庸》曰:“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者自成,为仁由己。这种道德的修养无法依靠任何外力或他律,而是需要建立主体的道德自觉,在不同情境中不断修养,日渐臻于至善。
《中庸》曰:“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大学》曰:“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都凸显了主体道德性对于外在行为的基础或根据意义,如果没有将价值观念本身内化于心而实有诸己,何来外化于行?这一维度,正是我们目前关于“诚信”的认识中最薄弱的部分。我们在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过程中,首先应该挺立起价值主体的德性。如此,内在德性如源头活水,能够源源不断地给予开展实践活动之动力,保障道德行为的持续性。
2.2 交游称信
如果说“诚”偏重于人自身的内在德性,那么“信”则更多关涉了社会人际交往或者国家治理的价值规范,我们也可以大致将二者的差异归为道德与伦理的差别。人类社会是人构成的,无人就无所谓社会,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在儒家看来,人的社会性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关系伦理。《说文》曰“伦,辈也”,段注云“同类之次曰辈”,“辈”即有类别和次序二义[12]。引申之,人之类别次序、关系就谓之“伦”,可见古汉语中“伦”常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表明,人是在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候应该遵循的原则和规范。梁漱溟先生曾用“伦理本位”概括中国社会的特点,他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西方社会注重团体和个人,而中国社会却消融个人与团体两个集团,是从家庭关系出发,推而广之,使得“每一个人对于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任务”[13]。对此,费孝通先生也提出了“差序格局”加以阐发,实为精辟之论[14]。
基于中国社会的这一特点,儒家学者特别关注人伦规范的问题。孟子在《滕文公上》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虽然人与禽兽在生理欲望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人之为人而异于禽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具有道德伦理。其中,父子、君臣、夫妇、长幼和朋友五种人伦关系被认为是人类社会中最为基本的几种,简称“五伦” 或“五常”。“信”,即诚实不欺,恪守信用。最初被认为是与朋友交往的一般原则。如《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公冶长》:“朋友信之”。朋友在五伦中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父子是具有血缘关系的,而夫妇是家庭内部的,君臣和长幼又是具有上下对待的。可见,只有朋友一伦是既没有血缘关系且双方地位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基于此,处理朋友关系的伦理规范和原则是可以推广为社会交游之道。所以,“信”从狭义的朋友交往原则逐渐扩展为更具一般性的社会交往原则。《礼记·曲礼上》曰:“交游称其信也。”所谓“交游”,不是针对某一类特殊的人群而言,而是泛指一般的社会交往。《礼记·大学》云:“与国人交,止于信。”国人,指一般的平民百姓。在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就是凭借着“信”这一原则进行交往。可见,“信”又被认为是一个普遍广泛的交往原则。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原则,“信”也被引入政治治理中,成为治理原则和立国根本。如《左传·僖公七年》:“君以礼与信属诸侯”,又《论语·子路》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这里的“情”指实情、实际情况。这是说上层的统治者如果诚恳守信,人民百姓就没有人不说真话,反映实情,为国家治理贡献力量。同样,“信”也是统治者在选用贤能时的重要参考标准,所以《论语·阳货》曰:“信则人任焉能”。
从朋友之间的交往推广到一般性社会交往,再到国家治理原则,“信”这一原则贯穿于父子、君臣、夫妇、朋友、长幼乃至治国理正、邦交等关系领域和事务中,并且作为基本性原则。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诚信的道德价值是人在社会中立身行事的核心根本,也是具有普遍性的人伦关系原则。
2.3 成己成物
当今世界,自然危机是一个严重威胁人类未来发展的大问题。自然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世俗人文主义将自然视为外在于人的、供人类改造利用以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客观存在。如此,自然只是一个提供资源的存在,人类需要做的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利用科技手段,不断认识和改造自然。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自然的只是其有用性。据《庄子·人间世》载,庄子曾面对一棵大树发出“材与不材”的感慨[15]。人们衡量一棵大树的价值是它是否符合我们的有用性,如一棵树长得笔直,对于木匠而言就是有用的,也就是有价值的。然而,庄子面前的这棵大树却是自然长成,既不符合木匠的需要,也无法给世人提供什么实际利益。可是正是它的这种“无用之用”,让庄子看到了自然的美,一种天地无言之大美。在这种美的享受中,主体和天地自然融为一体,与物同春,心灵涤除凡尘,达到至美境界。美学家朱光潜先生也列举过人类面对一棵松树的三种不同态度:实用的、科学的和美感的[16]。由于只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认识自然,我们看到的自然就只是一个实用的自然,即便对自然有科学性的研究,但这种研究也往往是功利性的。我们的眼里,从来看不到美的自然。如此,我们更奢谈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呢?
儒家主张连续的有机整体宇宙观,即儒家将天地万物都作为一个有机整体[17]。在这样的宇宙观中,人和天地万物都是天道化育的产物,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并非毫无关系的原子式的个体存在,宇宙整体也不是一个各种元素的集合体[18]。儒家看来,人与天地万物是有机联系的,以天道贯穿所有存在,正如宋儒张载所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在有机整体宇宙观中,人与天地万物如何和谐共生共处?儒家认为,“诚”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核心原则。我们从《中庸》的一段话谈起:“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前提是两者能够处于平等的价值地位,而不是主人与奴仆、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西方“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无法否认一种以自我价值衡量外物的强烈倾向。若此,自然万物便是经过人的价值衡量切割后的自然,自然万物本身却并不在场。如何才能够让万物呈现自我,与人类处于平等的位置?这就需要“诚”。前文已述,诚即真实,即是其所应是。天地和合化育万物,万物禀赋各自的规定性(即“性”),天然是其所是。然而人因为有理性思虑,往往会放失良心,失其本性,进而执着于自我。在与自然万物接触的过程中,本应该如镜子照察万物,自然流行,不滞于我与物。王阳明说“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19]。”正是由于自我的执着,人以自己的价值私欲对万物妄加分别;由于私利小智的干扰,人往往不能一视同仁,而指向特定的满足对象。如此,万物在人的价值分别中不断僵化、片面化,万物的本来面目便障蔽了。
因此,要想改变上述的局面,首先就要使得自己“诚”,即通过道德修养排除自己虚妄的价值态度,让自己回归本性,让心灵恢复澄清,此即“尽性”。只有做到人类自己的“诚”或“尽性”,才能够“尽物之性”,即让物自身呈现其本性、彰显自身价值。故《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人和自然在此时处于平等的价值地位,就能够顺从天道运行,实现人与自然“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局面。
2.4 天人合一
与世俗人文主义强烈的反神圣精神不同,儒家人文主义并不否认或忽略超越力量,而是主张天人可以合一。天人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主题,天人合一是指人道与天道、自然与人文的相同、相类和统一。《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表明,在儒家看来,人与天是相通的。天道运行,化生人与万物,赋予了人以生理生命与道德生命。孟子认为,人性当中天然向善的资质就是天赋的,通过认识自己内在的善性,就能够认识天道。因此,人之善性既是内在于人的,又因其来源于天而具有超越性,这正是儒家人文主义宗教性的维度。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们认为天道具有超越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人文主义承认存在一个人格意义的神或天,与西方传统宗教信仰外在超越的人格神不同,儒家的人文主义是内在而超越。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儒家思想具有宗教性,但儒家更接近哲学而非宗教。
《中庸》曰:“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自然天道化生万物,从不偏私;变化四时,周行不殆,这就是天道的“诚”。“天地之大德曰生”,“诚”代表了生生的创造性,没有自然天道之诚,就没有天地万物,更没有人类社会,因而是最高的最宝贵真实和守信。儒家思想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天道具有的“诚”的高贵品德,是世人应该效法的德性。这种效法并不是机械地模拟自然规律,而是具有人文色彩的宗教性。我们可以借助康德关于宗教的观点,来对儒家思想中的超越性和宗教性作进一步地说明。康德将宗教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对外在神力地祈祷和屈服来得到幸福或人格完善;另一类是凭自己的道德意志,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一个更好的人,无须借助任何外在的力量。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看到,对自己道德意志的坚信和为此付出的德性修养和道德实践本身就体现出了某种宗教意味,但却具有强烈的人文性、道德性和伦理性。同样地,儒家坚信具有“诚”之品格的天道内在于人,我们应该时时自觉地“诚之”或“思诚”,这是一个反求诸己的过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体证内在的德性,以确立道德本体,追求人性的完成和价值的实现,达到一种崇高的理想道德境界。此时的“诚”就兼具了超越本体和工夫论两个层面的意义。
3 结语
综上所论,“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体现了核心价值观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从本义上来讲,“诚信”作为一个道德伦理范畴,包括真实不欺骗、信守承诺等含义。我们对“诚信”的这种理解易于将其化约为处理社会人际交往的原则,从而忽略其丰富的价值内涵。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规范,我们应挖充分掘“诚信”的传统资源,在此基础上立足现实,推陈出新。“诚信”是儒家的核心价值理念,将其置身于儒家人文主义的背景中考察,能够获取更为立体的“诚信观”。在儒家人文主义的视野下,诚信首先要求树立道德主体,培养道德自觉,这是价值的源泉所在。由此向外推广,诚信是处理朋友关系、进行一般性社会交往和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不诚无物”,“诚信”也是人与自然和生共处的核心原则。“诚信”既是内在于人的道德品质,又具有外在超越意义,因而具有道德宗教性,能够通过体证和修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最终实现人性的圆满完成。从身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人心与天道四个维度展开“诚信”的深厚内涵,有助于唤醒人之内在的善性良知,由此逐渐在社会实践中挺立起“诚信”价值原则,进而完善社会诚信体系。
[1]王易,白洁.试论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与创新性发展[J].思想理论教育,2014(5):14-17.
[2][美]陈荣捷,杨儒宾,等.中国哲学文献选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
[3][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4][美]保罗·库尔茨.世俗人文主义概述(一)(二)[J].任事平,译.科学与无神论,2008(2):46-50.
[5]彭国翔.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
[6]曾明珠.启蒙的反思(节选)——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J].世界哲学,2005(4):16-23.
[7]杜维明.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杜维明卷[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2.
[8]张九成,杨新勋:张九成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57.
[9]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43.
[10]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591.
[11]王夫之.船山全书:尚书引义尚书稗疏[M].长沙:岳麓书社,1988:353.
[12]潘光旦,潘乃谷.潘光旦选集(第一册)[M].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352.
[13]梁漱溟,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三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81-82.
[14]费孝通.乡土中国[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25-32.
[15]郭庆藩,王孝鱼.庄子集释(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4:181-182.
[16]朱光潜.谈美[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18-22.
[17]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M].王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3.
[18]杜维明,刘诺亚译.存有的连续性:中国人的自然观[J].世界哲学,2004(1):86-91.
[19]王守仁,邓艾民.传习录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13.
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17)02(c)-0012-06
张南(1990-),男,云南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2016级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宋明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