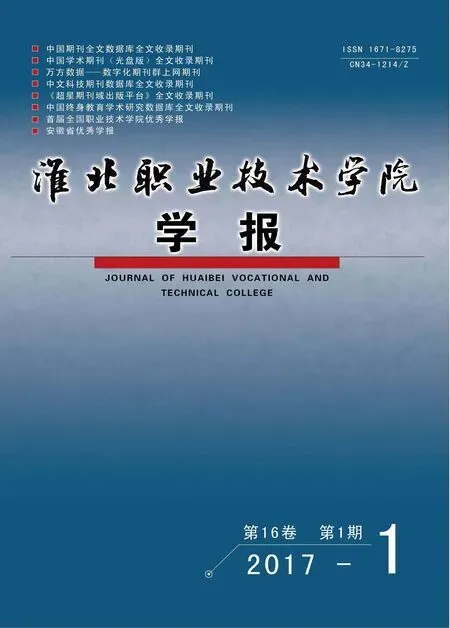《徐渭集》校勘札记
靳亚萍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徐渭集》校勘札记
靳亚萍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华书局点校本《徐渭集》(1983年版)是目前的通行版本,被誉有“搜罗完备”之称,颇有助于学者的研究,但其中也有不少问题。今仅就校勘方面略陈管见,就教于方家。
《徐渭集》;校勘;札记
中华书局点校本《徐渭集》[1](1983年版)收录了《徐文长三集》《徐文长逸稿》《徐文长佚草》,又据《盛明百家诗》《一枝堂稿》和书画题记等辑补了前三本书中所未收录的作品。另外,还将明刊本《徐文长三集》中仅有存目的《四声猿》全文刊出,被认为“虽不以全集为名,已有全集之实”[2],颇有助于学者的研究。但其中也存在不足,此前徐朔方和张淼在其论文中已进行的部分校勘,本文不再列述。
现以中华书局《徐渭集》(下简称“中华本”)为底本,以原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万历二十八年商维浚刻《徐文长三集》[3]影印本(以下简称“国图本”)、原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万历四十二年(1614)钟人杰刻《徐文长文集》[4]影印本(以下简称“钟本”)、传世藏书《徐渭集》[5](下简称“传世本”)为参校本。部分参校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万历二十八年商维浚刻《徐文长三集》[6]影印本(以下简称“台本”),现仅就《徐文长三集》部分,写成校读札记二十六条。
1.《梅赋》:“往予薄游海外,闻罗浮之胜而未得登焉,盖昔所称八梦之种,不可得而见之矣。”(卷一)[1]41
按:“八”,国图本、钟本、传世本并作“入”。“入”是也。此处化用赵师雄于罗浮山梅树下梦仙一典,出自唐代柳宗元《龙城录·赵师雄醉栖梅花下》[7]9,言师雄被贬罗浮,于罗浮山梅树下梦到仙子。后代咏梅多用此典,明代叶颙《冬夜梅边即事》:“罗浮山下白云深,一枕师雄梦未成”,王冕《素梅五十八首(其二十八)》:“酒边漫说罗浮梦,忘却瑶台月下时。”本句谓昔日传言的可使人入梦境的那种梅树,今不得见。作“入”则正切文意,“八梦”于典籍未见。盖“八”乃“入”字之讹。
2.《梅赋》:“彼称既醉,逼清气而不胜,我则舍毫,占春光于长住,斯亦可谓一节之高,而未足以尽旷然之意。”(卷一)[1]42
按:“舍”,国图本、钟本、传世本皆作“含”。“舍”乃“含”之误。“含毫”指含笔于口中,喻构思为文或作画,于诗文中习见。晋·陆机《文赋》:“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唐·钱起《春夜过长孙绎别业》:“含毫凝逸思,酌水话幽心”等均以“含毫”指构思。“彼称既醉,逼清气而不胜,我则舍毫,占春光于长住”为骈体四六句句式,讲究对仗,上下句义正相反,意谓你(梅花)不堪清冷之气,我就构思为文(以这种方式)留你到春天。又同卷《荷赋》有“含毫续藻,俾世称四赋”意略同此,亦为证。
3.《他日大雨雪复泛蜻蜓池》:“冒曙曳裾徃,至昃引缆征。”(卷四)[1]61
按:“徃”,国图本、传世本并作“往”。《正字通·彳部》:“往,俗作徃。”是“徃”为“往”俗字,盖排印致误,当据改。
4.《将游金山寺,立马江浒,奉酬宗师薛公》:“十载并一朝,倏已成梦寐,帷余谆复情,千秋永蓍蔡。”(卷四)[1]68
按:“帷”,国图本、传世并作“惟”。当从国图本作“惟”。《说文》:“帷,在旁曰帷”,《释名·释床帐》:“帷,围也,所以自障围也”。“帷余”不词,是“帷”乃“惟”误字,当据改。
5.《蒋扶沟公诗(之六)》:“伏龙旧岩石,结构齐云浮。当时炼药处,依然霞色绸。”(卷四)[1]81
按:“石”,国图本、传世本并作“在”。“在”是也。“伏龙旧岩石”与“结构齐云浮”上下对句,“伏龙旧岩”对“结构齐云”,“浮”为动词,则上亦应为动词。若作“石”则词性不同,作“在”则正相符,此其一。上言“伏龙旧岩在,结构齐云浮”,用“在”,写明往日之处今仍存,正启下句“当时炼药处,依然霞色绸”抒发忆古追今之情。如作“石”则凸显不了今昔对比之状,语义衔接不如前者。作“在”字于义为胜,此其二也。又各本并作“在”,不知中华本何据。
6.《避暑豁然堂大雨》:“乃偕二三子,挂絺于其地,买酒穿布中,炮鳖腥道器。”(卷四)[1]87
按:“布”,国图本、钟本、传世本并作“市”。作“市”,“穿市”谓横穿集市,明代张萱《正月十三夜元陟先生见过观灯留酌喜而赋之》:“不须穿夜市,何必问更筹”意略同此;作“布”则文不成意,盖为“市”形近误字,当据改。
7.《钱刑部公楩》:“饘粥不得饱,啖枣充饥肠。如是者三载,郑魄归苍茫。”(卷四)[1]88
按:“郑”,国图、传世本并作“掷”。“郑魄”不词,当是“掷魄”之误。《广韵·昔韵》:“掷,投也”,“掷魄”谓投魄、放魄。“掷魄归苍茫”盖谓放其魂魄归于混沌之境。钱楩是徐渭同乡,乃修道之人,此处两句均言其修道状态。作“掷”是也。
8.《赠吕正宾长篇》:“楼中唱罢酒半曛,倒着儒冠高拂云。”(卷五)[1]113
按:“曛”,各本均作此。当校作“醺”。《玉篇·日部》:“曛,黄昏时”,《说文·酉部》:“醺,醉也”。“楼中唱罢酒半曛”表其半醉之态,“曛”字于义未安,当校改作“醺”。又《闻人赏给事园白牡丹》(卷六)“爱憎谁与定,赊酒借花醺”,《答李参戎》(卷十六)“扬尘缕缕起道上,醺然几坠”,表醉态均作“醺”。作“曛”者,音误字也。
9.《云岳篇》:“太岳山中高士室,长裙大带何人织。”(卷五)[1]119
按:“裙”,国图本、台本、传世本并作“裾”。作“裾”是也。《释名·释衣服》:“裙,下裳也。裙,羣也,联接羣幅也。”《释名·释衣服》:“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其在后常见距也。”作“裙”,则“长裙”多为女性穿着,唐代卢照邻《辛法司宅观妓》“长裙随凤管”、明代张昱《奉萱堂为陈彦廉作》“长裙曳翠佩珊珊”,于义远矣;作“裾”,则“长裾”形容高士超逸之姿,于古诗文中习见,《文选·邹阳〈上书吴王〉》“不可曳长裾乎”、《谢朓〈拜中军记事辞隋王笺〉》“长裾日曳”、唐代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承上句“高士室”,“长裾大带”当为高士的服饰,亦证作“裾”不误。又各本均作“裾”,不知中华本何据。
10.《观猎篇》:“今朝立马祈连上,不见匈奴一骑还。”(卷五)[1]124
按:“祈”,国图本、台本、钟本、传世本均作“祁”。“祁”是也。“祁连”指祁连山,“祈连”一词未闻,盖误录,当据改。
11.《老子出函谷图友人索题寿其所好》:“关门古树白月昏,一授道德五千言。”(卷五)[1]125
按:“月”,钟本同,国图本、台本、传世本并作“日”。“日”是也。《说文·日部》:“昏,日冥也。”“白月”指晚上皎白寒凄的月光,唐·刘长卿《宿北山禅寺兰若》:“青松临古路,白月满寒山”,作“月”则与“昏”意相悖。且“白日昏”一说于古诗中习见,意谓日暮之时,白日昏黑之景。唐代严维《送少微上人东南游》:“瘴海空山热,雷州白日昏。”李商隐《赠刘司户》:“江风吹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刻本“日”字、“月”字字形相似,钟本出自《三集》,盖因形近而误作,中华本沿其误。
12.《锦衣篇答赠钱君德夫》:“啸蹙风雪悲下雨,丈夫自是人中虎。”(卷五)[1]126
按:“雪”,国图本、台本、传世本并作“云”。“啸蹙风云悲下雨”先言“风云”而后“下雨”正相应,作“云”则上下相通也,作“雪”则与“下雨”相悖,义不可通。不知中华本何据,当校作“云”。
13.《摩诃庵括子松下听弦上人弹琴》:“十指引出七条水,松清琴妙听者寒。”(卷五)[1]136
按:“妙”,传世本、钟本同,国图本、台本作“玅”。作“玅”是也。《说文·弦部》:“玅,急戾也”,《尔雅·释诂》:“妙,好也”。诗言“松青琴玅听者寒”,“松清”“琴玅”相烘托,产生出“听者寒”的效果。作“妙”,则仅侧重琴音之美、好,未可使“听者寒”,于意有未安;作“玅”则琴音之急促、冷硬之态可显,正恰诗意。中华本失校,当校作“玅”。
14.《洞岩入鳖口有石枰石桥及石池诸景》:“桃根倒殭虫囓久,蜜脾夕挂蜂归稀。”(卷五)[1]166
按:“夕”,国图本、台本、钟本、传世本均作“仄”。《说文》:“仄,倾斜也。”“桃根倒殭虫囓久,蜜脾仄挂蜂归稀”上下句对文。作“仄”,则“倒殭”与“仄挂”正相对,上下正相通也;若作“夕”,则失对矣。刻本“仄”字形难辨,中华本盖误录。
15.《河豚》序:“味大约似鲐。越渔取鲇多于雪候从水柳窾中得之。”(卷六)[1]191
按:“鲐”,国图本、传世本并作“鲇”。《正字通》:“鲐,河豚别名。”是鲐、河豚本一物,不必言味相似。其下称“越渔取鲇”,诗中“河豚荻笋尖”“烂柳窾中鲇”又以鲇、河豚对比,正应序言“味大约似鲇”也。是“鲐”乃“鲇”形近误字,当据改。
16.《夕霞三首》下注“第一二首鱼劳则尾赤,《诗》云:‘鲂鱼赤尾’。”(卷六)[1]193
按:“一二”,国图本、钟本、传世本均作“三”。若言“一、二首”则不必加 “第”字,且序中注“鱼劳”正见于第三首“白鱼劳尾变,红石补天长”一句,亦证作“三”不误。“一二”盖刊误也,当据改。
17.《次韵答少颠师》:“悟后思仇成一笑,借君如意鼓盆歌。”(卷七)[1]228
按:“思”,国图本、传世本并作“恩”。应作“恩”。本诗是徐渭在狱中写给其师僧人少颠的,前一句“他年夜雨还思不,此日风波奈若何?”意谓日后是否还会想起,今日入狱之祸的无奈。“悟后思仇成一笑,借君如意鼓盆歌”,后半句用《庄子》击盆而歌一典,表明一种了悟之后的超然旷达。作“思仇”则仅放下了心中的仇怨;作“恩仇”,意谓恩也罢仇也罢,统统付诸一笑,更符击盆而歌的旷达,于义为胜。又元·许有壬《六州歌头·次马明初韵书所见》:“付恩仇一笑,漫且啄莓苔”意近此,亦可参。各本并作“恩”,未知中华本何据,盖形近致误,当据改。
18.《游齐云岩》:“九重海下酬恩诏,西海应多求福人。”(卷七)[1]232
按:“海”,国图本、传世本并作“每”。“九重”谓“九重天”。《玉篇·屮部》:“每,事屡也。”则本句谓天上多下诏令凡人入仙界,西海应该有很多求福的人。作“海”,则“九重海”一词未闻,且与“应多求福人”不相应。是“海”为“每”之误甚明。
19.《日者孙养静为推予命,无以酬之,因其索号诗,赋此以了人事》:“臣听鬬蚁将生慧,性悦青山不待观。”(卷七)[1]237
按:“臣”,国图本、传世本作“卧”。应为“卧”。诗题点明此为徐渭酬谢孙养静之作,孙乃一算命师,徐渭不当自称为“臣”,其证一;全诗乃诗人自述平生际遇,“卧听鬬蚁将生慧,性悦青山不待观”是写徐渭平日生活,其证二也。作“臣”于义远矣,作“卧”则上下相通。“臣”乃“卧”形近误字,当据改。
20.《建阳李君寄驯鹇,俄殪野狸,信至燕,哀以三曲(之三)》:“忆昨舍凄下主庭,殊芳远嫁俨姬嬴。”(卷七)[1]298
按:“舍”,国图本、钟本、传世本均作“含”。“舍”乃“含”误字。诗题点明诗寄哀情,作“舍”则上下文意不通,且于义亦远;作“含”则正显哀情,上下文相通也。又各本均作“含”,未知中书局本何据,当校改。
21.《宴游烂柯山(之四)》:“帷巾谈笑静风尘,只用先锋一两人。”(卷十一)[1]343
按:“巾”,国图本、钟本、传世本皆作“中”。“中”是也,意谓在军营的帷帐中指挥战役。作“巾”则文不成意,盖为“中”形近误字。当据改。
22.《牡丹(之二)》:“豪端紫兔百花开,万事惟凭酒一杯。”(卷十一)[1]397
按:“豪”,国图本、传世本并作“毫”。“毫”是也。《牡丹》“富贵花将墨写神”言画牡丹之事,本诗沿上仍写画牡丹之事。作“豪”不合文义;作“毫”,则“毫端”正为笔端,合画牡丹之事。又卷一《梅赋》“含毫”,意略近此,亦可证“毫”不误。当据改。
23.《代谢阁下启三首(之二)》:“恭维某官耆旧望隆,躬承帝眷,丝纶寄重,口代天言” (卷十五)[1]444
按:“维”,国图本、传世本并作“惟”。“恭惟”一词乃古人书信中惯用语,《尔雅》:“惟,思也”,“恭惟”即“我认为”,是表达自己想法的一种谦逊的说法。又该组诗之三中“恭惟某官留意东南”正作“惟”,是“维”乃“惟”误字明矣。当据改。
24.《奉答少保公书(之二)》:“天气消凉,病或消减,渭即驰赴函丈。”(卷十六)[1]459
按:“消”,国图本、传世本并作“稍”。“稍”是也。此乃徐渭病中答少保公胡宗宪的书信,前文称“渭谨昧死请乞再假旬余”,一则作“消”不足以表徐急切恢复健康以为主效劳之情,再则作“稍”与下句中“即驰赴”相应,上下文语气连贯,亦胜于“消”,作“稍”为胜。此处“消”盖涉上“消”而误作。
25.《与季友》:“菽粟虽常嗜,不信有却龙肝凤髓,都不理耶?”(卷十六)[1]461
按:“有”,钟本同,国图本、传世本并作“弃”。句末语气词“耶”有反问义,若作“有”,则与“耶”语气不谐,若作“弃”则正相洽,作“弃”为胜。
26.《代白卫使辨书》:“闻某同寮亲出战少挫衂,问其罪矣;某同僚不出战卫贼寇,问某罪矣。”(卷十六)[1]469
按:“其”,国图本、传世本并作“某”。此乃徐渭代笔谢罪书,该句乃论若进退均问罪于我(即浚),则他人将畏战,同下文 “某……,问某罪” 句式一致,均应作“某”,指代白卫使;且上文“闻某官迎敌,我挫衂,问某罪矣;某官束手,为我寇,问某罪矣”亦与该句句式一致,可证作“某”不误,当据改。
[1] 徐渭.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徐朔方.评《徐渭集》的编辑和校点[J].杭州大学学报,1989(3).
[3] 徐渭.徐文长三集[M].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808册).影印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4] 徐渭.徐文长文集[M].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807册).影印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5] 季羡林.徐渭集[M].传世藏书本.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
[6] 徐渭.徐文长三集[M].影印本.台北: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1968.
[7] 柳宗元.龙城录(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2:9.
责任编辑:张彩云
2016-12-11
靳亚萍(1990—),女,河北邯郸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传统语言学典籍整理与研究。
G256
A
1671-8275(2017)01-01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