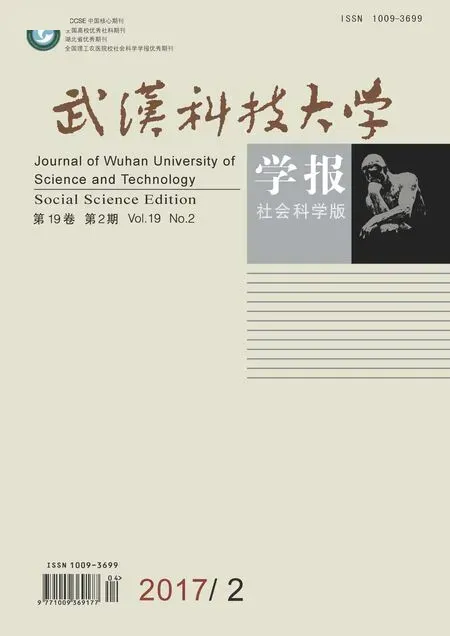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社会意义
强 以 华
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社会意义
强 以 华
(湖北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德里达指称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实质特征的一个概念,其社会意义在于它从形而上学的角度通过为人类提供人类之根支撑起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精神家园。德里达通过发现潜藏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中的替补游戏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指出逻各斯作为原始起源的概念不过是补充的神话。德里达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就解构了它的社会意义,他通过把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建构的人类之根连根拔去而把人类(西方社会中的人)从不合理的一元价值观下解放出来,但也使人类(西方社会中的人)成了无家可归四处飘零的个人。
德里达;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社会意义
作为重点解构西方哲学传统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与其解构对象一样,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哲学理论问题,而且也是(甚至更是)人类社会的问题。由于德里达解构主义是在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过程中确立的思想,所以,本文试图联系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社会意义来探讨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社会意义,并且对其进行评价。
一、逻各斯中心主义及其社会意义
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德里达指称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实质特征的一个概念。在德里达看来,逻各斯中心主义总是主张一种以在场的逻各斯为中心的不平等的二元对立结构体系,在这种结构体系中,作为对立的一方,逻各斯与它的对方处于暴力的等级制度之中,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价值上它都居于中心地位,统治和支配着另外一方。逻各斯是中心,与它对立的一方就是边缘;逻各斯是在场,与它对立的一方就是在场的替补……如此等等。在逻各斯中心主义那里,由于逻各斯具有最高的逻辑地位和价值地位,所以,在它看来,在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乃至西方文化中,凡是离在场的逻各斯越近的范畴就具有相对较高的逻辑地位和价值地位;反之,凡是离在场的逻各斯越远的范畴就具有相对较低的逻辑地位和价值地位。因此,根据不同范畴与在场的逻各斯的远近关系,便可以产生出一系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衍生形式,例如以本质为中心的本质与现象之间的不平等的二元对立结构、以理性为中心的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不平等的二元对立结构、以自然为中心的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不平等的二元对立结构,等等。尽管如此,以逻各斯自身为中心的逻各斯与其对立面(例如思维)的不平等的二元对立结构还是最为基本的二元对立结构。
在西方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的发展史上,逻各斯其实是作为实体的逻各斯,实体就是作为基础的世界,它是逻各斯的载体,而逻各斯则是它的本质。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哲学家那里,实体、世界在不同的意义上被理解,逻各斯也成为了不同的实体、世界的本质。德里达曾把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形而上学史上的逻各斯概括为四种典型意义上的逻各斯,他说:逻各斯“这个中心连续地以某种规范了的方式接纳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名称”[1],其中,主要包括从前苏格拉底或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的逻各斯、从上帝的无限理智或人类学的意义上来理解的逻各斯、从前后黑格尔的意义上来理解的逻各斯,以及从海德格尔的意义上来理解的逻各斯[2]13。德里达的概括无疑是一种正确的概括,但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分类方式来表达德里达所概括的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形而上学史上诸种逻各斯的典型意义,即古希腊哲学以及部分近代哲学所理解的世界基础上的逻各斯,它把世界理解成为外在客观世界(或者表现为外在的物质世界,或者表现为外在的精神世界),逻各斯则表现为外在客观世界的规律、尺度、理性;中世纪神学以及其他神学所理解的上帝基础上的逻各斯,它把世界理解成无限实体上帝所创造的有限实体的世界,逻各斯则表现为无限实体上帝的理性的命令(神的语言);近代主体性哲学所理解的世界基础上的逻各斯,它把世界理解成为内在世界(“主体”所产生的世界,例如笛卡尔由“我思”推论出的世界,特别是康德由人为之立法产生的世界),逻各斯则表现为(就康德说)人先天具有的用于给世界立法的法则(逻辑形式和道德法则);海德格尔哲学所理解的世界基础上的逻各斯,它把世界理解成为生存世界,它既是人在生存中(最后通过语言“赋予含义”)开启的世界(早期哲学),也是大道的道说(语言)向生存着的人显现的世界(后期哲学),逻各斯则表现为语言(大道的道说)显现世界中的尺度(神的尺度)。尽管不同时代的不同哲学家对于世界以及作为世界之本质的逻各斯的理解有所差异,但是,逻各斯都是作为世界本质的逻各斯,并始终处于逻辑和价值的中心地位。根据德里达的观点,这些以不同的形式或者不同的名称表达出来的连续的逻各斯或逻各斯中心主义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历史。
逻各斯中心主义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这种社会意义就是它通过一种确定的世界本质从形而上学的角度为人类提供了人类之根,支撑着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并且通过共同价值观向人类展现了一个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在西方传统哲学中,人和万物都是世界的产物,人则特别地表现为世界的本质亦即逻各斯的产物,因此,逻各斯作为实体、世界的本质也就是人类之根;换句话说,实体、世界本质的逻各斯决定着作为其产物的人类的共同本性,不仅如此,它还通过规定人类的共同本性进一步规定了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从而规定了人类应然的生存方式。由于逻各斯是人类的共同本质,它所规定的人性也是一种“共同的”人性,所以,它规定的人类的价值观也是一种“共同的”或“普遍的”价值观,这就是说,逻各斯的作用归根到底在于它力图使人类的价值观成为“共同的或普遍的一元价值观”。 当人类(其实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例如西方社会)有着共同的一元价值观并且在应然的意义上遵循着这种共同的价值观的时候,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就成了他们共同的精神家园。由此出发,我们发现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尽管是一种哲学理论,但它却具有十分明确的社会意义,它为西方社会共同的一元价值观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从而也为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提供了形而上学的根据。
二、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
德里达把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当作自己的首要哲学任务。逻各斯中心主义之所以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一个关键之点在于:它在中心和边缘(非中心)之间设置了一条非常明确的界限,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直线的线性关系,中心始终支配着边缘,而作为中心的替补,边缘尽管在实质上也会偏离中心甚至威胁中心,但是在表面上它却始终束缚于中心;因此,中心和边缘之间乃是有着确定意义的、不可动摇的“不平等关系”的封闭结构。德里达的解构就是要拆除这个封闭结构,让它变成一种开放性的具有无限可能的意义网络。那么,德里达究竟是如何具体通过解构来拆除逻各斯中心主义那有着确定意义的、不可动摇的“不平等关系”的封闭结构的呢?他的解构是一种阅读方式和哲学策略,尽管他也说解构是无目的的任意的解构,但是他的解构实际上是要通过双重姿态、双重阅读和双重写作来颠倒和置换逻各斯中心主义以逻各斯为中心的不平等的二元对立结构,通过发现阅读文本中的以逻各斯为中心的不平等的二元对立结构之直线线性关系中的某种“间隔”或者说“断裂”,从而发现中心并非中心、边缘也非边缘,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结构并非具有确定意义的不平等的二元对立结构;并且,它们作为没有中心、边缘和二元对立结构,因而也没有任何确定意义的东西也就变成了一种开放性的具有无限可能的东西,在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旧的意义不断被置换,新的意义不断被植入,它们在开放性的无限的可能性中无目的、无方向地一路撒播。因此,文本不是一种具有确定意义的东西,它只是一种不断生成意义的东西,它是一种充满差别的字符通过撒播式的流动编制出来的意义网络,在这种意义网络中,没有任何结构、基础、本质或中心。在哲学的文本之中,一切区分和对立都被解构,文本的作者亦即哲学家所做出的逻各斯与非逻各斯的对立,以及真理与谬误的对立、逻辑与修辞的对立、语言与文字的对立等,最终都会被阅读和写作所解构。
德里达在不同的著作中解构了不同哲学家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对卢梭的言语中心主义的解构。根据德里达的观点,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中心和边缘关系中,边缘作为中心的替补可以是一个替补之链。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存在着一个最为典型的替补之链,即逻各斯—思维(真理)—语言—文字。其中,思维之所以是逻各斯的替补,因为它以逻各斯为中心(所指),它束缚于逻各斯并以正确地反映逻各斯(真理)为依归;语言之所以是思维(真理)的替补,因为它是表述思维(真理)从而也是表述逻各斯的符号,它束缚于思维(真理)并以正确地表述思维(真理)从而也以正确地表述逻各斯为依归;文字之所以是语言的替补,因为它是为了避免遗忘而记录语言从而也是记录关于逻各斯的真理的符号,它束缚于语言并以正确地记录语言从而也以正确地记录关于逻各斯的真理为依归。在“逻各斯—思维(真理)—语言—文字”的替补之链中,文字是最后的符号和最后的替补,它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应该是因离逻各斯最远从而最有可能曲解逻各斯的东西,也是对逻各斯威胁最大的最不确定的东西。因此,在逻辑上和价值上贬低文字并从语言和文字相互关系的角度确定语言的中心地位从而把文字驱逐到最为边缘的地带成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共识,它使言语中心主义成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实质。德里达认为在所有的言语中心主义中卢梭的言语中心主义具有代表意义,所以,他将其作为主要的解构对象。
卢梭在语言与文字的起源关系中确立了语言对于文字的中心地位,也就是说,确立了言语中心主义。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人的自然需要导致了语言的起源。在卢梭看来,人的自然需要包含作为第一需要的生存需要和作为第二需要的情感需要,由于语言与人的聚合相关而生存需要使人分散、情感需要则使人聚合,所以,情感需要更是语言的起源。卢梭强调,作为温带的南方比作为寒带的北方更加适合人的生存,它使南方人不需过分考虑生存问题,从而为南方人情感需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南方因其更加注重情感而成了语言最初的起源之地。当南方语言转向北方语言时,北方寒冷恶劣的生存条件“迫使”北方人用“帮助我”代替了南方人的“爱我”,并用北方人的有助“理解”的清晰语言(它注重音节的划分)代替了南方人的唤起“情感”的生动语言(它注重的是重音)。这种代替使北方语言作为南方语言的“替补”导致了文字(普通文字)的诞生。文字被插入到了语音开始划分音节的地方,音节则是语言成为文字的基础,“文字的历史乃是音节的历史”[2]394。卢梭认为,在语言和文字的二元对立结构中,语言作为在场始终处于中心地位,文字作为在场的替补或者说语言的替补则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它使语言在逻辑上以及价值上高于文字;并且,由于文字作为替补是一种外在(而非内在)的替补,它开始远离在场,也就是说,它既取代语言又抹去(歪曲、阉割等)语言,所以,它还是一种危险的替补。因此,作为北方语言划分音节之产物的文字的诞生便是充满生动性的有生命的语言被阉割的结果。卢梭还更进一步地将语言和文字的对立与自由(统治)和不自由(奴役)的对立联系起来,认为“一个民族不可能既维持其自由,又说着这种(无法让集会者听明白的奴役性的——引者)语言”[3]。由此出发,他认为文字是“不平等”的根源。德里达对卢梭的这种言语中心主义进行了无情地解构,在他看来,卢梭在“指出”了文字的绝对外在性的同时却又“描述”了文字原则对于语言的内在性,这表明在卢梭的思想之中潜藏着自我解构。具体表现就是:在卢梭那里,南方和北方(因而也是语言和文字)之间并不存在如他自己深信的那种确定的直线线性关系;也就是说,南方和北方(语言和文字)的对立并非事实上的对立而只是结构上的对立,因此,语言与文字并没有绝对的中心地位和边缘地位的对立。所以,在卢梭那里,存在着一种替补的游戏,不仅北方是南方的替补,南方也是北方的替补,不仅文字是语言的替补,语言也是文字的替补。在这种替补游戏之中,“没有所指可以逃脱构成语言的指称对象的游戏,所指最终将陷入能指之手。文字的降临也就是这种游戏的降临。今天,这种游戏已经盛行起来,它抹去了人们认为可以用来支配符号循环的界限,它吸引了所有可靠的所指,削减了所有的要塞、所有监视语言原野的边疆哨所”[2]8。
由此出发,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起源概念发起了挑战。其实,语言之所以能是文字的中心,更进一步说,逻各斯之所以是其他范畴的中心,不过是因为它作为世界的原始起源而构成了世界的本质或说逻各斯。然而,根据德里达在卢梭言语中心主义乃至一切逻各斯中心主义中发现的替补的游戏看,起源的概念只不过是补充的神话,剩下来的只是不断取消边界并且抹去全部界限的痕迹、分延。从广义上说,线条、图案、雕刻、记号、荒野小径都是文字,它们是人为的痕迹,所以,文字是痕迹、分延的别名。但是真正说来,“文字是一般痕迹的代表但不是痕迹本身。痕迹本身并不存在……”[2]242。
三、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社会意义
实际上,在德里达之前,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逻各斯的具体内涵也在变化,并且,它的强度还在变化中逐渐转弱,从而不断地弱化着逻各斯作为人类之根或人类的共同本性的强度,也不断地威胁着人类之根或人类共同本性所支撑的人类共同的一元价值观和精神家园的稳定性。古希腊哲学(以及部分近代哲学)的外在的客观世界把“客观的”逻各斯作为人类之根或人类的共同本性的最终基础,这种基础因其“客观性”从而使以它为特征的人类共同本性具有最高的强度,并使以这种人类的共同之根为支撑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和精神家园也具有了最高的稳定性;中世纪神学(以及其他神学)的上帝(无限实体)把“权威的”逻各斯(具有权威的上帝的理性命令)作为人类之根或人类的共同本性的最终基础,尽管上帝的“权威性”具有不可动摇的特征,但是,它在强度上仍要弱于外在客观世界之逻各斯的“客观性”特征,所以,以上帝的理性命令为基础的人类共同本性在强度上要弱于以外在客观世界之逻各斯为基础的人类共同本性,并使以它为支撑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和精神家园的稳定性也得到了一定的削弱;康德哲学的内在世界(人为之立法的世界)把“先天的”逻各斯(先天的逻辑形式和道德规则)作为人类之根或人类的共同本性的最终基础,尽管康德力图用“先天性”来保证逻各斯的“客观性”特征,但是,这种属于主体的“先天性”在强度上又会进一步弱于上帝的“权威性”特征,所以,以先天的逻辑形式和道德法则为基础的人类共同本性在强度上又会进一步弱于以上帝的理性命令为基础的人类共同本性,并使以它为支撑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和精神家园的稳定性遭到进一步的削弱;海德格尔哲学的生存世界(它由大道的道说显现出来)把“神秘的”逻各斯(神的尺度)作为人类之根或人类的共同本性的最终基础,尽管海德格尔也把逻各斯看成是一种“尺度”,但是,他却反对西方传统哲学的那种具有不可抗拒意义的“刚性法则”,他的“尺度”不过是一种只有诗人才能猜度的“神秘”,它已基本失去了逻各斯的规范性强度,所以,以神的尺度为基础的人类共同本性也基本失去了约束人的强度,并使以它为支撑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和精神家园基本失去了任何稳定性。由此可见,随着西方哲学的逻各斯从古希腊哲学到海德格尔哲学在强度上的逐步弱化,逻各斯作为人类之根和人的共同本性的强度也越来越弱化,而由逻各斯和人的本性支撑的人类共同的一元价值观和精神家园也越来越失去它的稳定性。因此,逻各斯的逐渐弱化越来越威胁着人类(西方社会)的共同的一元价值观和精神家园。正是在此基础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开始以更为彻底的方式来冲击人类(西方社会)的共同的一元价值观和精神家园。但是,德里达对逻各斯的解构与以往哲学对逻各斯的弱化不同,它不是用一种新的弱化了内涵的逻各斯取代另外一种逻各斯,而是要彻底摧毁逻各斯,因此,它对人类的共同本性以及对以人类共同本性为基础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和精神家园的摧毁作用一定会非比寻常。在这种非比寻常中,我们将会看到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社会意义。
我们曾说,逻各斯的社会意义就是它为人类提供了共同的精神家园,或者更严格地说,它作为人类之根通过人类共同本性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精神家园提供了形而上学的根据。逻各斯之所以是逻各斯就在于它作为世界的起源和本质具有中心地位,并且以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结构表现出来。现在,德里达已经通过自己的解构主义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结构,逻各斯因其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结构也失去了作为中心的自身,因此,逻各斯自身便遭到了拆毁或消解。逻各斯的拆毁或消解意味着西方传统哲学给人类建构的人类之根被连根拔去。一旦人类之根被连根拔去,人类就失去了共同的本性,人类的共同的一元价值观因失去了人类共同本性的支撑而被打碎,从而使人类陷入了各自为政的多元价值观的状态;随着人类共同的一元价值观的打碎和人类陷入各自为政的多元价值观状态,人类也失去了自己共同的精神家园,它们被分裂成为一个一个孤立的单子。这些失去了共同精神家园的一个一个孤立的单子因失去了作为“类”的存在而成为了无家可归从而四处飘零的人,就像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作为“中心”的逻各斯自身被德里达解构之后所剩下的一路撒播的“痕迹”一样。这些就是德里达解构主义(“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所产生的社会意义。
那么,德里达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究竟该作何种评价呢?我们认为,德里达通过消解逻各斯来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摧毁西方社会的人类之根和共同本性,以及以共同本性为基础的共同的一元价值观和精神家园,用价值多元论摧毁共同的价值一元论,体现了一种理论的进步并且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其实,逻各斯作为世界的本质乃是一种“拟人”的结果。康德曾指出了传统形而上学(这里指他之前的旧形而上学)之本体的“拟人”实质。康德认为,旧形而上学由于没有更好的超验工具飞跃经验去认识“本体”,它只能采用一种“拟人论”的做法,亦即错误地把自己(人)关于超验世界的想法强加给了超验世界,将其看成是超验世界自身的实际状况。“拟人论创建了一种绝对的或超越感觉的领域的学说”[4],逻各斯的学说就是一种绝对的或超越感觉领域的学说。所以,逻各斯作为超验的世界本质也是一种“拟人”的结果,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神学的逻各斯是“拟人”的结果,海德格尔的逻各斯甚至康德本人的逻各斯其实也是“拟人”的结果。但是,“拟人”只是“少数”哲学精英以及利用逻各斯学说的“少数”政治精英才能从事的工作而非大众都能从事的工作,正因为如此,这些精英便成了逻各斯的“代言人”。据此,当逻各斯被解释成为人类之根和人类的共同本性并以人类之根和共同本性作为基础进一步解释人类共同的一元价值观和精神家园的时候,这些哲学精英和政治精英便成了人类之根和人类共同的一元价值观和精神家园的“代言人”。这样一来,他们的价值观便成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他们作为主流价值观的代表也代表着主流社会;与其相反,那些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甚至矛盾的价值观便被边缘化,持有边缘化的价值观的人也会被边缘化,甚至受到压制。由此可见,在以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形而上学之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中,从逻各斯推出人类之根和人类的共同本性、并进一步从人类之根和人类的共同本性推出人类共同的一元价值观和精神家园的做法,会使社会成为一种不平等的社会。惟其如此,人类价值观的多元化便意味着人类平等的增加,从而也就意味着社会的进步。我们曾说,从古希腊哲学到海德格尔哲学的发展历程也是哲学领域中逻各斯逐步弱化的过程,并且这一弱化过程(与相关的社会政治原因一起)导致了人类共同的一元价值观逐渐走向了多元的价值观,其实,与此过程相伴的正是人类(西方社会)逐渐从古代(特别是中世纪)不平等的专制社会逐渐走向近现代的相对平等的民主社会的历程。但是,正如弱化了的逻各斯以及逻各斯中心主义依然存在一样,民主社会中的主流价值观(例如西方社会中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价值观)也还存在,它仍包含了不平等。因此,德里达便用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方式来彻底消解逻各斯,他的这一做法实际上体现了他的一种抱负和努力,即彻底拔去人类(西方社会)之根,并且彻底摧毁人类(西方社会)共同的一元价值观之形而上学的基础,把人类从共同的一元价值观下彻底解放出来走向多元的价值观,最终在彻底消除主流价值和边缘价值之不平等区分的基础上实现持有任何不同价值观的人们之间的彻底的相互平等。就此而言,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具有十分积极的社会意义。
当然,德里达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既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也具有消极的社会意义。一般来说,在人类社会中,人类或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甚至一定范围之内的群体,它们若要成为一个共同体,必须要有一定(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共同的价值观,并且这种共同的价值观通常都会以一元价值观的形式存在。若没有一定或最低限度内的共同的一元价值观,那么,任何共同体都会缺乏必要的共同的真假善恶的判断,也就不会有任何凝聚力,最终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共同体。因此,哲学作为世界观因而影响人类价值观的理论,不能仅仅停留于“解构”之中。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虽然通过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而在把人类(西方社会)从不平等的共同的一元价值观下解放出来走向更为平等的多元价值观的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他若进一步考虑在保留人类多元价值观的同时,如何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重建更为平等的人类(西方社会)共同的一元价值观则可能更好。当然,我们也许不应苛求德里达,因为就他个人而言,他只把“解构”当作自己的哲学任务也无问题,但是,后人的哲学则应该在此基础上走得更远!
[1]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M].Translated by Alan Bas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1:353.
[2] 雅克·德里达. 论文字学[M]. 汪堂家,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 让-雅克·卢梭. 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摹仿[M]. 洪涛,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33.
[4] Claire Colebrook. Philosophy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from Kant to Deleuze[M].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41.
[责任编辑 李丹葵]
2017-02-2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编号:15FZX009).
强以华,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与西方哲学研究.
B565.59
A
10.3969/j.issn.1009-3699.2017.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