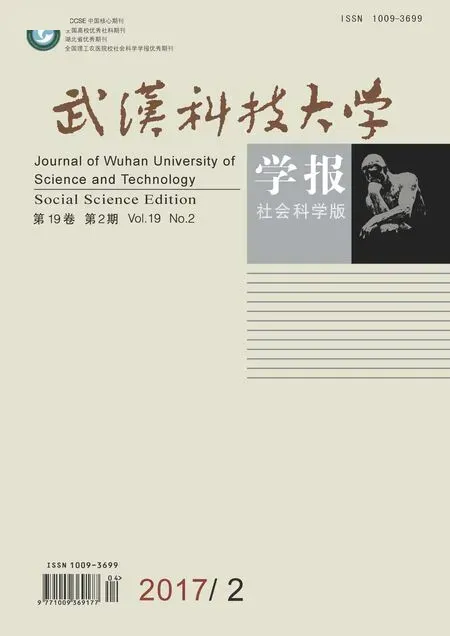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危机
张 三 元
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危机
张 三 元
(武汉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资本逻辑把“自然物质的自然力”“人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有机地统一起来,并有效地宰制着它们,从而创造出强大的生产力系统,驱动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由此造成了人的发展的悖论:在极大促进人的发展的同时,又导致深刻的人的发展危机。人的发展危机实质在于“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其重要表现形式则是“完全的空虚化”和“全面的异化”。克服人的发展危机,必须以扬弃资本逻辑为前提,让主体性回归人自身,并把资本逻辑置于其掌控之中,这个历史任务由马克思提出来,而由中国共产党人在忠实地履行。
资本逻辑;人的发展;自然力;生产力;发展危机;扬弃资本
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现代社会人的命运总是和资本逻辑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资本逻辑具有两面性,因此,资本逻辑在确立人的主体性和促进人的发展的同时,又把人的命运归结到资本逻辑之中,受资本逻辑所支配和控制,从而导致人的异化或物化,造成深刻的人的发展危机,在根本上,这是由资本的主体性造成的。资本的主体性僭越人的主体性,使人失去独立性和个性,从而使人隶属于资本的统治,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又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唯物史观的历史使命在于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而要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对资本逻辑作辩证的考察与反思,在利用资本和占有资本的基础上扬弃或消灭资本,从而把人的命运真正掌握在人自己手中。
一、资本逻辑造成人的发展的历史性契机
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独到而又深刻,他认为资本不是一般的物,而是以物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社会关系,即物化的社会关系,换言之,资本不是生产资料本身,而是市场化的社会关系。这个物化的或市场化的社会关系有着“魔法师”一般的神奇“魔力”,它把“自然物质的自然力”“人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①有机地统一起来,并有效地宰制着它们,从而创造出强大的生产力系统,驱动着生产力的空前发展。毫无疑问,这是资本逻辑“伟大的文明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逻辑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性存在是文明的伟大创造者,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赞美的口吻肯定了这一点。的确,资本逻辑在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特别是机器大工业代替手工劳动以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广泛应用,对“自然力”的征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逻辑这种“伟大的文明作用”有更多、更深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成为人的对象、成为真正的有用物。人终于摆脱了自然界的统治,而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自然界必须服从于人的需要。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主体和客体、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关系。二是资本出于增殖自身的目的,一方面,它要不断地扩大需要,使生产扩大化和生产多样化,这样,大量人口就像被法术呼唤出来一样,从而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扩大化生产不断地生产出剩余劳动,剩余劳动的不断增加,既意味着资本增殖的不断扩大化,也意味着人的劳动能力不断提高。三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逻辑,不断地克服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满足现有需要的闭关自守状态和落后的旧生活方式,从而打破民族和地域界限,使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总之,“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91。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论述资本逻辑“伟大的文明作用”时,“现实的人”从来没有缺席,即资本逻辑“伟大的文明作用”肯定要通过人自身体现出来,因此,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创造人的发展的历史性契机,促进了人的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这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中蕴含的基本思想。在生产力系统中,人是唯一有思想、能动的要素,因而是起主导作用的要素,没有人的发展,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人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或根本因素,因此,资本逻辑就必须激发出“人的自然力”。“人的自然力”是资本增殖的基础,它与“自然物质的自然力”一道构成社会财富的源泉。所谓“人的自然力”,是指蕴藏于人自身的生命力,亦即人的劳动力或劳动能力,具体地讲,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所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其中,作为物质基础的人的体力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人的知识、技能、意志力以及创造能力、实践能力等更具有关键性意义。只有把“人的自然力”充分地开发出来,资本扩张才能成为现实,因此,资本家出于资本增殖的需要,总是想方设法地开发“人的自然力”,譬如,对工人进行技能培训。在资本生产中,资本家把劳动者即工人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熟练工人是需要成本的,即需要花钱培训的;非熟练工人则不需要任何成本,即不需要花钱培训。尽管需要培训费用,但资本家还是选择了对工人进行培训,因为,只有雇佣工人的劳动技能提高了,才能提高生产效率、才能使价值增殖最大化,因此,工人的技能培训是资本增殖的必然要求。资本家还非常重视工人意志力的培养,这里所讲的意志力实际上是指工人劳动的持久性和耐力。在劳动过程中,由于机器生产导致工人器官的高度紧张,工人必须要有顽强的意志、高度集中的精神以及持久的忍耐力,而且,由于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使工人的劳动变得毫无内容,劳动的方式也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来越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活动来享受,在这种情况下,就越是需要这种意志。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意志是资本增殖的源头活水,因此,对于资本家而言,意志力的培养显然属于固定资本投资的一部分,是资本增殖的客观要求。总之,在资本逻辑中,客观上,人的潜力被发展到极致,人的体力和智力的运用也达致极限程度,一方面体现出资本主体性的残酷无情,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人的潜能、促进了人的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是“片面的”“畸形的”,但相对于那种可笑的“原始的丰富”的发展,其历史的进步性显而易见。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新的充实和新的证明,或者说,资本逻辑是人的发展逻辑的物化形态,它以物的形式昭示出人的本质力量。
资本逻辑对人的发展的“伟大作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即拓展出人的广阔发展空间并昭示出人的未来发展趋向,对此,马克思有一个重要论述:“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更高级的新形态”无疑是指未来新社会,而在未来新社会的“各种要素”中,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最根本的要素,也就是说,资本文明面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那么,资本逻辑是如何呈现出这一发展趋势的呢?
资本逻辑的最终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资本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就必须使“每个人的自然力”驱使尽可能多的“自然物质的自然力”,并从而形成巨大的“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即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雇佣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缩短,剩余劳动时间不断增加,而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则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增大,马克思指出,“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马克思之所以如此肯定资本创造的剩余劳动,是“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1]69。对于人的发展而言,“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这是一个最低的要求,也是一个最高的标准。之所以称之为最低的要求,是因为只有这样,人才能从物(工具)的地位超拔出来而成为真正的人。之所以说这是最高的标准,是因为只有这样,人的劳动才能不以物质需要的满足为目的,而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自主活动,自由性、超越性、创造性和全面性构成其本质特征。
剩余劳动之所以有可能使“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方面,是由于剩余劳动不仅创造剩余价值而且还是社会财富的来源,而社会财富则是构成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或表征。在马克思看来,这又表现为:①社会财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体现或证明。社会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或者说,是人对自然力即“自然物质的自然力”和“人的自然力”的有效统摄与运用,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创造性的发挥是至关重要的。②社会财富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表达了这个思想,认为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满足既是人获得解放的前提,也是劳动者从事科学、艺术、文学和交往等活动不可缺少的基础,同时,社会财富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证明,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发展和新充实。在生产社会财富的过程中,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另一方面,剩余劳动有可能创造出自由时间,而自由时间是个人“发展的空间”。尽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创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根本上是为了把这些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从而使之成为资本增殖的“发展空间”,但从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剩余时间具有转化为自由时间的现实可能性。事实证明,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剩余时间不可能全部被资本所吸收,总有一部分(或多或少)转化为自由时间,而且,这种转化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当然,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自由时间并非与资本逻辑无涉,而正是资本逻辑所必需,它为资本扩张拓展出新的空间。但是,一旦资本的主体性坍塌,资本被社会地占有和利用,它所创造的剩余时间也就会被社会地占有和支配,从而全面地转化为自由时间。自由时间不仅会使个人在艺术、科学和交往等方面得到发展,而且“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1]204。在资本统治中,这种主体只是作为生产过程中纯粹的主体,但在资本逻辑被扬弃之后,则成为人自身的主体——主体和客体的有机统一。
二、资本逻辑导致人的发展危机
资本逻辑在尽可能地激发“人的自然力”的同时又在拼命地吮吸“人的自然力”,因而,它一方面生产出人的全面性,另一方面又使人的发展碎片化、片面化和畸形化,使资本主体性压制、禁闭或取代人的主体性,从而导致人的发展危机。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发展危机的本质:“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1]137-138由此可见,人的发展危机的根源和实质在于“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其重要表现形式则是“完全的空虚化”和“全面的异化”。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的一度之中,深刻地揭示出资本逻辑反人性的一面。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在资本逻辑中,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被彻底颠倒了,对于资本而言,剩余价值是目的,劳动只是手段,或者说,“人的自然力”“社会劳动的自然力”以及“自然物质的自然力”只是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因此,人与其他的物一样,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不具有目的价值。“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3]269。对资本来说,任何一个对象本身所能具有的唯一的有用性,只能是使资本保存和增大。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只因为它是一种有用性的工具,能够创造比自身价值大得多的价值即剩余价值。正因为如此,在资本逻辑中,“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物的价值的增殖和人的价值的贬值成正比。
人的内在本质的“完全的空虚化”主要表现为资本在疯狂地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又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并受到限制等,资本逻辑吞噬掉了人的内在本质的实在内容,使之变得空洞而抽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自由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即是说,劳动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因而是“自由的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把“自由的活动”提升为“自主活动”,显然,后者更能体现或确证人的本质。劳动具有自由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这不仅是“人的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的自然力”的根本区别,而且还是人的本质力量最深刻的证明。在资本逻辑中,由于人沦为一种工具,劳动不再是一种“自由的活动”,更不是一种“自主活动”,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一种被迫的活动”,这种异化的、被迫的活动是一种不自由的活动,是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对于工人而言,这样的活动毫无乐趣可言,而只是一种痛苦与折磨。当然,劳动在给工人带来痛苦和折磨的同时,却给资本家带来享受和生活乐趣,资本的最大乐趣是雇佣工人的劳动能给它创造最大的剩余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自由自觉的内在本质已不复存在。
在劳动中,由于单个工人只是机器的一个部件,“死劳动”疯狂地吮吸“活劳动”,“人的自然力”的某一方面被发展和运用到极致,而其他方面的潜能则受到严重压制甚至戕害,致使人成为“机器人”或“单面人”。机器大工业和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理想,使工人固定在机器上,成为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完全服从资本增殖逻辑的支配。资本逻辑要求每个工人从小都学会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适应机器整齐划一的运动,而资本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3]486-487,从而使人成为“机器人”。
与人的内在本质“完全的空虚化”相联系的是“全面的异化”,“全面的异化”是“完全的空虚化”的另一种表达,其更深刻、更具体以及更全面地揭示出资本逻辑对人的统治。在马克思那里,异化的主体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费尔巴哈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是根本不同的,是指处在一定生产关系中从事劳动的具体的人,即现实的人或现实的个人。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抽象地谈论“异化”不同的是,马克思深入到资本的本质之中,揭示出资本逻辑之中的“异化劳动”。现代社会的危机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危机,马克思正是以“异化劳动”这个核心概念为基础,深刻地揭示出资本逻辑下人的发展危机。马克思认为,对人的确证的生产劳动,在资本统治中却表现为对劳动者——工人的奴役与统治,这种工人从事的但反过来奴役与统治工人的劳动就是异化劳动,产生异化劳动的根源是资本及其逻辑。如果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初步揭示出异化劳动的根源在于雇佣劳动以及私有制,那么,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则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资本。资本逻辑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促进了文明的进步,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人的主体性,但资本逻辑是以资本增殖为唯一目的,因此,它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而绝不会把人的生产力即人的自然力的增长作为它的理想目标。在这种逻辑中,文明的进步只会使资本支配工人劳动的权力更大,即造成资本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反而被压制、禁闭甚至消解。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种结论,更重要的是一种方法,即只有深入到资本逻辑之中,才能把握异化劳动以及人的发展危机的实质、才能洞悉资本统治下的人的命运及其未来走向。
在异化劳动条件下,资本逻辑主宰着人的命运并限制着人的发展空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释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其中,第三个规定即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是最根本的,其他三个规定都是其表现形式,因为当人与自己自由、自觉和自主的类本质相异化时,人的主体性就被釜底抽薪,人受抽象的统治,人的命运被资本所主宰。显然,强制性的、被迫的劳动只能使人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人们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人既失去了自由自觉的劳动,也丧失了赖以实现和确证其活动的对象世界,因而导致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人的内在本质被“完全的空虚化”,因此,资本逻辑必然造成“人的自然力”的枯竭与僵化,进而造成“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枯竭与僵化,最后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以及人和社会发展潜能的丧失。
物化是异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或者说,随着资本逻辑日益主宰着人的命运,异化就越来越表现为物化。在这个意义上,异化劳动即是物化劳动,作为物化的社会关系,资本对人的统治必然造成人的物化,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了物的性质[5]。一方面,资本逻辑必然造成人和人关系的物化。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其他人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因而形成人和人之间的物化关系。马克思也认为在资本逻辑之中,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再没有别的关系了。另一方面,资本逻辑必然造成人的物化,特别是人的意识的物化。可以把人对物的依赖性看成为物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更深刻地说,人对物的依赖性是人的本质物化的表征。更令人担忧的是,正如卢卡奇所言,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性结构越来越普遍地、深入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从而形成了物化意识[5]。物化意识一旦形成,人便彻底地沦为物的奴隶,从而完全地失去了自由,因此,马尔库塞认为在技术理性统治下,由物化意识所支配的人作为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或文化存在,人所应具有的批判精神被技术理性所消解,从而成为“单向度的人”[6]。物化意识以及由其所铸造的“单向度的人”是人的发展危机的深刻写照,表征着人的主体性回归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
三、扬弃资本,克服人的发展危机
“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4]11,这是唯物史观发出的一个绝对命令,显然,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再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始终都遵循着这一绝对命令。马克思的一生,始终服从着这一内心的绝对原则和目标,而资本关系即以物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社会关系是现代社会“一切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甚至是根本的关系,也就是说,确立人的主体性、实现人的尊严以及克服人的发展危机必须以推翻资本关系为前提,这个论断是科学而彻底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推翻资本关系何以可能呢?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关系仍然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资本逻辑仍然是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逻辑。即使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资本力量也仍然是强大的,资本逻辑在经济领域的统治地位仍然没有丝毫的动摇,而且还在不断地壮大自身。在某种意义上,资本力量以及资本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鲁品越所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是世界范围的资本逻辑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最后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这是《资本论》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最伟大的续篇,是用当代中国活生生的实践写就的新时代的鲜活的《资本论》[7]。发展生产力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而我们尚未找到比资本力量和资本逻辑更有效地驱动生产力的动力系统,当然,这不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把资本力量看成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力量,把资本逻辑看成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逻辑,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马克思辩证批判的深刻性在于它把资本逻辑看成是一种历史性的客观存在,是一个过程,因此,历史必将终结资本逻辑,而不是资本逻辑终结历史。当然,资本逻辑终结的时候还远未到来,因为在它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之前,在“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被创造出来之前,它是决不会灭亡的。
尽管资本逻辑造成了深刻的人的发展危机,但在客观上,“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扬弃资本本身”[8]543。资本逻辑在促进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使工人得到了发展,而工人的发展,从短期来看,作为生产力中的主导性因素,将有利于资本扩张,但从长远来看,将会扬弃资本,这是由人的本质力量所决定的。异化劳动的存在方式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证明,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沉沦与毁灭。在本质上,扬弃异化劳动是人类走向自由的必由之路,而扬弃异化劳动就必须扬弃资本,因为资本逻辑是造成异化的渊薮。在马克思看来,扬弃异化劳动并进而扬弃资本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资本积累所导致的“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744达到不堪忍受的程度,这种积累实际上是人的发展空间被压缩到极限,人从根本上失去了发展的权利;二是人获得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这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是扬弃异化劳动和资本的前提,又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当然,这两个条件“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4]581,也就是说,这两个条件都以资本逻辑为前提。资本要实现自身的不断增殖,就必须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即疯狂地发展生产力,在任何时候,它是停不下来的,它会一直走下去,一直走到它的尽头。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在确立自己主体性的同时,也在创造另外一个主体——资本的“掘墓人”。
在资本力量仍然强大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创造另一个主体并使资本逻辑置于他的掌控之中,这是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实际上,这个任务早就被马克思历史性地提了出来,马克思所讲的“扬弃资本”不是一味地消灭资本,而是一分为二,既克服又保留,当然,消灭资本是一个终极目标。“自为存在的资本就是资本家。诚然,社会主义者说,我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被看作纯粹的物,而不是被看作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在自身中的反映恰恰就是资本家”[8]262。尽管这段话是马克思对所谓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但却内蕴着深刻的建设性内容。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资本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更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这两个方面都不是纯粹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既相反相成又相辅相成,是一体两面,当然,后者是其本质,因此,马克思的这个批判可以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启迪:①当资本被社会普遍占有和利用时,是否可以把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与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剥离开来呢?理论和实践都提出了这个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的是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而不是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事实上,我们现在所占有和利用的资本,在一定意义上,主要是指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当然,从现实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来看,把两者完全地剥离开来是不可能的,但在一定条件下相对地剥离开来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只有如此,才能使人从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是人控制、支配资本,而不是资本控制、支配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必须积极扬弃私有财产以及由其产生的雇佣劳动。对私有财产以及雇佣劳动的积极扬弃,意味着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意味着彻底消灭人与人、人与自然界的敌对关系,建立起人对自己的本质、对其他人和对自然界的合乎人性的关系;意味着人的活动不再局限于谋生和对对象的排他性占有,而以全面的方式欣赏对象、享受生活和发展自己。②人是目的,资本只是手段。我们之所以需要资本,是因为资本是为人服务的工具,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它体现出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基本立场。在康德那里,“人是目的”是一个“绝对命令”,毫无疑问,这个思想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继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就是以“人是目的”这个“绝对命令”为最高统率和提领的。与康德不同的是,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人是现实的人,是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中现实的劳动者,而且,“人是目的”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得以贯彻,只有在资本被人所占有和支配,从而转化为人们共同的社会财富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马克思提出的这个历史性的任务正由中国共产党人在忠实地履行,由此开辟出独具特色而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道路。一方面,我们必须占有并支配资本,利用资本追求自身价值增殖的本性,不断实现社会物质财富的积聚。物质财富的不断积聚既是社会主义由初级阶段通达高级阶段的阶梯,也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诚如马克思所言,我们占有和支配的资本是作为物质生产资料的资本,而不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资本及其增殖只是手段,而绝不是目的,只有人才是目的——以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为目的。这一点,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清楚:“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这个科学论断是马克思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的具体运用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以人为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是手段,实现共同富裕才是目的,而共同富裕的主体是人民,也就是说,在本质上,社会主义是以人为目的、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的,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所在。只有以人为目的,才能摆脱资本对人的统治,进而实现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反之,只有实现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0],从而也就成为资本的主人。只有当主体性回归人自身,人的发展危机才能最终被克服。
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必须辩证地对待资本逻辑。资本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资本逻辑仍然是我们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发展和壮大资本仍然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在运用资本的过程中,一定要驾驭资本,用社会主义制度抑制或克服资本逻辑邪恶的一面,从根本上瓦解资本的主体性,让劳动者成为资本的主人,占有资本、利用资本以及驱动资本。要始终坚持以劳动为基础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倡导劳动光荣的优良风尚,坚决抵制和防范拜物教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对人的精神的侵蚀。当然,我们这里所讲的劳动,不是资本统治下的异化劳动,而是服务于全社会的、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为目的的创造性劳动。
注释:
①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了“人的自然力”。如“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8页)。“劳动的这种自然能力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所固有的自我保存的能力,正像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属性,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不断占有表现为资本的不断自行增殖一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0-701页)。“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又提出了“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3页)。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7-928.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1.
[6]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导论.
[7] 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512.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6.
[责任编辑 周 莉]
2016-11-1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编号:14FZX019);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5207).
张三元,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从事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文化问题研究.
A811
A
10.3969/j.issn.1009-3699.2017.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