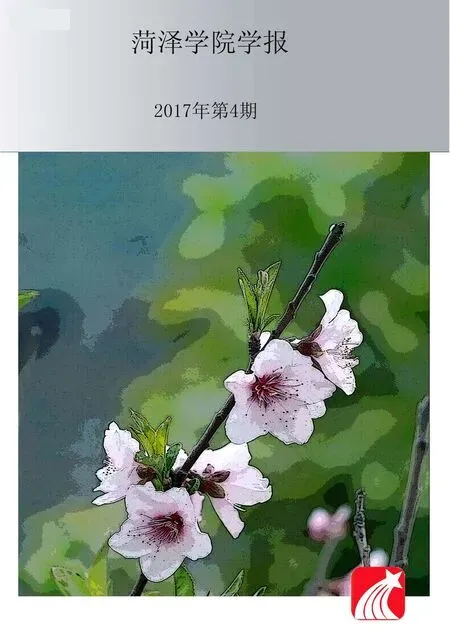农村家庭养老现状及发展路径研究*
王朝霞,曹婉莉
(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四川南充 637000)
农村家庭养老现状及发展路径研究*
王朝霞,曹婉莉
(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四川南充 637000)
在农村日渐严重的老龄化背景下,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种种挑战,已经难以担当起农村老年人养老的重任。自我养老、社会养老、社区养老等养老模式在当下农村成为关注的热点。通过对家庭养老存在的基础、现状、影响因素等相关文献的梳理,认为农村家庭养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农村养老的主流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其进一步完善的对策,同时认为当前应该重视农村家庭养老变化方面的研究,结合地区实际状况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农村养老;家庭养老;自我养老;社会养老
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尤为的严重和突出。根据2014年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显示,农村留守老人的数量已近5000万,有54.6%的农村老人还在从事职业性劳作;从收入来源上看,超过68.4%的老人主要靠子女资助生活,其次是新农保和土地收入[1]。由此可见,在农村地区仍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选择依靠子女养老,家庭养老在当下的农村仍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受到人口流动、家庭结构变化、养老观念变迁等因素的影响,家庭养老在农村的地位受到学界的普遍质疑,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整理,认为当前学界关于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家庭养老存在的基础、家庭养老与其他养老模式的相互替代性、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家庭养老的未来发展路径等。
一、家庭养老存在的基础
关于家庭养老不同学者都在自身理解的基础上给出了相关的定义,有的学者从广义上将家庭养老界定为:家庭养老是指由家庭承担养老责任的文化模式和运作方式的总称[2]。具体来讲:钟涨宝认为,家庭养老是指以血缘关系为基石,由子女、配偶或其他直系亲属为老年人提供经济上的赡养、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准的一种最为传统的养老方式。[3]学者肖倩认为,家庭养老是指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这三个方面由子女(包括儿媳)为60岁以上的老人所提供的养老服务。[4]综上所述,家庭养老实际上是我国独特的代际关系的外在表现。我们可以将家庭养老简单的概括为代际间(尤其是指子女对父母)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及精神慰藉等方面的赡养关系,而以上所提及的三个方面也可以作为家庭养老具备的独特的功能。当前家庭养老存在的基础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经济基础、社会基础。
(一)影响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
在农村家庭养老存在的经济基础方面,学界的观点比较统一,争议较少。具有代表性的是学者刘庚长,他认为对家庭养老产生影响的经济基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农村老年人经济来源少,需要依赖子女的供养;农村单一而特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农村社会福利较差,社会化养老资源不足;以及农村医疗水平低等都构成了农村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5]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农耕社会的影响,家庭养老一直是我国农村主要的养老模式,在经济因素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和改善的情况下,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变革上也就无法获得额外的经济力量的支撑,所以家庭养老就长久地维持下来了。
(二)影响家庭养老的社会基础
1.孝道观念。“孝”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我国的孝道思想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较为深远。孔子认为,“孝”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道德规范,是其他一切道德规范发展的前提;同时他认为在精神上的孝,意义要远大于物质上的供养。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孝道尤其的看重尊老、敬老,然而随着孝道文化的传承,孝道文化在精神方面的赡养功能逐渐的退化,子女对老人的养老更多的偏重了物质供养,而逐渐忽视和弱化了精神方面的慰藉。穆光宗结合当今社会出现的这种精神赡养弱化的境况提出了一种新的“孝养观”,他认为新的“孝养观”要不同于以往的子女只站在自身的立场和角度上来赡养父母,而是能站在家里老人的立场和角度来关爱他们,结合老年人自身的需求来满足他们,使老年人能够切实的在精神上感到满足。同时,他提出新的孝养观明确主张孝与养要充分结合,并且以孝当头,以养相托。[6]
在穆光宗看来,“孝”说到底也是一种代际关系,所以从孝道的代际传承来看,子女对家中老人的赡养又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学者李健从代际关系的角度对孝道观念进行了诠释,他认为,成年的子女更多的把孝道的思想观念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责任,而为了让自己老的时候能够老有所养,为人父母的成年子女会以身作则的遵守孝道伦理观念,成为下一代子女学习的榜样。[7]所以孝道伦理思想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能使家庭养老的基础更加的巩固。
2.代际关系。代际关系即在家庭中子代与亲代之间相互的代际赡养或抚养关系,费孝通的“反馈模式”堪称是对中国农村家庭养老中代际关系的经典诠释[8],反馈模式是指在子代年幼时父母抚育子代,子代长大成人后除了继续抚育自己的下一代,还要对父母有反馈式的赡养义务,这种带有反馈式的代际赡养关系是为了区别于西方的“接力式模式”,即没有子代对父母的反馈这一环节。费孝通认为,在这种反馈模式里,代际关系基本上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即父母为了抚育子女付出的艰辛与父母年老时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付出是均衡的。
然而关于费孝通所提及的“反馈模式”当前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当前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子女对父母的反馈已经演变成一种经济性的交换关系,如学者王海娟通过实地调研论证得出,在当前的华北农村,子代与老人之间的代际赡养关系不再是费孝通所提及的以传统伦理为基础的反馈型养老,而是更多的基于经济互惠性的交换型养老,赡养老人也不再是一种伦理性的道德行为,而是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物质化、指标化的经济性行为。[9]对于王海娟的观点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杨云刚认为当前父母与子代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而存在,老年人与晚辈之间的代际关系虽然是不均衡、不对称的交换关系,但这不同于由“理性经济人假设”所衍生出的“交换论”。也就是说当前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互动关系不是基于“交换论”而存在的。[10]尽管当前不同学者对农村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赡养关系看法不一,但争论点也只是在代际关系的存在是否是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础,以及这种代际赡养关系能否以简单的“交换关系”来评说;但总的来说,学者们普遍都认为不管代际关系是否是以理性的交换为基础存在,都是一种不均等的、失衡的关系。
(三)影响家庭养老存在的其他因素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还有一个因素对家庭养老的持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即家庭养老本身具有其他养老模式不可取代的功能性。关于家庭养老的功能性,学界形成了较统一的观点,即都认为家庭养老的功能主要有三方面:经济(物质)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经济供养主要是指子女在家中父母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对其提供物质方面的供养,来满足其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这种经济供养的需求在农村地区尤其突出,城市的老年人一般都有退休养老金来满足自己年老时的基本物质需求,而农村老年人在有活动能力时虽然也会为自己攒下部分养老钱,但大都补贴给了子女,以期在自己丧失劳动能力时子女能够赡养自己。生活照料一般指老年人尤其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被人照料的需求,而家庭成员是照料老人的不二人选,在农村地区一般是儿子或儿媳承担起生活照料的义务,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女儿在农村家庭养老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精神慰藉是指老年人在年老之后尤其是子女忙于自己的事务不在身边时渴望得到情感上的慰藉,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老年人希望子女能在自己身边享受天伦之乐,希望子孙满堂来获得生命的满足感。
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养老面临重重挑战,却依然存在于广大的农村地区,一定程度上因为家庭养老的某些功能具有不可替代性。学者辛妍认为,家庭养老之所以一直存在至今,是因为它有其他养老模式不可取代的优越性。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家庭关系中利他主义的行为都让子代对老人的赡养行为更加切合老人的需求。且家庭养老提供的养老资源灵活多样、成本较低,也更容易被老人接受。[11]这些因素都让家庭养老成为农村老年人的首选养老方式,而这些因素又是其他的养老模式所替代不了的。
二、现阶段农村家庭养老的现状
(一)农村养老模式多样化,家庭养老仍是主流
在广大农村地区,家庭养老不再是老年人选择的唯一的养老模式。在农村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家庭养老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都发生了改变,在经济基础层面上,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土地的经济保障功能逐渐减弱,农村的医疗服务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社会福利也在缓慢的倾向于农村;而在社会基础层面上,传统的孝道文化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代际关系伴随着父权制的衰落凸显出中青年在家庭中的影响力提升。这一系列的变化让家庭养老“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虽然整体上家庭养老在农村所占的比例下降了,但这不一定表明家庭养老功能已经弱化,而可能只是养老方式多样化的一种反应[5]。
理论上说农村养老模式选择的多样化对家庭养老会产生挤压效应,但由于家庭养老存在根基历史悠久,又有其不可取代的功能性,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家庭养老仍是农村养老模式的主流,且相当长的时间都不会改变。如田北海通过实证调研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虽然随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农民的养老意愿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是由于“养儿防老”的意识在农村社会根深蒂固,多数老年人仍然会选择依靠儿子、依靠家庭来养老[12]。学者钟涨宝也认为,家庭养老模式在较长一段时间都将会是农村社会最主要的养老模式。他从两方面来论述了这一观点,一方面是目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还比较低,而以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难在短时间内提高农村养老保障待遇,而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基本上处于空白的起步阶段。另一方面,老年人普遍越来越注重精神慰藉方面的需求,而传统的家庭养老在精神慰藉方面能较好的满足老年人的需求。[2]所以家庭养老模式这一暂时不可取代的功能性,使得家庭养老在广大农村地区仍持续存在着。
(二)家庭养老与自我养老关系成为研究热点
近年来,家庭养老与自我养老关系的研究成为热点,且研究结论多倾向于自我养老将成为农村的主流养老模式。如学者黄闯认为,由于传统家庭保障功能不断弱化,社会保障供给严重不足,使得自我养老保障成为了农村老年保障实践中最主要的方式。[13]而在自我养老模式能够趋于主流的原因分析上,不少学者都提到了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如李俏通过分析发现:农村家庭养老的功能弱化和社会养老的缺失是导致自我养老日渐趋于主流的原因。[14]
也有不少学者对自我养老模式对老年人的保障能力提出质疑,并认为自我养老在当前农村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且要实现农村老人的自我养老需要具备某些经济条件。如学者穆光宗认为老年人要实现自养需要有较多的积蓄或者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如果满足不了这个条件,其自养能力一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健康的退化而降低[5]。程启军也认为,自我养老的养老方式需要有充足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支持,适用于农村地区的富裕家庭,而能够满足老年人情感和生活照料需求的家庭养老在广大农村地区仍是主流养老方式。[15]
在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的关系上,有学者认为两者是可以有机的结合起来的,并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不一样的主次关系。如朱劲松指出,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在现实中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二者完全可以有机的结合起来。在当前的情况下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自我养老为辅,在将来则可能转变为自我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辅。[16]
笔者对上述的研究结论并不十分赞同,而是比较倾向于以下的观点。结合当下农村的现状来说,老年人自我养老与家庭养老并不矛盾,当老年人处于低龄老年阶段时,在经济方面可以实现自我供养,可以认定其是处于自我养老阶段的,当老年人处于高龄老年阶段时,失去自我保障的经济供养能力、生活照料能力等,依靠自我及配偶已经难以满足养老需求,这个阶段只能依靠家庭养老。所以自我养老与家庭养老适应于农村老年人不同的生命周期,并不是相互矛盾、非此即彼的关系。[9]
(三)社会养老前景广阔,家庭养老不会被取代
关于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关系,不少学者认为虽然当前农村仍旧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但向社会养老的转型发展是其必然的趋势。如学者刘春梅从养老资源的供给角度认为:当前农村养老资源的供给依然以家庭为主,但社会养老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7]周莹从农村家庭养老跟土地的关系角度论证指出社会养老是未来农村养老发展的必然趋势。她认为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是以土地为共同的经济基础而存在的,在经济方面由于土地的基础保障性作用力在逐渐减弱,且呈现出不可持续性的趋势,这就使得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向社会养老模式过渡成为必然的趋势[18]。 通过对苏北某县的调查,陈芳也认为长远来看,欠发达地区农村养老的出路也是会走向社会养老[19]。虽然众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论证了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发展关系,但都认为社会养老会是农村养老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家庭养老是否终会被社会养老所取代上,也有学者持否定的观点,认为社会养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家庭养老存在替代效应,但不会彻底取代家庭养老。如张川川经过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当前在农村广泛推广的社会养老保险对传统的家庭养老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但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低,仍需要进一步的发展才能产生较好的替代效果[31]。孙岩也认为,不管现代社会如何变迁,家庭养老模式会随着家庭的存在而长久的存在,不会被社会养老模式所彻底取代,在不会被取代的原因分析上,她认为是传统的孝道伦理思想观念以及当下农村现状让家庭养老只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转变而变迁性适应性的发展成为新型的家庭养老模式。[20]不只是社会养老,余秋华认为家庭养老模式不会被其他任何的养老模式所彻底取代,因为传统的家庭养老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并不是走向了没落,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转变成为一种新型的家庭养老模式[21]。
(四)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可相辅相成
在家庭养老和居家养老关系方面的研究较少,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背景下应着力发展农村社区,依靠农村社区来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不同于城市里居家养老的意义,这里所提到的居家养老更多的偏向于依靠农村社区养老。慈勤英在提到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的关系时认为农村家庭养老在当前的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但由于家庭养老目前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还具有广泛的存在性与某些不可取代的功能性,应该将家庭养老和居家养老结合起来各取所长、相辅相成。同时她认为,家庭养老之所以在当前的农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因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一个大家庭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家庭式的小农生产模式,而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多、农村经济发展多元化,大家庭分裂成一个个独立的小家庭,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传统的家庭养老也就难以为继了。[22]
综上所述,当前对农村家庭养老现状的研究不再是单一化研究家庭养老的发展状况,而是与其他养老模式一起对比研究,尽管不同的学者对家庭养老发展前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总的来说都认为当前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已经弱化,单纯的依靠子女来养老已经难以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且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向乡村的浸润,父权制的衰落、农村经济模式的转变、家庭结构小型化、孝道文化变迁等因素的影响,当前的村落文化也发生了较大的变革,再不是费孝通“乡土中国”里面的“封闭”“落后”的模样,而是充满了“现代化”气息。土地经济保障功能的弱化刺激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又促使乡村邻里关系、家庭代际关系更趋向于经济互惠理性关系。而以传统孝道伦理为根基的家庭养老受到这种经济互惠理性的冲击,衍生出诸多的问题,除了上文所提到的经济因素,影响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因素还有很多。
三、现阶段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影响因素
当前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的变化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是学界较公认的普遍性的影响因素。如赵倩倩研究发现,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家庭规模趋向小型化,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让传统依靠子女进行养老的家庭养老难以为继,家庭结构的变动让农村老年人面临着“老无所养”的困境,养老资源出现暂时性的短缺;农村的代际权力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父辈在家庭中的权威全面削弱,这些对家庭养老的维持和可持续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3]李俏也将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原因归结为:家庭结构的变化和老人经济权力的丧失,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家庭结构小型化加重了家庭养老的负担,而农村老人经济权利的丧失则减弱了传统家庭中老人的权威和话语权。[13]
纵观当前农村家庭养老的发展现状,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农村家庭养老的发展,钟涨宝对诱发家庭养老困境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中提到了引发家庭养老困境的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他认为传统宗族长老制度的影响力已经趋于弱化,父权制也逐渐衰落[24],随着家庭中男性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留守在家的女性在家庭中地位和影响力得到提升,婆媳矛盾也随之激化,这些变化性因素也从侧面加速了大家庭的分化以及家庭养老保障力的减弱。
还有学者认为人口流动也是影响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弱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如陈芳认为,由于人口流动严重削弱了传统的家庭养老,使得农村养老从传统的家庭成员为家里老年人提供物质、生活、精神方面的照料为主变为老年人对自己(包括配偶)进行日常生活照料的满足。[18]而这种境况主要是由人口流动带来的家庭空巢化所引起的。
刘庚长也提到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延续产生很大的阻碍,同时他也指出农村老年人观念的变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4],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的经济、生活、文化等方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农村的养老观念的变化尤为的显著,之前在农村较为盛行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年轻一代的老年群体里已经逐渐的淡化,家庭结构小型化及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让留在父母身边的子女数量减少,这迫使农村老年人不得不改变之前的养老观念来寻求新的养老方式。而且伴随着生育和抚养下一代成本的提高,农村年轻一代生育子女的数量也变少,也更为注重子女以后的生存和发展质量,所以年轻一代的养老观念更是在悄然变迁,而代际间养老观念的变迁也让传承了上千年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了变化。
除了以上所提及的影响因素,当前农民土地生产经营风险加大及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对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产生了影响,农村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分散经营,整体上增加了土地的生产经营成本,土地的投资成本在市场化条件下有逐年提高的趋势,而粮价却趋于平稳,农民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相对减少,何玉桃认为这种土地经营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大了农民的经营风险[25],也就减弱了土地对家庭的经济保障功能,这也迫使农村闲散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逐渐向农村渗透,在人口流动带动下发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碰撞和交流加大了农村代际之间的隔阂,从而间接的影响了传统家庭养老的延续和发展,家庭养老的保障功能也趋于弱化。
四、完善农村家庭养老的对策
(一)以家庭养老为基础,增强老年人自我养老能力
在完善农村家庭养老的发展思路上,较多的学者提到了要加强农村老年人自我养老的能力。如赵倩倩指出要提倡农村老年人掌握一定的技能,增强自我养老的能力,减少在经济上对子女的依赖。[22]刘培培也认为,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养老发展尚不完善,无法从社会层面上对老年人提供照料资源,而子女也因为种种原因难以满足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所以老年人只有不断的提高自我养老能力来保障老年生活[26]。而为了要增强农村老年人的自我养老能力,有学者认为应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只有老年人的经济能力增强了,才能加强自我养老能力。马亚静在此思路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一个新的农村养老模式—企业式自我养老作为农村家庭养老的补充,即在农村范围内以村为单位,由县、乡民政部门牵头,在农村中开办一些带有福利色彩的小型的老年人企业,如手工艺品加工、养殖、种植园等。[27]
(二)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有不少学者认为,社会养老是未来农村养老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当前应该走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道路。袁春英认为,单纯的家庭养老已经难以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社会养老会是农村未来的发展趋势,而当前社会养老保险在农村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难以满足农村居民的养老需求,所以当下可以选择走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养老相结合之路[28],而等到社会养老保障系统在农村发展日趋成熟时,社会养老将会逐渐的取代传统的家庭养老。李健也认为,为了化解农村家庭养老弱化所带来的养老风险,政府所主导的社会养老保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应该完善农村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将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结合起来[6]。杨政怡在提到将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时提到了新农保在家庭养老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建议提高新农保的待遇。她认为,家庭养老的部分功能如精神慰藉难以被社会养老替代,因此在积极鼓励农村居民参与新农保并逐步提高新农保待遇的同时,应该突出家庭养老的重要性,促进农村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互补,从而有助于农村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发展局面的形成。[29]
(三)发展农村社区,建立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现有文献中,将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相结合的研究较少。慈勤英认为应该将农村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结合起来,在农村建立社区化的居家养老服务支持系统,采取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投资运营方式,以此来缓解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难以为继的矛盾[21]。何玉桃提出了一种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新的路径—居家型社会养老保险。即一方面让老年人居住在自己家中,与其家人共同生活;另一方面,让老年人居家养老成本的承担主体多元化,通过政府和社会分担承担养老成本,来减轻单个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24]。以上观点同样需要注重农村的社区建设,增加社区的社会化养老服务功能。这跟慈勤英的观点也是不谋而合的,即都是需要注重农村社区的发展来增强老年人的养老保障能力。
除了以上所提及的三个完善对策,还有学者认为传统孝道文化的淡化也是导致家庭养老弱化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所以在完善农村家庭养老的对策上应该继续弘扬有些没落的孝道文化,以及对实施家庭养老的子女及家庭进行鼓励。王红认为,可以对赡养老人的家庭实施家庭养老资助计划,政府对承担赡养责任的家庭给予补贴或奖励,同时还应该重构和弘扬新孝道,增强道德在社会行为中的约束力,形成敬老、爱老的新风尚[30]。
在完善当前农村家庭养老的对策上,虽然现有的文献对各种模式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在探索研究中仍发现有不足之处,而最大的不足之处莫过于当前的研究过于的偏向于理论上的预见和思考。当下农村的发展日新月异,且地区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所以当前的研究应与当下农村地区实际状况相结合,一概而论的谈农村家庭养老未来发展路径无异于纸上谈兵。其次虽有不少学者认为未来农村自我养老或社会养老等必然会取代传统的家庭养老,在本文看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家庭养老将一直存在,而自我养老、社会养老等只能作为辅助的养老方式作为家庭养老的过渡阶段或一部分而存在,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变迁,自我养老、社会养老的功能性和适应性将会得到持续的增强,但家庭养老却也不会消亡,只是以另外一种形式适应性的融合在农村老年人的生活里。
[1]曹鹏程.让老年人生活得更有尊严[N].人民日报,2015-06-10(5).
[2]韦加庆.新时期农村家庭养老的可持续性思考[J].江淮论坛,2015(5)42-45.
[3]钟涨宝,杨柳.转型期农村家庭养老困境解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6(05):22-28.
[4]肖倩.农村家庭养老问题与代际权力变迁—基于赣中南农村的调查[J].人口与发展,2010(6):52-59.
[5]刘庚长.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存在的基础与转变的条件[J].人口研究,1999(3):41-42.
[6]穆光宗.我国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理论分析[J].社会科学,1999(12):26-30.
[7]李健.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因素研究[D].山东:济南大学,2010:1-15.
[8]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1983(1):6-15.
[9]王海娟.论交换型养老的特征、逻辑及其影响—基于华北平原地区的调查[J].南方人口,2013(5):53-60.
[10]杨云刚,现阶段农村老年人养老现状研究[D],湖北:华中农业大学,2013,38-39.
[11]辛妍.农村人口流动对家庭养老的影响研究[D].陕西:陕西师范大学,2013:1-13.
[12]田北海,雷华,钟涨宝.生活境遇与养老意愿—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偏好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2(2):74-85.
[13]黄闯.农村老人自我养老保障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探索,2015(2):125-129.
[14]李俏,陈健.农村自我养老的研究进路与类型诠释:一个文献综述[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7(1):98-104.
[15]程启军.博弈与理性:农村养老方式的选择[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5(1):89-93.
[16]朱劲松.试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农村自我养老模式选择[J].农村经济,2009(8):79-81.
[17]刘春梅.农村养老资源供给及模式研究[D].陕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3:1-15.
[18]周莹,梁鸿.中国农村传统家庭养老保障模式不可持续性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06(05):107-110.
[19]陈芳,方长春.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与出路:欠发达地区农村养老模式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4(1):99-106.
[20]孙岩,我国农村新型家庭养老模式研究[D].河北:河北经贸大学,2015:25-40.
[21]余秋华,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解析[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06,51-55.
[22]慈勤英.家庭养老:农村养老不可能完成的认为[J].武汉大学学报,2016(2):12-15.
[23]赵倩倩.山东农村家庭养老现状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2012:10-15.
[24]钟涨宝,杨柳.转型期农村家庭养老困境解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6(05):22-28.
[25]何玉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家庭养老问题思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6):93-95.
[26]刘培培.河南省农村养老问题研究—基于驻马店农村的实地调研[D].河南:河南大学,2014:41-42.
[27]马亚静.企业式自我养老,农村社会保障的补充形式[J].开放导报,2006(6):63-64.
[28]袁春英,薛兴利,范毅.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理性选择—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养老相结合[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2(06):431-433.
[29]杨政怡.替代或互补:群体分异视角下新农保与农村家庭养老的互动机制—来自全国五省的农村调查数据[J].公共管理学报,2016(1):117-127.
[30]王红,曾富生.传统农村家庭养老运行的基础与变迁分析[J].学术交流,2012(10):130-133.
[31]张川川,陈斌开.“社会养老”能够替代“家庭养老”?—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4(11):102-115.
[32]徐勤,郭平.老龄化社会提倡老年人自立[J].人口学刊,1999(3):57-59.
(责任编辑:王佩)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Aged Providing
WANG Zhao-xia, CAO Wan-li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China)
Under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aging background, the traditional family pension faces various challenges and it has been difficult to bear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rural elderly care. Self support, social and community pension mode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rural area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oundation, basic statu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family pension and believes rural family pension will remain the major mode of rural old-aged support for a long time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or its further improvement to meet the pension needs of the aged in rural areas.
rural pension; family pension; self pension; social pension
1673-2103(2017)03-0041-07
2017-03-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部级项目(SC14B123)
王朝霞(1990 -),女,河南新乡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养老保障。曹婉莉(1980-),女,四川南充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养老保障。
F328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