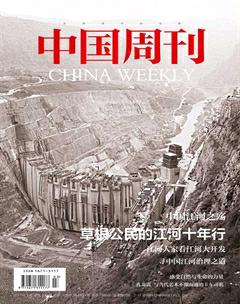江河人家看江河大开发
江河边的人家,或许一辈、或许数辈、或许祖辈生活在江河边上,饮江中之水、耕江边之地、育江边子孙。“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江水悠悠,大江大河是江河人家血液中流淌的根基,承载着千百年来对美好日子最坚定的渴望。
2006年,“江河十年行”在第一次出行的途中,随机走进了江河边十户普通的人家。之后,每年都来探访。十年过去,他们中有的还生活在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上,有的因水电大坝的修筑不得不离乡背井。修坝者一再强调,兴修水电是为了帮助当地人脱贫。“江河十年行”用十年的行走,见证了“无坝”和“有坝”人家的生活,他们的与建坝者的预期完全不同的生活。十年,只是浩瀚岁月的沧海一粟,但十年间,这十户人家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他们与江河之间的关系与命运,却是中华大地翻天巨变的真实写照。
江河变迁,人家迁移,谁来驻守江河血脉?
“没什么发愁的事。”
——陈明 汉族 四川都江堰紫坪铺水库移民
2006年,紫坪铺水库边,陈明家的小饭馆和小商店才开张,一群人坐在小餐馆的外面边喝茶边打牌。从那儿走过的 “江河十年行”队伍,感受着成都人的悠闲,于是就走进了他家。这一进,就进了十年。
陈明家所在的这个村,既是水库移民,也是2008年5.12地震受了大灾的人家。2007年,陈明的饭馆和商店没生意,他和同村人一样,外出打工;2008年,因不习惯外面生活,陈明回到村子,房屋在地震中受损;2009年,当地政府拆旧房盖新房,陈明家亦被拆;2010年,因盖新房,陈明家中生活困难;2011年,陈明家没有搬进新村,他和村书记、村长对换房子,重新做起了生意;2013年,除了有个小卖部,陈明还买了两个麻将桌,一个月加上他扫街挣的钱,说是能有3000多块的收入;2014年,靠小店为生,新添两孙辈,儿媳在地震遗址卖小吃。
移民后,没有了土地,原有土地没有得到补偿,占了农民那么多土地的房地产项目也迟迟不见开工。村里有的移民还在找门路,反映征地款标准低的问题。陈明没有参加上访,他说如果能够补发,也会有我的;如果不行,还是这样过日子。
“搬到外头去,我们就不同意去。我们的地在山林里,种苞谷、粮食。人搬出去,太远了,野兽来了,野猪来了吃我们种的粮食,我们就没有收成了。”
——荣东江措 藏族 四川康定木格措人家
2003年木格措要修水库,经媒体和民间环保组织呼吁,2006年当地政府发布木格措停建大坝发展绿色经济的消息。当时,荣东江措骄傲地和记者们说,“我小时这里是什么样,现在这里还是什么样。”但当时在场12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无一例外说,小时侯自己家乡的水是清澈的,现在干了,脏了,没有了。
2007年,荣东江措乐观地期待政府修路后,能给自家的农家乐带来更多的游客;2008年,当地政府把木格措景区承包给张家界私人老板,老人家被通知要搬出景区;2010年,老人和当地承包部门发生冲突,犯病住进医院;2011年,荣东江措二儿子两口子辞掉了珠江的工作,想着回家大发展。回来后,却遭到不让扩大房子开旅馆的现实和被迫搬迁的窘境;2013年,再次请荣东江措老人带“江河十年行”去书记家聊聊,可老人不肯去了,他认为“江河十年行”来了那么多次,既帮不上他家什么忙也没能给村上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很失望;2015年,老人说现在养老保险、低保,每个月到时间你去取就可以了,政策好。
“都十年了,家门口的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修好。当地人要走电站的路,可以办手续,但很麻烦。”
——代兴民 汉族 雅砻江锦屏水电站旁人家
代兴民,一个当过民办教师的农民,生活因锦屏电站的修建起起落落,虽然自豪于自己的学生有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但他也安心于现在养猪、种青椒的普通村民的日子。
2006年,靠一个小卖部和跑运输维持生计,代兴民希望家门口的水电工程可以多找些活路,还专门买了一辆大卡车准备拉活儿,后来还是把大卡车卖掉了,因为工地多用自己带来的人,不用当地人。2008年,采金把江里挖得一塌胡涂,挖沙還导致江边农民的地被淹没,那可是全村的口粮地。养蚕的桑叶被过往大卡车扬起的烟尘覆盖,弄得蚕都不吃了,蚕不能养了。2011年,路太坏,用水困难。代兴民家一年收入有五万多人民币,但开支增大了,老婆一个月要800块钱的药费,还要交纳电费等。2015年,小卖部还开着,原来小卖部可以维持家里两三个人的生活,现在不行了。
“我当年的希望,靠着二滩电站的建设,已经都实现了!”
——张宗洲 汉族 四川二滩水电移民
张宗洲是农民,从二滩电站筹备起,才开始当上了小包工头。在十来年的时间里,花了120万修建了四层楼高的漂亮的张府酒店,完全是靠他自己赚的钱修起来的,一分贷款也没用。2006年,张宗洲形容自己今天的生活到也实在:“一天三打扮,一嘴肉来一嘴饭”。他说的一天三打扮,形容的是有衣可穿,可换。2007年,张忠洲的老婆和女婿在经营着他们家花120万元盖起的餐馆。每年的毛收入能在五、六十万元。家里又从别人手里买下一个矿。张宗洲和儿子一块在忙乎矿上的事,发展刚开始。2008年,张宗洲家的饭馆,这几年生意一直都不错。只是今年以来,山上的水越来越少了,他们开始担心,没有了山泉,以后饭馆怎么开。而山泉水的断流,有施工的原因,也有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2011年,酒店完全交给了女婿,张宗洲本人一直在他家开的矿上,但全球经济危机也牵连到了他们这么偏僻的小饭馆。
“祖先选的地方,就是好地方。”
——李家珍 汉族 长江第一湾石鼓镇
李家珍祖上从内地到石鼓镇当巡抚,爷爷和纳西族的奶奶结婚。李家珍的母亲又是纳西族,而老李自己找的媳妇还是纳西族。难怪他称,我有1/4的纳西血统,到我儿子辈就是1/2的纳西血统。我的女儿嫁给了纳西族,孙儿也是和纳西族通婚,我们家基本被纳西族同化了。
2006年,李家珍家的庭院里挂满了黄黄的老玉米。院子里养了一棚兰花,婷婷玉立,散发着淡淡的幽香。李玉珍老人得意地向记者们介绍着那一盆盆兰花的价钱。粗粗地算了算,竟有十多万元。2009年,李家珍和老伴又养了7头猪,30多只鸡,还打理耕地和果树,每年的收成小麦700斤,稻谷1000斤,基本上用于自家食用。果树主要是樱桃,能产2600斤,按市价四元钱计算,至少有一万元的收入。这样下来,加上卖猪的费用,全家的年收入,能达到10万元左右。2011年,李家珍年纪大了,不常去村里和人一起演奏的纳西古乐了,可是下地回来拉上一首古曲是他日常生活的内容之一。他家猪满圈、鸡满院、羊撒欢,有着吃不完的粮食和蔬菜以外,家里的墙上还多了一片炭写的短诗,细细看来,原来是一段赞扬鲁迅的诗,李家珍说是为教育孙子的。2013年底李家珍因癌症去世。
“希望政府对我们这些移民的问题给予解决。”
——刘玉花 汉族 澜沧江小湾电站水库移民
2006年,刘玉花听说要让他们村移民,村里人心惶惶。2008年,玉花说:政府说他们要是不搬就要让他们“漂汤圆”(就是家全淹了的意思)。老房子拆只折300块钱一平方米,新房子建要500元一平方米,差价五万块钱,玉花只好卖粮、卖腊肉加上还没长大的猪都用于新房子修建。2009年,搬到新村,地没有分下来,因会做黄焖鸡玉花开个小饭馆养家糊口;2010年,因生活压力玉花晕倒去村医务室输液;2011年,不能种稻米,改种烟叶却不会晾晒致发霉;2012年改种甘蔗,大旱;2013年,前几年没有分到地,没有分到田,现在都有了。改种火龙果,完全没有种过的他们,还加入了火龙果协会。小饭馆生意并不好,但维持家用也将就了。2014年,刘玉花认为搬新村虽然房子质量有问题有好多裂缝,但是过日子特别是小孩上学看病比以前还是方便了。
“在农村,院子是什么,是儿子娶媳妇办酒席的地方,现在没有了。”
——何学文 傈僳族 怒江小沙坝移民
怒江上的水电项目未批先建,何学文于2007年搬到移民新村。2008年,何学文说他家现在除了不能再养牲畜,原来有的60多棵芒果树、10多丛竹子、20多窝芭蕉、10棵石榴、4窝咖啡、8棵桃子、600多棵大桐油树、200多棵小桐油树、600多棵果皮树、5棵木棉花、10棵树瓜随着水库的修建也将被占用和淹没。现在虽然还没有淹,可果树都在老村,搬到新村的他们无力再去看管那些果树。因为六库水电站还没有最后批准,虽然小沙坝的人被当成移民搬迁了,关于水田和旱地、菜地,村民们和政府签的还是临时补偿的协议。何大爹给记者看的对他家的补偿,让我们真的不知这两年他们一大家子人靠这些钱是怎么过的。2011年,现在院子小得不能种树,甚至不能养猪养牛。以前喝自家牛挤的奶,现在早上儿媳要出去扫马路挣钱,80多岁的何大爹要自己去买袋装奶,老人说不好喝。2012年,何大爹说:电站还没有修,国家给水电移民一个月50块钱,一年600塊,可是只给了他们一年就不给了。2014年,“江河十年行”与当了村领导的何学文的儿子发生了正面冲突,何学文的儿子报了警,“江河十年行”未采访到。
“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真不想搬迁。”
——李战友 纳西族 怒江人家
2007年,李战友正在申请开个家庭旅馆,房子已经建起来了。他说政府给了他们村一百多头牛,谁家想养就可以养。但是外面来的牛在这里怎么养都养不肥,瘦得很,大家认为一定是牛水土不服。靠种玉米、种水稻,唱歌跳舞、卖米酒,老李说,家里的日子过得去。2008年,有2亩水田 、3亩旱地,主要种水稻和玉米。收获的粮食用于自家吃。养了 9头猪,都是小猪。此外家里还有4亩果树、4亩林地,属于自留林,还不能收获。真正结果的是十几棵核桃树,今年没有卖都自己吃了。家庭旅馆根据旅游季节阶段性的收入,大概一年能收 2000~3000元。2009年,因为不能洗澡,家里的小旅馆生意不好,再加上镇上盖了几家大的旅馆,抢走了不少客人。2010年,板栗几乎不结果实,核桃长得也没有往年好,找不出其他原因。本来核桃和板栗也是家里的收入,现在不行了。2011年,核桃不卖,自己吃;柿子不卖,自己吃;牛不卖杀了自己吃;猪不卖,自己吃。玉米给猪吃。完全自给自足。2013年,李战友因肺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