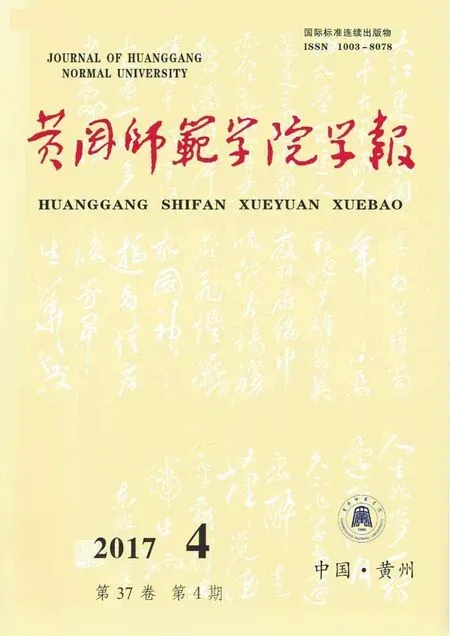现代诗人的传统情结变奏
——论郑愁予思乡恋国诗
秦 剑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现代诗人的传统情结变奏
——论郑愁予思乡恋国诗
秦 剑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郑愁予作为台湾现代派的代表诗人,在其迁移及远行的旅途中创作了大量的表现思乡和恋国的诗歌。这类诗歌尽管在外在形式上呈现出不同的美学风范,但在时尚的外衣下包裹着的却是浓郁的古典韵味,其骨子里透出的是传统情结,并以其传统情结或隐或现地演绎着一个文化放逐者对家的思念、对根的皈依。
郑愁予;思乡恋国;家国意识;根的皈依
台湾现代诗坛虽然名家辈出,但郑愁予依然卓越出众。“他自觉的陶洗,剥离和熔铸古典诗美积淀中有生命力的部分……由此生成的‘愁予风’,确已成为现代诗歌感应古典辉煌的代表形式:现代的胚胎,古典的清釉;既写出了现代中国人(至少是作为文化放逐者群族的中国人)的现代感,又将这种现代感写得如此中国化和东方意味。”[1]也就是说,郑愁予的诗歌在时尚的外衣下包裹着的却是浓郁的古典韵味,其骨子里透出的是传统情结,并以其传统情结或隐或现地演绎着一个文化放逐者对家的思念、对根的皈依。
传统情结又可以称为古典情结,是指受过古典文学的熏陶,对四书五经、文赋、唐诗宋词及元曲等中国古典文学有过学习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古典文学修养的作家,在进行创作时追求古典艺术,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民族文化靠拢,对古人的思想和情感,艺术技巧等等各方面的继承。因此,古典情结的现代表现形态可谓多姿多彩:喜爱古典服饰、运用古典设计、把玩古代器物是古典情结;眷恋戏曲舞台、痴迷诗词文赋也是古典情结,等等。但种种的外在形态内化的却总是一个不变的情怀即源自于民族伦理情感传统的对家的思念、对根的皈依。这也便形成了中国传统诗歌千古不变的一个主题——乡愁和爱国。此主题跨越千年一直延续至今,绵延到台湾诗人郑愁予的情怀中。
一般意义上,家是一种生活,国是一个概念;而在深刻的意义上,家是一种思念,国是一种想念。因此,只有远行者才有对家和对国的殷切思念,也只有远行者才有深刻意义上的家和国。郑愁予童年随戎马倥偬的父亲辗转大江南北;少年随母亲迁徙于内陆各地,逃避战乱;青年未婚时长期在基隆码头就职,终日与大海为伴。这三个时期的他甚至没有一般意义上“家”的生活,漂泊不定的际遇使他始终游离在“家”之外。而自1949年开始,离开故土大陆,到台湾生活,一道窄窄的海峡又将他彻底地隔离在“家”之外。中年移居海外之后,他成了“国”的真正的远行者。尽管在地域上与家和国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是在感情上却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家和国的意义。也正是这种日益充盈的对家和国的思念,直接催生了诗人一系列的思乡恋国的诗歌。应该说,郑愁予的思乡恋国诗大多都是主题先行,而创作过程只是去提炼并建构最能传达他那浓郁的思乡恋国情感的意象。尽管如此,他的诗作仍以优美、洒脱、富有抒情韵味著称,且意象多变,温柔华美,自成风格。
一
初识诗人郑愁予,一般是从《错误》开始。那踏碎无奈而美丽错误的“达达的马蹄声”、 那凄迷、朦胧、缱绻的意境、那容颜娇美亦如莲花般开落的女子的神情……不知让多少读者为之神牵梦萦!因此,《错误》普遍被认为是“现代抒情诗的绝唱”,评论者们也一致认为这是一首用现代手法写闺怨的诗歌。尽管诗歌的主体部分的确描写了一位在春闺中等待归人的多情女子,但笔者认为仅仅将此诗看做闺怨诗或爱情诗还是有失偏颇。
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作家的创作无疑与其所处境遇及特定心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郑愁予《错误》一诗创作于1954年,正值旅居台湾之初。而包括郑愁予在内的初到台湾的大陆人的处境及心境如何呢?我们从作家白先勇的系列小说便不难体会:那些新贵的太太和夫人们念念不忘的是苏州的丝绸刺绣、大前门的点心、从前的戏院;那些旧日的官僚想念的仍是自己昔日的风光;舞女金大班怎么也挥之不去的是自己曾有的辉煌、聪明的尹雪艳更是明白生意兴隆还得是上海名菜就着绍兴花雕……可见那个时代被迫迁移到台湾的人,身在台湾却没有归属感,更难产生认同感。而这种强烈的“无根意识”直接弥漫的是台湾社会普遍盛行的“漂泊感”及对家国的依恋,因此,“回乡”便成为了漂泊者们强烈的现实诉求。然而,当强烈的“回乡”诉求遭遇到现实政治语境又如何呢?那只能是“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余光中《乡愁》)的无奈。
作为一个敏于现实的诗人,郑愁予自然比一般人有更深刻的感受。应该说,《错误》一诗正是诗人的诗才与“对家的思念、对根的皈依”之情的凝结,其主旨也自然超越了“闺怨”而变得更为隐晦而空灵。由于象征与隐喻的运用,诗歌中“过客”和“女子”的身份变得多重起来。“过客”象征的是漂泊在外的台湾及台湾人,“女子”则象征的是祖国大陆及大陆亲人。因此,诗歌《错误》隐晦而深沉地表达出了游子对祖国家园回归的期盼。其实,骨子里有着传统情结的郑愁予却以“错误”一词为诗题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错误”是一个观念性很强的逻辑判断,以其为诗题不但有违中国传统诗歌诗题习惯,而且也对诗美有很大的损害。显然,这一“错误”的出现是诗人有意为之,那么意欲为何呢?我想它不但暗示了诗中所描述的一切都是错误,甚至也含蓄地提醒着读者如果简单地将之理解成爱情诗将是一个错误。也就是说,诗人借“闺怨”这一传统诗题观念性地暗示了祖国分离、骨肉难聚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错误。正是于此意义上,我们认为诗人郑愁予以《错误》为代表的思乡恋国诗,由于特定语境及心境的注入而超越了一般的“家园意识”,拓展为宽广的“家国意识”,深刻地表达出了台湾人,特别是台湾文化人对故里、文化母体的强烈回归感。又因为诗歌《错误》借助象征和暗示来传达诗人的情思、主旨,所以诗歌仍旧呈现出古典诗歌特有的含蓄隽永、空谷幽兰之美。
虽然“感情浓烈时,不宜作诗”,但是当无边的不可抑制的感情汹涌而来时,诗人的情思亦如江河决堤,一泻千里。在诗人郑愁予的思乡恋国诗里,“对家的思念、对根的皈依”的诗情有时如《错误》般冷静、优美,有时也会大气磅礴、豪情汹涌而呈现出一种豪放的美。
郑愁予的长诗《衣钵》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诗人借助心目中的“革命” 领袖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和人生理想,诗情可谓热烈而直露。“啊 革命 革命 /好一个美的让人献身的概念啊/同志 同志 这是多么震响的称呼啊/统一 统一 这是和平的第一线”,这里,诗人不但让“革命”“同志”“统一”这样的政治语汇直接入诗,而且故意以“黑体”(诗歌发表时三个语汇以黑体标注)示人,其澎湃的诗情、直白的诗意自然不言而喻。应该说,在战争远去了的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在台湾与大陆分裂的历史事实面前,诗人自然将自己的一片爱国热情寄托在海峡两岸统一的主题上来。非但如此,“统一”既是当年“革命” “同志”那一代人的伟大志愿,也是今天台湾民众对“家的思念、对根的皈依”情感的当然选择。
在《春之组曲》中,诗人郑愁予的“家国意识”更是直白而热烈得近乎歇斯底里。“忍不住把爱挖了根奉献/就这样移植给祖国”,这里,我们不难感受到诗人强烈的爱国热情——生命有多长,对祖国的思恋便有多长,必要时拿生命奉献也在所不惜!这是何等让人敬仰的一份爱国痴情啊!在这样一份厚重而执着的情感面前,读者几乎忘记了是在读诗,但仍然能强烈地感受到诗歌带给我们的那份壮美。
应该说,诗人郑愁予的思乡恋国诗,尽管抒情方式各有不同,但不同的仅仅是诗歌的外形式结构,而不变的却是诗人那份对“家国意识”的守望。
二
我们已经知道,“对家的思念、对根的皈依”一直是郑愁予诗歌不懈弹奏的旋律。同时,由于禅宗对诗人诗歌的进入,又使其诗歌意境显得更加飘逸而深沉。
文学自先秦以来,便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积淀,是一种认识世界、理解生活的方式;再有就是作家自身的宗教倾向或者宗教信仰,会影响到他的题材选择和文化立场。”[2]因此,“宗教不管是基督教,还是非基督教,不管是被肯定的,还是有争议的宗教——都一再成为文学创作的永不枯竭的源泉”。[3]特别是唐宋以后,“以禅入诗”更是成为风尚,王维便是突出的代表。有着传统情结的诗人郑愁予自然深知宗教与诗歌都是对人生的关怀,而且由于禅宗的进入会给诗歌的意境带来空灵、飘逸而深沉的美。那么,当诗人郑愁予那强烈的思乡恋国的情感遭遇到虚无的禅宗情怀,其诗歌又呈现出怎样的美学特征呢?
诗歌《佛外缘》无疑是郑愁予“以禅入诗”的经典之作。如果单从诗歌表层上来看,《佛外缘》似乎只是一首以佛为题讲述佛外之缘的清幽、宁静的宗禅诗歌。在诗歌中诗人首先建构了两组表面对立而内在诉求统一的意象群:一组是由佛教圣物“舍粒子”、“菩提树”、“念珠”等构成的一个神圣的意象群;一组是用 “一阴一阳两尊肉身”、“心魔”、“情孽”等构成的反佛教教义的意象群。这两组意象群的并置,显然是有意为之。诗人试图在相互对立的不和谐中,来传达“佛”与“佛外”的对抗,“佛外”对“佛”的背叛。我们知道,“佛”代表的是至尊无上的“道”,是佛教徒追求的终极境界,它要求人们通过克制各种世俗的欲念以达到无欲无求的境界。而“佛外”却用“一阴一阳两尊肉身,默数着念珠对坐千古”来表达对泯灭人的本能欲望而刻意追求佛圣的反叛。因为在“佛外”看来,成佛无需刻意规避俗世的爱欲、诱惑,而应让其顺其自然并由有而化为无,从而达到由凡而入圣。因此,“佛外”在其精神指归上与“佛”的追求不但不矛盾,反而高度契合,“佛外”反叛的也只是“佛”那为达终极目标所采取的手段而已。正是如此意义上,诗歌《佛外缘》在主旨上达到了神性与人性的高度统一。
然而,当我们撩开佛衣进入诗歌的深层次,又会发现怎样的别有洞天呢?诗歌一开头便明确交代“她走进来说:我停留/只能亥时到子时”, 亥时到子时就是从晚上九点到第二天凌晨一点,这正是生理学认为的人由浅层睡眠进入深层睡眠的时间。也就是说,“她”是走进了诗人的梦中,而诗歌《佛外缘》实则是诗人的一次虚幻梦境的记录。“你来赠我一百零八粒舍粒子/说是前生火花的相思骨/又用菩提树年轮的心线/串成时间绵替的念珠”,“那舍利子已化入我的脏腑心魂”,试想,是什么竟有那么大的魔力能让作为海外游子的诗人郑愁予夜不成寐、魂牵梦萦呢?无疑就是诗人那痴痴守望的“家国意识”并由此挥之不去的那份对祖国和故乡绵延不绝的眷恋之情。但由于现实语境的原因,诗人曾拥有过的大陆生活只能是恍如隔世的“前生”而潜藏在记忆里、停留在梦境里;诗人的那份痴痴的眷恋也只能化为痛彻心扉的“相思骨”。可尽管如此,诗人却从没放弃,而是放任这份对国对家的思念深入骨髓、流入血脉。因此,诗歌《佛外缘》表达的是骨肉相连,血浓于水的深沉的爱国之情。同时,由于“禅宗”的入诗不但深远了诗歌的意境,更将诗人的那份滑入骨髓的“相思”推至决绝、极致。
应该说,诗歌《佛外缘》由于将宗禅与爱国情思的勾连贯通,不但诗歌主题的表达更加深沉,并呈现出幽深曲折之美,而且宗禅的神秘深邃也使得诗歌意境愈加飘逸而隽永。“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所有的海外游子尽管为了生活忙忙碌碌、浪迹天涯,但从未改变的仍旧是那份“对家的思恋、对根的皈依”。诗人郑愁予正是由于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情绪,并借助自身切肤的体验而创作了系列思乡恋国的诗歌。
三
众所周知,任何作家的创作都必须依托其丰富而深厚的生活体验。因此,对于经历了被迫迁移台湾、饱受思乡之苦的诗人郑愁予来说,中年后旅居海外的异域生活对其创作显然是如虎添翼。因为,新的人生经验、新的生活的刺激、新的苦闷与挑战都将丰富其作品的色彩,并直逼多维的生命内涵。当然,中西文化的冲突,传统文化的缺席,母语环境的丧失无疑会给每一个旅居者带来思想和精神的双重压力,并常常陷入无家、无国、无根的茫然。而这样的变化自然会让其时常处在一种时而冲动、时而迷惘、时而信心饱满、又时而空虚无依的境地。应该说,诗人郑愁予对这种心境远比一般的旅居者有着更为深切的体验。由于参加保钓运动而被吊销护照,其政治身份变得尴尬而模糊,看似有国有家而实则无国无家。因此,对于旅居地的他乡而言,诗人郑愁予仅仅是一个“过客”,并由此产生一种强烈的“不知今宵酒醒何处”般茫然而无助的“孤儿情结”。 而难言的孤独和身份的迷失自然常常衍生出一种难言的隐痛,伴之而来的便是在人生坐标之上找不到位置的大孤独和大寂寞,于是肉体与精神必将承受着双重的放逐压力。
一般来说,漂泊者的精神的空虚及无法寄托大都会产生一种对于母体文化的依赖心理,并不自觉地向自己的祖国靠拢,亦愈发地的对故土亲人的思念。而对于饱尝由于文化母体分离而触发的痛彻骨髓的乡愁之感的诗人来说,对文化母体的依赖心理自然要更为强烈一些。于是,异乡体验与故乡意识的深刻交融,漂泊欲念与回归意识的相辅相成,这一永远充满魅力的人生悖论让诗人品砸不尽,进而化为诗品既慰藉着自己,也温暖着读者。
应该说,正是基于上述深刻的心理体验,郑愁予创作的思乡恋国诗都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贯穿始终,那便是对于传统文化、母体文化的自觉不自觉的承袭。用现代人的感受方式处理传统诗歌题材、意境,用传统的诗歌语言表达现代人的情绪、心境成为了郑愁予思乡恋国诗歌的显著特色。因此,他是“西化”的台湾诗坛中的“中国的中国诗人”(杨牧语)。[4]329也就是说他的现代诗歌如古代诗歌一样的典雅,除了执着于传统离人乡愁题材之外,还在诗歌诸多外形式结构上烙上了传统的印记:一是在诗歌意象的选择和意境的营造过程中刻意向中国传统诗歌靠拢,有时甚至直接选择“窗帏”、“流苏”、“诗锦”、“箭眼”等古典意象作为其诗歌的轴心意象;二是在诗歌语言的选择及运用上极具中国传统诗歌语言的特色,如学习古文运用“恕”、“欲”、“且”等单音节词汇来增强诗歌的节奏感、对传统诗歌经典句式的直接使用或对古典诗句的灵活化用等现象在其诗歌中也屡见不鲜;三是其诗歌中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出现,如用“锦帕”作为定情信物来表明对爱情的忠贞(《小诗锦》)、中国传统节日或时辰“惊蛰”“清明”“亥时”“子时”等直接纳入诗中、“舍利子”“念珠”“坐化”“心魔”等本土佛家语汇的大量运用,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如同标签般昭示着郑愁予及郑愁予诗歌的“中国化和东方意味”,也深刻地体现着诗人对传统文化、母体文化强烈的认同感。
总之,郑愁予作为一位海外诗人,运用诗才将自己对家国的依恋和漂泊在外的切身感受用诗歌“记录”下来,化成了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思乡恋国诗。这些诗歌借助极具“中国化和东方意味”而又不失现代性的外形式结构,营造了时而含蓄隽永,时而空灵飘逸,时而激越豪放的意境,既深刻地表达了诗人郑愁予对“家国意识”的守望,也表现了远行者“对家的思念、对根的皈依”的强烈的现实诉求。所以,郑愁予诗歌内蕴之丰富和深邃是其他作家所无法比拟的,这无疑奠定了他在海外华人诗坛的重要地位,也使他的诗歌作品成为了海外华文中的“明珠”和“奇葩”。
[1]沈奇.美丽的错为——郑愁予论.台湾诗人散论.台北:尔雅出版社,1996:251.
[2]张艳梅.赵德发宗教题材小说论[J].时代文学,2012(05,上半月)213-214.
[3]K.J.库舍尔.神话学与现代文艺思想[M].三联出版社,1995:55.
[4]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29.
责任编辑 张吉兵
2017-03-14
10.3969/j.issn.1003-8078.2017.04.12
秦剑(1966-),男,湖北红安人,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I206.7
A
1003-8078(2017)04-004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