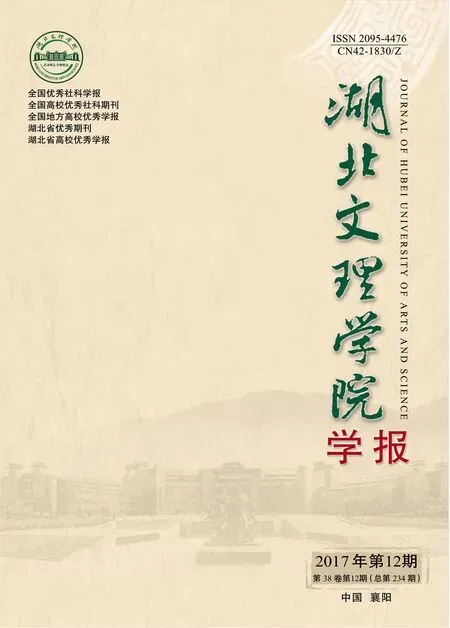论鄂西土家族织锦工艺的生态美学特征
刘精科
(1.湖北文理学院 美术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2.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论鄂西土家族织锦工艺的生态美学特征
刘精科1,2
(1.湖北文理学院 美术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2.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武陵山腹地的鄂西土家族传统织锦工艺具有悠久的历史,不仅满足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需求,而且承载着独特的心理倾向、文化观念和审美趣味等内容。鄂西土家族织锦工艺对于自然的依赖、自由率真的创作意识以及重建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体现出鲜明的生态美学特征,蕴含着丰富的生存智慧。
鄂西土家族;织锦工艺;少数民族文化
J01
A
2095-4476(2017)12-0068-04
2017-09-28;
2017-12-06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5Q198)
刘精科(1979— ),男,湖北襄阳人,湖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讲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艺术美学。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文化在丰富中华文化内涵,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以及向心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土家族作为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出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织锦工艺是土家族得到完整传承的手工纺织技艺,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鄂西土家族主要聚住在湖北西南部的武陵山腹地,这是巴文化、楚文化、蜀文化以及武陵先民土著文化的交汇地,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鄂西土家族织锦工艺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是鄂西土家族群众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宗教观念以及审美趣味等的集中体现。鄂西土家族传统的织锦工艺体现出对自然的依赖,具有鲜明的自由率真的创作意识,要求重建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因而具有鲜明的生态美学特征。
一、从材料来源来看,鄂西土家族织锦工艺是一种真正的“自然生态艺术”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频繁出现,人们深刻意识到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有学者指出,“对自然环境状况的分析,特别是作为诸因素相互影响综合体的生态系统的平衡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生产力发展所达到的新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其应对自然承担义务的认识以及对社会生产系统界限的认识。”[1]因此,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类社会必须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和谐。生态美学的出现,实际上是人们对于自然灾害和生存危机的一种反思,是对自然与人类之间依存关系的深刻体认,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和审美共感”,努力“唤起人与自然的生命之间的共鸣”。[2]从生态美学对于自然的认识以及手工艺的材料来源来看,鄂西土家族织锦工艺是一种真正的自然生态艺术。
首先,织锦工艺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材料及相应的自然环境。材料是传统手工艺制作的重要基础。很多传统手工艺使用的是直接来源于自然界的材料,这些材料总是依赖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鄂西土家族位于武陵山腹地,这里峡谷众多,气候温暖湿润,境内有清江等多处水系,动植物等各类资源非常丰富。同时,鄂西武陵山地区是巴文化、楚文化以及蜀文化等不同文化的交汇之处,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使得鄂西土家族文化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并且为土家族织锦工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当地的织锦工艺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独特的民俗文化使得织锦工艺的造型与装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寓意。有学者指出,“土家族人长期生活在川、鄂、湘、黔各省的交界地域,具有粗旷、忠厚、淳朴、豪爽的性格和气质。这种性格和气质,不仅体现在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活动中,同时也反映在传统的土家民族织锦艺术里。”[3]因此,特定自然环境所提供的材料及相应的制作工艺,对当地土家族的织锦工艺产生出重要影响。同时,土家织锦生产使用的是传统的手工挑花技艺,以棉线为经,以丝线或者棉线为纬,用手工织成具有几何图案的艺术品,体现出鲜明的自然质朴等特征。
其次,织锦工艺主要是从自然界中直接获取材料,并且充分发挥出材料自身的独特属性。在手工艺生产中,人们往往会从自然界中选取合适的材料,借助于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和一定的技术手段,制作出满足于人们生产生活所需要的手工艺品。这些手工艺人“对材料的认识结构是在长期的劳动中形成的,这是一个既充满人文观念、情感和伦理色彩,又在科学理性意识中反复陶冶的认识结构。”[4]在鄂西土家族生活的武陵山区,由于动植物的种类众多,因此,土家织锦用于染织的多为植物染料、少数动物以及矿物等天然染料。土家人用植物的果实、花朵以及枝叶制作成染料,使得织锦图案具有丰富的色彩,产生出独特的视觉效果。例如,土家族织锦中的黑色染料主要是由马桑树叶制成的,蓝色染料主要来自于竹叶菜梗或者蓝靛。土家人用动植物以及矿物制作染料,色彩比较稳重、沉着,具有浑厚古朴的韵味。更重要的是,在生态文明观念的影响下,人们深刻认识到,从自然界获取的染料,不仅能够有效降低环境污染,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在色彩方面,土家织锦沿袭着“尚黑忌白”的观念。由于土家织锦的染料是用自然矿植物制成的,黑色等色彩比较厚重,在日常生活中较为耐污,在长期的传承中,土家族人喜欢黑色等颜色,而白色往往与灾祸相联系,土家人一般用在丧祭等场合。伴随着生态美学观念日渐深入人心,鄂西土家族织锦工艺保持材料自然属性的技艺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最后,织锦工艺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推动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存,这是生态美学的一个重要主张。在鄂西土家族织锦的生产过程中,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织锦工艺生产不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造成明显影响。可以说,鄂西土家族织锦工艺的生产及制作过程是一种真正的“绿色生产”,始终与自然环境之间保持一种友好相处的关系。例如,鄂西土家族的织锦是人们使用来自于自然界的材料进行加工而制作成的,不仅线是土家族人自己纺织的,而且色彩和图案也是人们使用天然的染料加工制成的。因此,鄂西土家族的织锦工艺生产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同时,提高了人们在使用织锦制品中的舒适感。对植物材料的巧妙应用已经成为鄂西土家族织锦工艺的重要特征之一。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手工艺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精神相通。在很多生态学者看来,自然不仅是一个生命的存在,而且还具有独特的精神意义和审美价值。中国古人强调“天人合一”,这种观点“不仅是人与自然在客观物质层面的和谐,更为重要的是人与自然精神层面的和谐。”[5]鄂西土家族织锦的图案非常广泛,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织锦中出现的植物图案,不仅是对人们现实生活场景及内容的重要揭示,而且传达出土家人强烈的生命意识,蕴含着非常独特的审美体验。还有一些符号与图案,也与鄂西土家族人的民间信仰等密切相关,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和文化涵义。
二、从创作方式来看,鄂西土家族织锦工艺具有自由率真的特点
在很多生态主义学者们看来,现代工业社会对于理性思考和科学算计等的苛求,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技术理性的张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显著提升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的偏执发展必然会使人与自然之间处于对立状态并且引发生态危机。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指出,在工业文明时代,片面发展起来的技术手段,“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6]工业文明对于科学技术的崇拜,对于人的主导地位的推重,显然并没有给人类社会带来他们所期待的美好生活愿景,反而使人们遭受到一系列环境灾难以及生存危机的困扰。甚至在工业社会中“理性”“科学”等观念的影响下,艺术也开始重视对形式、结构、语法以及逻辑等进行科学研究和理性分析。由于人们对科学、逻辑以及艺术形式等因素的片面追求,艺术创作中的灵感、无意识等受到抑制,很多学者发出艺术走向终结的感叹。因此,生态美学要求人类活动摆脱科学以及理性等因素的束缚,凸显经验感觉等感性因素的积极作用。而少数民族手工艺的制作过程,则体现出生态美学的这种主张。
在工业化时代,由于人们对于生产的规范化以及工艺的标准化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单件制作”的手工艺生产无法适应市场的发展需要,因此,日益陷入衰落的窘境。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现代社会中,传统手工艺仍然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价值。传统手工艺承载着的丰富情感与文化内涵不仅能够满足人们追求自由与个性化的心理需求,有效避免大机器生产所造成的单调、冷漠以及缺乏人情味等弊病,而且手工艺生产中传达出的自然、随意以及优雅等品质是大机器生产所无法实现的。
首先,手工艺人在制作过程中处于身心合一的状态。在工业文明时代,工人受到技术的压制,成为机器生产流程里重复劳动的工具,丧失了自由表达的能力。有学者指出,在工业文明时代,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人们被迫去机械化地从事简单的工作,“强迫他们否定自己的人性并像机器人那样做着重复简单的劳动。人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不能表达他们自己”[7]。工业化时代的生产方式削弱了人们自由创造的能力,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使人类社会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而鄂西土家族织锦主要是由土家族女性完成的,在制作的过程中,“他们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均是随意的、概念的表现,或是规整的概括,或是装饰的均衡,或是模糊的抽象,或是大胆的夸张。只要他们认为好看的、美的,就都是合情合理的,这是一种可贵的主体意识”[8]。由于土家族织锦最初主要用于姑娘陪嫁品、情侣间定情信物以及服饰等,因此,土家族女性在制作织锦的过程中,处于身心合一的自由状态,她们用自然界的花鸟虫鱼以及各种想象中的图案纹样对织锦进行装饰,使得她们的手工艺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艺术性。
其次,手工艺人的经验感觉等因素在手工艺制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经过长期的生活观察和制作实践,土家族女性能够准确把握织锦工艺的创作规律,她们能够灵活处理织品结构以及图案中的平衡、参差、疏密等各种关系,增强了织锦的生活情趣和艺术感染力。有学者指出,传统手工艺的“造型不受对表达意义无任何作用的客观自然逻辑的约束,它是按表意的目的来造型,以超出自然客观逻辑的自由,随心所欲的移动空间,超越自然,拿一切物体来为表达我意而用。这种自由时空的造型法为民间艺术的写意赢得了充分的表现力,同时也为创造形式美开辟了一条自由大道”[9]。在土家族人制作织锦的过程中,并没有严格遵循科学的构图比例,也不注重所谓近大远小以及近实远虚等透视原则,而是根据自身意愿和情感表达的需要进行安排,因此织锦的图案及色彩显得生动而富于个性。即使是同一种图案,由于人们的情感、愿望以及判断不同,他们于纹样以及色彩的设计处理也会有所区别,使得织锦的色彩、明暗、淡浓以及线条的粗细等产生出明显差异。
最后,手工艺通过特定的艺术手法表现出独特的生命样态。有学者指出,“中国美学要求艺术作品的境界是一个全幅的天地,要表现全宇宙的气韵、生命、生机……”[10]把生命作为整体进行把握,这是中国美学以及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传统,也是生态美学的重要主张。元代人吴融说:“一片石,数株松。远又淡,近又浓。不出门庭三五步,观尽江山万千重。”[11]尽管只是片石数松,但是却传达出整个宇宙的无限生机。图案是鄂西土家族织锦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土家织锦的制作中,人们对人物、鸟兽、植物以及其他意象进行艺术加工,创作出具有深刻寓意的各种艺术形式。在土家族文化不断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图案经过“这种长时间积淀,导致审美判断和审美价值的相对稳定性,进而形成一种生命意象的群体性审美范式,一种社会群体性的心理定势和固有的审美惯例”[12]。而这些装饰性图案对于生命整体样态的表现,离不开特定的艺术表现手法。“鄂西土家族的动物图形多运用夸张、提炼、概括的变形手法,是在记忆表象的基础上产生的以创造想象为心理过程的新形象。”[13]“龙凤龟”就是鄂西织锦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吉祥图案,将龙头、凤尾与龟身结合在一起,传达出吉利喜庆、迎祥纳福等美好意愿。
三、从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来看,鄂西土家族织锦工艺强调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融合
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艺术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研究者们关于艺术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着显著区别。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前,艺术被看作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或者再现,“对自然本体摹仿的真实程度决定了艺术成功的程度。现实是艺术的本源,它规定着艺术的内容和本质,要求艺术仅仅用美的形式去反映‘对象’的本真(真实),从而获得艺术存在的本体依据”。[14]而到了工业社会之后,人与自然、社会生活之间发生分裂,艺术不再追求对于现实的模仿,而注重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许多学者看来,艺术成为摆脱技术理性控制的重要方式,被看作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力量,揭示出人和自然在现实中受压抑和受排斥的那一面”[15]。因此,在工业社会中,艺术具有拯救人性的重要功能与价值,能够使人们从现实生活中的工具理性以及技术规则等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实现情感的自由表达与精神的圆满自足。
但是,应该看到,由于现代社会中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对立,艺术以及人类的生存面临巨大威胁。有学者提出,“现代社会在区别生产与审美和道德的调控方面是独一无二的。现代社会无视它们的对象嵌入社会的方式,用包装代替了一种内在的审美技巧,对技术的意外后果给人类和自然产生的影响漠不关心。各种系统的危机就源于这种技术、道德和审美的人为分离。”[16]随着生态文明观念的兴起,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艺术与现实生活之间重新融合的必要性,艺术活动不应当是少数人群或者某一阶层的特权,艺术活动的场所不再是音乐厅或者博物馆等传统艺术空间,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固有界限逐步瓦解,艺术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17]因此,对于生态美学来说,不仅要构建起一种新的美学形态,而且要借助于全新的美学观念来指导人们的现实生活及日常实践,借助于生态观念以及美学理论来改善人类的生活环境,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社会问题,重建艺术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
传统手工艺的产生和发展,总是与当地群众的生产劳作以及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注重艺术审美和实用功能的之间的协调与统一。在现代社会中,有些传统手工艺品仍然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独特的审美属性。还有些手工艺制品,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使用功能,但依然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给人们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成为完善人们现实生活重要载体。
可以说,传统手工艺是当地人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们对于宇宙、自然、社会以及人生等的思考和经验。鄂西土家族传统织锦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土家族人的现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独特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但是,到了现代社会中,“现代化的纺织品以其物美价廉的特点极大地改变了土家人的生活方式,人们更倾向于接受市场上的服饰和床上用品,就连婚丧嫁娶的物品都可以随时买到,土家织锦正在淡出土家人的日常生活。”[18]鄂西土家族织锦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一般来说,手工艺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且凝结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传达出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具有鲜明的自然质朴的色彩与品性,在增强文化记忆以及强化文化认同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到了生态文明时代,少数民族手工艺的传承和发展,必须要凸显其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强化传统手工艺生产的“文化记忆”。“在现代性的生产结构中,手工艺生产的文化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于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现代重构,这种重构只有与当代的生活需求和生活情趣相结合,才能实现为生活服务的功能,焕发新的生命力,发挥真正的生产意义。”[19]因此,在鄂西土家族织锦工艺的传承过程中,必须要重构传统织锦工艺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使织锦工艺产品真正走入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去,充分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这样传统手工艺才能得到传承和发展。近年来,鄂西土家族织锦工艺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土家织锦的观赏功能和情感价值得到重视,人们开始把织锦制成壁挂、沙发巾、电视罩甚至手机套等,土家织锦与人们现实生活之间的结合更加密切。
鄂西土家族织锦工艺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当地土家族人特殊生产生活方式的活态显现,承载着土家族人的文化个性、生活习性以及文化观念等内容,在土家人的现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到了工业化时代,由于商业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鄂西土家族织锦工艺受到较大冲击。伴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和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如何唤起起社会对于传统手工艺的重视,推动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传承,已经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
[1]D.扎尔科维奇.生态危机与经济发展[J].国外社会科学,1991(4):62 -64.
[2]徐恒醇.生态美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36.
[3]李 敏.鄂西土家族织锦的“图式文化”特征[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65-67.
[4]潘鲁生.民艺学概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126.
[5]张善平,周永民.“自然”美学观对当代生态艺术设计的影响[J].文艺争鸣,2010(1):116 -118.
[6]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84:187.
[7]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45.
[8]袁浩鑫.论中国民间美术的艺术特征[J].装饰,2005(6):107.
[9]向思楼.论中国民间美术意象结构的审美特征[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263-267.
[10]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27.
[11]卢辅胜.中国书画全书:第2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387.
[12]尹笑非,陈勤建.独特的生命图像象征艺术——中国传统吉祥图像的美学解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95-98.
[13]辛艺华,罗 彬.土家族民间美术[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4:51.
[14]王岳川.艺术本体论[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4.
[15]马尔库塞.单面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25.
[16]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26.
[17]朱明弢.艺术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谈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艺术对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探索[J].文艺评论,2011(9):24-27.
[18]谭志满,霍晓丽.文化空间视阈下土家织锦保护与传承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0):48-51.
[19]鲍懿喜.手工艺: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生产力量[J].美术观察,2010(4):12 -13.
刘应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