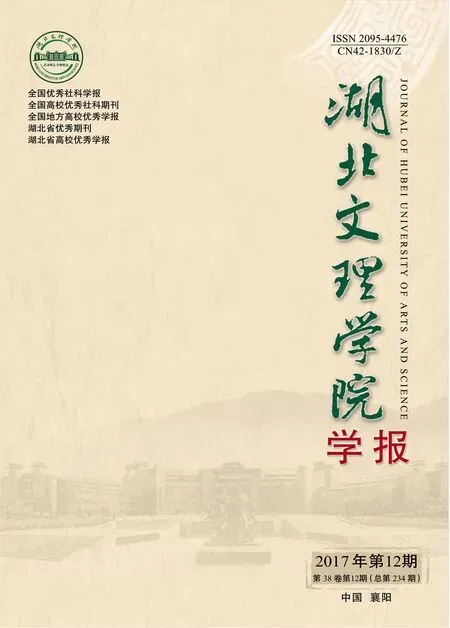论古代咏萱诗赋的形象书写及其主题表达
高尚杰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论古代咏萱诗赋的形象书写及其主题表达
高尚杰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萱草是中国古代植物审美文化系统中颇具内涵的一类花卉形象,早在《诗经》时代就已出现,并进一步被赋予忘忧的核心主题。萱草在古代文学的书写中具有其独特的审美形象,并成为建立其象征性的基础。随着文化思潮的发展以及文学内部艺术规律的要求,萱草在忘忧的主题之外逐渐形成代母、孝亲的新型象征,并盛极一时,出现了形式内容多样的文学创作现象。萱草被认为的宜男象征则在现实经验、创作演化以及女性形象的转变中逐渐远离了主流话语,但依然属于萱草象征意义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萱草;审美形象;象征意义
I206.2/.4
A
2095 -4476(2017)12-0057 -06
2017-06-26
高尚杰(1992—),男,山西娄烦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生成演变过程中,在天人合一观念的强大语势之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加以强化,体现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则是比兴象喻和意象寄托的艺术方式及表意体系的高度成熟。可以说,四时之景、万物之态都无不与作者的情思意趣有着多样的关联,进而推动文学创作以积累态势向深闳富博的方向前进。在这样的传统文学文化背景下,萱草则成为中国古代文学草木意象系统中较为富有社会生活和群体心理内涵的一类品种。
一、萱草的文学表现
萱草进入文学创作而被赋予一定主体意蕴的过程始发于《诗经》,《伯兮》篇云:“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其中对谖草的理解,疏云:“君子既过时不反,己思之至甚,既生首疾,恐以危身,故言我忧如此,何处得一忘忧之草,我树之于北堂之上,冀观之以忘忧。”[1]这是历史上对萱草赋以忘忧之意的开端。
忘忧的前提是萱草的可“观”。《本草纲目》云:“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谓忧思不能自,遣故欲树此草玩味,以忘忧也。”品其“玩味”一词,则意下将萱草视作可观可赏之物,在赏玩中暂时忘却烦扰。萱草在春季萌发甚早,绿叶成丛,极为美观,古人常于自家庭中植萱而供赏玩助兴,如项安世《方太君生朝四首(其四)》诗中所说:“天边历草记年华,一日东风一荚花。春到平分争一英,庭萱吹出碧云芽。”[2]27335吴稼竳《嘉秀堂宴集》诗:“园葵发红彩,庭萱组丹绣。丝竹间清响,埙篪合奇奏。”[3]于是,对于人们普遍的审美认知规律而言,萱草的外在物色形态美感是作为兴发创作感思的基础和前提。
关于萱草常见品种和形态的记载,《广群芳谱》记其“有黄、白、红、紫、麝香、重叶、单叶、数种”,此外另补二种,名曰“凤头”“金台”。高濂《遵生八笺》言萱草“有三种,单瓣者可食,千瓣者食之杀人,惟色如蜜者,香清叶嫩,可充高斋清供,又可作蔬食之,不可不多种也”[4],可见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见者多为三种,且与人们的饮食经验有关。陈淏子《花镜》中描述萱草“茎无附枝,繁萼攒连,叶弱四垂,花初发如黄鹄嘴,开则六出,色黄微带红晕”,后言萱草有三种,一千叶,一单叶,一种色如蜜者,而“惟千叶红花者不可用,食之杀人”[5],因此前所谓千瓣即此言千叶者,开红色花。综合此类材料的描述,可以从中得知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见之萱草品种不是很多,一般未达《谱》所言数种,且人之所见皆本于其一定的用途,或以食用,或以观赏,开花者基本以红、黄二色居多。
有不少咏萱作品将萱草的自然美感形诸文字。萱草生长期较早,花色也并不单调,作者关注的重点往往集中于萱草的枝叶花色之美。如魏澹《咏阶前萱草诗》:“绿草正含芳,靃靡映前堂。带心花欲发,依笼叶已长。”[6]朱松《记草木杂诗七首·萱草》:“纷敷翠羽丛,绛英烂如赭。 诸孙绕银鹿,采摘动盈把。”[2]20723陆游《冬暖园中萱草蓊然海棠亦著花可爱作路浚井皆近事也》:“暖景变严冬,谁知造化功。少留萱草绿,探借海棠红。”[7]将花叶之色彩对比写得更为集中而着意突出花色的是夏侯湛的《宜男花赋》:“远而望之,灼若丹霞照青天;近而观之,炜若芙蓉鉴渌泉。萋萋翠叶,灼灼朱华,晔若珠玉之树,焕如锦绣之罗。”[8]对于萱草物象的择取,一般以春季为背景,将盎然春意蕴贴于葳蕤盛草中。如张良臣《萱草》:“雪色侵凌绿剪芽,枝抽寒玉带金葩。”[2]28460周复元《萱草》:“嫩叶初擎金凤花,盈盈玉砌蹴春芽。 东风殿后还应觉,自是偏承雨露赊。”[9]初春萱草,纤柔俏立于庭阶之间,自是惹人怜爱。
在表现萱草花叶的视觉物色效果之外,萱花之香也颇引起文人的注意。咏萱创作中提到的萱香多属麝香萱,《农政全书》注“焉得谖草”下云:“又有一种,以色言之则名金萱,以香言之名麝香萱。”萱草花色与花香的结合,将立体的观赏画面塑造得富有神采韵味。如王炎《麝香萱草》诗:“秾绿丛中出嫩黄,折来时吐麝脐香。”[2]29804许及之《麝香萱》诗:“南薰吹麝馥,背树染鹅黄。 里许香为德,中央色自庄。”[2]28336此诗写花色花香皆以为德之正来进行考量,视其为道德意义上的心正之草。《左传·桓公六年》有言“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反映出萱草的象征寄托所具备的思想伦理基础。以花、叶、香等多个方面进行的整体组合描写,使其更具立体化、形象化的审美效果。如李峤《萱》:“黄英开养性,绿叶正依笼。色湛仙人露,香传少女风。”[10]张羽《咏萱草花》:“丹华丽晴日,翠叶艳朱光。 盈盈列芳挺,淡淡发轻香。”[11]俞允文《谖草赋》:“总修茎兮,綷若翠羽腾绿波;舒丛葩兮,灼若雕霞晃朝日。引崇兰而泛景,转芳蕙而凝碧。香摇少女之风,露湛仙人之液。”[12]相比于其他赋作,俞赋对萱草的外在形态描写铺陈要更显全面集中、立体可观。
在此类整体描绘萱草的诗赋作品中,最能传神体现萱草轻盈飘逸、柔缓流动的内容当属以“少女风”来喻指花香的笔法。梁简文帝萧纲《咏风诗》云“欲因吹少女,还将拂大王”,徐陵注引《管辂传》谓“辂曰:‘今夕当大雨,树上已有少女微风,若少女反,风其应至矣。’”[13]萧纲以其写入咏风之作,有意描摹突出轻风慢拂之态,并透露出宫廷咏物之作的绮旎之风。后王之道《秋兴八首追和杜老(其七)》诗言“宦情薄似贤人酒,诗思清于少女风”[2]20227,则全然写风所形成的轻微细摇之感,已然脱去与女子相关联而产生的轻艳色彩。因此,在这样的语境转换背景之中以“少女风”来写风中所传萱草花香,则将其似有还无、缥缈清绵的柔细之感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来,所构成的语意想象空间极富韵致。
二、萱草忘忧主题的文学书写
萱草被赋以忘忧的意义自《诗经》中发端,到嵇康之时已然成为一种常识,即所谓“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毛传与嵇康的说法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很大,宋人洪刍认为“焉得谖草”并非实指萱草,胡仔引毛、嵇二条予以反驳:“笺云:‘忧以生疾,恐将危身,欲忘之。’又嵇康《养生论》云:‘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李善引毛苌《诗传》与《诗注》同,然则驹父之言真误矣。”[14]胡氏所引表明此二论对于萱草忘忧的这一主要认识实际上具有推动定型的意义。
萱草可食,其食用之效也被古人所关注。《本草纲目》云:“嫩苗为蔬,食之动风,令人昏然如醉,因名忘忧。”此处所言“昏然如醉”可能是因为鲜苗多食的缘故,因身体不适而引发客观上的忘忧结果。《六家诗名物疏》云:“萱味甘而无毒,主安五藏,利心志,令人好欢乐无忧,轻身明目。”[15]从药理角度而言,萱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清热利尿、凉血止血的功效,因此施之于人体则能够起到镇定安神、消烦去躁的生理作用,这也是人们对于萱草忘忧之效在物理范畴内进行的探讨和解释。
关于萱草忘忧的功效,在文化史的讨论中,则时有论争。孔颖达为《诗》之正义提出:“谖训为忘,非草名。”后宋人袁文对此论做了进一步演发:“萱草岂能忘忧也!《诗》云‘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者,谖训忘,如‘终不可谖兮’之谖,盖言焉得忘忧之草而树之北堂乎。背,北堂耳。其谖字适与萱字同音,故当时戏谓萱草为忘忧,而注诗者适又解云‘谖草令人忘忧’,后人遂以为诚然也。”[16]对此,大体与袁文同时的王观国则并不支持,他说:“萱草之萱亦作藼,亦作蕿。然《伯兮》诗曰‘焉得谖草’,而不用上三字。按字书,谖音暄,诈也,忘也。古人假借字,取其意而已。桑葚用黮字,取其色也。萱,忘忧草也,用谖字,取其忘也。字虽假借,而意则不失也。”[17]王氏以字的通假和义的取用作通达之说,是符合古人用字习惯的,此说似更合理。清人焦循也表示反对,其云:“崔豹《古今注》引董仲舒云:‘欲忘人之忧,赠之以丹棘。’《说文》:‘藼,令人忘忧草也。’诗曰:‘焉得藼草。’重文作萱。《文选》注引诗作‘焉得萱草。’以忘忧得有谖名,因谖而转爲藼、萱。谓萱取义于谖可也,謂谖草非草名不可也……若谖仅训为忘,则忘草为不辞。至于经义,正以忧之不能忘耳。”[18]观其诸种反对之说,无论从解释经典的历史和学理角度而言还是从古汉语通假通用的现象去证明,都更为充实和合理。且从争论本身来看,足以反映萱草忘忧主题在传统文化中打下的深刻烙印,同时也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镌刻。特别是在古代文学中有一种忧世伤情的普遍创作心态与之契合更为密切,有研究者对此总结道:“文人用敏感的心灵体味现实人生,体现深重的忧患意识与感伤情绪,这是文学中一个永恒的主题。这种在文学中表现忧愁感伤的创作传统便是萱草意象作为忘忧草可以长期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19]
宋人叶适言:“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中国古代文学所表达的“忧”一直都是抒情传统中的核心要素,它扎根于以儒学为基石的文化意识下用世保身的矛盾以及血缘社会体系中人伦关系内部所形成的普遍秩序。其中与萱草的结合不仅是早期文化意识中具有始发性的表达结构,更是后世文学创作系统中意义拓展的丰富源泉。宋祁所作的《西斋新植萱草甚多作问答绝句二首》是两首问答诗,其一云:“腻花金英扑,纤莛玉段抽。萱如解荣悴,争合自忘忧。”此为提问,其二诗回答云:“我有忘忧号,君为忧世人。欲忧忧底事,胡不暂怡神。”[20]对萱草的不解中实际上含有忧心难释的固结,其中自我无奈而求宽慰的情愫显为人见。当然结合萱草以抒发无忧自适、澄心味景的诗作,也能够将心境和外物融为一体而具超妙之趣,如陆游《冬暖园中萱草蓊然》:“少留萱草绿,探借海棠红。筑路横塘北,疏泉小岭东。欣然得佳处,忘却岁将穷。”[7]4041范成大《题赵昌四季花图·葵花萱草》:“卫足保明哲,忘忧助欢娱。欣欣夏日永,媚我幽人庐。”[21]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家铉翁的《萱草篇》,此诗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明清时期以萱草代母而表祝的文学功能:“诗人美萱草,盖谓忧可忘。人子惜此花,植之盈北堂。庶以悦亲意,岂特怜芬芳。使君有慈母,星发寿且康……抚俗时用乂,事亲日尤长。萱草岁岁盛,此乐安可量。”[2]39941诗中明确指出萱有两重意义,一以植萱悦亲,一以萱来代母,由此可见萱由忘忧以至娱母,再至成为母亲的象征,在宋代已经出现了完整的发展链条。
萱草与忘忧主题的联结,重点不在于“忘”,作者更多地将欲忘难忘,忧从中来作为逻辑关注的重点。梅尧臣《和石昌言学士官舍十题·萱草》诗:“人心与草不相同,安有树萱忧自释。若言忧及此能忘,乃是人心为物易。”[22]此诗纯为说理,但所论述的问题在于萱草忘忧的原理机制,由此可以看到萱的本质实际上被界定为沟通心物之间诗意建构的桥梁。蒋薰《萱花》诗:“绿叶因风起,黄茸乱蝶飞。忧来常不断,何自满岩扉。”[23]沈赤然《小园萱花戎葵盛开各赋一绝句(其一)》诗:“朵朵黄花似凤头,瘦茎尖叶护阶稠。频年看尔开还落,不疗先生半日愁。”[24]本是忘忧却反使忧心更加凸显,是作者创作咏萱诗歌之时最常见的营构形式。具体而微,以咏萱而表忧心,涉及到文人现实生活与心态内涵的许多方面。韦应物《对萱草》诗:“何人树萱草,对此郡斋幽。本是忘忧物,今夕重生忧……还思杜陵圃,离披风雨秋。”[25]故园之念外,萱草也似乎因“树之北堂”的关联而引发亲故之思。还有以忧国伤民为主形成的寄托,如石延年“移萱树之背,丹霞间金色”,“我有忧民心,对君忘不得”[26]。季芝昌《萱花》诗:“时艰丰稔为先策,民力东南仅数州。膏雨不来心百结,对花翻觉动生愁。”[27]石介的《植萱》则用语刚健有力,用亢劲的语声为国而呼:“一人横行,武王则羞。今西夷之鬼,抗中国而敌万乘。西夷之服,升黄堂而骄诸侯。尊于天子,满于九州。王法不禁,四民不收。植萱于阶兮,庶忘吾忧。”[28]此诗创作之际正值宋与西夏之间战事屡败,危机重重之下文人将内心的国忧发诸诗文,辞气激荡。此外,以萱写忧亲的诗篇也真情流溢,有动人之处。刘应时《萱花》诗:“碧玉长簪出短篱,枝头腥血耐炎晖。北堂花在亲何在,几对薰风泪湿衣。”[2]24236花可重开而人不可重生,无疑是面对萱草之时诗人内心所产生的最大悲慨,而以萱写母之题之所以能够进一步演化,与此种真情寄托的表达方式不无关系。
三、萱草主题表达的转换及其特征
萱草忘忧的主题在文学文化历史脉络中经历了较长时期之后,从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暂时抽身,而集中向萱草代母、写母的中心靠拢,产生了一系列与母亲有关的祝告、祈愿、赞美、忆念等作品,并且在这一语境的影响下,萱草作为中国母亲花的象征意义被特别强化,这一文学现象在明清时期尤为显著。
以萱代母反映在语汇的使用中体现为萱堂、椿萱等含有萱字的词语组合。萱堂最早出现在宋代,如“先生方婆娑泉石之间,作萱堂以养母,未暇出也”[29]。尽管以萱代母入于文学作品,但关于萱的主题象征内涵的发生和演变,从宋人开始便产生了怀疑与争论。王楙言:“今人称母为北堂、萱堂,盖祖《毛诗·伯兮》诗‘焉得萱草,言树之背’……盖北堂幽阴之地,可以种萱。初未尝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为母事。借谓北堂居幽阴之地,则凡妇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独母哉?”[30]这种质疑实际上反映了以萱代母在实际创作中的变化形势。
明代官方的思想理论体系所树立的核心规范便是围绕着纲常伦理所展开的道德规范法式,这其中,忠孝理念是主流意识话语的一个突出表现。理学家宋濂将忠孝视为做人的根本,其云:“濂闻‘忠孝’者,天地之间大经大法也。为子克尽其孝,为臣克尽其忠,始合乎物则民彝之正。无是者,非人也。”[31]刘基也盛言孝行之道:“孝,百行之首也。为人子而志于孝,夫奚为而不淑哉?”[32]152因此,诗文创作贯穿忠孝意识是与政治形态统一的必然表现。明代文人对以萱代母创作实践的关注空前提高,并从理论上为萱草的主题象征转换寻求合法性,形成了三个主要依据。一是对忘忧主题加以延伸,体现为以萱草孝亲的情态表达。龚敩在其《寿萱堂记》中说:“尝读卫风《伯兮》之诗,有曰:焉得谖草,言树之背。由昔人久别怀思,视谖草以忘吾忧,如见其人耳。然情爱之钟,莫切于子母也。若虚之心,岂不以出处不常,恐贻线衣之念,欲其亲视萱草无恚,以忘其惟疾之忧,而寓之斯耶。”[33]二是依据北堂为母之所居,因此自然有代母之义。金实《椿萱堂记》云:“诗曰:‘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背,北堂也。萱草能忘忧,而北堂又奉母之所,故以之况母。”[34]汪舜民《思萱图记》云:“诗云‘焉得萱草,言树之背。’背乃堂北,妇人之所主也,呼母为萱堂,其以是与。”[35]三是以宜男之义出发,因子由母所生,则可得萱草为母之义。林弼《怡萱堂记》:“萱有宜男之名,故为子者托以为母之义焉。”[36]131又其《寿萱堂记》云:“故树萱于北堂,而朝夕致培植之力,犹事亲于高堂,而晨昏谨定省之节也。”[37]137其中所言树萱以求事亲,是明清时期文人文化心态的一个普遍写照。
同样,萱草代母主题的演变过程中也自有论争。袁枚论“萱草称母之讹”云:“《珍珠船》言萱草,妓女也,人以比母,误矣。此说盖本魏人吴普《本草》。然《毛诗》‘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注:‘背,北堂也。’人盖因北堂而傅会于母也。《风土记》云:‘妇人有妊,佩萱则生男,故谓之宜男草。’《西溪丛语》言今人多用北堂、萱堂于鳏居之人,以其花未尝双开故也。似与比母之义尚远。”[37]俞樾则推举宋学观念,谓“宋人犹不以北堂萱堂称母”。而赵翼对萱堂代母之说表示支持:“俗谓母为萱堂,盖因诗‘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注云,背,北堂也……按古人寝室之制,前堂后室,其由室而之内寝,有侧阶,即所谓北堂也……凡遇祭祀,主妇位于此。主妇则一家之主,母也。北堂者,母之所在也,后人因以北堂为母,而北堂既可树萱,遂称曰萱堂耳。”[38]对此争论,刘基之说深入探究了时人心态,其从社会心理方面加以调和的努力,或可代表这一时期的文化心理。其云:“按萓,草名也。《诗》曰:‘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谖与萱同音,而谖之义为忘,故草名萱,亦取其能忘忧。北堂谓之背。妇洗在北堂,见于昏礼之文;而萱草忘忧出于嵇叔夜之论。后世相承,以北堂喻母道,而又有萱堂之称,盖不知其何所据。若唐人‘堂阶萱草’之诗,乃谓母思其子,有忧而无欢,虽有忘忧之草,如不见焉。非以萱比母也。又按医书,萱草一名宜男。以萱谕母,意或出此?盖不可知。然萱能忘忧,既寿矣,又无忧焉,人之所愿欲遂矣。子之奉母,不过欲其如是,则寿萱之名,不必其有所据亦可也。”[32]160因此,萱草代母之说实际上并非无稽之论,其蕴含着深层的文化心理和现实诉求。它既受到明清以来以理学为社会意识的整体舆论环境的助推,也顺应了文人孝义亲情的表达以及艺术形象的随时而变。
以萱写母为传统的咏萱作品提供了更为多样的艺术途径,但又易于形成固定化的表现模式。萱草娱母是在忘忧主题之下表达孝亲之义的一个重要角度,薛章宪《萱草花赋》谓“子树背兮怡母,母服膺兮宜男”,“俨慈颜之可悦,信幽忧之能忘”[12]5267。林弼《怡萱堂记》云:“亲一体也,非承颜色养,不足尽人子之道……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必有愉色,必有婉容。”[36]132于是以萱草悦母的功能模式就受到了创作者的欢迎。如柯潜《寿萱堂为城东顾彦真知事题》诗:“庭前不肯种凡草,种得萱花长自好。欲教慈母百忧忘,期与萱花同不老。”[39]此外,这一时期文人的创作多为代题诗或题画诗,一方面孝母行为是社会普遍的文化情结,题诗赠诗以寿母成为社会风尚;另一方面,画萱为图成为为母庆寿时一种渐趋普遍的礼物。这类诗歌一时剧增,如王世贞《题萱寿太医邢生母》、宗臣《萱草词四章为伊母夫人赋》、王士祯《题松萱图四首寿姜节母西溟之母》、翁方纲《丁小疋奉萱图二首》等等,潮流所及,一些声名显著的作者也参与其中。但此类诗作围绕孝亲庆寿立题也常陷入颂美、称好、良祝等创作固化的弊端,艺术成就相对有限。从以萱比母的角度来看,作品往往能够直接体现萱草与母亲之间所形成的象征关系,如杨荣《寿萱堂为王都御史题》:“高堂有母今垂老,鹤发慈颜喜长好。爱日惟存慰母心,阶前多种忘忧草。愿将此草喻慈亲,一度春风一度新。……慈亲安乐萱长茂,九天雨露栽培厚。有待他年昼锦还,拜舞花前庆亲寿。”[40]此外,较能流露作者真实情意的作品是丧母之后对母亲的忆念感怀,有程通《梦萱吟》、张宁《梦萱八韵》等诗,如程诗云:“有梦到门闾,宛然见萱草。秋风忽披拂,颜色宁复好。觉来坐蓬窗,忧心有如捣。泪坠沾衣裳,天空月正皎。”[41]在辞赋的创作方面,有限的几篇作品中对慈母的怀念亦发于铺叙,典型如徐泰然的《萱草忘忧赋》。此赋借鉴主客问答的体式,客之所问基于萱草忘忧的题旨,但主人的回答却谓其“不识孺慕之难蠲”,语意的转换表明所要申发的乃是对母亲的悼忆怀念。“云山绵邈,道路几千。慨寝帷兮不见,集苞栩兮流连。胡为觞我以翩反,动我以芊绵。物犹如此,人何以堪”,逝母不见的悲慨竟无以排遣,只能徒增痛楚的忆念。继而写“开萱室以张筵,奉萱觥以娱老。寿觞既倾,慈颜皞皞”[12]22876,赋以忆母与奉母并举,承续了萱草代母主题创作的主流。
除以上两种主题象征外,萱草还有宜男的象征意义。萱草宜男主题的建立在魏晋时期,但是并没有得到深入发展,仅仅在后世的创作中演变为一个意象指代符号,对此笔者以为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人们对草本身性状有一个逐渐客观化的认识过程。早期人们认为萱草具有宜男之效,陈大章《诗传名物集览》引述云:“《本草》注:一名鹿葱,花名宜男,妇人怀胎,佩其花生男……《风土记》:宜男,妊妇佩之,必生男。稽含《宜男序》:可以荐俎,世人多女,求男,服之尤良。”[42]但在实际生活经验中这样的行为和结果并不多见,如褚澄《褚氏遗书》所记:“问曰:‘求男有道乎?’……‘然妇人有所产皆女者,有所产皆男者,大王诚能访求多男妇人谋置宫府,有男之道也。’”[43]此外,社会经验与传统科学的进步,使后世对萱草宜男的功能基本不予认可,谢肇淛云:“萱草一名鹿葱,一名宜男……宜男自汉相传至今,未见其有明验也。”[44]李渔云:“佩此可以宜男,则千万人试之,无一验者。书之不可尽信,类如此矣。”[45]二是作为文学创作的题材和意象出现了两种演化,第一,如前文所述,这一象征向代母主题发生了转变。第二,萱草宜男的象征演化为女子对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的期待向往。如南朝梁萧绎《宜男草诗》与唐代于鹄《题美人》,此二诗为论者所常引,诗中的主角实际上并非萱草,其主要作用在于衬托女子对生活的无限憧憬和期待,也透露出女子情感命运坎坷的无奈失落。其三是古代女子形象以及男子关注视野的变化。陆淳《春秋集传微旨》云:“卫侯游于郊,子南仆。公曰:‘余无子,将立女。’不对。他日又谓之,对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图。’”[46]由此可见,女子身份之地位卑贱是其求子需求产生的社会本因。至唐宋时期,女子形象的审美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生育象征的强势语境。明代将理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明人极其重视对贞女形象的树立,吴国伦认为,“若所谓男而婿婢,女而妇奴,即有奇节,不得附青云之士以传,岂贱其人而羞称之乎”[47]。明清时人还都十分关注女性所表现的文学才华,女性诗文集数量大幅增加,集子刊刻也融入了男性的参与,这种对女性的支持欣赏心态,是既往罕有的。明人叶绍袁云:“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儿昭昭乎鼎千古矣。”[48]无论男女皆以德居首,但对女子才华的关注,则烨然进入文人的视野,成为一种常规的社会心理状态。正因为在文学文化发展不同阶段对女性的关注愈加丰富多样,女性的身份属性也逐渐剥离为子而存的狭隘性,这是萱草宜男象征在后世弱化的又一原因。
综上,萱草所具有的植物审美意义是其产生其他象征内涵的基础,而在萱草象征主题演变过程中,《诗经》在文学和思想上的双重经典地位成为忘忧主题植根的深厚土壤。萱草主题的表达在宋代由忘忧而衍生出娱母功用,进而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代母的新形式。这一形式随着明代社会思想的转变,以萱代母、孝亲之义的表达成为其时主流。萱草宜男的象征则在昙花一现之中基于现实经验的发展而脱离了其滋生的客观基础,同时又向萱草代母的创作模式加以转变,最终推动了萱草文学文化主题的最终形成。
[1]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87.
[2]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吴稼竳.玄盖副草[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 -186.济南:齐鲁书社,1997:555.
[4]高 濂.遵生八笺校注[M].赵李勋,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628.
[5]陈淏子.花镜[M].伊钦恒,校注.北京:农业出版社,1962:337.
[6]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陆 游.剑南诗稿校注[M].钱仲联,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8]韩格平.全魏晋赋校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164.
[9]周复元.栾城稿[M]//四库未收书辑刊:5 -22.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170.
[10]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M].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
[11]张 羽.静居集[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7.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745.
[12]马积高.历代辞赋总汇[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13]徐 陵.玉台新咏笺注[M].穆克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320.
[14]胡 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00.
[15]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0.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11.
[16]袁 文.瓮牖闲评[M].李伟国,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 -3.
[17]王观国.学林[M].田瑞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288.
[18]晏炎吾.清人诗说四种[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289.
[19]付 梅.论古代文学中的萱草意象[J].阅江学刊,2012(1):142 -148.
[20]宋 祁.景文集[M]//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277.
[21]范成大.范石湖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57.
[22]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朱东润,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51.
[23]蒋 薰.留素堂诗删[M]//四库未收书辑刊:7 -19.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250.
[24]沈赤然.五研斋诗钞[M]//清代诗文集汇编:4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15.
[25]韦应物.韦应物集校注[M].陶 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520.
[26]陈景沂.全芳备祖[M].程 杰,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536.
[27]季芝昌.丹魁堂诗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57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88.
[28]石 介.徂徕石先生文集[M].陈植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30.
[29]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卷四十八.
[30]王 楙.野客丛书[M].郑 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41.
[31]宋 濂.宋濂全集[M].黄灵庚,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020.
[32]刘 基.刘伯温集[M].林家骊,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33]龚 敩.鹅湖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33.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63.
[34]金 实.觉非斋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13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88.
[35]汪舜民.静轩先生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13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89.
[36]林 弼.林登州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27.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7]袁 枚.随园随笔[M]//王志英.袁枚全集新编:14.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317.
[38]赵 翼.陔余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63:963 -964.
[39]柯 潜.竹岩集[M]//续修四库全书:132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60.
[40]杨 基.文敏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40.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7.
[41]程 通.贞白遗稿[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35.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77.
[42]陈大章.诗传名物集览[M]//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99.
[43]褚 澄.褚氏遗书[M].许敬生,校注.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25.
[44]谢肇淛.五杂组[M].傅 成,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83.
[45]李 渔.闲情偶寄[M].单锦珩,校点.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265.
[46]陆 淳.春秋集传微旨[M]//丛书集成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218.
[47]吴国伦.甔甀洞稿[M].明万历刻本:卷四十四.
[48]叶绍袁.午梦堂集[M].冀 勒,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3.
Image Writing of Ancient Poetry and Prose Related to Hemerocallis Fulva and Its Theme Expression
GAO Shangjj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Hemerocallis fulva represents the image of flowers and plants with connotation in the plant aesthetic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 recorded early inThe Book of Songs, and it was given symbolic meaning of nepenthe.Boas⁃ting its special aesthetic image in ancient literature, hemerocallis fulva became the base of symbolistic poetry gradu⁃ally.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houghts and requirements of internal literary artistic rule,hemerocallis fulva began to build such new symbolization beyond nepenthe as godmother and filial piety,and it had been popular for a period, literary creation with various forms and contents consequently emerged.Besides, hemerocallis fulva used to symbolize having boys.However,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al experience, creation and female image, such symbolic meaning lost its mainstream discourse little by little,but this kind of meaning is always seen as one of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hemerocallis fulva.
Hemerocallis Fulva; aesthetic image; symbolic meaning
倪向阳)
——萱草价值和应用前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