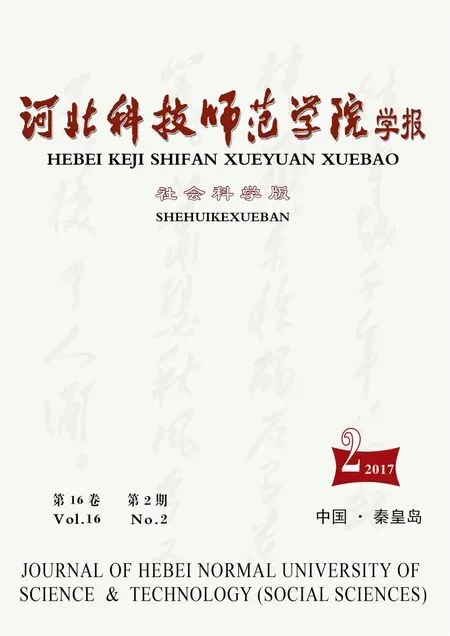蓝鼎元文学理论探微
凌 丽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蓝鼎元文学理论探微
凌 丽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蓝鼎元的文学理论,是了解他文学创作的关键。他的文学理论包括文论和诗论,他的文论主张学习经史和名家,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强调文道观念,以及文气的作用等;他的诗论秉承文论,主张情、理、气三者的结合。蓝鼎元的文学理论不仅反映了他的文学创作,也对清初闽地的文风起到了引领和改善的作用。
蓝鼎元;文论;诗论
蓝鼎元(1680~1733年),字玉霖,号鹿洲,是清初的一位名气甚大的学者和散文家。他自幼熟读经史,尤善古诗文。年少时随军赴台,提出治平台湾方略,这些治台理念,于今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蓝鼎元也因此被冠名为“筹台宗匠”[1]。蓝鼎元不仅谋略过人,其散文创作亦十分特别,自成一派。其散文集大成者《鹿洲初集》二十卷,不仅反映了他的散文创作成就,也体现了其散文创作的高度。《鹿州公案》二卷以散文笔法讲述案情故事,可读性十分强,堪称其为“散文小说”。除此之外的专著如《女学》《棉阳学准》《修史试笔》《鹿洲藏稿》等反映了其理学、史学等方面的思想,而有名的《东征集》《平台纪略》则记录了其平台、治台的一段经历,尤其是对台地人文、战事等方面的文学书写都使之声名大噪。考察历年来对蓝鼎元文学创作方面的研究,据笔者收集的有直接关联的约有2篇,如蓝荣钦的《蓝鼎元及其<鹿洲全集>》,该文以蓝鼎元的文集《鹿洲初集》为主,简要论述了蓝鼎元的书、论、说、传、赞、赋、檄、铭、记、序、考等文学特征,又选取《东征集》《鹿州公案》中若干有代表性的檄文来做分析,认为它们笔锋锐利,立论精妙,逻辑性强,议理透彻,无可辩驳,行文通达顺畅,极富说服力[2]45。青禾的《作为散文家的蓝鼎元》一文即依据《鹿洲初集》中的记和赋来初步归纳出蓝鼎元散文特点,认为蓝鼎元的散文“放在当时的文坛上看,也是颇具风采的。写人记事,可以与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相媲美,记游写景则不在姚鼐《登泰山记》之下”[2]56。
蓝鼎元身为康雍时期的一位古文家,其散文创作由来已久。他自小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其家学渊源以及师友的耳提面授都使之濡染甚久,并自觉地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当中,因此他的文学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浓厚的理学色彩。蓝鼎元不仅崇尚朱子理学,同时也偏爱经济之文,故在他的所有著作当中,“理学”和“经济”成分所占比例最多,堪称其文章的主要特点,其门人有云:“夫子之文,在所必传,学术醇正,践履笃实,所以绍濂、洛、关、闽之绪,传道脉于千秋万世。”[3]446《四库全书》也有言:“鼎元喜讲学,又喜讲经济,于时事最为留心。”[4]1324这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则是:“文笔条畅,多切事理,在近人文集中犹可谓有实际者,固与雕章绘句殊矣。”[4]1324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散文数量蔚然可观,且其散文成就在清初闽地学者兼作家群中可谓是佼佼者,甚至将之放在清代文坛上亦不遑多让。例如他的散文就写得比较有特色,语言雅洁之处近于桐城,然而行文结构以及文风气势却独树一帜,与清初散文诸家迥然不同,有属于自己的风格特征。“文辞之雄劲,录次之简净”[5]一语则扼要地归纳出了其散文的一大特征。《漳州府志》也称:“为文章,雄快警辟,长于议论;有眉山父子风。”[6]将蓝鼎元与三苏父子相提并论,亦可见蓝鼎元的文风雄劲明快特点之一斑。然而蓝鼎元的文章除了具有以上的特色之外,笔者以为其关于文学尤其是诗文方面的理论正是其文学创作的一次回顾,值得人关注,这其实是研究蓝鼎元散文创作的一大线索,也是对其文学创作进行一次清晰地梳理和概括。
一
蓝鼎元的授业门人曾说过:“邑侯鹿洲蓝夫子,以程朱之学术,为经世之文章。”[3]453学术和文章的紧密关联在蓝鼎元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得异常明显。在他看来,“学统以鲁、邹为唐虞,而濂、洛、关、闽奋乎百世之下,实能继孔、孟之薪传,开后人之聋聩。至论说之富,启迪之详,则程、朱之功尤为大备,千秋正学至此如日月中天。学者不崇尚程、朱,则鲁、邹之戾人也。”[3]463蓝鼎元眼中的学者应当是程朱理学的忠实维护者,否则不足以称作正统,只能沦作“戾人”一类的人物。同时他认为学者的文章必定是博通百家,文史兼备,以及攸关性理的经世之学:“吾所谓学者,取材千古,陶铸百家,措之方舟而咸宜,施之民物而各当。藏之名山,俟百世圣人而不惑,盖有用之实学也。沉浸于四子六经,以正其本;讲究性理先儒诸书,以清其源。熟读紫阳《纲目》,左、国、马、班以下诸家之史,周、秦、汉、唐、宋、明以来诸家之文,泛滥乎诸子百氏之著述,以广闻见。”[3]465在这段话中他指出学者须熟读经史以及秦汉以来的古文大家之文来充实自己的见闻,可见蓝鼎元对经史以及古文名家的推崇。这种推崇放在他的文学创作上就体现为散文思想内容上尊经尊圣的传统。蓝鼎元又有言:“吾所谓学者,非穷高极远,幽渺难行之谓,即在尔室屋漏,人伦日用之间。”[3]196在他看来,人人皆可为学者,但须以拥护程、朱学说为前提,此外才来论学者之文应当博通和经世,可见他对学者的定义是站在理学的立场上,将理学与学术相结合,是故,“儒者传心,唯有文章千古,既已著书立说,奥学贯乎天人,并且竭力致身,精诚笃于君父,屹然乾坤之柱础,伟哉名教之干城……庶几无忝所生,浩气塞苍旻,方为不负所学。”[3]334身为儒者,蓝鼎元秉持朱子之要义,阐发濂、洛、关、闽之真传,于一篇中三致意,也确实可称作有为之学者。他不仅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且也以身践行之,可见其“学适于世用,而心常存乎世道人心,词不尚浮夸,而论切中乎人情物理”[3]522,王者辅对他的评价算是合情合理的。
除了对学者及学者之文做出规定外,蓝鼎元就诗中也谈到了文学创作尤其是散文所要注重的几个问题。其诗有云:“其次论文章,经史为酝酿。古作秦汉前,八家当醢酱。制义本儒先,理明气欲王。洗伐去皮毛,大雅是宗匠。”[3]914在这几句诗中他提到了散文创作的内容、义理、语言、方法等方面的要求,这其实相当于他的散文创作总述。“经史为酝酿,古作秦汉前,八家当醢酱”三句说的是作文要以经史为体要,以秦汉文为模仿对象,其次以唐宋八大家之文作为佐料辅助。这其实强调的是散文创作的内容要求,即需以古文名家为范本。“制义本儒先,理明气欲王”强调的是散文创作思想上当以义理为标准,即儒者作文须有制义的成分。所谓的制义即言之有物,序之有度,还要有理有据,更应不能少了气势。制义一科作为国家取士之举深为广大士子所推崇,蓝鼎元也不例外。他说:“当世以制科取士,士竞习为科举之文,镂心呕血,刻意时趋,若宇宙间经天纬地之事业,无有出于此者。既已敲金戛玉,学成一家,而闻者见者,熟视犹之无睹,几欲发狂跳叫,乃有人焉。”[3]95可见士子们以制义求仕为目的前仆后继,其举动深为人所惊叹。深谙此道的蓝鼎元也认为制义一科可明圣贤之道,可正豪士之心,“国家以制义取士,既可明圣贤之道,又可纯豪杰之心,岂诸子百家所可同日语哉?”[3]97字里行间无不是对科举的热衷。“理明气欲王”一句言文中所讲的道理要明晰准确,方能使文气盛大,统辖全文。这一说法放在当代的散文创作上同样适用,也可见这一观点的实用性,经久不衰。“洗伐去皮毛,大雅是宗匠”一句则认为语言要去华就实,恢复本色,强调语言的清真雅正,认为大气文雅才是散文语言的标准。总的来说,蓝鼎元就散文的内容、方法、思想和语言四个方面对其散文创作理论进行了一次总的概括,初步呈现了他的文学理念。
二
蓝鼎元的文学思想反映了明清之际散文创作的规范和法度,这种规范由来已久,成为清初以来古文家们的作文要义。然而后人却对此不以为然。周寅宾在《明清散文史》中指出:“明清散文有致命的弱点,其形式与语言,均以《史记》《汉书》、唐宋八大家文为标准。”[7]即明清的古文家一直沿用史、汉、韩、欧的体裁,同时代的戏曲与白话小说体制在不断改进,而古文却一直遵循“定体”,除晚明小品文外,不再出现新的体裁。至于明清散文的语言,也一直沿用《史记》《汉书》、唐宋八大家时代的文言,脱离白话,尚雅忌俗。虽然这是明清古文家诗文创作的一个要义,但这一点在今人看来却是具有其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贯穿于整个清王朝,直到白话文兴起,古文才逐渐衰落了下来。但是作为明清文学的一个显著标志,一种文体代表,它却是推动明清文化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蓝鼎元在散文理论中极力强调这一点,并将之运用于古文创作。其具体表现在:
(一)文本大家,无取陋习
蓝鼎元以为:“为文章必本经史古文先辈大家,无取平庸软靡之习。”[3]49他强调了文章不仅要本于经史古文,同时也要多效仿古文大家的创作,最忌讳的是平庸软靡的风气,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蓝鼎元重视文章要有特拔阳刚之气。其次,蓝鼎元以为文章除了借鉴秦汉及唐宋诸家的作品外,还要以程朱之学为要义,“耳及而求为名世之文,则意者本之六经,以固根柢。参之左、国、史、汉、唐、宋大家,以壮魄力;研穷程、朱诸儒,谆谆论辩之旨,以清障蔀。”[3]96唯有如此方能尽去平庸软靡之习,以达到“厚其气味,伟其声光,洗伐皮毛,锤练精髓[3]96”的目的。
(二)经世致用,去华就实
蓝鼎元最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在其所有的古文创作中,言多经济者不可胜数。
首先,他认为经济为文章之大要。“经济者,文章之大本领也。”[3]86蓝鼎元以为“经济”之学是文章的大要,“事不关经济学术,虽镂金错采,终属浮谈,言无补世道人心。”[3]98所以那些“敷衍风云月露之词,花鸟禽鱼之状”[3]86,自以为可与马、班、李、杜等人一较高下,然而在他看来,文章若是不实用,那么写得再漂亮也没有用,正如“鬼怜萤火,熠耀目前,虽使穷巧极工,为人世不恒有之物,终与草木同腐耳”[3]86,而“孰若布、帛、菽、粟,有功于人世也。”[3]98他举了个例子,说就像灵芝仙草和甘甜的泉水,即便再美好也无益于百姓;然而像布、帛、菽、粟这样实在的东西,能使人世不饥不寒,于民生有大益处,才是值得人可取。因此,蓝鼎元指出:“非有关世道人心,裨益民生国计之文皆为苟作,君子不忍以有用之精神耗费于不急之地也。”[3]86
其次,他强调实学与经济的结合。所谓“无本之学,空疏浅陋,夏虫不足与语冰,非吾所谓学也。无用之学,风云月露,雨珠不可以为襦,非吾所谓学也”[3]465。在他看来,空疏浅陋以及雕饰浮华,一个无本,一个无用,皆不能称作实学。那么何为实学呢?他将经济文章与实学联系在一起,提出:“经济文章皆为有用实学。”[3]254他又将今人作文与古人作文做了对比,认为“古人本经济为文章,六经字字皆可见之施行;今人经济文章分而为二,沾沾于八股制义”[3]465,他表明古人将经济、文章合为一体,是值得效仿;而今人热衷于八股时艺,将二者割裂开来,以至于“辞华焉已尔,不足以载道,不足以用世”[3]465,所以蓝鼎元批评今人之文不过雕虫小技,就像那《三都》《两京》之作,即便费尽毕生精力,也不见得有多大用处,因此最后他总结道:“君子不贵无益之笔墨,不为无用之文词。”[3]465
最后,写好经济文章之道。蓝鼎元认为要写好经济文章不仅要时常充实知识,还要留心世务,即,“随处检点,察识扩充,则可驯致与圣贤之域;又讲求经世理物,礼、乐、兵、农、刑、名、钱、谷之设施,使全体大用皆备于我。”[3]95运道顺畅时则可以无往而不利,为生民立命;运道窘困时又能安分守时,为百姓留下不朽的著作,唯有如此的心态才有可能写就“宇宙之文章”[3]95。蓝鼎元将经济之文称作宇宙文章,可见对经济之文的重视。
(三)文道观
蓝鼎元在他的文中时常提到的是文与道之间的关系。何为道?蓝鼎元眼中的道是存在于人伦日用之间,人的一举一动以及饮食间都带有道的含义在里面。“道非高远即在人伦日用之间,臣忠、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居室、朋侪恰比,一举一动,皆有当然不易之则,”[3]109“饥而食,渴而饮,人人皆然也,而食所当食,饮所当饮,即道也。”[3]110所以说道很小,人事的一举一动皆可称作道;然而道又很大,它存在于天地之间,“践而履之为德行,措而施之为事业。”[3]267道的本质在于亲身实践而不是用言辞来说明,故“有体无用,不可以言学;有畴不用,不可以言锡”[3]267。蓝鼎元的文道观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文以载道。他说:“文以载道也,道莫备于孔、孟,而发明于程、朱,制义阐孔、孟之蕴,衍程、朱之传者也。诗、词、歌、赋,不可谓文。秦、汉、唐、宋之文,名为古,不能古于六经、《语》《孟》。今之为古文者,摹秦、汉、唐、宋耳。”[3]97他又说:“世人沾沾举子业,以为极宇宙间之能事,高者习雕虫,摹佶屈,自命诗文大家。大雅君子亦乐之,不知文所以载道也,必有益于天下国家,身心性命,乃为可贵,讵徒以辞华而已。”[3]98在蓝鼎元看来,所谓的诗、词、歌、赋以及秦、汉、唐、宋之文都不能算古文,只有六经、《论语》《孟子》这样能阐明孔、孟思想,发衍朱子理论的才是真正的古文。可见蓝鼎元先是筛选了在他看来符合文以载道的文章典范,接着指出文所以载道在于有益于天下国家,而不在于辞藻修饰;辞华只是雕虫小技,未能有补于世道人心,故蓝鼎元对此持不屑态度。
第二,文以明道。“文所以明道也,必有益于天下国家,为世道人心所不可或缺者,然后为之。如以辞华而已,何贵有是文哉!六经文字非后人所能及,以其载道也。”[3]500不论是以文载道还是以文明道,蓝鼎元都强调了文章要对天下国家和民生有所裨益,文章只是手段,而道才是最终的目的。蓝鼎元又说自秦汉以后,“文日繁而道日晦”[3]500,韩愈的文章因其高扬文道统一观而最接近道,然而“朱子犹谓其止是学文,所以见道不亲切”[3]500,更别说那些辞藻华美的文章了。可见文为道服务的观念在蓝鼎元这样崇尚朱子学说的儒者脑中已是根深蒂固。
第三,文道合一。“所谓道之显者谓之文,非浮夸粉饰,欺人媚世之谓也。胜质之文,不可为文;风云月露,雕绘辞章之文,詹詹渺小,亦非吾所谓文也。”[3]272蓝鼎元以为,文为道服务,“文胜质则野”[8]12,文采胜过内容的,那就不能算作文,至于那些藻饰雕绘的更不可同日而语。显然蓝鼎元依旧高持着以内容质实为基准的旗帜,对文采藻饰派加以反对抨击。他在《艺文小序》里也说道:“道之显者谓之文。子瞻言‘为文必与道俱’,朱子非之,谓其视文与道二也。后世以学文学道为两途,如冰炭之不相入,雕琢辞华,镂金错彩,靡然于伦理经术之外而命之曰文,自以为登韩、柳之堂,排欧、苏之闼矣。或摭古字,使人难识,掇拾梵音,矜心高妙。由君子观之,曾涕唾之不若耳。”[3]121甚至于苏轼之文先文后道的说法在蓝鼎元这样的朱子学家看来都是不符合文道规范的,而惟有文道合一,这样的文章才是蓝鼎元所谓的经世之文。故他又言:“若夫经世理物,发挥至道,有益于天下国家身心性命之文,与夫起衰拭靡古雅高清之韵,海潮雄浩之观,则所望于此邦作者匪细也。”[3]121
既然文与道要合一才能算是阐发人心世道之文,那么具体又该如何做到呢?蓝鼎元说:“淑乎礼乐,自日用、饮食、洒扫,应对进退之地,居敬以收放心,读书穷理以扩充其知识,致力于修身齐家之要,而讲求乎经世理人,有体有用之学,笃实辉光,日新月异,斯可谓天下之至文矣!”[3]272所以要熟悉礼乐,应对日常进退有序,做到居敬守礼;广读诗书,做到身修家齐,提高自身的素质,还要时常学习经世致用之学问,做到温故知新等等,惟有如此才能写就天下间最极致的文字,即经济之文。
(四)文气论
自孟子以来就提出的“吾善养吾浩然正气”[8]62这一命题,曹丕在《论文》时以气喻文,遂开文气一说。韩愈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9],尤为深造自得之言。延至明清,更是大而广之,刘熙载也说过:“文得元气便厚。”[10]由此可见文气说的影响之大。蓝鼎元在论人论文亦时常提及之,他说:“余读《宋史》,见公正色立朝,直言敢谏,扶纲常、植国本、除新法、恤民命、进君子、抑小人,有旋转乾坤之力,忘身殉国之节,至大至刚,浩然不可挠之气”[3]322“百世下见君之书,忆君之品,觉君之生平奇气,磅礴郁积于龙跳虎卧之间”[3]332“盖浑身雄浩之气充塞,洋溢勃勃而不可遏”[3]332等,可见其对浩然正气的推崇。天地万物,生来即富有正气,所谓:“气之移者,浩然常塞于天地之间。”[3]909然而人生来没有,却是可以通过学习知识而后天培养成,即,“造物清明之气,钟之独厚,而意见知识又未有以梏其灵,则夫见美而能趋,见恶而能去,亦吾身自有之迹也。”[3]854蓝鼎元以为文章不可无气,所谓“文章意气,千古不蔽,虽有乔松,岂能加焉”[3]327。唯有读书明白道理后才可以养其气,“故曰:‘文以气为主。’”[3]500文章不可无气,更不可无浩然之气,所谓“善养浩然之气则发为文章,正大雄厚,无靡曼邪僻之习”[3]500。只有文章有了浩然之气,才具备雄健笔力,方能抒发议论,纵横于天地,写就不朽之文章。“养雄健之笔力,奋浩然之正气,夫是以发为文章,声金振玉,纵横天地”[3]465,更甚者,“高者闻天,深者入渊,迅疾如风雷,镇重如山岳,而议论和平,尽情切理,节奏闲雅,谐协宫商,斯可以谓之文矣。”[3]500所以说蓝鼎元的文气说要点在于他推崇浩然正气,并将之运用于文章当中,强调好的文章需要雄健的笔力,更需要充溢雄劲之气。
除了强调文气外,蓝鼎元还将文章与国运联系起来,认为:“文章与国运相关,盛世元音,晚季变徵,低昂正自有辩。”[3]92蓝鼎元以为文章发声高低与国运紧密相关。文章气盛则国运强盛;文章气衰则国运低迷。曾国藩也以为:“文章与国运相关,天下事可知矣。”[11]因此,“士君子不幸而穷,当借为他山攻错、进德修业之资,而往往狂跳叫号,堕造物之坎窞束缚,颠倒颓废,百端何工之云?”[3]92蓝鼎元借此对那些士人提出批评,认为一代之文章便有一代之国运,士人不努力进德修业反而陷入颓废的窠臼,这极大地违背了文为道服务,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初衷,因此“讲求经世理物,兵、农、礼、乐之经济,使皆有体无用达”[3]109,惟有这样才可成为国家之名臣,才能更好地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五)反对时文,提倡制科
蓝鼎元在其文论中明确表示出对时文的反对。时文与古文自明清起便相对立,蓝鼎元认为“时文小道,亦建旗鼓”[3]101,对时文的轻蔑由此可见。他说:“余惟时文一道,本非可见诸施行有益于民生国计,又非可与经史百家并垂不朽,特为国家以此取士,不得不镂心刻骨,敲戛金石,期足以辅翼经史,黼黻皇猷。”[3]93他认为时文既不能有益于民生国计,又不能永垂不朽,只是国家取士的手段,故他不得不俯就。正如他在自序里曾说道:“余少薄帖括,以为文辞末也,帖括抑又末矣。虽勉效操觚,心弗善也。顾以国家取士,舍此末由,即有君相特达之知,奇才异能之荐举,乡俗犹将以偏途病之,而征辟荐举,旷世罕逢。虽有经济才能,无以见诸事业,于是俯首治帖括焉。”[3]104事实上蓝鼎元早年为求科名力攻过时文一段时间,《先王父逸叟先生暨王母陈孺人行状》一文有载:“不孝鼎元既稍长,为时文颇自负。先生曰:‘程、朱曾为时文否?’鼎元曰:‘非是无由得科名。’先生曰:‘皋、夔、尹、说皆得科名否?’鼎元不敢复言。”[3]355又如《朱贞女传》有言:“诸妹喜为时文,贞女独不,曰:‘非阃内事也。’”[3]183可见时文一道并不为程朱学者所看重,就连闺阁中女子也有所不为,故此蓝鼎元才日轻之。尔后蓝鼎元专攻古文辞,并日益进步,他对清初古文家所写的散文情有独钟,也因此改变了自己作文的态度还加以模仿:“始则喜成、弘、庆、历间之文,既而以为俭也。恣肆于启、贞两朝,及国初诸公宏博深厚之作,虽画虎类狗,栩栩然帚千金尔。”[3]104同时他的授业恩师如陈汝咸、沈涵等人又对之加以鼓励,这更增强了蓝鼎元的信心:“四明廷尉陈公,方宰吾邑;归安阁部沈公,督学闽南,皆不以余为谬,期许甚奢。”[3]104
蓝鼎元一向主张经世致用之学,而时文却不足以称为有体有用,他说:“时文之大用,不过弋获科名,即使传之不朽,亦等雕虫细玩,何补于世道人心?”[3]95故在他看来如时文之类的应世之文并不能称作文,就算长篇大论也没有什么用处,还不如“躬行体验,随事省察,内淑其身心,外宜其民物”[3]98,这才是有道君子之所为,唯有这样,“不期文而文至焉”[3]98。世俗所谓的时文不过是如皮毛、形体般外在的东西,与身心性命无关痛痒,“锥之不痛,刺之不痒,随意增删,不见短长。”[3]100只是因为某一天被主考官相中就认为时文是金科玉律,然而真正的君子是不待见它的,惟有那些庸鄙浅陋的人,才视之为珍宝用来谋求科名:“浅夫掇取油滑,学究剿袭饾饤,纡青拖紫,有如拾芥,以此博科名。”[3]93即以此来衡量,天下间那些真正能知文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是百中难求其一。更何况对于那些汲汲于此道的士人来说,“不学为圣贤,祗欲以文章自表见己,非余之所望。况斤斤科举之文章,以主司意见为贤否,余亦乌知戋戋而以此起耳。”[3]96
不过蓝鼎元虽对于热衷此道的士人不客气地加以批评,但对制义一科却持肯定态度,他说:“当世以制科取士,士竞习为科举之文,镂心呕血,刻意时趋,若宇宙间经天纬地之事业,无有出于此者。既已敲金戛玉,学成一家,而闻者见者,熟视犹之无睹,几欲发狂跳叫,乃有人焉。”[3]95他认为制义一科可明圣贤之道,可正豪士之心,“为制义者,疏六经、《语》《孟》精微糟粕,则视乎为者之能不能,岂制义之过哉!虽有绝世聪明,而不学为制义,自诩作古文诗赋,其中必有扞格难合。似是而非之,病其心思,不纪其经术,亦必不醇。国家以制义取士,既可明圣贤之道,又可纯豪杰之心,岂诸子百家所可同日语哉?”[3]97
此外他也重视馆阁之文,认为其气象雍容,正表现出盛世风貌。他说:“场屋廊庙之章,必有中正和平、昌明驯雅之气象。”[3]97他强调文章写作的规范,即自然而然方为中式标准,他说:“匪高、匪深、匪新、匪奇,炼不造作,刻不伤气,镕经铸史,不见饾饤,自然而然乃为中式,岂无一定之绳墨哉?”[3]97故“前车之轨辙,后车之率由,从绳则正,天下所以无弃木也”[3]97。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中式呢?在他看来,“欲言则言,欲止则止,无描头画角,岛瘦郊寒之态。故命意欲高,措词欲确,筋脉欲真,精神欲旺,结构欲圆,气度欲雅,锤练精纯,韵味悠永,斯可以言中式矣。”[3]104
对于八股文章,蓝鼎元持有与他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八股文章若是符合道,且于世道人心有所裨益,那么也是可以受而广之的。“若八股文章,亦必有当乎道,经经纬史,有理有气,可以传之后世而不敝。”[3]465他对八股文持较为开明的态度,这一点颇值得人肯定。
三
蓝鼎元论诗,主张情、理、气三者的统一。他说:“凡作诗文,必有情、有理、有气,三者缺其一不可也。”[3]500故首先他认为诗以意理为主。何为意理?意理犹义理,即有想法有根据。正如其所言:“作赋吟诗,尤必以意理为主,诵诗三百达于政而能专对。”[3]465又言:“诗必有义理,惟深于道者能知之。不持作诗者久不讲,即论诗者亦鲜及之矣。无理无义,则为无益之浮谈。雕饰虫鱼,藻缋风月,俨然自命为仙翁,吾不知其何为也?”[3]500他认为作诗若是缺乏义理,只有文采雕饰,那便称不上是首有用的诗,作诗有义理有根据才是深于此道,可见蓝鼎元论诗仍然强调它的实用性。此外蓝鼎元也强调诗歌的功能,认为诗歌能够检验人的德性品行,即,“诗文虽辞章之学,可以觇人品,验德性,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忠臣孝子、端人正士,才能志节,福泽勋名,未有不隐跃流露于诗文之间者。”[3]500
其次,他强调诗歌需有真情,并阐发忠君爱国之意。他举了个例子,说杨时认为苏轼的诗:“多讥玩,无恻怛爱君之意,此善于言诗者也。”[3]500蓝鼎元赞同杨时的观点,夸他善于论诗,可见他也认为诗歌需以忠君爱国为意,所以他对苏轼的诗作亦颇有微词:“诗不本忠孝节义,虽穷巧极工,亦不足言,况讥玩乎?子瞻未闻圣人之道,徒欲以诗戏谑而已,学者戒之。”[3]500再者蓝鼎元也认为诗贵真挚,以真情实感为先备,其次再来论技巧之工。“诗以道性情,必真挚而后工焉。有一字不从肺腑中流出非诗也。”[3]500
最后,诗要有浩然之气。在蓝鼎元看来,要作好诗,就需要读书养气来培养,所谓:“心粗气浮,不可以为诗;格调卑弱,意杂味短,词野字俗,庸腐浅陋,雕凿小巧,皆不可以言诗也。故欲老、欲清、欲雅、欲深、欲纯,雄浑沉痛、悲壮苍古、悠游平淡,各造其极,方得为之,非十年读书养气,其孰能与于斯?”[3]92蓝鼎元强调气对诗歌的作用,他不仅认为文章需有文气,诗歌也应有浩然正气。“善养浩然之气则发为文章正大雄厚,无靡曼邪僻之习。高者闻天,深者入渊,迅疾如风雷,镇重如山岳,而议论和平,尽情切理,节奏闲雅,谐协宫商,斯可以谓之文矣。然非读书穷理以养其气者不能也,故曰:‘文以气为主。’作诗亦然。”[3]500可见蓝鼎元强调诗歌是情、理、气三者的结合。
此外,他对诗穷而后工的观念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诗穷而后工不过是针对有为之人而言,并不能统而概之,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穷者劳筋饿肤,幽忧拂郁,矻矻无所成就,发之于诗,镂心呕血,悲凄激楚之韵,或足以动天地、泣鬼神,而和风庆云,清庙明堂之气有所不足,则亦非邦家太平之瑞也。”[3]92就这一点上看,蓝鼎元依然秉持着诗歌的风雅传统,认为诗歌的本质主要还是发为宗庙之音,为盛世所服务。
可见蓝鼎元的诗歌理论与古文相似,依然不脱实用性。与“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思无邪”[8]8相比,他对诗歌的思想要求得更严,即必须发为宗庙之音,表达忠君爱国之意;他认可诗言情这一功能,但更倾向于言忠君爱国之情;他的诗言志,却多言义理与道,虽发为浩然中正之气,却不脱理学气息,是典型的理事诗。他认为诗可以检验人的品性德行这一观点虽然依然从道学的角度出发,但论述得却颇为新颖,令人眼前一亮。
结 语
蓝鼎元的文论和诗论都秉承着程朱一脉传统,以理学为宗旨,以学术为载体,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将学术、理学与文学三者结合起来,体现了清初闽地的文学传统。他的文学理论指导着他的文学创作,并逐渐引导、影响了闽地文风。清初闽地文学氛围其实并不浓厚,但理学氛围之浓厚尤其是道南理学一派却在文学史上甚为出名,如黄道周、李光地、蔡世远等人皆引领着闽地的理学风尚。蓝鼎元亦是一位理学大儒,但他的经世致用之文风却成为闽地文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说他独特是因为他以自己切身的经历常提出卓为有用的见解,清乾隆帝就甚为赞赏他的《东征集》《平台纪略》诸书,《东征集》中有清高宗的御批:“蓝鼎元所著《东征集》,其言大有可采,着常青、李侍尧购取详阅,于办理台湾善后时,细加查核。有与见在事宜确中利弊者,不妨参酌采择。”[3]602著名历史学家连横也说道:“鼎元著书多关台事,其后宦台者多取资焉。”[12]可见他的经世之作于清王朝乃至今日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而闽地的经世致用之风亦自蓝鼎元以来一直延续下去。
[1]谢金銮.蛤仔滩纪略[M].台北:台湾大通书局,2009:369.
[2]林奕斌.蓝鼎元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3]蓝鼎元.鹿洲全集[M].蒋炳钊,王钿,点校.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
[4]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M].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译编.台北:台湾书房出版有限公司,1985:634.
[6]光绪漳州府志[M].沈定均,续编.吴联熏,增纂.北京:中华书局,2011:34.
[7]周寅宾.明清散文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8.
[8]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95.
[9]韩愈.韩愈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8.
[10]刘熙载.艺概注稿[M].袁津琥,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11]罗益群.曾国藩读书记[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229.
[12]连横.台湾通史:卷34(列传6) [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0:705.
(责任编辑:刘 燕)
Study on Literary Theory of Lan Dingyuan
Ling L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Minnan Normal University,Zhangzhou Fujian 363000,China)
It is illustrated that Lan Dingyuan’s literary theory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his literary creation. His literary theory includes prose theory and poetics, on prose theory, he proposed that the article must be learnt for prose masters and classics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advocating the thought of studies for practical utility, emphas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ilosophy of Confucian school of philosophy to be utilized, and the role of style of writing. His poetics adhered to prose theory, combined with real feelings, argumentation of essays and style of writing. Lan Dingyuan’s literary theory not only reflects his literary creation, but also plays a leading and improving role in the literary style of Fujia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Lan Dingyuan; prose theory; poetics
2017-03-05;
2017-05-28
凌 丽(1991-)女,福建省福州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10.3969/j.issn.1672-7991.2017.02.006
I207.62
A
1672-7991(2017)02-002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