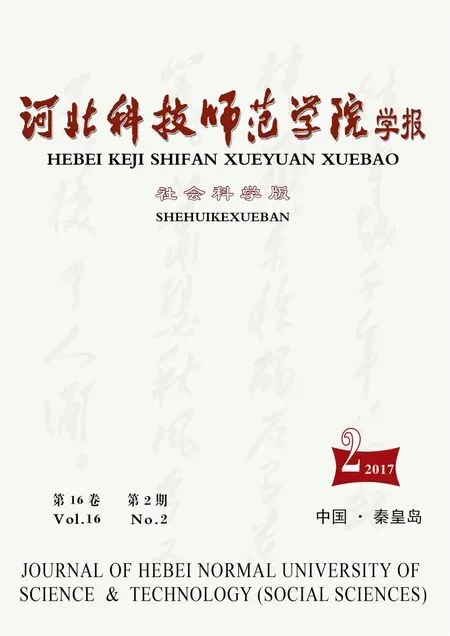论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的叙述缝隙
贾晓梅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论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的叙述缝隙
贾晓梅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创作于1980年的《爬满青藤的木屋》虽于1981年获得短篇小说奖,并为古华赢得了一定声誉,但却反映了作家新时期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靠拢的功利性目的。现代性叙事、人道主义叙事与情爱叙事是小说反叛“文革”话语的三大叙事类型,而讲述话语时代和话语讲述时代之间的时间裂缝,则使它们呈现出各自的叙述缝隙:现代性追求的无力感、人道主义中的女性声音以及情爱话语的欲语还休。
《爬满青藤的木屋》;反叛性叙事;时代交替;叙述缝隙
在《木屋,古老的木屋》一文中,古华曾透露《爬满青藤的木屋》取材“文革”时期一位守林人的真实故事。小说由传统封建愚昧思想对民众的毒害进而转向对现代文明的呼唤,似乎顺理成章。但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认为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古华创作故事的1980年代,正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决定了《爬满青藤的木屋》不仅仅是一个纯文学上的小说文本,小说对现代文明的呼唤也不仅仅是作家的个人诉求。在写于1981年的《对精神文明的呼唤——简谈<爬满青藤的木屋>》中,雷达虽然指出了古华对传统落后思想的揭露以及对封建愚昧与“文革”极左路线这二者的同构,但却没有看到政治意识形态对古华创作的影响。事实上,以“文革”作为叙事背景,并对极左路线和“四人帮”专制统治进行控诉的《爬满青藤的木屋》,与其说是作家机缘巧合取材现实的文学作品,不如说是其在新时期初迎合国家话语和主流叙事的策略性文本。而以叙述缝隙重新解读《爬满青藤的木屋》,不仅有利于还原文本被遮蔽的叙述声音,同时也有助于揭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小说创作与当时国家政治文化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性别/政治策略下的现代性叙事及其无力感
在回复读者来信中古华谈到:“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变革时期”“时代对作家如此慷慨,作家怎能辜负了时代。”[1]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迫切希望实现创作突破的古华,积极响应“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政策。写于1980年的《爬满青藤的木屋》,“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造而成”[2]:因怀疑自己的女人和新来知青存在不正当关系,五岭山脉没有文化的守林人将两人痛打致残。这一悲剧故事折射出了传统封建思想对守林人的严重毒害,但小说将其与“文革”左倾路线相互指涉,则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初作家对“拨乱反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等国家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主动靠拢。
为了凸显与“文革”时代的断裂,新时期的中国吸收着新的思想,承载着新的任务,同时也呼唤着新的文明。1980年代初,为了推进“两个文明”和“四个现代化”建设,我国进入了社会建设的新阶段。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中国建成现代性民族国家的一项重要方案,也得以凭借新的面貌在新时期继续施行。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向往,反映了新时期中国的现代性诉求。而文明背后所代表的进步和开放,不仅对中国传统封建落后思想形成了反叛,同时也回应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对以封建专制思想为温床的“文革”左倾政治路线进行否定的主流话语。在新时期语境中,由于现代民族国家在本质上属于建立在文明、科学与进步基础之上、新的“菲勒斯”中心秩序。因此,这一时期的小说往往通过具备“父性权威”的男性与带有现代特征的知识分子的结合,以期实现后革命时代对中国的现代性想象。而女性在这些小说中则继续承担他者身份,扮演着被男性知识分子施以现代启蒙的“蒙众”角色。正如1980年代小说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表述成“男人与女人之间启蒙与被启蒙、施救与被救的故事,甚至是一次代表着文明与愚昧两种力量的两类男人间对女人的争夺”[3],把性别/政治融入小说创作,亦成为《爬满青藤的木屋》实现现代性叙事的一项重要策略。
在李幸福的协同下,盘青青最终完成了由一个封建专制受害者向急切渴望现代文明的“人”的转变。但当把目光投向两位男性时,小说的现代性叙事却显现出了反叛的无力感。首先,李幸福无力承担现代启蒙者角色。尽管1980年代,古华有意将李幸福塑造成从城市来到乡村,并承载着拯救蒙众的现代启蒙者。但小说文本从1975~1981年的时间缝隙,却使李幸福的实际行为偏离了原来的人设。小说中李幸福是一个在“‘文革’初期误入过歧途”并“被林场有关人士视为异类”的“时代的‘弃儿’”[4]41和“可怜巴巴的断臂知青”[4]40。尽管他掌握着现代文明和科学知识,但王木通在绿毛坑建立的封建家长专制以及国家权威赋予王木通的权力(林场主任设定的约法三章),却使他一再受挫。在护林建议被王木通否决后,李幸福不仅“气馁了”[5]9,而且也“对王木通不由得生出了一种畏惧的心理”[5]9。而之后遭到场部领导训斥后,他更是“恨不能变成个文盲愚昧大老粗,加入王木通们的行列里去”[5]23。作为“文革”年代的受害知青,李幸福对科学文化知识,并非坚信不疑,而“建立学习小组,学政治”[5]9以及为参加革命可以不惜加入王木通队伍的想法,则反映了其对“文革”政治和左倾路线的认同态度。
其次,对以王木通为代表的古老落后文化,古华的态度复杂而暧昧。虽然小说将王木通及其所表征的中国传统落后文化与“文革”路线相互指涉,但无论是对于王木通还是古老落后文明,古华都很难做到完全颠覆。在对王木通的刻画中和对其结局的设置上,古华是留有余地的:在揭露王木通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劣根性的同时,亦表现了其苦吃蛮干、勤劳质朴的传统美德;而在小说结尾,则让王木通带着两个孩子继续到另一处深山老林传宗接代。其次,对于古老落后文明及传统生活方式,古华也没有做到完全否定:绿毛坑虽落后封闭,却环境优美,宛如世外桃源;小说结尾,王木通到天门洞传宗接代“顺乎人情天理”[5]27。面对传统,在反对声音最为激烈的“五四”时代,周作人尚且明确指出:“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6],而1985年,风靡一时的文化“寻根”热也未能完全解决现代与传统间的复杂关系。因此,对于中国自前现代社会便沿袭下来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身处新时期的古华无法做到单方面否定,也在情理之中。
二、人道主义叙事中的女性声音
如果说时间缝隙的存在,使《爬满青藤的木屋》的现代性叙事展现了叙事逻辑上的矛盾和分歧,那么另一反叛性叙事——人道主义叙事,则于时间缝隙的前后错位中,使隐匿其中的女性声音得以发声和强化。并非“空白之页”的女性人物正是在获得发声契机的同时,于人道主义叙事中撕开了文本的另一道叙述缝隙。
197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通过“改革开放”表达了对“文革”政治的颠覆和反叛,而新时期文学则凭借对“文革”专制文艺思想的反思,逐渐确立了自身在交替时代下的价值定位。但事实上,无论是国家意识形态对“文革”的颠覆,还是文学界对“文革”的控诉,在话语背后都表达了急切的现代性诉求。而伴随着中国进入后革命时代,对人道主义的重视和重提成为新时期对“文革”进行反思和对现代性进行向往和憧憬的重要策略。最早在1979年,朱光潜就以人道主义为立场,反思了“文革”对人性的禁锢。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中,朱光潜指出,文革时期“四人帮”法西斯专政设置了许多禁区,其中之一便是“‘人性论’这个禁区”[7]。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人道主义作为否定和反思专制政治的价值体系,在文坛获得了自身的历史合法性,而呼唤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回归也成为新时期文学反叛“文革”话语以及表达现代性诉求的重要项目。而正如“文学与政治对人的备加关注的强大共鸣效应,使得文学对于人的价值尊严的重新肯定成为新时代的自然趋势”[8]。作家对人性、人道主义主义的讨论,成为中国1980年代前期推动文学创作发展的重要思想文化现象。《献身》《湮没》《相逢在黑夜尽头》《夜客》《三生石》以及《人啊,人!》等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反映人性复苏和人的本质回归的代表作品,它们的发表,引发了新时期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文学创作潮流。而同为创作于这一时期的作品,《爬满青藤的木屋》亦对当时人道主义文学创作潮流进行了回应。
虽然“人道主义”在不同理论倡导者那里有着不尽相同的阐释,但通常意义上,“泛指一切强调人的地位,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幸福,满足人的需要和利益的思想体系。”[9]在《爬满青藤的木屋》中,正是通过盘青青“人”的意识的觉醒,古华肯定和维护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并实现了对新时期人道主义文学潮流的附和。在李幸福带来的现代文明的引领下,盘青青逐渐从一个被人驯服的生育机器蜕变成具有反抗精神的“人”。在这一变化中,小说叙述者古华亦始终不断强调,盘青青对李幸福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都是一样的可怜人。盘青青觉得“那后生家和自己一样的可怜”[5]14,“只有‘一把手’还尊重她,把她当个人”[5]14。而当李幸福对自己的主动接近面露难色时,她更是对李幸福生发了“不像个人”[5]21的怨恨。
新时期以来,大部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作品都借由受害女性的觉醒来探讨人性的价值和呼唤人道的回归。但正如《爬满青藤的木屋》中,盘青青最后说出“随便你。反正你到哪里,我就跟你到哪里”[5]26这一对男性的依附性话语,1980年代初,在大多数作家眼中,女性不过是他们人道主义叙事的工具,即所谓的“空洞的能指”和叙事的“他者”。然而,在分析《青春之歌》林道静形象时,贺桂梅曾指出:“‘能指’本身从来就不会是‘空洞’的,它总是在具体的、历史的语意结构关系中展开意指过程的。”[10]因此,女性人物并非皆为“空洞的能指”,《爬满青藤的木屋》中的盘青青也并非古华所希望的那样,仅仅满足于成为受人理解和尊重的“人”。事实上,盘青青始终都存有自身的女性意识,虽然人道主义叙事具有遮蔽作用,但在王木通和李幸福所代表的两种话语权力的相互抵牾中,盘青青实则获得了女性话语的言说空间。李幸福未到绿毛坑之前,盘青青曾要求王木通帮自己购买用来梳妆的镜子,也提出到场部去看一看。由于王木通的阻拦,她选择了服从自己的男人。而李幸福到来之后,王木通虽然将自己与李幸福二人的矛盾转化为对妻子的进一步“施虐”,但却使盘青青在“受虐”过程中,意识到女性自身的牺牲地位。小说中,盘青青在遭到施虐后,生发了一系列重建女性自我主体性的反抗行为,如晚上睡觉时,她不再面向丈夫,同时也开始注重起自己的穿着打扮。盘青青虽未曾在拉普特朗所谓的“幻想时刻”看见自身,但“受虐是性的建构时刻,因而也是主体的建构时刻”[11]190,在“受虐”中,她实现了“反求回到主体自身的自我”[11]190。此外,盘青青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还表现在对女性自我尊严和女性形象的维护中。比如尽管每晚盘青青都遭到丈夫的打骂,但在李幸福面前她却一再否认,她不愿让自己受辱被李幸福知晓。再者,盘青青在与李幸福的交往过程中也总是处于主动位置。虽然李幸福由于自身的现代性启蒙者身份,将盘青青置于被拯救者的位置,但他实则缺乏启蒙角色应有的主体性。而每当李幸福退缩之时,出来占据主动位置的正是盘青青。对于李幸福这样一个处处受到排挤的可怜人,盘青青不仅不由生发出“一种母性的爱怜”[5]20,而且当李幸福出于对王木通的畏惧不敢和她主动往来时,她则选择主动帮李幸福洗衣服,主动为其购买生活用品。
三、情爱叙事的欲语还休
1982年,《芙蓉镇》的获奖让古华声名鹊起,但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便已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1978年,古华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莾川歌》出版,这部集子收入了古华于文革前后创作的三十多个作品。由于受“文艺从属于政治”“ 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演中心”等“左”倾思想的影响,这些作品在艺术成就上有所欠缺,未能获得更多认可。随着1976年“四人帮”集团的瓦解以及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的讨论,1977~1979年,中国文坛出现了一大批恢复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文学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古华不仅认识到了自己以往创作的不足,亦深刻意识到文革“三突出”原则对自己的严重束缚。因此,对古华而言,在创作方法上寻求突破和转变,是他新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方向。
对于1970年代末我国文学创作的特点,孟繁华曾谈到:“1970年代末期的文学,首先迈入了人的精神情感领域,它大胆地撕开了种种面纱,揭开了人的最隐秘、也最具私人性的角落,文学的私人性话语时代的帷幕,在谨慎而羞涩中缓缓启动。”[12]其中提到的“私人性角落”便包含男女情爱这一内容。“文革”时代,由于受国家意识形态的抑制,表现男女之情的情爱叙事一直是文学创作的禁区。而到了后革命时代,作为对国家话语在政治层面上对“文革”进行反叛的响应,新时期作家开始在文学创作领域打破禁区,尝试情爱叙事。《爱情的位置》《我应该怎么办》《爱的权利》以及《爱,是不能忘记的》是1970年代末以探讨爱情为内容的代表性小说。而到了1980年代,情爱叙事则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发表于1980年代初的《雨,沙沙沙》以及《北极光》便突出表现了人物在追求爱情道路上的执着与勇敢。面对新时期小说的新变化,一直将寻求突破、反思历史作为创作目的古华,无疑看到了情爱叙事对“文革”话语形成的强大反叛力量。在《爬满青藤的木屋》中,李幸福和盘青青之间的爱情故事是小说情爱叙事的重要内容,但由于故事讲述时间和故事时间之间的错位,这一叙事呈现出了叙述上的缝隙。因此,如果说在《芙蓉镇》中,古华通过对胡玉音等人的情欲书写,实现了情爱叙事的淋漓表现,那么在《爬满青藤的木屋》中,他则无奈遭遇了这一叙事的欲语还休。
正如王宇在分析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地位转变时总结道:“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意识形态变更使知识分子从社会权力结构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社会的启蒙者、引导者、代言人、民族国家大业的中流砥柱。”[3]131198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实现了较大的逆转,其在文学创作中的“臭老九”污名化身份也在不同作家笔下被不断颠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知识、有文化、有良知”“在作品中占压倒优势”[13]的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小说中大多以男性身份出现,而女性形象和自然化、本质化的“女性气质”则作为一种尴尬的能指,成为作家们“寻找男子汉”项目的组成部分。正是希望借助男性长期积累的性(权力)资源以及男女两性欲望话语的回归,新时期小说期望完成对现代知识男性主体身份的建构。而《爬满青藤的木屋》中欲望话语的呈现,既是古华对“文革”文学的反叛,同时也是其建立男性知识分子自我主体性的策略。
小说中,李幸福的欲望话语不仅呈现出些许急切与躁动,而且还包含着对盘青青肉体的着迷与沉醉。初到绿毛坑,李幸福不是将盘青青当作亲人意义上的“姐姐”来对待,而是产生了男女之间不适合走太近的想法:“注意着和人家保持个应有的距离”[5]5。但“年轻人总是不耐寂寞”[5]5又让他的内心躁动不安。当在对孩子们进行刷牙等现代生活方式的启蒙时,小青一句“阿妈最喜欢和我亲嘴了,她的嘴巴好甜,你不信,就自己去亲一下,闻一闻”[5]7,让李幸福不禁脸热心跳,而“仿佛自己有了什么不正当行为”[5]7的负罪心理,则表明李幸福似乎早已对“亲嘴”行为进行了自我想象和思想实践。如果说保持距离和“亲嘴”想象属于隐性欲望,那么小说以李幸福的人物内心视角对盘青青突然造访时进行的衣着和身体描写,则揭露了其对盘青青的肉体欲望。小说中李幸福注意到,劳作回来的盘青青由于衣衫单薄吃紧,领口下的纽扣被绷开,那具有极大诱惑而丰满的胸脯,便半遮不掩地显露在他的眼前。而面对此情此景,李幸福则不禁失魂落魄、沉迷其中。作为下放知青,李幸福虽然可怜,但在盘青青那里,却是幸福的。他不仅从盘青青那里获得了精神上的支持,还可以通过对她身体的欣赏,获得身为欲望观看主体的征服力和满足感。因此,将盘青青设定为李幸福的欲望对象,古华的用意再明显不过:通过知识男性对女性的欲望话语,建立李幸福现代男性知识分子主体性,并对“文革”的禁欲叙事进行反叛。
然而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是,李幸福始终身处话语讲述的“文革”时代。事实上,他无法从根本上完成后革命时代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既定任务。因此,当听到小青无意说出亲嘴的话时,他尽管有所向往,但下意识做出了转身躲闪的逃避举动。而当盘青青主动上门请求帮忙时,他虽注目欣赏,并一度将她置于“被看者”位置,但随后他的“抬不起头”、神色“惊惶”[5]20以及说话结巴等,无不真实表露了其内心的怯懦、恐慌与缺乏自信。正如在现代性叙事中,身处“文革”时代的李幸福背负着来自以王木通为代表的传统落后文明以及以场部为代表的“文革”政治意识形态两方面的双重压力。在小说的情爱叙事中,李幸福仍旧无法避免这一艰难处境。一开始,国家权力机器的政治态度便表明了李幸福的“被改造者”标签,不仅在场部领导那里,李幸福无权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到了林场也无法与有国家政权作为支撑的“山野粗人”王木通相抗衡。在以政治身份定义一切的“文革”时代,李幸福的政治“去势”无疑使小说的情爱叙事大大削弱。因此,如果说李幸福一开始对盘青青心生好感却又保持距离,是源于伦理道德的规约以及青年知识分子的羞怯,那么之后他对盘青青的刻意躲闪,则反映了他对政治身份比自己优越的王木桶的畏惧、害怕以及因政治“去势”而产生的自卑、妥协心理。
《爬满青藤的木屋》在盘、李两人情爱叙事上所遭遇的叙述困境,虽然某种程度上受20世纪年代初主流爱情题材小说注重圣洁精神恋爱这一叙事的约束,但欲望主体李幸福的向后退缩却是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身处故事讲诉的1975年,李幸福受到来自以王木通为代表的前现代封建专制以及场部领导为代表的“文革”国家意识形态的双重压制。因此,他对盘青青的欲望话语无法像置身于后革命时代的古华那样,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并表现出古华所期望的欲望主体性。小说情爱叙事的叙述缝隙表明,当创作文本存在后革命时代与革命时代的时间裂缝时,所谓的反叛性叙事,不过是作家着眼于所处时代而进行的策略性建构。
结 语
由于古华曾说“这篇小说,是对精神文明的呼唤”[4]43,众多评论者随后便以此作为自己的评论基调,从而忽略了作家对守林人故事蓝本进行加工利用的真实意图以及这种意图所带来的叙述缝隙。性别/政治策略下的现代性叙事、人道主义叙事以及情爱叙事,是古为华反思“文革”并回应后革命时代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而精心设计的三类反叛性叙事策略。但讲述话语时代与话语讲述时代之间的时间错位,致使其他声音从三类叙事中旁逸斜出,并形成小说的三大叙述缝隙:现代性叙事的无力感、人道主义外衣下的女性发声和情爱话语上的欲语还休。
[1]古华.遥望诸神之山的随想[M]//《人民文学》编辑部.作家文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385.
[2]古华.作家谈创作:古华谈《爬满青藤的木屋》[J].作品与争鸣,1981(8):76.
[3]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4]古华.木屋,古老的木屋——关于《爬满青藤的木屋》[M]//巴伟,虞阳.中青年作家创作经验谈.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
[5]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83.
[6]李子云,赵长天,蒋思和.世纪的回响·批评卷:周作人批评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222.
[7]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J].文艺研究,1979(3):39.
[8]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00(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38.
[9]马国泉,张品兴,高聚成.新时期新名词大辞典[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123.
[10]贺桂梅.“可见的女性”如何可能:以《青春之歌》为中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3):4.
[11]周蕾.爱(人的)女人:受虐、幻想与母亲的理想化[M]//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12]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70.
[13]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159.
(责任编辑:杨燕萍)
Study on the Narrative Gap of Gu Hua’sTheIviedCabin’s
Jia Xiaomei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Shandong 266100,China)
AlthoughTheIviedCabinthat was created in 1980 got the award of excellent short story of China in 1981 and won reputation for Gu Hua,it reflects the author’s utilitarian purpose of approaching the discourse of modern nation-state in the new period.The modernity narration, humanitarian narration and love narration are this novel’s three narrative types which rebel agains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discourse,but the gap of time between the age of telling story and the story time causes them to show their respective narrative gap: the powerlessness of modernity pursuit, female voice in the humanitarian and hesitant statement in love discourse.
TheIviedCabin; rebellious narration; alternation of the age; narrative gap
2017-03-26;
2016-05-06
贾晓梅(1993-),女,四川省西充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10.3969/j.issn.1672-7991.2017.02.007
I206.7
A
1672-7991(2017)02-003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