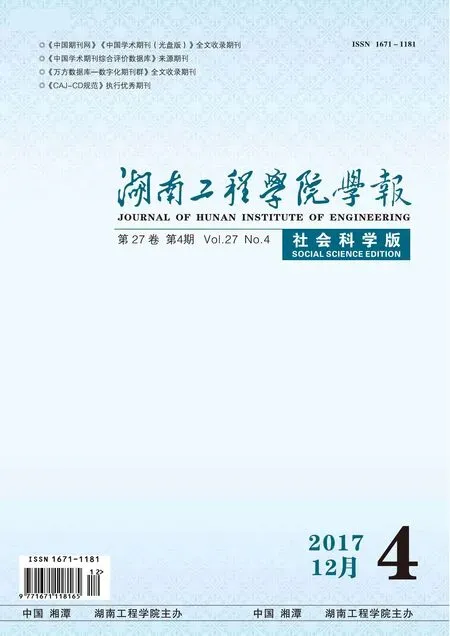1926年湖南水灾与北伐战事
张 妍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1926年湖南水灾与北伐战事
张 妍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1926年夏,北伐战争之湖南战场遭遇特大水灾。占据长沙的湘鄂联军将领叶开鑫不但没有做好救灾工作,反而千方百计地搜刮军费与军粮。此举遭到了本地各官、民团体的反对,他们纷纷呼吁息兵救灾,军心为之动摇。战事方面,湘鄂联军以大水为险,疏于防备,北伐军则利用时机与水势大举反攻。财、军两困的叶开鑫被迫放弃长沙,退守岳州,北伐军胜利完成第一期作战计划。灾荒是对战争双方的特殊考验,能否成功应对挑战,将对战争的结局产生重要影响。
湖南;水灾;北伐;叶开鑫;唐生智
1926年7月1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下达北伐部队动员令,宣布了“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1]的北伐进军计划,北伐序幕正式拉开。在地处要冲的湖南战场,战斗已经先行打响。由湘军投向革命的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此时正率部与吴佩孚任命的湘军总司令叶开鑫对峙于涟水和渌水两岸。战事胶着,占取长沙成为战役的关键。与此同时,从6月底开始,《申报》《晨报》《大公报》等各大报纸陆续刊出关于长江水灾的报道,湘、鄂、赣、宁、皖、浙诸省先后告急。特别是湖南省境内,大雨不止,山洪暴发,湘、沅、资诸水及洞庭湖泛滥,长沙城内尽成泽国,而各县亦多被水封城,损失惨重。自古以来,“天时”就是影响军事进程的重要因素,那么,此次空前的大水灾害,对如火如荼的北伐战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交战中的各方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导致了怎样的结局?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往往将北伐在湖南战场迅速取胜的原因归结为北伐将领的正确指挥、革命军队的英勇战斗、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援、北洋军阀的腐败没落等。①这些研究成果自有其学术价值,但囿于分析视角的局限,没能充分展现湖南战场的个性特色以及长沙战役的具体社会环境。本文试图突破传统的革命史视角,以1926年湖南水灾这一自然事件为切入点,考察湘省军阀、本地湘民、北伐军这三者围绕水灾展开的较量以及对战争进程产生的影响。从灾荒与战争的关系入手,不仅有利于更深入地揭示北伐战争时期湖南的政治生态与社会民情,也为我们进一步思考自然、社会、军事之间的相互影响提供新的启示。
一 军需不足:叶开鑫与灾民争食
军需包括军饷、军粮、武器装备等是军队作战的重要保证。然而,此时驻守在涟水北岸并控制省城长沙的叶军早已面临着巨大的军费短缺与军粮不足的问题。自民初以来,由于连年兵荒马乱,社会动荡不安,湖南经济已经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再加上省内军阀割据争夺,战无宁日,湖南财政濒临绝境。1926年,赵恒惕任内的财政积欠高达2000万至3000万之巨。[2]在此情形下,为了应对频繁的军事战斗,叶开鑫想方设法筹集军费,却始终无法满足战争的巨大需求,“前方转报行军将断炊,正需筹款接济”。[3]不仅本省的湘军等待供应,由吴佩孚指派的援湘鄂军也频频催饷,这使得苦于军需问题的叶开鑫十分忧虑。[4]此时特大水灾的到来,无疑是雪上加霜,将北军推向了弹尽粮绝的境地。
6月26日起,受大雨影响,湘江水迅速上涨。6月30日,湘江水开始入城,沿江县乡受灾。到7月3日,长沙关水表已由16尺涨至41尺,数日之间陡涨25尺。长沙城内半成泽国,水深数尺,舟楫沿街往来;邮电交通俱因大水断绝。附属县乡受水患影响,农田受淹、房屋被毁,老弱残幼溺水身亡。[5]滨湖各属“数称产米之区”,时“皆一片汪洋,所有新旧堤防,溃决殆尽”。全省因水灾“损失近千万,死亡甚重”。[6]根据杨鹏程在《湖南灾荒史》[7]中的统计,1926年湖南受水灾影响的县有42个,是民国前期湖南受灾最严重的年份之一。
水灾造成的巨大损失使湘省经济受到极大的摧残,也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贫困程度。困苦不堪的湘民自保几无可能,更无力负担巨额军需。对于此时正面临紧急军事任务的叶开鑫来讲,原本已经十分不易的军费和军米的筹集更加困难。1926年6月27日,湘潭县议会电呈叶总司令、蒋总指挥,恳请免去摊派的军饷(包括军米四千硕、军费三万六千元)。[8]长沙县县长曹楚材因军粮紧急,以田赋券作为抵押,向省城各米业筹米五千石,米业公所特开紧急会议,请求曹县长收回成命。[9]湘乡县署会议筹派饷粮的结果亦是无法满足军米五千石、洋五千元的要求,请求总司令收回成命。[10]

受灾属县,不仅不能满足军需供应,反而亟待赈恤。自6月底开始,各处报灾请赈的电报与函文纷至沓来。湘潭县饱受水患之苦,县议会及各公法团向总司令和华洋筹赈会发电请赈:“属县一日以来,淫雨不止。被虫伤,近复洪水暴涨,城乡皆成泽国,难民遍野,惨不忍观。各公团发粥施赈,专事奔呼,惟杯水车薪,施惠难遍。伏恳迅颁赈款,以救灾黎。”[11]湘乡县也同样希望总部能够筹集民食:“此次战事发生,大军扼河而守,县东三十余都胥为唐据,城内向来仰给湘潭暨本乡贩,县东既沦于唐,河运又复断绝,则接济之来源日形减少。”[12]
面对此天灾惨祸,叶开鑫不得不抽出部分精力,办理赈灾事宜。7月3日起,总部组织警署分组派船,沿河渡救被淹灾民。7月5日,大水稍退,叶开鑫在省署召开急赈会议,与各机关长官、各团体代表以及中外慈善家等共百余人商讨急赈办法。[13]7月6日,叶开鑫向陈嘉谟、吴佩孚等军政要人及各省湘绅通电,乞求筹款赈济湘灾。[14]然而,仔细分析此次赈灾的情况就会发现,叶开鑫等将领采取的所谓赈灾措施,大多是出于职务要求所做的官样文章。他们并没有认真地把精力投入到赈灾事务上。在此次救灾、赈灾中真正发挥作用的主要是湘省的民间力量。水灾发生后,各种团体组织和个人陆续加入到赈灾行列。7月1日,长沙赈务分会、总商会、慈善总公所、淮商公所、贫民救济会、觉化慈善堂、积善小铺堂七团体组成水灾急赈会,调查灾情,设厂放赈。[15]此后参与煮饭放赈的善堂增加到了十多家。这些机构和团体不仅发放钱米,还从医疗救护、收容安置、卫生防疫等各个方面参与水灾赈济与善后,将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叶开鑫仍然没有停下筹备军需的脚步。他一方面呼吁各方救济灾民,另一方面却又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搜刮军费。为了筹集资金,总部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第一,增加税收。6月29日,总部发布《矿税增加军事特捐之要令》,于各项矿产正税之外,附加百分之一,作为军事特捐。[16]与此同时,整理此前各县长年拖欠的契税,用减免优惠等方式一次付清,以补军需。[17]再者,还通过县农会,向烟酒业增加附加税。[18]第二,抽收湖田验照费。7月6日,总部宣布举行湖田验照,专门检验此前从未查过的湖田执照。[19]第三,发行短期军用公债。总部为筹集发行金库兑换券所需的准备金,用政府各处官产向长沙总商会抵借八十万。[20]为保证军需筹集,总部还特别成立了军资处办理筹款事宜,[21]真可谓是费尽心思。
但是,正如上文所反复强调的,饱受天灾人祸的省城与各县属早已山穷水尽、罗掘俱穷。农田被淹、商市被毁、财物流失,满目疮痍的市镇城乡无论政府采取何种手段都不能搜刮出更多的膏脂。即便稍显殷实的商户公所,救济遍地的灾民尚且不够,决不愿多借给军队一丝一毫。三仓所留少许积谷,是补种晚稻、恢复农田的最后保证,绝不能充作军粮,断送民生。再加上此时前湖南省长赵恒惕在湖北筹集军费进展不顺,迟迟无法返湘,叶开鑫的处境更加艰难。内源已断而外援不至,失去军需保证的护湘军退出长沙是必然之事。
二 军心动摇:湘人呼吁息兵救灾
水灾发生后,叶开鑫不顾灾情执意搜刮军费的行为遭到日益激烈的抵制和反对,而南、北两军之间的战争也因此被看作是置人民于死地的兵祸。此前就流传的“弭兵”之说一时间大为兴盛。湘省各机关、团体纷纷发出通电,请求军队息停兵事,以救垂死灾民。原本寄希望于叶开鑫的绅商群体也纷纷转向,希望南北两军同时撤出,使湘省重新回归到“自治”的状态。
7月5日,湖南赈务协会向吴佩孚、陈嘉谟、赵恒惕、蒋介石、唐生智、叶开鑫等军政要人发出呼吁停战之要电:“请暂将湘中战事设法停止,从赵炎公之调停,南北两军同时退出湘境。一意专办赈务,以慰来苏;一俟民力稍纾,再供军用。若战事永无解决,则赈无可赈,海内外仁人君子无术相助。”[22]继湖南赈务协会之后,省城各公法团体继而起之呼吁,希望湘中战事停止,专意筹赈,藉恤灾黎,救人民于水火:“淫雨为灾,沟壑盈尸,死者无人收殓,生者无术安养。纵有一息存者,亦不能再事剥削。若再横征搜刮,恐将揭竿而起。铤而走险何则,人生不过一死,不死于水,则死于兵。”[23]湖南省议会在捐款一万元赈灾的同时,也向叶、唐两军通电,痛述水灾、请求息兵,并向叶开鑫请求两事:“一、请以积谷救灾,毋征发为军食;二、希望停止军事行动,筹集巨款,办理急赈。”[24]在官方机构的带动下,湖南民间组织如湖南公民联合会、湖南救国励进会、湖南中华工会,湘西实业研究会等团体也纷纷电致各军政长官、各省同乡请求息争救灾。[25]
呼吁息兵的声音不仅在行政机构和民间团体中大为流传,在军队方面也得到了部分共鸣。在吴佩孚支持下取得援湘军指挥权并意欲返湘的前湖南省长赵恒惕,此时也借水灾之事大呼罢兵。他多次劝说唐生智主动下野,使南北客军一律出境,非到万不得已,不愿与粤桂军宣战。赵恒惕因水灾问题与叶开鑫在战、和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对北军的军事形势和军队士气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军事作战方面,赵恒惕命令尚未抵达前线的援湘军暂驻原地,等他回到湘省后,如和平解决无望,再行前进。这使正在涟水和渌水北岸苦苦挣扎、等待救援的叶军处境更为艰难,军事危机骤然加重。而事实证明,北伐军正是利用了援湘主力尚未全部到达的时机,一举攻破叶军防线。在军队士气方面,呼吁和平罢兵的呼声也影响了将领作战的积极性。叶开鑫指挥的北军由多省军队组成,除系属湘军的刘铏、贺耀祖两个师以及邹鹏振、刘雪轩、林拔萃三个旅外,还有余荫森旅的鄂军、唐福山所部赣军以及谢文炳、陈修爵、韩彩凤、沈鸿英等粤桂军残部。对于外省各将领来讲,此次入湘参战纯为湘人卖力,自己并无地盘可得,认真备战已属不易。当他们听到这种“恢复原状,请客军出境”的呼吁,心中不免怏怏。因此,当时传出了“援湘军不愿替湘军垫背,退至岳州后始肯参加作战”[26]的说法。吴佩孚派来的援湘海军兵舰十余艘,也因厌战而陆续开走八、九艘。[27]
军队中军心动摇,不仅各将领态度消极,总司令叶开鑫也心生退意。鉴于此时面临的军事危险、军费无着、灾情惨重、官民愤恨的困难局面,叶开鑫反复催促赵恒惕返湘主持全局。他劝说赵恒惕不要因为筹集军费之事延误回湘日程,也不要因为湘省的领导权问题有所顾虑。如若赵恒惕能够及时回湘,他愿意主动让出总司令职位,恢复赵恒惕省长名义,自己则退为第三军军长,专管军事。经过反复权衡,赵恒惕终于决定于7月10日乘兵舰回湘,恢复省长职务。但由于赵恒惕只到岳州,不来长沙,叶开鑫也不愿在陷入僵局的省会要冲久留。这就为日后叶开鑫战事失利时放弃长沙、移驻岳州埋下伏笔。
三 军事失利:北伐军借水势反攻
众所周知,交通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信息报送、军备运输、队伍行进,都要求交通线路保持畅通。然而,连日的大水对受灾区域的邮电交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铁路方面,湘鄂、株萍两路军事要线,因大水冲毁桥梁或轨道,完全停驶。轮船方面,长常、长益、长潭、长阴间之内港小轮,则因大水溃堤、航行危险,已全部停班;湘、汉之间三公司大轮船,并不逐日开行,致使内外消息隔绝。[28]电报业已中断,一时不能恢复,长沙报纸仅刊本省新闻、无中外新闻已经数日。汨罗洪桥被水冲没十余丈,现江水过桥三尺,一时不易通车。[29]到7月5日,大水减退,轮船已可航行,但火车尚不能通行。[30]
除交通外,大水对双方的战争工事也带来了较大的损伤。7月3日,据《申报》报道,叶军前线阵地湘乡,连日大雨使该地桥梁多被淹没。交通不便,水势仍涨,军士大多浸泡在水泊之中。小船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希望省部派多艘火轮以便应用。再如湘潭,连日大雨使城街水深数尺,战事工作均被淹去,兵士移居高埠。余荫森旅所驻易家湾地面,全浸水中,移居昭山。该部电请总部特派一艘军轮、二十一艘大帆船以供兵士群驻。[31]《兴华》也报导称宁乡、平江、浏阳、湘阴等县受灾至烈,唐、叶两军所掘之战壕,多为水淹。[32]在此种情形下,唐、叶两军被迫休战,“叶军扼守涟水,因大雨兼旬,无战事”。[33]
然而,休战中双方对于战事的准备却大不相同。由于受大雨影响,涟水暴涨,水面宽阔,不利军行。北军自恃掌握船只,并且有兵舰为助,谅北伐军绝难飞渡,警惕大大放松,许多将领相率逍遥于长沙、汉口。蒋锄欧、邹鹏振因赵恒惕电召赴汉,先后来省城就商于叶开鑫,未返前线。而北军前敌总副指挥谢煜焘、郑鸿海,也与代师长唐巘去往湖北,前线疏于防备。[34]再加上士兵因军饷问题心怀不满,受息兵救灾主张影响士气低落,整个军队备战状况很不理想。
相比于备受困扰的北军,北伐军(南军)由于得到了广东国民政府提供的充足的军需补给,[35]受水灾影响不大。面对大水形成的涟水天险,北伐军不但没有消极懈怠,反而一直积极备战。考虑到“(北军内部)尚相疑惧,不能统一指挥”,“团结未固之机攻之,易于瓦解”,唐生智与陈铭枢审时度势,于6月28日电告国民政府,力主不待北伐军集中完毕,已入湘之第四、第七及第八军应提前全线进攻。[36]7月3日,当第四军到达前线后,唐生智制定了作战计划并电报总部:“承敌部署未竟,以在湘所有部队联络,决然进攻,求敌主力而击破之,并进取长沙。”[37]
7月5日,“出了太阳,刮着东风,水也跟着退了”,[38]北伐军下令分四路大举反攻。“李品仙任第一路攻湘潭,第四军之张发奎师助之;何键、刘兴任第二路,渡涟水而前;第七军胡宗泽、钟祖培部任第三路,进攻宁乡、益阳,以包抄长沙;周澜及第四军之陈铭枢部任第四军出湘东茶陵以攻醴陵。”[39]经过连续几日的英勇作战,北伐军先后攻克娄底、谷水、潭市、湘乡、湘潭、醴陵等重要县市,北军一路向后溃退。由于涟水、渌水防线已被摧毁,长沙东南防务尽失,湘中水路交通中断,省城无坚可守,7月9日晚,叶开鑫召集官员开会,决定放弃长沙。7月12日,北伐军进入省城长沙,并未遇到过多的抵抗,叶开鑫在蒋锄欧等将领的保护下退守岳阳,与离汉返湘的赵恒惕汇合。
分析此次战役的全过程,除了两军备战的不同态度外,能否利用水势也对战争的结果产生了影响。在非常关键的易俗河战役中,面对余荫森等部大炮的猛烈进攻,北伐军以木排巨筏,四围钢板作掩护,借助大水向北猛冲,前仆后继;并以五十多支商轮用作战船,输运敢死队,最终得以强渡涟水。[40]除借助水势外,北伐军取胜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援湘军”为水路所阻。广东国民政府出兵援唐之后,吴佩孚也分兵两路大举援湘,在东路以宋大霈为“援湘军”第一路总司令,西路以王都庆为“援湘军”第二路总司令。7月初,宋大霈、王都庆等部“援湘军”,虽均准备出发,但都被水所阻,输送困难。[41]北伐军之所以选在7月5日突然发动反攻,也正是选准了北方援军尚未进入湘境这个时机。此次大水成为北伐军最好的挡箭牌。由此可见,能否处理好并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也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北伐军占领长沙后,湘中局势大半平定,北伐第一期作战计划基本完成。此次克复长沙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正如北伐军司令部的俄国顾问加拉罕向莫斯科事先报告的那样:“如果最近一周内广州军和唐生智联合起来确实占领长沙和湖南全省,那么在这里、在北方将产生一场巨大的结果,这将是对吴佩孚新的沉重打击,可能使吴佩孚全军覆没。”[42]与此同时,克复长沙也极大地鼓舞了国民革命军的斗志,坚定了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信念。
四 结 语
从具体的史实来看,1926年夏这场突如其来的水灾,确实是将湖南战场的战争进程向有利于北伐军的方向推进。然而,水灾毕竟只是战争面临的自然环境与偶发因素,能否成功应对灾害造成的后果才是决定战争结局的主要因素。护湘军原本在军事对阵中占有优势,但由于叶开鑫不但没有做好救灾工作,而且不顾灾情千方百计搜刮军费,最终失去了湘民的信任和维持军事行动的经济来源。战争中受害最深的本地湘民,则借水灾之机,重提“弭兵”与“自治”主张,客观上加剧了湘鄂联军的分裂。相比之下,北伐军则在水灾中展现了极高的能动性,克服大水险阻,出奇制胜。
对于北伐战争之湖南战场的研究,水灾的发生以及由此引发的湘省境内政治生态与社会舆情的变化,是以往未曾重视的方面。这也进一步引发我们对于自然、社会、军事之间相互关系的思考。在军事战争中,自然因素(包括气候条件、地理环境、自然灾害等)一般来讲只是影响战争进程的外部原因,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转变为主导结局的关键。特别是当自然因素影响到社会内部力量对比与舆论环境时,其作用会显得更加重要。另一方面,军事、社会等人为因素也常常改变自然因素的作用方式与力量强弱,并最终反作用于自身。因此,在战争史的研究中,应特别注意自然、社会、军事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
注释:
① 欧阳雪梅的《试论北伐战争中的唐生智》(《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和《梁汝森的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的历史作用——兼与黄德林、吴东华同志商榷》,(《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突出了唐生智、叶挺等将领在北伐战争中重要作用。薛学共的《北伐战争与湖南工人运动》(《湖湘论坛》,1999年第4期)和薛毅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与北伐战争》(《江汉论坛》,2002年第4期)阐明工农运动是北伐军克敌制胜的群众基础,相关的专题性和通史性著作的论述也基本集中在这几点。
[1] 万仁元,方庆秋.蒋介石年谱初稿[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603.
[2] 欧阳志高.湖南财政史[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8:81.
[3] 军资处昨日举行成立仪式[N].大公报(长沙),1926-7-7.
[4] 叶开鑫缺乏饷械[N].民国日报,1926-7-2.
[5] 湘省大水入城之巨劫[N].申报,1926-7-9.
[6] 湘鄂水灾中之军讯[N].申报,1926-7-12.
[7] 杨鹏程.湖南灾荒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407.
[8] 湘潭县议会恳免军饷之呼吁[N].大公报(长沙),1926-6-27.
[9] 米业昨日开会之情形[N].大公报(长沙),1926-6-28.
[10] 县署会议筹派饷粮之结果[N].大公报(长沙),1926-6-30.
[11] 湘潭惨遭水灾之电告[N].大公报(长沙),1926-7-5.
[12] 湘乡县请筹民食致总部电[N].大公报(长沙),1926-7-7.
[13] 总部昨日之急赈会议[N].大公报(长沙),1926-7-6.
[14] 湘省水灾之乞赈声[N].益世报,1926-7-12.
[15] 长沙水灾急赈分会昨日成立大会记[N].大公报(长沙),1926-7-2.
[16] 矿税增加军事特捐之要令[N].大公报(长沙),1926-6-29.
[17] 整理各县契税之通电[N].大公报(长沙),1926-6-29.
[18] 烟酒业反对县农会附加税之会议[N].大公报(长沙),1926-6-29.
[19] 政府行将举行湖田验照[N].大公报(长沙),1926-7-6.
[20] 总部以官产向商会抵借八十万作为发行金库券准备金[N].大公报(长沙),1926-7-7.
[21] 军资处昨日举行成立仪式[N].大公报(长沙),1926-7-7.
[22] 赈务协会呼吁停战之要电[N].大公报(长沙),1926-7-5.
[23] 省垣公法团呼吁停战之要电[N].大公报(长沙),1926-7-6.
[24] 省议会昨日之重要协议会[N].大公报(长沙),1926-7-6.
[25] 四团体电请息争救灾[N].大公报(长沙),1926-7-7.
[26] 湘战停顿之内幕[N].申报,1926-7-12.
[27] 张静如.北伐战争:1926-1927[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50.
[28] 湘省大水入城之巨劫[N].申报,1926-7-9.
[29] 湘鄂皖水灾[N].申报,1926-7-12.
[30] 湘鄂水灾中之军讯[N].申报,1926-7-12.
[31] 湘省大水入城之巨劫[N].申报,1926-7-9.
[32] 湖南长沙大水为灾[J].兴华,1926(27):44.
[33] 湘鄂水灾中之军讯[N].申报,1926-7-12.
[34] 叶开鑫离长退岳之真相[N].盛京时报,1926-7-20.
[35] 蒋中正命令.军事政治月刊[J].军事政治月刊社,1926(5):1-3.
[36] 罗家伦.革命文献(12)[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8:1852-1853.
[37] 章伯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北伐阵中日记(1926.7-1928.5)[M].近代稗海(第十四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0.
[38] 唐生智.大革命北伐的片段记忆[A].广东省文史资料委员会.国民革命军北伐亲历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10-11.
[39] 王云五,李圣五.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史[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23.
[40] 叶开鑫离长退岳之真相[N].盛京时报,1926-7-20.
[41] 湘南战事因水暂停[N].益世报,1926-7-11.
[42]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442.
TheFloodinHunanProvinceandtheNorthernExpeditionin1926
ZHANG Yan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In the summer of 1926, there was a serious flood in Hunan whe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just broke out. Faced with this situation, YE Kaixin, the military commander of Changsha, didn’t do a good job in the disaster relief work. On the contrary, he tried his best to plunder money and grain to supply the battle. His behavior was strongly opposed by the natives.They called for peace and thus soldiers were influenced. In the preparation of battle, the Northern Army treated the flood as natural obstruction while the Southern Army overcame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attacked ahead of time. The result was that YE Kaixin lost Changsha and the Southern Army won the war. This battle indicated that disaster is a test for the participants in war and the one who overcomes challenges will be the winner.
Hunan; flood;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YE Kaixin; TANG Shengzhi
2017-02-17
张 妍(1989-),女,山西太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K262.34
A
1671-1181(2017)04-005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