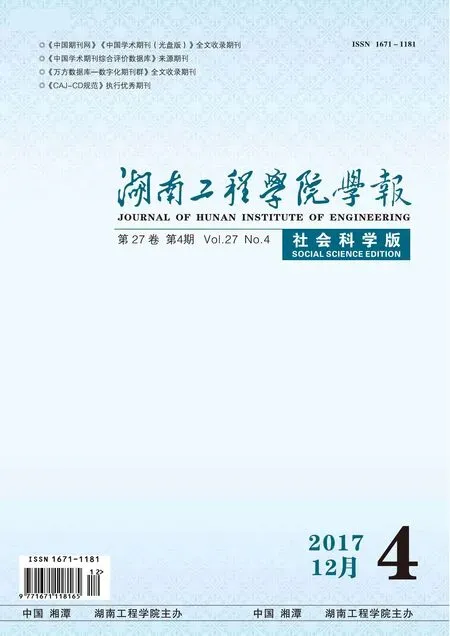戴着镣铐跳舞
——论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桎梏
叶吉娜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戴着镣铐跳舞
——论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桎梏
叶吉娜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最大差异在于它的隐含对象为儿童,儿童的一切都处于生发期,因为这个主要特点,所以儿童文学被倡导担负起人生教育、普及知识等任务。但也因这一层桎梏,文学创作的触角被束缚于叙述禁忌之中;作家创作的灵性被消磨于“语重心长”的教导中;美学内涵、哲学思考在道德教育、知识普及面前被挤向边缘,作品亦很难充满灵气了。这种创作倾向对于儿童来说也许反而阻碍甚至扼杀了他们的哲学思考、心灵发展。
中国儿童文学;叙述禁忌;教育主义;哲学内涵
在儿童本位论的影响下,儿童文学作品的隐含对象——儿童,被不少创作家、理论家设定为永远幼小、天真、脆弱的个体。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小心翼翼地剔除真实社会里存在的悲剧因素,总是指向美好和纯真。试图圈定叙述禁忌,将一切社会真实悲剧排除在儿童文学门外,期望保护儿童不受冲击。然而这种保护就像温室,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儿童,当真正遇到人生的悲伤时,受到的打击将会更大。另一方面,由于儿童处在人生的起点,人生观、价值观、知识水平都有待形成,儿童文学因此被许多理论家呼吁担负起儿童人生教育、道德教育、知识普及的任务。在这种理论影响下,许多儿童文学作品被教育主义、科学主义主导,成为教育、科普的工具,以至于模糊了文学的本质,作品也因之流于说教,失去了美学涵养、哲学深度。本文即从叙述禁忌、教育主义、知识普及三方面入手,对比西方儿童文学,分析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困境。
一 不该如此的对象禁忌——中国儿童文学对悲剧的排斥
钱钟书先生曾说过:“我认为寓言要不得,因为它把淳朴的孩子教得愈简单,愈幼稚了,以为人世里是非分别、善恶的回报,也像在禽兽中间一样的公平清楚,长大了处处碰壁上当。”[1]48-49窃以为钱钟书先生的这番话对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作品的叙述禁忌问题正是切中要害的评论。在不少作家、理论家心中认为,儿童文学的主流读者——儿童是天真、纯洁的,是脆弱、稚嫩的。这样的看法无可厚非,儿童处于人生初级阶段,接触社会现实较少,各方面的经验感受确实不足。但是把儿童看作是永远天真、纯粹的,而非一个发展的个体,这样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作家在创作作品时始终本着保护儿童,使其远离成人现实世界各种悲伤、痛苦的出发点,将一些反映社会现实悲伤的题材排除在儿童文学大门之外,形成了儿童文学中的叙述禁忌。这种理论观点与创作方法对儿童来说也许会带来更大的阻碍与伤害。
儿童文学中有意剔除反映社会悲剧、社会真实面貌现象的后果之一就是将我们的儿童永远包围在作家小心翼翼建立起来的温室中。然而这种营造的“永远”的安全快乐却又只是“自欺欺人”的永远,儿童总要成长,当他们进入现实社会后,面对社会的种种悲伤、风雨、困境,他们如何能带着一颗作家小心翼翼呵护的,从未感受过风雨而脆弱的心去接受、处理这一切?我们的儿童文学面对的是未来将要独自站在天空下的儿童,这片天空洒下的不仅只有阳光,还有雷电和风雨。所以我们应该“给孩子们以温暖,还要教给他们不怕寒冷”[2]87。怎样教给孩子们不怕寒冷,首先应当是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寒冷。儿童未经历世间的种种,不知现实的伤痛与悲欢离合,儿童文学应当以一种相对现实而言较温和的方式向孩子们展现真实的世界,如汤锐所说,让他们在进入社会前从文学阅读中感受心灵的震撼,为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流下同情的眼泪,从阅读中产生有关生与死,爱与恨的思考。这样,当真正经历现实时,才能坚强地面对。

国外优秀作家们深知悲剧情怀的意义,安房直子的《小狐狸的窗户》、奥斯卡·王尔德的《快乐王子》、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等都把握住了发人思索的悲剧的价值,带给读者们深沉的思考。中国儿童文学界出现过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故事从一个稻草人的角度展现了生活的现实样貌,失去亲人孤苦无依的老人又遭受稻田虫灾的打击;可怜的妇人为摆脱被丈夫卖掉的命运绝望地跳入河中等等,最后稻草人自己也倒在田地里。作品的悲剧情怀从稻草人“口中”慢慢“道”出,读者受到心灵的震惊继而思考为何生活会有灰色的存在,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真实的世界。
但也并非说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可以泥沙俱下,儿童之为儿童,由于其处在一个特殊的、敏感的生命阶段,他们的心智还未完全成熟,心理接受能力有限,怎样的材料可以进入儿童文学作品中,应当以怎样的方式进入,这些在作家创作过程中都需要严谨考虑。即或是写有深刻悲剧价值的材料时,作家也应当注意叙述方法,以一种相对温和的形式展现,避免悲剧夹带着血腥、恐怖剧烈地冲向儿童。
二 戴着镣铐跳舞——中国儿童文学需防范因教育主义而遗失哲学内涵
儿童文学一直被强调需要承载教育作用。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十分看重孩子们“读了以后的实际影响怎么样”[3]446。 强调和重视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正如朱自强所说:“张天翼的所有儿童文学创作就是从‘针对孩子们这种问题’,教育孩子改正缺点出发的。”[4]169在《宝葫芦的秘密》中,张天翼想要批判一部分人总想坐享其成的恶劣品行,于是安排王葆烧葫芦、砸葫芦。但这样的创作安排却抑制了孩子想象力的发散,作品的思想深刻度、哲学内涵在教育主义的压制下显得很单薄。
儿童文学若能在带给儿童美的享受的同时起到教育的作用,亦是其不经意间的功劳,但当儿童文学承载教育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就像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儿童文学便无法发展得那么轻松了。文学创作的触角被束缚于叙述禁忌之中,作家创作的灵性被消磨于“语重心长”的教导中;美学内涵、哲学思考在道德教育、知识普及面前被简化成直接苍白的说教,作品亦很难充满灵气了。这对于儿童来说也许反而阻碍甚至扼杀了他们的哲学思考、心灵发展。
当时,在儿童文学理论界就儿童文学教育观即产生过不小的争论。许多理论家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方卫平教授没有否定儿童文学的基本教育作用,但也明确表明把教育作用当成儿童文学观念的出发点,客观上造成了儿童文学自身品格的丧失。刘绪源先生批评了教育工具论,认为教育效果只能在审美之后产生。此后,汤锐在《现代儿童本体论》中指出:“作家主观创作上若以审美为主,作品客观上自然能起到教育的作用。”[5]139并不是说儿童文学不该教导儿童,但作为美的文学,思维深度、美学价值、哲学思考当是更深层的内涵。当一部作品在这些方面浑然天成后,文学的教育作用也就水到渠成,自然能起到引导孩子进行哲学思考、体会美学内涵的作用了。周晓先生定义儿童文学的本质是文学,认为教育作用只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功能,要把儿童文学从狭隘机械的政治思想和道德伦理的灌输中解放出来。这样的评论在今天看来也是有警示作用的。也许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政治思想的灌输相比上个世纪已不再那么严重,但大多数作品将教育奉为儿童文学的本质却仍是阻碍儿童文学大步发展的重要问题,在全力注重儿童文学教育作用情况下,作品的美学内涵、哲学思考被挤向边缘。
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哲学意蕴应当说是作品背后深层的内涵,体现了作家的思想高度和美学涵养,对儿童有非凡的引导作用,这种引导并非直白的说教所能达到的效果,而是像无形的线牵引着儿童展开奇幻、深层的哲学思考。乌沙丘夫的《大海的尽头在哪里》在这方面堪称极品。作品围绕蚂蚁和大象这样一组对比鲜明的组合开展了一波三折的情节设置。于童趣中包含了深刻的哲学主题。当文末大象在听金枪鱼回答说“海的尽头就在这里”后又可爱地反问“那么海的开头在哪里”,如此追问体现了个体对终极的追寻,同时彼岸、此岸的转换,尽头、开头的对转又体现了相对命题的转换。短小的一篇文学作品包含了如此丰富的哲学内涵,并且这层哲学思考就像周作人先生所说的果汁冰酪里的果汁一样,完美地融在了作品中,而非枯燥的哲学说教。此外,笔者以为,《大海的尽头在哪里》有些接近于周作人先生在《儿童的书》中提到的那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了。
梭罗《亨利徒步历险记》同样是一部于乐趣、美感中水到渠成地反映人生哲学的上乘之作。亨利与朋友都想去菲茨堡旅游,有了念头后,亨利拿起拄杖、背起行囊马上出发了,在途中他看到了迷人的月夜、美丽的鲜花,享受掏鸟窝、摘草莓的乐趣。而朋友选择攒够了钱坐火车去。为此他努力除草、工作,终于攒够了钱坐上火车,比亨利早些到达了目的地。但在图画书中,亨利享受的鲜花、月夜和朋友工作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作者就在这样的对比中抛出了为目的而目的还是为过程而目的人生哲学问题。另一部优秀作品《猜猜我有多爱你》,并没有不断高亢地喊出“我爱你”,而以一种充满哲学色彩的处理方式表达出深沉的爱。台湾作品《谁大》《猴子变人》亦达到了童年的天真与哲学的逻辑之间完美结合。没有苦口婆心地向孩子宣讲哲学知识,而是引导儿童跟随两个可爱孩子的思维探讨世界哲学问题与生命进化发展问题,达到了思想性、哲学思考、美学涵养的统一。大陆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也有集哲学意味与童年趣味并佳的作品,叶圣陶先生的《小马过河》与发表在1986年第4期《小朋友》上的小诗《春天的山》是其中代表,达到了童真和哲学的和谐统一。但这样的作品相对而言仍是凤毛麟角,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在这方面需要探索的道路还很长。
三 文学非科学——儿童文学应当是文学作品而非说明书
在科技创新、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人们对科技文化的推崇越来越高,反映在儿童文学中,作品的科普作用也为许多作家重视。法布尔的《昆虫记》、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吉卜林的《森林报》等,在孩子们享受文学同时润物无声地普及了科学知识。这些作品留给孩子的不是强迫阅读的苦恼而是发现世界的乐趣。《是谁嗯嗯在我头上》中鼹鼠愤怒地寻找嗯嗯在他头上的家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小动物,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纷纷以自己的嗯嗯作为证据努力澄清,阅读这部作品时,读者们不禁为其中一些画面发出爽朗的笑声,间或流露出对小动物的嗯嗯“嫌弃”的表情,也正是在这样欢乐甚至有些无厘头的氛围中,这部作品起到了很好的科普作用,用方卫平教授幽默的话来说,孩子们通过这部作品,对动物们嗯嗯的形状、颜色、质感等都有了了解。
在欢声笑语中增长孩子的知识,一部优秀的作品就这样成功达到科普的功能。将理趣与情趣完美融合,这是科普类作品成功的最重要条件,然而不少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却出现只重理论而忽视情趣的倾向,普及科学知识的要求可能恰巧成为儿童文学发展的桎梏。如林力的《机器的心脏——发动机》,极其详尽地向读者们介绍了什么是发动机,什么是风力发动机、水轮机、蒸汽机等,还科普了它们的工作原理。但这部作品在叙述时,完全使用科学的语言来说明,使用了大量生僻、专业的词语,让孩子们难以理解,如“机轴的回转”“活塞蒸汽要先推动活塞做来回地运动”“进气冲程”“做功冲程”等,“俨然博物馆讲解员,忽视、摒弃了儿童文学特色的叙述方法如:形象塑造、情节规划等,而采用大量堆砌理论、机械说教的方法,这样会导致儿童不堪知识的重负,好奇心被厌恶感取代,影响求知欲和想象力”[6]116。卞德培的《日食与月食》一书,同样是过多知识机械堆积,导致作品毫无灵气可言。
周作人先生在《儿童文学小论》中提到过:“向来中国教育重在所谓经济,后来又中了实用主义的毒,对儿童讲一句话,脥一脥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到了现在这种势力依然存在,有许多人还把儿童故事当做法句譬喻看待。我们看那《伊索寓言》后面的格言,已经觉得多事,更何必去模仿他。”[7]64他提出:“其实艺术里未尝不可寓意,不过须做的如同果汁冰酪一样,要把果子味混透在酪里,决不可只把一块果子皮放在上面就算了事。”[7]64这也应当是儿童文学作家们应该警惕的。另一方面,“儿童文学的深度不是故作艰深,不是玩弄玄奥,而是在单纯中寄寓无限,于稚拙里透露出深刻;在质朴平易中就悄悄地带出了真理,传递了那份深重、永恒的情感”[8]159。这些充满前瞻性、智慧性的论述向儿童文学家们提出了要求,怎样做到作品的美学涵养、哲学思考与童真、灵性地完美结合,同时又能润物无声地起到教化作用,这是需要作家们长久探索的。
[1]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 王丹军.论悲剧与儿童文学[A].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 张天翼.什么是幽默[A].吴福辉,黄侯兴,沈承宽.张天翼研究资料[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4] 朱自强.儿童文学的本质[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
[5] 汤 锐.现代儿童本体论[M].南京:江苏少儿出版社,1995.
[6] 侯 颖.论儿童文学的教育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7] 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8] 方卫平.略谈儿童文学的深度及其实现方式[A].儿童文学的当代思考[M].济南:山东新华书店,1995.
DancingWithShackles:TheShacklesofChineseChildrenLiterature
YE Jina
(School of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children literature and adult literature lies in its implicit object for children.Children are all in the germinal period of the main features. Therefore, children literature has been advocated to take on the task of life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so on.However, due to the shackles of this layer, the tentacles of literary creation are bound in the narrative taboo.The writer’s inspiration is broken in the course of teaching.This tendency may hinder or even stifle children’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narrative taboo; educational doctrin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2017-03-06
叶吉娜(1993-),女,浙江杭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I28
A
1671-1181(2017)04-0051-04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