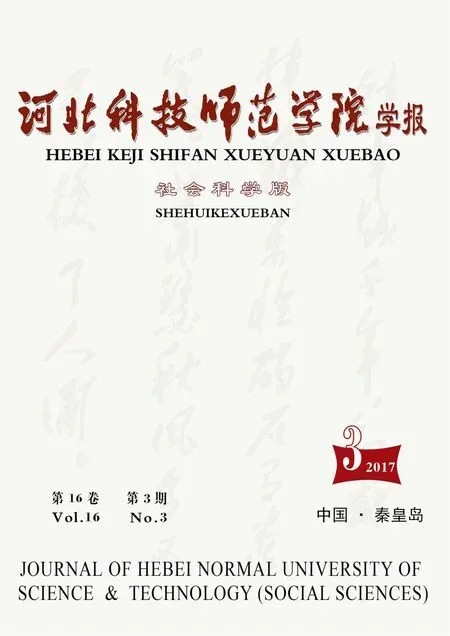《圣殿》:女性形象视阈下“阿特柔斯房屋的倒塌”的艺术再现*
王 钢
(吉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圣殿》:女性形象视阈下“阿特柔斯房屋的倒塌”的艺术再现*
王 钢
(吉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圣殿》在福克纳小说体系中具有承先启后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它和其它描写女性罪恶的小说一样是福克纳女性形象视阈下“阿特柔斯房屋的倒塌”主题艺术再现的文学范本。福克纳在女性形象塑造上与圣经神学思想具有明显的承袭关系。他以圣经观念为基准和出发点,探讨现世之恶的宗教起源,并结合自己对南方的复杂情感,从解构南方传统淑女形象角度来揭示南方“阿特柔斯房屋的倒塌”主题。
福克纳;《圣殿》;女性形象;罪恶;“阿特柔斯房屋的倒塌”
海明威在《死于午后》一书中曾这样揶揄和讽刺福克纳小说的主题和风格:“人家打听得消息告诉我说,由于有了威廉·福克纳先生的优秀作品,出版商现在也不要你把作品的大部分都删去,他们倒是什么都肯出版了。我期待着有一天写写我年轻时候在这块土地上最好的妓院里花的那些日子,在那里结识的最聪明的朋友。这个背景材料我一直留着到我晚年再来写的,到了那个时候,由于年代相距远了,就可以把当时情况看得非常清楚。”[1]海明威所说的以“这块土地上最好的妓院”为背景材料的作品指的是福克纳出版于1931年的长篇小说《圣殿》。小说以哥特手法,结合侦探故事的叙事技巧叙述了主人公女大学生潭波儿·德雷克自甘堕落,被残忍强奸的故事。南方学者柯林斯·布鲁克斯在《威廉·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乡村》一书中以“邪恶的发现”为标题来探讨《圣殿》的主题,认为小说对邪恶和暴力的描写体现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强大力量”[2]。评论家俄康纳也有类似看法,他认为《圣殿》里集中描写了“性欲的罪恶”,而这种罪恶既“同世界的衰老和腐败”有关,也同“葡萄、忍冬花四季的变迁”有关,集中反映“在这个社会中,性只是一种欲望,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只是一种不道德的结合而已”[3]166。当代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也撰文认为,如果从《圣殿》“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主义、有可能令人眩晕、使人感到阴暗、悲观的残暴和愚昧来看,它几乎是让人无法忍受的”[4]。
视《圣殿》为福克纳将邪恶主题推向顶点的一部小说获得了绝大多数评论家的认可,而福克纳的这一创作倾向也可以从《圣殿:原始文本》中得到部分印证。那么,福克纳为什么要写作一部如此可怕、充满罪恶的小说呢?福克纳自己的回答是为了“赚钱”和“使用骇人听闻的手法制造出轰动效应”:“我开始从可能获利的角度考虑写书的问题。我决定还不如自己想法子搞到点钱呢。我抽出了一小段时间,设想在密西西比州一个人会相信什么是合乎当前潮流的,选择了我认为是正确的答案,构思了我能想象到的最最恐怖的故事,用了大约三周的时间将它写出来,然后寄给刚刚接受《喧哗与骚动》的史密斯,他立刻给我写信说:‘好上帝呀,我可不能出版这玩意儿。咱们俩都会进监狱的。’”[5]177尽管此种创作意图出自作家本人之口,但学术界早有公论认为即使是作家本人的表述也未必完全真实可信。事实上,无论是就“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整体建构,还是就“阿特柔斯房屋的倒塌”主题的艺术化传达,《圣殿》在福克纳的小说体系中都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化意义和价值。
一、关于女主人公谭波儿形象的论争及其隐喻意义
诗人托·斯·艾略特曾提出著名的“客观对应物”观念,即“用艺术形式表现情感的唯一方法是寻找一个‘客观对应物’,换句话说,是用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连串事件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感,要做到最终形式必然是感觉经验的外部事实一旦出现,便能立刻唤起那种情感”[6]。以“客观对应物”观念审视《圣殿》的小说文本,结合小说标题的暗示,毫无疑问居于邪恶中心、最能体现作家情感倾向的人物是女主人公潭波儿·德雷克。
英国当代小说家、评论家戴维·洛奇曾指出:“小说里的名字决不是无的放矢的。就算它们是再平常不过的名字,它们肯定也有特殊的意义。”[7]评论家俄康纳也曾提醒说:“在福克纳的小说里,角色的名字占该角色性格很重要的地位。”[3]173从词语构成角度来看,标题《圣殿》与女主人公的名字潭波儿·德雷克(Temple Drake)确实存在内在逻辑联系。“德雷克”(Drake)这个姓在英语中的意思是“公鸭”,西方文化中令人生厌的动物形象;“潭波儿”(Temple)的英文意思是“庙宇”或“圣殿”,在《圣经》中指代“肉体”,典出《新约·哥林多前书》:“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样,在小说中“潭波儿”就具有了双重意义:从小说文本出发,作家主要是表现女主人公潭波儿没有灵魂,没有思想和主见,在生活中一切全凭本能的欲望和肉体的冲动,自甘堕落,受欲望控制和奴役的本性。而就形而上学意义来看,喻指以潭波儿为代表的女性失去了精神的家园和人生的终极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因背离上帝而导致生活迷失、人性堕落。在《圣殿》研究批评史上关于潭波儿的人物形象究竟如何定位有着巨大的争议。多数评论家都认为潭波儿遭受强奸是咎由自取,是人性堕落的集中表现。评论家奥唐奈在《福克纳的神话》一文中曾明确指出潭波儿是“堕落而尚未被玷污的南方女性”,是“现代精神暗中的同盟者”,通过这一人物形象说明“南方女性已经堕落得不可救药”,因为,“她存心眼看着穷白人被宣布有罪并被私刑处死;接着她被财富带去欧洲作毫无意义的躲避,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8]欧文·豪则认为潭波儿的名字中虽有“圣殿”的含义,但她却丝毫没有任何“神圣的观念”,甚至在被带到妓院后,是在“急切地接受堕落”[9]。还有批评家认为潭波儿“对自己的被强奸着了迷”,正是她自己一步步将“淫邪”引入金鱼眼的世界之中[10]。1989年评论家弗莱德里克·R.卡尔出版了两卷本《威廉·福克纳:美国作家》一书,其中谈到《圣殿》时仍认为女主人公潭波儿“没有内在思想,像一个空器皿,一个反面的礼拜场地,缺乏并失去了忠诚和道德”,是“丧失了精神的肉体”[11]367。而对潭波儿形象定位的转变、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看法则是随着女权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一种反对的声音认为将潭波儿定位为堕落女性形象完全是男权中心话语选择的结果。持此种观点的批评家认为小说中真正恶的体现和代表毫无疑问是金鱼眼,不仅一切犯罪活动都是他所为,而且正是在他邪恶的势力下,潭波儿才产生恐惧心理,以致鹦鹉学舌般地行动。在此意义上,潭波儿不仅不是恶的化身,反而是恶的受害者,是男人眼中性的工具,将一切归因于孩子般幼稚的潭波儿是不公平的。另一种反对的声音从作家角度入手,认为谭波儿形象性格的塑造是福克纳“厌女症”的集中表现和反映。持这种观点的批评家尖锐指出,不仅在小说文本中,而且在实际生活中,福克纳都是一个有着鲜明“厌女”倾向的作家。福克纳曾多次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达对女性的看法。其中在《喧哗与骚动》中他借昆丁父亲之口发表的一段高谈阔论最为明显:“女人就是这样,她们并不掌握我们渴想熟谙的关于人的知识,她们生来具有一种猜疑的实际肥力,它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一次收成,而且往往还是猜对了的。她们对罪恶自有一种亲和力,罪恶短缺什么,她们就提供什么,她们本能地把罪恶往自己身上拉,就像你睡熟时把被子往自己身上拉一样。她们给头脑施肥,让头脑里犯罪的意识浓浓的,一直到罪恶达到了目的,不管罪恶本身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12]62除了借小说人物之口外,福克纳在小说中塑造的大多数女性形象,如《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我弥留之际》中的艾迪等都属于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影子人物”,这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印证了他明显的“厌女”态度。此外,在接受采访时,福克纳也在多个场合流露出了类似倾向。如他在劝告年轻作家不要一味追求成功时,就曾拿女人做过讽刺性的比喻:“成功是阴性的,像个女人,你蔑视她,她就会来追求你,奉承你,但你如果去追求她,她就会看不起你。”[13]219类似的说法后来又出现在1956年接受《巴黎评论》记者斯坦因采访时:“成功是阴性的,像女人一样,你要是在她面前卑躬屈膝,她就会蔑视你,因此对待她的方式就是让她看看你的手背。这时也许她会巴结你。”[13]240尽管对这些指责福克纳本人曾做过相应的辩解,也明确表示:“要是我的作品给任何人一种印象:我认为女人在道德上要比男人低一等,那我会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我并不是这么认为的。”[13]126-127但考虑到福克纳在现实生活中与妻子、情人之间的婚姻和情感纠葛,批评家们还是认为福克纳是在掩饰和狡辩。如果“厌女症”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福克纳把潭波儿描写成一个亲近罪恶、令人厌恶的女性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各家关于潭波儿形象的看法和观点从某种角度来说都有合理性,同时也都存在遮蔽和辨识不清之处。之所以在此问题上会出现纠缠不清、莫衷一是的情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许多思考的立足点始终没有脱离小说暗示或作家本人所表达出来的性别立场。如果能开拓视野,转换思路,结合美国南方地域文化特征加以详细分析,完全可以在新的视野中重新厘清脉络,进而解决其中诸多的悬而未决的矛盾之处。笔者即结合福克纳小说“阿特柔斯房屋的倒塌”的总主题,对相关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和再诠释。
二、对谭波儿形象及其隐喻意义的再思考与再阐释
回归文本是阐述观点、解决问题的基础性前提,所以有必要仔细检视福克纳在小说中对潭波儿这一人物形象的细节描写和刻画。在潭波儿的性格特征中,非理性和放任自由意志是主导方面之一。当她被带到老法国人宅院时,她不断恳求他人帮助、并告诫自己要离开,结果她却没有主动离开。她在“金鱼眼”这帮私酒贩子中间穿来穿去,刻意展示自己,以吸引他们的注意。鲁碧告诫她呆在一个地方不要乱动,她却置若罔闻,竟然在就寝时当着男人的面脱掉外衣、并拿出胭脂盒涂抹起来。小说中这些细节描述无疑都是典型的故意挑逗行为,这正是她后来遭受性侵犯无可推卸的自我主观方面的因素。接下来小说写到当“金鱼眼”来到床前抚摸她时,她的心情竟然是既恐惧又渴望,把自己想象成“头发花白、带着眼镜的老师”和“长着长长白胡子的老头”。当她被强奸、继而被带到巴莉小姐的妓院后,她更是学会了酗酒,并对性爱越来越感兴趣。她开始随波逐流,自暴自弃,心甘情愿地接受“金鱼眼”的控制,称其为“爹爹”,直接与自己的父亲等同。在小说结尾的法庭场景中,她不仅带着骄傲讲述自己的遭遇,而且还当庭作伪证,把“金鱼眼”的罪恶行径完全推到戈德温身上,从而导致无辜者戈德温被暴徒活活烧死,她本人却对此没有一丝的愧疚感。从上述小说细节中可以看到,既使有客观原因存在,也不得不承认发生在潭波儿身上的这起骇人听闻的恶的暴行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她的主动承受和放任自流,其自身原因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并与最终结果难以完全脱离干系。换言之,将潭波儿完全看作是一个单纯的受害者既不客观也不符合文本实际。事实上,在《圣殿》中福克纳还塑造了一个类似潭波儿的女性形象——娜西莎。她不仅在《圣殿》中出现,同时还在短篇小说《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女王》中出现。在后者中,福克纳集中描述了她因偷情事件被一陌生男子知晓,为了守住秘密,不得不以肉体交换的方式换回证据、保全自己的故事。通过这篇短篇小说故事情节的描述,福克纳已经暗示娜西莎本质上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堕落的女人。在《圣殿》中她亦如此。为了避免哥哥高文·斯蒂文斯卷入案件中,也为了尽早有个结果了却事端,她不顾哥哥的胜败,也不在乎谁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不分善恶以及是非曲直,放任自己的行为,主动向对手通风报信,助纣为虐,帮助别有目的的检察官把无辜的戈德温定为凶手。其性格主导和本质与潭波儿相差无几。那么,在同一部小说中,为什么福克纳要如此热衷塑造出两个堕落的女性形象呢?福克纳又为何不沿袭“南方家庭罗曼司”固有的女性形象传统而非要反其道而行之?如果将《圣殿》置于与福克纳其它主要小说的互文考察中,会进一步发现不仅是在《圣殿》中,而且在其他小说中福克纳对女性的刻画也大多遵循了类似思路,即集中展示堕落、罪恶的女性形象,《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是最明显的一例。尽管福克纳表示凯蒂“太美丽了、太动人了”[14]1,是他的“心爱的宝贝”[14]6,但他还是为她安排了悲剧性的命运结局以及堕落的人生趋势。福克纳在谈到《喧哗与骚动》的构思和创作时曾说:“小说从小女孩被泥弄脏了裤衩这一画面开始,她爬到树上往客厅窗子里看,她的几个兄弟没有勇气爬上树去,都等着问她看到了什么。”[14]1而正是“满是泥的裤衩”这一象征成为了凯蒂堕落的中心意象和标志,也正如福克纳后来在补写康普生家族附录时所说的那样:“她命中注定要做一个堕落的女人,她自己也知道。她接受这样的命运,既不主动迎合,也不回避。”[12]208这里似乎就存在一个创作矛盾,既然福克纳表明了对凯蒂这一人物的喜爱,又何以忍心安排她成为纳粹军官情妇的悲惨结局?难道仅仅是“厌女”倾向在作祟?
综合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和《圣殿》两个文本中处理女性形象的一贯趋势可以见出问题绝没有那么简单。《圣殿》中一段关于“伊甸园神话”的摹仿叙事也许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一种可靠的路径。福克纳这样描述:“她说那蛇早就看见夏娃了,但要等到几天后亚当让夏娃挂上一片无花果树叶时才注意到她。你怎么知道的?她们说,她就说因为蛇早就在伊甸园里,比亚当还早,因为它是第一个被赶出天国的;它一直就在那儿啊。”[15]福克纳在这里暗示出一种重要的基督教女性观念,即基督教中女性形象的原初定位就与罪恶紧密相连。在《圣经·创世记》的伊甸园故事中,女性夏娃被看作是诱惑男性亚当犯罪的工具,女性夏娃从一开始便是有罪的,便是受上帝诅咒的,后世女人即使没有完全遗传夏娃之罪,至少也是倾向于重复夏娃行为的。而蛇则代表“欲望的心理投影”,是人性腐化的动物本能的反映,是“通向撒旦主题路上的起始点”[16]。蛇与女性二者的结合正是构成罪恶的生命基始。福克纳在女性形象塑造上与圣经神学思想明显具有承袭关系,他以圣经观念为基准和出发点,探讨现世之恶的宗教起源,并结合自己对南方的复杂情感,从解构南方传统淑女形象角度来揭示南方“阿特柔斯房屋的倒塌”总主题。换言之意味着,堕落的女性形象是揭示“阿特柔斯房屋的倒塌”主题的一个侧面,一种载体和表现方式。正像评论家拉瑞·莱文格所说,不管福克纳小说最终能衍生出多少个主题,但其中最基本的一个主题和观念是福克纳始终认为“小说是社会的镜子”,要照出笼罩在黑暗力量之下的那个社会[17]。在此意义上,回顾马尔科姆·考利对《圣殿》主题的评价便显得公允得多:“它是颠倒过来的弗洛伊德公式的一个实例,它充斥着性的梦魇,其实它们都是社会的象征。在作者的头脑里,反正此书与他认为南方被强奸被败坏的看法有关联的。”[18]以女性主义研究而擅长的戴尔尼·罗伯兹也表达过类似观点,她认为福克纳在《圣殿》中再现了南方淑女文化观念在资本主义新南方社会中是如何瓦解崩溃的[19]。这意味着女性的身体及其罪恶行为和堕落本质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与南方整个社会内在肌理联系在一起的。福克纳本人也明确表述过这种观点:“我书中那些不讨人喜欢的女人并不是我故意把她们写成让人不舒服的人物,更别说不讨人喜欢的女人。她们是被我用来当工具,做手段的,目的是为了讲故事,讲一个我想讲的故事,我希望借此表现不公正确实存在,你不能光是接受这个不公正,你必须想点办法,采取一点措施。”[13]125
三、“阿特柔斯房屋的倒塌”主题下《圣殿》的重新定位
整体来看,福克纳在《圣殿》中塑造谭波儿等“恶”的化身的女性形象是有着特殊的创作动机的,它明显关乎福克纳在小说中一贯展现的“阿特柔斯房屋的倒塌”的总主题。所谓“阿特柔斯房屋的倒塌”,喻指因为罪恶和不可抗拒之痛苦的承担而导致的一种人在本质方面的失落,其故事本源见于古希腊神话传说。阿特柔斯是珀罗普斯和希波达弥亚的儿子,坦塔罗斯的孙子,阿伽门农和墨涅拉奥斯之父,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伊利斯国国王。阿特柔斯家族的父辈们,或为了满足自我扭曲的情感,或为了满足物质上的收益而不断残害亲子,遭至诅咒,从此整个家族开始了持续长达五代的血亲仇杀、并终致衰败。福克纳在小说中不仅逼真再现了这一故事关于罪恶及其所折射出的人本质堕落的主题,而且还高度聚焦了故事中“倒塌”和“衰败”趋势蕴含的隐喻性文化指向。对此,弗莱德里克·R.卡尔进行过详细分析:“福克纳思想的神话内核是阿特柔斯房屋的悲剧性倒塌,父子相残,兄弟反目,诅咒已经进入家庭生活的每一个缝隙,毁掉了所有的关系。”[11]161卡尔在此界定了福克纳小说“阿特柔斯房屋的倒塌”主题的两个关键点:其一是“阿特柔斯房屋的倒塌”就本质而言是一种社会道德的沦丧,人性的式微,是人在善和美好遭受破坏之后的一种重要心理感受,其中蕴含着堕落与救赎的内在逻辑联系。通过“阿特柔斯房屋的倒塌”这一宏大主题,福克纳为南方现世罪恶找到了一种普遍的共性支撑,继而将“南方的话题”成功地转换成了“美国的话题”,并实现了对南方地域主义的超越。其二是“阿特柔斯房屋的倒塌”揭示出了福克纳小说艺术呈现的一个重要链接点,即美国南方以家族血亲为纽带的家庭观念,这使得福克纳得以从家庭的视角显现和窥视整个南方的社会面貌。
按历时性顺序,学术界一般将美国南方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旧南方时期、内战与重建时期、新南方时期。福克纳所生活的时代南方正处于由旧向新的社会转型关键期。经过内战的洗礼,旧南方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以农业经济形态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北方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及其价值观大举入侵。而20世纪前半叶,尤其是一战后,南方社会的商业化气息日益浓厚,这使得地域特色浓郁的南方渐渐消融于美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对此福克纳描述道:“在三角洲上也出现了北方人开的伐木场:现在是二十年代中期,在三角洲,棉花业还有伐木业都很蓬勃。但最为蓬勃的是金钱本身:金钱孽生出一种穴居人,而他又繁衍出一对双胞胎的穴居人:欠债与破产,这三者如此迅速地让金钱在这片土地上大逞淫威,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在它旋风般使你窒息之前赶快将其摆脱掉。”[5]21经济基础变化,必然引发思想观念变化,“新南方”的价值体系随之兴起。这在具有相当保守主义倾向的福克纳看来非但不是南方社会的进步,相反却是一种倒退,是对南方既有传统的伤害,人本质的失落和社会道德的衰退就发生于这种悄然的变革之中。在《喧哗与骚动》1933年版前言中,福克纳明确提出南方早已为内战所杀死,他讽刺地说道:“有那么一个东西,被异想天开地称作新南方,不过那并不是南方。那是一块移民者的土地,他们按照堪萨斯、衣阿华和伊利诺斯的城镇的样式在重建城镇,用摩天大楼和条纹帆布篷来代替木结构的阳台。”[12]229可见,在福克纳心中,现代文明改变了南方旧有的一切,包括人性和人的精神。而在小说《野棕榈》中福克纳又借主人公之口再一次提出了现代南方的精神危机问题:“假如耶稣今天回到人世,我们不得不出于自我保护立即把他绞死,以便当今的文明合法化并延续下去。”“假如维纳斯能够返世,她会周身污秽地出现在地铁的厕所里,一只手里捏着一把法国明信片。”[20]针对南方社会现实给福克纳带来的困扰,卡尔评述说:“福克纳置身于两种激烈冲突的观念和运动之间:一个是他土生土长的、代表整个南方社会进步的固步自封的牛津社区;另一个是在想象中使其脱离牛津和地方性的敌对的现代主义观念。他的创作和生活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11]7卡尔所说的“摇摆”的直接结果显然是福克纳对世界本质认知的转变,其中以全新的艺术视野来深入探讨南方社会的矛盾性和荒谬性是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意义上,作为“家庭罗曼司”重要组成角色的女性形象自然不可或缺。因此,《圣殿》及其它描写女性罪恶的小说应该被看作是福克纳在女性形象视阈下艺术化地再现“阿特柔斯房屋的倒塌”主题的文学范本。
[1]海明威. 死在午后[M]. 金绍禹,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173.
[2]CLEANTH BROOKS. William Faulkner: The Yoknapatawpha Country [M].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P, 1963:116.
[3]威廉·范·俄康纳. 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M]. 张爱玲, 林以亮,于梨华,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4]巴尔加斯·略萨. 谎言中的真实[M]. 赵德明, 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285.
[5]WILLIAM FAULKNER. Essays, Speeches & Public Letters [M].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2004.
[6]陆建德. 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M]. 卞之琳, 罗经国,李赋宁, 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180.
[7]戴维·洛奇. 小说的艺术[M]. 卢丽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43.
[8]李文俊, 编. 福克纳的神话[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10.
[9]IRVING HOWE. William Faulkner: A Critical Stud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60.
[10]ROBERT PENN WARREN. Faulkner: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M].Englewood: Prentice Hall, 1955:130, 133.
[11]FREDERICK R. KARL. William Faulkner: American Writer[M].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9.
[12]WILLIAM FAULKNER. The Sound and the Fury: A Norton Critical Edition[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Norton & Company, 1994.
[13]JAMES B. MERIWETHER, MICHAEL MILLGATE . Lion in the Garden: Interviews with William Faulkner, 1926-1962 [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8.
[14]FREDERICK L., GWYNN, JOSEPH BLOTNER. 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 Class Conferen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57-1958 [M].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59.
[15]WILLIAM FAULKNER. Sanctuary[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7:159.
[16]保罗·里克尔. 恶的象征[M].公车,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260-262.
[17]JAY PARINI. One Matchless Time: A Life of William Faulkner[M].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4:136.
[18]MALCOLM COWLEY. The Portable Faulkner[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3:xxi.
[19]DIANE ROBERTS. Faulkner and Southern Womanhood[M].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4:129-139.
[20]WILLIAM FAULKNER. The Wild Palms [M]. London: Vintage Books, 2000:115.
(责任编辑:刘 燕)
Sanctuary:ArtisticReproductionof“theCollapseofAtreus’House”inthePerspectiveofFemaleFigures
Wang G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Jilin 136000, China)
Sanctuaryhas important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 Faulkner’ s novelistic system. It is the same as other novels depicting women’ s evil, which is a literary example of artistic reproduction on the theme of “the Collapse of Atreus’ House” in the perspective of Faulkner’ s female figures. Faulkner has obviously inherited relations with biblical theology thought in the creation of female figures. He regards biblical concepts as a base and a starting point to discuss religious origin of evil in the world, and reveals the theme of “the Collapse of Atreus’Hou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construction of southern traditional lady images with complex emotions to the south.
Faulkner;Sanctuary; female figures; evil; the Collapse of Atreus’ House
I712
A
1672-7991(2017)03-0039-05
10.3969/j.issn.1672-7991.2017.03.008
教育部2015年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圣经之维:美国南方文学经典的文化诗学阐释”(15YJC752033);吉林师范大学2016年青年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文学经典的文化记忆书写”(jscxjj2016-29)。
2017-05-11;
2017-05-31
王 钢(1978-),男,辽宁省鞍山市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欧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