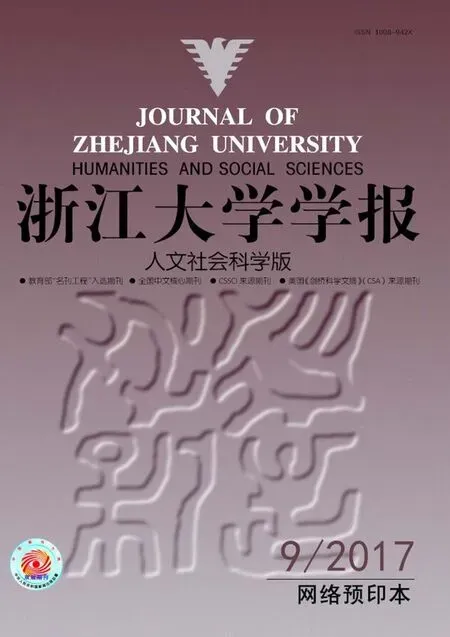东西文化观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
——以日本“另类”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为考察中心
肖 朗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近代日本的建立和发展始终受到日本人对东西方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的认识的深刻影响。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从明治初期古典亚细亚主义的诞生,发展到后来的大亚细亚主义,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走过了一段从理想主义转化为现实主义的历程。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始终可见日本对亚洲文明以及中国文化认同与否的态度变化。可以说,对儒家学说及中华文明如何评价成为衡量日本亚洲认识的一个计量器。”[1]36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对儒家文化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近代日本对华及对亚洲国家外交政策的催化器。以森有礼、加藤弘之、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大都以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他们将近代西方文明视为人类文明的典范,主张摒弃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及东亚传统文化。特别是堪称近代日本最著名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他全盘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形成了“文明=欧美”“野蛮=亚洲”以及“脱亚=脱儒”的逻辑构架及思维模式,为“脱亚入欧”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把这种思想推向了对外侵略的方向,客观上对甲午战争的爆发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关于福泽谕吉及其“脱亚入欧”思想,详见肖朗《近代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思想探源——以福泽谕吉及其“脱亚入欧”思想为中心》,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5-19页。。然而,明治初期与福泽谕吉比肩齐名的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体察、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概括出“敬天爱人”的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实质,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以此认识为主要思想背景,中村敬宇与王韬、黄遵宪等晚清中国文人、学者开展了多姿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其代表性著作、译作也经梁启超等人引介而传入中国。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村敬宇是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另类”代表人物。鉴于国内学界对中村敬宇的思想、活动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讨*国内学者如严绍璗、王家骅、王克非、刘岳兵、郑匡民、高增杰、薄培林等人在论述日本的中国学史研究、儒家思想对日本近代思想及现代化的影响、近代日本的中国观、近代中国启蒙思想中的日本因素等问题时曾涉及中村敬宇,或在开展近代中日政治哲学思想比较考察时以严复与中村敬宇等日本启蒙思想家为个案,但总体而言比较零碎,关于中村敬宇迄今尚未形成全面的、系统的研究成果。,本文拟探讨中村敬宇关于东西方文化的主要观点及其思想特征,具体考察中村敬宇与王韬、黄遵宪等人的交流活动及由此形成的近代中日文化、思想的双向交流,并力求得出中村敬宇研究的当代启示。
一、 中村敬宇及其东西文化观
(一) 启蒙思想家的双重身份: “儒学者”和“洋学者”
中村敬宇,原名钏太郎,后改正直,又名敬辅,号敬宇,别号无思散人、无思陈人、无所争斋等,1832年出生于江户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父母笃信佛教。据载,其母曾前往日莲宗的本传寺拜佛求子,后生下中村敬宇,中村遂于6岁时受父母之命书写《法华经》4段120行字奉献给本传寺;6岁那年他患病,又因父母祈祷佛祖保佑而康复[2]1-4。有学者认为,中村敬宇毕生崇敬佛教即与上述家庭环境的影响分不开[3]213-214。他自幼聪颖,好学强记,3岁从师学句读和书法,10岁就读昌平黉,曾因刻苦用功而得赏银。他11岁时开始研习汉籍,15岁时入井部香山开办的私塾,进一步接受汉学及儒学的熏陶;17岁时入昌平坂学问所*昌平坂学问所是德川幕府的官学,明治维新后称昌平学校,即东京大学的前身。,拜著名儒者佐藤一斋为师。佐藤号称德川幕府时代“阳朱阴王”的思想家,对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均素有研究。有日本学者在介绍佐藤一斋的“学风”时明确指出:“一斋乃宽政之后有数的文章家,其儒学是折中主义的。”[2]10这主要指佐藤一斋外奉朱子学而内宗阳明学,同时力求把“主事”的汉学与“主理”的宋学调和互补[4]223。中村敬宇晚年回忆道:“余少一斋先生六十岁,同以壬辰生。甫五岁,先考携余,往谒先生于杨子沟之居,先生命余书大字,众人环视,纸积成堆。先生曰:子盍暂休焉,食果而复书。余掉头曰:否否,纸不尽不休也。先生大赏其英气,令嗣亦光年十四,立刻印以赐余。此余受知于先生之始也。既而先生年七十,起为幕府儒官,往昌平学官邸。余成童修门人礼,侍讲习,奉指诲,多历年所。及先生没,亦光嗣为儒官,余亦被擢辱其末班。呜呼,余之不才而得至此,皆先生之赐也。”[5]卷九,15中村敬宇在学术思想上深受佐藤一斋的影响,这不仅因为他在佐藤一斋的教诲下通过钻研汉籍而奠定了汉学和儒学的扎实基础,更主要的是佐藤一斋使他从年轻时就养成了“博综广采,禁党戒偏”[6]344的开放胸怀和治学风范。1855年,中村敬宇开始任教于昌平坂学问所,六年后他被幕府任命为“御儒者”*御儒者为幕府官名,其职责主要是进讲经典。,成为官方认可的正统儒学者。
中村敬宇生活的时代正值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近代西方各种学说纷纷传入的历史时期,始而是以荷兰为代表的“兰学”,继而则是欧美各国的“洋学”。早在入昌平坂学问所前,中村敬宇即“窃习兰籍(兰学典籍)”[6]343*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注,下同。;入该学问所后他进一步接触兰学,据称“汉籍置于桌面,而兰书暗藏抽屉,无人时悄然阅读”[7]31。1855年,中村敬宇开始学英语,据其当年撰写的《穆理宋韵府钞叙》介绍,他曾借助英国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Morrison,中村敬宇译作“穆理宋”)编纂的英华辞典学英语,后又从友人处借得荷兰人编纂的英语、荷兰语、汉语对照的辞书并全部誊抄下来[5]卷五,2。1862年,通英语的箕作奎吾拜中村敬宇为师研习儒学,中村敬宇便常向他请教英语的发音、阅读等。伴随着荷兰语、英语的学习,中村敬宇开始阅读外文书籍,同时参阅了魏源的《海国图志》,遂对西方政教文明有了初步的认识。1866年,受幕府派遣,中村敬宇以监督官的身份率12名留学生渡海赴英。因年龄限制,中村敬宇在英国未能正式入学,但接受了英国教师的个别指导,并专心自学。据其自述,“朝课暮绎,较短角长。锥股悬梁,何暇忆乡”[6]344。学习之余,他和留学生一起参观了水晶宫、造船厂、炼铁厂、兵工厂、植物园、报社、朴次茅斯军港等。值得注意的是,他还了解到英国早期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Legge)翻译的英文“四书”及有关研究成果。在英期间,中村敬宇结识了几位友人,其中对他影响较大的是弗里兰(H.W.Freeland),后者毕业于牛津大学,知识渊博,著译颇丰,其内容广泛涉及欧洲周边地域、东方问题及阿拉伯世界,“他可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绅士的典型之一”[4]237。弗里兰平时对中村敬宇十分友善,赠予后者的饯别之物便是斯迈尔斯(S.Smiles)的名著《自助论》。
1868年,中村敬宇途经法国回到日本,出任静冈学问所教授,四年后被明治政府起用而返回东京,在此期间他撰写了《敬天爱人说》《拟泰西人上书》等代表作,并将《自助论》和约翰·穆勒的《论自由》翻译成日文,分别取名为《西国立志编》和《自由之理》。日本学者记载:“世人将福泽氏(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内田氏(内田正雄)的《舆地志略》和先生的《西国立志编》三部畅销书合称为‘明治三书’……先生继《立志编》之后,又续刊《自由之理》和《西洋品行论》等。《自由之理》研究民权,《品行论》则如《立志编》的补翼,亦为社会所欢迎,销售不让前书,均发行数十万册。当时之读者,不限于少年子弟,乃横亘各阶层,尤其官吏及教职人员,若不通读此三书,则被视为于资格有所欠缺,皆不得不争而诵读。故先生之声名,郁然高于海内,至儿童走卒,莫不知先生之名与其著述者也。”*中村敬宇将斯迈尔斯的另一部著作Character,翻译成日文,取名为《西洋品行论》。[7]66我国学者也高度评价《西国立志编》及中村敬宇翻译此书的影响:“此书记叙西方自古以来三百余位立志成名的名人的事迹,鼓吹自立自主,发奋向上,备受读者尤其是青年的欢迎,被誉为‘明治之圣经’。”[8]第1卷,149此后,中村敬宇以“洋学者”的身份不断致力于启蒙宣传活动及文教事业。1873,他设立了洋学塾“同文社”,被誉为“明治三塾”之一*其余两所分别为福泽谕吉设立的“庆应义塾”和近藤真琴设立的“攻玉社”。。同年,他与西周、森有礼、西村茂树、加藤弘之、福泽谕吉等人结成“明六社”*1873年即明治六年,故名“明六社”,一般认为“明六社”是明治日本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社团,所谓明治启蒙思想主要是指“明六社”成员宣传的启蒙思想。详见大久保利謙《大久保利謙歴史著作集6·明治の思想と文化》,(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年版。,并创办《明六杂志》。他还积极参与训盲院和东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工作。此后,他出任东京大学教授,并担任贵族院议员等公职。
总之,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身兼“儒学者”和“洋学者”的双重身份,他的东西文化观也因此在当时表现出不同凡响的鲜明特色。
(二) “敬天爱人”: 东西方文化的思想要素及精神实质

至于日本究竟应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什么这个关键问题,中村敬宇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幕府末期的有识之士已认识到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并将西方科技文化与中国的道德文化对比起来加以把握。例如,佐藤一斋便明言:“西洋穷理,形而下之数理;周易穷理,形而上之道理。道理,譬则根株也;数理,譬则枝叶也。枝叶自根株生,能得其根株,则枝叶从之。穷理者宜自易理而入也。”[10]284这种观点后演绎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思维模式,且逐渐成为幕府末期部分知识人士的共识。中村敬宇起初也持这种观点。他在1858年左右撰写的《洋学论》中宣称:洋学非在儒家之“道”外,故为儒者份内之事,其内容唯技艺而已[9]439。但1866年赴英前夕,他在《留学奉愿候存寄书付》一文中写道:“西洋开化之国中,大凡学问可分为两项:性灵之学即形而上之学,物质之学即形而下之学。文法之学、论理之学(逻辑学)、人伦之学、政事之学、律法之学,以及诗词、乐律、绘画、雕塑之艺等,属性灵之学;万物穷理之学、工匠机械之学、精炼点化之学、天文地理之学、本草药性之学、稼穑树艺之学,属物质之学。”[6]279并指出迄今为止一般认为西方的学问只有“物质之学”,而“性灵之学”尚不充分,其实后者对西方各国而言十分重要、有用,且须专门研究,进而透露了自己愿赴欧洲研究“性灵之学”的意愿。这表明中村敬宇突破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思维模式,已认识到西方的“物质之学”与“性灵之学”存在内在联系,因而西方文化是包含两者在内的统一体。中村敬宇后来的相关认识可谓这种看法的衍生、发展和升华。
赴英两年,中村敬宇留心观察英国社会,促使他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有些地方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表现在日后他在翻译《西国立志编》《自由之理》时所写的若干序跋及按语中。如他写道:“余尚记童子时,闻清英交兵,英屡大捷,其国有女王,曰维多利亚,则惊曰:眇乎岛徼,出女豪杰乃尔,堂堂满清,反无一个是男儿耶。后读《海国图志》,有曰英俗贪而悍,尚奢嗜酒,惟技艺灵巧,当时谓为信然。及前年游于英都,留两载,徐察其政俗,有以知其不然。今女王不过含饴弄儿孙耳,而百姓议会(指众议院)权最重,诸侯议会(指参议院)亚之,其被抡于众,为民委官者,大抵学明行修之人也,有敬天爱人之心者也,有克己慎独之工夫者也,多更世故、长于艰难之人也,而权诈獧薄之徒不与焉。其俗则事上帝,尊礼拜,尚持经,好济贫病者……凡百之事,官府之所为,十居其一,人民之所为,十居其九,然而其所谓官府者,亦唯为民人而设之机关耳,如贪权势、擅威刑之事毋有也。抑以通国之广、人民之众,岂不有奸宄不法之徒乎,然审其大体,则称曰政教风俗擅美西方,可也。”他还写道:“余又近读西国古今隽杰之传记,观其皆有自主自立之志,有艰难辛苦之行,原于敬天爱人之诚意,以能立济世利民之大业。”[5]卷一六,29-30在中村敬宇看来,国家的强盛不是靠个别明君,而是靠议会制度及其议员的素质,归根结底有赖于全体国民的素质以及造就这种素质的社会风俗及教育,而其实质则主要体现为“敬天爱人”的基督教精神。早在赴英前,中村敬宇就认识到风俗的重要性:“风俗之于国,犹元气之于人身也。善养生者,不恃药石而务养元气,元气实则百体坚,百体坚则疾病奚由而生焉。善治国者,不恃法令而务正风俗,风俗正则国本固,国本固则祸乱何自而起焉。”[5]卷三,4赴英后,他发现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先进国家的治国之本,认识到以基督教精神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政教风俗培养了人的“敬天爱人”之心,塑造出高尚的绅士人格。
另一方面,凭借其深厚的汉学功底,在进一步深入研读儒学经典及日本儒学者的著作后,中村敬宇认识到东方儒家学说中富含“敬天爱人”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关于“敬天”的思想,他举例道:“仲虺之诰曰:钦崇天道,永保天命。说命曰:明王奉若天道。诗曰:敬天之怒,罔敢戏豫。孟子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张子曰:乾称父,坤称母。朱子曰:见古圣贤,朝夕只见那天在眼前。薛文清曰:天地者吾父母也,凡有所行,则知顺吾父母之命而已。又曰:敬天之心,瞬息不敢怠。又曰:敬天当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谓能敬天者妄也。贝原益轩曰:或问儒者一生之事业、平日之工夫何如。曰:事天而已。事天之道何如。曰:仁而已。为仁之道何如。曰:存心养性者,所以仁之体立也;爱育人物者,所以仁之用行也,乃所以事天也。敬天之说盖如此。”[5]卷三,15关于“爱人”的思想,则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鲁恭曰: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则天气为之舛错,故爱民者,必有天报。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心必有所济。西铭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颠连而无告也。真西山曰:为政者,当体天地生万民之心,与父母保赤子心,有一毫之惨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薛文清曰:处乡人,皆当敬而爱之,虽三尺童子,亦当以诚心爱之,不可侮慢也。爱人之说盖如此。”[5]卷三,15-16据此,中村敬宇认为“敬天爱人”并非基督教及西方文化所特有的思想因素,它也代表了中国及日本儒家文化的思想传统。
为了进一步阐明东西方“敬天爱人”思想以求两者会通,中村敬宇着重论述了下列观点:(1)“敬天”与“爱人”合一。以中村之见,“敬天”与“爱人”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他说:“天者生我者,乃吾父也;人者与吾同为天所生者,乃吾兄弟也。天其可不敬乎。人其可不爱乎。”[5]卷三,16换言之,天乃我之父母,故应敬之;人乃我之兄弟,故应爱之,因为人我皆为天之所生。中村敬宇又说:“敬天,故爱人。爱吾同胞,由于敬吾父。”[5]卷三,17由此说明“敬天”是“源”和“本”,“爱人”是“流”和“用”。关于两者的辩证关系,中村敬宇进一步分析道:“敬爱不可相离。天者,尊乎人也,故敬为主,而爱在其中;人者,与我同等也,故爱为主,而敬在其中。”[5]卷三,17(2)“天心”与“人心”合一。中村敬宇说:“天者无形而有知,无质而无所不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勿论人之言动,不循其昭鉴,乃一念之善恶动于方寸,亦不漏其视察。王法之赏罚,时有所不及,天道之祸福,虽速迟异,而决无所愆。盖天者理之活者,故无质而有心。”[5]卷三,16至于天以何为其心及其根据何在,中村敬宇明确指出:“天以何物为心,曰以仁义为心。曰由何而知之,曰由造化之迹而知之。观乎日月之所以交代、寒暑之所以推更、万物群汇之所以生育,岂不足以窥其大慈大惠之一斑乎。观乎祸福报应之验于人世者,岂不足以察其义刑义赏之一端乎。”[5]卷四,13-14因此,中村敬宇强调,天心“即好生之仁也,人得此以为心,即爱人之仁也。故行仁,则吾心安而天心喜矣,行不仁,则吾心不安而天心怒矣”[5]卷三,16。(3)“道理”与“德行”合一。在通过上述两点诠释了“敬天爱人”思想的理论意义后,中村敬宇又试图揭示“敬天爱人”思想的实践价值,即努力将“天道”转化为“人伦”。他分析道:自古善人君子因“知头上常有天之监临者,则诚意慎独之功,自不容于不至也;知有俨然尊乎我者,则虔洁奉事之心,自不容于不切也”[5]卷四,14。于是,“以诚敬行己,以仁爱接人,随境地之所遇,尽职分之当然,原于良心之是非,求合于天心之默许”,对自己能做到“极富贵而不骄,立勋绩而不矜,受穷苦而不忧,跌功名而不沮,虽被祸害受阨灾而快乐之心不为少损”[5]卷三,16,对他人则能做到“彼此协力,小大同心,智恤愚,强扶弱,富济贫,众不暴寡,邦国如一家而福利崇焉”[5]卷三,17。由此,中村敬宇指出基督教文化可以培养西方人的信心、望心、爱心,而东方儒家文化也同样可以培养人的“敬天爱人”之心和“克己慎独”之德。这说明在造就西方绅士人格和东方君子人格这一点上,由于东西方文化均包含“敬天爱人”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实质,其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中村敬宇参酌东西方“敬天爱人”的思想因素和传统并努力加以融合和会通,认为“不论古今,也不论东西南北,生民之所具、所行之道德,大抵通而为一,大同小异”[6]327,并提出了“古今东西道德一致”的著名论断,从而构成中村敬宇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观点,也是其东西文化观的特色之所在。在此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中村敬宇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先后发表《支那不可侮论》《汉学不可废论》等文,批驳当时日本片面追慕西方文化而全盘否定儒家文化的思想,与此同时,他热心与王韬、黄遵宪等晚清中国文人、学者交游,探讨彼此关注的问题,从而谱写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绚丽篇章。
二、 中村敬宇与晚清中国人的交游和对话
(一) 王韬访日及其与中村敬宇的交游
中村敬宇对汉学及儒学有深厚的造诣,同时他又以擅长用古汉语写作而名世。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井上哲次郎曾称道中村敬宇乃“明治年间秀绝的文章家”[11]。《敬宇文集》中收录了中村敬宇生前撰写的大部分文章,其中便包含了他为王韬《扶桑游纪》所写的序文,该文简要地介绍了王韬1879年游历日本的缘起、经过等,成为后人了解这一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盛事的重要文献。
王韬在他生活的时代堪称率先接受西学、走出国门的中国先进人士,也是近代中国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驱。早年他任职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开办的墨海书馆,协助那里的外国来华传教士翻译西方科技著作。1862年,他来到香港,结识了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并帮助他翻译《尚书》《诗经》《春秋左传》等儒学经籍。五年后,他受理雅各之邀远赴英国,在助其翻译《易经》《礼记》的同时游历各地,并在牛津大学发表汉语演说;他也顺道访问法、俄等国,结识了儒莲(S.Julien)等欧洲汉学家。1870年,王韬伴随理雅各回到香港,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同时创办了《循环日报》,评论时政,宣传变法自强的思想。这一时期,王韬对世界大势及国际形势也十分关注,普法战争爆发后他即在精通英语的张宗良等人的帮助下开始撰写《普法战纪》一书,并于1873年刊印。此书因有助于时人了解这场战争以及欧洲的形势,被广为传诵,不仅在中国多次重印,而且迅速流传到日本。据日本《邮便报知新闻》主编栗本锄云在《王紫诠(王韬)来游》一文中的记载,若干年前他在上海购得《普法战纪》,书中对战争过程的生动描述和作者充满新意的评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是自欧阳修《新五代史》以来罕见的史学杰作,于是邀请中村敬宇、重野安绎等学者加上句读并训点,于1878年由陆军文库刊印[12]392-393。当时的日本知识阶层读了该书后给予高度评价,如汉学家冈千仞称赞道:“《普法战纪》传于我邦,读之者始知有紫诠王先生,以卓识伟论,鼓舞一世风痺,实为当世伟人矣。”[13]237不妨说《扶桑游纪》在日本的传布为王韬访日提供了直接的契机,正如美国学者柯文(P.A.Cohen)所指出的,“王韬在日本的名声部分是由从香港返国的日本人的报道所致,但主要还是由于他的《普法战纪》一书带来的”[14]。因为正是这批读了《普法战纪》的日本文人、学者向他发出了访日的邀请*关于日本文人、学者邀请王韬访日的背景,详见肖朗《近代日中文化·教育交流史に関する覚え書き——中村敬宇の場合を中心として》,载《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部纪要(教育学科)》1993年第2号,第79-89页。。
关于邀请王韬访日的具体情况,日本学者龟谷行介绍道:“戊寅(1878)之春,余与栗本匏庵(栗本锄云)、佐田白茅探梅于龟井户,归途饮于柳岛。匏庵曰:吾闻弢园王先生者(王韬)今寓粤东,学博而才伟,足迹殆遍海外,曾读其《普法战纪》,行文雄奇,其人可想,若得飘然来游,愿为东道主。白茅曰善矣。余友寺田士弧曾至南海,与先生善,乃有东游之约。士弧与重野成斋(重野安绎)、冈鹿门(冈千仞)诸人,遂欲邀之。余告以匏庵言,于是成斋始与匏庵交。匏庵每置酒会友,未尝不津津乎王先生也。己卯(1879)之夏,先生遂航海而至。”[13]67中村敬宇的记述也印证了上述有关情况,他写道:“呜呼,人生朋友之际,声应气求,肝胆相照,千里来会,恨相见晚者,夫岂偶然哉,无非由于我有诚以感,彼有诚以应,缠绵牵合,交孚凝聚,而遂成一大盛事也,余于王弢园先生游吾邦之事而益知其然也。忆四五年前,余于重野成斋机上始见《普法战纪》,时成斋语余曰:闻此人有东游之意,果然则吾侪之幸也。察其意,若缱绻不能已者。其后栗本匏庵过余而论文,酒半睨余曰:吾既与佐藤白茅诸子游梅园,盟于暗香疏影之下,约共招王弢园,子亦不得不与此盟矣。盖成斋与匏庵之景慕先生,出于诚意如此。其他如冈天爵(冈千仞)、龟谷省轩(龟谷行)、寺田士弧等,皆先于先生之未东游而感召牵引,亦与有力焉。明治十一年(此误,实为明治十二年),先生遂来游。”*该序文最初发表于《同人社文学雜誌》1881年第46号,第1-3页。[13]153-155中村敬宇先为《普法战纪》训点,后又参与邀请王韬访日,可见他为促成这一盛事做出了较大贡献。
在中村敬宇等人的共同策划、推动下,1879年4月29日王韬从上海启程赴日,同年8月31日返回上海,后撰写《扶桑游纪》,详细记载了此次访日的经过。据载,他游历了长崎、神户、大阪、京都等地,5月15日抵达东京。当天,他拜访了任职于文部省的重野安绎、任职于大藏省的松方正义等人,这些人午后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王韬也在宴会上见到了栗本锄云等人。当月21日的《邮便报知新闻》报道了王韬访日的消息以及他的作品等[15]。此后,王韬除观光外几乎每天都要会见日本友人。据有的专家考证,王韬在日期间会见的日本人已逾百名[16]。中村敬宇曾对这种盛况描述道:“都下名士,争与先生交,文酒谈讌,殆无虚日,山游水嬉,追逐如云,极一时之盛。”[13]155据《扶桑游纪》记载,王韬与中村敬宇见面主要有两次。5月29日,王韬往访《邮便报知新闻》主编栗本锄云未遇,报知社老板小西义敬设宴招待王韬,中村敬宇即在座。中村敬宇对王韬说:“贵国文人学士游敝邦者,百余年间,时时有之,如先生者,可谓后来者驾而居上。”王韬答道:“前世不可知,若明朱舜水、张斐文、沈克异、载曼公等人,节义文章,炤耀后人,仆盖已叹来游之殊晚,而深欣吾道之不孤。”[13]83并赠诗中村敬宇曰:“修文馆里曾相见,知是骚坛擅盛名。自愧东游真草草,未携行卷谒先生。”[13]828月21日,王韬与中村敬宇再次见面。这天重野安绎等日本友人在中村楼设宴饯别王韬。席间,王韬挥笔写下长诗,在座的其他宾客也都写诗与之唱和。中村敬宇的诗曰:“闻紫诠先生将归,赋此寄呈。飘然乘兴日东游,才学如君乏匹儔。笔役风雷多逸气,胸罗星斗足奇谋。久思对榻纵谈未,能肯名车来访不。那忍匆匆分手去,天涯好会再难求。中村敬宇送紫诠先生南归即席赋呈。”[13]223生动地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
王韬访日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而隆重的欢迎,固然因为中日两大民族间长期存在的友谊,日本人视他为中国文人的代表,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更主要的“是王韬‘逍遥海外作鹏游,足遍东西历数洲’,深为渴望了解世界、走向世界的日本知识分子推重”[17]148。中村敬宇也曾表述了类似的看法:“夫清国之人游吾邦者,自古多矣,然率皆沽客,而又限于长崎一方。近来韦布之士来东京,间有之,然其身未至而大名先闻,已至而倾动都邑,如先生之盛者,未之有也。抑先生博学宏才,通当今之务,足迹遍海外,能知宇宙大局,游囊所挂,宜其人人影附而响从也。”[13]155-156王韬在日本交游甚广,结识的朋友中固不乏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人士,但大多是以重野安绎、冈千仞为代表的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而像中村敬宇这样的“洋学者”却为数极少,由于他们均在英国生活过,两人之间的共同语言自然相对多一些。这方面虽限于资料不得而知,但王韬在与不少日本友人交谈的过程中也表达或流露了他的一些看法和态度。当重野安绎把他称为“今时之魏默深(魏源)”,甚至认为“默深未足以比先生”时,王韬说:“当默深先生之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惜昔日言之而不为,今日为之而犹徒袭皮毛也。”[13]48-49在与西尾为忠讨论“中西诸法”时,王韬针对当时一些人盲目崇洋而不顾国情的做法,指出:“法苟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合之道矣。”[13]103他读了冈本监辅的《万国史略》后认为:“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又其病在行之太骤,而摹之太似也。”[13]130相对来说,王韬比较肯定日本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的态度,即“师其所长而掩其所短,亦欲求立乎泰西诸大国之间,而与之较长絜短而无所馁也”[18]59。本着这种见解,他批评洋务派学习西方仅限于器物和技术层面,而主张在科举、学校、法律等方面开展较为全面的改革,从而对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就中村敬宇而言,他主张学习西方应不局限于器物和技术的“形而下”层面,而向人伦之学、政事之学、律法之学的“形而上”层面推进,并认为“敬天爱人”是东西方文化共同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实质。面对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王韬和中村敬宇提出的改革方案虽不相同,侧重点也不一致,但在深化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不乏异曲同工之妙。
(二) 《同人社文学杂志》: 中村敬宇与黄遵宪的诗文对话
王韬访日期间结识了不少友人,其中也包括驻日公使馆的中国官员,主要是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以及参赞黄遵宪,何如璋甚至想招募王韬入职公使馆。就在王韬离日后不久,黄遵宪致函曰:“相聚不多日,匆匆告归,此怀何可言……宪与阁下虽新相知,而钦仰高谊已久。星使(何如璋)尤爱重公,意欲罗致幕府。顾以南岛属藩之事,波澜未平,行止靡定,虽经上书当路,而此间属员有额,方且告归请撤,未便增设……惟宪私心窃冀亟欲得阁下共处朝夕,时领教益,今既不能,因是独介介耳。”[19]301黄遵宪仰慕、求教王韬的诚意跃然纸上。信中还写道:“阁下此来,东国(日本)文士齐声赞叹无异词。”[19]302对王韬访日予以高度评价。此后,黄遵宪不断将自己的《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等作品赠送王韬以求其指教,两人长期保持通信联系,建立了终身的友谊。
如果说王韬访日尚属“走马观花”,对日本了解有限,他本人身上也染有风流倜傥的文人习气,那么黄遵宪以外交官的身份驻日多年,则对日本现状及历史的方方面面都有较为细致、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并在《日本杂诗事》《人境庐诗草》中留下了许多记载,最后汇编撰成专著《日本国志》,所以他堪称一位从事日本研究的严谨专家。1877年黄遵宪应何如璋之请,以清朝驻日公使馆参赞的身份随何东渡日本,1882年他奉命前往美国旧金山出任驻美总领事。驻日五年间,他利用外交官身份之便,结识了伊藤博文、榎本武扬、大山巌、重野安绎、中村敬宇、冈千仞、宫岛诚一郎、源桂阁(大河内辉声)等众多政治家、文人、学者。黄遵宪与中村敬宇之间多有诗文往还,彼此围绕中日文化问题开展了深度对话,黄遵宪写的若干诗文还经中村敬宇推荐发表于《同文社文学杂志》*据笔者初步统计,《同人社文学杂志》刊载的黄遵宪的诗文主要有《日本杂事诗抄录》(1880年第41号)、《牛渚漫录序》(1881年第62号)、《钞出墨子中与西学相合者》(1881年第62号)、《黄参赞答社长中村敬宇书》(1881年第62号)、《皇朝金鑑序》(1882年第76号)等。,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别开生面。
黄遵宪驻日之际,正值中村敬宇积极致力于启蒙宣传活动及文教事业之时。在此期间,中村敬宇相继翻译出版了《西国立志编》和《自由之理》。他关心日本的女子教育和师范教育,1875—1880年间出任东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摄理(校长),并开始从事创设训盲院的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876年他主持创办了《同人社文学杂志》,该杂志内容丰富、新颖,不仅发表了阐述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文章,而且发表了中村敬宇本人论述女子教育和介绍英国盲人音乐师范学校的文章,而黄遵宪的若干诗文也刊印其中。由此可见,《同文社文学杂志》不仅是中村敬宇本人及日本知识分子宣传西学的重要平台,也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窗口之一。
为了解和掌握日本女子教育及幼儿教育的真实状况,黄遵宪曾托付中村敬宇为之采集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师生的绘画,中村敬宇就此写道:“黄公度(黄遵宪)以绢嘱绘于东京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及生徒,各经写就,并缀俚言,伏希鉴政。”并亲自赋诗曰:“画法来中夏,俊逸贵高雅。泰西巧写生,但觉韵味寡。有耕霭女史,能事兼二者。进境何可量,精神常倾泻。婀娜女弟子,丰姿生笔下。相与绘群芳,五色灿如也。岭南黄赞府(黄遵宪),下交情不假。征画感虚怀,因之各力写。吾亦妄涂鸦,题诗愧庸野。工拙且休论,欲附骚人社。”[20]黄遵宪收到上述画、诗后复函中村道:“伻来,奉到尺书并素绢。此诗此画,可称双绝,将永藏筪笥为子孙宝,岂第屏幛生辉已也。诗称耕霭女史兼中、东(日本)、西能事,果然不谬,画家有南北合法,今更上一筹矣。乞先寄声致谢,容日将觅土物,附以拙诗,亲诣学校谢之。梅雨连绵,凉燠不定,惟珍卫为祷。卜日当偕二三友人来观学校,再图良晤。”[20]黄遵宪在信中高度赞扬师生的画和中村的诗,并表示将择日参观东京女子师范学校。不久,他走访了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并欣然写下三篇诗文[19]24-25。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积极创立近代学校教育体制,女子教育和幼儿教育即为其中的重要环节。黄遵宪在诗文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幼儿园成立的背景及经过,着重介绍了其教学内容和方法,指出它们主要导入和借鉴了西方近代教育的模式,并表示了肯定和赞赏。在此基础上,日后黄遵宪又在《日本国志》中以“学术志”为题,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日本近代学校教育制度[19]1420-1426。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刚刚起步,女子教育和幼儿教育尚十分落后,在此之际黄遵宪率先将日本教育改革的有关信息传入中国,其意义自不待言*关于黄遵宪的教育改革思想,详见肖朗《论黄遵宪的教育改革思想及其影响》,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第169-177页。,而中村敬宇对此所做出的贡献也不可埋没。
黄遵宪同意王韬对当时中日两国部分人士盲目崇洋而不顾国情的做法的批评,并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进一步说明中国文化及其传统不能全盘否定和抛弃。在阅读日本人撰写的《牛渚漫录》后,黄遵宪应邀写了一篇序文发表在《同人社文学杂志》上,文中指出:“西人之学,每偏于趋新,而吾党之学,每偏于泥古。彼之学术技艺,极盛于近来数十年中,古不及今,其重今无足怪也。吾开国独早,学术技艺,数千年前已称极盛,吾之重古人,古人实有其可重者也。不究其异同,动则剿袭西人知新之语,概以古人之所见斥为刍狗,鄙为糟粕,呜呼,其可哉!”中村敬宇在此文后附记道:“敬宇曰:黄公度先生此论,精确不磨。”[21]黄遵宪驻日期间,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方兴未艾。1878年11月16日,在与源桂阁等人的笔谈中,黄遵宪写道:“近者士风日趋于浮薄,米利坚自由之说,一倡而百和,则竟可以视君父如敝屐。”[19]670他又撰《皇朝金鑑序》一文发表于《同人社文学杂志》,指出:“余窃以为天下者,万国之所积而成者也。凡托居地球,无论何国,其政教风俗,皆有善有不善。吾取法于今日,有可得而变革者,有不可得而变革者。其可得而变革者,轮舟也,铁道也,电线也,凡可以务财、训农、通商、惠工者,皆是也。其不可得而变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凡关于伦常、纲纪者,皆是也。”中村敬宇在此文之后附记道:“余少时作《穆理宋韵府钞叙》,以可变者与不可变者,两两对比,颇与此文暗合。”[22]遂将《穆理宋韵府钞叙》一文刊于其后,该文中写道:“天地之所复载,人物之所蕃生,邦各有俗,民各成风。百尔制度,鲜有不异者,而至乎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之伦,则未尝不同也……自乾坤出开以来,政治风俗之变,何啻千万,盖亦古今代谢,不可已之势也,至于纲常伦理,则未尝少变。其不可恃者,时势之变也,其可恃者,民彝之不变也……今之时既异乎古之时,今之政独可同古之政乎,唯留心于纲常伦理,则有可恃者存焉。”[23]这说明,当时黄遵宪和中村敬宇均努力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角度理解与把握中日现代化改革的方向和趋势*黄遵宪后出使美、英等国,对西方近代政教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其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外学者对此均有论述。详见Noriko Kamachi, Reform in China: Huang-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郑海麟《黄遵宪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赴英后的观察、研究和体验使中村敬宇确信所谓“不可变者”及“可恃者”乃“古今东西一致道德”,其核心是“敬天爱人”的观念,它既集中体现了基督教精神,也存在于儒家学说之中,因而体现了东西方文化共同的思想要素及精神实质。基于这种观点,中村敬宇不但认为东西方文化不存在对立,甚至认为基督教和西方科技也在儒学范围之内。他说:“呜呼,孔子之道,行于欧罗巴,孙子兵法,用于欧罗巴,而我亚细亚或有不及焉,可胜叹哉!……或疑欧罗巴宗教则尚耶稣,理学则宗培根、牛董(牛顿)等,何以言孔子之道行于欧罗巴也。曰:余之所谓孔子之道云者,指其实也,非指其名也。孔子言仁爱,言忠恕,而彼之所以教于家而施于政者,实亦不外于此道矣。孔子言致知,言格物,而彼之所以穷物理而利民用,实亦不外于此道矣。由是观之,则彼耶稣者,培根者,牛董者,岂不在于孔子范围之中耶。”[5]卷一三,8-9黄遵宪却不赞同中村敬宇的这种观点。他批评道:“西学既盛,服习其教者渐多,渐染其说者益众。论宗教,则谓敬事天主,即儒教所谓敬天;爱人如己,即儒教所谓仁民;保汝灵魂,即儒教所谓明德。士夫缘饰其说,甚有谓孔子明人伦,而耶稣兼明天道者。”[19]1414关于这一点,有学者也曾明确指出,中村敬宇“是黄遵宪在日本的友朋中对西学最有认识的人,曾与黄遵宪讨论西学及基督教问题。但黄遵宪其时对基督教并无兴趣,亦不觉得基督教对中国有何好处”[24]267。
以黄遵宪之见,基督教“敬天爱人”之说及西方近代科技源于墨子的学说。他曾明言:“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其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绪余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经》上下篇。”[19]1399他又引用墨子的《尚同篇》《兼爱篇》《天志篇》《法仪篇》《尚贤篇》《非输篇》《鲁问篇》等文,撰成《钞出墨子中与西学相合者》一文发表于《同人社文学杂志》,以佐证自己的观点。同时,他致信中村敬宇,强调:“仆向读墨子,以谓泰西术艺,尽出其中。至尚同、兼爱、尊天诸篇,则耶稣之说教;米利坚之政体,亦隐括之。自明利玛窦东来,吾国始知西学,当时诧为前古未闻,不知两千余年之前已引其端。乃知信昌黎(韩愈)一生推许孟子,而有孔必用墨、墨必用孔之言,盖卓有所见也。”并说:“仆曾钞出墨子中与西教相合者数节,今以敬呈。先生学综汉洋,幸为仆断其是否。”[26]中村敬宇在收阅《钞出墨子中与西学相合者》一文后写道:“余未读墨子,忽得公度先生此抄本,始惊其见识卓然,真有不可磨灭者焉。”[25]在赠别黄遵宪的诗中,中村敬宇又述道:“公度先生轩霞表,使我对之俗念了。一夕谈话十年书,如泛大海采异宝。尝论墨子同西说,卓识未经前人道。”[27]
黄遵宪的上述观点可谓当时流行于中国的“西学中源说”的产物,虽未能获得科学的证明,但与中村敬宇的东西文化观一样,其表现出来的尝试融通东西方文化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
三、 中村敬宇著作、译作在晚清中国的导入
(一) 从《教会新报》到《万国公报》:《拟泰西人上书》的初刊及再刊
引人注目的是,《同人社文学杂志》不仅刊登了黄遵宪的若干诗文,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产生了影响,也刊载了近代来华欧美传教士的文章。中村敬宇曾将美国来华传教士林乐知(Y.J.Allen)的《中西关系略论》翻译成日文刊于《同人社文学杂志》。该文论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呼吁清政府与各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28]。后《同人社文学杂志》又刊载了中村敬宇题为《中西关系论题辞》的两首诗作:“中西关系尚须论,况乃车书谊久敦。只使二邦(中日两国)盟带砺,河清海晏谧乾坤。”“中东(中日两国)和好善坚持,外国其谁敢侮之。同运连枝宜协力,愿相爱敬莫相疑。”[29]表达了他本人希望中日友好的真挚愿望。再如,他将英国来华传教士韦廉臣(A.Williamson)于1870年出版的JourneysinNorthChina,Manchuria,andEasternMongolia:WithSomeAccountofKorea的部分章节翻译成日文发表于《同人社文学杂志》[30]47。该文介绍了中国的自然环境、政治、商业、文化以及留学生、学者等内容,最后把亚洲的前途寄托于中国[31]。事实上,正是由于林乐知和韦廉臣的努力,中村敬宇的代表作《拟泰西人上书》才得以传入中国*中村敬宇还曾为韦廉臣的重要著作《格物探原》写序,该序文参见《敬宇文集》卷一五,(東京)吉川弘文馆1903年版,第28-29页。。
韦廉臣最初于1855年从苏格兰渡海来华,在上海传教,两年后回国,1863年再度来华,在烟台传教。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议决成立益智书会,负责编写教科书,以供教会学校使用,韦廉臣担任该会秘书。次年,他因病回国。1884年,韦廉臣在苏格兰组织同文书会进行募捐活动,用所募钱款购置印刷机器,在上海设厂印刷中文书籍。不久苏格兰同文书会因故解散,韦廉臣第三次来华,并联络林乐知等人于1887年在上海成立同文书会,后于1894年改名为广学会。另一方面,林乐知于1860年从纽约渡海来华,在上海传教。1868年,他创办中文周刊《中国教会新报》,次年改名《教会新报》,主要刊登传播基督教教义的文章以及中国教会活动的报道,偶尔也刊载教育方面的新闻。因《教会新报》的内容偏于宗教方面,其发行量严重受限,遂于1874年改为月刊《万国公报》,并于1887年成为广学会的机关报,此后它便成为晚清影响最大的传播西学的杂志之一。《教会新报》创刊第四年曾连载署名“日本人”的《拟泰西人上日本国君书》一文[32],据考证,此文即为中村敬宇的《拟泰西人上书》*关于这一点,详见肖朗《近代日中文化交流史の一断面——中村敬宇の「擬泰西人上書」を中心に》,载日本歴史学会編《日本歴史》1998年8月号,第83-95页。。1877年1月《万国公报》再刊该文,无署名,题目改为《拟泰西人上书》,编者加按语道:“此书系由烟台韦廉臣先生寄来,后附评语,嘱登公报。查此则本书院已于《教会新报》第四年报中业经登过,兹蒙寄嘱再列,且其书中亦多利益,再后有评语,颇为确当,特申明再登之,由供诸同好是幸。”[33]可见,《拟泰西人上书》传入中国实为林乐知和韦廉臣两人努力的结果。
在《拟泰西人上书》中,中村敬宇以“外臣”自居并模仿西洋人的口吻,先赞扬明治维新后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改革并取得显著成效,总结道:“凡此等新法新政,莫非取外国之善,收他邦之长者,自非有陛下宽大之量,与人民自新之心,何以臻此,是实外臣之所称赞而不已也。”[5]卷一,6然后笔锋一转,指出:“然此等,究不过西国之糟粕焉耳,顾至其精神,则殆如胡越之不相知焉,此西国人之所窃笑,而外臣之所为陛下惜者也。”[5]卷一,7接着,中村敬宇切入正题道:“陛下其亦知西国之所以富强乎。夫富强之原,由于国多仁人勇士,仁人勇士之所以多出者,莫非由教法之信心、望心、爱心者,西国以教法为精神,以此为治化之源,匪独此也,至于妙绝之技艺,精巧之器械,有创造者,有修改者,其勤勉忍耐之大势力,莫一不根于教法之信、望、爱三德者。盖今日西国之景象者,不过教法之华叶外茂者,而教法者实为西国之本根内托者,贵国喜其枝叶之美,欲尽得之于己,百方试学,不愧如猴猿之为,而顾遗其所由之本根,其亦惑矣。”[5]卷一,7并一再强调:“西国治化之美,文艺之善,机器之巧,贵国之所艳慕者,皆末流也。西国之教法,贵国之所嫌恶者,其本源也。今贵国喜其末流,而恶其本源,可谓惑矣。”[5]卷一,8“善树结善果,恶树结恶果。今日之开化日新者,果也。教法者,树也。陛下若以西国之果为善耶,则请无疑于其树之善也。”[5]卷一,9在中村敬宇看来,所谓议会、学校、通信、技术等皆是基督教精神带来的“华叶”,也不过是西方文化的“糟粕”,而其“本根”则是基督教精神,这才是西方文化的精髓,归根结底就是要造就具有“敬天爱人”之心和“克己慎独”之德的“仁人勇士”。在《拟泰西人上书》中中村敬宇秉承和发扬了其一贯的观点,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并无新意,但他运用了诸如“华叶—本根”“末流—本源”“果实—树木”这类表述方式,遂使其观点进一步形象化、生动化,并彰显出深入浅出的特色,从而更具说服力、感染力。正因如此,日本著名学者吉田造作指出阅读此篇后“惊叹中村先生持有独特而卓异的见识……故不得轻视本篇及与之相关的诸篇在明治思想史上的意义”[34]解题,10。韦廉臣也高度评价该篇“情真语挚,言大而不邻于夸,意刻而不失之薄,非深识治体、洞悉利弊者不辨”[33],充分肯定了《拟泰西人上书》对近代日本学习西方所具有的借鉴价值。
与此同时,韦廉臣借机向中国人介绍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现代化改革的概况。他在“评语”中写道:“是书(《拟泰西人上书》)上后,日本之君臣奉为圭臬,亿兆化之,设立讲堂,以读书谈道为务,其政教号令之革新鼎故者不可枚数,而尤得力于泰西者有二,曰造器曰用人。”在“造器”方面,他列举轮船、铁道、电信等设施;在“用人”方面,他指出日本在颁布近代学制的基础上创立了包括大学、中学、小学的三级学校体制,“文人学士丛集其中,养贤育德,以为异日教育之资……即匹夫匹妇莫不读书,教化兴人才自盛,其势然也”[35]。与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一样,中村敬宇的《拟泰西人上书》及韦廉臣的上述介绍在晚清中国可谓最早传入了明治维新的有关信息,有助于当时中国人了解近邻日本现代化改革的最新动态,并从中获取教益和启示。
(二) 梁启超与《西国立志编》在晚清中国的引介
如前所述,中村敬宇从英国回日本后投身于启蒙宣传活动及文教事业,尤以翻译《西国立志编》和《自由之理》而成为明治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之所以翻译《西国立志编》,一方面是因为他始终坚信日本应向西方学习的并非军事、技术、经济等有形之物,而是隐藏在这类有形之物背后的无形的民族精神及社会风气,他自述道:“余译此书,客有过而问者曰:子何不译兵书。余曰:子谓兵强则国赖以治安乎,且谓西国之强由于兵乎。是大不然。夫西国之强,由于人民笃信天道,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权,由于政宽法公。拿破仑论战曰:德行之力,十倍于身体之力。斯迈尔斯曰:国之强弱,关于人民之品行。又曰:真实良善为品行之本。盖国者人众相合之称,故人人品行正则风俗美,风俗美则一国协和,合成一体,强何足言。若国人品行未正,风俗未美,而徒汲汲乎兵事之是讲,其不陷而为好斗嗜杀之俗者几希,尚何治安之可望哉。”[5]卷五,6他认为西方的富强不是源于“兵强”,而是源于“人民有自主之权”和“政宽法公”的民主制度,而这种制度又源于“人民笃信天道”“真实良善”的品行和风俗。另一方面,《西国立志编》主要面向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下层以及广大劳动群众,以论述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及其伦理道德为重点,这在中村敬宇看来更符合其改造日本人民的民族素质、提高其国民道德与品行的初衷和愿望。《西国立志编》出版后深受日本读者欢迎,在明治时期多次被用作小学修身教科书[4]279。据日本学者介绍,《西国立志编》对日本近代民众“自立论”及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西国立志编》在近代日本产生的深远影响,还可参见平川祐弘《天ハ自ラ助クルモノヲ助ク:中村正直と「西国立志编」》,(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36]297-396。因此,《西国立志编》难逃同为启蒙思想家的梁启超的慧眼,深深打动了他的心。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日期间,梁启超广泛阅读各种日文书籍,不仅接触到以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卢梭、康德、孔德、约翰·穆勒等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思想,也熟知吉田阴松、福泽谕吉、中村敬宇、加藤弘之、中江兆民等日本思想家的学说。他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刊物,以“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中国”[37]文集之六,54为宗旨。作为在日本发表的第一部著作《自由书》,梁启超收入了他平时撰写的文章,其中包含依据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所写的《文野三界之别》、介绍加藤弘之进化论思想的《加藤博士天则百话》,同时收录了中村敬宇为《西国立志编》所写的六篇序及题为《书西国立志编后》的跋。他介绍道:“日本中村正直者,维新之大儒者也,尝译英国斯迈尔斯氏所著书,名曰《西国立志编》,又名之为《自助论》,其振起国民之志气,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气,功不在吉田(吉田阴松)、西乡(西乡隆盛)下矣……今将其各编之序录出,虽尝鼎一脔,犹足令读者起舞矣。”[37]专集之二,16
继《自由书》之后,梁启超撰写《新民说》等论著,努力塑造近代国民的形象,并强调近代国民必须具备“独立自尊”的意识,主要表现在经济上的“自立”和政治上的“自治”。他在自己的论著中常引用《西国立志编》中“天常助自助者”这句名言。他曾说:“西谚曰:天常助自助者。又曰:我之身即我之第一好帮手也。凡事有所待于外者,则其精进之力必减,而其所成就必弱。自助者其责任既专一,其所成就亦因以加厚。”[37]文集之三,63-64此外,《西国立志编》中提到的拿破仑、哥伦布、士提反孙(现通常译为“史蒂芬孙”)、瓦德(现通常译为“瓦特”)等欧美历史上的名人,也经常出现在梁启超的论著中,成为他用来鼓励国人“自助”的典范。学界一般认为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借鉴了福泽谕吉关于“独立自尊”的思想,但从上述材料来看,《西国立志编》所倡导的“自助自立”思想对梁启超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小觑。
毋庸置疑,《西国立志编》主要阐明了西方特别是英国的近代伦理道德观,梁启超便以此为思想资源进一步阐发其教育改革观。他指出:“英人之言曰:吾英人不以金钱财产留贻子孙,所留贻于子孙者,金钱所不能购买、财产所不能蓄积之敢为活泼之精神,独立自活之能力而已。是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类皆有强矫自助之风,彼其幼年童稚,在家庭学校之中,其父母教师,皆不视为附属之物,务使活泼自由,练习世事,不依赖他人而可以自立,其自助之精神最强,虽艰阻而强立不返……惟英人能发挥自立之志气,故能养成独立自营之伟大国民。”[37]文集之十四,7在借鉴英国近代伦理道德观的基础上,梁启超又指出近代英国的教育宗旨即在于塑造自主自立的人格,并认为此乃英国近代教育的最大特色。他分析道:“英人常自夸曰:‘他国之学校,可以教成许多博士学士,我英之学校,则只能教成人而已。’人者何。人格之谓也。而求英人教育之特色,所以能养成此人格者,则惟授之实业而使之可以自活,授之常识而使之可以自谋。”[37]专集之四,73他具体分析道:“其教育之宗旨,在养成活泼进步之国民,故贵自由,重独立,熏陶高尚之德性,锻炼强武之体力,盖兼雅典斯巴达之长而有之焉。英国之学校,特注重于德育体育,而智育居其末。若以学科之繁、程度之高论之,则英国之视诸国,瞠乎后也,而绝大之学者、绝大之政治家、绝大之国民出焉。何也。其教育之优点,不在形质而在精神。”[37]文集之十,56较之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主张“废科举”“兴学校”“重师范”等制度层面的改革,到日本后其教育改革的重点已发展为创立近代教育宗旨、塑造独立自主的国民人格等精神层面,这不能不说是由于他受到西方及日本近代价值观念特别是《西国立志编》的影响。
另一方面,中村敬宇认为近代人格的核心是具有“敬天爱人”之心,对此梁启超并不同意,有学者指出,梁启超甚至因此在《自由书》中抄录中村敬宇为《西国立志编》所写的序跋时有意改动了原文[38]119-120。但他们一致主张从国民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入手,通过对民众开展启蒙宣传工作来改造其精神素质,从而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准和品行,就这一点而言,两人都接受了《西国立志编》的主要观点。
四、 结语: 中村敬宇研究的当代启示
面对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及知识分子大多站在反儒的立场上,其对儒学的批判在当时无疑起到了启蒙民众的积极作用,但他们片面接受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全盘否定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从而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与此相反,中村敬宇对汉学及儒学有深邃造诣和深刻体认,认识到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强大的文化潜能,并善于发现和阐扬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与传统。针对那些不顾历史传统、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论调,他回顾道:“吾邦于支那,为邻国……自千余年来,至于中古,礼乐文物,工艺器具,大抵无不从支那朝鲜输入,儒佛二教即从两国传来。故于幕府时代,如朝鲜人来聘,其仪式甚为殷勤,且择文人学士相结伴,彼等亦以选中为荣,笔谈问答,诗文往返,一时称盛。来自长崎商舶的支那人,偶有有文事者,即为当时之汉学家所敬重,或相聚笔谈,或乞诗文之批正,如能得一言之褒,则视为金玉也。然与欧美外交之事起,以至于百事以其为师,邦人或自以为在支那人之上,鄙视支那人之弊遂起。”[6]324并指出这种数典忘祖的浅薄心态是不足取的。他进一步批评那些以文明开化自居而蔑视中国的日本人:“今我邦之开化,为外人使之开化而非以自国之力而进步,有非用外人而为外人所用之态,以不相应之薪金雇用外人……今我若以得欧美之一分之心情而鄙视支那人,恰如借人之美服而鄙视穿着破烂者,岂不为有识者所讥笑耶?”[6]302-303可见,对儒家学说和中国文化,中村敬宇固然怀有尊敬的感情,但更持有理性的态度,体现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对于当下传承和弘扬儒家学说的合理因素及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以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不乏启示价值。
然而,中村敬宇并非泥古不化的守旧派,早在明治初期即以翻译《西国立志编》《自由之理》等西方近代名著而闻名遐迩,并积极从事启蒙宣传活动,对日本的现代化改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村敬宇超群卓绝的可贵之处,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待和处理东西方文化问题时成功地突破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试图理性地分析东西方文化的长短优劣,洞察和把握双方的特点,进而加以融合与会通。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村敬宇“是用一种求同存异的发展眼光来看待儒学的”[39]34,可以说他也是用这种眼光来处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会通的。明治维新后,面对日本汲取西方文化的强劲势头,中村敬宇坚持汉学不可废的立场。在他看来,汉学不但在维系社会伦理、裨益世道人心方面仍可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掌握西方文化的精髓。他主张寻求和发现儒学与西学的“大同”之处,进而架起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这样无论儒学还是西学,皆可使其摆脱固有的局限性,从而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意义。他说:“不论古今,也不论东西南北,生民之所具、所行之道德,大抵通而为一,大同小异。”[6]327又认为:“盖道无古今东西之异,譬如太阳,天地间唯一而已。智者悟其大同,而昧者则迷其小异。”[5]卷一四,10进而把治学方法归结为“集众异以备思察,濯旧见以冀新得”[5]卷五,10。对比参照,集思广益,舍其小异,取其大同,这就要求学者具有开放的胸怀、平等的精神、包容的心态。事实上,中村敬宇与王韬、黄遵宪等晚清中国文人、学者开展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虽主题内容不尽一致,方式方法也各不相同,但都采取了平等对话、求同存异的基本态度,即便看法不同、观点各异,也未妨碍彼此的交流。如前所述,中村敬宇认为“敬天爱人”代表了基督教和儒学的共同精神,黄遵宪不同意这种观点而主张基督教思想与墨子的学说多有吻合之处,中村敬宇得知后表示由衷的钦佩;梁启超也不赞成中村敬宇的上述观点,但这不妨碍他对《西国立志编》的积极引介。在当代多元文化和跨文化交流日趋兴盛的国际大背景下,彼此尊重和相互理解的开放、平等、包容的原则尤其值得坚持和倡导。
中村敬宇的东西文化观中还包含了人类和谐、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和诉求。早年中村敬宇在探讨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时即认为一个国家必须立足于道义之上,坚持正义的立场,他反复指出:“理直则克,曲则败……理义之强,天下莫不尚也。”[5]卷三,1-2对西方列强侵略东方弱小国家的行径谴责道:“外洋诸蕃,挟其强大,以逞亡厌之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5]卷三,6日后他坚持各国平等的近代国际关系准则,又借鉴儒家关于大同的理想,进一步阐述道:“天生斯民,欲人人同受安乐,同修道德,同崇知识,同勉艺业,岂欲此强而彼弱、此优而彼劣哉。”进而强调:“地球万国,当行学问文艺相交,利用厚生之道,互相资益,彼此安康,共受福祉,如此则何有乎较强弱竞优劣哉。”[5]卷五,6明确反对西方列强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暴贫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反观福泽谕吉,早年他也提倡以“世界普遍的道理”为原则的平等的国际关系论,指出富强的欧美国家欺负贫弱的亚非国家“则和大力士用腕力拧断病人的手腕一样,就国家权利来说是不能容许的”[40]。但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扩张,其思想逐渐向对外侵略的方向倾斜,无视并力图斩断日本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甚至主张日本加入西方列强的行列“奋起逐鹿中原(中国)”[41]313。章太炎曾说:“他日吾二国(中国和印度)扶将而起,在使百姓得职,无以蹂躏他国、相杀毁伤为事,使帝国主义群盗,厚自惭悔……是吾二国先觉之责已!”[42]376孙中山也说:“中国古时常讲‘济弱扶倾’……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43]742章太炎和孙中山的观点可以说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他们在这种传统的基础上,从保护弱小民族的天职与使命的高度表达人类和谐、世界大同的诉求。在这一点上,中村敬宇与他们的心是相通的。诚然,19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欧美发达国家已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甲午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也逐渐演变为帝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已成为这些国家的本质特征之一,因而要求它们能坚持平等、公正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不现实的,就这一点而言,中村敬宇的思想可谓具有理想主义色彩。
[1]王屏: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Wang Ping,TheAsianisminModernJap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
[2]高橋昌郎: 『中村敬宇』,東京:吉川弘文館,1966年。[Takahashi Masaro,NakamuraKeiu, Tokyo: Yoshikawa Kobunkan, 1966.]
[3]荻原隆: 『中村敬宇研究——明治啓蒙思想と理想主義』,東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90年。[Ogihara Takashi,AStudyofNakamuraKeiu:EnlighteningThoughtsandIdealisminMeijiPeriod, Tokyo: Waseda University Press, 1990.]
[4]松沢弘陽: 『近代日本の形成と西洋经验』,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Matuzawa Hiroaki,TheFormationofModernJapanandWesternExperience, Tokyo: Iwanami Shoten, 1993.]
[5]中村敬宇: 『敬宇文集』,東京:吉川弘文館,1903年。[Nakamura Keiu,TheCollectedWorksofNakamuraKeiu, Tokyo: Yoshikawa Kobunkan, 1903.]
[6]大久保利謙編: 『明治文学全集3·明治啓蒙思想集』,東京:筑摩書房,1967年。[Okubo Toshiaki(ed.),TheCompleteWorksofLiteratureinMeijiPeriod,Vol.3:EnlighteningThoughtsinMeijiPeriod, Tokyo: Chikuma Shobō, 1967.]
[7]石井民司: 『自助的人物典型·中村正直傳』,東京:成功雑誌社,1907年。[Isiyi Minji,ARepresentativeofSelf-help:ABiographyofNakamuraMasanao, Tokyo: Seiko Periodical Office, 1907.]
[8]严绍璗: 《日本中国学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Yan Shaodang,AHistoryofJapaneseChinaStudies,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9]松本三之介: 『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学問と知識人』,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Sannosuke Matsumoto,ASeriesofModernJapaneseThoughts:LearningandIntellectuals, Tokyo: Iwanami Shoten, 1988.]
[10]家永三郎: 『日本思想大系46·佐藤一斋 大盐中斋』,東京:岩波書店,1980年。[Iyenaga Saburo,ASeriesofJapaneseThoughts,Vol.46:SatoYiisai&OsioTyusai, Tokyo: Iwanami Shoten, 1980.]
[11]井上哲次郎: 「教育家としての中村正直」,『教育』1932年第5号,第5-7页。[Inoue Tetujirō,″Nakamura Masanao as an Educator,″Education, No.5(1932), pp.5-7.]
[12]栗本鋤雲: 『匏庵遺稿』,東京:裳華書房,1900年。[Kurimoto Sukikumo,PosthumousManuscriptofHoan, Tokyo: Syoka Syobo, 1900.]
[13]王韬: 《扶桑游纪》,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Wang Tao,TravelsinJapan, Taipei: Wenhai Press, 1968.][14]
[美]柯文: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P.A.Cohen,BetweenTraditionandModernity:WangTaoandReforminLateChingChina, trans. by Lei Yi & Luo Jianqiu,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15]佚名: 「府下雜報」,『郵便報知新聞』1879年5月21日。[Anon.,″News of Tokyo Prefecture,″PostNews, 1879-05-21.]
[16]实藤惠秀: 『近代日支文化論』,東京:大東出版社,1941年。[Saneto Keishu,OnModernJapaneseandChineseCulture, Tokyo: Daito Publishing Co., Inc., 1941.]
[17]锺叔河: 《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Zhong Shuhe,GoingtowardstheWorld:TheHistoryofChinesePeopleInvestigatingtheWest,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18]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Wang Tao,TheCollectedWorksofWangTao:TheAdditionalVolume, Shenyang: 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4.]
[19]陈铮编: 《黄遵宪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Chen Zheng(ed.),TheCompleteWorksofHuangZunx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
[20]中村敬宇: 「诗二首」,『同人社文学雜誌』1879年第34号,第8-9页。[Nakamura Keiu,″Two Poems,″TheLiteraryMagazineofDojinsha, No.34(1879), pp.8-9.]
[21]黄遵宪: 「牛渚漫録序」,『同人社文学雜誌』1881年第62号,第4页。[Huang Zunxian,″Preface toUsinakiManroku,″TheLiteraryMagazineofDojinsha, No.62(1881), p.4.]
[22]黄遵宪: 「皇朝金鑑序」,『同人社文学雜誌』1882年第76号,第9-11页。[Huang Zunxian,″Preface toKotyoKingan,″TheLiteraryMagazineofDojinsha, No.76(1882), pp.9-11.]
[23]中村敬宇: 「穆理宋韵府钞叙」,『同人社文学雜誌』1882年第76号,第11-12页。[Nakamura Keiu,″Excerpts from R.Morrison’sADictionaryoftheEnglish-ChineseLanguage,″TheLiteraryMagazineofDojinsha, No.76(1882), pp.11-12.]
[24]蒋英豪: 《黄遵宪师友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Jiang Yinghao,HuangZunxian’sTeachersandFriends,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2.]
[25]黄遵宪: 「钞出墨子中与西学相合者」,『同人社文学雜誌』1881年第62号,第8-14页。[Huang Zunxian,″Excerpts from Mo Zi Which Accord with Western Learning,″TheLiteraryMagazineofDojinsha, No.62(1881), pp.8-14.]
[26]黄遵宪: 「黄参赞答社长中村敬宇書」,『同人社文学雜誌』1881年第62号,第15页。[Huang Zunxian,″Reply to President Nakamura Keiu by Counsellor Huang,″TheLiteraryMagazineofDojinsha, No.62(1881), p.15.]
[27]中村敬宇: 「奉赠黄公度先生」,『同人社文学雜誌』1882年第72号,第20页。[Nakamura Keiu,″Presenting to Mr.Huang Gongdu,″TheLiteraryMagazineofDojinsha, No.72(1882), p.20.]
[28]中村敬宇: 「中西關繫略論抄譯」,『同人社文学雜誌』1877年第12号,第13-18页。[Nakamura Keiu,″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ofOnSino-WesternRelations,″TheLiteraryMagazineofDojinsha, No.12(1877), pp.13-18.]
[29]中村敬宇: 「中西關繫論題辭」,『同人社文学雜誌』1879年第37号,第9-10页。[Nakamura Keiu,″Inscription ofOnSino-WesternRelations,″TheLiteraryMagazineofDojinsha, No.37(1879), pp.9-10.]
[30]刘岳兵: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三卷(1840—1895)》,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Liu Yuebing,Japan’sViewofChinasinceModernTimes:Vol.3, 1840-1895,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31]中村敬宇: 「英人韦廉臣支那論」, 『同人社文学雜誌』1879年第35号,第1-4页。[Nakamura Keiu,″The Englishman A.Williamson’s View of China,″TheLiteraryMagazineofDojinsha, No.35(1879), pp.1-4.]
[32]日本人: 《拟泰西人上日本国君书》,《教会新报》(四),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第1877-1878,1887-1889页。[Japanese,″Imitating a Statement Submitted to the Emperor of Japan by a Westerner,″TheNewsofChurches(4), Taipei: Huawen Book Company, 1968, pp.1877-1878, 1887-1889.]
[33]佚名: 《拟泰西人上书》,《万国公报》(六),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第3386页。[Aono.,″Imitating a Statement Submitted by a Westerner,″TheGlobeMagazine(6), Taipei: Huawen Book Company, 1968, p.3386.]
[34]明治文化研究会編: 『明治文化全集·思想篇』,東京:日本評論社,1967年。[Meiji Bunka Group(ed.),TheCompleteWorksofCultureinMeijiPeriod:Thoughts, Tokyo: Nippon Hyoron Sha Co., Ltd., 1967.]
[35]佚名: 《拟泰西人上书》,《万国公报》(六),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第3388-3389页。[Aono.,″Imitating a Statement Submitted by a Westerner,″TheGlobeMagazine(6), Taipei: Huawen Book Company, 1968, pp.3388-3389.]
[36]藤原暹: 『日本における庶民的自立論の形成と展開』,東京:ぺりかん社,1986年。[Fujiwara Noboru,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theSelf-relianceTheoryamongJapaneseCivilians, Tokyo: Perikansha Publishing Inc., 1986.]
[37]林志钧编: 《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Lin Zhijun(ed.),ACollectionofWorksofLiangQich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9.]
[38]郑匡民: 《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Zheng Kuangmin,TheJapaneseAcademicBackgroundofLiangQichao’sEnlighteningThought,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3.]
[39]刘岳兵: 《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Liu Yuebing,ModernChineseandJapaneseThoughtsandConfucianism,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40]
[日]福泽谕吉: 《劝学篇》,群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Fukuzawa Yukichi,OnEncouragingLearning, trans. by Qunl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58.]
[41]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全集』第5巻,東京:岩波書店,1959年。[Fukuzawa Yukichi,TheCompleteWorksofFukuzawaYukichi:Vol.5, Tokyo: Iwanami Shoten, 1959.]
[42]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徐复点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Zhang Taiyan,TheCompleteWorksofZhangTaiyan:TheFirstVolumeoftheCollectedWorksofZhangTaiyan, proofread by Xu Fu,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43]魏新柏编: 《孙中山著作选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Wei Xinbai(ed.),SelectedWorksofSunYat-se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