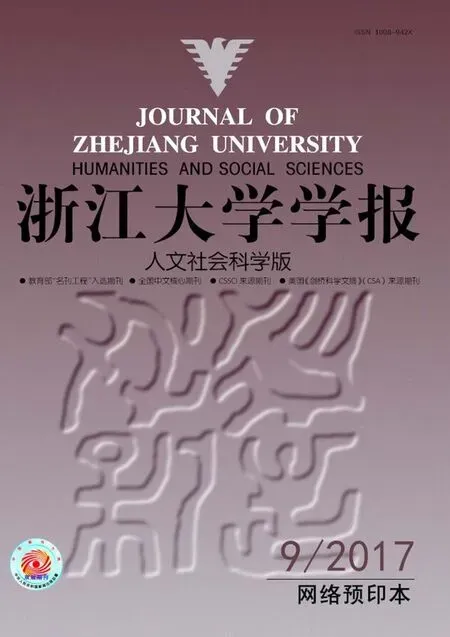政社良性互动的生成机制: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社会自治的互动演进逻辑
汪锦军
(浙江省委党校 公共管理教研部, 浙江 杭州 311121)
政府与社会关系问题是现代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问题。过去几十年来,理论和实践领域都积累了大量关于政社互动的认识,这些认识主要在三个层面展开:首先是宏观理论层面的讨论,从20世纪80年代的市民社会讨论,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法团主义模式在中国的适用性争论,学界一直致力于构建对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认识。其次是微观机制的探讨,与宏观理论探讨不同,很多研究发现,微观机制层面的政府与社会互动呈现显著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这也间接回应了宏观理论探讨可能并不能有效回答政府与社会互动中的多元机制问题。最后是政策层面的表述,这以党和国家制定的政策为代表。比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三个层面的认识推进既相互影响,又存在各自的独立性。遗憾的是,这些不同认识在很多方面相互矛盾,这表明理论与实践探索依然缺乏一个有效理解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共识性框架。宏观理论层面的讨论无论是多元主义还是法团主义,实际上都存在用西方的建构性理论来套用对中国的解释问题,因此,这些讨论都不得不修补原有理论以与中国独特实践对接,导致至今仍缺乏一个关于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模式的共识性认识基础。而微观机制的讨论虽然将视角更多转向了正在发生的地方实践,却由于过多关注微观多元性而忽视了这些多元性背后的基础性理论建构,因此在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抽象方面往往没能再前进一步。政策层面的认识和表述体现了国家层面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战略导向,却需要将政策理念与现实形成有效对接,这些对接依然有赖于对政府与社会互动现实的规律性认识和诸多的政策创新。因此,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认识需要一种全新的分析路径,这种路径既需要超越简单套用西方理论的模式化认识,也需要在中国实践基础上为新理论的发展提供可能,并在此基础上为实现党和国家的政策目标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本文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尝试在已有研究和实践分析基础上对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进行更为细致的解构,从政府与社会各自不同主体的相互关系演进路径方面分析政府与社会互动的逻辑。与一般泛泛而论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分析不同,本文将在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发展等多个层面的互动网络中分析这些主体的行为逻辑,在此基础上揭示目前政社关系的总体结构性特征,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社会自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提出实现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良性互动所需要的赋权、吸纳与嵌入之间的平衡战略。
一、 寻求相互增权的互动合作: 政府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政府与社会是两大治理主体和治理领域,如何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政府与社会互动的理解从以二元冲突为主的解释转向合作的解释,并达成了现代治理体系建构的基本共识: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既是可能的,也是可以有效的,这也符合对中国政社关系发展的基本认识和判断。
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一直受一种固定思维的影响,即认为政府与社会的整体权力规模是恒定的,一方如果强大了,则会挤压另一方的权力空间,也即政府与社会是一种零和博弈关系。比如科尔曼就认为政府的介入会使非正式网络减弱,减少社会资本。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发现政府与社会之间并不完全是零和博弈关系,很多时候政府可以与社会形成一种合作关系,政府与社会双方的互动在特定环境下能相互增权,即同时加强双方的权力[2]。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带来了诸多的地方治理变革,合作治理在近几十年的公共领域治理实践中迅速发展[3]171,成为理解政府与社会互动实践的重要理论认识框架。公私伙伴关系、合作生产和跨部门协同等理论的发展都是这一认识框架的具体体现。
中国实践中的政社关系处在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中,这种调整源于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政府需要不断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与一个越来越开放而多元的社会建立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近年来,学界对政社关系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中国的政府与社会之间不是对抗性的关系[4],而越来越多呈现出合作关系。在政社关系的互动中,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进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互动增权的过程[5-6]。这种认识表明中国的政社互动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具有趋同性,即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主流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因为合作不但可以提升政府的能力,而且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但目前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在具体运行层面还没有形成逻辑一致的制度框架,各层级政府与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呈现整体合作化趋向与微观碎片化多向度发展并存的特征。对于政府与社会的整体合作化趋向,很多学者用法团主义进行解释*但法团主义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比如在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方面,很多社会组织并没有像法团主义所描述的那样被整合到政府体系中,而且政府与各种组织的制度化连接并不完备。不过也应当承认,相对于多元主义而言,中国的政社互动关系确实更接近法团主义特征。。在这一整体性的认识之下,如果把目光聚焦于微观关系,则可以发现具体领域中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无论在主体还是在机制方面都呈现出碎片化、多元化发展的特征。就主体而言,不同层级的政府、政府的不同部门和不同的社会主体在互动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甚至有时不同主体之间的行为相互矛盾,并不是逻辑一致地相互合作,这也部分反映了相互关系背后混乱的制度体系。就机制而言,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规范体系和连接机制的缺乏,使得具体的互动关系形态千差万别,在具体互动中往往不同主体具有不同的策略选择。目前实践中有两种情形同时存在:一方面,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之间的有机互动存在制度性障碍,很多时候是政府的过多介入削弱了社会进行自组织和协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的创新实践又确实形成了一种合作治理和良性互动的格局。很多地方的创新都越来越强调通过政府与社会的有机互动以形成合作治理的格局,从而既提高政府能力,又增强社会自治。因此,在“整体性合作”的判断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考察政社互动的碎片化、多元化的内在机制,是理解未来政府管理和社会自治能否实现良性互动的重要认识路径。
二、 政社关系变迁中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社会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领域的发展和变化带来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而这种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又受政府角色的影响,因此理解中国的政府角色如何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就显得非常关键[7]。政府与社会是如何相互影响又相互塑造的?对此问题的解答不但需要对中国政社关系的宏观把握,也需要对互动中的微观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如果我们把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放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社会自治的互动结构中观察,可以发现这三者在特定的制度结构和政策目标中都起着不同的作用,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一) 中央政府“地方—社会”双重战略下的政社关系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社会领域被整合到国家的制度体系之下,基层社会被单位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化形态无缝隙占据。这一时期的国家和社会是一体的,因此被称为全能主义国家、整体性社会。单位组织以及各级行政组织像蜂窝壁一样将社会分割为互不沟通的部分[8]。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城市改革,以单位制和人民公社为特征的组织结构开始解体,各种要素开始流动,很多人脱离了原来的单位体制,这深刻地改变了社会活动和社会依赖的类型。国家必须越来越多地以其他形式的与社会互动的关系来取代终身隶属于单位管理的模式,包括完善能够规范社会行为和裁决资源分配争端的法律体系[9]190。
因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央的理念和政策逐步转变,政策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从过去忽视、限制社会发展到主动引导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自治和公民参与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中,中央始终在有效管理地方和有效管理社会的两大战略中寻找政策平衡点。一方面,中央希望社会在国家引导下健康有序发展,能够成为政策执行和公共服务的伙伴;另一方面,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过去的放权与收权往往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困境,因此,在中央、地方和社会的关系中,中央越来越依赖向社会放权来制约地方政府滥用职权的问题。不同研究和观察都可以佐证这种判断。比如李侃如认为,1987年出台的村委会组织法是试图通过真正的村级选举来激起农民的热情并限制地方权力,同时使村干部负起执行税收、计划生育等上级委派任务的责任[9]190。而一项对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研究也发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态度往往是不同的。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更多地公开信息,而地方害怕潜在自治权的丧失或腐败暴露使其决策过程的细节置于中央政府的监督下[10]。理解中央的这双重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中央对社会发展的态度具有重大的战略考量: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不但可以协助中央有效执行政策,而且有助于防止地方政府滥用权力。
通过党中央会议的表述可以发现,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领域和政策对象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党的十五大之前,对社会的理解主要停留于社会稳定的范畴,十五大报告中对“社会”一词的论述,要么是放在经济范畴中的,比如提出“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这里的社会中介组织主要是一些和经济发展相关的组织;要么是从社会安定团结角度讲的,比如“搞好社会治安”“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而真正将社会作为一个政策领域来对待的,是党的十六大。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目标,而之后不久,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社会建设的全新理念,这表明中央将社会建设作为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并驾齐驱的战略来推动,为此,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而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纲领,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社会建设的目标是“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因此,从党中央报告表述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策的调整,而且这种调整的方向非常明确,即从关注社会稳定到聚焦于社会治理和社会活力。这表明党和政府既希望通过政策调整以顺应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的变迁,也希望能够使社会在国家引导下良性健康发展。
与党的政策方向相一致,与社会领域相关的各项制度规范自改革开放以来也不断调整。从实行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与社会领域相关的社会组织、社区建设的基本制度框架。在社区法律规范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7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并于1998和2010年两次修订。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则早在1954年就颁布,1989年又颁布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该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组织法的颁布和实施使基层自治走上了规范化管理的发展道路。在社会组织规范方面,目前与社会组织相关的主要法律性文件是民法通则和基金会、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条例。根据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法人分为四种类型: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社会组织相对应的是社团法人。而对社会组织的规范最早的制度可追溯至1950年政务院制定通过的《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1988年《基金会管理办法》出台(不过,该办法依然将基金会看作是一种社团),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1989年国务院通过《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修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国务院又专门颁布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这一系列法规颁布与实施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框架。但总体而言,政府在导向上主要是规制而不是鼓励社会组织发展,比如在制度上设计了双重管理体制、重大活动报告制度、限制竞争和跨地域活动等,而对社会组织赖以发展的免税资格等则没有予以明确。
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在社区建设和社会组织发展方面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调整,在中央创新社会管理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战略方向下,以民政部为主导的中央政府部门开始大力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组织管理创新,其基本特征是推动社会力量的成长、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众的参与。在社区层面,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进一步得到加强,并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领域加强具体操作性的机制建设。在社会组织方面,随着社会组织的大量涌现,中央开始鼓励地方的各种创新,2013年以来,中央开始加速推进社会组织发展和改革创新,包括探索部分类型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取消或下放一些社会组织的登记或审批权力;推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这些创新使政府在社区层面的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得到强化,而社会组织则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 地方政府与社会的“选择性合作”策略
尽管地方政府与上述中央政府同属政府范畴,但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地方政府的表现往往与中央政府迥异。影响这种差异性的主要结构性因素有两个:首先,我国地方政府是一个多层次的层级制结构,每一层级政府在职能上都可以说是中央政府的翻版,钱颖一等学者将这种地方政府结构称之为M型组织结构,以区别于苏联计划经济时期的U型结构。这种M型结构的地方政府拥有半自主的权力[11],即在各种事务处理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也包括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不完全遵照中央政策而自我解释和自主处理的权力。其次,地方政府又处在一个压力型的结构*荣敬本等人曾经提出了“压力型体制”的概念,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他们认为,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推进经济增长和社会事务的方式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动员型体制,即由各级党委直接动员民众来完成中央下达的各项任务。进入改革的起始阶段即“放权”之后,计划体制下由中央掌控的财政权和人事权逐级下放给地方,以调动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同时保留中央给地方规定的各项指标,以控制和监督地方官员完成这些指标,并由此确保政治上的一致性。荣敬本等人认为,这种分权的“压力型体制”实质上表现为一种政治承包制,将各项任务量化分解到下一级政府或具体的机构和个人,并根据完成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这些任务和指标中的主要部分采取“一票否决制”,即一旦某项任务没有达标,将不得给予各种先进称号或奖励,乃至将其全年的工作成绩视为零。在上级和下级之间形成了权力(职位)与任务(指标)之间的交换关系:权力成了一种施与,而完成任务则是一种回报;反过来,任务/指标完成得出色,理论上可以产生更大的权力预期。参见荣敬本、崔之元、王拴正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中,即地方政府自主性是相对的,在压力型体制下,下级政府不得不想尽办法完成上级设定的任务和指标,否则其官员很难在职位晋升中胜出。这种体制使地方政府为了取得良好政绩而展开地方竞争,被认为是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原因之一[12],但也使地方政府在政绩的综合考量中决定是否以及如何与社会开展合作,而不一定反映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这两个结构性因素是理解地方政府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两个基本背景。
实践中的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很多时候表现出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戴慕珍认为,在中国农村地方社会层面,代表国家的县政府、代表市场的企业与代表社会的村庄,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彼此合作、互相交织的关系格局,这一结构形态完全不同于市民社会特征[13]99。当然这种结构性特征并不能涵盖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所有关系,除了合作,地方政府与社会之间也存在不少冲突、分隔,甚至是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对社会的侵蚀。
地方政府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往往遵循“选择性合作”的策略,即地方政府会根据特定的情形来决定是否与社会力量进行合作。选择性合作意味着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关系是在特定环境下的理性选择,这种关系往往不是制度化和持续性的。
三个因素决定了地方政府是否选择与社会力量合作。首先,是上级的政策导向和政策框架。如前所述,地方政府是处在一个压力型的层级结构中的,这种源于计划经济的政府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上级在政策动员方面对下级有重要的影响力。21世纪以前,当中央和上级政府将重心放在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上时,地方政府也会更关注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组织和机构。21世纪以来,当中央将社会建设作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后,关于民生和社会建设的政策不断出台,地方政府因此需要制定相关细则以落实中央的社会建设任务和目标。比如,在近年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中,很多省直接在指标体系中增加了社会建设相关的考核内容,中央的政策导向因此直接转化为地方的政策实践,地方政府为此开始进行更多的社会建设与公民参与的创新实验。其次,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变迁,且社会治理、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属于全新的施政领域,地方政府在施政中遇到了很多政策和法律的模糊甚至空白领域,这些领域尽管为政社互动关系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却因此为地方政府与某些社会组织的选择性合作关系带来了可能性。比如,在一个关于中国草根组织生存空间的研究中,Spires发现,当一些草根社会组织致力于社会需求,而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希望他们辖区内的问题能够以一种不会引起上层不满的方式来解决时,双方各取所需的合作默契便实现了,草根组织能继续其工作,而官员也就可能不会很在意这些组织是否合法的问题[14]。最后,由于社区和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具有政府无可比拟的优势,当地方政府觉得与这些组织的合作有利于提高政府政策的执行力和服务供给的绩效时,会主动选择合作[15]。而相反,对一些地方政府认为无助于甚至会影响地方发展的社会组织,则可能会予以压制。比如在我们研究的一些行业协会的案例中发现,当行业协会诉求与政府部门的希望相冲突时,这些协会就往往逐步走向没落[16]。
上述三个因素相互作用,决定了地方政府与社会互动中合作或不合作的策略选择。这种选择会随着时间变化和政策变革而不断调整。比如,在民工子弟学校方面,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早在2002年就颁布并于2003年实施,但地方政府真正将民工子弟学校作为基础教育提供的重要伙伴是在好几年以后。在对上海的研究中发现[15],在2008年以前,民工子弟学校和政府的关系走得比较远。2008年,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一项政策,允许民工子弟学校登记并得到政府的资助,民工子弟学校每年由此获得生均2 000元的资助,并接受政府的监管,学生的学费也因此基本可以免除。这一个案的态度背后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基本趋势,那就是随着近年来中央大力倡导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组织发展,以及地方在应对各种复杂社会矛盾冲突中的无奈,地方政府越来越求助于社会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合作正在不断增强。比如,自2000年以来,在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发起的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中,入围项目达到139项,而其中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相关的项目高达92项之多,占总项目的66%以上[17]。而且,与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合作治理类入围项目数量始终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不同,社会领域协同治理类入围项目数量总体上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这不但反映了党和政府倡导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目标,而且也表明地方政府越来越倾向于用合作的方式来处理社会问题。
(三) 社会的依附性自治及近年的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开始变革,其中的重要标志就是社会领域的自主性开始增强,全能主义政府的解释已不再适应新形势,学界因此开始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来分析社会结构的变迁及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都开始探索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社会成长的可能性。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区在倡导自治的组织法推动下也开始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官办的社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这些组织在扩展政府服务、扩大国际交流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在当时,社会力量往往被认为是反抗政府的,因此,在早期对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解释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市民社会理论和多元主义理论。如高登·怀特提出当代中国出现了市民社会的萌芽,并且正在向市民社会的方向发展[18]。赵文词、倪志伟等都认为中国未来变革的方向应该是市民社会[19-20]。而鉴于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特殊环境,一些学者渐渐开始调整市民社会概念,用“半市民社会”[21]、“国家领导的市民社会”[22]等概念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不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似乎并没有完全按照所谓市民社会理论预设的路径演进。一方面,尽管非官办的社会组织快速发展,而官办社会组织也开始变得更加独立以增强社会合法性,但这些组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追求与政府的合作而不是对抗;另一方面,在对社区和社会组织的管理方面,政府的介入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发展而弱化,只是在形式方面越来越多样化。为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更接近法团主义模式而不是多元主义。由于此处重点在于探讨社会的发展空间问题,因此关于法团主义模式本身的适用性不做过多分析。
总体而言,在社会领域自主性增强的过程中,社会对政府的依附性一直存在,因此这里用依附性自治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领域的发展特征,这一概括凸显了社会领域发展的两大主要事实特征:依附性和自治性。
作为观察社会发展的两大领域,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都呈现出目前制度和发展环境下一定的依附性。在社区发展方面,尽管社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被强调自治,但这种自治从一开始就不是绝对的,在城市和农村的组织法中,在关于基层自治组织的定位方面,除了强调其自治组织性质外,同时强调基层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基层社区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由于基层社区组织自治的范围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规界定,而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上级交代的各种任务和考核,越来越明显地将各种任务交给社区解决,基层社区的自治性被逐渐侵蚀,而行政化趋向则日益明显[23]。社会组织方面也是如此,这不但体现在管理上明确要求有业务主管单位才能登记*近年一些类型的社会组织登记已不再需要有业务主管单位。2014年9月,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做客中国政府网在线访谈时表示,全国共有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开展或试行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工作,有1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先后出台了推进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的相关政策文件,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等四类社会组织可直接登记。,而且在日常管理中对社会组织的年检评估、党建等方面都有相应的管理规定。由于社会组织缺乏使其独立自主的规制框架,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从属性的合作关系[24]。比如,1998年清华大学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有46.6%的社会组织是由业务主管部门提供办公场所的[25]53-54,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许多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附性。2010年,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对浙江和北京各种社会组织的问卷调查数据也显示,在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特点的认识方面,认为两者是地位平等的合作关系的比例为19.6%,而认为是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比例最高,为40.4%。多数社会组织认为自身与政府之间不是平等合作的关系。
因此,虽然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空间,但无论是对社区还是对社会组织发展而言,都必须与政府进行良好的互动,尽管在与政府的互动中往往具有某种不平等性,政府在互动中处于明显强势[26],有大量的资源和手段对各种社会力量施加影响。正因如此,政府在社会组织发展方面是选择性的,政府采用分类控制战略[27],重点发展一些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相关的组织,而对其他诸如境外组织等则持谨慎的态度。为此,我们把这种特征概括为依附性。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近年的发展还表明,随着社会的多元化,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引导策略也在发生变化,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表现为制度和管理上的限制的话,那么现在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具有开放性,管理手段也更加多元,社会对政府的依附性从过去的管理制度的刚性依附逐渐转向柔性依附和意识性依附。
在依附性这一基本格局之上,社会的发展也确实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自主性。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变革,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以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的自主性在增强,自治空间在扩大,作为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管理双重制度环境下的社会力量,在多重博弈中找到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在理念上,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各种主体自身,都认识到现代多元社会中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因此构建一种符合多元社会的现代治理体系是政府与社会的共识,社会对政府的过度依附并不符合政府的治理转型战略。从近年来一系列政府创新中可以明显看到政府推动社会自治的意愿。比如在2011年“社会管理创新”主题提出后,面对原有的行政主导体制治理困境,地方创新中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参与逐渐增强[28]。在社区方面,不同地域和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与过去政府不断介入社区事务的乡镇基层政府行为逻辑不同,市县级政府近年创新的路径是对政府和社区职能重新进行界定和梳理,以为社区腾出一定的自治空间,这以江苏太仓的政社互动创新为代表。对于社会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官办的社会组织开始越来越希望通过增加独立性,而不是强化官办色彩来获得合法性。政府顺势而为,2013年,发改委、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负责完成《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对党政干部在社会组织兼职(任职)做出严格规定,计划在2014年试点工作基础上,到2015年年底前真正脱钩。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近年也开始大量涌现,尤其是公民兴趣爱好、环境保护、社区公益慈善等领域的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可见,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在成长过程中对政府的依附性始终存在。而另一方面,近年来社会领域确实呈现出更强的自主性,无论是从新兴社会组织的出现,还是官办社会组织的转型,或是社区的发展,都可以找到很多实践证据,而政府的政策也由以怀疑和限制为主开始转为鼓励和激发社会活力。
总体而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社会自治的互动发展是在一个制度空间和历史变迁的环境中进行的。中央政府的战略规划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形塑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制度框架;地方政府则在中央政府的战略框架、地方政府自身的自主性以及压力型考核激励的多重环境下,选择与社会领域各主体互动的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了社会发展的具体运行环境;而社会自治的发展则在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监管和引导下不断寻找可能的策略路径。各主体在互动中相互影响,不断推动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演进。
三、 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机制构建: 赋权、吸纳与嵌入的平衡之道
综上所述,中国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关系是在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自治各主体的互动中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而非对抗是基本的发展趋势,但这种趋势并不意味着合作可以自然而然形成,而是越来越依赖思想观念的变革、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微观机制的跟进。如前所述,目前的政社结构呈现的是中央的政社双重策略选择、地方政府的选择性合作和社会依附性自治的特征,这种结构是不平衡的结构,依然存在大量的制度空白,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因此,需要从各主体在互动中的角色和激励结构两方面来分析构建面向未来的互动合作机制的可能路径。未来的政策选择应该寻求能够消解这种不平衡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核心在于寻求赋权、嵌入与自治的平衡之道:通过政府向社会赋权,来激发社会自主性的成长,从而重新平衡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吸纳社会多元力量,使政府与社会的互动走上更加制度化的轨道;通过探索政府对社会的合理嵌入机制,使社会从依附性自治走向有嵌入的自治。通过这些策略的选择,来推动政府与社会关系朝着良性互动的方向演进。
(一) 赋权: 重新平衡地方—社会的关系
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前提是社会本身需要成长。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自主治理正在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但对一个能与政府有效互动的独立主体而言,社会主体的成长还只是刚刚开始。社会自主性的发展首先要解决基本的制度体系问题,这种制度体系需要中央的统筹改革考虑,以赋予社会发展更大的自主空间,因为只有社会自主性成长以后,才可能在地方政府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中重新平衡双方力量,社会不会因此被地方政府过分侵蚀,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平等合作和良性互动才有可能。这种良性互动无论对社会发展的活力而言,还是对作为监督地方政府有效运行的手段而言,都是必要的,一个弱小的社会不可能成为政府治理体系的伙伴。为了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赋权意味着政府需要重新梳理与社会各主体的关系,赋予社区和社会组织更大的自主空间,从而使社会形成自我调节的机制,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未来政府赋权过程需要一系列的机制建设和统筹改革创新,包括为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系列机制,深化社会体制的综合改革,以及在村委会组织法和居委会组织法基础上对基层政府职能与社区自治职能进行可操作化界定等。全国人大、民政部正着手修订关于社区组织法、社会组织的各项条例,社会自主性有望在统筹的制度改革框架下逐渐生长。
社会自主性成长有赖于两个方面:首先,需要在社会互动中推进社会共识性价值观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进程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政府社会政策的滞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传统的基于家族和宗族的社会组织化体系的瓦解等诸多原因,使得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出现断裂。如何重建社会信任与社会共识,除了依靠政府之外,更多地需要依赖社会自身的机制来逐步消解相关问题。通过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沟通,重建社会的基本共识,形成社会的基本认同和公共意识。其次,社会自主性成长有赖于多元化互动网络的形成。尽管传统社会也有“社会”的领域和空间,但与现代社会仍存在诸多差异,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在传统社会组织化形态瓦解之后,形成一个适应现代社会的组织化网络。在传统社会,社会组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是差序格局,费孝通指出,这种差序格局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是不一样的,因为差序格局是以己为中心的与别人相联系而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而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中,社会成员是立在一个平面上的[29]27。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家族和宗族制度随着人口流动和家庭小型化而逐步解体,社会结构需要从传统的依赖家族组织的差序格局向市场经济下的基于平等和契约的人际互动网络转变。工业化和全球化下的社会风险在加剧,社会的组织化越来越需要强调平等和多元互动的网络合作。因此,中国未来社会领域成长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政府的纵向网络发达的环境下,生长出社会领域发达的横向网络,以应对多元社会的挑战。当社会的自主性增强后,社会才可能成为政府政策执行的有效伙伴,成为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的积极力量,从而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治理。
(二) 吸纳: 从选择性合作到构建制度化连接机制
政社良性互动不但需要社会自主性的进一步增强,还需要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更多的系统化连接机制。这些机制不但是政府与社会有效互动的载体,也是避免政府与社会之间冲突的缓冲器。中国当前社会治理的结构性特征在于政府纵向制度与社会横向机制之间存在结构性断裂[30],因此如何构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连接机制是双方能否实现良性互动的关键。随着以单位制和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逐步向社区自治和社会组织发展方向迈进,政府需要重新构建与社会的互动和沟通机制。这种沟通机制除了中央的统筹外,更有赖于地方各级政府在与社会互动中的各种沟通性、互动性的制度创新。这一过程以吸纳各种社会参与为主要特征,因此可以称之为吸纳的过程。吸纳一词源于金耀基对我国香港地区发展的研究。金耀基认为,香港政治发展是“行政吸纳政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此一过程,赋予了统治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一个松弛的但整合的政治社会得以建立起来”[31]27。金耀基关于吸纳的阐述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未来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因为不只是香港地区,任何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都存在吸纳的问题。随着社会本身不断分化,如何吸纳不断变化的社会各种利益诉求,是政府与社会互动发展中的基本问题。这种吸纳是政府面对不同利益诉求的一种整合机制,在法律的框架下,将不同利益诉求吸纳进政府决策中需要如前所述的一种制度化的连接机制,通过这种连接机制,社会能被有效整合到政府体系和政府决策中,促进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共治。
这种沟通机制的建构首先需要政府的自觉,即政府应当成为这种连接机制建设的积极推动者,政府需要认识到只有这种连接机制的发展,才能在社会发育不充分的条件下为社会腾出更大的发展空间,避免政府对社会的侵蚀。其次,连接机制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调适过程,需要随着社会发展和结构变革而不断调整机制,这对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尤其重要,因为社会结构的变革和政府职能的调整意味着过去任何一种机制都无法涵盖政府与社会连接的所有可能。比如,对于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的发展,政府需要重新调整与基层社会的互动方式,而社会组织的兴起也需要政府探索与社会组织互动的方式和机制。在政府与社会连接机制的宏观制度性建构方面,目前最主流的解释是法团主义的结构,即社会力量被有序和制度化整合到政府体系中。但这种解释与其说是中国的现实,还不如说是学界对政社互动的良好愿景,因为社会的组织化力量在不断变化,目前政府无法实现对社会各种力量的整合,很多社会组织甚至还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因此,实现政府对不同社会力量的整合,需要政府统筹推进政府与社会之间各种连接机制的创新,以实现双方的多元无缝隙的互动。最后,政府与社会的连接机制是一个多元的协同体系。基层社区自治和社会组织的发展瓦解了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渗入基层社会的方式,近年来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确实形成了更为多元的互动沟通形式,这包括基层政党组织体系的建设,使政党和党员成为政府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基层官员成为基层社会互动的纽带;政府通过诸如购买服务、召开决策论证会等方式吸纳社会组织的参与等。而随着政府加强对基层的公共服务建设,政府与社会之间在公共服务领域变得更加紧密,政府与社会成员的互动更为频繁。不过,多元连接机制的出现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即如何实现不同沟通机制之间的有效衔接,从而使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成为一个协同共治的整体,这方面目前在基层治理中确实存在诸多挑战,未来需要进一步探讨不同机制在政社互动中的有效性,从而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开放的互动网络中实现合作治理。
(三) 嵌入: 从依附性自治走向有嵌入的自治
如果说吸纳关注的是社会整合到政府的路径,那么嵌入则关注政府介入社会的路径。嵌入可以简单理解为国家介入社会的过程,它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法律制度、管理组织对社会生活的介入;第二个层面是代表国家的基层官员与社会的多元互动[32]。由于实践中的政府嵌入与社会自治是不平衡的,政府嵌入社会的机制处于强势地位,而社会自治依然呈现出依附性从属性特征,因此,目前政社关系的优化不是在一个拥有良好自治传统的社会中来推进,而是在一个政府嵌入角色明显、自治资源相对不足的社会中进行探索。因而社会自主性的强化不可能是自生的,必须在政府的嵌入结构中展开。这种结构的自主性生长应该从一种依附性自治的状态,走向有嵌入的自治。这就需要探索一种依赖政府嵌入力量来推动的社会自治变革的方式,也即需要一种政府主导的,并且是可以推动社会自治的政府嵌入方式,来培育社会的自主性。嵌入的策略包括制度性嵌入和操作性嵌入。在制度性嵌入方面,主要依赖地方政府来实现法律和政府政策与基层自治制度之间的有效衔接,实现相关法律和政策对基层自治的嵌入。比如在村委会和居委会组织法中,都明确了基层政府要指导村委会和居委会开展工作。在日常的相关基层自治的制度制定中,也需要基层政府和基层官员的参与。操作性嵌入是指基层官员需要在日常事务中寻求与基层社会实现网络化的互动,从而保证基层自治能够在相关法律政策框架内健康发展。目前所推动的党员进社区、干部进社区等相关创新,可以认为是政府在操作层面寻求嵌入社会的方式。当政府官员在基层社会中不断地与社会成员互动合作时,便实现了政府对社会的嵌入,形成政府与社会有效的互动。
因此,在与社会的互动中,政府需要把握自身权力运行、社会自主性和双方互动机制的协调运行,过于强调赋权,则社会发展会失序;过于强调吸纳,则政府发展会失去自主性;过于强调嵌入,则社会发展没有自主性空间。反之,没有赋权就没有社会的发展;不吸纳新的社会力量则无法实现政治的整合;没有嵌入则会使政府与社会相互分离。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发展过程应该是赋权、吸纳和嵌入的平衡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是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与社会自治之间不断互动合作的过程。
[1]J.Coleman,FoundationsofSocial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J.S.Migdal, A.Kohli & V.Shue,StatePowerandSocialForces:DominationandTransformationintheThird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3]敬乂嘉: 《合作治理:再造公共服务的逻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Jing Yijia,CollaborativeGovernance:ReinventingtheLogicofPublicServices,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4]邓正来、景跃进: 《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见邓正来: 《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Deng Zhenglai & Jing Yuejin,″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 Society,″ in Deng Zhenglai,EssaysonTheoreticalStudiesofCivilSociety,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2002, pp.1-26.]
[5]M.Manion,″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 Vol.90, No.4(1996), pp.736-748.
[6]X.Wang,″Mutual Empowerment of State and Peasantry: Grassroots Democracy in Rural China,″WorldDevelopment, Vol.25, No.9(1997), pp.1431-1442.
[7]H.B.Chamberlain,″On the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ModernChina, Vol.19, No.2(1993), pp.199-215.
[8]李强: 《后全能体制下现代国家的构建》,《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第77-80页。[Li Qiang,″Modern State Building under Post- All- Round- System,″StrategyandManagement, No.6(2001), pp.77-80.]
[9]
[美]李侃如: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K.Lieberthal,GoverningChina:FromRevolutionthroughReform, trans. by Hu Guocheng & Zhao Me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0.]
[10]J.W.Seifert & J.Chung,″Using E-Government to Reinforce Government-Citizen Relationships: Comparing Government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ocialScienceComputerReview, Vol.27, No.1(2008), pp.3-23.
[11]钱颖一、许成钢、董彦彬: 《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M型的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3年第1期,第29-40页。[Qian Yingyi, Xu Chenggang & Dong Yanbin,″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 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ComparativeEconomic&SocialSystems, No.1(1993), pp.29-40.]
[12]周黎安: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Zhou Li’an,LocalGovernmentinTransition:Officials’IncentiveandGovernance, Shanghai: Truth & Wisdom Press;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13]J.C.Oi,RuralChinaTakesoff:InstitutionalFoundationsofEconomicReform,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4]A.J.Spires,″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Vol.117, No.1(2011), pp.1-45.
[15]J.C.Teets,″Reforming Service Delivery in China: The Emergence of a Social Innovation Model,″JournalofChinesePoliticalScience, Vol.17, No.1(2012), pp.15-32.
[16]汪锦军、张长东: 《纵向横向网络中的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机制——基于行业协会行为策略的多案例比较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4年第5期,第88-106页。[Wang Jinjun & Zhang Changdong,″The Interactional Mechanisms between NGO and Government in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Networks: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Trade Associations Strategies,″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 No.5(2014), pp.88-106.]
[17]何增科: 《国家和社会的协同治理——以地方政府创新为视角》,《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5期,第109-116页。[He Zengke,″Cooperative Governance of State and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on,″ComparativeEconomic&SocialSystems, No.5(2013), pp.109-116.]
[18]G.White,″Prospects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aoshan City,″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 No.29(1993), pp.63-87.
[19]R.Madsen,″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 A Research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ModernChina, Vol.19, No.2(1993), pp.183-198.[20]V.Nee,″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Vol.101, No.4(1996), pp.908-949.
[21]B.He,TheDemocraticImplicationsofCivilSocietyinChina,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22]B.M.Frolic,State-LedCivilSociety, New York: M.E.Sharpe, Inc., 1997.
[23] 汪锦军: 《从行政侵蚀到吸纳增效: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政府角色》,《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第162-168页。[Wang Jinjun,″From Administrative Erosion to Absorbing Efficiency: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Innovation of Rural Social Management,″MarxismandReality, No.5(2011), pp.162-168.]
[24]郭小聪、文明超: 《合作中的竞争: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新型关系》,《公共管理学报》2004年第1期,第57-63页。[Guo Xiaocong & Wen Mingchao,″Competition in Cooperation: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PO and Government in China,″JournalofPublicManagment, No.1(2004), pp.57-63.]
[25]邓国胜: 《非营利组织评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Deng Guosheng,Non-profitOrganizationEvaluatio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1.]
[26]汪锦军: 《浙江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机制:资源依赖理论的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第31-37页。[Wang Jinjun,″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on the NPO and Government in Zhejiang: An Analysis Based on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ZhejiangSocialSciences, No.9(2008), pp.31-37.]
[27]康晓光、韩恒: 《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第73-89页。[Kang Xiaoguang & Han Heng,″The System of Difference Controls: A Study of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in Contemporary China,″SociologicalStudies, No.6(2005), pp.73-89.]
[28]张小劲、于晓虹: 《中国基层治理创新:宏观框架的考察与比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72-79页。 [Zhang Xiaojin & Yu Xiaohong,″Innov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China: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ison in Macro Framework,″JournalofJiangsuAdministrationInstitute, No.5(2012), pp.72-79.]
[29]费孝通: 《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Fei Xiaotong,FromtheSoil:TheFoundationsofChineseSociet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30]李友梅: 《中国社会管理新格局下遭遇的问题——一种基于中观机制分析的视角》, 《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第13-20页。[Li Youmei,″Problem Encountered in the New Pattern of Social Management of China: In the Perspective of Meso Level Mechanism Analysis,″AcademicMonthly, No.7(2012), pp.13-20.]
[31]金耀基: 《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中国政治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45页。 [A.Yeo-chi King,″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 Political Model of Hong Kong,″ inChinesePoliticsandCulture, Hong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1-45.]
[32]汪锦军: 《嵌入与自治——社会治理中的政社关系再平衡》,《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2期,第70-76页。[Wang Jinjun,″Embedding and Autonomy: Re-balanc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al Governance,″ChinesePublicAdministration, No.2(2016), pp.7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