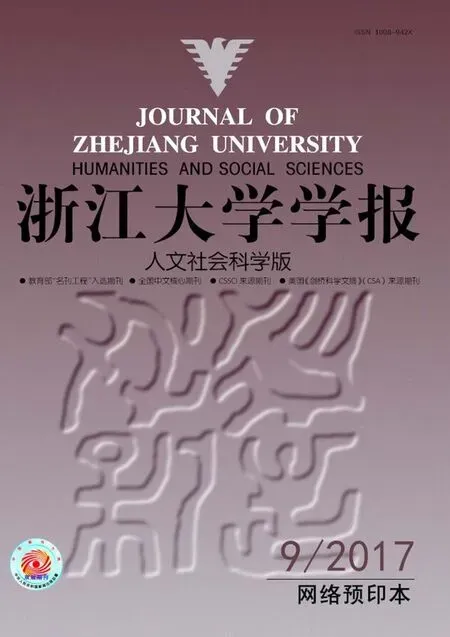弗里茨·诺依曼和德国民主法治国的构想
李哲罕 张国清
(1.北京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871; 2.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07;3.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一、 引 言
1933年希特勒上台,魏玛共和国崩溃。在魏玛德国公法学四大家中,汉斯·凯尔森和赫尔曼·黑勒流亡国外,鲁道夫·斯门德避居哥廷根大学改而研究相对冷门的教会法,唯有卡尔·施米特受宠于一时,但在1936年之后也被纳粹政权所冷落。不过,德国公法学界并未中断对法治国问题的思索。一些流亡海外的德国学者结合民主世界的生活经验,考察各种民主理论,反思纳粹德国之所以产生的智识背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民主法治国的建构做好了思想准备。德国犹太裔学者弗里茨·利奥波德·诺依曼(Franz Leopold Neumann)正是这样一位法律和政治思想家。
诺依曼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外围成员,虽未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担任过正式研究岗位,学术影响力也远不如他前后辈的法哲学家施米特、黑勒和哈贝马斯,但他对法治国的思考构成了现代德国法律和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篇章。诺依曼的政治立场和个人经历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成员多有重叠,不过其主要工作并不在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首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框架之内。诺依曼是在韦伯、施米特、黑勒和哈贝马斯关于德国法治国的法哲学路线上,也即在德国公法学、马克思主义和民主法治国论域内,开展他的工作。国外学界讨论德国纳粹问题和二战后德国法治国建设时,诺依曼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除本文所涉及的文献之外,尚有W.E.Scheuerman, Between the Norm and the Exception: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Rule of Law, 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 1994; M.Stolleis, A History of Public Law in Germany: 1914-1945, trans. by T.Dula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M.R. Stirk, Twentieth-century German Political Though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等等。。相比之下,国内研究尚未很好地认识到诺依曼思想的重要性。
有鉴于此,笔者将通过考察诺依曼对以下三个递进性问题的一系列回应来揭示其学术工作的价值:(1)魏玛共和国为什么会失败?(2)纳粹政权的本质是什么?(3)二战之后如何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诺依曼在其不同人生阶段中依次回答了这些问题,描绘了一幅德国二战后重建的法治理想国蓝图,迈出了德国民主法治国的关键一步。
二、 魏玛共和国失败原因的考察
诺依曼生于1900年,早年就读于布雷斯劳、莱比锡、罗斯托克和法兰克福等大学。1918年,他加入社会民主党,同列奥·洛文塔尔和恩斯特·弗兰克尔一起创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学生团体。1923年,他在刑法学家和法哲学家马克斯·迈耶尔指导下以研究国家和刑罚关系的论文获得第一个博士学位,随后担任曾参与制定《魏玛宪法》的法学家、社会民主党人洪果·辛茨海默的助手。1926—1932年,他任教于法兰克福“劳动学院”。1929—1933年,他任教于柏林“德国政治学院”,并担任过社会民主党劳工事务方面的律师。他在魏玛共和国后期经常参加施米特和黑勒的讨论班。
从其早期经历可知,作为一位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德国犹太裔公法学家和政治学家,诺依曼受到以施米特和黑勒等为代表的反实证主义法学思潮的影响,也受到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有马克斯·阿德勒和卡尔·伦纳等)的影响,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左派的社会民主党,拒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由主义议会民主制和实证主义法治国。德国公法学和马克思主义也持这种拒斥态度,两者都反对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方案*关于施米特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可以参见C.Thornhill,″Carl Schmitt and Early Western Marxism,″ in A.Schrift (ed.), History of Continental Philosophy, Vol.Ⅵ: Poli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p.19-45。。诺依曼在1932年给施米特的信中写道:“如果一个人接受在德国最为根本的政治分歧是经济冲突,在德国决定性的敌友群体划分是劳资划分,那么在这样的政治冲突环境下,显然不再有可能通过议会来进行统治了。”*F.Neumann, ″Letter to Carl Schmitt,″ 7 September 1932,转引自D.Kelly, The State of the Political: Conceptions of Politics and the State in the Thought of Max Weber, Carl Schmitt and Franz Neuman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58。在诺依曼的著述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般交错着以施米特为代表的德国公法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和用语,但他同时也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和调和。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经历对诺依曼来说弥足珍贵。他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在德国这个时期开始于魏玛共和国——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已经开始有一个决定性的转变。”[1]47魏玛共和国从产生之际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所采用的战时经济体系使垄断资本势力得到极大发展,而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正是通过与垄断资本势力以及军方达成私下协定才得以维持自身的统治。在诺依曼看来,早期资本主义的经济方式(自由竞争)、政治组织方式(议会民主制)和法律形式(实证法)等方面在历史上虽有进步意义,但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这种情况却已发生根本变化。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方面必然会导致(或不能阻止)经济领域垄断资本势力的形成,垄断资本势力进而通过议会民主制和实证法等建制实现对国家的控制,从而削弱了正义与自由。正如英国学者桑希尔所言:“像马克思一样,诺依曼认为,自由主义民主制所保证的形式平等,只是促进资本支配地位的合理手段。”[2]93诸如在对待政治—法律这个问题上,诺依曼认为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所预设的抽象、普遍的政治—法律制度不足以解决社会问题,这套政治—法律制度最终导致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资本势力将影响政治—法律制度,并使自身优势地位通过政治—法律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也正如桑希尔在另一处文献中所指出的:“所有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关联的理论家,他们都论证了,自由主义为法西斯主义的最终形成提供了经济与认识前提。而且所有理论家都认为,自由主义所提倡的法律结构、法律观念与法律理性的原则都支持了法西斯主义的发展。”[3]482其实,不论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论断,还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反实证主义法学的公法学家们(施米特、黑勒和斯门德等)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法律层面上都存在着问题,诺依曼与这些传统都保持着高度一致。
更进一步地说,这需要联系诺依曼对自德意志第二帝国以来占据支配地位的实证主义法治国观念的分析和批判。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私法领域反对概念法学的“自由法运动”(Freirechtsbewegun),直至魏玛共和国时期施米特、黑勒和斯门德等反对凯尔森的“纯粹法学派”,对实证主义法治国观念的批判是德国法治国观念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诺依曼的民主法治国思想其实非常接近于黑勒因英年早逝而未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法治国思想。这种接近不仅是由于两人理论背景和出发点的相似性,更是因为诺依曼曾求学于黑勒。关于黑勒的相关思想可以参见李哲罕《需要“实质性内容”的公法学——赫尔曼·黑勒公法学思想论析》,载《浙江学刊》2016年第2期,第176-181页。。实证主义法治国的弊端在于忽视法治国的政治维度(正当性)而过分追求法律维度(合法性)。诺依曼表示:“在德国(实证主义)法治国中,权利不是通过公民在普遍意志中形成的参与,而是通过构建一个最高程度可计算性的、精心制作的法律系统而被保护的。”[4]89后来的历史表明,这套构建精致的实证主义法治国并不能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诺依曼指出了问题所在:“在拉班德的影响下,德国法律理论已经放弃了法律的普遍性(generality)这个概念,而替代性地建立起形式和实质法律之分。”[1]50诺依曼进而指出,在进一步的法律实证化的进程中,“(德国的)自由主义将法治排他性地认为是依靠实证法,而非习惯或自然法进行治理”[1]33。德国实证主义法治国(Rechtsstaat)观念和英国法治(Rule of Law)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分歧。他将自第二帝国以来德国公法学传统的实证化归因于下面的现象:“德国的资产阶级安于他们和国家的关系之中。德国的法官和法学家们不再需要诉诸自然法体系以反对敌视它的实证法体系。因此,自然法和法哲学两者都消失了。实证主义不仅在法律适用方面(在这个方面它曾有其进步意义)也在与之有关的法律理论方面获得了胜利。这也就相当于废除了所有的法律理论和不加批判地接受懒散的相对主义。”[1]45-46在诺依曼看来,实证主义法治国观念实则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政治妥协的产物,同现代法治要求的真正有效地限制权力与保障权利相去甚远。诺依曼的任务是在与实证主义法治国相对的地方重建德国国家理论。这正是施米特、黑勒和斯门德等重要的德国公法学家想要实现却没有实现的目标。
诺依曼曾在发表于1937年的一篇论文中对德语“Recht”一词包含的“客观法律”和“主体权利”这两个意思进行过区分,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司法术语表达了‘客观法律’和‘主体权利’两个概念事实上的差别(在德国,这两个含义都可以被Recht这个术语涵盖)。‘客观法律’指法律是被主权所创设的,或至少是可以归之于主权的;‘主体权利’指个体法律主体的主张。前者否定了个体的自治;而后者则预设和肯定了它。”[1]23实证主义法治国割裂了两者的联系,结果只能是作为手段的客观法律的充分发展和作为目的的主体权利的相对缺失。“主体权利”必然涉及自然法理论,诺依曼在考察历史上各种自然法理论后指出:“(自然法)或许没有多少(内容)。但这些没有多少(的内容)正是站在威权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对立面的。”[4]91诺依曼因此提出了实证主义法治国要取消与自然法相联系的“普遍法”主张,并指出相关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普遍法是法律的根本形式,以及如果法律不仅是意志,也是理性,那么一个人必须声明威权国家的法律不具备法律属性。法律作为与主权的政治命令不同的现象,只有当它表明自身为普遍法的时候才是可能的。在无法把对权力的约束作为原则的社会中,法的完全普遍性是不可能的。”[1]66
这需要联系诺依曼对《魏玛宪法》进行社会主义化重新解释的主张。诺依曼认同辛茨海默的观点,旧的古典自由主义权利和新的社会主义权利在《魏玛宪法》中以一种毫不相关的方式并置在一起,导致其中混杂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成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发挥社会主义成分来克服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问题,其实质是通过社会主义的普遍性法律克服资本主义的阶级性法律。诺依曼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宪法法律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魏玛宪法第二部分中积极的社会方面,并以确定的形式提出它们……社会主义法学的中心任务就是……对基本权利进行社会主义解释,以防止它们在资产阶级宪法理论中复活。社会主义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在实践中实现这些基本权利。”*F.Neumann,″Die Soziale Bedeutung der Grundrechte in der Weimarer Verfassung,″ 转引自[德]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孟登迎、赵文、刘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5页。那么,如何实现《魏玛宪法》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呢?英国学者凯利分析道:“诺依曼的中心主张是《魏玛宪法》中的民主成分只有通过一个强力的、主权性的国家的介入方可得到支持和提升。”[5]272诺依曼不仅在对自由主义议会民主制的批判上与以施米特为代表的德国公法学的观点保持了高度一致,而且深受其影响。施米特认为,自由主义议会民主制因为代表社会中的多元势力,只能在它们之间寻求妥协,而不能产生决断。所以,施米特寻求一个主权者的出现。他可以超越社会多元势力的分立而做出决断。诺依曼在此迥异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提出需要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强力的、主权性的国家作为主权者。只有这个凌驾于社会多元势力之上的主权者,才可以通过“普遍法”实现正义与自由。
魏玛共和国的失败正是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致,只可惜现实中解决魏玛共和国矛盾的方式是通过纳粹,而非诺依曼所预想的一个与垄断资本势力相对立的、凌驾于社会多元势力之上并运用政治权力和法律以实现正义与自由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强力的、主权性的国家。不过,对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性质国家的设想是他后来克服德国实证主义法治国的民主法治国思想的萌芽。
此外,诺依曼对魏玛崩溃问题的“一个德国”的整全性看法与以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为首的保守派知识分子以“权力”和“文化”区分的“两个德国”的观点相对,影响了以哥伦比亚大学为据点的德国研究者伦纳德·克吕格和弗里茨·斯特恩等人的基本观点。不过与他们倾向于关注德国政治文化不同,诺依曼更侧重于关注德国经济、政治、法律等建制层面的问题。
三、 纳粹政权本质的揭示
纳粹上台后,诺依曼开始了自己漫长的流亡生涯。1936年,他在伦敦政经学院两位左派学者哈罗德·拉斯基和卡尔·曼海姆的指导下,非常有现实针对性地从事了对法治问题的比较研究,并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他随后在拉斯基的推荐下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管理研究所临时安置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图书馆。诺依曼后来移居美国,凭借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提供的临时工作和一些大学临时教职养家糊口。他在1942年发表巨著《比蒙德:民族社会主义的结构和实践,1933—1944》,分析了纳粹政权的本质。这是英美世界乃至全世界最早以纳粹政权为对象的研究成果。诺依曼从政治、法律和经济的多重视角揭示纳粹政权本质,有别于同时期的其他许多单学科进路的研究。这本书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也改变了他的困难处境。
诺依曼在该书中否定纳粹政权是一个国家。他写道:“如果国家将法治作为其属性,我们对这个问题(纳粹政治系统是一个国家吗?)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我们否认在纳粹德国还有这样的法存在。”[6]467桑希尔对此评论道:“(对于诺依曼而言)自由主义社会中具有法律形式的国家包含了一些理想的、规范的因素,这些因素不能还原为纯粹工具性的或压迫性的策略,国家的这些因素只能为纳粹的统治所取消。”[3]481这与诺依曼在第二部博士论文结尾的见解遥相呼应:“在纳粹德国不存在法律,因为法律现在是将领袖的政治意志转化为宪政实在的一项排他性技术。法律不外是一个秘密统治(的手段)。”[7]298在诺依曼对法和国家的对勘式定义下,纳粹政权不是一个国家。他用和霍布斯比喻为国家的“利维坦”相对应的另一个上古巨兽“比蒙德”(Behemoth)来类比纳粹政权。当然,诺依曼也是为了与施米特1938年出版的《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一书相对应而有意为之。诺依曼在书中多处流露出对施米特的批评,不过他在本书导言中对魏玛共和国的失败进行批评时又不得不经常在马克思主义术语之外,借用以施米特为代表的德国公法学词汇。
依据诺依曼第二部博士论文对国家下的定义,“国家是只有主权的存在。主权国家独立地存在于社会中不同的斗争集团之外”[7]3,纳粹政权不能称为国家。诺依曼指出:“在纳粹系统下的卡采儿组织,已经不再是私有市场的组织,它们已经成为在国家政策下运行的行政机构了。”[8]274正是因为纳粹政权代表社会中特定的利益集团上升而成的主权的所有者,而不是代表独立地存在于(凌驾于)社会中不同斗争集团之外的主权者,所以纳粹政权所做出的决断绝非根本性的、政治的——也即主权的——决断。换言之,纳粹政权不是一个国家。
诺依曼以法和主权对国家所下的双重定义实则并不矛盾,因为这正是施米特和黑勒等在诺依曼之前的德国公法学家们围绕合法性与正当性这对矛盾掀起的反实证主义法学浪潮的核心观点,即一个国家必定要展现为法治(合法性)和主权(正当性)的统一,但纳粹政权无疑在这两方面都是成问题的。依照诺依曼对国家的这个双重定义,我们可以发现纳粹政权在法律方面(以政治意志取代实证法)和政治方面(特定利益集团窃占主权)的双重意义上都不符合国家定义。
诺依曼认为,纳粹政权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但如果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不是一个国家,那么它是什么?我斗胆认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统治集团直接控制了剩余人员,而且并不存在迄今为止所知的以国家理性而强制的组织为中介的社会形式。这种新的社会形式并未被完全地认识到,但这种趋向存在于对这个政权本质的界定中。”[6]470但诺依曼对纳粹政权本质的分析并未满足于此。通过他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波洛克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这个概念的批评,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诺依曼对纳粹政权本质的探询。正如桑希尔所指出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们,特别是波洛克)得出结论说,民族社会主义可以最准确地归为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在希特勒的统治下,自由资本主义的私有主义特征从经济中消除了,私人经济的自主经济集团为国家所支持的经济协同体所取代,国家开始把最初私有化的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分配过程置于直接的政治控制之下。”[3]478但诺依曼并不同意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他指出,“‘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是一个词项上的矛盾”[6]224。因为这个术语并非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的,一旦国家成为生产工具的唯一所有者,“那么这样的国家就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它或许可以被称作一个奴隶国家或一个经理独裁制度或一个官僚集体主义系统。它只能被政治的而非经济的范畴所描绘”[6]224。在诺依曼看来,即使“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成立,“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纳粹”[6]226,纳粹应该被称为“极权垄断资本主义”(Totalitarian Monopoly Capitalism)[6]261。诺依曼认为,在纳粹德国,垄断资本势力成功地控制了政权,以指令形式代替了市场行为,取消了原先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些较为理性和自由的部分,法律则彻底沦为专断的个人意志外化而来的命令,它们只是还具备着法律的外在形式。最为重要的是,纳粹德国依旧保持着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纳粹政权控制了政权的垄断资本势力,和凌驾于社会多元势力之上的国家不同,它本身就是参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逐利者之一。
简言之,在诺依曼看来,纳粹政权的本质是垄断资本势力控制了国家,而非国家控制了垄断资本势力。纳粹政权代表的是垄断资本势力,在上台后只能是通过政治权力(只是垄断资本势力而非普遍意志,即不正当的政治权力)和法律(只是具有法律形式的、某些专断的个人意志外化而来的命令,即不合法的法律)进一步巩固垄断资本势力的优势地位。然而,诺依曼所期望的国家,是与垄断资本势力相对立的、凌驾于各种社会势力之上、运用政治权力和法律以实现正义与自由的、强力的、主权性的国家。
四、 德国民主法治国的构想
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局面,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的混乱情形重演是美国政府当时的工作重点。诺依曼在英美等西方民主国家十多年的生活经验,加上他对许多民主政体和民主理论的比较性研究,使他在后期收敛了原先相对左倾的思想,并成为一位坚定而又保持批判态度的民主制度的支持者。他开始将自己早期持有的社会主义性质国家的观点凝聚到“民主法治国”这个观念上。1942-1948年,他效力于美国政府情报部门OSS(战略事务局,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并成为对纳粹德国进行分析和宣传的中欧部门负责人。他在二战后积极投身德国政治生活的重建,并在1948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席位,1950年获得正式教授席位,却不幸于1954年意外因车祸离世,未能赴任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诺依曼后期工作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重建德国民主法治国。根据近年来美国政府解密的文献,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他在这个时期的工作。依照诺依曼的分析,在二战结束后,如果苏联进入德国本土,那结果将会得到一个结合民族独立与革命(推翻旧统治集团)两者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政权。这不是诺依曼希望的,“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群体将不能构成德国未来民主政府的基础。因为工人、中产阶级、军官团和纳粹领导层中的‘左翼’分化的利益正如它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不能统一起来一样,也不可能在纳粹倒台之后统一起来”[9]151。因此,在诺依曼看来,西方世界如果在二战后进入德国本土(出于西方世界的利益以及德国的前景,必须阻止苏联人进入德国本土),就必须要让德国人在战败之后彻底放弃民族主义的主张,而且不能启用或者留用原先那些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但同时又必须要满足德国人的革命主张,即推翻原先的统治集团*诺依曼认为,这并不仅限于纳粹政权高层,他非常马克思主义式地指出:“这些势力(支持德国侵略主义的势力)是由容克、工业和金融业、德国军官团和公务员的高层所组成的,他们构成了德国的统治阶级。”参见F.Neumann,″The Treatment of Germany,″ in F.Neumann, H.Marcuse & O.Kirchheimer, Secret Reports on NAZI Germany: The Frankfurt School Contribution to the War Effort, edited by R.Laudan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440。以及民主化地改造经济基础。诺依曼认为,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望在战败后的德国成功建立起一个有效运作的民主政权。
诺依曼表示:“(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两者不仅在功能上,而且在基因上(genetically)相互联结;即经济权力是政治权力的根基……因此没有‘纯粹的’经济权力,也没有‘纯粹的’政治活动。经济作为政治的手段正如政治作为经济的工具一般重要。”[10]12而“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源自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反动,而是出于压制民主运动的目的。因为民主运动希望使理性和民主具体化在经济之中。”[11]265在诺依曼看来,德国政治生活的重建必须建立在对原先由垄断资本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的彻底改造之上,但这并非像某些英国学者提出的摧毁德国原有经济基础、让它彻底沦为一个农业国家,而是要以民主和法治形式对经济进行支配,杜绝基于原先经济基础上的政治势力再次影响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法律。这正如他所说的:“民主的力量如果不在德国的社会结构中发生的剧烈变化,则将不能被充分释放。这个剧烈的变化将剥夺那些(统治)集团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经济基础。”[12]441
诺依曼被后世誉为“联邦德国政治学之父”,不仅因为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大学是在他的建议下依照美国式样建立起了政治学系,也因为他广泛参与对一般公民的政治教育。其实早在魏玛共和国后期,他就已经开始从事政治教育的实际工作了。有论者指出,诺依曼在这里所要面对的正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过的问题:“有能力提供适当政治定向(direction)的建制形式需要一个理性的和受过教育的公民群体的存在为前提条件。但悖论的是,这样的理性的和受过教育的公民只有在这样的建制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发展起来。”[5]13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的德国,如何使外来的民主(宪政)观念有效地结合自身的传统,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一个现代国家,这是摆在诺依曼及其同代人面前的重要问题。不过正如诺依曼所说的,可惜的是,“现在或过去都没有一个可以被用于在德国建立一个政府的合适的宪政模式。德国的宪政生活已然不成模样”[13]414。但值得庆幸的是,战后联邦德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同时也保存着适当的德国特性(诸如《基本法》中的社会民主倾向)以修正典型盎格鲁-撒克逊式民主的缺陷,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两方面同时得到良性互动的建设和发展,并成功地朝民主法治国的方向稳步发展。
在后期相对成熟的观点中,诺依曼将自己早期持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观逐渐凝聚到民主法治国观念上,继续发展早年持有的强国家主义以反对社会多元存在的立场,认为这是与英美资本主义的形式民主相对应的“真实民主”。在他所预设的民主法治国观念中,国家的正当性是基于政治成熟的公民在民主的政治建制下积极参与而形成的普遍意志,同时国家又凌驾于社会多元存在之上,通过“普遍法”这一理性而又强制的方式(合法性)赋予公民以正义与自由。联系他对法和国家的定义,便可以理解在自身对民主法治国的限定之下,他的观点会如此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一贯持有的对国家的不信任态度:“我不能同意国家一直是作为自由的敌人……国家有时也内在地或外在地捍卫自由。”[14]201
此外,因为受纳粹德国的经历影响,诺依曼对大众民主心存抵触,这也令人联想到施米特对“简单投票计数式民主”的敌视。诺依曼指出:“民主政治系统的本质不在于政治决断中大众的参与,而在于做出政治上负责任的决断。”[15]192这对应于上文的分析,即政治上负责任的决断需要政治成熟的公民积极参与所形成的普遍意志,而政治成熟的公民只有在民主政治建制下才有可能产生以至积极参与。诺依曼的论断所针对的是形式民主或非理性的大众民主,因此这与其所主张的“真实民主”并不矛盾。我们须联系从韦伯到施米特这条脉络——诺依曼深受其影响——对民主问题的一贯看法:民主并非仅仅是被统治者参与政治行为的方式,更是主权者使自己的主权行为正当化的方式。在这点上,诺依曼所提出的民主法治国观念也迥异于典型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制。
可以简要地说,诺依曼背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家消亡理论,也区别于传统自由主义所设想的作为“守夜人”的国家观念。但最为显著的是,诺依曼以“真实民主”克服了德国实证主义法治国的局限性,实现了德国法治国观念迈向民主法治国的关键一步。诺依曼所谓的“真实民主”和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还是有所差别的,主要在于他秉持德国公法学传统一直以来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性利益的不信任态度。可以说,他在批判德国实证主义法治国的同时,也对英美民主持一种有所保留的态度,而他提出的“真实民主”实则是为了超越地对待前述二者,为现代社会开出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
五、 诺依曼法哲学思想的价值
综上所述,诺依曼法哲学思想介于德国公法学、马克思主义和民主法治国之间。“反对施米特的施米特主义者”“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民主主义者”这三个标签可勾勒出诺依曼法哲学思想的轮廓,但不能充分揭示其蕴含的重要价值。如果说罗尔斯的学术贡献在于通过论证公平正义和自由民主社会的可能性,试图探索在当前充满冲突和纷争的国际条件之下建立一个普遍的自由民主社会的可能性,那么,诺依曼则试图从法理上解决二战之后德国自由民主国家的重建问题。我们得出以下几点作为本文的结论:
首先,虽然诺依曼1954年意外去世,不过美国政府在二战后依其建议在联邦德国全面实施“去纳粹化、民主化、去军事化和去卡采儿化”的所谓“4D政策”(Denazification, Democratization, Demilitarization and Decartelization),最终使联邦德国成功跻身西方民主国家之列。诺依曼之后的德国公法学界,特别是以哈贝马斯为首的新法兰克福学派,在学理上承继和发展了他的民主法治国观念。因此,诺依曼曾经在德国民主法治国重建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是其他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都做不到的。仅凭这一点,诺依曼就应当在现代德国法律和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其次,诺依曼所提出的民主法治国是对之前魏玛宪政危机时德国公法学种种争论意见的一个综合。它克服了魏玛共和国时代众多公法学家对实证主义法治国的“破而不立”,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众多批判中为数不多的建设性观点。诺依曼对民主法治国的思考和实践,帮助联邦德国不仅以民主法治国的形式重建了后纳粹时代的政治生活,同时也因其鲜明的德国特色而有别于甚至是超越了典型英美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诺依曼的这些思考和实践所针对的论域虽然从表象上而言只限于近现代德国,但其实质却是现代社会的普遍性问题,因此具有普遍价值,对后发展的现代国家尤其具有借鉴价值。
再次,依照后来哈贝马斯的看法,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首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低估了民主—法治国家的传统,而没有引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足够重视的诺依曼则正好克服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缺陷。诺依曼的法哲学思想和政治实践活动对哈贝马斯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哈贝马斯正是通过汲取以诺依曼为代表的德国公法学思想,才克服了在二战后依然萦绕在联邦德国学界与法律实务界的施米特主义的幽灵。诺依曼关于民主法治国的思想则在哈贝马斯后来关于民主法治国的更为精致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扬弃。
最后,以诺依曼为代表的德国学者们的相关思想也反诸作为战胜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并使其中的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和反思自身政治、法律和经济方面的诸多不足之处。大半个世纪以来,魏玛共和国和纳粹的案例总是成为西方理论家严肃对待和思考的对象,而他们在进行相关研究的时候,又总是不得不援引诺依曼。我们相信,诺依曼的法哲学思想除了具有现代法哲学方面的纯学术意义外,对当前中国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事业也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1]F.Neumann,″The Change in the Function of Law in Modern Society,″ in F.Neumann,TheDemocraticandtheAuthoritarianState:EssaysinPoliticalandLegalTheory, edited by H.Marcuse,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7, pp.22-68.
[2]C.Thornhill,PoliticalTheoryinModernGermany:An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2000.
[3]
[英]克里斯·桑希尔:《德国政治哲学:法的形而上学》,陈江进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C.Thornhill,GermanPoliticalPhilosophy:TheMetaphysicsofLaw, trans. by Chen Jiangjin,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4]F.Neumann,″Types of Natural Law,″ in F.Neumann,TheDemocraticandtheAuthoritarianState:EssaysinPoliticalandLegalTheory, edited by H.Marcuse, Chicago: The Free Press, 1957, pp.69-95.
[5]D.Kelly,TheStateofthePolitical:ConceptionsofPoliticsandtheStateintheThoughtofMaxWeber,CarlSchmittandFranzNeuman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6]F.Neumann,Behemoth:TheStructureandPracticeofNationalSocialism1933-1944, Chicago: Ivan R.Dee Publisher, 2009.
[7]F.Neumann,TheRuleofLaw:PoliticalTheoryandtheLegalSysteminModernSociety, London: Berg Publishers, 1986.
[8]F.Neumann,″German Cartels and Cartel-like Organizations,″ in F.Neumann, H.Marcuse & O.Kirchheimer,SecretReportsonNAZIGermany:TheFrankfurtSchoolContributiontotheWarEffort, edited by R.Laudan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264-284.
[9]F.Neumann,″The Free Germany Manifesto and the German People,″ in F.Neumann, H.Marcuse & O.Kirchheimer,SecretReportsonNAZIGermany:TheFrankfurtSchoolContributiontotheWarEffort, edited by R.Laudan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49-166.
[10]F.Neumann,″The Treatment of Germany,″ in F.Neumann, H.Marcuse & O.Kirchheimer,SecretReportsonNAZIGermany:TheFrankfurtSchoolContributiontotheWarEffort, edited by R.Laudan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436-447.
[11]F.Neumann,″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ower,″ in F.Neumann,TheDemocraticandtheAuthoritarianState:EssaysinPoliticalandLegalTheory, edited by H.Marcuse, Chicago: The Free Press, 1957, pp.3-21.
[12]F.Neumann,″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F.Neumann,TheDemocraticandtheAuthoritarianState:EssaysinPoliticalandLegalTheory, edited by H.Marcuse, Chicago: The Free Press, 1957, pp.257-269.
[13] F.Neumann,″The Revival of German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Life under Military Government,″ in F.Neumann, H.Marcuse & O.Kirchheimer,SecretReportsonNAZIGermany:TheFrankfurtSchoolContributiontotheWarEffort, edited by R.Laudan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412-435.[14] F.Neumann,″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Freedom,″ in F.Neumann,TheDemocraticandtheAuthoritarianState:EssaysinPoliticalandLegalTheory, edited by H.Marcuse, Chicago: The Free Press, 1957, pp.201-215.[15] F.Neumann,″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Freedom,″ in F.Neumann,TheDemocraticandtheAuthoritarianState:EssaysinPoliticalandLegalTheory, edited by H.Marcuse, Chicago: The Free Press, 1957, pp.16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