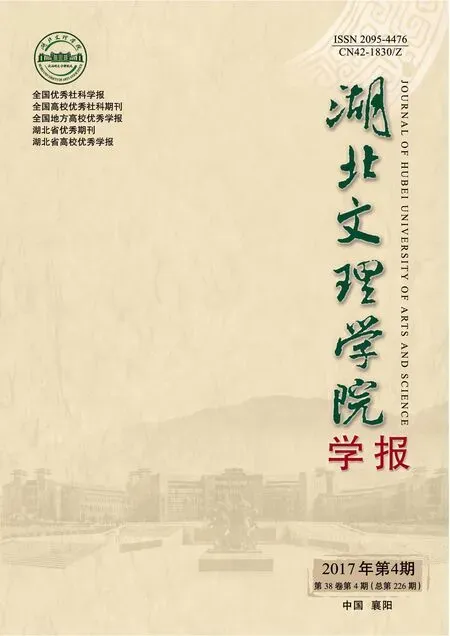戴之麟生平及其文学研究考述
朱佩弦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文学、语言学研究
戴之麟生平及其文学研究考述
朱佩弦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戴之麟是民国时期湖北钟祥极负盛名的文化名人,与赵鹏飞、关云门合称为“钟祥三怪”。他出生于业儒世家,虽因科举取消仅取“秀才”功名,却不懈学习,得以就读于襄阳道师范学堂,并参与中华编译社的国文函授学习,结识了林纾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桐城派”文学思想影响。戴之麟文学研究著述颇丰,撰有《填词法述》《千家诗志疑》《楚辞注解》等。其中《楚辞注解》曾寄呈毛主席,毛主席托郭沫若予以复函。还著有《楚辞补注疏》稿本12册计70余万字,填补了《楚辞补注》专书研究近800年的空白,在《楚辞补注》的研究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可以说,戴之麟在钟祥历史、湖北文化史乃至楚辞学史上都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
戴之麟;钟祥三怪;桐城派;《楚辞补注疏》
一、戴之麟的生平
(一)戴之麟生平简介
戴之麟,一名更生,字麒生,又字芝灵,号祺生。根据《楚辞补注疏》稿本卷首落款,他又自号旡三欠一生。生1880年①《钟祥县教育志(1905—1987)》(钟祥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1990年)称其生1880年,李传嗣《民国时期的“钟祥三怪”》一文(《湖北档案》,2003年Z1期)称其生1869年,根据戴之麟本人于《文学杂志》创刊号(苦海余生刘哲庐编辑,上海中华编译社发行,1919年1月)《与友人论文书》一文中“某伏处穷乡,垂四十年矣”的说法,当取前者。,殁1959年。戴之麟早年家贫,但聪慧好学,1905年在时任湖北学政的李家驹(后署理学部左侍郎)主考下,入县学为生员(即俗称的“秀才”)②戴之麟《世伯母戴孺人寿序》云:“乙巳孟夏,余与慕颜并受知于李柳溪侍郎,补博士弟子员。”见《文学讲义》第1期,中华编译社1918年再版,《函授成绩》第10页。按:慕颜实即戴之麟本人,详见下页注④。。因科举取消,故于1906年,入安襄郧荆道师范学堂(即襄阳道师范学堂),1907年卒业③戴之麟《世伯母戴孺人寿序》云:“乙巳孟夏,……明年,慕颜就学于山南东道。……又明年,慕颜在道校卒业。”见《文学讲义》第1期,中华编译社1918年再版,《函授成绩》第10页。,赴省城武汉多方求仕未果,遂归乡从教。曾历任县立多级、单级两模范小学堂堂长,1912年任县立乙种农业学校校长,1916年6月前后加入中华编译社国文函授部,1923年任私立中强中学校监。1931年以县堤防委员会主任委员身份从政,因堤防款项被侵吞挪占,旋愤然辞官。1935—1937年参与编修《钟祥县志》,1939年前后任县救济院院长。日占期间,在家开设私塾,传授国学课业,自此正式开始文学研究并进入高产期。1948年任京钟县立中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即校长),1950年工作于县文化馆,1953年任荆州博物馆馆员,1954—1959年任钟祥县第一、二、三届人民委员会委员,1959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第二届委员。
(二)戴之麟的家世及其交游
1.戴之麟的家世
戴之麟出生于书香世家。其先祖为闽中莆田陈氏,于清初迁至钟祥④何成章《陈科九先生轶事》云:“先生氏陈,庠名文运,科九其字也。原籍福建莆田,其先人于清初迁钟祥。”见湖北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湖北省博物馆整理:《湖北文征》,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卷234页。。曾祖陈文运,字科九,曾以弱冠补诸生。1937年版《钟祥县志》云陈文运“强记忆群经,朗朗成诵,于四子书注解,尤一字不遗。家贫,倚授徒为生,塾课悉口授,校改文字,命生徒侧立,口述口易之。性刚严,从游者皆敬惮焉。张云骞太守应翔,黄让卿方伯元善、张小园拔萃希庾,先后出其门,卒年八十二。所著《大学中庸释义》,皆授课时命诸生所笔记也。”祖陈绍章,以朴学教授乡里。①见林纾《戴秉彝墓表》。(民国)李权:《钟祥金石考》,《历代碑志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册679页。父陈世堃,字秉彝,以入赘戴家而袭戴姓,嗜星卜、天文诸学,于医术尤有心得,著有《医学笔记》,由戴之麟裒辑而成。世堃于光绪戊子年的全县大疫,救治、全活县民众多。近代大翻译家、文学家林纾曾表世堃之墓。戴之麟的外家戴氏,先祖为戴文润,湖州德清人,以兴王府良医落籍钟祥。戴文润生戴经,字伯常,号楚望,以世宗从龙功授锦衣卫千户,迁卫佥事,与文学家归有光往来频繁。戴氏后裔多落籍钟祥。可能正是因为戴氏先祖为兴王府医官,戴之麟的外祖父戴光裕才令戴秉彝学习医学。②《戴秉彝墓表》云:“族舅戴公光裕器之,故公遂壻于戴氏。舅无子,因袭其姓。命习岐黄术于张光荣先生家。”见(民国)李权:《钟祥金石考》,《历代碑志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册679页。也正是因为戴秉彝学习医术与堪舆学,未能继承先祖的儒学一脉,遂令之麟继承家学,学习传统国学课业。③《戴秉彝墓表》云:“公遇之麟极严,尝以课读扚其额,误中目,公抚之而泣曰:‘吾莫继先业而为儒,欲儒汝,督责过深,是吾过也。尔善体吾意者,或不以吾为酷也。’”见(民国)李权:《钟祥金石考》,《历代碑志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册680页。此外,戴家除专擅医术,亦世袭儒业,戴之麟于《世伯母戴孺人寿序》中称:“孺人工书史”,戴孺人即戴之麟母亲。本篇寿序乃戴之麟假作他人,以旁人口吻写出,故称其母为世伯母。④《世伯母戴孺人寿序》云:“孺人之子慕颜,与余为总角之交,故知其家事最稔。慕颜本姓陈氏,其曾大父科九公,以朴学教授乡里,邑之名公巨卿,多出其门,学者尊如山斗。秉一封翁,即先生冢孙也。封翁幼承家学,致力诸经,尤精于《易》,风鉴、岐黄诸书,莫不浏览,远近羡之,佥谓陈氏有子矣。咸丰中,捻匪寇郢,翁未弱冠,为贼所得,以智脱。孺人父吉昌公奇之曰:‘是儿能自脱于虎狼之口,其智足多。’请于先生,欲赘以为子。先生曰:‘淳于豪士,实开此端。近代黎樾乔京卿,亦循此轨,湘乡相国,不以为非,姑徇子请可也。’……初,吉昌公保赤心笃,尝仿后唐太祖故事,养他人子以为己子。若辈骄奢性成,尽耗家财,财尽身殁,子孙有不免冻馁者,孺人仰体翁意,收抚存养,且为之授室。……孺人生平只一女,择壻亦不徇俗见。慕颜有弟子杨仲煊,驯谨异常,孺人爱之甚,商于翁,以女妻之。”又《戴秉彝墓表》云:“同治初年,捻匪犯钟祥,见(秉彝)公幼愿,乃置之马上而去。……明年,贼败,东北窜。公脱贼中,归。寄食于族兄宏锦家,族舅戴公光裕器之,故公遂壻于戴氏。舅无子,因袭其姓。命习岐黄术于张光荣先生家,先生课《灵》《素》之书,二鼓命息烛寝,公潜然之伏读至于夜午。又心好堪舆家言,受学于叔舅瀛公;浙人濮某精星卜学,公又从而师之,……娶戴孺人,即光裕公长女,仁而善家。有女弟适某氏,以产子亡。孺人取其孤而子之,庖偶得肉,孺人必先择其精者饲妹子,而后始奉光裕公。……子之麟,女适杨氏。”可知以下几点:1、慕颜与戴之麟的曾祖父同为陈文运;2、慕颜的父亲叫戴秉一,戴之麟的父亲叫戴秉彝;3、慕颜与戴之麟的父亲都善医术与星卜、堪舆学;4、慕颜的父亲与戴之麟的父亲都入赘戴家;5、慕颜与戴之麟的外祖都称吉昌公(《楚辞补注疏》第2册《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第5册《天问》“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第12册《九思·疾世》“鸲鹆鸣兮聒余”数句疏证戴之麟皆称“先祖吉昌”,以父亲已入赘,故称祖而不称外祖);6、秉一与秉彝都曾被捻匪掳去,且自行逃回,为吉昌公所称赞,不过一在咸丰,一在同治;7、吉昌公还曾经收过其他养子(或上门女婿)。8、慕颜的母亲与戴之麟的母亲都曾存恤母家孤儿;9、秉彝和秉一的女儿都嫁给了姓杨的人家。即便我们假设吉昌公仿后唐太祖故事,收的就是上门女婿而不是养子,且是陈家另一子秉一,也仍有说不通的地方,即如果慕颜与戴之麟分别是秉一与秉彝的儿子,他们应该是堂兄弟,戴之麟在作寿序时断不该称“世伯母”这样见外,也不会称慕颜为“总角之交”了,且根据陈家取名的习惯,之麟通芝灵,麒生同祺生,秉彝很显然应该就是秉一,更遑论一个家族基本不可能同时送两个儿子入赘给同一家人做上门女婿。尤其是慕颜与之麟的母亲都存恤母家孤儿,秉彝与秉一的女儿都嫁与杨家、两人都精通医术与堪舆学、两人都被捻匪掳去并自行逃脱(一曰咸丰,一曰同治,可能事在咸同之交,故有出入),这种巧合出现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的。显然,慕颜就是戴之麟。慕颜一名,或其乳名,或其别名,或出杜撰(根据戴之麟《<向晓山房诗草>序》,戴之麟曾与李光渤慕白有过交往,慕颜一名,或即本此而杜撰,或取“倾慕颜回”之义),已不可考。戴母以女子身份,亦能工书史,足见戴家亦家学深厚。因此,无论从父家还是母家说来,戴之麟家学渊源都较为深远。
2.戴之麟的交游
戴之麟僻居乡邑,鲜作远游,故其结交的大多是本县人士,如赵鹏飞、关云门等等,这些人常在戴之麟的文学研究著述中出现,以他们的亲身经历作为实证材料引用。但戴之麟跟当时政界、商界巨子也有一定程度的交往,如时任教育部主事的陈锡赓曾为其父墓表书丹,其学生杨仲煊为商界名人,成为他妹夫等等。远至当时极具声望的林纾,“中国考古学之父”“清华第五导师”李济的父亲李权,戴之麟都与他们有着亲密的交往。
(1)与翻译家、文学家林纾的交往
可能正是因为戴之麟原籍闽南,故他在参加中华编译社国文函授部学习时,能与同为闽人的林纾,有较为频繁和亲密的交往。这从其函授结业文章《世伯母戴孺人寿序》发表在林纾主编、中央编译社发行的《文学讲义》第一期(1918年10月再版)中,又于1919年中央编译社发行的《文学杂志》(林纾亦参与大部分编辑工作)创刊号中,发表《与友人论文书》一篇,《郢中竹枝词》九首即可见一斑。林纾也在《戴秉彝墓表》中说道:“予乐之麟之孝,因为文以表其阡。”[1]而通篇只字未提与戴秉彝有何交集,以当时文坛领袖身份,亲自挥毫为国文函授部一介学生之父作墓表,足见出戴之麟与林纾交情匪浅。
(2)与文史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父亲李权的交往
李权是钟祥著名的文史学家,幼年丧父,以自学苦读成才,因参加1907年的举贡会考,成绩为鄂籍第一,列学部七品官。后历任北京多所中小学教职,及民国内务部警政司、民治司诸多职务。毕生最大的成就是培养了“中国第一位哈佛人类学博士”“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为我国的考古学乃至田野考古事业的发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另一主要成就是完成了“钟祥三考”(《钟祥金石考》《钟祥艺文考》《钟祥沿革考》),成为1937年版《钟祥县志》(李权亦为总纂官)中《艺文》和《方舆》《建置》等部分的主体。戴之麟曾给李权编纂《钟祥金石考》提供材料,李权在《戴秉彝墓表》后称:“之麟即麒生,时以拓片或所抄碑目见寄,助予成是编者也。是表亦系抄稿,故无年月可纪,然予知麒生之必将付石爰录之以殿吾编,且以俾后之考吾邑金石者之得有所采云。”[1]可知戴之麟与同出钟祥书香大家的李权有很紧密的交往,给李权提供了大量的金石拓本和抄稿资料。
(3)与本地邑人文友的交往
戴之麟曾与赵鹏飞(参加湖北新军,投身革命,曾任湖北民政厅秘书主任)、关门云(留学日本,精通医理,曾任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一同参与编修1937版《钟祥县志》,与二人合称为“钟祥三怪”,并与两人有亲密的交往。关云门为戴之麟总角之交,戴之麟曾为其母黄孺人作墓表。①见戴之麟《关母黄孺人墓表》。(民国)熊道琛等:《钟祥县志》,1937年版,卷15第18页。戴之麟常于《楚辞补注疏》中称“吾友赵鹏飞”。戴之麟在《<向晓山房诗草>序》中云:“甲子仲冬,余客东乡长吉小学,与座客李光渤慕白论诗,慕白亟称先生,且言‘先生无后,手辑本近存某家,拟付报章,次第登载,藉资表扬’。……(余)爰就全稿删去一百九十三首,计存七百五十八首,卷仍其旧。呜呼!即此亦可以传先生矣。”[2]570-571知戴之麟曾与本地诗友李光渤一同整理邑人郭开益的诗集。此外,戴之麟还与本地的名医朱兴铨有诗文唱和往来。[3]
从仅存的较少的文献资料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戴之麟的交游,上至政界高层、文坛领袖,下至县邑文友、闾里医官,是较为广泛的。并且,其交游多是立足于文化本位的。
二、戴之麟的文学研究
(一)戴之麟的文学思想
1.戴之麟的文学思想渊源
由于戴之麟父亲及先祖著作皆亡佚不复得见,我们不能窥见他从家学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文学思想,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戴之麟的生平及其学校教育经历中,考见戴之麟的文学思想渊源。
(1)“尚用”与“崇文”的传统思想矛盾
中国历史上,道统与政统常处于紧张的态势,这极容易造成士人自尊与自卑结合的奇妙特殊心态。他们自诩为真理的裁定者和价值的拥护者时,心理上有一种极强的优越感和自信,但是往往这种心理优越感在现实中是软弱无力的,在现实政治权力和世俗价值面前,他们的思想武器毫无价值,这造就了他们的自卑心态。因此,古代士人普遍存在“轻视”文人的思想倾向,他们人生的第一选择,往往不是为文而是经世。然而,越是在经世的过程中不得志,往往又越能从反面刺激士人的创作欲望,“文穷而后工”,反映出文学创作是穷困潦倒后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此,“尚用”与“崇文”实际上是一对看似矛盾,但又相互依存促进的思想观念。
从前文可知,戴之麟本来生于书香世家,后来又参与文学函授进修,得到林纾的抬爱,得以与当时文学界、学术界的风云人物同台讨论(仅《文学杂志》创刊号,就发表了梁启超、康有为、林琴南、马叙伦等多位名家的作品),但他早年似乎并没有对文学研究产生太大的兴趣。戴之麟早年走的都是中国传统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或者说,他注重实业兴国,注重知识的经世致用,所以更愿意从事教育工作乃至更贴近生产实际的农业学校教育,也愿意参与关乎国计民生的防汛工作。这种思想倾向,对他晚年仍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虽然他在愤然辞去县堤防委员会主任委员后,声言不再参与政事,且后来确实长期在荆州博物馆、钟祥文化馆从事文化工作,但他仍以出任县救济院院长②戴之麟任救济院院长,应该还有一部分原因要归结于父亲从医的影响。戴之麟在其父遗著《医学笔记》的序言中写道:“先严知医,医书靡不浏览,有得则笔之于书,语多独到。先严存日,之麟尚未知其宝贵也。己未仲秋弃养,之麟以舌耕不能读父书,自憾不肖等赵括,都先严所有庋藏之。于今年乙丑,六易裘葛,几忘其中尚有手泽存焉耳。春仲,石儿病瘟,几不起,日更数医,其用此症忌药如柴胡、羌活、葛根等,为昔日闻诸先严者,虑不确,乃发其书参考之,先严手泽犹新,忆父殁而不能读父书语,不禁泫然涕下,幸考证有资,石儿以瘥,于是将昔日所庋藏者,录其笔记,汇成一帙,上书原作,下注何书、何篇、何条,以便翻阅,公诸世人,先严其亦许我乎?”(李权:《钟祥艺文考》,《地方经籍志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45册603-604页。)林纾《戴秉彝墓表》也称:“民国己未八月,公以疾卒于里第,命焚券。券盖乡人十年中所假贷者,决其莫还,因曰焚之,勿贻后人为构讼资也。”(李权:《钟祥金石考》,《历代碑志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册680页。)戴秉彝的高超医术与医者仁心,应该是促使戴之麟出任救济院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第二届委员等形式表达他“修齐治平”的政治民生关怀。我们不难看出,戴之麟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尚用”与“崇文”这一矛盾的文学观念的。他首先选择的是经世而不是为文,直到他经历了求仕未果、供职县政机关遇到贪腐不能伸展其政治抱负、日寇进占等多方打击,他才选择了文学研究,并产生了优秀的著作《楚辞补注疏》。正是“崇文”的无用,导致了戴之麟“尚用”求仕的未果;而“尚用”的挫折又促成了戴之麟“崇文”的精进。
(2)直承“侯官”,远绍“桐城”
戴之麟曾参与中华编译社的国文函授部,中华编译社是由苦海余生刘哲庐创办的,刘氏为陈衍学生,林纾、陈衍为同榜举人,都是服膺于“桐城派”的,称“侯官派”。林纾、陈衍都为中华编译社的社刊《文学杂志》《文学常识》《文学讲义》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这三本刊物同时也是函授课程的教材。因此,戴之麟的文学思想远绍桐城姚鼐,且直承“侯官派”。这从其《楚辞补注疏》中频繁引用姚鼐《古文辞类纂》亦可见一斑。
2.戴之麟的文学思想
(1)“守先待后”“兼容古今”的散文观
刘哲庐在《文学杂志》发刊辞中称,各栏作品“发圣贤之遗臭,振经传之坠绪”,坚持“守先待后,冀维文教于不叛”的立场,与日益高涨的新文化运动激烈争鸣,极力为桐城派“古文论”张目。同时又指出创刊的目的在于“使学者酌新理而不泥于古,商旧学而有得于今”,认为“理有古今而势无古今,责任不可移而因时之道异也”[4],与桐城派将时文的写作提升到古文的高度是一致的。因此,戴之麟的文学思想也很明显带上了这种“守先待后”“兼容古今”的思想,追求时文与古文的融合。他在《与友人论文书》中就曾经指出:“夫一部十三经,惟《周易》为四圣之书,《周礼》为周公所著;《尔雅》《孟子》及《左》《公》《谷》三传,为一人自著;此外如《尚书》《论语》《仪礼》《礼记》,则非出自一手;《诗经》则羁人、怨妇、女侍、巷伯、手迹,无不层入。不敢致力,亦奴性太深矣。虽然,六经岂易求哉?一经有一经之例,即有一经之面目。袁随园云:‘孟学孔子,孔学周公,三人文章,颇不相同。’随园文人,经师轻之,今观其言,于经学用力甚深,而举世不知随园通经,随园亦以文苑中人自处,羞与章笺句释者为伍,岂知其穷经之术,别有在哉!”[5]表现出很强烈的“今文经学”思想倾向,主张对经典、文学的阐释应该随时而变,应该注意阐发微言大义。并且他还指出“张南皮相国著《輶轩语》,谓明人评经,亦以评时文之法评之,诋其侮经。某则谓明人评经,未可厚非,特不当‘以评时文之法评之’耳。”[5]极力反对时文与古文泾渭分明的做法。
(2)“比兴托喻”的诗词观
戴之麟在《<向晓山房诗草>序》中指出:“《诗》三百篇,多男女相悦之辞,此有托而然。孔子以‘一言蔽之,曰思无邪’,凡以明诗人之志也。屈原《离骚》,借美人香草以喻君子,太史公称其得风雅之旨,故曰‘其志洁,其称物芳’,又曰‘推此志,足与日月争光’,殆以托兴遥深,语在此而意在彼也。……抑余考其(郭开益)词间有涉于绮丽者,《隐恨歌》一首,亦似有托而然。”[2]569-570从《诗经》《楚辞》的“托喻比兴”拓展到诗词整体层面。
(二)戴之麟的文学研究
日寇进占钟祥后,戴之麟因其不屈的民族气节,不愿出任伪职;更为了抵制日寇的奴化教育,保留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选择在家自办私塾,传授传统的国学课业,并由此引发了对文学研究的兴趣。早在《楚辞补注疏》(初成于1941年,1948年曾定稿,但直至1951年仍作有补订①《楚辞补注疏序》云该书“计自庚辰莫春始,至今年辛巳莫春止,初稿聿成”,钟祥市图书馆藏该书稿本封面所题定稿日期为戊子年,而稿本中页眉页脚的校补日期最晚至辛卯年。)之前的己卯、庚辰(1939、1940年),他就完成了《填词法述》《千家诗志疑》等多部著作。②见《楚辞补注疏序》。而他对《楚辞》一书,可谓是烂熟于胸,浸淫多年。他不仅保持了每天晨读背诵《楚辞》篇目的习惯,也长年从事《楚辞》的研究工作,《楚辞补注疏》自序云“吾寝馈五年而始熟”,其致时任钟祥图书馆董馆长的信亦称“不佞费数十年心血,旁求博采,不闻寒暑,幸而告成”,足见其对《楚辞》研究用力之勤。曾著有《楚辞注解》八册,并寄呈毛主席,毛主席托郭沫若予以复函,惜今不见当时信稿。又著有《楚辞补注疏》,专事对《楚辞补注》进行疏证。戴之麟认为,《楚辞集注》及《楚辞补注》在名物训诂方面,都不能令人信服,使人释然,这都是因为前人学者“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贴近底层大众生活,不能从事实际生产活动的结果。因此,他们训诂名物往往有所错漏。而对于某些自然现象的阐释,往往又流于神怪之说,不能合理利用科学知识去解释。而在很多很明显的问题上,如《七谏》《九叹》的作者问题,从文本中即可找到有力内证,却一仍前错,不加改正,这就是典型的‘强不知以为知’了。而洪兴祖《楚辞补注》是最为善本的,历来被视为《楚辞》阐释史上第二座高峰。故戴之麟从此下手,专事为其注作疏证,一扫前人注释《楚辞》的积弊。①见《楚辞补注疏序》。《楚辞补注疏》的出现,填补了《楚辞补注》专书研究近800年的空白,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
戴之麟殁后,其学术著作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虽然他在致时任钟祥县图书馆董馆长的信函中称“拙作(《楚辞补注疏》)似不可长眠箱箧,徒饱蠧鱼,应响应号召,公诸屈馆,就正有道,俾成完璧”,但该书仍然只被《中南、西南地区省、市图书馆馆藏古籍稿本提要》收录,并无系统的整理研究。且除《楚辞补注疏》以外,戴之麟其他的文学研究著作都已亡佚。幸而湖北省政府启动“《荆楚全书》编纂”项目,为留存湖北的文化典籍作出了重要贡献,戴之麟《楚辞补注疏》也因此得以点校出版。目前来说,为拓宽加深国内的楚辞研究,并填补完善湖北文化史,就《楚辞补注疏》展开专书研究,并详细考证梳理戴之麟的生平经历与相关思想,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1] 李 权.钟祥金石考[M]//历代碑志丛书:第2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680.
[2] 李 权.钟祥艺文考[M]//地方经籍志汇编:第4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3] 李传嗣.清末民初钟祥的四大名医[EB/OL].(2011-06-01)[2016-02-06].http://www.zhongxiang.gov.cn/html/yangchunbaixue/yuanchuangzuopin/20111007/391.html.
[4] 苦海余生.发刊辞[J].文学杂志,1919(1):2-3.
[5] 戴芝灵.与友人论文书[J].文学杂志,1919(1):11.
A Textual Research on Dai Zhilin’s Lif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ZHU Peixi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Xiangyang 441053,China)
Dai Zhilin was one of most famous cultural figures from Zhongxiang(Hubei Province)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considered as“Three Eccentrics of Zhongxiang”with Zhao Pengfei and Guan Yunmen.He was born in a Confucian family,because of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he just got the degree of“xiucai”,but he kept learning again and again,so he was admitted to study at normal school of Xiangyang-do,and participated in Chinese correspondence study of China Editing and Translating Press.There he got acquainted with Lin Shu,who was the most famous translator and litterateur in modern times of China,in addition,he was affected by Tongcheng School’s literary thoughts to a great extent.Dai Zhilin had many researches on literature,such as The Methods of How to Write Song Dynasty’s Lyrics,Suspections on 1000 Poems,Explainations of Chu Ci,and so on.Explainations of Chu Ci had been consecrated to Chairman Mao.Besides,he also had the Supplemental Explanations of Chu Ci Bu Zhu,which was a manuscript included 12 volumes and 700 thousand words in total,it filled nearly 800 years’blank of research on Chu Ci Bu Zhu,linking the preceding and the following.So,Dai Zhilin had taken a non-negligible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Zhongxiang and Hubei’s culture and the study of Chu Ci.
Dai Zhilin;Three Eccentrics of Zhongxiang;Tongcheng School;Supplemental Explanations of Chu Ci Bu Zhu
I207
A
2095-4476(2017)04-0051-05
(责任编辑:倪向阳)
2017-01-03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0ZD093)
朱佩弦(1988—),男,湖北襄阳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