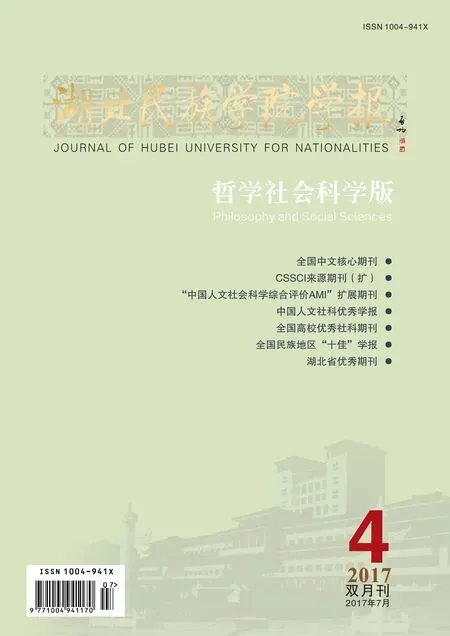财产权的社会本质及其现代形式
——涂尔干《社会学教程》①的财产权学说释义
潘建雷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社会学教研部,北京 100044)
一、驯化资本:涂尔干思想的核心问题
社会生活的全面世俗化与理智化是19世纪西欧社会转型的大势。在涂尔干的时代,以上帝为中心的基督教神圣世界已经处在一种系统崩溃的边缘,在社会各个维度上,大有为资本所取代之势,后者以摧古拉朽之势荡涤了前资本时代的自然秩序与道德秩序,一切自然的、社会的物或关系似乎都被纳入到了资本核算体系,形成了以资本为惟一“价值单位”与“存在基础”的评价体系;这一切造成了19世纪后期悲惨的社会状况[1],[2]329。经过基督教两千年浸润的西欧社会所经历的这种遽变,在思想界引发了持久的惊愕与回响,关于新旧社会的种种理论纷至沓来。就涂尔干这一代思想家而言,他们面临的共同任务便是在清理旧制度的残垣断壁基础上,系统重建新的社会形态,以解决资本的异化扩张、政治权威衰落与价值观念紊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3],其中最具威胁性的问题无疑是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对社会结构的全面殖民与对人心秩序的深度戕害。
面对马克思“前资本—资本—共同体主义(communism)”的辩证革命逻辑及其社会影响力,涂尔干试图以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哲学视角来解释19世纪后期西欧社会的“悲惨状况”,并寻求“经济生活的组织化与道德化”的途径[4]。按照他在《社会分工论》中确立的社会团结的一般理论,任何社会都是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经验配置与统一,而以分工与交换为特征的有机团结在历史演进中必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2]93,132,135,219,223-226,229这种演变转型的过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19世纪后期的社会紊乱状态已经证明这一点,但这不意味着这个时代已经濒临“末日”。在涂尔干看来,西欧社会之所以出现“严重的道德与法律的失范状态”,是因为它正处在一个“旧式的诸神都已经老去或死了,而其他的神又没有降生”的道德间隙期(moral hiatus)*从事后来看,涂尔干低估了这次社会巨变暴戾的能量与持续的时间;两次世界大战与法西斯主义正是这次转型暴戾能量的释放。;一方面,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商业扩张与18世纪中叶的产业革命已经令传统的“教会—庄园”社会彻底瓦解,另一方面以分工交换为基础的新社会形态还在地平线上。[5]339
就如何摆脱当时社会的失范状态、尽快完成社会转型这一问题,涂尔干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与方案。一方面,他抨击当时的复古思潮,认为中世纪的社会传统与现代性精神的罅隙是不可调和的,“复活已经不符合当前社会状况的各种传统习俗”纯属徒劳;另一方面,他也不赞同一切纯粹观念领域的主义论争与革命学说,认为社会遵守其客观的运行法则,不可能依照某种学说或主义重起炉灶。涂尔干尝试倡导一种“道德科学”(社会学),通过“运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讨论道德生活的诸种事实”[5]pxxv,发现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及其不同历史时期的转型规律,确定特定的规范“凌驾于人们心灵之上的原因”,进而在经验层面上甄别当下社会的道德要素的有效性及其运作形式以作为社会重构工程的指南与基础。这是理解涂尔干“道德科学”及其思想体系的要旨。
任何一次社会大转型都涉及到整个社会及各领域的道德心理与组织结构的重塑,对西欧社会来说,从“封建庄园—宗教国家”向“自由市场—公民国家”的转型无疑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过程。按照涂尔干1895年讨论圣西门与社会主义学说时的设想,这项重建工程主要涉及两个方面:1.改变世俗制度与规范,使它们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保持一致;2.重塑共同的观念体系(ideology),作为这些制度的道德基础[6]。他在《社会学教程:民风与权利的物理学》等著作规划的道德重建蓝图具体而微地发展了这一早期设想,力图构建以人的价值、尊严与权利(道德个人主义)为信仰、以新型的财产—契约制度、职业团体与公民国家为组织结构与实践礼仪的新社会(宗教)体系。如上所言,资本主义对人心秩序与社会结构的侵蚀是涂尔干要处理的首要问题,也是其道德社会结构重建工程的首要任务。作为财产权的现代恶性变种,资本是市民社会运行的支配性力量,因此能否有效“驯化资本”直接关系到市民社会的交往(交换)规范程度与有机团结的成色。较之马克思对资本声嘶力竭的批判及其革命逻辑,涂尔干试图从社会史的视角揭示财产权的社会本质及其演变路径,证明其内容、限度、神圣性(正当性)与交换规则都源自所在社会的集体意识,据此主张现代社会应当确立以人的价值、尊严与权利为原则与限度的新型财产制度,明确财产在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则及其承载的社会义务,以纠治经济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交往(交换)中的种种不道德状况。
二、财产权的实存状态
何谓财产权?从表象上说,它是一种道德与法律的约束关系,在物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持续性的道德共同体,类似一种排他性的引力场;这种道德状态使得两者在社会生活中可以共享、提升彼此的状态(status:地位)[7]117。那么,是什么力量能让人与客体(object)之间建立这样一种“人造的”(synthetic)道德联系,且不受时空的限制?[7]101-102对一位“道德科学家”来说,要回答这个问题,准确把握财产权的本质或者说普遍的财产权观念,首先应当考察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实存财产权形态。涂尔干的考察结果可以归纳如下:
1.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财产权的主体与可以成为财产的客体有很大的出入,并无统一模式。个人、家庭、村落、社会团体、国家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都可以或不可以获得主体资格;至于什么东西可以成为财产也有类似特点。[7]110-111
2.有两类物基本不能作为财产权的客体,即“圣物”与“共有物”。“圣物既不能交易,也绝不能让予,不可能成为任何物权或债权的对象”;而空气、海洋、公共道路等社会共有财产,也排除了个人占有的可能,它们归国家机构管理,却不归其所有。劳动与意志在这里无用武之地。[7]110
3.不能依据所有者的权利范围定义财产权。“使用权”“收益权”与“处置权”,并不能定义或揭示财产权的本质。当我们谈及财产权时,都预设一个主体可以针对被占有对象执行某些权力,但要想准确说出它们又必须回到具体的社会场域中就事论事。事实上,具有财产权的人,权力(权利)清单常常破碎不全,在具体的社会场域中受到了明确的界定与限制。例如,古代社会家族世袭的财产是不能随意处置的,挥霍无度的家庭成员也可能被剥夺财产权等;而没有财产权的人或团体,却可能具有近乎完整的权力(权利),例如家庭会议对个人的财产、公民对无主土地的果实的权力、法定监护人对未成年人或能力缺陷者财产的权力等。[7]111-113,116
4.“排他性”是财产权的普遍特征。如上一点所言,财产的肯定性权利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真正相同相通其实是一种否定性状态,即“给定的个体不允许其他个体与集体实体使用某物的权利”[7]114。如涂尔干所言,财产权的要义是一种防止其他主体使用乃至接近的隔绝状态,使其从公共用途中分离出来。当然,要补充一点,在很多社会中,国家、村社(communes)等集体实体在特定情况下是可以征用乃至没收个人财产的。可见,即便是排他性也受到既有的社会舆论与法律的限制。[7]114,116
以上考察表明,一个物能否被占有及占有的权限,并不取决于物本身的性质,而取决于它在特定集体心智中呈现的形象,取决于当时社会约定俗成的集体共意及其结晶形式“法律”[7]110-111。进一步讲,财产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因时因地而异的,所以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财产权定义。[7]172
三、对“劳动学说”与“意志学说”的批判
涂尔干对既存事实的考察的目的是驳斥各种“反社会”或“非社会”的个人主义财产学说与思潮,遏制其功利主义倾向对现代市民社会有机团结的威胁,其主要对手是以洛克、穆勒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派的“劳动学说”与康德的“意志学说”。
(一)劳动学说
穆勒等人主张的“劳动学说”认为,财产是“个人对自身官能的权利,对运用这些官能所生产的物品的权利以及在公平市场中用这些能力获得的一切物品”;劳动作为个人官能的运用过程,使得“人本身投射到自身之外,蕴藏入外物之中”,铸造了人与客体的排他性约束关系,并赋予物以价值[8]122。据此他们主张,财产权惟一的正当基础是劳动,赠予、继承的受益者,特别是无遗嘱的继承者,因为不是所得财产的直接创造者,不具备完整的正当性与所有权,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至于交换可以视为劳动的交换。针对这一学说,涂尔干提出了以下几点反驳:
1.劳动本身只是身体官能的消耗,身体力量对物的改造的力学效果是劳动成果对个人的使用价值的变化;无法据此直接形成一种社会普遍承认的财产形式,这中间缺乏必需的逻辑环节。
2.劳动学说与既有的财产制度相矛盾。人类社会已知的财产制度,绝大多数都是承认继承、遗赠或赠予的,继承者本人几乎或完全没有参与财富的积累,但较之劳动形成的财富,集体意识对这些方式的正当性的认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7]99
3.劳动学说不能解释交换形成的财产所有权。交易双方很可能对交易物品都没有付出任何实质性的劳动,只是因为物品被交换者“合法”占有,也就是说,通过交换获得的物品可能与劳动无关,其所有权的转换与确认来自另一个重要的社会要素:契约。[7]134,138
4.劳动学说不能解释财产权的排他性权限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人对财产的处置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乃至取缔,例如国家对个人财产的合法征用、人的年龄与智力水平等。因此,财产权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的,不是理所当然无条件的,而是依具体情况而定的[7]98。这些限制常常是对劳动—财产权的否定,也表明财产的权属规定来自其他要素。
5.劳动不仅不是财产权的基础,也不是物的价值(价格)尺度。物的价值不取决于耗费的劳动量的大小,而取决于经济领域既有的交易评价体系。例如,房子无疑是劳动的成果,但若无人购买,它就一文不值,而钻石无需雕琢就价值连城。据此涂尔干认为,关于劳动量(时间或产量)作为价值尺度的主张,与其说陈述了一个事实,不如说是关于未来社会的主张与憧憬。[7]100-101,172
由此可见,劳动不是人—物的所有权关系的充分要件乃至必要条件,不能构成财产权的正当基础,更不能解释其起源。的确在现代法律中,“物质上的占有与持有,并与之保持密切关系”已经成为财产正当性的一个认定要件,但这一观念其实是近代(洛克)之后才逐渐形成的,与其说它揭示了财产权的本质,不如说它是财产权的现代形式。
(二)意志学说
康德等人的“意志理论”主张,财产权只涉及客体与主体之间的智识关系(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这种关系源自个人的意志。康德宣称,意志是一种本体、实体或自在的官能(faculty),其活动不受时空与现象的约束;不论何时何地,个人意志只要“合法”实施,都可以合法决断确认物的所属,而且有获得承认与尊重的权利,这在法律上与事实上都是有效的。“当我的意志根据其自身权利确认了自己的时候,它必须得到尊重;一句话,这是意志的神圣属性,只要它本身遵从行为法则。”[8]128正是意志的这种特殊性质创造了物与人格之间的智识约束关系(intellectual bond)[7]102,107。就“意志作为人—物关系的纽带”这个命题,康德还就以下两个问题做了解释:
1.如何保证不同个体意志在确认物的所有权时不发生冲突,或者说意志的相互豁免问题?对此,康德确定了两个评判标准,首先是时间上的先占,先占这一要素足以为占有提供一种法理与道德的基础,只要“其他人尚未确认划归为我所有的东西的权利,我的权利就是绝对的”;其次是占有与保护物的能力,就个人能占据多少土地(到18世纪后期土地依然是主要的财产形式之一),康德主张“我可以合法划归己有的物的范围只取决于我的力量的限度”。[8]130,133,134
2.如何解决冲突与维持秩序?按照康德的逻辑,要形成普遍的财产观念,必须实现“我的意志”与“他人意志”的相互承认与熔合,为此他先虚拟了一个人与客体的“原初共同体”,宣称只有在一种共同占有的关系中,个人才能以集体意志的名义确认他对物的占有,“人类承认个人有权占据他能占据的一切,但也必须保证其他人同时享有的权利”[8]129。康德依据这个虚拟的原初共同体及其高级法(superior law)熔合了两个异质的意志实体,由此财产权就有了逻辑的前提与基础。进而,他又主张必须构建一个相对应的事实社会共同体(公民国家:Civil State)及其规则(法律)来“承认”与“保卫”个人的权利[8]131。注意,是承认与保卫,而非确认,这意味着,个人意志及其与物的占有关系,在正当性与逻辑上都先于后来事实的公民国家与法律。
康德的逻辑一言以蔽之:物若不被占有,就违背了人类的特性;大地上的任何占有都是合法的,因为已经被占有了;支配占有行为的意志,一旦公开宣布,就有得到尊重的权利,即便此时个人(或者说主体)与物没有任何关系[7]105。他的理论之所以在19世纪的西欧大受欢迎,因为它为财产的先占者与既有分配状态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说辞,甚至可以说为“资本积累”与“殖民扩张”进行了学理强辩;同时他把“劳动”贬低为占有的外在标志,否定了根据“劳动学说”改革乃至颠覆既有财富分配的学理正当性。
康德看似缜密的理论设计隐含着一个致命弱点,它强调先占权的法理与道德正当性,并假设意志不会相互侵犯,“因为就同一个客体而言,不同的意志不会在同一个物理平面发生碰撞”。[8]132实际上,“意志,凡其所能是,都可以是”,它并不受制于时空结构中已经表达的其他意志,所以必然发生种种冲突:
冲突点1:曾经有主、而现在无主的财产的归属标准是什么?如果我要把一个之前经过他人意志确认、但实际未被占有的东西归为己有,那我是否有否定他人意志的道德正当性,又或者这是一种侵占行为?[8]132
冲突点2:若两人或多人同时对无主物体确认意志,归属是否纯粹取决于力量?
如果说前一类冲突还可以通过引入“国家意志继承”之类的规定,那后一类冲突的确是康德理论无法解决的,“尚力”的原则必然引发无休止的争斗。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对18世纪处在狂飙期的西方文明、日耳曼民族与资产阶级来说,其学说正符合他们的扩张需要,减轻了殖民者的道德负罪感,推动了他们征服世界的步伐,但对19世纪末逐利成风的欧洲来说,这就是一种危险学说了。
相较之下,卢梭的观点更为周全,他不仅主张意志确认与先占权,且附加了两个条件:1.劳动与耕作对真正的占有是必要条件;2.主张把占有者的权利限制在正常需求的范围内,“每个人都有占有他所需事物的自然权利”,同时“只能占用他生存所需的土地”。作为一位自然法学说的集大成者,卢梭尝试用人性的自然均衡状态,把“先占”、“劳动”与“有限需求”作为形成财产权的三维要件。
理论上说,卢梭的主张可以缓和康德理论的“尚力”缺陷。可是,19世纪血淋淋的欲望“发烧”状态让涂尔干觉得,卢梭的财产观“如今只剩下历史研究的意义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已经用一种持续变动的混乱状态代替了我们在动物身上看到的稳定不变的均衡状态,用不再是维持生存必需的需求代替了所谓的自然需求,而且完全合理合法。”*20世纪以来,欧美盛行的累进制财产税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卢梭的主张,所以还不能完全说卢梭的财产观成了一个历史概念,相反,它似乎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一些发达国家成了一种具有集体意识性质的价值观念,而不仅仅是一种学说。可见,身在转型巨变中的涂尔干也常常谙于历史的大势。
(三)简评
劳动学说与意志学说都试图以人格为起点演绎人与客体关系,虚拟一个超越时空的人与客体的单纯关系,而没有认识到人与客体的关系始终以既有的社会结构为底色,或者说,人与客体的关系嵌入社会既有的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他们的学说有很强的地域性与时代局限性,与既有的财产权观念相去甚远,而且其学说呈现出一种近乎独断的道德理想,一种可能或正在成为社会事实的道德理想,而不是关于道德事实的科学。
正如涂尔干所言,我们总不能要求既存的各种实践迁就一些先验的公理[8]125。实际上,“劳动”与“意志”两个要素不仅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而且也没有得到现实法律的认可。法国当时的《民法典》第711、712条即规定,“财产是通过遗产、赠予或遗赠的方式获得的,是通过继承、代代相传的占有或有约束力的义务作用获得的”[7]134,遗产等要素与劳动或意志几无关系。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劳动学说可以目之为现代世界新兴产业阶级对旧式世袭封建庄园制度的舆论抨击,而唯意志论关于尊重财产是尊重个人人格的延伸的论点,则反映了个人的地位在社会结构与集体意识中日渐尊崇的社会事实。其实,诸此种种都是社会总体转型的一个面向。
四、财产权的社会起源与生成机制
既然劳动与意志都不是财产权的正当基础,那么人与客体之间的这种道德关系是如何形成的;财产权又该包含哪些内容?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涂尔干充分利用了他学术生涯后期广泛涉猎的民族学与社会史知识,试图以一种之前未有的社会史视角,从更原始、更古老、更简单的社会中探索财产权的起源,还原其“原初”的形式与要素,呈现转型流变的脉络。这正是他讨论初民社会“塔布”的目的。
(一)塔布与财产的社会史亲缘关系
1.塔布(taboo)的首要属性:禁忌
涂尔干分析了古代希腊罗马、波利西尼亚、火奴鲁鲁等地塔布现象(taboo:神圣的禁忌),发现这些社会通过一些约定俗成的仪式,把某些物从社会空间中分离出来,宣布其为塔布,使之进入神圣世界。此后,只有与之有亲缘关系的人才能接近与使用它们,其他人则禁止与标志为塔布的圣物接触。可以举行塔布仪式的不只是巫师、酋长、国王这样神圣的人,普通人在特定时期(例如收获季节)也可以通过这种仪式为自己的物品赋予神圣性,以达到保护它们的目的,只是其神圣性等级比较低[7]115。
在现代社会的财产权关系中,我们不难发现同样的隔离状态与使用规则,“被占有物如同圣物一样,其周围都是真空。除了那些有资格占有和使用它们的人,其他人都不得不敬而远之”。[7]115涂尔干认为,圣物与财产之间有相同的社会效果(神圣、禁忌、排他),“宣布某物是塔布,与占有该物没有什么区别”[7]115;这表明它们的社会史亲缘关系。据此可以推断,财产权最初可能就起源于塔布之类的宗教圣物,而财产是原始宗教圣物在后来世俗生活中的一种流变形式。[7]115,117
2.塔布的另一属性:传染(传递)
塔布的禁忌特征已经可以解释财产的排他性与垄断性的使用权,那如何解释所有者对财产收益的占有呢?涂尔干发现,塔布圣物除禁忌之外,还普遍具有另一项特征:“传染”。圣物可以与接触的人与物(世俗)持续沟通,使之分有不同程度的神圣性。“无论神圣性在何处,从根本上说都带有传染性,可以传递给与之有关的一切对象……所有触及神圣实体的物或人,都会像圣物或生人一样成为神圣的。神圣实体具有的潜能,可以从集体的想象力中找到,只要环境是开放的,它就能随时传遍各地。”[8]148同样,财产权也具有类似的传染性,它总是想从所在对象扩展到一切相关对象,特别是衍生物上,如奴隶主对奴隶劳动成果的占有,土地所有者对地里的果实、文物、矿藏等增益物的权利,牧民对牲畜幼崽的所有权等都是例证,事实上也为很多国家的法律所认可。*当然,各国法律也都有相应的限定。
3.塔布的第三个属性:不可转让
如上所言,塔布圣物与所属的人或团体之间通过特定的仪式形成了独特、永久、排他的道德共同体,二者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拒绝任何形式的切割或转让。的确,从理论上说,不可转让的财产是财产权的至高阶段,它意味着,物与占有主体之间的约束关系最牢固,对社会其他个体或团体的排斥也最严格。[7]119-120塔布圣物与古代社会世袭财产都具有类似的不可转让属性,这是其神圣性的一种具体表现,而现代社会财产的可转让性(流动性)则表明了其世俗化特征。
(二)塔布转化为财产的社会学机制
1.塔布、仪式与对神圣世界的禳解
塔布的产生机制是什么?涂尔干以土地这种最古老的财产形式为例进行了考察。他指出,在部落社会、古代罗马、希腊、印度都有类似的禁令,即“绝不允许外人穿越氏族土地的界标”*在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禁令,“禁”字本身就是山林海泽为天子诸侯所有,平民不得入内的意思。。古罗马每一块土地周围都有一条狭长地带以作隔离标志(类似中国古代社会的田埂),这一地带的神圣性不亚于诸神的神权,谁若耕作它,就可能受到灭族的惩罚(不仅是土地,围绕门、墙也形成了类似的信仰与仪式)。[7]119-120为了维持与强化界标界石的绝对神圣性质,罗马人在这些神圣的土地上定期举行固定的仪式活动,经年累月,周而复始,逐渐以特定的神的形式人格化与实体化这一地带,而以不可移动的土地边界为载体的“巫术环圈”具有最强的神圣效力。按《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说法,这些仪式是生产与再生产塔布的社会机制,可以隔离、贮藏与强化塔布的神圣性。
古罗马人为什么要举行这些仪式,把土地边界奉献给诸神成为塔布圣物?涂尔干认为,应当把这些仪式放入整个宗教(社会)体系中来看待。在古人的世界观里,“整个自然都具有一种神圣的性质,众神遍布各地,宇宙及芸芸众生都在神圣本原的永恒源泉之中”。[8]154这种“万物有灵论”的世界观意味着,土地与河流、果实、谷物等自然要素都具有神圣性质(圣域),“共同体生活的本原(principle)就寓居其中,并使之神圣”[7]129。土地界石的仪式与初收谷物的仪式、房屋的奠基仪式一样,都是一种奉献牺牲的禳解仪式。这些仪式,一方面是稀释,更准确地说,转移土地潜在的神性,让土地能为世俗所用之物,另一方面,祭祀者借此与土地或房屋的神祇之间建立了一种道德约束关系,即保护—奉献关系,在一定时期内(例如1年)分有对物的支配权;当然神祇并没有从这块土地中消退,而是转移到了田埂这样的特定范围内,对外人(世俗者)来说,它们依然具有令人敬畏的力量。[7]124-125,127一言以蔽之,物的神性品质在仪式的作用下经过漫长的削减、驯化与疏导传递到了特定人群的手中,所以人对物的所有权只是神的所有权的衍生物。*涂尔干对古代罗马、希腊社会的财产观及19世纪人类学家笔下初民社会“塔布”的考察,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尚不能说概括了普遍意义的所有权,特别是古代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共有形态”,就不能按照“塔布”这种模式来推演,而必须回到传统社会的伦理关系中考察;当然,这与涂尔干所说的所有权关系要以既有的集体意识为基础是一致的。
(三)神圣性转移的本质:家族所有与特许租借
在今天看来,这些信仰与仪式近乎神秘乃至荒诞,如何理解它们?对此,涂尔干沿用了其一以贯之的“道德科学”解释模式。他写到,“当人群心智的虚幻景象散去之后,当虚构的神灵烟消云散之后,这些幻象再现(represent)的现实以其本来面度呈现之时,我们会发现社会才是每年贡品的供奉对象,而信仰者就是依靠这些贡品最初从诸神那里获得耕耘土地的权利。”*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此处涂尔干还提出一个观点,即牺牲与各种初收的果实是税收的原初形式,向神偿还债务、教会的什一税、国家定期赋税是一脉相承的。这种观点似乎缺乏详细的论证,个人以为,税赋的发展可能与部落的战备需要有关。信仰者的崇拜对象归根到底是社会,神对个人的至高无上,其实是群体对成员的至高无上;而神祇只不过是以物质形式人格化、结晶化的集体力(collective forces),是社会的持续在场物(social representation)。[7]128-129即是说,私人占有的前提是一种原初的集体占有。信仰者通过仪式为自身赋予了诸神的权利,其实质是个体为自身赋予了集体的权利。私人财产形成的社会学机制是个人在转向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运用了社会激发的敬畏之心,并把这种敬畏之心传染转移到占有物。换而言之,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通过仪式获得的“神圣占有”,其本质是对共同体财产的特许租借(concession)。[7]130
从社会史的角度说,特许租借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一场革命,即农耕定居。农业的出现使得较氏族规模远小的家族(family group)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与稳定性,成为土地特许租借的最初社会载体。土地从神圣世界的剥离与家族从氏族群体的分化是社会结构在人世关系与物权关系这两个维度上的一对共变量,家族与土地形成了一种相互占有与持续强化的道德关系。一方面,家族群体通过仪式从诸神那里租借土地,分有土地的神圣性,与之形成道德联接,并为土地赋予一种与家族人格类似的统一性与凝聚力。[7]130-131另一方面,土地使家族成为有吸引力的核心,法律或约定俗成的规矩也把个体束缚在他们从事耕作的土地上,“各个个体以整体的形式生活在彼此隔离、神圣的小‘岛’上,这些小‘岛’构成了特定的地域”[7]131,逐渐形成了明确的形式与坚实的结构。可以说,家族亲缘关系之所以成立,主要是因为他们共同使用了某块地域,若有人与这种经济共同体断绝关系,那么与一切既有的亲属关系都随之切断。从古代社会家族世袭地产的排他性与不可向外转让的属性,可以判定“物占有人的程度至少可以达到人占有物的程度。”*这里,涂尔干其实是用其道德科学重新解释了康德的意志学说。
(四)个人所有的两种形成机制与发展趋势
财产的家族所有形式是如何演进到个人所有形式的;人之于物的优越性及其支配关系又是怎么形成的?涂尔干认为,存在两种可能的发生机制:
首先是家族群体的父权制的个体化流变。随着农耕定居的普及与战争的需要,家族群体关系逐渐固定化,权力集中于某个男性成员,即家长,他享有凌驾于家族成员的优先权。家族的集中化形成了垄断与世袭的权力,整个群体的道德与宗教意义都集中到家长的人格,这种高高在上的道德和神圣权力使之成为“家族人格化的实体”。与之相应,家族的重心也从诸神赋予的物转向家长个人,而维系物与家族群体的纽带也转型为物与群体内享有神圣特权的家长人格的联系。于是,占据这一地位的特殊个人便享有了占有或所有权,在事实上也意味着,“个人变成了完整意义的所有者,因为物已经隶属于人了”[7]132。久而久之,随着家父长制的衰落与家族子孙的个体性获得承认,个人所有者的色彩也就日益凸显,由此形成的个人财产还具有浓厚的“共同占有”色彩,因为个人获得财产的主要形式是“继承”。继承本质上是集体财产的延续,是集体神圣性的个体化,它是与家族—封建社会匹配的财产制度。而按照涂尔干的设想,现代社会是以道德个人主义作为统摄性的集体意识,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大家族乃至小家庭都不再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另一方面财产的保有也以个人存在(生命)为始终,所以他断言继承获得的财产权是“现时代已经不再起作用的古老概念与礼仪(practices)”*涂尔干这个判断有些极端,当然今天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高遗产税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涂尔干的预言。,因为随着组织形态与集体意识的转型,继承者与财产之间的关联的正当性将日益削弱直至消亡。
其次是动产在商业与工业时代的兴起。如上所言,农耕时代,地产在整个家族场域中具有独特的神圣属性,它与家族是一种共同体内的相互所有关系。农耕时代的一切动产只能是地产的附属物,而且只要产业依然以农耕为主,地产“可以把一切物都限制在自己的行动范围内,防止它们获得与之特征相应的法理地位,防止其中某些新的权利生根发芽”[7]132;可见,不动产的神圣性很弱或世俗性很强。然而,随着中世纪后期欧洲工商业的复兴,动产开始独立于地产,成为经济生活一种自主乃至主导要素*这种转变反过来也逐渐削弱了土地等不动产的神圣性质,因为不动产不再是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心,准确地说,在资本时代,一切不动产都具有动产的性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按照涂尔干的观点,动产与不动产实质上是两种农耕与工商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财产形式,它们也各自对应了不同的社会团结形式。。作为新兴的财产要素,动产不具有与地产类似的神圣与公共属性,在脱离地产之后,动产在社会空间结构中就处于游离流动状态,其神圣性与正当性还不如持有者本身,持有动产的个人可以更自由、更灵活、更完整地处置它;进一步说,动产的“神圣性”属性就来自持有者。按照涂尔干“神圣性传染”学说,在人(道德人格)本身成为神圣要素的现代社会,个人的神圣性也必然会扩展到与其有密切法理关系的物,对人的尊重不只是对身体意义的人,他所拥有的对象也必然分有这种性质。[7]136-137而契约便是现代社会道德人格向财产传递其神圣性的社会机制。
涂尔干关于财产个人所有的这两种社会机制的讨论,实质是对应了中世纪后期欧洲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趋势:家族—封建庄园(农耕)的解体与自由市镇(工商)的兴起,而他对两种机制的判断也是基于两种社会形态此消彼长的历史事实。显然,资本/商品市场中的“流动性财产”是财产的个人化所有形式的主要源头,而且必然成为现代社会主要的财产形式。
五、涂尔干的设想:道德个人主义与财产权的现代形式
鉴于现代社会的转型趋势是以道德个人主义为基本信念(信仰)、以自由市镇(市场)为主要场域的新社会,一种与之匹配的新财产权自然要应运而生。那么,在现代社会,个人对物的占有在何种条件下是正当的,它又需要遵从何种规范与义务?据上所述,既然现代社会的财产权源自道德人格,或者说物权依附于人权而非相反的“异化”,那财产的运动(交易)规则与社会义务都应该以人的尊严、价值与权利为准度。
按涂尔干的设想,道德个人主义包含两项基本义务:1.公平义务(duty of justice):a、分配公平:主张人与人的社会差别应该基于人本身的禀赋(gift)、能力(faculty)与功绩(merit),因据此以法定方式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职位、级别与财富,并从一切法令制度中削弱至根除出身、种姓等非个人的因素;b、交换公平:要求履行等价交换原则,交易所得到的东西能大体补偿提供的物或劳动服务。[7]174-1752.慈善义务: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同情感与对普遍的、抽象的人的尊重。它主张每个人不应为自然禀赋负责,而应忽略一切天赋的特殊功绩或遗传获得的心智能力;天赋者与残疾人在“人”的观念面前应一视同仁,“一个人能够像爱他的兄弟一样爱他的同类,而不管他们具有何种能力、智力与价值”[8]220。涂尔干感言这是公平的顶点,是“社会对自然的全面支配与立法,把人世的平等凌驾于与生俱来的生理不平等”*涂尔干这一主张继承了卢梭在《论政治经济》的观点。。据此可知涂尔干关于重塑新社会的财产的权限与分配原则:
1.公平义务与“等价”原则。人们得到的任何财富应当与他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服务或物品等价;若出现不等价的情况,例如薪酬过低、恶意欺诈等,就意味着特权享有的超额价值来自对他人劳动的剥削,集体良知(法律)应该对这种剥削所得采取法律限制、征税、罚没等措施。这一新的财产权原则应当超越市场交易的范围,成为现代财产权的正当基础与共识;其理想的财富分配效果是人们之间的贫富分化全部来自人与人之间为社会提供的服务(劳动)差别,而不是其他与个人无关的给定因素。[7]171这里要再次强调,涂尔干对按劳分配的肯定,不意味着他承认了马克思等人的劳动财产观;根据财产一节综合而言,正是以道德个人主义为基础的集体意识,使个人、劳动与财产这三个概念发生了关联,主张依据个人的服务(劳动)的价值配置财富,而不说是劳动本身天然是衡量财富的尺度。[7]171
2.正义义务与遗产继承制度的废除。在个人本位的现代社会,个人财产应该以“个人”为始终,因此财产的继承,不论是否基于遗嘱,都与个人主义的精神相悖,应该予以严格限制乃至废除,这种对处置权的限制非但没有损害个人的财产权,反倒是强化了它的个人所有性质。[7]170如其所言,遗产继承是古代家族共同占有制的残余,而家族与家庭作为一种总体组织正在瓦解,终究为现代社会所淘汰,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家庭已经不再具有代际传递与继承的功能,相应遗产继承制度也必然随之丧失正当性。所以涂尔干认为,废除这种与个人主义伦理格格不入的制度是顺理成章的,它非但不会扰乱现代社会的道德结构,而且是促成转型。“今天,我们已经不允许一个人通过遗嘱把他在世时获得的头衔爵位或职位遗赠给他人。那为什么财产就可以让渡呢?”[7]172在涂尔干的时代,尽管道德个人主义正在得到各文明民族集体良知的认可,但还没有得到法律的正式确认,因此他呼吁处在转型期的欧洲社会能根据这些原则废除基于亲属关系的遗产继承权,特别是立即废除无遗嘱情况下的亲属顺位继承权。
涂尔干很清楚,废除遗产继承权无疑会遭到当前社会的反抗。首先是根深蒂固的家族风俗的强烈反抗,家庭家族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并没有完全消失,“旧制度从不会完全消失;它们只是退到后台,渐渐销声匿迹。这一制度在历史上曾经举足轻重,很难想象它会彻底绝迹”。[7]173所以,他不要求立即彻底废除继承权,主张有一个渐进铲除的过程,可以允许家长把某些特殊的家族遗物留给子孙,只要不严重影响到正义契约的运行即可。其次,也会遭到社会多数人的反对,因为他们惧怕后代进入社会时陷入一无所有的悲惨境地,但涂尔干相信,如果他的财产制度与分配原则可以得到落实,那当前这种贫富悬殊的社会境况就会很快消失,所以新生个体面对的社会环境大体是公平的。[7]173
至于如何对待个人遗产的处置问题,这是涂尔干理想的社会形态里比较棘手的问题,实际上他也没有规划得特别清晰。首先是继承资格与分配任务应该由职业团体承担,相对于日薄西山的家庭与“愚蠢笨拙、挥霍无度”的国家,涂尔干认为,职业团体的规模更有限,更能从细节上清楚事实,也具备处理特殊利益的能力,可以延伸到全国各地,掌握区域差异与地方习惯,完全可以在经济领域成为家族的替代者。[7]174其次,所得遗产应该定期分配给社会成员,至少把劳动必需品分配给劳动者,以确保起点的公平与生产生活的必需。[7]173第三,尽管在《社会学教程》中这份建议他未曾明确提到对弱势群体的救助问题,但鉴于人道宗教另一项基础性义务“慈善义务”的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像爱他的兄弟一样爱他的同类,而不管他们具有何种能力、智力与价值”,职业团体所得的遗产应该分配给各类弱势群体,以维护其为人的基本尊严与权利。
3.慈善义务决定了每个人都对同胞负有基本的道德义务,在保证自我持存的情况下,对其他同胞的生命与尊严负有不同程度的义务,即是说,个人的财产负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义务,这就为累进制税与慈善捐助提供了学理依据。尽管涂尔干的时代慈善义务尚未形成浓厚的社会氛围,但他坚信,真正意义的慈善精神一定成为未来社会的集体良知与人们行动的准则,进而成为严格的义务与新社会制度的源泉。[7]174-175事实上,日后西方社会的发展也证实了涂尔干的预见。
[1] 涂尔干.自杀论[M]. 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71-275.
[2]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 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
[3] 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理论的逻辑(第二卷)[M]. 夏光,戴胜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07.
[4] 安东尼·吉登斯.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M].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28-129.
[5] Durkheim & Emile.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M].Translated by W.D.Halls.New York:Free Press,1984.
[6]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M].李鲁宁,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84.
[7] 涂尔干.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渠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 Durkheim & Emile.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ivic Morals[M].Translated by Cornelia Brookfiel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