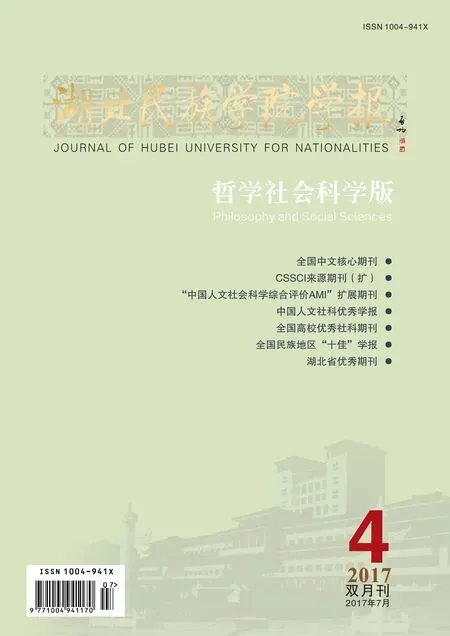亲属关系研究的变革与困局
——评萨林斯《亲属关系的是与非》
刘 倩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一、亲属关系研究的生物性—文化性之争与本体论的转向
人类学发端于对亲属关系(kinship)的关注,亲属关系人类学和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相比,被视为更基础的研究,几乎每一个进行过田野调查并撰写民族志的人类学家,在自己的作品中都要首先阐明当地民族的亲属关系,这是一切社会关系,特别是前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的基础。而今,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也在晚年开始深入这一研究领域,于2013年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亲属关系的是与非》(What Kinship Is — And Is Not),试图重新定义“亲属”,同时扫清人类学研究传统中对于亲属关系的谬见。萨林斯在本书前言中开宗明义提出——“亲属关系是文化性的,不是生物性的”[1]1。可见,萨林斯论述的起点是亲属关系研究领域著名的“生物性—文化性”之争。
历史上,亲属关系人类学受生物学的影响极深,难以摆脱其束缚。早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中,就有这样的分析:“亲属关系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血缘关系;第二种,姻亲关系……在人所可能设计的任何制度形式之下,都存在着一个自然的系统……任何一种形式,由于都建立在自然的规则之上,所以它们既是普世的,又是永恒的。”[2]在这里,摩尔根认为亲属关系的规则是“自然的”“普世的”“永恒的”。近代,亲属关系研究领域的经典理论主要有“一纵一横”两种[3],共同奠定了系谱理论的基础。其中,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单系血统理论,将生殖产生的亲子关系“父—母—子”和子女间关系视为亲属关系的核心和来源,认为所有社会的亲属关系都是从这个核心家庭扩展和延伸出去的,通过生与被生的血亲关系联系起来的,最终形成“世系群”[4]。在这里,核心亲子关系与系谱的纵向传递是基本规则,而按照父系还是母系传递则是每个社会的独特规定。而列维斯特劳斯的联姻理论则认为,社会集团之间制度性地交换女人构成婚姻的关系是亲属关系的核心,亲属关系的网络是由法律与习俗规定的配偶的血亲和血亲的配偶(统称为姻亲)在空间上横向编织起来的。列维斯特劳斯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写道:“从最普遍的观点出发,血亲之间的性禁忌表达了从血缘这一自然事实向联姻这一文化事实的过渡。”[5]这些人类学学科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类作为同一个物种具有同样的身体和生殖系统,人类纷繁多样的亲属制度,必然是每一社会的文化依据某种先在的自然事实或生物事实来设计的。
然而从施耐德开始,人类学家开始对这种生物/文化的两分提出了质疑。施耐德指出:欧洲文化中流行的“血浓于水”的论断(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毕竟是一个欧洲文化的命题,而不只是对生物学关系的承认,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命题到底附加了哪些文化因素[6]。简而言之,我们在刻意划分社会性和生物性的时候,欧洲以外的民族心目中究竟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先在的生物事实(例如“血缘”)?抑或这只是人类学家臆想出来的假设?蔡华也曾明确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则或立场在知识论层面画地为牢,把亲属关系人类学锚定在人的生物属性上?”[7]蔡华和施耐德的共同点是,认为和人类学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欧洲现代生物学,诞生于19世纪,在此之前的社会以及西方以外的社会,是没有现代生物学知识的,各个独立生存的民族无法达到同样的生物学水平,更不存在一致的对身体的认知。在人类的观念中,既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土著生物学知识(folk biology),那种“自然的”“普遍的”可以作为亲属关系坚实基础的生物学“事实”便并不存在。蔡华认为,我们应该研究的,是作为每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性解释的“身体再现系统”*蔡华认为人类有文化和社会,并且文化对生殖行为的逻辑、机理和因果关系都有自身的解释,与对动植物的繁衍机理解释不同,构成了一个社会关于人口再生产的认知和观念,被此社会信以为真、深信不疑,就是蔡华所提出的“身体再现系统”。身体再现系统解释了本文化中两性在人口繁衍中的作用,解释了后代从两性身体继承并传递给自身后代的同一性物质,并且每一个社会都有规定,这种物质通过双系或单系传递,在世代间无限传递或者传递一定世代之后自动消失,即若干代以后不再被视为亲属;同时,具有同一性物质的亲属之间绝对不能发生性关系。“身体再现系统”完全是文化性的,因此据此认定的亲属也完全是文化性的,被更确切地称为“社会血亲”。对于蔡华的具体观点,可参见蔡华.人思之人[M] .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可见,施耐德和蔡华都是从人类社会不同的认知体系来否认亲属关系的生物性、论证亲属关系的文化性的。
这场亲属关系的“生物性—文化性”之争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萨林斯以其为论述起点并贯穿于全书,试图终结这个世纪争论,这是他本书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他的理论野心并不止步于此。萨林斯的目光,始终紧跟着国际人类学界最新的理论动向。
从20世纪末开始,整个人类学界迎来了一场“本体论”的转向(抑或称之为转向“本体论”),美国人类学学会2013年年会(AAA)的讨论是其集中体现,Donald Davidson,John D. Kelly,Viveiro de Castro Eduardo是代表人物。这一趋势主张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关怀都不再纠结于对他者文化解释或翻译是否可能的“认识论”问题,而是“转向事物本身”,认为“差异性”和“他者性”是“本体论”层面的,而不仅仅是认识论层面的。这一转向主张,文化的独特性不是人类的语言、知识和概念图式等“表征”的不同,而是每个民族的整体世界观、宇宙观、人观存在着根本的不同,“本体论”是多样的和复数的(ontologies)[8]。在这场人类学本体论的转向大潮中,亲属关系研究也概莫能外,这决定了亲属研究再也不能将视野局限于每个民族的生殖解释和土著生物学知识,而要关注每个民族中关于人的终极来源、人的生命构成、人的合法性、人的再现性与传承性等一系列“人之为人”的问题,这涉及到人与同代人的关系、人与前代人的关系、人与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非人的关系(针对某些视其他物种也为亲属的民族)、人与神圣力量(主宰生命之神)的关系、人与精灵(鬼、祖灵)的关系、人类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关系等等;而人类世界与精灵世界的关系、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的关系、生活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关系,又涉及到“世界是如何构成的”“宇宙是如何运转的”等一系列宏大问题。这场本体论的转向,巴西人类学家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Viveiro de Castro Eduardo)是旗手之一,他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人观和世界观,发现当地民族将人、其他特定物种、死者灵魂、精灵等视为具有同样主体性和灵性的存在,同一灵魂可以拥有不同躯体,人和其他物种可以互相变身,也可以互称亲属[9]。卡斯特罗复兴了人类学历史悠久的泛灵论(animism),萨林斯的这本专著就大篇幅地引用和对话了卡斯特罗的理论,表明了他希望在本体论层面彻底变革亲属关系研究的野心[1]58-60。在具体操作中,萨林斯抱着兼容并蓄的心态,从前辈学者和同时代学者中汲取营养,试图重建亲属关系的普遍理论,走出一条变革的新路。接下来,笔者将详细论述萨林斯是如何一步步迈向自己的目标的。
二、重新建立亲属关系理论体系:提倡实践论、互渗论与泛灵论
(一)萨林斯对社会建构理论的吸收——实践论
萨林斯首先梳理了亲属关系研究领域流行的社会建构论(Constructivism),这一理论质疑了两性生殖是亲属关系的惟一来源。
根据符号的建构和文化的不同,人们对于男女双方在生殖中的贡献的认定各不相同,有的文化认为是孤雌生殖,将妇女视为媒介,否定父亲的作用,而最极端的情况是将两者的贡献都否定。在古印度的摩奴法典中,母亲被认为是一块土地,无论什么种子撒在上面都能长出植物。在古希腊作家艾斯克勒斯的剧作《复仇女神》中,奥莱斯特并不被认为是他母亲克吕泰墨斯特拉的亲属,众神认为她只是他的保姆。[1]3-4
在很多社会,第三方力量被认为是生殖行为中必须的成分和生命的来源,如祖先、神、澳大利亚土著神话中黄金时代的精灵,以及从被打败的敌人中获取的能力……仅有男女是不足以产生孩子的。[1]4进而,萨林斯受社会建构论的启发,证明了在很多社会,生殖以外的行为和实践同样能够产生亲属,并且,有的社会并没有在由生殖构成的亲属和由实践构成的亲属之间作出特意区分,往往是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整体亲属关系。在阿拉斯加北斜坡的纽皮特人,人们用死去的人的名字给孩子命名,被命名者自动成为死者家庭的成员。一个纽皮特人可能会拥有四个到五个名字和随之而来的家庭[1]5。在新几内亚的内比尔耶峡谷,亲属关系,无论是基于生殖,还是基于社会实践,都是被同一种介质传递的——“油脂”或“脂肪”,“这是生命体的基础构成材料”。在新几内亚高地,“油脂”被认为通过部落成员的劳动,从人体流入土地、芋头、猪和其他食物,最后又通过吃这一行为流回人体[1]5。在新英格兰,一个祖先的所有后代(通常也耕种在同一块土地上)被认为是“共同的兄弟”,不仅因为他们之间享有共同的生物起源物质,而且因为他们跟土地和产出物资也拥有共同起源物质[1]7。可见,通过神、抚育、赐名、共同拥有土地和共同劳动实践等途径,亲属关系都可以建立起来。
第三,萨林斯认为,后天的实践行为不仅能够建立亲属关系,还可以解除亲属关系。格林兰岛人如果认为亲属不令自己满意,可以解除这种亲属关系。人们并不被严格的血亲规则所限制,而是可以选择大部分亲属……因纽特的亲属体系是高度实践性的,人们之间业已存在的亲属关系是不稳定的:一直会被事件改变并且可以相互谈判。[1]9
(二)萨林斯对亲属关系的再定义——存在的相互性
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萨林斯将“亲属系统”定义为:主体间多种形式的互渗(participation),存在的相互性(mutuality of being)的网络[1]20。萨林斯说:“总的来讲,亲属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属于彼此,是彼此的组成部分,彼此共存,他们的生命是联结在一起并且相互依赖的。”[1]21“民族志材料已经反复展示了亲属关系在身体、情感、经验各方面建立了跨个人的联结。”[1]21
接下来,萨林斯列举了一系列民族志材料和人类学家的分析, 这些例证和前文中社会建构论的案例一起,丰富了亲属之间“存在的相互性”的表现形式。毛利人有一个说法:“你生于我之中,我生于你之中。”毛利人的人称代词“我”除了指称自己,还可以指称自己所在的整个亲属群体,包括过去的祖先和现在的亲属,包括亲属世系的整体和其中著名的人物[1]21。毛利人就是这样,将亲属团体的历史视为他自己的,忠于他的国家并为此战斗以保存祖先的传统,这个团体是不可破坏的同一的“我”,存活于整体的每一部分。[1]35马达加斯加的卡热博拉人(Karembola)认为兄弟和姐妹是一个人,他们拥有(own)彼此[1]23。血亲互相占据了对方人格的重要部分甚至全部。楚克人(Trukese)认为源自同一条独木舟的即为兄弟,这是在说,那些在危机四伏的大海上彼此支持的人们就是兄弟,他们“分享了彼此的存在”(shared existenc)[1]30。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也会因为共同经历了一场在冬日冰海上艰难的打猎而选择将彼此纳入亲属的范围。[1]31总之,共享某种同一性物质(油脂)、共享某一种精神存在(神的力量、祖先灵魂、姓名、集体记忆、部落历史)以及共同参与某一种实践(劳作、冒险、狩猎),都可以彼此成为亲属。
(三)萨林斯对“存在”意义的更新——“存在”与“互渗”
萨林斯仔细辨析自己使用的两个概念——“存在”与“互渗”,通过其复杂的行文,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首先,“存在”(being)这个观念突破了孤立的身体观,不把人只视为肉体(body)和实体(substance)的存在,而将人视为物质(substance)、意识(intention)、实践(action)和关系(relations)的存在;其次,“存在”的概念是一种主体间(intersubjective)的共在(co-presence);第三,存在先于本质(essentialism),萨林斯认为个体通过在一生中的实践、不断的与他人的符号互动行为(symbolic interaction),最终实现了亲属关系的本质——存在的相互性。[1]31-33
“互渗” (participation)这一概念来自于列维布留尔提出的原始思维的“互渗律”。互渗律意为思维既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区别、又无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这一特征乃成为原始社会法术与图腾崇拜的思维基础和认识前提。萨林斯从这位前辈学者那里借用“互渗”,不是在思维层面使用,而是在本体论层面使用,意为存在的分享性(shared existence)。这是一种对边界分明的存在状态的否认,对个人与他者截然对立的否认。萨林斯引用列维布留尔的话说,“互渗并不是一种建立在个体失去或保留其身份上的融合,而是互渗构成了存在本身。个体存在之时,互渗就已经是其固有的组成部分”[1]34。或者说,亲属关系不是从外部附加给边界清晰的个体的,亲属关系应该被视为个体自我的内在组成部分[1]22。同时,亲属关系是个体与他者、个体与整体之间的“融合”和“彼此占有”。
(四)亲属关系的影响力和责任——一种动态的分析
萨林斯认为,亲属关系具有激发社会行动的动力(motivation)的作用,这体现在它的影响力(effect)上,也就是人们相信发生在亲属身上的事,同样也会发生在个体身上,反之亦然,同样的遭遇(experience)在人们之间具有传递性[1]45。在世界各地的葬礼,人们往往通过脱掉衣服、不洗澡、不工作以及其他脱离日常生活的仪式行为,来象征性地表明自我断绝(self-mutilation)以及和死者一起死去,以防止死亡的命运真正地发生在自己身上[1]46。亲属关系的动力作用,还体现在亲属的责任(responsibility)上,也就是亲属对彼此的错误行为负有赔偿的责任,对彼此的被伤害负有报复的责任[1]44。报复和赔偿的对象都是亲属集团而非某个个体,这也体现出亲属群体对个体负有的责任。
(五)亲属关系本体论的转向——泛灵论
通过对亲属的主体间性、相互影响性和共在性的考察,萨林斯试图更进一步,将亲属关系上升到本体论(ontology)的高度。他大篇幅引用巴西人类学家卡斯特罗(Viveiro de Castro Eduardo) 的观点,认为亲属关系、礼物交换、巫术都是泛灵论(animistic)的表现形式——与现代社会将人与物做严格区分不同,土著民族将所有的人和物都看作具有灵性和影响力的主体(subjects),通过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对彼此可以施加影响*萨林斯还曾引用卡斯特罗的话:“如果人是不朽的,那么,可以与宇宙混为一体,得以长存。但人既是必死的,社会就必须与外在于它的某些东西联结——并且是社会性的联结。”对于卡斯特罗的具体观点阐述,可见Viveiro de Castro Eduardo.The Gift and the Given:Three Nano-Essays on Kinship and Magic[C]∥Kinship and Beyond:The Genealogial Model Reconsidered.edited by Sandra C.Bamford and James Leach.New York:Berghahn,2009:237-268.。亲属关系、礼物交换、巫术这三种社会关系常常互相包含。[1]58
莫斯的经典研究——毛利人的礼物交换,发现毛利人的“礼物之灵”和人的自我具有紧密关系,礼物之灵可以进入人的自我,人在给出礼物的同时也交出了一部分自我。没有履行回礼义务的人被认为“偷走了送礼者的一点生命”。人们通过礼物的流通进入了彼此的生命,建立了同伴关系,而这种主体间性的“互渗”也是亲属关系的特征。人们在进行巫术仪式时,通过命令、祈祷、祈求、取悦,在自己的思想和有灵性的主体之间建立了一种共同的意向性的联结,而黑魔法可以被视为一种亲属关系的反面——没有支持、滋养他人的存在而是伤害、消耗了他人的存在[1]58-59。所以亲属关系、礼物流通、巫术这三者之间互相包含了对方的元素,具有某种同构性。这种建立在泛灵论上的对影响力(effect)的信奉,带有神秘的色彩,和现代商品经济形成了鲜明对照——相对于商品经济对一切人的物化,泛灵论将一切物看作有灵性的主体,人和物之间也可以建立跨物种的亲属关系——“白薯是我们的兄弟,在夜里看不见的地方漫游,美洲虎脱掉他动物的衣服,原来是我们吃人的姻亲……”[1]60
综上所述,萨林斯试图用实践论、互渗论和泛灵论来重新解释亲属关系。
三、集中批判生殖中心论与系谱法
萨林斯在定义了亲属关系是文化性(存在的相互性)之后,又试图从反面对此命题加以巩固,提出亲属关系不是生物性的,力争对影响亲属关系理论的生物学阴影进行彻底扫除,而其手段就是集中批判生殖中心论。
萨林斯认为,社会建构论者否认了生殖行为是亲属关系的惟一来源,认为后天的实践行为也可以建构亲属关系,但是,在人类学亲属关系研究领域,依然存在着这样的思想:“真正的”亲属关系或者说亲属关系的“典范”仍然是由生殖行为建立的——就连“血亲”这个概念都带有明显的生殖色彩。较大的世系族是从生殖构成的亲子关系和核心家庭扩展而来[1]63,而由后天的实践构成的亲属只能被视为“模拟的”亲属、“想象的”的亲属,或者“隐喻的”亲属[1]65。萨林斯对此进行了批判:
(一)社会实践构成的亲属关系在时间上可能先于生殖构成的亲属关系而存在
在新几内亚峡谷的例子中,联姻行为和生殖行为发生之前,耕种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居民和后代因为对“油脂”的摄入已经被视为亲属了。萨林斯评论说,生殖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人类受孕和孕育的过程,因为所有的亲属关系都来自于土地和共同劳动;并且,在生殖行为发生之前,所谓的“扩展的”亲属网络已经先于核心家庭而存在了[1]68,核心家庭并不具有时间上的先在位置,亲属网络也并不是从核心家庭延伸形成的。
(二) 生殖行为是嵌入(embedded)在已有的社会制度之中的
萨林斯说,将生殖产生的亲属关系视为基础的先天的亲属关系,其他的亲属关系被视为次级的模拟的亲属关系,其实是将生育者及其后代看作了脱离其社会背景的抽象的“人”。但是,“我们涉及的并不是一对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上独自产子的夫妇。”[1]75在印度尼西亚东部,虽然是父系制,但是娶舅舅的女儿(姑舅表婚)是通行的婚姻制度,并且妻子一方家庭要比丈夫一方家庭社会地位高。这个社会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是按照不对称的结构组织起来的,不对称的婚姻制度是社会运转的轴心。男方家的财富和生命都被视为女方家所赐予的。母亲的“血”因此被认为是人口再生产中传递的最重要物质,也被视为权力和财富的再生产所传递的物质。因为己身的母亲与父亲的母亲是来自于同一个家族,所以己身与父亲也被视为同一血缘,血缘按照母系传承的同时并没有违反父系继嗣原则。同时人们更热衷于谈论母亲在生殖中的作用,认为母方是血的终极来源。[1]77-78在这里,血缘的传承不仅仅有关于两个异性个体的生殖,更是体现了父方和母方两个亲属集团的不对称关系,因此跟更广阔的社会亲属网络(the universe of kin)联系起来,嵌入到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制度中。我们一贯认为的亲属网络是从抽象的个人和核心家庭延出来的观点在逻辑上并不成立,生殖行为和核心家庭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先在位置。
(三)生殖行为是对完全的存在的相互性的隐喻
萨林斯对“生殖是一种隐喻和象征”的论证颇为曲折,他是从亲属关系的称谓来入手的。在本书中,萨林斯多次提到亲属称谓的“假借”问题:在非洲有记录称舅舅被称为“男性妈妈”。马达加斯加人将兄弟和姐妹视为同一类人,一个男人可以声称生育了他姐妹的儿子:“我是他的妈妈。他是我的孩子。他从我的肚子里生出来,靠我养活,向我要奶吃。”同样的,一个女人也可以声称是她兄弟的孩子的父亲[1]5。在北美欧及布威族,被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意味着也同样得到了这个人的人格、社会身份和全部亲属关系,如果一个男孩被以一个女性的名字命名,那么这个女性的父母同样可以称这个男孩为“女儿”[1]70。新几内亚人将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人视为这块土地的后代,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兄弟”。[1]72
萨林斯由此认为,在有些社会,所谓的父亲、母亲、子女、兄弟姐妹的称谓也许最初是基于生殖行为,但是随着文化的高度发展渐渐已经并不是基于生物上的联系(biological),而是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表达了一种共生的社会关系(sociological),一种在日常共同生活的实践中形成的“完全的存在的相互性”(the full mutuality of being)[1]73。核心亲属关系称谓提供了一套语汇和模型,人们用来描述最紧密的社会关系;生殖行为因其本身的极端私密性,被拿来作为一种象征或隐喻(metaphor)[1]73。这样,人们通常认为的“文化实践所建构的亲属关系是对生殖产生的亲属关系的模拟”的命题就被反转过来,生殖才是对密切的实践所形成的“完全的存在的相互性”的隐喻。综合以上三点,萨林斯通过否认生殖行为是产生亲属关系的时间起点和逻辑起点,否认亲子关系在产生亲属关系上的优先位置,证明生殖行为是嵌入在已有的社会网络之中,生殖行为是对完全的存在的相互性的隐喻,认为自己彻底扫清了生物学在亲属关系研究领域的阴影,由此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亲属关系是文化的,而非生物的。按照萨林斯的逻辑,以生与被生为纵向纽带的系谱法也随着对生殖中心论的否定而大大失去效力。同时,萨林斯又再一次巩固了自己对于“亲属是存在的相互性”的定义。
四、总结——萨林斯的变革与困局
(一)人观与亲属观的双重变革
萨林斯试图用“存在的相互性”来超越传统的生物—文化两分法,认为所有文化的所有亲属,都是从本质上参与了彼此存在的人们,力图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关于亲属关系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这一理论在更新亲属观的同时,也更新了“人观”。萨林斯引用人类学家罗杰·巴斯替德(Roger Bastide)的观点,“美拉尼西亚人将自己看作参与关系的一个节点;他外在于他自身更甚于内在于他自身”,个体融入在宗族、图腾部落、大自然、伙伴群体等更大的整体之中。而西方的传教士带来了孤立的身体观,认为个体是由身体的边界所划定的。巴斯替德提出在美拉尼西亚社会,个体的自我(self) 是分离的、弥散的,自我分布在他者之中,正如他者也渗入了自我。萨林斯就此批判了西方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和“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c)[1]27,认为这种思维模式将亲属关系看作是原子化的个体之间的联结。基于对这种原子化的“人观”和边界清晰的身体观的批判,萨林斯提出了存在的相互性学说,认为人的存在是多元关系的集合,而亲属关系的存在是不同个体之间超越边界的“互渗”。更进一步说,亲属关系涉及到人与同代人的关系、人与前代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其他生物的关系等等。
(二)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双重变革
萨林斯从本体论上重新定义了人与亲属,同时,实践论、互渗论和泛灵论的提出,以及对生殖中心论的反对也预示着我们今后不可以再用单一的系谱法研究亲属关系。那种以“ego”为中心,以婚姻关系和生殖关系做连接纽带进行绘图的系谱法也不再适用于解释复杂社会中的亲属关系。萨林斯带给今后亲属研究的启示是:首先,我们要像萨林斯一样,在不同社会中考察不同的亲属认定标准,比如,神、抚育、赐名、共同拥有土地和共同劳动实践、共同记忆等,这些亲属认定标准可能与血缘系谱法的认定标准在同一个社会中并存、互补,也有可能互斥,具体情况应该具体考察。其次,我们应该时刻注意着不能将亲属关系与其他社会制度过分剥离开来进行抽象的几何式研究,而应该研究亲属关系所嵌入的政治经济制度。“亲属”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多元性,我们更应该将“亲属”和其他概念结合起来进行多元的分析。例如,王晓慧对1956年民族识别前海南五指山杞黎人的生产生活组织——合亩制进行过研究。合亩制意为“一起劳动”“大家的田”。作者认为作为黎族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合亩制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血亲联合制、血亲和姻亲联合制、血亲+外来户(入祖公)、血亲+外来户(不入祖公)。“入祖公”意味着来投奔的外来户抛弃原来的社会血亲身份,加入到合亩的血亲身份中,年龄辈分与亩头的子女相同,与后者是“兄弟姐妹”的关系,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合亩制度兼具生产管理、产品分配、政治庇护、社会调解等多种功能,亩头和亩众之间形成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和亲属关系,并且各种关系紧密交织在一起,分析合亩制度不可能只进行对亲属关系的分析。[10]
(三)泛灵论的启示与延伸
萨林斯对亲属关系神秘性和影响力(effect)的研究,认为亲属关系具有和礼物、巫术相类似的泛灵论的特征。这一观点启发我们在研究亲属关系以及人观时,要将其神圣性和世俗性结合起来,并且将亲属关系纳入到整个社会的信仰体系中进行研究。例如,张琪在《宇宙秩序中的人与精灵——白裤瑶人的宗教生活》中写道,在白裤瑶看来,父母提供给孩子身体,“瓦王”作为生命来源之神将灵魂与“花”(生命活力物质)从天门投入到母腹之中,与身体结合,才形成完整的人[11]40。人死后,一个叫做“瓦布”的地下的神派阴差带走他的灵魂。灵魂一分为三,第一个灵魂走过阴间的360个垌场,通过天门到达天上,第二个灵魂在坟墓周围,第三个灵魂附在家里的牌位上。祖先死的前几年,人们相信祖先的灵魂会化作蚂蚱和白头翁回来看望子孙。如果祖先在阴间过得窘迫,耕种困难,缺衣少食,或者坟墓毁坏,它们就会用制造惊吓、噩梦、致人掉魂的方式来警告家人。家人必须进行“补粮”和“赎魂”仪式,而人的灵魂的回归可以用蜘蛛作为化身。瓦王投放的灵魂和“花”有时候会先降落到祖先坟里,由祖先暂时看护和保管。一对夫妻久婚不育,就要请巫师进行架桥引线仪式,将生命所必须的物质牵引至家中[11]193-201。可见,人们认为死去的祖先依然跟活人的世界息息相关,祖先关心并影响着后代的生活,后代也关心祖先在另一个世界的生存状况。而神、灵魂、“花”、祖灵、其他灵性生物以千丝万缕的关系交织在一起。整个宇宙的构成和运转并非是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世界中心主义的,而赋予了“看不见的”世界和其他生物以同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泛灵论的亲属观在中国西南的很多少数民族中都有体现,例如水族、布依族、黎族等。
(四)萨林斯变革后的亲属关系理论体系是否具有普遍解释力?
在建立普遍理论方面,首先,萨林斯对“kinship”的定义,所谓“存在的相互性”,是一个内涵极窄,而外延极宽的定义。他的定义无限地扩大了血亲的外延,只要参与和分享了对方的存在就是亲属,这样,亲属无法与其他社会联系区分出来,人们很难从任何一个社会中有效地辨认亲属。在本书中,萨林斯列举的一系列例证,都可以在其中辨别出其他社会组织的影子:图腾、部落联盟……萨林斯也列举了现代社会的一系列表示关系的名词:员工、顾客、队友、同学……[1]28这些组织和关系中的人们,多多少少都分享并参与了彼此的存在(being),但是,他们显然不被视为亲属。按照萨林斯的定义,我们无法在一个人群中将亲属有效地辨认出来。而过分地扩大这个概念,无异于取消这个概念,使得“亲属”无法成为人类学领域有效的分析工具。正如迈克尔·G·佩勒兹所说,从19世纪就开始长久存在的“人类学与亲属关系既浪漫又极为模棱两可的关系”,“其精确的意义连最有耐心、最智慧的读者也无从得知”。[12]
第二,萨林斯用“存在的相互性”来作为亲属认定的标准,认为“存在的相互性”涵盖了民族志中各地血亲关系构成的多样性。共享某种同一性物质(油脂)、共享某一种精神存在(神的力量、祖先灵魂、姓名、集体记忆、部落历史)以及共同参与某一种实践(劳作、冒险、狩猎),都可以彼此互为亲属。这种认定标准看似统一了民族志中纷繁复杂的亲属认定标准,“存在的相互性”似乎也能解释所有共享性,但是,在逻辑推演上会导致一个必然的困境——这种共享性的平均主义无法将近亲(close kin)和远亲区分开来,对于各国法律上复杂的亲等计算法和世代计算法没有解释力,无法将每一个个体与其他个体区分开来,无法确定个体在亲属团体内的独特地位和身份。
而世代和亲等的确定,在很多社会中对于亲属关系的权利和义务规定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是系谱法一直作为亲属关系研究主宰性方法的原因。例如,中国封建社会是由父系家族组成的社会,以父宗为重。“准五服以制罪”是指对亲属之间的互相犯罪,根据五种丧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来定罪量刑。它在刑法方面的适用原则是: 亲属相犯,以卑犯尊者,处罚依次重于常人,服制越近,处罚越重;若以尊犯卑,则处罚渐轻于常人,服制越近,处罚越轻[13]。可见,如果萨林斯的亲属认定标准无法区分亲等,将会对大量社会现象失去解释力。
第三,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共同居住、共同劳动、互相照料等行为,萨林斯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些可能是由严格的社会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利和义务规定的,而不是随意性的。在很多社会,人们不是因为共同生活才成为亲属,而是因为身为亲属才共同生活,而这些都需要我们根据具体的社会进行仔细的辨析,否则就会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
第四,“kinship”的英语原义仅仅指血亲(relative by blood),并不包含姻亲(relative by marriage)。萨林斯试图用“存在的相互性”来定义“kinship”,并没有分别定义血亲和姻亲,忽视了这一领域至关重要的问题:血亲的产生之前,人类的交媾和婚配是有着严格的性禁忌的,或称乱伦禁忌(incest),也就是人类对能够选择的交媾和婚配对象范围有着否定性的要求。乱伦禁忌是在所有社会中都广泛存在的。这一禁忌也并非是生物学上的意义(动物之间并没有性禁忌),而是违反了人伦大忌,乱伦的人不被视为社会承认的“人”,形同禽兽。现代各国法律也都禁止了一定亲等内的血亲结婚。乱伦禁忌就此划定了亲属系谱在横向上的范围。萨林斯没有意识到,无论多么密切参与了彼此的存在,一些特定的人是永远禁止成为姻亲,也无法生产新的合法的血亲关系的。这也是用“存在的相互性”来定义亲属关系的又一问题所在:无法用明确的否定性原则来规定其概念外延,即,人与人之间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不具有“存在的相互性”?
(五)完全放弃生殖中心说与系谱法,何去何从
在否认亲属关系的生物学理解方面,我们要肯定萨林斯想让人类学和科学主义的生物学了结关系的努力,但是,认为在有些社会,“生殖行为是一种对完全的存在的相互性的隐喻”是矫枉过正了。萨林斯用亲属称谓的假借来论证“生殖行为是一种隐喻”,以及亲属之间的纽带并非生与被生的关系,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如果说生殖行为是一种隐喻和象征,是不同民族基于自己文化的建构,那么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偏偏选择生殖行为而非其他行为作为这种所谓的“完全的存在的相互性”的象征符号,为什么不同民族会不约而同地发明“母亲”“父亲”“儿子”“女儿”这些概念。真正原因只能是,这些概念不是和所谓的“存在的相互性”,而是和交媾、生殖以及对于人口再生产的机理的认识密切相关的。所谓母亲是生育己身的人,所谓父亲是和母亲有性关系并由此产生己身的人。虽然萨林斯证明了有的民族在生殖观念上持有的是“孤雌生殖”,否认父亲在生殖中的作用,但是萨林斯并没有给出民族志的例子,证明某个民族将父母双方在生殖中的作用同时否定。我们必须承认,很多社会存在干亲、义亲等虚拟亲属关系(fake kinship),但是不能就此彻底取消生殖行为的实在性,这种将生殖行为“隐喻化”的努力是难以成立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先民们都会慢慢注意到人口繁衍继嗣与交媾、孕育之间的必然关系,并形成自身的解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完全忽视生殖和在此基础上的系谱的重要作用,而现今存在的各种法律对亲等的规定也证明人们对于系谱的重视并非是一个可以由人类学家任意存废的事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可能完全放弃系谱法的原因。
在方法上,“存在的相互性”或者说“关系论”与系谱法相比,缺乏在分析上的精确性。如果萨林斯将“存在的相互性”在程度上加以区分,从“部分的不完全的相互性”到“全部的完全的存在的相互性”,甚至是一个连续统,其划分的依据是什么?这和传统亲属关系研究以己身(ego)为中心,以联姻为横向纽带、以生殖为纵向纽带、以代际为计数,以权利和责任关系为基本变量的系谱法相比,增加了难度且没有实际的可行性。可见,即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扬弃萨林斯的理论,也不能完全放弃系谱法的使用,而可以选择将系谱法和其他研究亲属的方法结合起来。如前文所说,“亲属”的关系应该是多元的,亲属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是多元的。
总之,萨林斯对于亲属关系的本质是“存在的相互性”的判断,对于亲属关系实践论、互渗论和泛灵论的强调,对于生殖中心论和
系谱法的批判,在更新亲属关系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上是有深刻意义的,但是在建立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方面是不完备的,在辨认亲属关系方面欠缺区分度,在解释亲属的权利与义务方面也显得说服力不足。萨林斯力图彻底变革原有的亲属关系研究,结果在变革后依然面临困局,更一步的探索只能依赖后来人进行了。
[1] Marshall Sahlins.What Kinship Is — And Is Not[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
[2] Morgan Lewis H.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the Human Family[M].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7:11.
[3] 蔡华.纳人亲属制度的结构与婚姻家庭悖论的终结[C]∥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北京:三联书店,2009:259-289.
[4] (英)A.R.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M].潘姣,王贤海,刘文远,知寒,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68-75.
[5] Lévi-Strauss Claude.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M].Boston:Beacon Press,1969:30.
[6] Schneider, David Murray.A critique of the study of kinship[M].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4:194.
[7] 蔡华.人思之人[M] .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1.
[8] 朱晓阳. 地势、 民族志和 “本体论转向” 的人类学[J]. 思想战线,2015 (5):1-10.
[9] Viveiros de Castro, Eduardo.Cosmological perspectivism in Amazonia and elsewhere:Four lectures given in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Anthrop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February-March 1998[J/OL].HAU Masterclass Series,2012(1).http://haubooks.org/cosmological-perspectivism-in-amazonia/.2017-10-30
[10] 王晓慧.人类学视角下的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研究——以五指山杞黎的合亩为例[J].青年研究,2012(2):69-82.
[11] 张琪.宇宙秩序中的人与精灵——白裤瑶人的宗教生活[D].北京:北京大学,2016.
[12] (美)迈克尔·G·佩勒兹,王天玉,周云水.20世纪晚期人类学的亲属研究[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学版,2010(1):38-52.
[13] 焦阳宁.探析唐律中的服制[J].法学研究, 2014(18):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