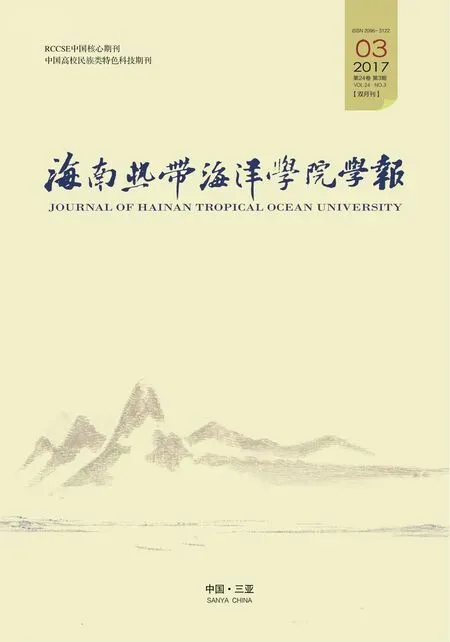敦煌民间文学中的民族观探析
——以变文为中心
罗尚荣,刘 洁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南昌 330013)
敦煌民间文学中的民族观探析
——以变文为中心
罗尚荣,刘 洁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南昌 330013)
敦煌变文作为地方性民间文学的代表,体现出敦煌百姓的审美特性和思想倾向。和传统的中原文化相比,敦煌变文由于所处年代,地域和受众的区别,蕴含着独特的民族观。其流民意识,边域意识及民间意识都不同于前代后世的中原文化。其中差别体现出在国力强弱,地域内外和执笔者文学素养等不同观照角度下的人文内涵。
敦煌变文;边域;流民;意识;民族观
民间文学即是由民间百姓创造,由底层百姓中文学修养不高的人执笔,主要是反映民间百姓的审美趣味,满足民间娱乐需求的文学作品。因为“观众的心理需要还有更大的对象化成果,那就是由第一度对象化成果(艺术的门类和样式)和第二度对象化成果(艺术的表现手段)所积累和塑造的审美心理习惯,也可称为审美心理定式。”[1]敦煌变文能够被作为成品记载并保存下来,作为民间文学的代表作,无疑它是敦煌百姓长期审美经验和审美惯性作用下的产物,它体现出来的文学审美趣味不仅是变文创作者或记载者,还应拓展成为民族性的,地域性的审美定式。
敦煌变文中除了佛教相关变文以外,有很多变文的情节内容延续的是之前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这些故事情节在敦煌变文中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敦煌人民带有特有的地域民间特色的解读。王重民先生对此也说:“讲述我国历史故事的变文,虽说写的是古代人物,但是通过了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把他们典型化,已经是现实主义的写实文学了,所以具有极充沛的思想性。”[2]所以敦煌变文虽然语言浅俗,部分情节构建荒诞,但是其中蕴含的边境人民的民族观念是最真实的。
明清小说中也大量地翻新了这些历史传说故事。不同时代的传承中,这些故事不复前貌,衍生出新的情节。从敦煌变文到明清小说的演变中,不仅能够解读出时代赋予文学新的内涵,包括在国力强弱不同的情况下,中原地区和边境地区的文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和执笔者文学修养也有一定的关联。
一、 地域视角下的民族观
敦煌从汉武帝时期即处于中原统治政权之下。汉武帝设酒泉郡和武威郡,其后虽然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乱,河西地区却相对稳定。在太宗、高宗乃至玄宗前期,唐朝中央政权对西域都具有绝对控制权。其中甘州(张掖),肃州(酒泉),沙洲(敦煌),瓜州,凉州(武威),兰州,伊州,西州,庭州,廓州,鄯州,河州,岷州都是唐朝在西域的重要城镇和半军事要塞,在怛罗斯之战前,唐的扩张达到了顶峰,但是在安史之乱后,肃宗即位,下令西域诸君东进勤王,西域处于军事真空状态。765年,杨志烈退凉州逃往甘州;766年,吐蕃攻陷甘州肃州,意味着河西逐渐沦为吐蕃控制。大历五年(770年)开始,吐蕃围攻敦煌,直至建中二年(781),敦煌陷落。经过大半个世纪后,大中二年(848),由张议潮带领的归义军爆发沙洲起义,之后河西地区农民起义不断,中原才恢复对河西地区的统治。
在中国古代,中原人民对于中原地区和边境地区的界限划分得很明确,中原文化和边境文化也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是从唐代中晚期至五代宋初,封建统治不稳定,边境频频作乱,对于边境的统治权也随之变化。在此情况下,处于边缘地区的敦煌人民对于异族的排斥和憎恨和对中原唐朝的向往与期盼,构成了十分强烈鲜明的边域观。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敦煌一直处于中原汉族和外族争夺之地,又因为丝绸之路的开通,也成为各种文化交融之地。敦煌变文出土于藏经洞,经考证为唐末至五代的抄写本,其时敦煌正处于风雨飘摇之境地。其中《李陵变文》中的李陵形象的正面化,可以透露出敦煌人民作为“二民”的真实心理.所谓“二民”,即由于身处边境地区,被两个国家交替统治的人民。
《史记》中对李陵降匈奴的描写较为简略:“陵食乏而救兵不到,奴急击招降陵。”[3]但是在李陵变文中则对此情节进行扩充,将李陵在面对匈奴强迫投降之下的痛苦心理放大。并且虚构了李陵投降匈奴是暂时变节保存实力的情节。这种美化的情节,实际上是民间文学对李陵的同情。而李陵在得知全家被汉武帝杀尽之后,则是痛苦万分:“陵闻老母被君诛,叫苦号眺而气咽,双泪交流若欲终,肝肠寸寸如刀切,使人泣泪相扶得,沙塞遣出肠中血。”[4]129变文中李陵俨然是一个悲剧的英雄角色,不仅忠君爱国没有变节,还是一个真实的被弃的臣子形象。变文中充满对他的同情和惋惜,这实际上是敦煌人民被吐蕃统治之后,被迫成为异族之民的痛苦。作为流民有国不能回的悲戚,对回归中原的渴望,他们能够感同身受李陵被迫降匈奴的心里挣扎。
这种对中原的寻根心理在敦煌诗词中也有所体现。《下女夫词》女方对男方发问:“人须知宗,水须知源”,这种寻根心理即使是在婚俗之中也能体现出来。陷蕃民众普遍有故国情结,思念唐朝,不忘唐服。如《新唐书》载:“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822年)元鼎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己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5]
与之不同的是,身处中原地区的白居易则著《汉将李陵论》,提出李陵没有死于战争即非忠,投降匈奴即非勇,因此事前功尽弃属于非智,导致全家被灭属于不孝,导致“遂亡其宗”这样的结局,李陵是个“不忠不勇不智不孝之人”[6]。
据《宋史》记载,杨继业是被契丹大军俘后,不甘受辱绝食而死。明代民间盛行熊大木的《杨家将演义》一书,并且改变成各地戏曲剧本或说书本子进行演出。在该书中杨继业兵败,困于狼心窝,“羊入狼窝,焉有生机”[7],此“窝”位处李陵碑附近,遂碰李陵碑而死。对这一情节进行如此改变,不仅是为了伟人化杨继业的形象,增加故事情节的感人效果,也是为了迎合民众的喜好。无论是在此书或者是改变的戏曲说词中,杨继业碰碑自尽这一故事情节都写得十分悲壮,此碑即“苏武庙”的“李陵碑”。将宁死不投降,放牧数十载的苏武和李陵并用于地名中,其实是对两者进行一次暗中的反衬,并以杨继业宁可撞碑自尽也决不投降的行为来讽刺李陵投降匈奴之事,虽然是一种艺术创造,但是从中透露出的是作者及受众们的审美倾向。“宁为杨业死,毋为李陵生”这样的价值观已经成为当时的主流。从变文到演义,这其中价值观的改变也是由于《杨家将演义》故事主要流传于山西一带,山西处于中原地带,靠近京城。一方面他们由于地域的差别,他们所经历的政治文化影响和异族来往的经历不同,所以他们不能和敦煌地区的边域之民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他们受中原文化影响强烈,明清理学不仅影响着文人的思想倾向,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普通百姓的思想。民间文学中对于李陵形象的定型,受到地域方面影响很大,以此为基础形成中原地区人民的民族意识。
二、 国力强弱观照下的民族观
王昭君下嫁和亲的故事自汉代流传下来,经过不同的流传者的润色,在唐代逐步定型。但是在敦煌文学《昭君变文》中单于的形象不同于前代流传的形象。从《汉书》到《后汉书》,乃至《琴操》中对呼韩邪单于的描写,对于昭君嫁入匈奴的具体生活描述都是一笔带过,而《昭君变文》中一改狭隘的汉宫怨的情愫,转而展示出昭君和单于的爱情,并用大篇幅刻画一个开明,深情的丈夫形象,将其从一个野蛮不开化的敌对形象转变成一个符合汉人行为规范的男性形象。
他听闻昭君的议论:“邻国者大而(大),小而(小),强自强,弱自弱。何用逞雷电之意气,争烽火之声(威),独乐一身,苦他万姓,”便“传一箭,号令攒军。”[4]157这决策使赤狄白狄,黄头紫头等都来庆贺明妃,并且选取吉日拜昭君为烟脂皇后。另外,变文中对于昭君的匈奴生活也进行了一定的描述,单于为解昭君的思乡之愁,不仅每每“善言相向”,还在“非时出猎”。昭君病重之时,单于“重祭山川,再求日月,百计寻方,千般求术,纵令春尽,命也何存”[4]157。昭君死后,单于“脱却天子之服,还著庶人之裳,批发临丧”[4]157。这种正面的异族首领形象,在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是没有的。昭君故事中侧重点的不同和对单于形象的不同刻画,展示出民间文学中对于和亲异族这一政治外交事件的包容性。唐代国力强盛,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高度包容的状态中,在这种高度开放的社会氛围的影响下,远在敦煌的人民也具有相当高的心理软实力。这种心理软实力是对于本身所处的国家硬实力的一种民族自豪和骄傲,在对外交往中不会常处于敏感焦虑的状态中。
唐代的昭君故事中的昭君下嫁已经完全带上了唐代的印记。唐代公主下嫁,都是唐朝处于优势地位的和亲,如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表现得十分恭顺,在《旧唐书》中他上表:“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如蒙圣恩,千年万岁,外甥终不敢先违盟誓。谨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马脑杯一、零羊衫段一,谨充微国之礼。”[8]另《资治通鉴》也有:“甥世尚公主,义同一家。中间张玄表等先兴兵寇钞,遂使二境交恶。甥深识尊卑,安敢失礼!正为边将交构,致获罪于舅;屡遣使者入朝,皆为边将所遏。今蒙远降使臣,来视公主,甥不胜喜荷。倘使复修旧好,死无所恨!”[9]这些语句俱是自降一级身份的言语。所以对于唐朝人民来说,下嫁和亲是一种正常的平等的外交方式,所以在《昭君变文》中,并没有过于强调昭君之恨,而是将重点放在平民乐见的爱情故事上。
但是对于元明清时代中的人民,时常处于被外族欺凌的紧张和恐惧中,他们的弱国心理十分明显。昭君故事在经过数百年的传说已经基本定型,在前期故事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和部分的增减,主要将主题设置为元帝和昭君的爱情。但是在《绣刊昭君和番双凤奇缘全传》*此书为[清]雪樵主人著,民国刻本,出版地和出版时间不详。中,昭君借助仙衣保存贞洁,妇人所贵节兼名,能自己身永不更。断臂毁容全白玉,此心肯让古田横。话说番王因酒后去扯昭君同赴巫山,谁知拉在仙衣上,忽然如万根银针直刺,刺得番王十指鲜血淋淋,最后投河自杀。 虽然其中将番王仍延续变文中的深情形象,但是增加了一个新的角色为昭君之妹赛昭君,扫平匈奴,成为皇后。这就将昭君所代表的汉朝和匈奴分隔开,仇恨化,尤其是从中透出的反番和反和番的情绪十分明显。《绣刊昭君和番双凤奇缘全传》此书文学水平不高,多杂糅前书而成,应该是书商逢迎市民喜好而粗糙著就。正因为这种民间性极高的书,其中的民间反番情绪才体现的更真实。
对于民间百姓来说,明代的政治军事一直处于外交弱势的地位,人民一直处于惶恐担忧的状态,清代更是属于异族统治汉族的状态,所以民间对于统治阶层的不信任和仇视,导致了汉民族的反抗精神日盛。在这种弱国的社会恐慌和政治高压下,民间文学中体现出的民族意识就是对异族外邦的统一排斥和反抗,在民族背景下,很容易形成狭隘的民族观。
三、 执笔者身份观照下的民族观
中国古代传统的文艺理论认为文学的本质即是“物感”,感于物而情志发。通常情况下,执笔者会根据自身的发展经历,形成一种无意识的寄托,将其虚拟在作品之中,所以文学作品的执笔者必然会将其自身的审美特性融进自己的作品中,以表达自己的审美品位和价值倾向。由此可知,作品的崇高与低下也是执笔者审美倾向的回声。
敦煌文学也被称为俗文学,主要是在经文的背面抄写或者练字所保存下来的文学作品。从正面经文的落款大多数为“学士郎”,“学仕郎”等称呼,可见其执笔者文学水平并不高。而敦煌变文又是为了说唱而变的文体,和佛教讲经文一样,是为了向民众说唱的文体,这就势必导致变文的语言内容不够高雅深奥,而是尽可能地通俗易懂,迎合民众的思想倾向。
在《李陵变文》体现出来的向往中原的“二民”意识和《昭君变文》中表露的民族友好意识,都是敦煌变文较之前后时代文学及中原文学不一样的地方,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独特的边域意识,极大程度上也是受执笔者本身的身份影响。在边域意识中,不同于中原文化或者其他时代文化的另一特点则是体现在对于封建统治君主的态度不同。
《唐太宗入冥记》中的唐太宗形象一反前人对于唐太宗英明神武的明君形象,而是将其描绘得十分猥琐胆怯。进得地府即忧心“今受罪犹自未了,朕即如何归的生路?”[4]320在判官院外等待时见人久不出来又“忧惶不已”。这种小民形象更接近于人们身边随处可见的平凡人,不会和受众产生距离感。《伍子胥变文》中伍子胥后来对楚王的报复是违背传统的对君主的盲目尊崇的。这种将对错原则凌驾于尊君之上的蔑君构造,是民间百姓独特的思想。对于受过儒家思想影响或者是处于封建统治阶层的人,都严格受到尊君思想的影响。他们的宗旨即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谨守君权神授的原则。但是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天高皇帝远是写实的社会情况,但是对于统治中心的好奇和臆测并不少,所以他们将自身阶层所存在的性格缺陷和人物特色熔铸进他们想象中的君主形象上,这就不同于文人笔下的君主形象。
但是在唐代以后,宋代的话本,元代的杂剧以及明清时期的小说,逐渐开始成为大众文学,执笔者也逐渐从民间艺人转为文人。如元代的关汉卿,马致远等,都是失意文人转而写剧本,明代的施耐庵,罗贯中等都是受过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在明前中期传奇创作中存在着审美趣味的文人化趋势。执笔者的文人化会相应地导致文学作品内容都符合文人的思想倾向,所以文人所创作或者润色过的文学作品中,极少出现丑化或者生活化君主帝王形象的情节。因为在儒家思想教育体系下,无论是否在学仕上获得成功的文人,尊君的思想是深刻进骨子里的。即使明清时期大多数小说都是经由书商删改及写作,但是书商不仅仅是作为商人存在,他们自身的文学修养也并不低,如明代陆云龙兄弟,不仅整理刊刻书籍,还进行原创。在他们的书中,君主的形象不可能出现滑稽,猥琐的形象,都是圣明形象。比如在《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中,即使熹宗放任魏忠贤等奸臣作乱朝政,危害社会,常年不理朝政,但是书中依然写道“天启爷爷”圣明等溢美之词。这种对君主的避讳不仅仅是由于社会规范,还由于文人士子们对于君主的崇拜,即使是做了错误的决定,也是奸臣蒙蔽的结果。
结 语
敦煌变文是典型的民间文学的产物,相比较于后世不断文人化的文学作品,在文学成就上可能不如,但是在民间艺术性方面是具有代表性。敦煌变文所处的独特的朝代和地域,都决定了它自身所彰显的民族观,包括流民意识,边域意识及民间意识等都不同于中原文化和后世文化。其中地域差别关照下的敦煌民间文学蕴含着敦煌民间百姓对于流落于外族手中的辛酸和对中原的渴望;国力观照下的敦煌民间文学又体现出身处于弱势地位的百姓对于和外族交往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感;执笔者的不同又体现出变文不同于文人文学的文学趣味。这些不同不仅构成敦煌文学的独特魅力,也是对历史文献的特殊补遗。
[1] 余秋雨.观众心理学[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46.
[2] 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2:217.
[3]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877.
[4] 黄征,张永泉.敦煌变文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6102.
[6]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407.
[7] [明]熊大木.杨家将演义[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8] [后晋]刘昫.旧唐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3639.
[9]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6:6791.
(编校:王旭东)
An Analysis on the Ethnological Viewpoint in Dunhuang Folk Literature —A Bianwen-centered Study
LUO Shang-rong,LIU Jie
(School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Dunham bianwen,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local folk literature,reflects Dunhuang people’s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mind-se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Dunham bianwen, due to its ag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audience, contains a unique aesthytic outlook. Its refugee consciousness, frontiers consciousness and folk consciousness are all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s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m. The difference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different humanistic factors such as national power, inside or outside the region and the different literary backgrounds of the authors.
Dunhuang bianwen; frontier; refugee; consciousness; aesthetic outlook
格式:罗尚荣,刘洁.敦煌民间文学中的民族观探析——以变文为中心[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7(3):93-97.
2017-03-24
罗尚荣(1968-),女,湖南长沙人,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刘洁(1992-),女,江苏盐城人,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I207.7
A
2096-3122(2017)03-0093-05
10.13307/j.issn.2096-3122.2017.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