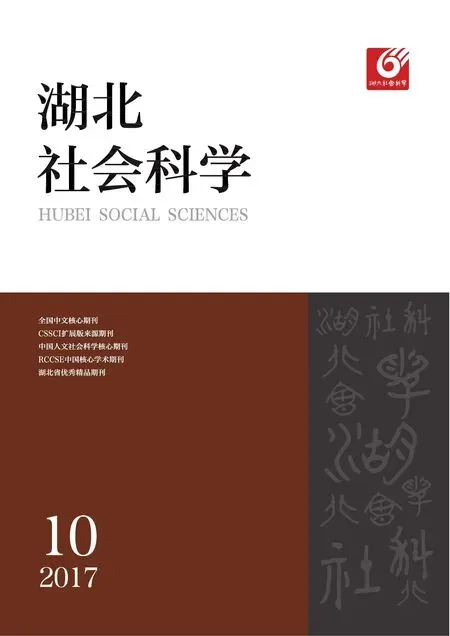碑志文的定型及相关问题
徐海容
(东莞理工学院 中文系,广东 东莞 523808)
碑志文的定型及相关问题
徐海容
(东莞理工学院 中文系,广东 东莞 523808)
我国先秦时期,已出现了碑。两汉以来,碑志文发展兴盛,这其中蔡邕为碑志文的基本成型作出了贡献。此后,韩愈借文体改革之机,对传统碑志文予以变革,使得散体碑志文风行一时,而欧阳修扇扬余烈,提出简而有法的写作准则,又大力创作新式碑志文,这就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使得碑志文最终发展定型。碑志文源远流长、分支庞杂,其文体分类及界定,经过了一个相当的过程。
碑志;文体形态;韩愈;定型
一、碑志辨体
“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1](p1)关于碑志文的起源,一般认为源于先秦,《礼记·丧大记》:“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又云;“凡封,用綍去碑负引。”[2](p1187-1189)《礼记·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恒楹。’”郑玄注:“丰碑,凿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繂绕。天子六繂四碑,前后各重鹿卢也……四植谓之恒,诸侯四繂二碑,碑如恒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无碑。”[2](p281)可见这时碑作为殡葬实物已经存在并广泛应用,随着时代变化,后人在其上开始刻写文字,以作坟墓标识、进而记事铭功,此可谓碑志文之滥觞,正如宋人孙宗鉴《东皋杂录》所论:“自周衰,战国秦汉皆以碑悬棺,或以木,或以石。既葬,碑留圹中,不复出矣。其后稍书姓名爵里其上。至后汉,遂作文字。”[3](p213)但是,后世碑的用途除墓葬外,还可用于建筑记功、会盟记事等,王兆芳《文体通释》解释古碑之分类流变云:“碑者,竖石也。古宫庙庠序之庭碑,以石丽牲,识日影,封圹之丰碑,以木悬棺綍,汉以纪功德。一为墓碑、丰碑之变也。一为宫殿碑,一为庙碑,庭碑之变也;一为德政碑,庙碑墓碑之变也。”[4](p223)
墓碑专为死者而立,最为常见,用途最广。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
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岩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古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4](p214)
其所论碑之起源发展,主要针对墓碑而言,并且指出,立碑目的在于传之后世,以求“不朽”,而材料上“以石代金”,证明载体发生了变化。
碑和碑志文是两个概念。碑是碑志文的载体,是物质存在,而碑志文则是刻于碑上的文字,是文学现象,两者不可混淆。但实际上,我国古代的碑有着器物与文章体式的双重含义,文论学家也常对此混淆。刘熙《释名》曰:“碑者,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谓之碑也。”[5](p32)其所论“碑”既指碑石,亦指文章。此后陆机《文赋》所云“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6](p201)及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也沿袭了这一观点。至宋代,有学者针对碑作为文章体式的说法提出异议,如孙何《碑解》云:“碑非文章之名也,盖后假载其铭耳。铭之不能尽者,复前之以序,而编录者通谓之文,斯失矣。陆机曰:碑披文而相质,则本末无据焉。”[7](p358)其后清人纪昀认为“碑非文名,误始陆平原,孙何纠之,拔俗之识也。”[8](p447)赵翼《陔余丛考》也云:“碑有序有铭,谓之碑文碑铭可也,直谓之碑则非也。”[9](p684)近代刘师培承继了这种说法,其《左庵文论》云:“树碑之风,汉始盛行,而东都尤盛,惟乃刻石之总名,而非文体之专称……盖凡刻石皆可谓之碑,而非文章之一体,与铭箴颂赞之类不同。惟以铭体居十之六七,故汉人或统称碑铭,碑则刻石,铭则文体也。”[10](p165)指出碑乃刻石之称,而刻于其上的铭文则是文体名称,就碑和碑文作了明确界定。
碑志文因碑而得名,这种因载体而定名的现象在古代文体发展中并不罕见,如石鼓文、甲骨文、钟鼎文、金文、檄文、诏令、札子、策论、乐词、露布等。这说明任何一种书写载体在演进过程中,因受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风气的影响,会突出某一方面的功能,并由此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制,一种较为稳定的表达方式,并为人们接受,此以碑志文尤为突出。自从《文赋》《文心雕龙》等以“碑”作为文体之名后,其说相沿成习,如明代两位文章学家吴纳《文章辨体序说》列“碑”,而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则列“碑文”,都在论述碑志文体。
碑志文(本文所论碑志文,主要针对墓碑文而言)首先是一种应用文体,有着强烈的应用性,陆龟蒙《野庙碑》云:“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窆,用木。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11](p4957)殡葬礼仪中,人们挖墓埋坟,立碑作志,以悼亡安死,垂之不朽,碑志文成为其抒发哀情、抚慰生命的最好寄托。其次碑志文也是一种文学美文,带有相当的文学性。就写作范式而言,碑志文是联结生死最为紧密的文体,于人于事进行记叙总结,评判论定,使已经远去的消逝的生命鲜活起来,彰显缅怀和哀悼之情,以满足丧葬礼俗的需要。所以碑志文具体写什么,又该如何写?这既要照顾到描写对象及其家属亲朋的情面,有所忌讳,表达伤悼之意、哀荣之礼,又要做到真实可靠、客观全面的记述,以取信公众、传之后世,达到作文立碑而求不朽的目的,这就涉及文人的写作水平,而任何应用文,因为广大文人的参与创作,都多少带有文学性。关于碑志文的写作准则,刘勰《文心雕龙·诔碑》所云“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4](p214)强调碑志写人记事要真实准确,以史为据,进而扬善隐恶、铭功彰美,王行《墓铭举例》则从具体条目上对碑志文予以界定,其曰:“凡墓志铭,书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讳,曰字,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其序如此。如韩文集贤校理石君墓志铭是也,其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讳,曰字,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葬日,曰葬地,曰妻,曰子其序如此,如韩文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是也,其他虽序次或有先后,要不越此十余事而已,此正例也。其有例所有而不书例,所无而书之者又其变例各以其故也。”[12](p381)可见碑志文尽管是由文人创作的,但往往又不是简单的文士个人化的行为,其成文涉及社会评判、道德衡量、文化风气及人情礼俗等多方面的时代性内容。所以说碑志文与人类生命的存活死亡、与历史现实、社会生活紧紧结合在一起,是时代文学的映射,文人创作碑志文的过程,就是对逝去生命的哀悼和探求、对历史事件的思考和感悟的过程,展现着文人的才情个性和社会生活体味。
二、蔡邕与碑志文的基本成型
汉代立碑作志之风浓厚,祝嘉《书学史》描述东汉碑刻盛况云:“光武中兴,武功既盛,文章亦隆,书家辈出,百世宗仰,摩崖碑碣几遍天下。”[13](p18-19)这就促进了以墓碑文为主的碑志文的写作。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说碑文“后汉以来,作者渐盛,”[14](p144)据文献记载,除蔡邕外,当时文人如崔瑗、胡广、桓麟、孔融、马融、卢植、服虔、边韶、张升、张超、皇甫规、刘珍、潘勖、繁钦等人,都投身于碑文的写作。虽然这些人所撰写的碑文,多或失考,或不存。从所存作品看,多能表现碑文的文学意味,[15](p59)典型如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从介绍张衡的名讳、门第、世系写起,就其天资才华,道德文章,术数制作、辞赋技艺、仕宦经历等一一叙述,铭词用四言韵语的形式概括张衡的一生,内容完整,条理清晰,其余如班固《封燕然山铭》《高祖泗水亭碑记》等亦循此例,行文称功颂德时都遵守“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16](p1047)的创作规范。
伴随着当时树碑风气的兴盛和诸多作家的努力,由秦至汉,碑志文的创作日臻成熟并基本成型,这其中贡献最大者当属蔡邕。蔡邕具有明确的碑文观念,对碑的源流、文体定位与写作功用有着明确认识,其《铭论》云:“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钟鼎礼乐之器,昭德纪功,以示子孙,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近世以来,咸铭之于碑,德非此族,不在铭典。”[6](p198)在具体的碑志作品中,蔡邕于此也多有说明,如《太尉杨秉碑》:“刊石树碑,表勒鸿勋,赞懿德,传亿年。”[17](p763)《陈寔碑》:“存荣没哀,死而不朽……铭勒表坟墓,俾后生之歌咏德音者,知丘封之存斯也……以褒功述德,政之大经,是以作谥封墓,兴于《周礼》,卫鼎晋铭,其昭有实……树碑刊石,垂世宠光。”[17](p781-782)都指出了碑文的文体职能在于宣扬死者声名,恢宏功德,垂芳后世、资求不朽。在具体的写作方法上,蔡邕认为碑文创作应持审慎态度,合乎礼制,具备史家的实录精神。在为名臣乔玄撰写的《太尉乔玄碑阴》中,蔡邕写道:“三孤故臣门人,相与述公言行,咨度礼制,文德铭于三鼎,武功勒于钲钺。官薄第一次,事之实录,书于碑阴。”[17](p775)就碑文的“实录”原则做了说明,强调碑文写作的严谨态度,其《太尉杨赐碑》再次重申这一观点:“纠合朋徒,稽诸典则,以为匡弼之功,政事之实,诏策之文,则史臣志其详。若夫道术之美,授之方策,则是门人二三小子所持贯综,敢竭不才,撰录所审言于碑。”[17](p784)蔡邕以自身写作的体会,表明作碑文不能率意而为,而要与碑主的门生弟子及亲朋好友,根据礼制共同商讨,据实书写,如此才能达到“求不朽”的目的。
蔡邕不仅具有明确的碑文观念,还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碑志作品。王应麟《困学记闻》卷十三云:“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铭墓居其半,曰碑,曰铭,曰神诰,曰哀赞,其实一也。”[3](p828)蔡邕碑文内容充实、结构完整,其往往前序后铭,序文依次介绍碑主的名讳、世系、祖功、官阶履历、才华政绩及丧葬情况等,铭文则对碑主进行综合评论,彰美表功,如《汉太尉杨公碑》写墓主家世:“公讳赐,字伯猷,弘农华阴人,姬姓之国有杨侯者,公其后也。”写其功德:“公承家崇轨,受天醇素,钦承奉构,闲于伐柯。……及至太尉,四时顺动,三光耀润,群生丰遂,太和交薄。三作六卿,五蹈三阶,受爵开国,应位特进。”行文前志后铭,记事颂功,体例严整,而言辞典雅纯正,古朴工稳,其余如《琅琊王傅蔡朗碑》《陈寔碑》《郭泰碑》《胡广碑》等篇章,都此写法,在体例格式上呈现出稳定的形态。范文澜《墓志铭考》曰:“东汉则大行碑文,蔡邕为作者之首,后汉文苑诸人,率皆撰碑。”[4](p232)身为文坛领袖,蔡邕的碑文影响广泛、多为时人效仿。
从理论指导到创作实践,蔡邕身体力行,为碑志文的基本成型做出了贡献。当然,因为时代的原因,蔡邕的碑志文因注重对墓主的歌功颂德而引发“谀墓”之说,《后汉书·郭太传》:“蔡邕谓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18](p2227)顾炎武《日知录·作文润笔》也云:“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蹇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19](p1108)因此,要说墓碑文“谀墓”之弊,当自蔡邕起。但瑕不掩瑜,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精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至矣。”[4](p214)对蔡邕碑文予以高度评价。蔡邕承前启后,为碑文创作树立了典范,为后世所宗,以至于“孔融所创,有摹伯喈;张陈两文,辨给足采,亦其亚也。”[19](p214)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孙绰之碑,嗣伯喈之后。”[20](p908)也以蔡邕为标准来评论孙绰之碑文。此后时运交替,质文相移,历代文人不断努力,从体例形式和思想内容上对碑志文不断丰富和完善,使得碑志文最终发展定型,这其中唐宋文人起了重要作用,而尤以韩愈和欧阳修为代表。
三、韩愈、欧阳修与碑志文的最终定型
韩愈、欧阳修都是文章大家,其借着文体革新运动的机会,对碑志文发起改革和完善,最终使其发展定型,影响深远。
汉魏以后,伴随着文学对审美内质的追求,文章写作逐渐向骈俪化发展,而尤以南朝为极。碑志文自然不例外,比如徐陵、庾信的碑文,皆以骈俪写就,铺陈排比,用典、藻饰丰富,句式上以四六为主,对仗精工,韵律和谐,辞旨华靡绮艳,而当时文人创作以徐庾为宗,这就形成了碑文创作以骈俪为体,注重形式美追求的思想倾向,而思想内容则日显空洞,使得碑文向着华靡流丽、浮艳夸饰的方向发展,可谓“辞采增华,篇幅增长,”[21](p172)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唐代前期,正如谢无量所云:“唐兴,文士半为陈隋之遗彦,沿徐庾之旧体。太宗本好轻艳之文,首用瀛洲学士,参与密勿,纶浩之言,咸用俪偶……率以华缛典赡为高。”[22](p213)
时至中唐,伴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特别是针对文章写作骈俪风行、内容空洞的思想倾向。韩愈发起了文体改革,借以振兴文坛,挽救时弊,以文学革新推动政治革新,这其中包括碑志文风的改革。韩愈在《重答张籍书》《上宰相书》《争臣论》《原道》等文章中,反复申明他撰写古文的宗旨是“修辞明道”和“抑邪与正,”[23](p133)阐明其以道统为中心的创作理论,其后在《送孟东野序》《答李翊书》中,又针对文章的具体写作进行说明,提倡“气盛言宜”、“不平之鸣”。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其对包括碑志文在内的文章写作理论的阐释。而宋代欧阳修等人扇扬余烈,发起文体变革时,于碑志文更以韩愈为宗,对碑志文的创作理论进一步发展,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欧阳修阐明自己的文章创作理念:“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24](p1777)在《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提出“简而有法”的碑志创作思想,而在与曾巩的讨论中,更明确了碑志文的写作准则:“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倡导“蓄道德而能文章。”[25](p253)欧阳修认为作碑志文要简而有法,就是倡导记人写事真实准确而简略得当,合乎微言大义的史家笔法。但更重要的,欧阳修和曾巩指出了碑志文虽追求史家笔法,但又和史传不同。史传于传主善恶必书,务求详细周全、资料齐备。而碑志文则更多取舍,扬善隐恶,详略分明。如此才能“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足为后法”,这就明确了碑志文与史传文的区别,其后在《与渑池徐宰元党书》《与王深甫论裴公碣》《再与王深甫论裴公碣》《与杜论祁公墓志书》《再与杜公论祁公墓志书》中,欧阳修连续对这一思想作了阐发,这就使得碑志文创作准则明确化。
其次,韩欧推进了碑志文内容格式的完整化。碑志文是一种古老的应用文体,伴随着文学演进的大潮,总是在稳定中变革,在变革中前进。在古人的观念中,文体有正变、雅俗、高下之分。古人往往推崇正宗的、古典的、高雅的、朴素的、自然的文体,相对轻视时俗的、流变的、华丽的、拘泥过多的文体。以雅正、品位高的文体去改造流变的、品位卑下的文体,以提高其格调和品位。韩愈发动古文运动即此例,欧阳修对韩愈碑志文的改造亦此例。[26]就创作实践而言,韩愈、欧阳修的碑志文量丰质优,堪称旷代文宗。韩愈创作碑志文达76篇,位居全唐作家之首。典型如《平淮西碑》《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致仕阳平路公神道碑文》《曹成王碑》《唐故江南西道观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左散骑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铭》《柳子厚墓志铭》等,以弘扬孔孟儒学为核心,倡导民本与仁政思想,反对藩镇割据,维护王道政治等,而内容充实,思想刚健,写人记事格式规范,体例谨严,于文体形态方面呈现出典雅宏正、伟岸大气的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蔡邕体碑文冗繁浩大、夸饰铺排、呆滞僵化之弊,完善了碑志文的内容体例。此为欧阳修等后世文人所继承,欧阳修共作碑文110篇,典型如《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太子太师致仕赠司空兼侍中文惠陈公神道碑铭》等,行文前志后铭,体例完整,结构谨严,思想上强调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道德意识,弘扬儒道精神和家国情怀,其内容充实,气势刚健,无论是写晏殊、余靖、程琳、王德用等达官显宦还是写黄梦升、胡瑷等贫士寒儒,都精准确切,评价得当,不溢美,不拔高,不谀墓,微言大义,简约凝练,在思想内容及体例格式上颇显谨严端正之美,影响到一代文风。
最后,韩欧完成了碑志文创作的文学化。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云:“唐代文学之所以异军突起,而凌驾魏晋,继述周秦者,以诗有李杜,继往开来以尽其变;而文有韩柳,错偶用奇以复于古……及韩愈闳中肆外,务反近体,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柳宗元翼之,茹古涵今,齐梁绮艳,毫发都捐,而后古文之体以立。”[27](p360)韩愈大力写作质实古朴、明道载物的碑文,这种碑文在价值取向上以倡扬孔孟儒道精神为核心,针砭时弊,推崇仁政,使得思想内容刚直有力,而在文体规范上挑战传统、求新求变,冲破了盛唐张说等颂美式台阁体碑志文的程式,特别是以小说化和诗化笔法行文,摒弃骈四俪六、藻饰文辞的形式主义文风,改骈为散,议论抒情,使得写人记事更为形象生动,情感浓郁,气势充沛,而语句清新流畅,灵活自如,增强了碑志文的文学性,如《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柳子厚墓志铭》《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等,写清正廉洁的贤吏,写反对奸佞的烈士,叙事记人丰富多彩而品节突出。李涂《文章精义》云:“退之诸墓志,一人一样,绝妙。”[28](p68)吴纳也说碑文“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袭。”[14](p52)而欧阳修与之发扬,其碑志文如《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黄梦升墓志铭》《胡先生墓表》等,也追求文学性,叙写人事精准确切,繁简得当,不溢美,不谀墓,微言大义,简约凝练,而语言尤为平易质朴、典雅通达,避免传统碑文流水账式赘述之弊,更显文笔之优美。碑志文本属于行政性应用文,但因为韩欧等大文人的努力,使得碑志文在保持传统应用性的同时,更向着文学化方向发展。钱基博云:“碑传文有两体:其一蔡邕体,语多虚赞而纬以事历,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人碑多宗之。其一韩愈体,事尚实叙而裁如史传,唐以下欧、苏、曾、王诸人碑多宗之。”[27](p360)伴随着欧阳修的领导文坛和后来曾巩、三苏、王安石等人的努力,文体革新运动不断展开,刘师培《论文杂记》云:“宋代之初,有柳开者,文以昌黎为宗。阙后苏舜钦、穆伯长,尹师鲁诸人,善治古文,效法昌黎,与欧阳修相唱和。曾、王、三苏咸出欧阳之门,故每作一文,莫不法欧而宗韩。古文之体,至此大成。即两宋文人,亦以韩欧为圭臬。……而韩欧之文,遂为后世古文正宗矣。”[29](p121)碑志文至此走上追求雄豪健拔而归于平淡隽永、质朴厚实的文学道路,其体例准则也最终定型,成为中国古代的重要应用文体,文体革新运动取得胜利,最终也完成了唐宋古文运动的进程。
四、碑志的文体分类与界定
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刘师培云:“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30](p20)一般而言,具有文体相似性的作品必须达到一定数量,才可能归纳为一种文体类型,并为人们所认可。徐师曾在谈到《文体明辨》一书的编纂方式时说:“是编所录,唯假文以辨体,非立体而选文,故所取容有未尽者。”[14](p78)碑作为一种文体的产生,同样遵循着这个规律。
关于碑志文,自汉代起,学者对其文体定位及写法要素,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如前所述蔡邕《铭论》及陆机《文赋》所云“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6](p201)给予碑文以独立的文体定位,强调碑文形式美的体征。值得一提的是,南朝刘宋时期是中国文学思想变迁的重要转折点,表现出鲜明的文学自觉意识和文体辨析观念。范晔《后汉书》对于作家作品著录次序,基本上是先诗、赋、碑、诔、颂、铭、赞、箴等“有韵之文”,后再表、奏、论、议、令、教、策、书、记、檄、说等“无韵之笔”,如无诗赋作品,则碑列在最前面,这一著录次序,反映出从汉末到刘宋,区分文笔的文体辨析观念、文体归类意识、文集编纂观念已趋明朗,也反映出碑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在文学创作中的繁荣状况及重要地位。刘勰《文心雕龙》亦专作《诔碑》一节,详细论述了碑志文的起源流变,对碑文在写作过程中与史传、诔文、铭文等互相借鉴、交叉影响的关系作了分析,表明碑既是一种铭器,也是因器得名的一种文体。
其后萧统《文选》以文章题目分类文体,分文体三十九类,将碑文与墓志分开。此后碑志文体的划分,逐渐标举详细,如北宋李昉编《文苑英华》分文体三十八种,对碑志文分作碑、志、墓表三类文体,仅碑下又分为儒、道、释、德政、记功、隐居、孝善、遗爱、台、陵庙、祠堂、祠庙、象庙、神道十四类。姚铉《唐文粹》分文体二十三大类,“碑类”下按内容又细分为二十六类。明代《文章辨体》和《文体明辨》对文体名称更是不断扩充,前者收录诗文五十九类,分碑志文作“碑、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墓记、埋铭”七类。后者分文体一百二十七类,碑志文分作“碑文、碑阴文、墓志铭、墓碑文、墓碣文、墓表”六类文体。这样简单以文章题目来定位文体,导致文体分类日趋庞杂,实不足取。《四库全书总目》于此就批评说:“千条万绪,无复体例可求,所谓治丝而棼者欤!”[31](p1750)此后文体分类渐趋简化,关于文章的功能定性不限于名目别称,而侧重于用途功能等。直至姚鼐编《古文辞类纂》,采用“以实不以名”,即以文体形态为主的“类从”法,将文章分作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文体。至于碑志文体,则整合了庙碑、墓碑、神道碑铭、墓志铭、墓碣铭、圹铭、圹志、墓表、阡表、权厝志、葬志等相关分支,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于之解释道:
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时,有石鼓刻文,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琅琊具之矣。……志者,识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圹中,古人皆曰志。为之铭者,所以识之之辞也。然恐人观之不详,故又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铭二之,独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义。[32](p17)
在碑志文体的功能界定和整合规划上,姚鼐固然也承继了“因文立体”的传统,但一改前人庞杂琐碎的流弊,注重从本体和实质出发,将墓志铭、墓表、碑文、神道碑等等本质相同的文章,全部纳入碑志文体,以简驭繁、系统概括。钱基博评之曰:“此分文体为十三类,每类必溯其源而竟其流,以视《昭明文选》之分类碎琐,立名可笑者,为简当矣。”[32](p8)姚仲实也云:“《文选》所分之类,颇嫌烦琐。……《古文辞类纂》出,辨别体裁,视前人乃更精审。……分合出入之际,独厘然当于人心。”[32](p8)都赞赏姚鼐对于碑志文体性的界定。事实上,中国古典文体学家认为无论文章外在形式如何变化,但内在的体用“未尝变”。范应宾《文章缘起注·题辞》云:“由两汉而还,文之体未尝变,而渐以靡,诗则三百篇变而《骚》,骚变而乐府,而歌行而律而绝,日新月盛,互为用而各不相袭,此何以故,则安在斤斤沿体为,体者法也,所以非法体也,离法非法,合法亦非法,若离若合,政其妙处不传,而实未尝不传。……不有体,何以拟议?不知体之所从出,何以为体?而极之无所不变。”[33](p1)此所云“文之体”指文章的本体,即文章的内质,姚鼐《海愚诗钞序》也云:“吾尝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天地之道,协和以为体,而时发奇出以为用者,理固然也。”[34](p110)强调文章的体用不二。随着时间的推移,姚鼐的文体分类法更为后世接受和认可,如吴曾祺编《涵芬楼古今文钞》及今人曾枣庄主编三百六十卷《全宋文》,在文体分类及编序上也秉承姚鼐的做法,于碑志文体单独分类,其下涵盖了墓志铭、墓碑、墓碣、神道碑等所有分支,可见姚鼐《古文辞类纂》的影响。综观碑志文分类的历史,其实也是中国文体分类及界定不断发展成熟的历史。
五、结论
综上所述,以蔡邕、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文人,身体力行,于碑志文的嬗变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体例格式、思想内容、结构章法方面都推动着碑志文作为独立文体的发展及定型。伴随着时代演进及文体革新的大潮,碑志文也不断创新发展,成为集应用性和文学性于一体的文体,繁荣兴旺,影响深远。而文章学家对碑志文的定性和归类,也反映出不同时代文体观念的变化。
[1]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2]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陶宗仪.说郛 [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刘熙.释名[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
[6]于景祥,李贵银.中国历代碑志文话[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
[7]徐乾学.读礼通考 [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8]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赵翼.陔余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刘师培.中古文学论著三种[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1]董诰.全唐文[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12]王行.墓铭举例[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3]祝嘉.书学史[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4.
[14]吴纳,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5]黄金明.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7]严可均:全后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8]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9]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0]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21]刘师培.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2]谢无量.谢无量文集·骈文指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3]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4]欧阳修.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5]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6]吴承学.辨体与破体[J].文学评论,1991,(4).
[27]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8]陈骙,李涂.文则·文章精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29]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0]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1]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存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2]吴孟复.古文辞类纂评注[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33]陈懋仁.文章缘起注·丛书集成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4]姚鼐.惜抱轩全集[M].上海:世界书局,1936.
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7)10-0118-07
徐海容(1976-),男,广东东莞理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代碑志文研究”(15FZW01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邓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