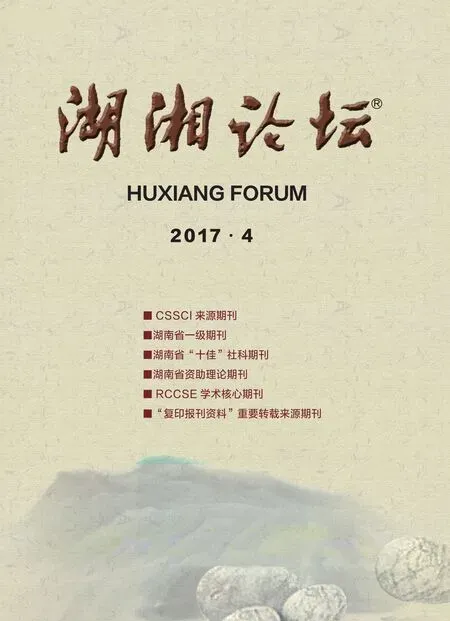家庭承包权的性质转变及其对农地产权结构的影响
周 猛
(湖南医药学院,湖南 长沙 418000)
家庭承包权的性质转变及其对农地产权结构的影响
周 猛
(湖南医药学院,湖南 长沙 418000)
随着家庭承包从经营层面到分配层面的转移,权利内容从使用权到处分权的扩展,家庭承包权已经转变成了一种次级所有权。家庭承包权的性质转变引起了农地产权分配结构、经营结构和处分结构的变化。
家庭承包权;次级所有权;农地产权结构
家庭承包权是我国当前农地产权中的核心概念,既是农村经营制度改革的产物,又是新一轮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起点。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将其界定为“经营权”,《物权法》界定为“用益物权”,然而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农民的不断赋权,家庭承包权的内容在不断扩展,性质越来越复杂,特别是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提出,使家庭承包权的性质成了一个难解之谜。研究发现,实践中的家庭承包从经营层面转移到了分配层面,承包权转变成了分配权,权利内容从使用权扩展到了处分权,家庭承包权已经转变成了分配给农民家庭的一种所有权,即次级所有权。家庭承包权的性质转变引起了农地产权结构的变化。
一、马克思土地产权结构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认为,所有权是一组权利,而不是单独的一项权利,这一组权利可分可合,时分时合,由此形成形态各异的所有权结构图式。[1]土地产权结构包括土地所有权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两部分。土地所有权内部结构是指所有权及其衍生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内部权能状况;土地所有权外部结构是指由经济行为引起的、以土地所有权内部结构变化为基础的各种土地产权状况。在土地产权结构中,内部结构是基础,外部结构是表现。马克思根据人类社会对土地的分配、经营和处分三种经济行为,主要分析了分配、经营和处分三个层面的土地产权结构。
(一)分配层面的土地产权结构
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所撰写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文中,分析了亚细亚、古典古代、日耳曼公社三种土地分配形式、所有权制度、土地产权分配结构,体现了马克思分配层面的土地产权分配结构思想。
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公社虽然都是“劳动的个人对其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原始所有制”,[2]是土地公有产权制度的三种主要形式。但由于土地分配形式不同,所有权制度形式及其产权分配结构也不一样。
亚细亚的土地分配形式是土地所有权的权利内容,即狭义所有权和其所衍生的权利束在共同体和成员之间的分配,所有制表现为公有制。总合的统一体是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公社是世袭的占有者或实际所有者,成员个人只是占有和使用者。产权结构是:所有权属共同体即总合的统一体;公社拥有世袭的占有权或实际所有权;公社成员享有占有和使用权。
古典古代的土地分配形式是狭义所有权的级次级所有权,即狭义所有权的终级所有权(或一级所有权)和次级所有权(或二级所有权)在共同体和成员之间的分配。所有制表现为国家所有同私人所有相并列的双重形式。古典古代的土地被分为了两部分,即公有地和私有地,公有地没有分配,分配的只是私有地的次级所有权。产权结构是:公有地的所有权属公社,使用权属全体公社成员;私有地的终级所有权属公社,次级所有权属成员。
日耳曼的土地分配形式是全部所有权分配。在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中,公社所有制仅仅表现为个人所有制的补充形式。日耳曼的土地也被分为了两部分,公有地没有分配,但私有地的全部所有权都分配给了成员。土地产权分配结构是:公有地的所有权属公社,使用权属全体成员;私有地的所有权属成员。
(二)经营层面的土地产权结构
在地租理论中马克思详细地分析了土地出租这一经营形式,恩格斯在研究法德农民问题时,则提出了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按土地入股的合作社经营设想。体现了马克思经营层面的土地产权经营结构思想。
1.土地经营形式及产权经营结构
土地经营形式按经营行为来分,可分为所有权人自主经营和非自主经营两大类型。自主经营的产权结构是一种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于一体的状况;非自主经营的产权结构则是一种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即所有权属所有者、经营权属经营者的状况。
非自主经营至少可分为出租和入股经营两种形式。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土地所有权、出租权属封建地主和大土地所有者,租赁权和经营权属租地农民和农业资本家。按恩格斯的设想,土地入股是把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成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农民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动的比例分配收入。[3]入股土地的所有权和股权属农民,入股后的土地即合作社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属合作社。
2.所有权内容分割是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实现条件
经营权与土地所有权可分可合,当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为一体时,经营权以全部所有权为基础。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时,经营权只能以部分所有权为基础,即核心所有权属所有者,使用权等权利束属经营者。当然,与所有权相分离的经营权究竟包含哪些所有权,则取决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约定,并且只能是所有权的内容分割。
(三)处分层面的土地产权结构
马克思在土地价格学说中分析了土地买卖引起的土地所有权流通,在地租理论中分析了抵押行为引起的土地所有权转移,同时也分析了古代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继承问题,体现了马克思处分层面的土地产权处分结构思想。
1.土地买卖
土地买卖是土地所有权作为特殊商品在市场上的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土地所有权流通。土地价格“不过是地租资本化的另一种表现。实际上,这个购买价格不是土地的购买价格,而是土地所提供的地租的购买价格”。[4]
当所有权人把土地用来买卖时,售卖者享有售卖前的所有权和销售权,购买者享有土地购买权和售卖后的所有权,由于买卖行为引起了土地所有权在卖买者之间的转移。
2.土地继承
土地继承是一定所有权制度下所有权在继承人和被继承人之间的转移。“继承并不是产生这种把一个人的劳动果实转移到别人口袋里的权利——它只涉及到具有这种权利的人的更换问题”。[5]
当土地作为财产用来继承时,继承前被继承人享有所有权,继承后所有权则属继承人所有,由于继承行为引起了土地所有权在被继承人和继承人之间的转移。
3.土地抵押
比较买卖和继承,马克思对土地抵押的论述相对较少,但并不影响马克思土地产权结构理论的完整性。马克思指出:“他究竟是自己收取地租,还是必须再把它付给一个抵押债权人,这不会在租地农场本身的经营上引起如何变化。”[6]
当所有者把土地用来抵押时,抵押人享有抵押权及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如果抵押人在合同期满后不能清偿债务,土地所有权将转归抵押权人所有,或者由抵押权人按规定处置,由于抵押行为有可能引起土地所有权在抵押人和抵押权人之间的转移。
二、家庭承包权的性质转变
由于家庭承包的层面转移,权利内容的扩展,使家庭承包权转变成了分配给农民家庭所有的一种次级所有权。
(一)从经营到分配:家庭承包的层面转移
改革初期的家庭承包只是一种经营形式,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从经营层面转移到了分配层面,转变成了一种土地分配形式。
1.农民诉求的本意是“分田到户”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20位农民冒着风险签订了一份“分田到户”的契约,[7]本意是要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希望通过“分田到户”的诉求,向政府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然而得到的允许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1986年4月《民法通则》首次提出“土地的承包经营权”,1993年《宪法》修正案界定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9年又将其修改为“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2.家庭承包的政策法律规定具有土地分配性质
“按户承包,按人分地”原则具有土地分配性质。根据“农村土地承包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权依法承包集体经济组织发包土地的是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所有成员,承包方是农户家庭。实践中的做法是,发包方发包土地时,是按照每户家庭所有成员人数来确定承包土地的份额,即“按户承包,按人分地”,只要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不论男女老幼,所有成员都有权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并无年龄、性别限制。比较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第六条之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按户承包,按人分地”原则具有土地分配性质。
家庭承包的客体、方式、程序、期限等规定也具有土地分配性质。家庭承包的客体主要是责任田、自留山、自留地等;承包方式是民主协商;程序主要包括村民会议选举承包工作小组、工作小组制定并公布承包方案、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组织实施承包方案、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期限由政策和法律规定;承包人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在土地所有权制度下,土地如何经营,本应由集体自主决定,但家庭承包是在政府领导下按照政策法律规定进行的,因此,也具有土地分配性质。
3.集体提留和农业税的取消使家庭承包的分配性质更加明显
家庭承包经营是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基础上发展而来,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除了按计划进行生产外,还要完成农业税和上级集体提留。家庭承包经营的集体提留和农业税是按照农民家庭承包的责任田面积来分摊的,是农民家庭对集体土地承包经营的一种代价,但集体提留和农业税取消之后,承包方因承包向所有权人付出的代价就自然消失,成为了一种无偿的土地分配。
(二)从使用权到处分权:权利内容的扩展
改革初期承包权内容只是使用权,随着国家对农民的不断赋权,其权利内容已经由占有、使用、收益等逐步扩展到了处分权。
1.从使用权到占有、收益权的扩展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就是把以使用权为内容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以完成集体提留和农业税为代价,用家庭承包方式把土地交给农民家庭经营,使农民家庭拥有了独立的农地使用权。随着农地承包经营期限的不断延长,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使农民家庭拥有了农地的占有权。集体提留和农业税的取消则使产品分配权转变成了收益权。从家庭承包权的权利内容来看,虽然已经由使用权扩展到了占有和收益权,但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仍然是以土地所有权内容分割为基础,权利性质仍然是一种经营权,法学界有学者将其界定为用益物权或债权。[8]
2.从占有、使用、收益权到处分权的扩展
(1)从经营权的转包到出租、入股。农民为了最大效益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使用和收益,实践中又将经营权以转包、出租、入股等方式进行流转。转包、出租、入股就是保留承包权,以占有、使用和收益权为内容的经营权流转。比较马克思对土地出租和恩格斯关于土地入股合作社经营设想的分析,保留承包权以占有、使用和收益权为内容的经营权流转,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是农民要求以承包权在市场流转的一种诉求。
(2)从经营权的出租、入股到承包权的互换、转让。互换和转让则是家庭承包权在集体成员之间的互换和转移,互换和转让本身就是所有权人对财产的一种处分行为。对实践中农民流转土地的诉求,国家通过法律给予了肯定,《农村土地承包法》作出了“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规定,农业部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以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
(3)从承包权的互换、转让到经营权的抵押、继承。如果说互换承包地,还保留了农民家庭对农地的承包权和集体成员身份的话,那么转让会导致承包权的丧失,抵押则会导致经营权的丧失。因为处分权是所有权四项权能的核心,是财产所有权人最基本的权利,处分权在多数情况下由所有权人享有,但在特殊情况下,人民法院、清算组和担保物权人也可以依法行使处分权。《农村土地承包法》对林地承包继承权的法律规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民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的赋予,标志着农民对家庭承包权和经营权具有了处分权。
《物权法》则将这种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并与所有权相并列,经济学界有学者将其称之为“准所有权”。[9]实际上,家庭承包权已经转变成为了集体所有权的一种次级所有权。
三、家庭承包权的性质转变对农地产权结构的影响
家庭承包权实际上只是集体土地的一种次级所有权。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的实质是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次级所有权、经营权分置。家庭承包权的性质转变引起了我国当前农地产权结构的变化。
(一)家庭承包权的性质界定及其产权分置
1.次级所有权:家庭承包权的性质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家庭承包是指将农村土地的经营权以农户家庭为单位,按照法定程序和原则承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一种方式。农户家庭享有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流转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权,承包地被征用、占用补偿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同时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赋予农民对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权、担保权和入股权。
由此可见,实践中的家庭承包已经由经营层面的经营形式转变成了分配层面的分配形式,权利内容已经由经营权扩展到了所有权,并且得到了政策支持和法律保护,转变成了一种土地所有权,即集体所有权的次级所有权。
2.集体所有权、次级所有权、经营权分置:“三权分置”的实质
正因为家庭承包权的这种次级所有权性质,实践中农民才能以退包、转让、互换、继承、抵押等形式处分家庭承包权,以转包、出租、入股等形式流转经营权,政府也才在坚持集体所有制不变的提前下,给予政策支持和法律保护。所以,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其实质就是集体所有权、次级所有权、经营权的分置,是在坚持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稳定农户家庭承包权(即次级所有权)、放活经营权。
(二)农地产权结构的变化
1.农地产权分配结构的变化
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都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这是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产权分配结构是:土地被分为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两个部分,城市土地属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
由于家庭承包经营权的性质转变,使农地被分为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分配给了集体成员所有的“农民家庭承包地”,主要包括耕地、自留地和自留山等;另一部分是没有分配的集体其他土地,主要包括“四荒地”、集体建设用地、预留地和包括道路、河流、水库、渠道在内的公共用地等。农地产权分配结构是:“农民家庭承包地”的一级所有权属集体所有,次级所有权则属农民家庭所有;没有分配的集体其他土地所有权属集体所有。
2.农地产权经营结构的变化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由于历史和习惯等多方面的原因,学界和国家政策法律都将家庭承包经营权和其他方式承包经营权合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产权经营结构是:所有权属集体,经营权属农民家庭或其他方式承包人。
由于家庭承包经营权的性质转变,“农民家庭承包地”的产权经营结构可分为自主经营结构和非自主经营结构两大类。自主经营结构是:一级所有权属国家或集体,次级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为一体都属农民家庭;非自主经营结构是:次级所有权属农民家庭,经营权属经营者。
集体其他土地的产权经营结构也可分为其他方式承包地和非承包地两个部分。其他方式承包地的产权经营结构是所有权属集体,经营权属承包人;非承包地的产权经营结构是所有权属集体,集体经营或成员共同使用。
3.农地产权处分结构的变化
根据法律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农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承包地不得买卖。由此可见,只有国家才有农地处分权,只有通过国家征收或者征用才能现实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转移。
家庭承包经营权的性质转变,使农民对承包地有了互换、转让、继承和抵押等处分权。性质转变后的家庭承包经营权只是一种次级所有权,一级所有权仍然属集体所有,所有制性质没有变。农民可以通过互换、转让、继承和抵押等处分行为实现农地次级所有权的转移。
综上所述,由于家庭承包的层面转移,权利内容的扩展,家庭承包权从经营层面的经营权转变成了分配层面的一种所有权。如果单从法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既不利于其性质的准确把握,也不利于说明其性质的转变对农地产权结构的影响。只有坚持以马克思土地产权结构理论为指导,对家庭承包的层面转移及其权利内容的扩展进行综合分析,才能解开“家庭承包权”性质之谜。
[1]黄和新.马克思所有权思想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1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7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0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414.
[6]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16.
[7]李振亚.改革开放二十年[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88.
[8]韩志才.土地承包经营权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48.
[9]洪明勇.马克思土地产权制度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500.
责任编辑:叶民英
F3
A
1004-3160(2017)04-0094-05
2017-04-21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家庭承包权性质研究”(项目编号:16C1163)。
周猛,男,湖南怀化人,湖南医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