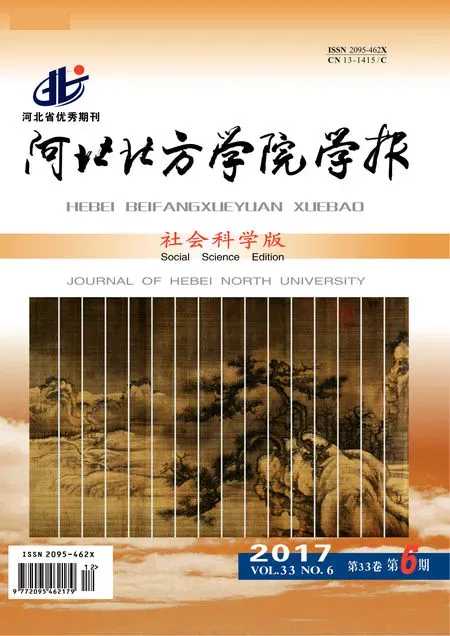明清与民国时期贵州方志中民俗书写变化研究
任 柳,陈婷婷(.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09;.绥阳县城镇管理局 环境卫生管理所,贵州 遵义 563300)
地方志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对中国地方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起到重要作用。它不仅是一种文献载体,更是中国古代乡绅阶层思想文化观念的表现。地方志具有特殊的话语功能,从其话语功能层面来讲,无论书写者持何种“客观”态度,本质上仍然是其思想观念的外在表现。其中,书写者的主观动机才是最主要的,风俗书写也不例外。从明清到民国时期,风俗书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国的风俗书写无论在书写内容还是书写方法上都与前代大不相同,这种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目前,学术界对民国风俗研究范围所及甚广,主要集中在民国风俗西化和社会风俗的变迁等问题上。李少兵[1]和司岩梅[2]等人指出,民国风俗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处于一个革故鼎新的转折时期,而新旧风俗交织在一起,不可能是完全的新,也不可能是完全的旧。所以,在当时呈现出新旧并陈和中西混杂的格局;严昌洪撰文指出,民国上层人士在“进步”观念的指导下,认为恶习陋俗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抵制了社会变革,不利于国民的健康与生计[3],为了促进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他们以移风易俗为口号,带领群众向落后的社会风俗挑战,倡导树立与新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的新风尚和新习惯。同时,主张社会风俗的演变要打破常规,并深化对社会风俗变迁的认识[4]。
在地方志书写中,风俗是重要的内容,书写风俗的必要性也是毋容置疑的,张俊颖在书写民国《兴仁县志》时云:“《易·观》之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岂不以民俗美敝为政教得失之关键也乎。”[5]98传统方志修纂者认为,风俗关乎政教,是方志必不可少的书写内容。风俗书写所反映的内容不仅是风俗本身,更是书写者主观判断与价值观念的表现。学术界大多注重民国风俗本身变迁的研究,而对这种“客观”风俗在书写者笔下变成“主体化”历史的研究相对较少。笔者拟从书写史角度来分析讨论民国方志风俗叙事所彰显的话语功能。
一、明清时期贵州方志风俗书写的特点
地方志是中央与地方沟通的重要媒介,又是地方官员统治与治理地方的重要参考资料。所以,关于风俗的书写在地方志中显得尤为重要。光绪《平越直隶州志·凡例》中云:“牧守者求治之要,莫先于风俗,故《周官》小行人适四方集礼俗为一书。风俗之征恶,即以知政治之得失,此志方舆者,所由不容不详也。”[6]郑珍和莫友芝在所修纂的道光《遵义府志》亦云:“《周官》小行人适四方集礼俗为一书,政治之得失,即风俗所由美敝,方志必详,此者固以备黄车之时询,而实守土者求治之要柄也。”[7]在修志者看来,风俗美敝是政教得失的直接体现,“风俗”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地方志中所记载的风俗内容对帮助州县官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效地推行因地制宜的治理措施,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编修了大量地方志,是方志修纂的繁盛时期,这时期贵州地方志的编修也取得了较大成果。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黔记》、万历《贵州通志》、康熙《贵州通志》和乾隆《贵州通志》等。这些地方志亦将“风俗”书写纳入其中,并作为其重要的一目,对贵州各地的风俗习惯均记载较为详细,这足以看出风俗书写的必要性。
在体例上,明清贵州地方志主要采用平分列目体和纲目体的形式叙述,关于“风俗”的归属,如明代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以当时的行政建置划分类目,其各细目下述及贵州各地的建置沿革、郡名、至到、风俗、形胜、山川、公署、寺观和祠庙等方面的内容,采用平分列目体形式,把“风俗”单独作为一类进行书写。清代康熙《贵州通志》采用纲目体的形式,其在舆图、星野、建置沿革、疆域、大事记、山川和风俗等目下相应地述及贵州各府、州和卫所的相关情况。“风俗”目下,在“序”中先总述了大部分贵州人民的来源及性情等方面的情况,接着以贵州府、州和卫所为子目来叙述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康熙《贵州通志》载:“余奉命总制滇黔七载于兹矣,兴釐之暇,每念两省之疆域、山川、人文、风俗,不可无记。”[8]乾隆《贵州通志》采用纲目体进行书写,把“风俗”归入地理志中[9]115- 117。总体上,嘉庆前的贵州地方志,主要把“风俗”隶于“地理”或“方舆”门下,或者直接将其作为一类目,如鄂尔泰所修的乾隆《贵州通志》,将“风俗”安排在“地理”门下,与舆图、建置、疆域、形胜、山川、关梁和邮传等共同作为子目;康熙《思州府志》将“风俗”隶于卷一“区域志”门下,位于子目星野、沿革、分界、形势、山川、关梁之后的位置[10]。清人修志多以天、地、人3大版块统摄全书,天文志写星野、气候和祥异等内容,风俗往往被置于地理部分,采风观俗,表征着中央王朝对于地方的统治权力,方志修纂者屡引《周官》“小行人适四方集礼俗为一书”,以证明它属于方舆或地理志应当书写的内容。
在内容上,明清地方志的风俗书写内容比较简单,主要记载地方文教和农业种植方面的内容,书写者往往以中原文化传播者自居,歧视少数民族风俗,提倡儒学教化,要求人们遵守“礼义廉耻”。如乾隆《贵州通志》描述贵阳府时云:“俗尚朴实,敦礼教,士秀而文,民知务本。端儒术重气节。处者耻为汗下之事,仕者多著廉洁之称。风土近刚,习尚从俭。性情每多质直,器用绝少奇淫。民务稼穑而鲜贸迁,士敦诗书而多彬雅。”[9]115按士农工商或春夏秋冬的顺序进行记载,从国家正统文化的角度去书写地方风俗,统一文教,惩恶扬善是其主要目的。
二、民国贵州方志风俗书写的特点
在西学和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新旧风俗交织在一起,一些修志者一改过去的封建思想,用现代的新知识和新视角去编纂方志,呈现出“新旧并存,中西兼容”的新特点,这在大多民国贵州方志中都有所体现。
(一)体例杂陈
就书写方式而言,民国贵州方志的编纂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体例上,民国地方志虽然大多仍采用纲目体,但一些书写者采用了西方的章节体结构进行编纂,如《榕江乡土教材》《荔波县志资料稿》《紫云县社会调查》和《遵义新志》等。在编纂时,对于风俗的安排比较“混乱”,没有固定的格式。有的将“风俗”载于“文教”或“民政”门下,如民国《桐梓县志》,“风俗”被安排在“文教”门下,与“学校”和“典礼”共同作为子目。民国《剑河县志》分上下编,在下编首门“民政”中有子目“祀典”“礼俗”“语言”“宗教”“保甲”“户籍”“仓储”和“卫生”;有的效仿清乾隆《贵州通志》,将“风俗”载于“地理”或“方舆”篇,如民国《黄平县志》将“风俗”隶于“方舆”门下;大多数将“风俗”隶于“风土”或“风物”,其中主要以刘显世和谷正伦编修的民国《贵州通志》及张俊颖编修的《兴仁县志》为代表;民国《榕江县乡土教材》则将“风俗”置于“乡土社会”中,其下涉及客家的婚丧、边胞婚姻及衣食住行方面;民国《紫云社会调查》中,“风俗”被安排在第三章“人文”下,与人口、语言、宗教和生活习惯等共同作为子目。
在研究方法上,民国一些方志编写者除了采用传统的访谈法和叙述法外,还开始利用西方新史学的研究方法,对贵州各属之内的桑梓文化和风土人情进行社会调查,如民国吴泽林编写的《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中制作了各种社会表,对摆金镇、苗寨马鞍井和夷寨么雪等地各家的生活状况及生活费用作了调查,并将分析结果附于志中。在食物和布料的价格方面也作了调查,并制作了《食料计价表》。此外,还有《燃料调查表》和《婚姻统计表》等,主要是采用调查和统计的方法编写而成。在乡土志中,绘有男女鞋式、女子缠足、头巾、夷女服饰、打田苗服饰及头巾等[11]301- 308。这种从现代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全面调查的方法,在当时是非常稀少的。志中不仅不失传统的叙述方法,而且更加突出运用计量化知识。因此,类似这样的志书涉及内容广泛,也具有现代社会学调查报告的范式。
民国地方志在编修方式上的变化是书写者思想变化所致,由于当时处于新旧交替和中西碰撞的社会环境中,其编修者对西洋文化极其崇拜。因此,在编写方志时也必然有西方文化的印记。
(二)“五族”并书
就书写对象而言,明清贵州方志编纂者在书写风俗时,偏重对汉族风俗习惯的叙述,尽管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也不乏记载,但在书写态度上并不将两者置于同等地位,而更多具有载记猎奇的心态。同时,一些地方志也并不将其置于“风俗”下,而是另列“苗蛮”和“蛮夷”等目加以区分。
辛亥革命胜利后,针对中国民族矛盾长期尖锐的现象,孙中山提出“民族主义”以教化各族人民,宣扬只要是中华民族,即使各族间在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也一律平等[12]592。民国地方志编修者在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将苗、回等族的风俗与汉族风俗摆在同等的书写地位,他们除了书写汉族的风俗外,把苗族、回族、布依族、彝族、黎族、瑶族、土家族和仡佬族等族的风俗与汉俗平列书写,同等对待。如:张俊颖所编修的民国《兴仁县志》,在其“风俗”目下,回族、苗族与汉族共同作为子目,分别叙述了婚姻、丧祭和时尚等方面的内容[5]98- 115;民国《荔波县志资料稿》第二章将布依族、水族、汉族、苗族、侗族及僮族的风俗习惯平列书写[13]443- 467;在民国《镇宁县志》的“民风志”下,汉族同夷、回等族一同放在子目“民风”中进行叙述,其内容主要是婚丧礼[12]592- 603;民国《郎岱县访稿》中也叙述了汉、苗、夷和土等族风俗习惯。类似这样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平等记载的情况,在民国贵州地方志中很多。民国《定番乡土教材调查报告》《兴义县志》和《普安县志》等,把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同等对待。民国《兴仁县志》作者张俊颖强烈批判封建时代民族之间的隔阂,并以兴仁县为例,指出该县自明以来形成了汉、回、夷3族,自为风气,嫉视日深,民元以前,每每酿成流血惨剧。因此,他认为应该消除民族隔阂,提倡民族团结,“今五族一家,平等待遇,非复封建时之阶级歧视,亟应泯畛域之芥蒂,进归一道同风,潜弭桑梓之隐祸,共挽危亡之神禹,方不负先总理民族主义之训示也”[5]98。这充分表明当时的地方知识分子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用比较平等的眼光来看待各族人民,并希望以此建立“大同之世”的局面。
(三)凌杂米盐
就书写内容而言,民国方志编写者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对“风俗”的书写内容大大增加,甚有“凌杂米盐”之势。除了记载明清时期方志中所记载的冠、婚、丧、祭及节序方面的内容外,还增加了时尚、服食、风水迷信、禁忌、杂俗、文化信仰和语言等内容。民国《册亨县乡土志略》第九章主要从4个方面书写风俗:一是生活状况,其下包括衣、食、住、行、起居、卫生、救恤制度、家庭状况、亲属关系、家庭制度、社会组织、土司遗制、劳工状况、失业人数和无业人数;二是社会习尚,包括交际、勤惰、嗜好、赌博、匪盗、娼妓、主佃关系、奴婢制度、赛会、讼争和械斗等;三是婚嫁情形,包括订婚办法、聘礼种类、结婚仪式、成婚后之礼节、结婚年龄、离婚习惯、结婚手续、改嫁手续、赘婿习惯、多夫或多妻制和童养媳;四是丧葬情形,包括始丧情形和入殓手续两个方面[14]609。民国《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在其“社会”下的生活状况中,记载了关于定番县人民的饮食、服食、住屋、燃料及杂用方面的内容[11]301- 308。民国《兴仁县志》还新立“恶俗”一目,把有违政治、法律和伦理的风俗归入其中,号召地方官员以此教导人民,禁止习染恶俗。“勿使弱小细民,受其蹂躏,良风美俗,受其破坏。”[5]106
总之,受社会环境和思想观念的影响,民国地方志的编纂在方法、对象和书写内容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民国地方志书写者们在书写风俗时开始把眼光转向社会研究方面,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看待地方文化。他们开始用一种被称为“科学”的理念去思考地方风俗,把地方民俗纳入现代民俗学的范畴中去。
三、民国贵州方志风俗书写变化背后的主观动机
地方志是一个具有话语目的的文献载体,从其话语功能层面来讲,不论书写者以何种“客观”的态度来叙述,其背后都会夹杂着书写者主观的目的性,地方志中的风俗书写也不例外。民国贵州地方精英阶层在书写风俗时,也难免在方志中流露出作者的话语诉求和书写动机。
(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
民国初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提出“五族一家”的口号,希望构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五族一家”思想对全国各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民国贵州方志的编纂者在书写方志时,虽然存在苗汉区分,但大都将汉与苗、夷等族排列在一起,平等对待其他少数民族。正如民国《兴仁县志》载:“今五族一家,平等待遇,非复封建时之阶级歧视,亟应泯畛域之芥蒂,进归一道同风,潜弭桑梓之隐祸,共挽危亡之神禹,方不负先总理‘民族主义’之训示也。”[5]98
在此情况下,地方士绅阶层开始以“民族主义”思想为指导对地方文化进行整合,他们认为风俗教化是治国的关键,所以开始关注地方风俗习惯。而编纂地方志就是其手段之一。由于贵州位于西南地区,相对于统治中心而言,处于一个容易被疏忽的边缘地带,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各民族间的矛盾较多。因此,他们比较关注贵州地区的风俗习惯,希望以此拉近贵州与中央的距离。在书写地方志时,对地方各民族的各种风俗进行对比叙述,并区分善恶,希望以此革除中国封建传统中阻碍社会进步和民族统一的“恶俗”,形成地方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局面,使国家走上富强昌盛的道路。
(二)改良风俗的执着信念
民国时期是一个中西文化碰撞、传统与现代交替的时期,人们的思想也异常激进。在西方社会进化论思想和自然科学的影响下,民国贵州方志的编纂者对中国传统的儒学体系和迷信思想进行否定,他们认为恶习和陋俗的存在已阻碍各民族间的交流和社会的发展,是中国落后于世界各国的重要原因。民国《兴仁县志·凡例》云:“回苗汉族杂居县境,习尚各殊,隔膜过深,欲谋相洽,非移易其风俗,不足为功,况各族恶俗甚多,背于现代潮流,阻止进化。”[5]16因而,他们希望通过地方志的书写来传播现代优秀风俗习惯,铲除恶习,推行现代教育,形成强大的话语功能,从而建立文明社会。
民国地方志的书写者们以西洋文明为指导,以地方志为主要工具对地方文化重新进行构建,把现代西方习俗和科技文化移植到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从而革除“恶俗”,冲击儒学在乡村的正统地位。如在婚姻上反对传统繁琐的婚礼习俗,主张只要订婚和结婚二礼即可,反对近亲结婚和门第观念等,以促进社会进化;在服饰上崇尚节俭;在卫生上主张推行新生活运动,劝导当地人民注重卫生,预防疾病;主张建立现代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组织,关注底层人民,对失业人数和劳工状况等方面进行统计,以缓解社会矛盾。这些主张基本按照西方现代的基层组织模式进行宣传,其目的一方面是革除传统社会的陋习,促进社会进步;另一方面是通过统一地方文化以构建现代“文明社会”,从而促进权力在基层社会中的有效运行。
(三)保存史料
保存史料和传承文明是文献编纂的一大功能,民国地方志也不例外。民国方志的编修者们在书写贵州的风俗时,其中一个动机即保存史料。民国《清镇县志稿》有云:“诸苗习俗,皆府志据时实记。由咸丰至今百有余年矣。与汉族同化者有之,夷俗尚存者有,然獉獉狉狉,不若畴昔之甚。今考志乘记载,与采访所得,据实志之,俾后之问故俗者,得其源流。”[15]民国《黄平县志》载:“《汉书》云:刚柔缓急,系水土之风气,谓之风;好恶取舍,随长上之情欲,谓之俗。风俗之不能强为同,由来旧矣。然忠弊救之以质,质弊救之以文,奢则示之以礼,风行草偃,政由俗革,安在不可挽颓风而进于隆古也哉?爰采之载记,略陈善败,俾观风者考焉。”[16]从上面所述可知,地方志编撰者们对于风俗的书写是希望能传承地方文化,并为后人在研究地方文化上提供文献资料。
地方志是介绍地方文化的“百科全书”,在整合地方文化上起了巨大的作用,是具有话语功能的文献载体。比较明清时期的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康熙《贵州通志》与民国时期的《兴仁县志》《镇宁县志》和《定番乡土教材调查报告》等相关资料可知,明清时期与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志中的民俗书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清时期,贵州方志中的民俗书写在体例上主要采用平分列目体和纲目体两种叙述形式。民俗书写的内容比较简单,主要记载冠、婚、丧、祭等内容。就书写对象而言,明清时期贵州地方志编纂者偏重对汉族风俗习惯的记载,在书写态度上往往以中原文化的传播者自居。
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志在书写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体例上,一些方志编写者采用了西方章节体结构进行编纂。在研究方法上,除了采用传统的访谈法和叙述法外,还开始运用西方新史学的研究方法,对贵州各属之内的桑梓文化和风土人情进行社会调查。书写内容上增加了文化信仰、风水迷信、禁忌和恶俗等。书写的对象上,地方志编修者在“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将苗、回等族的风俗与汉族风俗放在同等的书写地位。这充分表明当时的地方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和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用比较平等的眼光来看待各族人民,并希望以此建立“大同之世”的局面。总体上讲,与明清时期贵州地方志民俗书写的差异变化相比,民国时期出现变化的原因除了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外,最主要的是书写者个人思想观念的改变。
[1] 李少兵.民国风俗西化的几个问题[J].史学月刊,1994(4):56- 61.
[2] 司岩梅.民国风俗的“洋化”倾向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19(5):108- 109.
[3] 严昌洪.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改革与演变[J].近代史研究,1998(5):169- 183.
[4] 严昌洪.五四运动与社会风俗变迁[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38(3):108- 109.
[5] 冉晸,张俊颖.民国兴仁县志[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1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
[6] 瞿鸿锡,贺绪番.光绪平越直隶州志[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6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72.
[7] 平翰,郑珍,莫友芝.道光遵义府志[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2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412.
[8] 卫既齐,吴中蕃,李祺.康熙贵州通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2- 3.
[9] 鄂尔泰,靖道谟,杜诠.乾隆贵州通志[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115- 117.
[10] 蒋深.康熙思州府志[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5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488- 489.
[11] 吴泽霖.民国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7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301- 308.
[12] 胡翯,饶爕乾.民国镇宁县志[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4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592- 603.
[13] 潘一志.民国荔波县志资料稿[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5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443- 467.
[14] 罗俊超.民国册亨乡土志略[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7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609.
[15] 方中,龙在深,杨永焘.民国清镇县志稿[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36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538.
[16] 陈少令,李承栋.民国黄平县志(一)[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21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