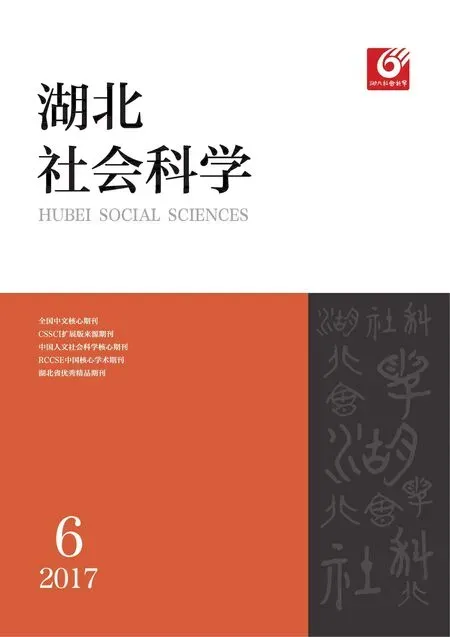辛亥革命时期共进会和文学社的离合关系探析
张亦弛,郭国祥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辛亥革命时期共进会和文学社的离合关系探析
张亦弛,郭国祥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辛亥革命时期共进会与文学社两大革命团体走向联合为武昌首义的发动及其成功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但湖北军政府成立以后,双方关系却逐渐恶化并最终走向分裂,本来占据主导地位的革命派在倾轧中丧失了对军政府的主导权,两大革命组织也两败俱伤最终烟消云散。而伴随着这个南方独立省份中最具标杆性的力量被立宪派所掌握,南京临时政府元气大失,辛亥革命的前途也随之走向了一个与革命党人设想相悖的未来。
武昌首义;文学社;共进会;辛亥革命
一百多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而这场革命中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就是武昌首义,正是武昌首义打响的“第一枪”将革命的火种点燃,使之形成燎原之势,从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武昌首义的成功,离不开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的密切配合和正确领导;但是在武昌首义取得胜利后,由于两个革命团体在各方面的分歧最后导致了革命领导权的旁落,被以黎元洪和汤化龙为代表的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掌握,最终使得辛亥革命的进程未能按照革命派理想方向前进。
一、文学社、共进会的历史由来及其发展
文学社的渊源关系可以追溯到湖北军队同盟会。湖北军队同盟会是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7月26日由原日知会会员任重远、李亚东等在武昌建立的反清革命团体。会员最多的时候达四百余人,多属新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推任重远为总干事,主持会务。并创办《通俗白话报》,由陈绍武主编,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为防止泄密,议决不定会章。后被清政府发觉,《通俗白话报》被迫停刊,任重远逃往四川,会务遂告停顿。1908年11月,光绪和慈禧先后驾崩,这给晚清政局带来了巨大的震动,革命形势也日益高涨。当时,湖北陆军正和江南陆军在安徽太湖一带举行会操,杨王鹏等原军队同盟会成员借此机会在太湖猫儿岭湖北陆军宿营地秘密商谈建立新的革命团体领导革命运动,新军返鄂后,杨王鹏又邀请了唐牺支、郭抚宸、邹毓琳、钟畸、章裕昆等革命志士共同参与新团体的创建工作,在经过反复磋商后,定名为“群治学社”,由钟畸负责起草学社章程,杨王鹏、钟畸、郭抚宸、邹毓琳、唐牺支、邹润猷、张文选、莫定国、万奇、章裕坤等十人作为学社的发起人。①据章裕昆《群治学社之始末》载:“戊申冬十月一日(十一月二十四日),湖北陆军开往安徽之太湖与江南陆军会操,两旬事竣。方待进行阅兵典礼,清太后那拉氏及清帝载湉告殂之电至,清吏对革命运动防范更密。各地同志谋之事,而鲜成功。未几,熊成基举事于皖,亦以失败闻。杨王鹏、钟畸、章裕昆等乃于太湖猫儿岭宿营地左近荒冢间密商进行,谓良机坐失,今后当鉴前车而遒来轸。有顷,奉营命用强行军,于是晚子正回驻小池口。越二日,附轮返鄂,到原驻地;即夕,杨王鹏邀唐牺支、郭抚宸、邹毓琳、钟畸、章裕昆讨论团体名义,磋商至再,始定名为群治学社。外避目标,内策自制,抑制宪章,推钟畸为草员,并以杨王鹏、钟畸、郭抚宸、邹毓琳、唐牺支、邹润猷、张文选、莫定国、万奇、章裕坤等十人为发起人。”章裕昆,《群治学社之始末》,《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为了防范清政府对革命政党的打击,群治学社名义上以“研究学问,提倡自治”为宗旨,实际上是通过该组织向新军发展,在士兵和低级军官间传播革命思想,发展新成员;之后,在刘复基(同盟会会员)之兄刘星澄介绍下骨干成员詹大悲收购了濒临倒闭的《商务报》,并在詹大悲、李六如、刘复基等共同努力下将该报发展成为“群治学社之喉舌机关也”,从此群治学社也有了自己的舆论宣传力量。庚戌(1910年)湖南抢米风潮爆发后,群治学社在黄申芗领导下在武昌策划响应,但风声走漏,湖广总督瑞澂在军中严加防范,群治学社的活动日益困难,最终被迫停止。群治学社停止之后,留鄂的同志又组织起了振武学社,由杨王鹏起草简章,宗旨标明联络军界同胞,1910年中秋在黄土坡“开一天”酒馆举行成立会议,推杨王鹏为社长,李抱良为文书兼庶务,继续进行革命事业,并得到新军士兵和低层军官的积极响应,其中第四十一标第一营左队队官潘康时对革命组织多方掩护,但久之也渐为协统黎元洪所知,黎将潘革职并委亲信施化龙继任队官,施化龙阳与杨王鹏交结,而阴则探其行动,报告黎元洪,黎又将杨王鹏、李抱良(李六如)开革,学社改由蒋翊武主持,之后又改名为文学社。从文学社发展上来说,可谓是一波三折,正如蔡大辅所说:“本社(指文学社)发源群治,过渡振武,成功文学”。[1]文学社成立时间虽然较晚,正式成立是在1911年1月30日(辛亥元旦),但其可以追溯到群治学社,可谓源远流长,而且其基本原则与群治和振武可谓一脉相承,都是以军队为发展源头,重视士兵和底层军官的发动,同时文学社还吸取经验教训,发展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因此在新军中迅速发展,及至1911年6月,新军中社员“将近两千人”,[2](p125)到武昌起义前夕更达“三千人之众”,[3]成为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成为革命中最主要的力量,“武昌首义,扛枪拖炮,以光复三镇,鏖战阳夏者,大抵皆文学社社员”。[4](p9)
共进会,发起于日本东京,其发端是中国同盟会于丁未新设的“联络部”,该部职责是联络各省秘密会党,焦达峰被推为调查部长,在他的联络下,湖北刘公、居正、彭汉遗、孙武、杨时杰,四川张伯祥、余晋城,江西邓文翚等思想比较激进的青年都纷纷加入进来。他们认为同盟会缓不济急,需另设可以团结会党的团体,即日起事;又提出同盟会誓约中的“平均地权”语意含糊,不是引车卖浆者之流可以理解的,将其改作“平均人权”,“以免收揽会党多费口舌”。②张难先《共进会始末》中对共进会成立有记载:“未几,达峰及川人张伯祥、余晋城、吴祥慈、赣人邓文辉、鄂人刘仲文,以长江各省会党头目,皆脑筋简单,非另设小团体,并委用熟悉会党情形者,分途招纳,不易收效”。又载:“又以同盟会誓约之‘平均地权’四字意义高深,非知识幼稚之会党所能了解,故另约一部同盟会会员,组织共进会,以司此项联络任务;且将‘平均地权’改作‘平均人权’,以免收揽会党多费口舌”。对思想激进的共进会成员来说,土地问题、民生问题都是次要的,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主要还是“排满革命”。
共进会在编制上采取了同盟会的“三等九级”,“以同盟会总理为(共进会)总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共进会是同盟会这个泛革命家大联盟下的外围组织,但它在组织上实际上是独立于同盟会之外的。③张难先《共进会始末》中载:“此事(指成立共进会)进行异常秘密,其编制三等九级,一如同盟会;并以同盟会总理为总理,直同盟会之外府也(达峰于立会前,尝举以告黄克强(即黄兴),克强以为不可,曾与驳论数次。及闻其已经成立,而总理放在越南筹划军事,未便商讨,遂亦置之。”同盟会首任会长为张伯祥,会员以湖北籍人士居多,共进会以“排满革命”为宗旨,要求汉族民众团结起来反抗清朝统治,以雪“屈辱于区区五百万腥膻之鞑虏”之奇耻大辱。共进会在组织上具有鲜明的会党色彩,订立山、水、堂、香为暗号,将扩张的方向瞄准在了会党和军队,提出了号召会党、运动军队的发展方向。1908年后,共进会成员先后从日本回国,回到原所在省份进行革命活动,东京共进会的使命也随之宣告结束。孙武回鄂后,在另一东京共进会成员郑江灏帮助下成立了共进会湖北分会,先后发展了刘玉堂、丁立中、立白贞、吴肖韩、邓玉麟、黄申芗等新成员,在这些新会员帮助下很多士兵和会党都纷纷加入进来,为了进一步加强管理,孙武将各地会党以镇的军事组织形式进行编制,但是成效不大。会党成员三教九流,角色多样,而且大都为图财牟利而来,作风散漫,不愿受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因此起事易走漏风声,起事后也经常不服管理,鉴于会党散漫的纪律作风,共进会湖北分会将目光逐渐转向军队,为了更好地“动员新军”,孙武对群治学社(文学社)的“抬营主义”政策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所谓“抬营主义”,是群治学社(文学社)在湖北陆军中发展成员所采用的政策,群治学社(文学社)主要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新军,利用士官身份结交新军中的低级军官,并将这些低级军官发展成为组织成员,再通过这些低级军官将其所统属的营、队成员都争取过来,这种将成建制的军队吸纳进入组织的动员方法就是“抬营主义”,通过这一方法,群治学社(文学社)力量得到很大的加强。①参见章裕昆:《群治学社之始末》,《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组织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490-491页。孙武在群治学社“抬营主义”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1)将军队作为动员对象可以消除清政府对共进会组织发展带来的威胁;(2)将军队作为动员对象可以有效减少训练革命运动的成本;(3)军队进行动员的对象是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4)动员时首先采取提供资金、结交朋友以及施予小恩小惠等办法同其拉近关系;(5)动员士兵和下级军官时可以以他们继续为清军效力没有前途的理由说服他们;(6)要充分激发士兵和下级军官对革命的信心,确保动员对象对革命运动的忠诚。②参见高筹观:《湖北起义首领孙武传》,《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七辑,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1页。孙武改良的“抬营主义”动员办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大量新军士兵加入到共进会组织中来,共进会力量得到了显著提升,成了文学社之外湖北地区又一大革命力量。
二、文学社和共进会在革命风暴中走向合作
1911年春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失败使得革命中心从岭南向长江中游一带转移,湖北革命党人对革命在长江中游首先发难的信念更加坚定,进一步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文学社和共进会分别积极在新军中发展组织,以至于出现这样的情形:同一标营内文学社和共进社都各有代表;同一名士兵,遭受两个团体争抢,从而造成不少矛盾和冲突。如当时马队的士兵开始并未正式加入文学社,文学社开代表会议时向马队发出邀请希望他们派代表参加,同时马队也收到了来自共进会发出的邀请参会函件,马队就公推黄维汉、章裕昆两位作代表前往两团体参会,考察哪个团体更适合加入再做决定。结果,先去了共进会后发现共进会并未开会,孙武拿出共进会志愿书请二人填写,黄维汉即握笔填写,而章则托故未填,之后又去文学社开了会,回来后章就指责黄单独填写志愿书是破坏团体行动之举,马队同志最后商议决定一致加入文学社,这使得黄维汉不得不修函向共进会提出撤销入会申请,并引发了共进会会员陈孝芬与章裕昆的反复辩难,后经刘尧澄出面调停才平息。③参见章裕昆:《文学社之组织与活动》,《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组织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498-499页。两团体经常互相攀比会员人数,甚至彼此相互歧视,给革命运动开展平添了诸多阻碍。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共进会与文学社走向联合是必需的。
1911年4月初,蔡济民、查光佛、梅宝玑、牟鸿勋、陈磊等在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组织团体中间积极奔走,多方斡旋,最终促成两个团体同意各推代表进行相互协商。双方的第一次会谈于5月11日在长湖堤西街八号龚霞初家中展开,故又称这次会谈为“龚寓会议”,文学社干部刘复基、王守愚等,与共进会代表杨玉如、杨时杰、李春萱做为双方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谈。双方就武昌革命方略交换意见,会议“畅谈颇久”,双方认为“彼此观点,无甚悬殊”。由于“双方代表系初次接洽,都存了几分客气”,因此会谈的总体气氛比较融洽,这也是因为这次协商只着重确定两个团体合作的基调,对于两个团体合并问题则并未有太多涉及。①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对第一次合作有详细记载:“经蔡济民、查光佛、梅宝玑、牟鸿勋、陈磊等多方斡旋,两团体均允推代表协商,遂于四月十三日(5月11日)在长湖西街八号龚霞初寓开会。文学社由刘尧澂、王守愚、蔡大辅出席,共进会由杨玉如、杨时杰、李作栋出席。杨、李与刘、王等先就武昌革命进行方略概括地交换意见,畅谈颇久。彼此观点,无甚悬殊。谈到两团体合作本题上,双方代表因系初次接洽,都存在了几分客气。杨、李云:‘我们两团体向殊途同归。现在正是同归不必殊途的时候了,只求双方在原则上同意合作,一切问题均可从长计议。’刘、王亦云:‘我们两团体宗旨目的都是一致的,合则两美,离则两伤;譬如风雨同舟,大家只期共和,到达彼岸就得了,有甚么不可商议?’于是彼此都以革命到了的紧急时期,提出一件应办的事来,拟令各标营两团体的代表极力避免摩擦,万不可互争党员,只要受了运动的同志,都是革命党员,不必分谋社某会的畛域。双方代表均赞同,决定即日实行。”共进会与文学社争论的焦点包括这样三个方面:(一)合并后新团体的领袖人选问题。杨玉如曾载:“龚寓会议,共进会本拟谈合并问题,但杨、李并未提出,以两团体各有历史,各有组织,尤其领袖人选不易解决。”据杨如云解释,虽然文学社领袖只有社长蒋翊武一人,但共进会领袖实际上有刘公、孙武、居正三人,虽然以刘公为会长,但刘公对武昌革命工作并没有以领袖自居也没有取得干部的拥戴,孙、居二人态度也是这样,共进会议事多采取合议制,属于典型多头政治,因此关于合并后新团体领袖属刘、蒋,还是孙、居,仍有很大的争议,是合并众多问题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据章裕昆载:(第一次会谈中)杨玉如谓孙武有款甚巨,拟拨付文学社补助费。杨时杰请改推孙武为领袖。文学社同人均反对。刘复基谓本社绝不受补助费;但孙武如有计划,在可能范围内,当竭诚接受,彼此不得猜疑,互肆破坏,众皆谓然。”②参见章裕昆:《文学社之组织与活动》,《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组织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498-499页。原载《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关于此事记载又见李廉方著《辛亥武昌首义纪》(见湖北通志局《鄂故丛书》记述云:“玉如提议文学社改推孙武为领袖,其社费由共进会补助之。尧澂曰:文学社社员饷械有着,社费则向例抽提薪饷,无须补助。惟军事指挥,首在情愿交孚,改推领袖不便。如孙武有所计划,当在可能范围内,竭诚接受,众无异言。”但杨玉如在《辛亥革命先著记》中本人回忆时认为并无此事,称“双方在极和谐气氛中进行,本人(指杨玉如)并没有提出更易蒋翊武的领袖与资助文学社经费的话”,认为上述论述“恐系未参与龚寓会议同志误听传言,向通志局投稿,李先生援稿编入致有分歧”。虽然此事可能并非事实,但原文学社成员章裕昆有此记载,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共进会以孙代蒋声音可能的确存在。可见关于共进会和文学社合并后新领袖问题的复杂性。(二)合并后新团体名称和新组织机构设置问题。这一问题在第一次协商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在7月20日第二次磋商上孙武、刘复基先后做出让步,刘公随后发言又宣布自愿放弃东京共进会时期被预推的湖北都督一职,而蒋翊武、王宪章随即也表态愿意放弃原文学社一应职务,从而最终达成了废除原有团体名义和原团体时期预拟的个人负责名义,克服了这一难题,并最终建立起新的革命总部和组织机构。③参见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419-420页。(三)文学社和共进会历史发展中遗留问题,这个主要表现在双方在过去争夺军队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矛盾。这里举一例说明,在孙武家中第二次会谈时,蒋翊武称“时间无论何事,应以少数服从多数”,认为文学社人数比共进会多,共进会应服从于文学社的领导,引起了孙武的不满,与蒋比力量、论大小;④参见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而蒋在第二次会谈结束后私下与陈孝芬交谈时说:“合作固好,但是他们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5](p72)对于这样一些争议性问题,共进会与文学社巧妙地选择了搁置,把革命运动放在了首要位置,甚至为了避免新矛盾产生,之后一次会议孙、蒋二人都没有参加,正是双方的宽容态度为共进会与文学社两个团体的顺利联合扫除了许多障碍。
1911年8月,四川保路运动风潮进一步扩大,清政府决定调湖北新军一部入川,在此情况下,湖北革命党人进一步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在这一情势下,9月14日(辛亥七月二十日)在武昌雄楚楼十号刘公住所召开了第三次联合会议,除蒋翊武因在湖南岳州驻防而缺席外其余重要人物一应参加,会议由刘公担任主席,蔡大辅作记录,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决定放弃原文学社、共进会名号,统称湖北革命党,统一组织领导,共同进行“排满革命”,最终完成了两大组织的合并。①参见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418-421页。文学社和共进会之所以能最终走向联合,共同进行革命,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他们的革命理念与方法上有其一致性。在革命理念上,共进会主张“排满革命”,对土地、民生问题漠不关心,其革命理念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②参见张难先:《共进会始末》,《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组织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473页。文学社由于为了组织隐蔽的需要,在简章上并未提出革命主张,但实际上却以“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③参见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文学社始末》,《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组织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为宗旨,而且无论是共进会还是文学社都对政治问题不甚关心,他们只在乎革命本身;在革命方法上文学社主张“抬营主义”,共进会尽管早年与会党联系密切但后期逐渐将重心转向军队,其方法上与“抬营主义”相似,正是在革命理念与方法上双方存在着一致性,才使双方能搁置争议,共同革命。二是革命中心的转移以及中部同盟会建立,为两个团体的联合创造了条件。过去,由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主张,起义一般选在沿海、沿边地区尤其是两广、越南一带进行,但这些起义都以失败告终。1911年春,同盟会精心组织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再次失败使越来越多革命者对孙中山的主张提出质疑,认为应在长江流域组织起义的主张逐渐占据主流,中部同盟会应运而生,共进会与文学社在全国革命地位显著上升。同盟会重要成员谭人凤回国后,衔孙中山命前往武昌视察,召集同盟会成员孙武、杨玉如、杨时杰等开会,希望其加入中部同盟会,并交给居正、孙武八百元钱供其活动,后在大江报馆同詹大悲会面时才知道文学社这一组织,随即同蒋翊武、李长龄、罗良骏、王守愚会面,得到了文学社同志支持,④参见章裕昆:《文学社之组织与活动》,《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组织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0页,原载《中华民国建国文献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二,台湾“国史馆”1996年版。很多文学社同志纷纷加入同盟会,中部同盟会建立为两党消弭分歧走向联合做出了很多工作,为其联合创造了条件。三是部分原共进会与文学社重要成员不懈努力。随着两大革命团体发展,冲突不断激化,矛盾不断凸显。为了缓解矛盾,部分有先见卓识的革命党人如文学社刘复基,共进会陈孝芬、邓玉麟、李作栋等开始从中斡旋,努力化解矛盾,为两个团体走向联合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刘复基和陈孝芬二人,为两方联合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李春萱谈及此事曾言曰:“(孝芬)与刘复基烈士确为当时斡旋最力者”。[6](p34-36)正是这些因素综合之下文学社和共进会才最终走在了一起,领导湖北革命党人在1911年10月10日(辛亥八月十九日)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在革命中建立起湖北军政府,也将行将就木的清王朝埋进了坟墓。
三、共进会、文学社在革命胜利后的分歧和冲突
武昌首义胜利以后,由于共进会和文学社主要领导人当时都不在武昌且相当一部分革命参与者认为文学社和共进会领导人欠缺威望和资历应推举有名望的有社会地位的人士担任湖北省都督,首先被推选出来的汤化龙婉拒了邀请,因此,原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最终被推选为湖北都督,组建起了湖北军政府。军政府成立后,出外避难或因病因事滞留在外的革命党人纷纷返回武昌,以“首义之功”出任要职。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政府的垮台看起来只是时间问题,而随着“排满革命”这一共进会和文学社合作的前提逐渐褪去,两个组织间并不紧密的联盟也出现了许多裂痕,加上以黎元洪、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势力政治上的分化,两个团体间矛盾再次上升,最终导致两个革命团体“分道扬镳”,联盟走向分裂,最终因为相互激烈的斗争而两败俱伤,致使“首义之区”的革命成果渐入旧势力之首,演发出一场巨大的历史悲剧。
在湖北军政府建立之初,黎元洪处境是非常尴尬且被动的,军政府绝大多数权力掌握在新军首义者手中,这些新军士兵瞧不起黎元洪,对他呼之即来,喝之即去,孙武、蒋翊武等主要革命者回归和汤化龙等立宪派上台后,黎元洪处境才开始有所好转,但总体而言仍然非常被动,军政府开会时总是“瑟瑟不语”,以黎名义发出的布告均由他人代为起草甚至连签名也由他人代笔。①据李西屏《辛亥首义纪事》载:“当时党人多亡匿在外,草创之际,因不暇因事择人。就其在场者各尽其能,互相推举。以张景良为参谋长,杨开甲复之;方定国为司令官;蔡济民、吴醒汉、张廷辅、邓玉麟、高尚志、徐达民、王宪章、王文锦、陈宏浩任谋略;李翊东为叙赏长,张振武副之;冯昌言为文书长;向讦谟为会计长;邢伯谦为军装科长。其余分隶各部任事,盖无一不得其用者。”见李西屏:《辛亥首义纪事》,《李西屏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在革命党人看来,黎元洪只是一个傀儡,“只想用黎的空名来镇定人心,并不需要黎负任何责任和过问一切事情”。②参见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75页。但是,黎元洪显然不甘心只是做一个“空头都督”,虽然他对革命依然心存疑虑,态度暧昧,甚至同汤化龙密谋派出柯逢时与清政府暗通款曲,以求后路;但他也开始在内部抓权,试图掌握主动,而他以清军高级军官身份出任新政权都督,自然成为“咸与维新”的旧人物所依靠的对象。在同汤化龙为代表的立宪派达成合作协议后,又将重点放在了分化两大革命团体主要领导人关系上,他最终将突破点放在原共进会的领袖孙武身上。
孙武是原共进会实际负责人,辛亥武昌首义主要领导者之一,为革命胜利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在起义前因为试制炸药不慎被炸伤而紧急送往医院救治未能直接参加革命,但他依然凭借其“首义之功”而在病愈后回到湖北军政府出任军务部长这一要职。根据军政府的组织条例规定,军务部主要负责军队行政工作,成员基本上都是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革命党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军务部是革命党掌控军队的特定形式,因此很有实权。但是,好景不长,随着革命领袖黄兴的到来,这种格局就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1911年10月12日清廷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领由陆军第四镇、混成第三协、第十一协编成的第一军大举南下,海军提督萨镇冰率巡洋舰队及长江水师溯流而上,对新生的政权采取合围之势,“阳夏之战”爆发,军务部面临着巨大的战争压力。尽管在战争初期军政府方面曾一度取得优势,但汉口前线指挥、旧军官何锡蕃收兵不发痛失乘胜追击的良机,随后上任的张景良更是通敌渎职,使汉口局势转危。在汉口战局处于千钧一发之际,著名革命领袖黄兴抵达武昌,督师汉口,但是面对冯国璋率领的北洋新军这支虎狼之师,民军最终失败,被迫退据汉阳。尽管如此,黄兴依然得到了军队的拥护,成为军政府军队实际指挥者,这就引起了以孙武为首的军务部的敌视。黄兴与黎元洪商议汉阳防务问题,在讨论到黄兴在军政府内名义和地位问题时,以蒋翊武、杨王鹏为代表原文学社主要成员提出推黄兴为两湖大都督,直接掌握两湖军政大权;但孙武等却坚决反对这一任命,认为“大敌当前,不宜动摇根本”,在宋教仁的调停下,此事最终被搁置,会上最终决定任命黄为“战时总司令”。但是,在“总司令”职权及由谁任命问题上又再次引发巨大争议,革命党人希望与黎元洪分权,因此提出“总司令”不经黎元洪委任;但孙武却和吴兆麟等为代表的旧势力联合力主由黎委任,孙武清楚黄兴就任总司令后自己的军事地位会受到很大冲击,而他自己在革命党中地位、影响力又都远不及黄兴,他害怕自己的权威受到压制,但又不敢直接挑战黄兴,因此他试图借助黎元洪来牵制黄兴,这是孙武选择与吴兆麟等旧势力合作的重要原因。正是在孙武等人的力争之下,革命党人最终选择妥协,黄兴最终在11月3日在武昌阅马场接受了黎元洪的拜将仪式。这一次会议后,孙武开始向黎元洪转向,而赢得了孙支持的黎元洪在政治上逐渐摆脱了尴尬的境地,进一步加紧了收权的步伐。黄兴成为“战时总司令”后,调集湖南援军援救汉阳战局,同时组织部队试图反攻汉口,这些都得到蒋翊武等原文学社成员的支持,但孙武、吴兆麟等则坚决反对,虽然计划最终实施,但以失败告终。不久,汉阳陷落,阳夏战争以民军惨败,汉口、汉阳相继失陷而告终,黄兴愤而离职前往上海。在黄兴担任战时总司令期间里,湖北军政府内部实际上形成了以“黄—蒋”和“黎—孙”的两方势力,围绕军政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斗争。[7](p320)黄兴与孙武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也给文学社与共进会造成了不小的裂痕,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关系走向破裂的开始。
阳夏战争期间,属于文学社系统的詹大悲、胡瑛、宋锡全等先后离鄂而去,这给孙武造成攻击和排斥文学社诸人的借口;汉阳失守后,曾与黎元洪过从甚密的汤化龙、胡瑞霖、陈登山等人因与首义诸人矛盾激化,也悄然离鄂赴沪,这样,武昌政治在经历短暂的模糊阶段后形成了一个“三武鼎立”的局面。而“三武”各执一端——孙武支持黎元洪,反对南京临时政府;蒋翊武亲黄兴,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张振武处于中间状态,更声言要进行“二次革命”。“三武”的不和,使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关系进一步走向破裂。
黄兴离职后,武昌形势一度极其危急,孙武貌似镇定,但内心畏怯,他极力鼓动黎元洪任命万廷献任战时总司令一职,但万担任一日后就离鄂去职,最终蒋翊武被任命为“战时总司令”,接掌了军事指挥权。文学社与共进会主要领导人之间分歧走向表面化。不久,民军第五协协统熊秉坤向军务部汇报其部属标统杨传连之前在汉阳保卫战时,曾临战脱逃,要求撤掉杨的职务,杨传连是蒋翊武的亲信,蒋得知消息后大怒,给军务部去函要求撤掉熊的协统职务。军务部为此召开会议,会上原共进会主要成员对蒋的行为大肆抨击,认为蒋翊武是“糊涂竖子”,“将来战事必败于一人(指蒋翊武)之手”,①参见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李西屏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要求蒋引咎辞职,并推选谭人凤为武昌防御使,代替蒋负责军务。最终蒋被被迫辞职,谭人凤任武昌防御使。②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载:“是夜谭人凤在武昌城内大街卞宅集杨玉如、李作栋、孙武少数人开会。杨如云:‘近日上海来电,已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想黄兴此时不能来鄂,总司令官一职,蒋翊武不过暂时护理而已。应另举人为总司令官,以便计划作战事宜。谭人凤先生系革命巨子,老成练达,素孚人望,当以谭先生继黄兴职。’在座人员皆赞成。旋谭人凤云:‘各位同志既举兄弟继黄兴之职,但此时武昌情形与汉阳不同。现在武昌系防御,将来必须北伐。人凤之意,将总司令官名义取消,应改为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盖防御者,防内奸而御外地也;招讨者,讨不廷而招之从我也。事切名实,各位同志以为如何?’于是在座者表示赞同,遂备文请黎都督任命。黎元洪即委谭人凤为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节制武昌各军,并各省援军,调蒋翊武为都督府顾问。蒋翊武因军事繁忙,事前毫无闻之,迨发表渠为顾问时,极为愤愤不平。后经大家劝解,顾全大局,始办交代。”实际上,谭只是顶了一个虚名,军政府的军事大权实际上集中到了孙武手中。
孙武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做出在政治上向黎元洪靠拢的举动,而黎则将孙更多的当作一杆枪在使,黎表面对孙十分谦恭,暗中却包藏祸心,背地里将各种劣迹责任全部推到孙武身上。孙武本人又作风跋扈,傲慢自大,对黎的“小动作”毫无提防之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武曾一度满心欢喜,携带巨资赴沪,以为能在南京政府里捞取一官半职,但最后一无所得,因此对黄兴和南京临时政府怀恨在心。③据方孝纯《辛亥首义之片断回忆》载:“孙乃报告黎元洪,携巨款赴沪,军务部职务由蔡济民代理。孙武抵南京,欲得陆军部总长职不可能,欲次长地位亦不可得,怀恨黄兴不帮助。”见方孝纯:《辛亥首义之片断回忆》,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1页。据陈孝芬回忆:“孙武于八月十九以后,与宪政派逐渐接近,旧日患难朋友反见疏远。黄申芗为人豪爽,见孙武如此,极感不快,不久遂有倒孙之事。那是不叫‘二次革命’名曰‘倒孙’。”方孝纯《辛亥首义之片断回忆》也称:”吾鄂有人称推倒孙武为‘二次革命’,此乃兄弟阋墙之争,非革命也。“陈孝芬回忆与方孝纯所载均载于方孝纯:《辛亥首义之片断回忆》,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116页。离沪返鄂后,他联合部分原共进会骨干成员组织“民社”,拥戴黎元洪为领袖,处处与同盟会作对。这自然进一步引发了原文学社团体和一小部分原共进会下层成员不满。以黄申芗为首的一批革命党人,利用群英会这个会党性反清团体,打着“改良政治群英会”的旗号,酝酿推倒由黎、孙组建的湖北军政府,之后又收缩目标,将矛头直指孙武。在他们的鼓动下,从四川返鄂的第三十一标组成的教导团,由文学社成员王文锦、王国栋领导的伤病团体毕血会,起义老兵组成的将校团,以及义勇兵等士兵组织,“同盟会、文学社中人亦暗与群英会携手”。这些人,有的是出于对黎元洪、孙武排斥革命异己的倒行逆施不满欲起而奋战,有的因“未居权要郁郁不得”而欲发私愤,既无统一、明确政治目标,更无严密组织形式,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组织,更像一个有计划的闹事和暴动团体,而他们目的也非常明确,就只是“倒孙(武)”,而并非事变后起事者所宣称的革命目标,因此部分革命党人将这场行动称为“二次革命”并不正确,比较合适的称呼是“倒孙行动”。1912年2月27日夜,将校团、义勇团、毕血会集众数千人起事,佩戴群英会会徽,“群向孙武家抄捣”,但未获孙武。群英会在起事之时声称意在“剪除民贼,改良政治……只诛孙武一人”,但实际上“举动紊暴,秩序大乱,军政机关,破坏殆尽,乱兵盛行抢劫,借机报复”,①参见查光佛:《武汉阳秋》,官纸印书局1916年版,湖北省图书馆藏。甚至在暴乱中还失误打死了原文学社重要成员、民军第二镇统制张廷辅并伤及其家人,使原文学社和原共进会成员之间关系更加恶化。在暴乱前得蔡汉卿报信而逃避至汉口的孙武在第二天宣称要调兵平乱,但实则已经无兵可遣,经武汉绅商与武昌黎元洪、汉口孙武协商,孙武被迫以自己“疲敝之身,久膺军务”请求“解职养疴”。②参见辛亥武昌首义纪念馆、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黎元洪关于孙武辞职等事致袁大总统孙大总统等电》,《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页。原刊于《民立报》,1912年3月4日。而借助此事,黎元洪不仅赶走了与自己既相互勾结但更对自己有威胁的孙武,成功扶起自己的亲信旧军官曾广大接替孙武担任职权大大缩水的军务司长一职,又成功的进一步激化了原共进会与原文学社成员之间的矛盾,使孙武及共进会成员将仇恨完全聚集在文学社身上,同时他又利用这个矛盾以文学社诸人参加“群英会”叛乱为由将文学社成员大加抓捕杀害,连部分已经离鄂的主要成员如蒋翊武、王宪章、胡玉珍等也未能逃脱。③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载孙中山复电:“冬电悉。军务司长孙武辞职,派曾广大接充,内务、教育两司,亦均得人,商民不惊,市井无恙。”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页。孙武在“倒孙”事件后十余天在《民立报》发表《孙武宣言书》称:“二十七日晚,近卫军、将校团、义勇团、毕血队以及诸闲散之军士,竟然集合暴动,枪弹乱放,刀械横施……沿途肆意抢劫,行同匪类,并将孙武家抄洗一空,军务部暨各部总稽查处打汇无存;枪毙二镇统制张廷辅,伤及家人;围杀四镇统制邓玉麟,绕攻各部,搜杀交通部长,自许总司令官……军队三五成群,时放枪弹,扰乱市面,威吓居民,掳掠劫杀,种种野蛮,惨无人理”,对“倒孙”参与者表达极度不满,称其“乱党”。孙武:《孙武宣言书》,原载于《民立报》1912年3月13日,选自《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254页。通过为期一天“倒孙”事件,黎元洪成功地清洗了湖北军政府的革命力量,使文学社和共进会两败俱伤并彼此愈加仇恨,再也没有了联合的可能,尽管孙中山努力调停但也收效甚微。一年之后,黎元洪又借袁世凯之手除去了其一直嫉恨的张振武,文学社和共进会从此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四、共进会、文学社关系分裂的原因探析
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首义胜利后从合作走向分裂,关系逐步恶化,因彼此的仇恨而争斗最终两败俱伤,退出历史舞台,并不是偶然的结果。文学社和共进会之所以最终走向分裂,其原因在于:
第一,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成员构成、政治理念和革命方略上存在着很深的门户之见。文学社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湖北军人同盟会,是一个湖北本土土生土长的革命组织,从一开始就以军队为发展方向,因此成员几乎都是新军士兵,在革命上注重低调踏实,但没有特别清晰长远的革命规划,只有一个“推翻满清”政权的短期革命目标,对于革命后政权建设等都缺乏考虑,而共进会发端于中国同盟会,骨干成员以留日学生为主,他们同会党联系密切,思想激进,在革命上比较注重高调起事,讲求声势,因此共进会成员对于文学社成员多瞧不起,认为他们是“土老帽”,而文学社也不喜共进会的作风,认为和共进会合作会吃大亏。①参见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2-73页。正是在政治理念上的不一致性,使得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失去“排满革命”这个共同利益基点之后再难生出一点同仇敌忾之心,原有的矛盾却在争夺新政权利益果实中不断激化,最终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走向对抗。
第二,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因地域关系存在畛域之见,湘鄂之争十分突出。文学社和共进会虽然都在湖北地区尤其是武汉三镇活动,但文学社成员以湖南人为主,对于湖北籍成员多有排斥,而共进会从湖北分会成立之初就以湖北籍人士为主,因此很多在文学社里遭受排挤的湖北籍成员在湖北共进会一成立后就纷纷加入,正是这种地域之见让两大组织在发展中就产生了很多不和,尽管后来因革命需要而被遮蔽,但随着黄兴的到来矛盾又再次突显。黄兴是湖南人,到汉督师后,因鄂军久战疲劳而多倚赖援鄂湘军,而在汉阳保卫战中湘军甘兴典部溃走岳阳,王隆中部又擅自退出战场,这更加引发原共进会成员不满。正是军政府内部鲜明的畛域分歧,让军政府内部斗争纷争不止,也让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在不断的地域冲突中走向瓦解,正如孙中山后来所说,“湘鄂之见已荫,而号令已不能统一矣。”[8](p208)
第三,文学社和共进会主要领导成员的性格缺陷致使冲突不断扩大,最终走向分裂。孙武出任军务部长后,“趾高气扬”,“行为乖谬”,不为大家所喜;蒋翊武“如田舍翁”,缺少机巧变通,不能服众;胡瑛革命后贪图享乐,贪念权位;②参见方孝纯的《辛亥首义之片断回忆》和潘康时的《记文学社》(两文均刊载于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編:《亲历辛亥革命——见证者的讲述(中)》,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章裕昆的《文学社之组织与活动》(《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组织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陈孝芬的《辛亥武昌首义回忆》(湖北省政协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刘公为人宽厚老实,缺乏权变。正是这些领导者在性格方面的缺陷,使他们难以很好的协调好革命党内部的矛盾,反而使他们不断激化,最终使得原本亲密合作的两个组织分道扬镳。
第四,旧势力的破坏和挑拨离间致使矛盾扩大。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旧势力不能容忍新政权被革命党所掌握,他利用革命党人之间的内部矛盾,不断地拉拢分化,最终使得双方彼此仇恨,联盟走向分裂。作为安徽巡抚朱家宝打入鄂军政府的高级密探孙发绪利用孙武的骄傲自大性格缺陷投其所好大献殷勤,博取孙武欢心和信任,并将孙武一步步诱入更深的歧途。正是旧势力的挑拨离间和破坏,使得两个团体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走向了破裂。
武昌首义的成功是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精诚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他们因为种种因素在起义胜利后没能继续携手共进,而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走向了分裂,这直接导致革命的前途发生了巨大的转向,本来占据主导地位的革命派在倾轧中丧失了对军政府的主导权。而伴随着这个南方独立省份中最具标杆性的力量被立宪派所掌握,以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失去了他们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最大助力后元气大失,辛亥革命的前途也随之走向了一个与革命党人设想相悖的未来。
[1]蔡大辅.启事[N].中华民国公报,1911-12-20(10).
[2]万鸿阶.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A].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
[3]前文学社同人公白:武汉革命团体文学社之历史[N].民立报,1912-10-7.
[4]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M].台北:正中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1.
[5]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A].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6]吴剑杰.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在湖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
[7]冯天瑜,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8]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A].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唐 伟
K251
A
1003-8477(2017)06-0116-09
张亦弛(1993—),男,武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郭国祥(1968—),男,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6-2017年度武汉理工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培育项目“清末民初湖北地方革命组织的发展及其嬗变研究——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例”(2016-YS-1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武汉市武昌首义中学校本课程文化建设的探索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