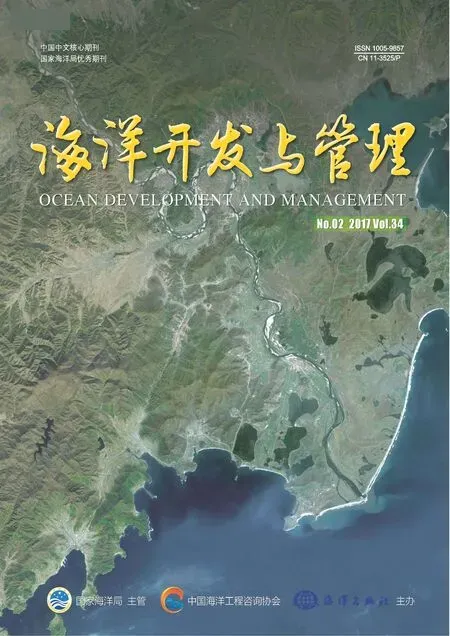浅谈区域划分与环境调查对沉船考古工作的重要性
赵子科,陈春亮,张际标
(广东海洋大学海洋资源与环境监测中心 湛江 524088)
浅谈区域划分与环境调查对沉船考古工作的重要性
赵子科,陈春亮,张际标
(广东海洋大学海洋资源与环境监测中心 湛江 524088)
沉船考古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工作,水下环境复杂、文物打捞操作困难、海洋人文资料缺失等因素制约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沉船考古工作不仅要对沉船本身及所载器物进行考古发掘,还要结合陆域考古学、海洋学划分重点沉船区域进行系统性发掘研究,对沉船本身及所载器物所处的海底环境和受腐蚀状况进行详细调查和研究,为文物修复和保护工作提供支撑。
沉船考古;沉船区域划分;环境调查
纵观世界历史发展轨迹,历史强国都是由大陆走向海洋、从海洋走向世界,最终走向强盛。陶瓷器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深受西方各国的喜爱,其大规模的输出为中外文明交流做出巨大贡献,而这一过程的实现正是通过海运完成。在唐、宋、元、明、清历代陶瓷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稳定的航线,这条航线后来被日本学者称为“陶瓷之路”[1]。由于古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比较落后,在面临复杂海洋气象环境时沉船事故时常发生。我国传统考古学研究主要集中在陆地性农耕文化及黄河、长江流域,而海洋考古发掘由于各方面限制而不被重视[2]。随着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和“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提出,海洋沉船考古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我国海洋沉船考古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收集汇总,分析沉船重点区域划分与环境调查对沉船考古工作的重要性,从而为海底水下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1 近年我国沿海沉船考古发现
20世纪80年代,英国人哈彻在中国南海盗掘一条明代沉船,由于当时中国水下文物保护工作机制不够完善,沉船中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流失海外[3],海洋水下考古发掘工作自此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此后开展了不同规模和性质的水下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以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公布的具有代表性的沉船为例,笔者通过搜集相关文献对这些沉船及沉船环境信息进行简单统计,主要包括:
辽宁绥中三道岗沉船[4],元代,位于大南铺村东南约3 n mile,船体只保留上半部分,附近有礁石,属商贸船,有陶瓷器、铁器,陶瓷器有较多完整保存;
山东胶南鸭岛沉船[5],明代,位于琅琊台海域鸭岛,船体已不存在、有凝结物分布,附近有礁石,属商贸船,有青花瓷器、铁锅、石碇,瓷器有较多完整保存;
浙江渔山小白礁沉船[6],清代,位于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东南约26 n mile处的渔山列岛海域,船体只保留上半部分、部分构件存在,附近有礁石,属商贸船,有陶瓷器、铜、锡、银、石、木,陶瓷器有较多完整保存;
福建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船[7],宋元,位于连江定海村东北约350 m、黄岐湾水域的一处近岸岛礁,船体只剩龙骨、有大型凝结物块,附近有礁石,属商贸船,有瓷器、金属,瓷器有较多完整保存、有大型凝结物块;
福建东山冬古湾战船[8],明末清初,位于福建省东山县古湾海滩,船体只剩龙骨、有大型凝结物块,附近为沙滩,属战船,有陶瓷器及古代作战类用具,瓷器有较多完整保存、铁器为大型凝结物块;
广东汕头“南澳一号”沉船[9],明代,位于汕头南澳岛东南三点金海域的乌屿和半潮礁之间,船体部分保存完整、尚存有多道隔仓,附近有礁石,属商贸船,有陶瓷器、铜钱、锡壶、木质秤杆、戒指、围棋棋子、果核,文物种类丰富、大多数保存完整;
广东台山“南海一号”沉船[10],宋代,位于广东阳江市上下川岛附近海域,船体保存较为完整、深埋沉积物中,属商贸船,有陶瓷器、金属器、漆木器等,大部分文物保存完整;
海南西沙群岛“华光礁一号”沉船[11],南宋,位于西沙群岛,船体部分保存完整、尚存有多道隔仓,附近有礁石,属商贸船,以陶瓷器为主、另有铁器和少量铜镜残片,大部分文物保存完整。
通过海底沉船信息可以发现:沉船发现地址分布较广泛,但最为集中的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海域,据推测仅在南海就有2 000艘以上的古代沉船[12];沉船绝大部分为商贸船,所载货物以陶瓷器最多,主要是用作国外贸易,此外还有船员所使用的日常用品如铁锅、锡壶、木质秤杆、戒指、围棋棋子等;沉船年代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宋代,并且沉船上所发现的部分陶瓷器的完整程度与年代无关,而与陶瓷器本身的质地、沉船瞬间所遭遇的气象和海洋地理状况有关;发现沉船的位置大部分位于近海海域,并且所在地址附近都有礁石存在。
2 重点沉船考古区域划分
“区域”研究不仅是地理学研究专有的方法和特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给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广阔的视角。早在20世纪8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就基于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单元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6大区系,此后才出现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家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历史文化进行的深入考察和研究工作。我国作为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海洋历史文化遗产研究和管理保护中引入区域视野,无疑将起到重要作用[13]。
目前我国已经发现水下文物点200余处、确认沉船遗址70余处,从东南沿海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时期对外文化交流、郑和下西洋直至近现代甲午海战、抗日战争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水下文化遗存都有发现[9]。参考陆地考古学区系划分,结合上述典型沉船遗址、环境及所载文物进行贸易学、历史学、考古学、海洋学、地质学的梳理分析,划分出沉船重点区域进行系统性研究,抢先重点发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水下沉船,对加快推进我国沿海沉船考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3 布局区域发掘项目,实施重点发掘
我国海洋国土辽阔、海岸线漫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仅沉没在我国领海内的商船就达数千艘之多。因此,对最具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水下沉船遗址进行抢救保护性的调查、发掘与研究成为我国考古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14]。
唐宋以来,中国海上贸易繁荣,商船从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地出发,途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到达波斯湾、红海乃至北非和地中海沿岸国家,海上航程长、航海技术落后等因素造成相当多的船舶沉没海洋,形成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区域。广东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活跃区,目前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整、文物储存最多的远洋货船“南海一号”在广东阳江被整体打捞,唤醒了沉睡海底800多年、估值约数千亿美元的“海上敦煌”;在广东汕头“南澳一号”沉船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在对沉船及船载文物进行清理的同时还重视对船体结构、埋藏过程的研究[15],其船体本身有利于对明代航海史和造船史进行深入研究。福建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水下文化遗产大省,拥有十分丰富的水下文物资源,已经发现的水下沉船遗址包括东山县冬古湾明末清初沉船、平潭“碗礁一号”清代沉船、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漳州“半洋礁一号”宋代沉船遗址、福建定海宋代沉船等。通过对以上重点沉船区域优先开展抢救性水下考古发掘和重点调查工作,可为我国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翔实的材料和依据[16],并最终形成一整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水下考古工作相关规范。
4 沉船遗址环境因子调查
沉船考古区域划分有利于相关部门开展我国水下文物考古发掘工作的整体规划,而参考海洋调查规范对沉船环境进行调查可为水下文物后期的修复和管理工作提供依据。古代船体沉没海底后通常快速腐败,直至船体及文物与周围环境逐渐达到平衡,腐败速率才逐渐变缓[17]。
4.1 海洋水文与海底地形环境调查
海洋水文调查主要包括水温、水深、盐度、潮流(流速、流向)、悬浮物、透明度、光照强度等,海底地形环境调查主要包括沉船所在海域的海洋空间立体环境[18]。温度是影响很多化学反应和微生物生长的重要因素,温度调查也可供潜水队员下潜打捞参考;水深测量在为沉船打捞工作提供参考的同时也可对海底环境进行大致判断;沉船海域因海面风浪频繁、水流急而多变,降低沉船打捞工作效率,有时还会危及船员和船上设备安全,因此在进行水下考古工作前进行潮流调查很有必要;潮流流向和流速极大影响水下作业,潮流卷起更多的悬浮物影响水下作业的可见度,当然水下可见度也与作业海域的光照和透明度有关。海洋地形环境调查主要是对沉船所在海底的情况进行记录,结合水深、潮流信息和沉船所处位置可以对沉船受腐蚀的基本情况进行大致判断;如沉船在礁石背面更不易受潮流冲刷所带来的物理腐蚀,而面对潮流的方向会增加沉船文物空间的紊乱程度从而增加文物受腐蚀的面积,此外若沉船处在入海河口而未被及时发掘则有可能被泥沙永久封存。
4.2 海水水质调查
海水水质调查主要包括金属离子、溶解氧、pH值、氯化物、营养盐。对沉船周围的金属离子进行调查是考虑到沉船木材材质长期在海水中浸泡后会发生严重降解,另外沉船所在海域的金属离子与沉船文物所形成的凝结物也给出水文物的修复工作带来极大困难[19];溶解氧是水下生物化学反应的重要反应因子,氧浓度的增加可使铁器的腐蚀反应速度加快,另外缺氧环境可导致一些五彩瓷器的彩料发生还原,使瓷器表面变色[20];pH值调查是考虑到沉船有可能处在被污染的海域,偏酸或偏碱的环境会导致某种化学反应速率加快从而导致沉船腐蚀加快;海水中大量氯离子的存在是使铁质文物腐蚀得以循环发生的重要外因,研究表明海水中打捞铁器的氯离子含量是室外保存的5倍左右[21];海底污损生物的种群和丰度受营养盐影响,另外沉船中营养盐的存在会使硫酸盐还原菌代谢产生大量的还原性硫铁化合物,在水分和氧气的作用下引发一系列反应,使沉船修复保存工作面临极大困难。
4.3 沉积物调查
沉积物调查主要包括底质类型、粒度、有机碳、氧化还原电位、酸挥发性硫化物(AVS)。海洋底质类型一般包括砾石、砂、粗砂、细粉砂、粉砂质黏土、软泥和黏土质软泥以及生物沉积等,不同的底质类型对文物的腐蚀程度不同,如海水的涌动带动大量粉砂可以对瓷器釉质形成冲蚀,而黏土质软泥可以形成厌氧环境从而使硫酸盐还原菌加速腐蚀铁质文物[22]。沉积物的粒度可以影响文物的埋藏环境,从而影响化学和微生物因素对文物的腐蚀速率;适中粒度的沉积物可以侵入船体内部,给出水船体的修复工作带来极大困难;若沉船所在海域受到一定的污染,还要对沉积物的颜色、气味等进行记录,并对沉积物中有机碳的含量进行测定;缺氧海泥中会形成还原气氛,使瓷器表面彩料变色,通过氧化还原电位的测定可以反映文物埋藏的氧化还原环境;有研究表明,底质中硫酸盐还原菌的丰度与底质中AVS的含量有显著的正相关性[23],而AVS又导致沉船中的铁质文物酸化降解。
4.4 海洋生物调查
海洋生物调查主要包括微生物调查、浮游生物调查、底栖生物调查、污损生物调查等。在海底环境中,沉船为各种海底生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古船木材材质受埋藏环境的生物、物理和化学作用,发生不同程度侵蚀变化。在沉船考古中经常发现海星、海葵甚至鲍鱼、贝类等海洋生物活体以船体为生长环境,海柳、船蛆、螺、寄居蟹等甚至直接将船体文物作为营养源,在上面扎根生长,这些生物的存在对船体结构造成严重破坏并最终导致文物的残缺及损坏甚至肢解船体[17]。如,“华光礁一号”沉船出水前表面覆盖大片生长良好的珊瑚及大颗粒的钙质生物砂,下层由交织成片的柱状珊瑚骨骼构成[11],沉船出水后质地变软、机械强度较差,自然干后会萎缩断裂;由于遭受海水长期浸泡以及华光礁基体中的珊瑚、软体动物、钙质生物等生物腐蚀,大量精美的陶瓷器表面被贝壳及其他硬质凝结块包裹,使清理修复工作变得极为困难,同时凝结物的包裹也阻延陶瓷器内盐类的析出脱除,延长文物修复保护工作的时间。
5 结论
水下考古专业力量不足、技术手段缺位一直是制约我国水下考古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速度和规模的主要因素,面对庞大的水下文化遗产,我们需要在梳理历史文献、环境资料和历史舆图的基础上,划分“目标区域”为优先调查行动区域,确立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大型沉船遗址为抢先发掘对象,开展全国海洋文化遗产重点区域研究。通过实施区域性和大型海底沉船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结合陆地文献调查和经验的积累,建立具有针对性的区域重点水下考古发掘工作的思路,并探索出一系列海洋考古发掘操作规范、技术规程等相关文件,以重点区域海洋沉船考古研究工作为抓手,为我国水下考古学研究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区域视野和调查技术支撑,促进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
[1]三上次男.陶瓷之路[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2]吴春明,张威.海洋考古学:西方兴起与学术东渐[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39-45.
[3]杜亮.被英国人哈彻“逼”出来的中国水下考古[J].东方收藏,2012(6):9-11.
[4]孙键.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的发现[J].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08(4):114-118.
[5]张荣大.青岛明代沉船遗址确定[N].中国海洋报,2002-10-8.
[6]林国聪,孟原召,王光远.浙江宁波渔山小白礁一号沉船遗址调查与试掘[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11):54-68.
[7]吴春明.定海湾沉船考古的新收获与宋元明福州港的对日贸易[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1):37-41.
[8]羊泽林.三千海底藏瑰宝研究保护重堪舆:与全国同步的福建水下考古[J].东方收藏,2012(6):14-16.
[9]刘曙光.2010年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与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73-78.
[10]张澜.“南海一号”的时空之旅:访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魏峻、水下考古队队长张威[J].中国科技奖励,2007(12):22-26.
[11]包春磊.“华光礁Ⅰ号”南宋沉船的发现与保护[J].大众考古,2014(1):35-41.
[12]周慧敏.中国南宋远海古沉船探秘[N].世界日报,2007-05-23(12).
[13]赵夏.文化遗产保护的区域视角[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8(1):14-19.
[14]张慧行.水下考古驶向海洋[J].百姓,2007(6):32-34.
[16]中国致公党福州市委员会课题组.福建沿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存在问题及其对策[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2):71-75.
[15]丁见祥,范伊然.关于水下考古学的几个问题[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3(2):1-4.
[17]宋薇.海洋环境对沉船遗址保存状况的影响[J].北方经贸,2012(8):187-188.
[18]I.D.麦克劳德,铁付德,陈卫.沉船内有色金属文物之腐蚀研究[J].中原文物,1999(1):106-115.
[19]杨恒,田兴玲,李秀辉,等.广东“南澳Ⅰ号”明代沉船出水铜器表面凝结物分析与去除[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2(2): 81-86.
[20]ALTERIO S,BARBARO S,CAMPIONE F C,et al.Microclimate management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2010,5(1):101-121.
[21]成小林,陈淑英,潘路,等.不同保存环境下铁质文物中氯含量的分析[J].中国历史文物,2010(5):25-31.
[22]马燕如.我国水下考古发掘陶瓷器的脱盐保护初探[J].博物馆研究,2007(1):85-89.
[23]杜虹,黄显兵,黄洪辉,等.深澳湾底质沉积物中酸可挥发性硫化物(AVS)和硫酸盐还原菌(SRB)的时空分布[J].海洋湖沼通报,2011(1):85-93.
The Importance of the Area Division and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in Wreck Archeology
ZHAO Zike,CHEN Chunliang,ZHANG Jibiao
(Monitoring Center for Marin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s of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Zhanjiang 524088,China)
Shipwreck archeology is an extremely complicated systematic work.Harsh conditions of the undersea environment,difficult salvage operation,lack of ocean humanities information and other factor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protection of China's rich coastal undersea heritage.Not only the wreck itself and the objects contained in it,but also systematic wreck area division with land archeology and oceanography in the important wreck area should be researched.In addition,detailed investigation of the undersea environment and corroded condition about the wreck itself and the objects contained could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restoration and protection of undersea heritage.
Wreck archaeology,Wreck area division,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P7;K87
A
1005-9857(2017)02-0065-05
2016-09-20;
2016-12-18
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201305038-6);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2013B021600015).
赵子科,硕士,研究方向为海洋化学,电子信箱:932377192@qq.com
陈春亮,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渔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电子信箱:1382258666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