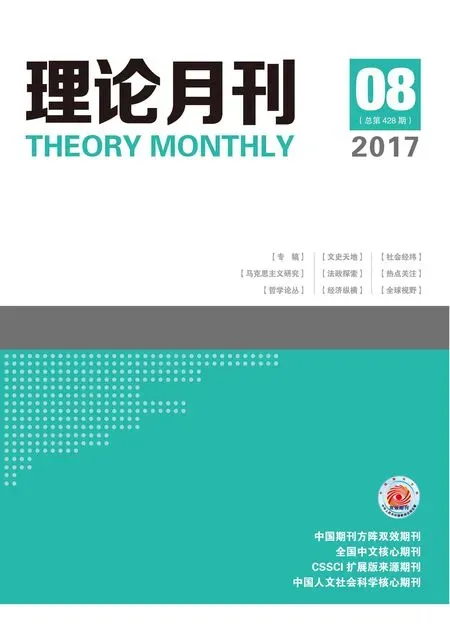“两田制”的征地补偿分配
□李平菊,寇浩宁,王茂福
(1.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2.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河北保定 071000;3.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北京 100083)
“两田制”的征地补偿分配
□李平菊1,2,寇浩宁3,王茂福1
(1.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2.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河北保定 071000;3.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北京 100083)
冀东北镇农村“两田制”的独特地权制度安排对征地补偿款分配产生的影响机制在于,与地权制度相联系的三类不同的土地(征地补偿)收益权——源于农地集体所有制的集体收益权、源于家庭承包经营的家庭承包农户收益权和源于其他方式(专业化、经营性承包)承包经营的非家庭承包农户收益权的分化。三权的分化造成了冀东北镇农村的地权制度安排对土地补偿款分配产生了直接影响,使村集体、家庭承包户以及非家庭承包户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补偿款分配差距。
两田制;征地补偿;分配逻辑;地权制度;土地收益权
1 研究问题的提出
在对农村土地的征收过程中,征地补偿款应该分配或补偿给谁,或者说谁有资格获得补偿款,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农地是农民赖以为生的基本生产资料,国家如果征收必须对失地农民给予补偿,这是失地农民的朴素要求,也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失地农民就是征地补偿的唯一对象?实际上,在我国的征地补偿政策规定和各地农村的实践操作中,这一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其它法律、法规、条例也依例用简称)第47条对征收农用土地的补偿费用列出了具体项目,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而对于这些项目的分配或补偿对象,则在随后出台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给出了原则性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也就是说,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是明确补偿给失地农民个人的,而土地补偿费则需要补给村集体,由集体共同使用或再行分配。由此,在法律意义上,农村征地补偿款的分配形成了如下原则或格局:土地补偿费给村集体(由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代表),部分支付给失地农户个人,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则直接补偿给失地农户个人,安置补助费根据失地农户意愿由自己支配或者再次均分土地后安置补助费归村集体(村或小组)。
冀东北镇农村普遍存在着一种有别于全国大多数农村的独特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两田制”,其基本做法是:将全部耕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为“口粮田”,在村民中按人口平均分配,另一部分称为“承包地”,是由村集体(一般是村委会)集中起来面向村民发包,村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来承包面积不等的土地,并向村集体缴纳相应的承包费。与全国大部分农村的“一田制”或“均分制”不同,这种“两田制”特别是“承包地”制度的设立,显然强化了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赋予村集体以更明确的、并得到农户普遍认可的地权主体地位。联系到当地的大规模征地开发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征地补偿款分配争议和纠纷,本研究希望关注的问题就是,“两田制”这一独特地权制度安排及与之关联的地权流转对征地补偿款分配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
本研究有待解答的核心问题是:村庄层面征地补偿款分配逻辑的形成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实践安排是何种关系,换言之,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实践安排对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或使用产生了何种影响,这种影响的内在机理是怎样的。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思路
很多学者提出,农村土地产权中所涵盖的各种权利的归属并非一致,而是模糊性和复合性的[1]。其中,所有权和使用权被分离开来,分别归属村集体和农民,而收益权和处置权的归属则比较模糊。这种产权的模糊性导致了各方权利归属者之间的纠纷和冲突。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众多社会学研究者们主要从中国乡村生活的实践逻辑的角度对土地集体产权的界定及其收益分配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申静、王汉生指出,农村的集体产权并非“模糊产权”,“实际上他们基于对某种原则的共识而形成的权利分配格局总是异常清晰的”[2]。折晓叶、陈婴婴认为,集体产权其实是社区内隐性的、非正式的“社会性合约”,这类合约主要不是依据法律来达成,而是各方当事人依据广泛认同的公平原则,在互动中自发建构出来的[3]。申静、王汉生指出,农村土地产权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建构过程,村民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灵活地运用多种原则,这些原则最首要的是“土地共有、收益均分”的“集体成员权”原则,基于市场交易的风险原则、承包(投标)原则和入股(分配)原则,以及内生于乡土社会文化的人情原则和强力(暴力)原则[4]。
这些研究表明,通过正式的法律或国家政策界定的土地产权固然重要,但在农村,很多时候法律或政策并不会成为界定收益权的主要或唯一依据,甚至可能不被村民接受而成为依据,农民们往往更多采取的是源自民间传统或习俗的地方性产权规则(或者可以称为社会规范和公正、公平观念)。
张静和曹正汉的研究还发现,在产权(当然包括收益权)的界定过程中,参与各方会利用各自的“政治力量”(或行动能力、或权力资源)来展开博弈,进行竞争、对抗,以取得对自己更为有利的产权安排结果[5]。“这并不意味着具有政治力量的组织和个人,可以在竞争中无视社会规范和社会公正观念的存在;相反,当各种政治力量都在竞争产权时,社会规范和公正观念将是一个潜在的“聚焦点”(focal point)引导着各方达成博弈均衡”[6]。
笔者认为,在中国农村当前所实行的“农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使用”的基本地权制度安排下,实际上形成了三种类型的土地收益权:一是源于土地集体所有权的集体收益权;二是源于农户承包经营权的个体收益权,该收益权又因为农户承包经营形式的不同而可以再分为两种亚类,一类是源于家庭承包方式的家庭承包收益权,另一类是源于非家庭承包方式(《土地承包法》称为“其他方式承包”,有学者称之为经营性承包,笔者这里统称为非家庭承包方式)的经营性承包收益权。
3 两类土地收益权的比较和对应
3.1 两类土地收益权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3.1.1 集体收益权是农地集体所有制的自然产物,是集体所有权的实现或表现形式,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出让或征收,意味着整个集体组织共同占有的土地总量的减少,每个集体成员可以占有或被分配使用的土地份额减少了,因此整个集体组织,包括每个集体成员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或者说索取相应的收益。
3.1.2 后两类收益权的相同点:都是因为农户承包经营所派生的产物,在现有的《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赋予农户以法定的、稳定的承包经营权,将承包经营权予以“物权化”的情况下,再考虑到农户在承包经营过程中所付出的投资和劳动可能带来土地的部分增值,因此当农户所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征收、出让时,出于对物权损失的弥补,他理应得到一定的补偿,或者说当他所承包经营的土地产生了巨额的增值收益时,他理应分享部分收益。这种收益显然不同于他作为一般集体成员而得到的平均的所有权收益,它是在所有权收益之外的收益,因为它只能以从事承包经营的农户个体为对象,所以也可以称为个体(性)收益权。
3.1.3 后两类收益权的不同点:一是承包方不同。家庭承包的承包方只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而其他方式承包的承包方,既可以是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也可以是经过本集体经济组织大部分成员同意的外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二是承包的对象不同。家庭承包的对象主要是耕地、林地和草地。其他方式承包的对象,主要是不适宜实行家庭承包的土地,包括“四荒”地以及果园、蚕场、养殖水面及其他零星土地。三是承包土地的原则不同。家庭承包的基本原则是公平,本集体组织成员人人有份。其他方式的承包不是人人有份的平均承包,承包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四是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方式不同。家庭承包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遵守法律的具体规定。其他方式的承包,双方当事人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通过平等协商,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五是权利的保护方式不同。对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按照物权方式予以保护。对其他方式的承包,则按照债权方式予以保护[7]。
明确了家庭承包和非家庭承包方式的区别,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源于家庭承包方式的家庭承包收益权和源于非家庭承包方式的经营性承包收益权的不同了。前者是一种保障农户基本生存权的、法定的、物权性的、带有社会保障和福利功能的、追求平等公平的农户个体收益权;后者是一种发展性的、非法定义务性的、债权性的、带有经营性和效率功能的农户个体收益权。
3.2 具体到征地补偿政策上,三种收益权分别对应了不同的征地补偿费项目
集体收益权对应的是集体所能获得的土地补偿费,根据河北省的有关规定,即“口粮田”的20%的土地补偿费和“承包地”的全部土地补偿费。
家庭承包收益权对应的是从事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户所能获得的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以及“口粮田”的80%的土地补偿费。
非家庭承包收益权对应的是从事非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户所能获得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当然,实际中二者也存在重叠之处,一个农户可能同时从事家庭承包经营和非家庭承包经营,既有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也有非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因此就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收益权。
由此,笔者认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正是通过集体收益权、家庭承包收益权和非家庭承包收益权这三种土地收益权而与征地补偿费的分配联系了起来,这三种土地收益权因此构成了地权制度与征地补偿费分配的“中间变量”,特定村庄社会的地权制度或结构通过决定、影响或改变这三种土地收益权的比例或结构进而决定、影响或改变该村庄社会的征地补偿费分配方式和分配结果。
4 集体收益权与集体所获征地补偿款
源于土地集体所有权的集体收益权,显然会倾向于要求对征地补偿款的分配尽可能多地采取“集体均分”原则。也就是说,在征地过程中,因为被征收的土地的所有权为集体,失去承包土地农户的后续安置也主要靠集体,所以各项征地补偿款(除明确为个人所有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外)应优先且尽可能多地补偿给集体,然后集体统一安排使用,可以采取在集体成员中平均分配的方式,或者优先分配给集体中有成员权但却无地、少地的农户和新增人口。
相比于要求集体均分的集体收益权,源于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农户个体收益权,显然倾向于对征地补偿款的分配采取“征谁地,补谁钱”原则。即在征地过程中,征地涉及的是那位农户的承包土地(包括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和非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那么就优先和尽可能多地将各种征地补偿费项目补偿该农户,而不是补偿给集体后大家均分。
这两种收益权显然是存在矛盾的。强调集体收益权和“集体均分”原则,会减少对直接被征地的少数农户的补偿收益,而强调农户个体收益权和“征谁地,补谁钱”原则,也会伤害集体成员整体的利益,特别是减少未被征地农户的补偿收益。村庄内部征地补偿款的分配矛盾和争议,往往根源于此。
调查发现,北镇农村的征地补偿款分配方式,一方面在大的原则上遵循了上述国家政策安排,但另一方面又因为与“两田制”的土地制度安排相关联而形成了带有地方特色的分配方式。
如前所述,理论上或在政策本原意义上,征地补偿款中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部分是对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村集体全部成员的土地所有权损失补偿,因此理应归全体村民共同所有,再经民主讨论和协商后予以使用或分配。但是,村集体获得(全部或部分)补偿款的前提是能够通过调整现有土地给予失地农户以不低于征地后村民平均承包土地面积的新耕地,也就是说,村集体需要先在村民内部重新分配调整“承包地”后,才可以以集体名义共同使用或分配征地补偿款。然而,由于国家在农村土地调整方面已经确立了“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的方针,即认可农户现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或使用权的长期化、稳定化,甚至趋于“实质私有化”,村集体对土地的重新调整分配不被鼓励,再加上在现有土地承包分配格局中受益农户(持有土地较多的农户)的强烈反对,所以重新在全村范围内调整承包土地几乎已不可能。也因此,在实践中,凡是不能重新调整土地的村庄,村集体就丧失了获取全部或大部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依据,所以,这些地方的基层政府在落实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补偿对象时,就采取了“征谁地、补谁钱”的原则,即除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直接补偿给失地农户个人外,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也全部或大部分补偿给失地农户个人,不再补偿给村集体供共同使用或分配。因此,在北镇所属的河北省,省政府在文件中明确规定“土地补偿费20%归集体经济组织,80%归被征地的土地使用权人或者按照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土地的农户”[8]。这显然是认可了“不调地、征谁地补谁钱”的补偿原则,将征地补偿费的大头直接拨付给失地农户个人,只留少部分划归村集体。
然而,这一力图减少集体获得补偿款的政策在遭遇“两田制”这一特殊地权制度安排时却发生了变异。在北镇农村,普遍实行的“两田制”尤其是强化集体所有权的“承包地”的设立,使村集体得以依据上述河北省政府文件中“被征土地没有土地使用权人和集体经济组织未发包以及实行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土地补偿费全部归集体经济组织,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分配或者使用”[9]的规定,而合理合法地获取被征收土地中属于“承包地”的全部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再加上村集体还可以从“口粮田”部分获取20%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因此,当地农村集体往往能获得大规模的高达千万巨额的征地补偿款。
5 个人收益权与农户所获征地补偿款
如前所述,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方式的不同,农户的个体收益权又分化出两种亚类型:源于土地家庭承包方式的普通农户承包收益权,以及源于土地非家庭承包方式的专业大户的承包收益权。
在农村土地制度“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的基本原则下,农户对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方式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家庭承包一种方式,而是广泛存在着家庭承包之外的其他承包方式。而近年来,在国家鼓励农村土地流转、适度集中、发展规模经营中所兴起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承包经营方式显然也属于不同于传统按人口均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方式。可以认为,以户为单位、均分土地的家庭承包方式注重的是土地对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生存功能和保障功能,各农户之间在土地使用上的平等性或公平性是其首要追求目标。而上述其他承包经营方式则偏重于土地的发展性功能和经营性功能,追求经济收入和效率是其首要目标。
在北镇农村所实施的“两田制”中,按人头均分的“口粮田”正是属于家庭承包经营的方式,而由村集体集中起来采取招标方式发包的“承包地”则显然属于上述其他承包经营方式之列。由于“口粮田”面积有限,不能满足普通农户的生活需要和经营性需求,因此大部分集体组织成员都会或多或少地承包少量的“承包地”,而少数集体组织内部或外部的种植大户、养殖大户等专业性农业生产经营者则会承包较大面积的“承包地”,成为在土地承包面积上远远高于一般家庭承包农户的承包大户。由此,在北镇农村就大致形成了两种类型的承包经营农户:一类是除拥有人均的“口粮田”外还承包少量“承包地”的大多数普通农户,另一类是除拥有“口粮田”外还承包大量“承包地”的少数承包大户。前者仍然属于典型的家庭承包经营方式,后者则明显属于专业化、商业化承包经营方式。这两种不同的承包经营方式,或者说这两类不同的农户之间所获得的征地补偿款自然也存在很大的不同。
5.1 家庭承包方式农户的征地补偿款
原则上,从事家庭承包经营方式的农户所能获得的征地补偿款包括:以“口粮田”为计算面积的80%的土地补偿费,(人均的)安置补助费,“口粮田”和“承包地”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人均一亩“口粮田”为单位来计算,征收该户多少“口粮田”则补助相应的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标准统一,只是因为各户“口粮田”面积和被征地面积大小不一,所以每户所获得的土地补偿费会存在差别。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如果是一般农田、只种植大田作物的(小麦、玉米)话,其补偿标准也是统一的,如果是种植经济作物,或从事畜禽养殖的农田,农田上建有一定的生产设施的话,则补偿标准会较高,所获补偿款总额也会大幅升高。而如果一个普通农户被征收一亩种植大田作物的“承包地”的话(地上附着物暂时不计),因为土地补偿费全部补给村集体,安置补助费没有,所以其所能获得补偿款只是青苗补偿费每亩3500元。
5.2 非家庭承包方式农户(承包大户)的征地补偿款
根据政策规定,从事非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大户如果是本村集体组织成员,那么他所能获得的征地补偿款自然也包括人均的安置补助费,自己“口粮田”的80%土地补偿费以及相应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除此之外,因为他承包有大面积的“承包地”,虽然不能获得被征收“承包地”的土地补偿费,但却可以获得“承包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因为他们的“承包地”大多从事专业化种植或养殖,种植或养殖有相当大数量的经济作物或牲畜、家禽,且一般建有相应的生产生活设施,所以他们所获得的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会远远高于种植大田作物的一般农户。
6 结论
首先,“两田制”的存在,以及后来农民自发和村集体有意识组织的土地流转,造成了当地农村农户之间土地承包经营面积的较大差距。有的农户只有每人一亩的“口粮田”,而有的农户成为承包大户,拥有“承包地”高达百亩以上,而这种土地面积的差距一旦面临大规模征地开发和获取补偿款,就转化为被征地农户之间极大的补偿款收入差距,这源于他们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的巨大的差异。
其次,“两田制”的存在,特别是所有权明显归属于村集体的“承包地”制度这一产权安排,赋予了村集体明确的土地的集体收益权(即获取征地补偿款的权利),使得当地农村在征地补偿过程中村集体合法合理地获取了大量补偿款(集体留存或留用),使集体土地产权得以“变现”,不仅大大增加了集体所拥有的可支配资金,而且使集体在征地补偿分配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也更进一步说明了当各种政治力量都在竞争产权时,社会规范(尤其是现有的制度规定)是一个潜在的“聚焦点”引导着各方达成博弈均衡。
[1]张曙光,程栋.复杂产权论和有效产权论:中国地权变迁的一个分析框架[J].经济学季(刊),2012(4):1219-1238.
[2][4]申静,王汉生.集体产权在中国乡村生活中的实践逻辑:社会学视角下的产权建构过程[J].社会学研究,2005(1):113-148,113-148.
[3]折晓叶,陈婴婴.产权怎样界定:一份集体产权私化的社会文本[J].社会学研究,2005(4):1-43,243.
[5]张静.土地使用规则不确定:一个法律社会学的解释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03(1):113-124.
[6]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六集[C].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712-807.
[7]丁关良,梁敏.农村土地两大类承包之异同研究[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20-25.
[8][9]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征地区片价的通知[Z].冀政[2008]132号.
[10]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北京:三联书店,1994:126-134.
[11]D·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北京:三联书店,1994:71-76
[12]陈健.中国土地使用权制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87-98.
[13]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95-201.
[14]中国法制出版社.农村土地承包纠纷[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23-44.
[15]胡吕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法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34-137.
[16]韩志才.土地承包经营权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65-71.
[17]齐晓瑾,蔡澍,傅春晖.从征地过程看村干部的行动逻辑:以华东、华中三个村庄的征地事件为例[J].社会.2006,26(2):327-329.
[18]丘昌泰.公共政策:基础篇[M].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0:246-249.
责任编辑 李利克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8.026
F321
A
1004-0544(2017)08-0138-0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FRF-BR-15-011A)。
李平菊(1978-),女,河南郑州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寇浩宁(1980-),男,河北宁晋人,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北京大学博士生;王茂福(1964-),男,湖北黄陂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